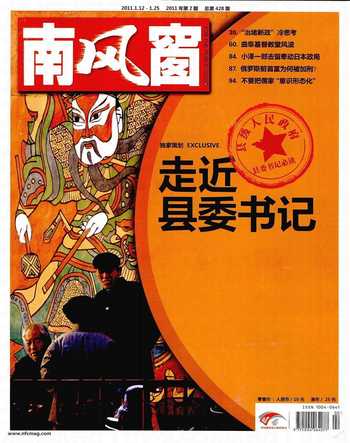“我们应该顺应历史潮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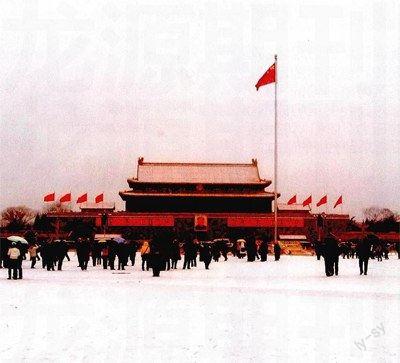
初冬的一天,记者来到位于武汉东湖之畔的珞珈山麓,走进刘绪贻教授的书房。
老人从书桌前站起来,步履稳健地走过来,热情地招呼记者坐下。红润的面庞,饱满的记忆,清晰的表达,很难让人相信,这位老人已经98岁高龄。在老人娓娓的谈话中,百年的历史沧桑都化为从容淡定。
辛亥革命爆发的第三年,刘绪贻出生在湖北黄陂县一个贫寒的知识分子家庭。这位自强不息的农村子弟一直奋斗,走出了乡村,走出了武汉,最终走进美丽的水木清华,如愿以偿地成为清华大学的学生。
抗战爆发后的第二年,刘绪贻和几位同学结伴南下,跋涉千山万水来到位于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继续学业。作为社会学系的学子,陈达、潘光旦、吴文藻、费孝通等社会学大师都是他的授业老师。在学术空气自由民主的西南联大校园里,他也有幸成为雷海宗、吴宓、冯友兰、叶公超等大师的及门弟子。
而今,人才辈出的西南联大已经成为中国大学史上的一段神话,当年的青葱学子也日渐凋零。在最近出版的回忆录《箫声剑影》里,刘绪贻所描述的西南联大不仅令读者神往,而且成为今日学子津津乐道的话题。
在工作了4年以后,刘绪贻毅然辞去政府工作,在抗战结束的前一年赴美留学,终获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硕士学位。当他回国之际,内战已经开始,知识界为中国的前途担忧。回国前思想已经向左转的刘绪贻开始关注政治,这位武汉大学的副教授在报刊上发表了许多时政文章,揭露国民党政府的专制和腐败,要求实行“人民自己做主的真正民主”。
建国后,思想进步的刘绪贻被任命为武汉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兼代秘书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从事了一段实际工作后,他于1964年重返武汉大学研究美国史,从此再也没有离开校园。
近半个世纪过去了,著述等身的刘绪贻已经成为著名的社会学家、历史学家。2002年,在完成了六卷本《美国通史》的主编和撰写工作后,年已九旬的刘绪贻再次拿起笔来,像60多年前一样,写下一篇篇时论文章,针砭时弊,抨击儒学的糟粕,鞭挞腐败。
刘绪贻曾坦言:“我对肃清祖国封建余毒,发扬科学与民主。以至人类之命运,均甚关切,自觉使命仍然不轻。”诚如他的好友李慎之所期盼的那样,90岁后的刘绪贻“以老迈之身,无畏之精神,大声疾呼,作悲壮之努力,发聋振聩。”
“北有周有光,南有刘绪贻。”就像105岁的周有光老人一样,年近百岁高龄的刘绪贻老人笔耕不辍,讲真话,摒伪学,讲常识,弃虚妄,绝不随风转舵,虚与委蛇。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是他们共同的终极关怀。
今日中国为什么出不了大师?
马国川:您在《口述自传》里讲到,您先后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大读书,接受的是博雅教育。什么是博雅教育呢?
刘绪贻:博雅教育就是通才教育,英文是Liberal education。它和苏联搞的那种教育体制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说。一个人的眼光要阔达,胸襟要开阔,有宽容心,兼容并蓄。
1952年进行院系大调整,完全是学苏联,照搬苏联的教育体制。当时许多学者都反对,潘光旦先生还公开提出“应该缓行”,可是没有用。
马国川:和那种苏联式的专才教育比起来。博雅教育还是比较科学的教育方式。
刘绪贻:一个人的知识如果太专的话,往往瞎子摸象,对于社会总是从他的专业角度看问题,很容易钻到牛角尖里面去,不能够看到整个的社会形势。因为胸襟不开阔,视野比较狭窄,也没有关怀全人类的浩然之气。
马国川:在您看来,西南联大的办学精神和经验是什么呢?
刘绪贻:10个字,科学、民主、爱国、艰苦、团结。主要还是民主、科学。
马国川:没有独立思想,就没有人才。国家总理都几次感慨地发问,中国为什么出不了大师?
刘绪贻:原因很简单,因为管得太死了,不让自主,所以就出不了人才呀。所民主、自由、法治。
马国川:后来为什么思想开始左倾了呢?
刘绪贻:原来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不喜欢政治,一直喜欢搞学问。但是后来国民党贪污腐化,让人失望。当时我认为,国民党不能够挽救中国的危亡,如果只依靠国民党的话,中国也很难现代化。后来我在美国认识了一个美国人,他可能是个以大学必须有自主权,没有自主权很难培养真正的人才。
我是一个“两头真”
马国川:您在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学习期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刘绪贻:我是1913年出生的,6年以后就发生了“五四运动”。在中学我接受的主要是“五四”的启蒙教育。直到大学期间,我都受到“五四”启蒙教育的影响。当然,我所说的“五四”主要是新文化运动。在大学里,包括后来到美国大学学习,我深深地受了自由主义的影响,信仰的是科学、美国共产党员,我受到他的很多影响。再加上我觉得反正国民党不行,所以慢慢就相信了共产党。
人民群众只要接触了新的东西,就会独立思考。现在我常常想,为什么我在解放前后那么盲目信从呢?因为当时我看的东西,都是人家愿意让看到的,都是他们做得比较成功的,比较好的,所以就相信了。现在各种观点不同的书籍都出来了,历史真相逐渐了解了,怎么还能够盲目信从呢?
现在不是有一种“两头真”的说法吗?我现在似乎也可以称为一个“两头真”。1979年起,我的主要工作是实事求是地研究美国史,2002年起,也就是90岁以后,我的主要工作就是写文章呼吁民主,呼吁法治,反对传统文化,主要是反对儒学里的腐朽和糟粕。
上世纪40年代,我在芝加哥大学留学期间的硕士论文,就是彻底揭露儒家学说的保守性和反动性,认为儒学统治是阻碍中国社会工业化、现代化的极其重要的原因。
马国川:您认为儒学的保守性、反动性是阻碍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重要原因,但是新儒学的代表人物,比如说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等人却认为,儒学可以进化,与现代社会相适应。
刘绪贻:你說的这些新儒学的领袖人物,我有一篇文章就是批判他们的。我说,儒学里本来是没有产生科学、民主的因素的。新儒学也承认儒学里找不出来产生民主和科学的因素,可是牟宗三认为,从道德的观点来说它应该有,所以就必须有。这是什么话?毫无道理。
民本不是民主
马国川:对于转型中的中国来说,有两条道路可以选择,一条路就是现代的科学民主法治的道路,另一条和它相反,那就是中国传统的专制的、人治的道路。如果有些人拒绝前一条道路,当然就会选择后一条道路。
刘绪贻:中国现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还是要反封建反专制。其实,早就有好多人提这个问题。中国的问题是反资产阶级太早,反封建不彻底,太不彻底。
到现在为止,儒家思想的影响还很大。比如,有的报纸上还提“父母官”,共产党的官应该是人民的儿子,怎么叫做“父母官”?父母官就是孔夫子的思想。报纸上
有时候还说“以民为本”,这也是儒家思想。民本不是民主,中国只有民本的传统,没有民主传统。
马国川:民本就是所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不是民主思想。
刘绪贻:以民为本,就是说要给人民一点小恩小惠,来换取统治者的绝对统治。而民主是让人民自己做主,完全是两回事,不能够替代。
马国川:看来,区分开民主和民本两个截然不同的命_题是非常重要的。
刘绪贻:李慎之原来以为是任仲夷最先提出这个问题,后来他才发现,是我最早提出来的。1948年,我在上海的杂志《时与文》上发表文章《只有人民自己当家作主才是真正的民主》,就指出了民主与民本的区别,呼吁人民群众不要上当。
马国川:当时为什么要写这样一篇文章呢?
刘绪贻:这篇文章是争论出来的。那时候我在武汉大学教书,住在教授的單身宿舍,每天晚上吃饭的时候,我经常和其他单身教授争论一些现实问题。当时,蒋介石搞小恩小惠,吹嘘自己是在搞民主。我有两个同事,都是老资格的教授,他们两个认为蒋介石是在搞民主,我就和他们争论。后来我就写了这篇文章,揭露蒋介石搞的是民本,不是民主。
马国川:当时您写这样的文章,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吧?
刘绪贻:没有直接的影响。
应该自觉地、自主地来搞民主
马国川:现在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发展最重要,如果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民主会随之而来。
刘绪贻:从前美国的老布什就是这个观点,他认为,只要中国积极不断地发展经济,将来总有一天政治会走上民主道路。能不能够是一回事,即使能够,也不知道等到哪一天啊。所以,还是应该自觉地、自主地来摘民主,而不是被动地让民主自然地形成。中国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其他领域的改革和建设步履蹒跚,亟待努力啊。为什么我98岁了,还要写文章呼吁民主法治?就是希望还是积极地推进民主和法治,希望能快一点。
马国川:但是,在目前的状态下,改革难以推进,有识之士都感到忧心忡忡。
刘绪贻:中国改革到了深水区,因为既得利益抵制社会改革。60多年以前我就讲过这个问题,当年我的硕士论文的副题是“既得利益抵制社会变革的典型事例”。今天中国改革同样面临着这样的问题,既得利益已经捞足了,要他们主动改革很难啊。
马国川:作为一个社会学家。您认为中国改革的突破口在哪里?
刘绪贻:美国建立与维护法治体制的做法,值得中国学习借鉴。你看美国的宪法,它很简单,很朴素。在美国,经常有人把案件提到宪法这个高度来起诉。
走向一个自由、民主、法治的和谐社会
马国川:现在,民族主义思潮也有抬头,还有民粹主义,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刘绪贻:我觉得民族主义讲一讲也可以,但是不能过分,不能搞过激的民族主义。
我认为,从社会学的观点看,人类社会是在不断扩大的。随着科学发展,随着技术、交通、交流不断地向前发展,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不断地提高,社会在不断地扩大,起初最基本的人类组织是家庭,家庭慢慢地变成氏族部落,后来变成部落联盟,然后变成国家,,现在又慢慢地有联合国。当然现在联合国还不起法律的作用,只能够起道德的作用。但是,像欧洲联盟现在把主权国家的一些权力加以限制,慢慢实现整个欧洲的一体化。我觉得,这个趋势还是会继续发展。
马国川:现在有一本书就叫《中国统治世界》。这次世界金融危机以后,有些人说,以后美国不行了,资本主义不行了。还是中国这一套行。
刘绪贻:中国怎么可能统治世界?这是瞎吹。动辄说,资本主义不行了,就我们自己行,不足为信。这种话说了多少次?
马国川:您注意到了吗,近些年有人大讲“中国模式”。
刘绪贻:中国模式还有待不断完善。通过不断的互相交流、互相理解,我们会不断走向一个自由、民主、法治的和谐社会。我们应该顺应历史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