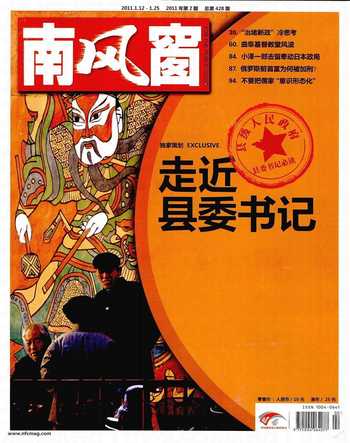辛亥革命的历史任务
丁学良
对于历史,保持一定的时间跨度和距离去观察,是很有必要的。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时间跨度够大了,我不是研究历史的,但恰好这半年读了一些亚洲史,距离也合适了。是时候可以谈一谈。
其实,辛亥革命最初要解决的是“族权”问题,即满汉之间的冲突。但在这个过程中,滿汉之中的一些有识之士,也正在对西方强权的侵略做出反思和积极的回应。他们很快发现,要解决“族树”没法绕过“国权”和“民权”。
所谓“国权”问题,实际上就是“驱逐列强、统一中华”,这在当时是最为紧迫的。近代中国一共经受了三次大的冲击。第一次和第二次冲击,来自第一波和第二波成功实现工业化的西方帝国的对外扩张,在这两次冲击中,不仅中国,亚洲其他国家也受到了侵略。对这两次冲击,后人有许多反思和评价,但与马克思以及他同时代知识分子做出的评价相比,大多有失偏颇。马克思认为,西方列强以枪炮来打击和攻击相对弱小、落后的国家,强迫它们签订不平等条约,进行不公平贸易,是不道德的。马克思的批评,超脱了民族主义,是站在国际主义的立场上做出的。但他同时指出,这些古老的帝国,如中国、印度等,之所以轻易地被来自万里之外的几艘炮舰打败,正是由于它们在历史进程中越来越落后、停滞和腐败。从历史发展的角度,马克思曾做出一个精辟的总结:西方帝国主义对东方,尤其是亚洲古老而落后的文明的冲击,是以野蛮的方式促发了历史的进步。
但这两次冲击对中国的撼动,远远比不上第三次——来自第三波成功实现工业化的日本的打击。当时,不仅中国思想最开放、最新锐的统治精英,还有帮助和参与中国建设现代陆海军的西方国家,都认为日本打不过中国。带着这样的自信,却在甲午中日战争中遭遇惨败,这对中国的冲击和打击是巨大的。但国权问题还没来得及思考清楚,却马上得出结论,认为日本之所以能够打败中国,是因为实现了君民共和制。要注意“君民共和”与“君主共和”是不同的,“君主共和”是君主治理,“君民共和”则跨过了这个阶段,实现了君民共同治理。
在这个认识基础上,清朝的统治者也主动进行了一些改革。但当时族权问题尚未解决,国权问题又没搞清楚,清朝统治者的改革不仅排斥汉族的官员,甚至连很多满族的官员都不相信,他们只相信皇室近亲。这样一来,事情就变得很糟糕。受到冲击后,本来应该扩大统治基础,但清朝反而越改越狭窄,最后把权力集中在几个皇室贵族手中c所以说,当时清朝的维新、改良和改革不仅是表面化的,而且是欺骗性的。到这个时候,民权问题也开始凸显。
族权、国权、民权三权纠结,辛亥革命要把它们一并解决,这使得辛亥革命从一开始就背上过重的负担。辛亥革命之后,成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Republic of China。当时先有英文名称,严格来说应该翻译成“中华共和国”,但革命者认为“共和国”不足以突出这种国体的先进性,因为中国是跨越了日本的“君民共和”,直接走向了民主的,最后决定翻译成“中华民国”。民主就是民权,以民权来解决国权和族权,这是“中华民国”架构设计的本意。
站在今天回看,一方面,要给辛亥革命的前辈们一个伟大的评价。“中华民国”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制国家,“共和制”这个概念直接来自古罗马文明的传统,包含着“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的理念,在100年前,有这样的认识,是很了不起的。无论从理念还是理想来看,辛亥革命的志士都达到了当时整个亚洲最高的认识水平。另一方面,必须说遗憾的是,中国并不具备把族权、国权、民权一并解决的客观和主观条件。辛亥革命的发动者,本来是想把满人驱逐回东北的,但马上遇到一个现实问题——东北是不是新成立的中华民国的一部分?所以后来确定,辛亥革命的目的不是要把满人赶走,而是要推翻满族的皇权,这样,族权的问题基本解决了。但到了国权和民权,就进行不下去了,现代经济和民间自主,这些建构现代民权的基础条件,当时的中国一项都不具备。所以说,100年前这个亚洲最先进的架构,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同时也是高不可攀的架构。
但不应忽略的是,辛亥革命后,无论政党还是个人,都在不同的情况下分享着100年前的这个理想主义。并用不同的方式,探寻和创造实现三权的道路和条件。这个历史性、跨世纪的动作,还有待不断完善。
——兼论《民权素》创刊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