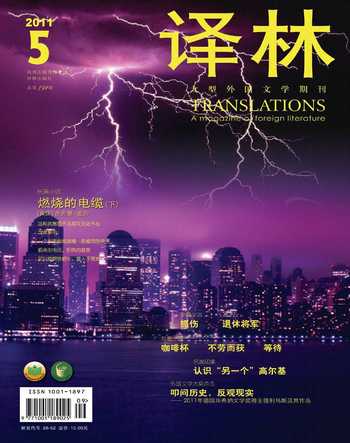《德黑兰的屋顶》:人类共有的情感体验
李美华 译
《德黑兰的屋顶》(Rooftops of Tehran)是伊朗裔美国作家马赫布•萨拉杰的处女作。小说自2009年问世以来,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和好评,并获得多项殊荣,如“美国书商协会杰出处女作选”、“2009年读书俱乐部25部最受欢迎小说”和“2009年湾区50部著名小说”等。
马赫布•萨拉杰出生于伊朗,十九岁时到美国求学,获爱荷华大学电影、播音方向硕士学位和指导设计和技术方向博士学位。萨拉杰走上创作道路有点偶然。他是五十几岁时因为失业才开始写作的。半自传体小说《德黑兰的屋顶》一炮而红。在访谈中,萨拉杰谈到了他创作的初衷就是要讲述一个关于友情、幽默、爱和希望的故事。他认为,这是任何时候任何地方的人都珍视的一种共同经历。小说主人公帕沙和扎莉感人至深的初恋、帕沙和阿梅德的友情、阿梅德和法伊美争取恋爱自由的反传统方式以及街坊邻居相互间的帮助和支持,这一切被萨拉杰置于波斯文化背景中,给小说带来了一股清新的气息。
问:你19岁来到美国,已经在这里生活了32年。是什么促使你在人生的这个阶段写出了你的第一部小说的?里面有多少东西是基于真实事件创作的?
答:谢谢你让大家知道我已经是个老人了!
问:老人?这怎么可能?我比你大几岁,可我还在生命的黄金阶段呢!
答:啊,可众所周知,编辑能够永远年轻。不管怎么说吧,回到你刚才的问题,我十岁的时候读了第一本小说,杰克•伦敦的《白牙》,从英语原著翻译成波斯语的,就是在我的小说所描写的那个屋顶上读的。从那时候开始,我就一直想写。可是,生活总是阻碍我写作。然后,几年前,我丢了工作。那可是发生在我身上最好的事了。我开始写作,从那时起就没停过。
至于小说,有些是基于真实事件,但不是全部。所以,我必须指出,《德黑兰的屋顶》不是传记,这点很重要。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必须指出,我把古莱索尔希写进小说后,把审判的日期以及他在法庭上自我辩护的话都做了修改。
问:你刚到美国时,还不怎么会说英语,但现在显然已经掌握了这门语言。你是怎么做到的?在一个陌生的国度,没有家人在身边支持,面对学外语这种可怕的挑战,你到底是怎么做的?
答:我希望能说自己已经掌握了英语。总是有更多的东西要学!学习一种新的语言,这是成千上万生活在异国他乡的人面临的一个挑战,况且学英语很难,是我做过的最难的事之一。我刚到美国的时候,吃了六个星期巨无霸、小薯条和小杯可乐,因为我只会点这些食物。我敢肯定麦当劳公司在那个季度的收入大大飙升!学任何外语的技巧都在于把自己融入到那个国家的文化中去,和说英语的当地人混在一起,多看电视,还有——还有一个不幸被很多人忽视的要素——尽可能多地阅读。我读的第一本非教科书的英语书是埃里克•弗罗姆的《爱的艺术》。对我来说,那该被翻译成“爱阅读的艺术”。从那时开始,我就很虔诚地阅读。我最喜欢的一些作家已经在《德黑兰的屋顶》里提到了:埃米尔•左拉、 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马克西姆•高尔基、杰克•伦敦、约翰•斯坦贝克、萧伯纳、诺姆•乔姆斯基,还有其他作家。
问:在小说中,你展现了20世纪70年代波斯人和美国之间既爱又恨的关系——还有一些很可笑的误解。美国是暴虐的国王背后的力量,因此也是他们憎恨的敌人,然而美国又是给他们自由和机遇的地方——这种矛盾能制造怎样的情感斗争啊!你刚到美国来的时候,最令你吃惊的是什么?你所碰到的美国人对伊朗有什么误解?
答:我不想给两个国家中的任何一个做概括,也不想得罪任何一方。所以,如果我接下来的话有冒犯之处,还请原谅。美国人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民族:善良、包容、诚实。他们怎么说就怎么做,并且是以公正、平衡的方式去做。这个国家的高等教育是一流的,无论从质量上说,还是从入学率的角度看,皆是如此。在这里,每个人都可以上大学。很多国家都无法接收这么多学生。顺便说一下,70年代来美国的多数伊朗人都是来受教育的。他们不会在某个早晨醒来时说:“我要去美国获得自由。”他们说:“我要去那里受教育。”这是很重要的区别。只是,他们在这里呆了一阵以后,便会完全欣赏我们所享受的自由。
刚来的时候,令我吃惊的是,尽管能获得很多信息,可只有一小部分美国人知道,或者说有兴趣知道,世界其他地方发生了什么事。很大程度上,今天也还是如此。比如,我碰到的很多人对伊朗几乎一无所知,对此我很震惊。我记得20世纪70年代自己上大学的时候,在一次课堂讨论上,我提到中央情报局1953年成功推翻了摩萨台——伊朗历史上唯一一位民主选举出来的首相,可一半的同学都指责我说谎,因为“美国政府不会做这样的坏事”。连老师都说我的事实是错的。
有些美国人盲信他们的政府。我的意思是说,得想一想。像美国这样制度化的民主国家不该支持、事实上应该反对世界上任何地方的非民主行为、运动和力量,至少理论上应该如此,不是吗?可实际并不总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有些美国人很难相信,甚至是不理解的原因。想想今天伊朗的形势,美国总统大选前的那个夏天,还有人在岩石底下寻找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他们真的无法看穿自己的政府在欺骗他们。
在这个问题上,伊朗人和美国人分处相对的两极。可能需要上天采取行动,才能让一些美国人相信他们的政府有些部门也很腐败;但同时,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你都无法劝说伊朗人相信他们的政府不腐败!很有趣,对不对?
至于目前美国人对伊朗的误解,我在媒体中看到很多不实的报道。因为伊朗政府与美国政府不和,所以我们倾向于把伊朗人刻画成邪恶的人。媒体宣传丑化伊朗人的形象和信息。同样,我们被鼓励去忘记一个事实:这些我们所谓的敌人,他们也有感情,也能够去爱,也有友情。我们把他们看得如此不同,以致无法想象我们与他们其实有很多共同之处。看到两个伟大的国家之间的隔膜如此之深,我真的感到很伤心。
问:美国人对波斯历史知道得很少。我对波斯人几个世纪以来经历的外来侵略者的长期占领和压迫特别感兴趣。历史是如何继续塑造波斯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呢?
答:伊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拥有很有趣、很动荡的历史。三次大规模入侵给我们的文化、心理、文学和艺术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伤痕。这些入侵者包括亚历山大大帝,他在伊朗被称为“受诅咒的亚历山大”,阿拉伯人,成吉思汗。在侵略中,几百万伊朗人失去了性命,遭受了无法想象的暴力侵袭。现代波斯人都没有忘记这些。除了异族侵略,我们的人民还饱受自己国家暴君残暴行为的折磨。每个国家的历史,以及它的人民对历史的回应,都帮助孕育了这个国家的文化。所以,由于我们的历史原因,我们倾向于对生活持严厉、宿命的态度。我们因悲观而遭罪。我们对权威人士持怀疑态度,总觉得自己成了牺牲品,坚定不移地相信存在看不见的力量暗中控制着一切事件的发展。我们看见了绳子却没看到木偶。同时,我们是个有自我修复能力的民族,在任何境况下都能生存下去,什么也无法摧毁波斯人热情洋溢的精神。这一点也很重要,值得一提。我们喜欢争论——不是讨论,而是争论政治。家庭对我们很重要。我们的友情名扬四海。伊朗是个慷慨的国家,人民善良,而且特别好客。即使是现在,很多到过伊朗的美国人都说,他们为在公共场所遇到的伊朗人的热情好客所折服。你会听到:的士司机没有收美国乘客的钱,吃了东西,餐馆老板却不要美国人付费,普通民众不厌其烦地帮助美国人。我知道有些读者会觉得难以置信,但这是事实。
问:你回过伊朗吗?你长大以后,它有什么变化?
答:我确实回去过。我父亲还在伊朗生活。我在德黑兰找不到路——发展太快了!人也不一样了。一踏上伊朗的土地,你就能感觉到空气中有种伤感意味。然而,令人大为惊奇的是,一旦回到日常生活中,你就会发现不屈不挠的波斯精神,那种“什么情况下我们都能活下去”的态度!
问:我认为伊朗是个岩石密布、荒凉贫瘠、炎热无比的沙漠国家。可当看到你发给我的一些德黑兰的照片,我惊奇地发现,那里绿化很好,有粗壮的大树,还下雪。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伊朗有多大,地理上有什么多样性?和贫困人口相比,中产阶级有多少人?
答:和通常认为的相反,伊朗是地球上最多山的国家之一。实际上,它是个很漂亮的国家,从国土面积来看,它是世界第十六大国,大约相当于美国的五分之一,各种各样的人口超过七千万,由诸如阿塞拜疆、俾路支、库尔德、鲁尔、亚述、亚美尼亚和其他很多民族组成。伊朗境内有两大山脉——扎格罗斯山脉和厄尔布尔士山脉。最高峰是座火山,谢天谢地,那是座死火山,叫德马峰,高5678米(或者说18628英尺)。这是很容易记住的数字,我在伊朗读中学的时候,地理小测验很爱考这道题目。伊朗东部有两座很大的盐沙漠,大部分地方没有人居住。各地区气候不一样。冬天很冷,西北部会下暴风雪。不管你在哪里,春天和秋天绝对是很不错的。有些地区的夏天又热又干,其他地区则很潮湿,特别是北部的里海边和靠近波斯湾的南部。至于富裕程度,联合国认为伊朗是半发达国家;国民生产总值排在世界第十五。所以,伊朗不是很多人认为的大荒漠。由于工作原因,我周游世界,而里海沿岸是我见过的最葱翠、最漂亮的地区之一。至于生活水平,根据我从互联网上看到的2007年的统计数字,大约18%的伊朗人生活在贫困线下(美国是12%)。构成劳动力的大约3000万人中,失业人口占15%—20%,看你相信谁的统计数字了。所以我认为,在伊朗,确实有中产阶级,但正在萎缩。
问:你已经回答了我关于伊朗的很多问题,我们还是回到《德黑兰的屋顶》来吧!我最早对小说感兴趣的原因之一是,帕夏和扎莉的爱情故事很浪漫。是你个人特别浪漫,还是出于波斯人的特性?
答:哪怕我暗示说自己身上有一滴浪漫的血液,我都会被朋友们嘲笑一辈子的!我妻子也会震惊不已。所以,我们得小心点!我想,读者会把自己和扎莉与帕夏联系在一起,是因为每个人都记得自己的初恋。扎莉和帕夏很年轻,这一开始就让他们陷入不可能相爱的境地,如果把社会习俗的约束和扎莉未婚夫的情况考虑进去,他们的爱就更是毫无希望的了。顺便一说,这是波斯文学中“浪漫”一词的定义。浪漫之美在于其不可避免的悲剧结局。值得你为之付出生命的东西,恰恰是你无法拥有的。对那些有兴趣了解更多关于这个话题的知识的人来说,迈克尔•希尔曼的《伊朗文化——波斯人的观点》(美国大学版,1991年)是很好的资料来源。
问:在小说的原始版本中,叙述者一直没有名字。你最初为什么这样安排,后来又为什么改变了主意,把他叫作帕夏?
答:哦,叙述者就是我。那些认识我的人马上就会认出他就是我。但我不希望他用我的名字。所以,我就让他无名无姓。我的逃避一直都很成功,直到你,我出色的编辑,让我相信,是时候把他和我分开了,让我们分道扬镳,过各自的生活。然后,我找不到名字给他用。最终我选择了帕夏•沙赫德。如果我没有取名为马赫布的话,帕夏就会是我的名字了。沙赫德是我父亲的笔名,也是我母亲少女时代的姓。我父亲是位苏非派诗人,在伊朗出了三本诗集。
问:在很多方面,小说的人物和事件都让我想起人类经历中共同的东西——乐于助人的朋友和家人必不可少的支持、帮助我们度过艰难时刻的幽默的力量,人们屈从的聪明和不那么聪明的方式,抵抗力,政治镇压,爱和被爱的欲望。然而,扎莉可怕的选择以及小说人物对伤痛的过度反应,两者都可能让西方读者感到很陌生。你能否将那些行为放在某个背景当中?这样可能有助于我们的理解。
答:可以。爱、恨、幽默、友情,这是所有国家所有人共有的特点。我们的文化影响了我们对各种情形做出反应的方式,这点你说对了。除了写作,我还教一门叫作“理解个人和文化差异”的课。波斯人,或者笼统地说,中东人,生活在专家们所称的“情感”文化当中。在这些文化中,人们自由地表达他们的情感,特别是在哀悼的时候。而美国人、英国人和德国人生活在“中立”文化中。在这些文化里,人们的情感不外露,被严格地控制着。比如说,在美国参加葬礼和在伊朗参加葬礼是很不一样的。中立文化的人在情感文化的人看来显得冷漠,没有感情。反过来,中立文化的人会认为情感文化的人情感太外露,表达太夸张。
至于扎莉的“可怕选择”,我最好不要多说,否则故事就泄露得太多了。除了一点,我得说明,她所做的在伊朗并不常见。确实有发生过,但很少。她精心选择这种极端行为是为了做出有力的表态。
问:你计划再写一部小说吗?能否透露讲的是什么呢?
答:我的第二本书已经写了一半。是讲一个男人有四个妻子,但他却认为自己一辈子都被剥夺了爱情!我还没想好题目。将来某一天,我也不敢确定是什么时候,我一定会写《德黑兰的屋顶》的姊妹篇。我只是需要些时间。
(本文为“厦门大学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资助”项目成果之一。)
(李美华:厦门大学外文学院,邮编:361005)TRANSLATIONS译林名家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