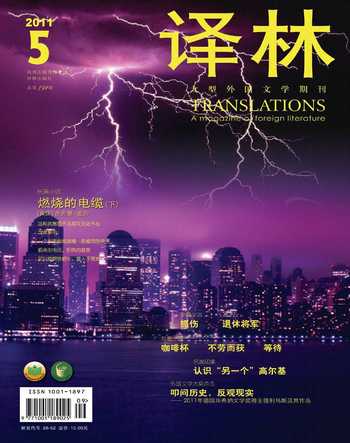阿尔勒散记
余中先
耳听为虚
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来到了多少年来一直魂牵梦绕的地方——阿尔勒(Arles)小城。
火车从巴黎的蒙帕纳斯站开出,一直向南而去,被法国人简称为TGV的高速列车,需要四个小时才能到地中海附近的阿尔勒。
之前,虽没有到过阿尔勒,却一直知道这个城市名。一是因为比才的歌剧《阿莱城姑娘》(阿莱城是Arles的另一种译法),二是因为画家凡•高,三是因为那里的古迹……
哦,对了,比才的歌剧《阿莱城姑娘》,严格地说,是他为歌剧编写的交响乐组曲。《阿莱城姑娘》本来是作家阿尔丰斯•都德写的一部歌剧,歌剧本身并不成功,倒是比才为它谱写的乐谱《阿莱城姑娘组曲》后来广为流传。
《阿莱城姑娘》说的是:年轻的普罗旺斯农夫费德里科爱上了阿莱城的姑娘。其母听说姑娘名声不太好,便反对婚事,要小儿子马克打听情况。马克打听来的消息不坏,母亲只好认了。大家正庆贺订婚时,长工梅迪菲奥求见。说他与阿莱城姑娘相爱,他还出示了两封信。费德里科看了信痛心疾首,恼怒自己所爱女人的如此行径。几经周折,费德里科决定忘掉阿莱城的姑娘而改娶别人。这时梅迪菲奥又出现了,他跟同伙说准备去阿莱城劫姑娘。这话被费德里科偶然听见,他妒火中烧,精神恍惚中竟以为听见了阿莱城姑娘被劫时的呼救,便爬上高楼,从窗户跳了出去……
火车离开巴黎后,约两个小时后到工业重镇里昂,然后,车速便慢了下来,再经过瓦朗斯、奥朗日、阿维尼翁等几站的停靠,马上就到阿尔勒了……
听说,阿尔勒人口不过五六万人,历史倒是非常悠久,古城内有古罗马人留下的不少遗迹。我一定得利用三星期的逗留时间,好好地看一看那些古迹,当然,还有那里很有特色的风光。
恍惚中,我的耳边仿佛响起了法国奏响的普罗旺斯民歌《三王进行曲》,一个金光灿灿的阿尔勒城展现在我的眼前。英俊的小伙子们招摇过市,靴子噔噔地踩响在古老的石板小路上……
优雅的长笛声飘然而至,竖琴情不自禁地伴唱起来,喧嚣的小城一时间变得如此安静,小伙子也停了脚步。人们想象中的阿莱城姑娘信步走在小街上,她粉蓝色的裙摆随风飞扬……
随着阿尔勒越来越近,我也变得越来越好奇,歌剧《阿莱城姑娘》中,那位“阿莱城姑娘”始终没有在舞台上露面,人们对她可谓众说纷纭,而小城阿尔勒,它究竟是什么模样?
因了“阿莱城姑娘”而变得谜一般的阿尔勒啊,我来了!
眼见为实
从地图上看,阿尔勒城位于法国普罗旺斯的罗讷河口省,是罗讷河汇流入地中海的地方,而地中海著名港口城市蒙彼里埃和马赛正好在河口三角洲的两边。
在著名传记作家欧文•斯通的笔下,小城阿尔勒在凡•高眼中是这样展现的:
“从拉马丁广场到市中心有两种走法。左边的那条环形路是马车走的,这条马路绕着城边缓缓盘旋到山顶,途中经过古罗马的广场和圆形竞技场。文森特选择了更简捷的路线,走这条路得穿过一条条迂回曲折、路面铺着鹅卵石的窄街小巷。他爬了很长一段山路之后,来到被阳光烤得梆硬的市政府广场。在向上走的途中,他经过了一些荒凉的石造庭院建筑。它们看起来像是从古罗马时代原封不动保存下来的一样。为了遮挡那能把人晒得发疯的太阳,这儿的胡同窄得只要文森特伸开手臂,指尖就能碰到两边的房子。为了避开法国南部海岸凛冽的西北风,这些街巷在山坡上故意弯来拐去,没有一段超过十码的直路,就像一座让人无法辨清方向的迷宫。”
终于到达了小城阿尔勒。车站只有矮矮的一排小房子,没有楼房。
出了火车站,便有一条大路向南直通阿尔勒古城,先得经过一个大型的广场,那应该就是人们所说的拉马丁广场了吧,过了这广场后,就看见了古城墙的遗迹,那是一段残墙,中间有两个圆堡,圆堡之间打通了行车道,两个圆堡的另一侧,则是两道小石门。无论是圆堡,还是石门,还是城墙,那上面的石头,都已经有些风化,硬岩上有了青苔,石缝间钻出了小草,质地松软的石头表面,已经是坎坎道道的了。
向右一望,看得见罗讷河。阿尔勒就是因这条大河哺育而生的。河面十分宽阔,比在巴黎见到的塞纳河,还有在里昂见到的同一条罗讷河和另一条叫索恩河的河都要宽。河边某处,耸立着两座桥头堡,上面是雄狮造型的雕塑,其中一头雄狮的脑袋上还立着一只海鸥,长时间里纹丝不动,使人竟以为是雕像的一部分。河对岸,有一模一样的两座桥头堡,只是距离远了,看不清雕塑的细节。水面上,还露着两个桥墩,桥墩上荒草丛生,钢筋支棱,分明是连接大河的大桥的遗迹。
那么,这桥建于何时,毁于何时,是如何毁的?我这个外乡人一概不知道。
我只知道,凡•高曾坐在罗讷河的这一地段,画过我眼前的这片景色:“河面宽阔、水流湍急的罗讷河,在阿尔勒城所在的那座山的山脚下急转弯向着地中海奔流而去。河流两岸是石砌的河堤。特兰凯泰莱宛若画成的一座城市在河的那一边闪光。文森特身后的群山,高耸到一片明亮的白光之中。一幅广阔的画面在他面前展开:耕过的田地、繁花怒放的果园、蒙特梅哲山高高的山岗、肥沃的谷地上千万条深翻的犁沟伸向天边,聚集成一个无限遥远的点。”
两千年的古城,你留下的东西太多了,让我怎么有时间看得过来呢?
凡•高的病院
从车站出发,走过七拐八弯的小巷,十来分钟后,就到了市中心我要住宿的凡•高中心。
大概,我走的是当年凡•高途经的同样的路,只记得有上坡路,有石造庭院,有市政府广场,有鹅卵石的窄街小巷,当然,也有一段可行驶汽车的马路……
这一次,我来阿尔勒的任务,是应法国文学翻译学院的邀请,为中国和法国的年轻文学翻译者作指导,跟另一位法国的指导老师,给六个年轻人讲课和辅导。
文学翻译学院,实际上是一个培训和服务机构,只有四五个工作人员,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翻译家在此短期工作。
我就住在凡•高中心属于文学翻译学院的宿舍,在三层楼上,房间十分简陋,但干净舒适,简直就是一个最小型的复式房间,底下只放一张桌子,床在小阁楼上。从朝东的窗户望出去,便是凡•高某幅画中的那个庭院。据说,凡•高第一次精神病发作后,被送入到阿尔勒的这一病院,在这里画下了《阿尔勒病院的庭院》(1889)。
我眼前的景色,跟绘画中展现的一模一样,换句话说,凡•高精神病发作时画的那幅画,无论从构图,还是从色彩和线条来看,都透着一种理智的把握,洋溢着一种有分寸的热情。
这不是,四四方方的庭院,大约一亩地的面积,比我想象的要小,院中央是划成八瓣的花圃,虽是冬天,却依然开着五颜六色的花,花朵如此娇艳,似乎有些假,给人一种画上去的感觉,没有任何沧桑之痕。四角的大树枝条突兀,落尽了叶子,无法给阳光下的院子提供一片阴影。后来,我下楼在庭院中注意到有一个地方摆放了凡•高那幅画作的复制品,边上正好有一个老师在给学生讲解说,花圃中有凡•高画中没有的一棵开紫花的小树,这才让我依稀感觉到,从凡•高画下的庭院,到如今我看到这庭院,时间过去了一百多年。
两个游客正跟这棵树合影,想必是在证明自己曾经来到过此地,面对镜头,脸上洋溢着甜蜜的微笑。庭院周围倒是跟绘画中最像,拱廊黄白两色,在阳光下格外明亮,绝无病院的那种压抑。
我住的是西侧顶楼上,最靠北的那一间。不知道凡•高当年住哪一间?
历史的天空
斯通的《凡•高传》的第六卷一开始,有这样的一段话:“脚下的这座城市,就像一道飞泻到罗讷河的千变万化的瀑布。一幢幢房子的屋顶拼凑成一幅错综复杂的图案。房顶上铺的瓦原本是红土烧的,但是由于炽热的阳光持续不断地烧灼,竟变得五颜六色,从最浅的柠檬黄色到清淡的银粉红色,直到刺目的淡紫色和沃土似的棕褐色,应有尽有。”
为寻找这样的意境,我走在罗讷河畔的几条小街中。
河道边的路灯,一盏接一盏地排列在路边,好似守卫河堤的兵士,蜗旋型的灯挂,四方倒梯形的灯盏,很像是当年头戴面罩,身着盔甲的罗马军团的士兵。
临河的博物馆,靠河是那么的近,河堤与博物馆的房间之间,没有什么空间可言,站在河堤上,伸手这么一摸,几乎就能摸到博物馆的外墙了。
沿河望去,有那么几段断墙残垣,据说年代久远得有两千年了。新开辟的汽车道都得拐个弯,绕开它走。想一想,这墙要是放在我国的城市,是不是早就被拆了,或是正被涂上了一个“拆”字?
正要绕过几辆停在路边的汽车时,发现了一道大门上方有一个石雕头像,那雕塑,也许是个名人,也许不是,我猜不出。只见它眺望着前方,仿佛一个历史老人注视着岁月的流逝。门前停放着几辆汽车。这汽车是谁的,游客的,房屋主人的,该不是那个雕像的吧……
满墙的藤蔓,因季节的转冷而显出不同的色彩来,配以枝条的纹路,似是又有颜色又有线条的画。雕像男子莫非就是一个画家,每年每季,画出这多变的图画来。
树梢之上的墙面上竟有一片蓝天,乍一看,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玻璃的反光。仔细一瞧,还是玻璃窗,亮光一闪一闪的。转过一个角度,但见那两个窗内还摆着两尊雕塑的头像,而且是面冲外。显然是主人故意让外边经过的人当作博物来欣赏的,一个老年人,古罗马人的样子,一个青年,围了一条蓝白红三色的带子,那么显然是当代法国人了。
阿尔勒早就进入了现代,那汽车便是明证。但它骨子里还是古城。这雕像,还有墙石上不知道哪个年代留下的纵横痕道可以作证。可以作证的,还有窗户中的那几尊雕塑,还有窗口周围纵横交错的藤蔓,还有我这颗既爱古城历史风貌,又爱现代文明便利的心……
古罗马浴池
这一天,跟汉学家尚德兰教授一起去看了古罗马浴池。阳光明媚,但天寒地冻。原以为去古罗马浴池要走很多路,其实走不了几步就到了,就在罗讷河畔。这城市也实在太小。
建于公元4世纪的罗马浴池早就毁了,只剩下了遗址。但高大的半圆穹顶还在,透光用的三个圆窗还在,一些散热用的砖石柱还在,一年四季都袒露着,任凭千百年的日晒雨淋,风吹霜打。
物质遗产剩得不多了,但无形的文明遗产还是留传了下来。浴池尚能看出个依稀的模样,让我们习惯了现代洗浴方式的人猜测当年人们是如何享用这热水浴的。
古罗马浴池是罗马人懂得生活的一个见证。据说,当年,罗马人总是喜欢泡热水澡,蒸桑拿,按摩,搓背(用一种叫strigile的刮子),这些都被认为有利于身体健康。而且他们的洗浴总是结合着运动锻炼的。
当年的浴池分为三个大厅,分别是热水厅(caldarium)、温水厅(tepidarium)和冷水厅(frigidarium),它们又各分为若干池室。现在只能见到前两个大厅的遗迹。热水厅里有炉火,把水烧热后,让水顺着管道,进入大厅,由砖石柱子群来散热,类似今天的暖气片。洗浴者先干蒸,然后泡热水,再用刮子刮全身的皮肤,之后就到温水厅或冷水厅,最后是一通很厉害的按摩。
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当年的浴池,每天下午都开,头一拨先让女人洗,之后再让男人来洗。是不是男人比较脏,安排在后面洗,莫不是尊重女性,在那里就成了习惯?
因为罗马浴池的圆形形状,当年的阿尔勒人把它叫做Trouille,意思是“圆家伙”,那附近的一条街就叫“Trouille街”。后来,不知怎么一来,这个词有了“害怕”的意思。如今,那条“Trouille街”也改成了以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牺牲的老抵抗战士的名字命名的“多米尼克•麦斯朵街”,这多了一些尊严,倒少了好多幽默。
古集市柱廊
在阿尔勒看的又一处古迹,是古罗马集市的柱廊,现在都湮没在了地下。从市政厅前门的楼梯旋转下去,地下好几米处,就来到了柱廊的南廊。
柱廊很长,约莫七八十米,西端向北连接另外的柱廊,然后便来到北廊。三段长廊,在昏暗的灯光下隐约显现出当年的威武相。
如今,北廊的上方,地面上就是集市广场,著名的凡•高咖啡馆就位于那里,但广场上最著名的,还是那两根古罗马的大柱子。上面顶了半个三角楣。
凡•高咖啡馆本名夜晚咖啡馆,因为凡•高当年常常来这里,后又画了以该咖啡馆为题的画,所以今天的人们也把它叫做凡•高咖啡馆。
凡•高画中的咖啡馆是在一个熙熙攘攘的小广场上。眼下,天寒地冻,周边早没了熙熙攘攘的景象,几家饭馆、咖啡馆也都关着门。咖啡馆墙面的颜色依旧保留着黄色,以此表示对凡•高的敬意,但也显得很扎眼。除此之外,咖啡馆看上去再普通不过了,除了凡•高,大概没有人会想到要去画它吧,也正是因为凡•高画过了,咖啡馆也才有了如今的名气。
如今的地下柱廊,当年却是在地上的,随着两千年的建设,目前的地面已经比那时高出了一层楼还多,所以,当年的柱廊就渐渐湮没到了地下,至于那上面的建筑,则早就被岁月和历史毁了。还多亏留在了地下,这些柱廊才能平安保留到今天。
置身于地下柱廊,只觉得冬天的寒气一扫而光,黑暗而温暖的空间,像是一个巨大的地下人防工事,令人想象那是一位文明母亲的宽广肚腹,它包容了多少历史故事,孕集了多少人类智慧……
古墓地孤游
如果让你做一道选择题,问:香榭丽舍的原义是什么?答:A.巴黎的豪华观光大街;B.香艳美丽的厅楼房舍;C.好人死后灵魂的归宿。恐怕很少有人会选择C。其实,香榭丽舍的法语原词“Champs Elysées”的本来意思还就是英雄或有德行之人死后灵魂的归宿。这是从希腊和罗马神话中借来的说法。
那一天我参观的阿里斯冈,就是古代阿尔勒的“Champs Elysées”。“阿里斯冈”(Alyscamps)一词中,“Alys”等于“Elysées”,而“camps”等于“Champs”。古人的“丽舍”和“香榭”。
按照老习惯,古罗马人的墓地,要建在城外,后来,阿尔勒人也继承传统,把坟墓群建在小城的南郊。保存至今的阿里斯冈地处阿尔勒南郊古运河边上,跟东郊的现代墓地遥遥相对。小城不大,步行约十五分钟,就到了古墓地。
天上刮着风,乌云一扫而空,太阳露出了脸。随着阳光的出现,气温反而下降了,感觉比前几天冷了不少。只因为这风是著名的米斯特拉尔(Mistral),凛冽的北风。
说到著名的米斯特拉尔风,倒让我记起了凡•高对它的形容。文森特•凡•高在一封写给弟弟提奥的信中是这么说的:“我也尝到了凛冽的北风的滋味。刮这种风,什么事也做不成。天空蔚蓝,阳光灿烂,冰雪差不多都消融了。但是这种风很冷,又干燥,令人起鸡皮疙瘩。”
古墓地建于泛希腊化时期,至今大约两千多年。当年,有身份的人死了火化之后,会把骨灰放进石棺中,上面再安上石碑。更高贵者,如贵族、教士、王室成员什么的,石棺上还会刻有一些浮雕。久而久之,墓地有了相当规模,几百上千的棺墓在这里排列成好几行,沿大路伸展开来。这些,如今都能看到。
后来,一些传说更是让这古墓地染上了不少神话色彩:查理大帝时代,这里还埋葬了一些法兰克战士,著名的武功歌《罗兰之歌》中的一些英雄就长眠在此。
再后来,意大利著名诗人但丁来阿尔勒时,这古墓地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其不朽作品《神曲》的“地狱篇”中描述的一些地狱形象,无疑受到了阿尔勒城的阿里斯冈的启迪。
当然,在没有亲眼看到那些棺墓之前,我只是在著名画家凡•高的画中,见识过沿大路排列得整整齐齐的这几长列石棺。
画家为后人留下了几幅墓地的画,记得画中的树多是蓝色的,据说是杨柳,而飘落的树叶都是金黄色的,画家画得最多的颜色。
正走着,一股不知道从哪里钻出来的阴风,把地面上的树叶刮得团团转,它们飞起来,与正在下落的树叶绞缠在一起,慢慢飞舞,慢慢降落。……凡•高曾看到的金黄树叶,我都看到了,那是被风刮起来,被风吹落的。风儿渐渐消失,也不知道钻回哪里去了,落叶复归于平静。
一个人在荒凉之地怀古,真有点像卢梭的“一个孤独者的漫步”。恍惚中,那一个个石棺,竟像是公园小径旁的一把把长椅,都怪凡•高,把那些石棺画得那么像椅子,让我一直以为那就是一把把椅子摆在树前。
来到破败的教堂前,竟然觉得它很像是中国什么地方的一处院子,几块乱石,几丛灌木,一扇破门,半壁颓墙。
那教堂据说是在一个基督教殉道者圣热奈斯(Saint Genès)的坟墓之上建造的,最开始只是一个礼拜堂,1040年前后成为一个修道院,归属于圣奥诺拉(Saint Honorat)的名下,12世纪时才又重建了罗马风格的教堂。当年,圣热奈斯因为拒绝签署驱赶基督徒的文书而被砍头,孤魂在此游荡了两千年。
独自游荡了半个小时之后,墓地中终于来了一行游客。他们在导游的陪同下,沿着大路,沿着石棺慢慢前行。
我不再是孤独一人了,当然,那些孤魂们也不会孤单了。TRANSLATIONS译林国外风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