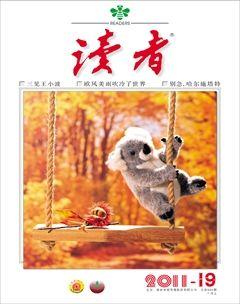张叔
刘若英
“张叔病了。”婆婆在电话的那头说着。
不知道为什么,我听了竟觉得“应该没事”。为什么?是因为多年来张叔不管有什么病痛,都能很快好起来?是我心里的张叔从不生大病?又或者,我打心里不允许他生病,不能接受他也会离开……
过去几年来,身边的老家人一个个都离开了我,我该有些心理准备的,但……但他是“张叔”啊!他是老家人里头最年轻的,也是家人中唯一一个我认识的时候还是一头浓密黑发的。在我的印象中,他会出状况的只有牙齿,掉了好些颗也不补,就那么龇牙咧嘴地笑,像是点缀性的带点风霜的痕迹。
张叔十四岁时跟我们家结下不解之缘,那是我出生前二十年。听祖母说,他小时候家境非常困难,人非常瘦,皮肤黝黑黝黑的,常常到我祖父在南京的办公室门口溜达。萧副官见他相貌端正,想收留他,就让他来当小小传令兵。就这样,小屁孩一个,被理了寸头,握着比他还要高的枪杆在我祖父家门口站岗。可以想象当时的他对这一身行头和未来的归宿充满了期待,所以每天都精神抖擞的。祖父来到台湾,他也就顺理成章地跟着来了台湾,从此以我家为他家。
从大陆到台湾的男丁里,他是当时唯一还没娶亲的。但一切都遵循着“老芋仔”的套路走,他在台湾娶了个本省媳妇。由于祖父不再涉足军政,不需维持排场,家里不用那么多人手,祖父鼓励还年轻的张叔趁此机会多读书,不能一辈子都只是一个传令兵。张叔从此奋发学习,靠着自己的努力考进了公路局,当了一个公务员。这期间,他生了两个儿子、两个女儿,一家人非常和谐地生活着。他的家人并不常出现,就是在年节时,张叔会带着大大小小一家人来拜年。记得小时候看见他儿子时我还会害羞,因为他儿子跟张叔长得很像,瘦瘦高高,相貌堂堂。
虽当了公路局的公务员,张叔每天还到我们家来。有时是早上上班之前来看看,下班有空也会来帮忙,大约他觉得自己有两个家。到他从公路局退休下来,他在我家的服务又从兼职恢复成全职。这时张叔已经六十多岁了,头发已经泛白。
他总是骑着一辆漆成荧光黄的脚踏车,说这样比较安全。也是,常常天没亮就出门,怕大车看不到他。当我自己有了收入,买了一辆单车送他,第二天就发现那车全身已被漆成荧光黄。我简直崩溃了,问他:“我还为了买那个颜色挑选了半天……你为什么不干脆自己全身穿成荧光黄算了?”
年轻如我,不懂得珍惜生命,不能体会时间流逝的急迫感,直到亲人不再理所当然地围绕在身边。有一回祖父参加完朋友的追悼会回来,心情不好,我觉得莫名其妙。张叔跟我解释:“你祖父坐在下面,应该会想,坐在身边的人越来越少,很快也会轮到自己……”祖父晚年时神志不太清醒,祖母的年纪也不小,扶不动祖父,我们请了菲佣照顾。当时担心的是,张叔跟菲佣、祖父,一个是口齿不清的湖南话,一个是菲律宾英文,一个是南京话,要怎么沟通?但三人发明了只有他们听得懂的沟通语言。祖父的最后两年,菲佣也败下阵来,祖父的吃喝拉撒就全靠张叔一个人。有一回过中秋,祖父坐在轮椅上,大伙吃饭,喝了点家乡的甜酒助兴。张叔说,祖父也说要一点。我自以为懂事地把白水倒进酒杯,心想祖父反正也分不出是酒是水。张叔立刻说:“你公公肯定会知道!”我不信。祖父才一沾口,立刻说:“张育才,你骗我……这是水……”看来张叔比我了解祖父,或者说,他比任何人都了解祖父。
他对祖父虽毕恭毕敬,但也有跟祖父闹别扭的时候。祖父是老军人,说话嗓门特别大,说气话时就更大了。有一回两人不知为了什么事起了争执,祖父说:“张育才,你明天不要来我家了!”第二天,都到七点了,张叔果然听从将军的指示没有出现。祖父嘴里不说,但是一直在房里走来走去,最后终于骂骂咧咧:“简直反了,报纸到现在还没有来!”祖母偷偷打电话到张叔家,张叔的太太接的,她当笑话说:“老张啊,一早就穿好衣服坐在客厅,但就是不出门,不安地起起坐坐,刚刚终于坐不住,出门啦!”说时迟那时快,大门有声响,接下来就是一双手捧进了当天的报纸。我跟祖母偷着乐,张叔和祖父跟没事人一样。
祖父临终时,张叔坚持亲自为他擦拭身体,像是在跟自己的大半人生告别。这样的两个人——老将军跟传令兵,没有血缘,没有债务,没有合约,凭的就是相互的感念。祖父应该是个讲情分的人,以至他带到台湾的部下始终不离不弃。祖父有付出,也获得了更大的福报。
每年上山给祖父扫墓,必须带上张叔,只有张叔找得到那条崎岖的路。上山时,他除了鲜花、香、纸钱,还带上一个自制的半圆形的铁网,说这样烧起来又透风,灰絮也不会飞得到处都是。他总是自顾自地开始跟祖父报告:“英英来喽,她来看你喽!太太都好,你放心啊……”仪式结束,他不忘帮安息在我祖父身边的几位朋友扫扫地、弄弄花什么的。仿佛受了他的启发,我会开玩笑说:“你要请这些邻居多担待,祖父的脾气不太好。”
祖父离开之后,老家人只剩下张叔,他依旧坚持每天来家中招呼祖母。长年在外地的我打电话回家,只要是张叔接的,他总不断地重复着:“家里都好,家里都好,你放心……你放心……”的确,我也总因为他这样说着,便更加放心地在外游荡。我知道,刘家大到存款,小到洗手台的螺丝钉,张叔都会一肩挑起;任何时候我回家,他都会一如既往地迎接我。
那几天台北雨下个不停,整个城市被浸得发霉。我正在路上这么想着,祖母来电话说:“张叔病了。”我真的从来没有想过张叔也会生病。他不是最年轻的、发丝乌黑的那个吗?他不是每天游泳,健步如飞吗?他不是一路背着萧副官回大陆探亲,还一路背他回来的吗?他不可以生病,他生病了我们怎么办?祖母怎么办?这就是自私的我当时问的问题。
但是,他确实病了,祖母说。他太太也说,他不爱吃东西了。当时正赶着唱片宣传通告的我,想去看他,祖母跟他的家人都劝阻:“张叔不放心你去,路程很远,下一趟,下一趟吧……”要不就说怕我找不到路。就这样,我失去了再见他一面的机会。这是我莫大的损失,不是张叔的。
我终于去了他家。的确有点远,不好找,但这也是这么多年来,他每天出门来我家须走的路。也没听他提过远,就这样一趟一趟的,一趟一趟的,几十年如一日……那条巷子,确实很窄,他确实需要荧光黄来保护他。我爬上了四楼,迎接我的依旧是那最灿烂的微笑,只是那微笑已被凝固在黑白相框里。他家的气味跟我家的一模一样,因为两个家都是他打理的,都是他的家。我跟姐姐向他磕头,姐姐念着:“谢谢张叔您这一辈子为我们刘家做的,您终于可以放假了……您安心吧!”说好不哭的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能啪啪啪地掉眼泪。我除了难过,还有说不出的生气……
跟他太太、儿子聊天时,我发现玻璃柜里有一张有点眼熟的相片。我走近一看,是张叔从报纸上剪下来的照片,是多年前我去高雄慰劳海军时跟官兵的合影。他将它框了起来,放在显眼处。小英英长大了去劳军,想必对他有非凡的意义。这又让我想起,我好像从来没跟张叔好好合过影,永远都是我们忙着要照相,把相机往他身上一丢,自顾自地站定了姿势。而张叔,永远都藏在镜头的后面,维系着我们家,照顾我们一家人。他十四岁到我们家,此后陪了我们六十多年。
他的太太这么说:“他这一生永远把刘家放在第一位,下来才是自己的家人。每年的年夜饭,他都是招呼好刘家,才愿意踏上归家的路……”张太太说时语气淡定,不含埋怨,像是她充分理解并欣赏先生的先人后己。看来张太太也是张叔的福分。
离开张家时,我在楼梯间见到了我送的那辆脚踏车,荧光黄已成了墨黄。明亮的颜色再也没能保护好我的张叔。
今年清明,我又想上山去看我祖父,拿起电话,才惊觉张叔已经不在了。有谁能再引领我走上那条慎终追远的路?他是六个老家人中最后一个离开的,他的离去,对我而言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一个只问付出不求回报的年代,一个把忠诚视作基本教养的年代。他们对祖父,就如同祖父对民族和国家。祖父,连同老家人,前后陆续离开了我。从此我益发孤单,生活中少了活生生的典范。我只希望,他们的气节永远伴随着我,留存在我的血液中。我只希望,祖父、张叔、易副官、萧副官……他们鲜明、高大的形象,会在我无助的时候,在我抬头处出现。
(深蓝摘自上海文艺出版社《我的不完美》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