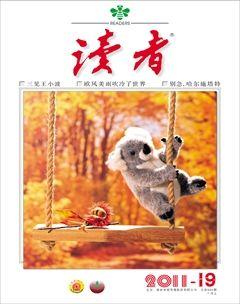三见王小波
钟洁玲
我跟王小波见过三面。
无法想象的是,第三次见面的地方,竟然是八宝山殡仪馆的一号大厅——追悼会现场,他躺在那里,与我阴阳相隔。那一天是1997年4月26日。
4月26日这一天,八宝山一号大厅外,大约来了300多人。除了王小波的亲友,大部分是自发前来的吊唁者。他们是首都传媒界的年轻人,哲学界、历史学界、社会学界和经济学界的学者,还有相当一部分是与王小波从未谋面的读者,有的甚至自千里之外赶来。奇怪的是,当中没有作家协会人员,没有一个小说家。
要知道,王小波是首先将自己看成小说家的。但是,到他死的时候,他的作品还没有进入主流文学的视野,今天仍然没有。
上午10点的光景,追悼会开始。大家排成两行,有序地进入大厅,向王小波的遗体告别。大厅里放着的不是哀乐,而是贝多芬的奏鸣曲。据治丧小组的人说,小波爱听这首曲子。
艾晓明提醒我,将《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三本书的封面摆在王小波身上,随他火化。她说:“他惦着这事,让他知道,封面已经做好了。”艾晓明是王小波的挚友、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是最早关注及评论王小波作品的学者。于是,我让胡贝将封面摊开,依次摆在覆盖王小波遗体的白色床单上,正好是黄、灰、绿三色。封面图案取自古希腊绘画中人类经历的三个世代,意境悠远古朴。
王小波遗容安详,只是额头有一块褐色的伤痕。据说,他是独自于郊外的写作间去世的。被人发现的时候,他头抵着墙壁,墙上有牙齿刮过的痕迹,地上有墙灰。他是挣扎了一段时间,然后孤独地离去的。
王小波没有单位,也没有加入作协,生前他说过:“听说有一个文学圈,我不知道它在哪里。”他是一个局外人,却是一个真正的作家,一个为自己的真理观服务的自由撰稿人。
在追悼会上张罗的,我只认得胡贝和线条。胡贝是王小波从小一块儿玩大的朋友、某软件公司的总经理。线条是个秀气高挑的女人,她就是王小波小说《似水流年》里面漂亮而激进的女一号,大家都依小说里的名字叫她“线条”,其真名反而不得而知。
追悼会大厅是一个会堂,前方正中的舞台上是湖蓝色的幕布,横匾是黑色的,上面悬挂着几个大字:安息吧,小波。下面用黑布巾结成了蝴蝶结,围着王小波的遗照。照片上是青年时代的王小波,小眼睛、厚嘴唇,一脸稚拙憨厚。
出发之前,我曾请一位朋友为王小波写了一副挽联,上联是:以独立意志出神入化笑写时代三部曲;下联是:持自由情怀沥血呕心哭说乾坤万年忧;横批是:小波不死!
我问胡贝:“怎么没有用我发来的挽联?”胡贝说:“我们想让小波平平安安地走。”
“平平安安”?我琢磨着这四个字。
王小波生前在《南方周末》等报刊开设专栏。那段时间,他几乎参与了所有的文化论战,引起多方关注,很不平安。他的随笔机智幽默,文理双修的视野,从容不迫的气度,引来大批年轻读者的追捧。胡贝说:“他说的都是总结性的东西,特精辟,一锤子砸得你骨髓都出来了。”
4月16日前后,王小波的死讯传开,几个城市都有媒体报道此事。自那天开始,无数电话打到治丧小组和报社。此时,王小波的兄弟在美国,妻子李银河远在英国,北京只有老迈的母亲。他的好友胡贝说:“小波没单位,也没加入作协,他的事得由我们来办了。”于是他们就在高教部宿舍(王小波母亲家)大院里面跟人借了一间二楼的房子,拉了两根电话线,接上一部传真机,作为“王小波治丧办公室”。此后每天24小时热线服务,接收全国各地的吊唁电话和传真。
还记得,第一次见到王小波是在北京西单的一个公共汽车站。那是1996年8月,公共汽车站是我们在电话里约好了的碰头地点。在广州的《岭南文化时报》上,我见过他的照片,并牢牢记住了照片旁附上的一句自白:“我这人老远一看不是好人,走近了还是好人。”出租车抵达西单时,我坚信没有看到照片上的王小波。车开过了一段,等我折回头的时候,已经迟到,仍没发现王小波,我认定他迟到了。
这时,从一群闲闲散散地站在路边的人里面,走出一个1米90的高个子。他有狂草一样的头发,身上的夹克衫和牛仔裤的皱折纵横交错,夹带着一路轻尘,仿佛是从附近某个工地走出来的。他迟疑地走近我,愣了两秒钟,我们才互相确认。然后我随着他拐进一条灰砖胡同。走着走着,不见了他,回头才发现他落在远处蹲着系鞋带,系好了,再拖着一双小船似的球鞋疾步赶来。前后穿插的自行车很多,我们交错而行,很难听清对方的话。天色灰暗,整个感觉就像走在一部粤语残片里。
进入他寓所的大院,院子破破旧旧的,据说是从前的郑王府。他熟门熟路地拐入门房小卖部买汽水。他说:“我屋里没水。”
岂止没水!我走进一间纯粹的写作室:一台电脑,一把靠背椅,一张床;电脑桌上搁着一瓶饮料,看不见打印机,他说他素来是交软盘给编辑的。这哪像一个“海归派”的窝呀!
他告诉我,第一部书出版得极度艰难,为找销路他走破了几双鞋,独自去闯二渠道,向书商兜售自己的小说,白的黑的都见过了,练得巧舌如簧。
“书出完了,我也快成书商了。幸好书的销路还不错。”
还有一次,为了在中央电视台做图书宣传,他和妻子李银河被拉去客串。两人在烈日下被调度了几十分钟,反复折腾,差点中暑,结果节目播出时这一截恰恰给剪掉了。
他说得轻描淡写,我听着几乎笑岔了气。无限辛酸,都付笑谈中。
自由撰稿人王小波,1952年生于北京,16岁到云南插队,然后到山东农村当民办教师;回北京后进过街道工厂,恢复高考后考上中国人民大学贸易经济系商品学专业;后来,赴美国匹兹堡大学取得文科硕士学位;还学过计算机,会编程序。1988年,王小波回国,他是真正的“海归派”。
回国后,他曾到北大和人大任教。1992年9月,为专心写作,他辞去教职。
早在70年代中期,王小波就开始写小说,第一篇叫《绿毛水怪》,写在一个大大的练习簿上。后来大家争相传阅,这篇小说成为“手抄本”,越传越远,传出了一段姻缘。王小波的写作缘于一种本能的创作欲望,没有利益,没有外界关注,他还一直坚持写下去。他说:“写了多年小说,还常收到谩骂性的退稿信……提起王小波,大家准会想到宋朝在四川揭竿子起义的那一位,想不到我身上。”即便这样,他仍说:“我相信自己有文学才能,我应该做这件事。”
搞纯文学的在世界各国都是最穷的。这点,王小波早有精神准备。有一次,他对朋友说:“作家就意味着随时有饿死的可能。”为什么选择了严肃写作这样一个趋害避利、既冒险又挨穷的反熵过程?他认为,文明的发展也是一个反熵过程。如果人人都进入趋利避害的熵增过程,随着大流而下,最后准会在一个低洼地汇集,“挤在一起像粪缸里的蛆”。因此,王小波认定反熵过程就是他的宿命。
王小波曾经感叹:“出版一本书比写一本书要难得多。”所以,他说,他若写墓志铭,会在“活过,爱过,写过”后面加上一句“书都卖掉了”。
从王小波那里,我带走了两个软盘,那是“时代三部曲”的原稿。
1996年11月,我将“时代三部曲”上报。12月上旬,花城出版社的选题会在湖南张家界召开,讨论到这套书时,有人认为王小波没有知名度,长达99万字的三部曲存在着发行等方面的风险。最终社长肖建国拍了板:王小波的作品有鲜明的艺术个性,哪怕冒点风险也要试试。
选题会后,12月中旬,我再次到京出差。
第二次见到王小波,是在紫竹院附近的中国企业家协会招待所——我的住处。
晚上匆匆一面,我告诉他“时代三部曲”已经列入1997年年度选题。我看着他,他脸上没有悲喜。我这才了解到,“时代三部曲”经历了漫长曲折的流浪旅程。它是在辗转多时、颠簸多地之后,才停泊在花城出版社的。
王小波在1994年已经成功。那一年,《未来世界》获台湾联合报文学奖,之前《黄金时代》也获过此奖。面对获奖,王小波说:“我觉得,这个奖不是奖给已经形成的文字,而是奖给对小说这门艺术的理解。”同年,华夏出版社出版了《黄金时代》,带给文坛一次小小的震动。敏锐的评论家说:没想到文坛之外有如此高手。
但这些成功未能为他铺砌坦途,他的余作在民间经历了漫长的苦旅。
王小波和他的朋友曾携书稿,天南地北,在多家出版社奔走。部分书稿一度以打印件的形式在社会上流传。打印件是用最老式的24针打印机,打在浅蓝色像一匹布那么长的打印纸上,很多文字有眼睛没鼻子的。奇怪的是,这副样子并未影响它们的传播。在出版社,在研究机构,在大学校园,各种人群传阅着。嗅觉灵敏的书商追上门,讲得洋洋洒洒,开口就是几万的印数,然后又音讯全无;出版社往往是今天接纳,明天变卦。为什么如此反复?皆因艺术上与思想上的无视禁忌。用艾晓明的话来解释,就是:“王小波无视禁忌的顽童心,他的幽默反讽才能和想象奇趣,远远超出这个时代的某种文学理解力。”
对于出书,王小波起初一惊一乍,折腾几次后便宠辱不惊了。
那天晚上,他外衣的颜色我已经遗忘,只记得他嘴唇乌紫。我以为是冷的,现在想来可能是病征的显现。记得他还说了一句:“作家有两种,一种是解释自己,像海明威式的;一种是到想象中去营造,像卡尔维诺,像尤瑟纳尔。我觉得真正的作家应该尝试做后一种。”
第二天我就回了广州。
这个冬天,我有了编辑生涯中永志难忘的一次经历。窗外是冬日蓝天,明朗的气息使人开怀,我正着手编辑“时代三部曲”。
翻开《青铜时代》,有这样的文字:“思维的快乐是人生乐趣中最重要的一种。本书就是一本关于智慧,更确切地说,关于智慧的遭遇的书。”
令我一读一惊心的是,作者凌空飞越的想象力。
我望文兴叹,叹为观止。王小波写知识分子的故事,却借助唐代传奇的背景和人物。也许,只有这样的氛围、这样的人物,才能传达他对趣味和智慧的解释。
猝不及防地,我被王小波所创造的飞雪长安、泥水洛阳及红土湘西引入一个遥远而陌生的诗意世界,那种汪洋恣肆的手笔、顽强的幽默精神,使我的工作变成一种愉快的阅读享受。在一阵阵的笑声中,冬天转瞬即逝,春天轰然而来。
王小波说:“世上只有两种小说,一种是好小说,一种是坏小说。”多么精辟!
无数周折使“时代三部曲”的出版成为王小波生命中至关重要的事情。可是,1997年4月11日他猝然辞世,当时,他的三部书稿还在发排之中。
那段日子,整个年轻的知识界悲情涌动,为王小波的英年早逝真诚伤痛。
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写消息、通稿、回忆、评介,校对、对谈、传真、复印……我脑子里昼夜转着的都是这些内容。出版社为“时代三部曲”成立了专项小组,衔接各个环节。终于,在5月13日王小波45周岁冥诞日,我们在北京现代文学馆召开了“时代三部曲”研讨会,每个与会者手上都拿着刚刚从广州空运来的三本新书。
在这一个多月里,共计有100多家海内外媒体发布了相关报道、评论和悼念文章,互联网上,有人制作了王小波专页,全文输入《黄金时代》。“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王小波的这句名言四方流传。
某大报用整版纪念王小波,上面的两个标题异常触目:“宛如一首美丽的歌”“死得其所的人”。艾晓明将这一版复印下来,用一个大大的原木相框将它镶好,送给了王小波的母亲。
出版社每天收到来自五湖四海的问询,购书单雪片似的飞来。“时代三部曲”经历了洛阳纸贵的阶段,登上各地排行榜。一位资深记者说:“多年来,没有哪一部严肃小说受到这样广泛的关注,它几乎是家喻户晓了。”
一套书遭遇这样的人世沧桑,实属罕见。
如今,我还记得当年艾晓明向我描述的未来情景:100年后,一位中文系的新生,在图书馆书架林立的长廊里逡巡,他说:“我要找一本书,作者叫王小波。”
这些年里,我的“趣味主义”倾向明晰起来。我觉得,活在世上的理想状态应该是:没有趣的人,不交;没有趣的事,不谈;没有趣的书,不出。这是王小波教给我的。
(萍水摘自《各界》2011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