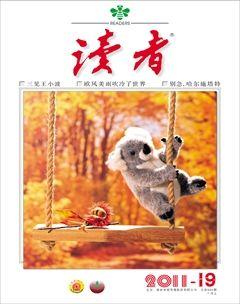黄永松:四十年守望民间
徐晋林



也许你没听说过黄永松,但你一定知道“中国结”。
说到黄永松,不能不提到《汉声》杂志,还有这本杂志的发起人吴美云。那是一个在美国长大的女孩子,书读得好,写作能力强,但常常被误认为是日本人。正是这种经历,促使她想创办一本介绍中国文化的杂志。而她能想到的合作人就是那个做过摄影师、导演的黄永松。而此时的黄永松正在台北和另一个导演拍摄一部关于中国戏曲京剧的纪录片。那富有生机的体现东方美学的戏曲艺术,深深震撼了一直接受现代美术教育的黄永松,同时他也痛心于这些艺术正在一点点湮灭。正是这份不谋而合的机缘,最终撞击出《汉声》这本反映民间文化的杂志来。
1971年,吴美云和黄永松创办的英文版《汉声》——《ECHO》出版了。它一面世就以其独特的民族气息吸引了众多的目光,当时销往三十多个国家。1978年,他们又创办了中文版《汉声》杂志。如果说英文版的《汉声》是东西方文化的横向交流,那么中文版的《汉声》则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纵向衔接。“历史像头,现代像脚”,有头有脚,却没肚腹,他们要做出一个把二者相连的肚腹。正是秉持着这样一种信念,他们才一直坚持做到今天,整整40年。
让黄永松自己也料想不到的是,在后来30多年的时间里,他的足迹将会随着《汉声》走出台湾,走遍中国内地的乡野和村落。米食、面食、风筝、泥塑、北方的农家土炕、陕北的剪纸、贵州的蜡花……每一个题目都曾是《汉声》杂志一期精美的专辑。黄永松在民间采集中亲身经历和感受到的人和事,那些可触可感、可亲可爱的活生生的故事,常常令他难忘。
我把灵魂留下来,身体给你
黄永松从典籍资料上查到了一种蜡染的古法,听说这种古法贵州尚存,他很兴奋。随后他走遍了黔东、黔南、黔西、黔北,寻找这种用木蜡和竹刀制作的蜡染,最终在黔东南地区麻江县龙山乡的青坪村找到了绕家的这种蜡染古法。青坪村绕家多长寿老人,其中有一位102岁的曹汝讲老太太。她的曾孙龙帮平和她住在一起。老人耳聪目明,虽然佝偻着腰,可身手敏捷,不需要年轻人照顾。她翻箱倒柜找出自己90岁时以古老的竹刀、木蜡绘成的背扇。这件点蜡之作,画面以螺丝花为主纹样,四周配置狗牙板。螺丝花宛转流畅,左右顾盼,她又在中心花头上略加三刀,形象似花似鸟。整件作品可谓鸟鸣花香,满幅春光。这就是这位满脸写尽沧桑的百岁老人的内心世界吗?看到这件作品后黄永松非常兴奋。他正准备在台北筹办一个“中国蓝印花布”的展览,为展览所需,就想购买一件。他和他的团队从不搞收藏,每次展览都是从收藏家那里借来的。这一点深受李济先生的影响。
李济先生是著名的人类学家,殷墟的考古挖掘者。他一辈子考古,却从不收藏古物。对此黄永松深有感触,因为在民间这么多年,他碰到了很多古物被买卖的事。有一次,他在山西民间调研的时候,看到一户人家厢房左边那扇窗子是完好的,右边的窗子却只用一块塑料布钉着。他问这家主人,主人说:“那一扇昨天被偷了。”到另外一家,又是这样,一问,说:“有个收古董的把这扇窗子买走了。”又有一次他在西递宏村考察,发现他们都在卖老门窗、老桌子、老椅子。这些事情在农村经常发生,深深触动着他。他想,他一天到晚做着收集整理的工作,不就是要它们得到完好的保护吗?加一个“卖”字如何接受?他也知道,有国外的朋友在安徽买了整栋农民的房子运到美国去。那时候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就把苏州的一个园林买过去在美国重新呈现。他也到那里去看过,可是觉得一点意思都没有,只是一个躯壳在那里。少了生活气息,离了本土的艺术只是一个躯壳在买卖,他觉得不宜。他要求他们的编辑在下去的时候“只许带走照相,留下脚印”,这已变成他们的家训。他坚决不允许编辑购买当地的民间文化物件,也不允许把城市矫揉造作、浮华的气息带到农家去。
但是,这一次展览中独独缺这种“竹刀木蜡”古法制作的作品,他很想带一块回去丰富展览,这也是他唯一一次破例。和老人的曾孙商量后,曾孙同意转让一件背扇给他。当他拿着这件背扇离开时,突然看到老人佝偻着腰追出来,边喃喃自语边冲过来,目标锁定了黄永松。黄永松不明所以,只有后退,老人却抢回了自己的背扇。只见她的曾孙一个箭步冲到老人身旁,嘴里同样说着什么,又是一番言语一番拉扯。老人三番五次将背扇抢了回去,再由她的曾孙送来,最终,老人用剪刀剪下背扇边缘的一小块布后对黄永松说:“我把灵魂留下来,身体给你!”然后不舍地离去。老人对自己作品的情感,让黄永松深受感动。对老人来讲那是与生命相关联的物品,是有灵魂的。
请认购一条夹缬吧
夹缬是中国一种古老的服装印染技术,曾在唐朝辉煌一时,唐代诗人白居易曾吟咏:“成都新夹缬,梁汉碎胭脂。”可惜的是,夹缬在宋代以后逐渐式微,时至今日,这门独特技艺早已失传成谜。黄永松在1997年时听说此项工艺在浙江南部苍南县宜山镇的八岱村尚存,就迅速赶到那里。在那里刚染制好的蓝花夹缬在作坊外的稻田边被摊开来晾晒。平生第一次看到古老夹缬工艺的他有一种得偿宿愿的感动。他和他的团队在那里驻扎了四天,把这项印染技术的每一道工序都完整地记录了下来。当他做完调查之后,染坊主人薛勋郎师傅却说:“这是最后一条夹缬了,以后不再做啦!就要打掉这个染缸了。”难道所见的第一条夹缬,竟是最后一条了?染坊主人准备关闭这个可能是中国现存的最后一个夹缬作坊,原因是这种布已经没人买了。他问染坊主人:“可不可以让它保留?”主人说:“不行,我们不能靠这个生活了。”他想,在唐代绽放奇光异彩,在民间默默传承的古老夹缬工艺,竟从此要在中国消失绝迹!他为之痛心不已。“要卖出多少货,才能维持作坊营运?”他不死心地追问。薛勋郎师傅沉吟一下说:“一年至少要卖出一千条。”“一千条?”一条夹缬有八到十米长,他的头脑里浮现出一千条美丽的《百子图敲花被》来。在这个世界上,一定有千位以上爱好传统民艺、愿以手工夹缬来点缀平淡无味的现代生活的人士吧?想了想,他毅然决然地对薛勋郎说:“一千条,我们订了!”为延续作坊一年的寿命,《汉声》竟成了千条夹缬的认购者。回到台湾后,他就在《汉声》杂志的开篇,写下一篇名为“千条夹缬”的声明,希望那些不想看到这一传统工艺消失的人认购一条夹缬。没想到,杂志出版后,千条夹缬竟然供不应求,被抢购一空。现在,夹缬不但在继续生产,而且已经成为民间工艺品,为越来越多的人所喜爱。2005年,浙南夹缬被列入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红遍世界的中国结
黄永松在一次民间考察时,偶尔看到一家农户的床幔上挂着一件好看的饰品,不知为何物。这家人告诉他那是“结”。他觉得这些藏在民间的小饰品很有意思,并觉得这种“结”很含蓄,蕴涵中国美学的意味——退一步,顾全大局,烘托主角的成人之美。道家就有这个思想:退一步海阔天空,退一步美不胜收,退一步余味无穷。这些思想在这个物品上被充分表现出来。他非常喜欢,回去后就把这种“结艺”定为选题,从此开始四处寻访会打结的人。为整理中国传统的“结艺”,把所有形式的中国结艺都搜集起来,他遍寻台湾会编结的老奶奶,一样一样地学,一步一步地记录。后来,他又找到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老工友,跟他们学习许多古代宫廷的编结工艺。经过四五年的时间,从民间最常见的纽扣结到台北故宫珍藏的玉如意上挂的结饰,都被他挖掘整理出来,最终把编结艺术总结成11种基本结,14种变化结,并将其命名为“中国结”。1981年,《汉声》出版《中国结》专辑,随后又有英文版、德文版面世。由于它富有民族韵味,又简单易学,深受人们的喜爱。从此“中国结”红遍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象征。
建立民间文化基因库
那还是早在1981年《中国结》的德文版即将付梓之际,黄永松赴德国进行编辑间的磋商。他提出希望德文版能附上在德国出售各种手工线绳的商店地址。德方编辑认为不需要,因为德国到处都有手工艺店,要买线材是非常容易的。晚餐时,德方总编辑和黄永松半开玩笑地说:“中国的历史悠久,手工艺一定非常多,不只有中国结,但是像中国结这样被好好整理的不多,《汉声》应该继续整理好其他各种手工艺。”他指着黄永松身上的莱卡相机说:“这是德国人发明、制作的相机。”他问:“《汉声》是搞出版的,印刷机是不是用海德堡?那也是德国人发明的。”又问:“你们也有很多人开德国的奔驰车吧?”接着,他笑容一敛,郑重地说:“德国的工业为什么这么好?就是因为德国注重手工艺。一个民族,只要手工艺好,它的手工业就好;手工业好,轻工业就会好;轻工业好,重工业就会好;重工业好,精密工业就会好。”他又说:“中国替欧美、日本做很多代加工的事情,要知道,如果没有自己的品牌,没有自己的设计,替人家代加工,就只能获取微不足道的利润。”随后,他指出一件更可怕的事——“很多工业制造材料是有剧毒的,那些毒都排放在中国的土地上……”这番话尤如醍醐灌顶,深深地触动了黄永松。这也促使他致力于建立一个民间文化基因库。目前,这个基因库中已有5大种、10类、56项共计几百个民间传统文化项目。
2005年,美国《时代》周刊刊登了一年一度的“亚洲之最”指南,其中台湾的《汉声》杂志被誉为“给内行看的最佳出版物”。2006年,《汉声》杂志的创办者黄永松又被冯骥才基金会授予“中国民间守望者奖”。其《曹雪芹扎燕风筝谱》获2006年“中国最美的书”奖。创刊于1971年的《汉声》杂志在40年之后再次掀起世界关注中国民间文化的热潮,而其创办者黄永松也四十年如一日地践行着全面记录和保护中国民间传统文化的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