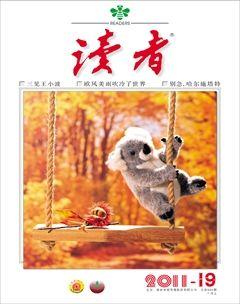司徒雷登:归去来兮的政治隐喻
徐琳玲

杭州半山的安贤园墓地,寂静得只有虫鸣鸟叫声。
6月的风轻轻拂过一块八成新的墓碑,碑上刻着寥寥数字:“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学首任校长”。
46年的等待
2008年11月17日,经过46年的漫长等待,美国将军傅履仁终于完成了父亲的遗愿——把司徒雷登的骨灰带回中国。下葬当日,到场的有时任美国大使的雷登,以及五六名白发苍苍的老者——他们是从京、沪等地赶来的原燕京大学校友。
司徒雷登与这片土地之间的奇特关系,就和他魂牵梦萦的回乡之旅一样充满痛苦的政治隐喻。
1955年,早在去世7年之前,79岁的司徒雷登就立下遗嘱:希望自己的骨灰能安葬在燕京大学校园,与妻子的墓地为邻。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建交,这让追随他一生的秘书傅泾波看到了一丝曙光。他四处奔走,与中方高层沟通,以落实回葬事宜。
情势于1986年有了突破性进展——傅泾波接到中方通知,经中共中央书记处同意,北大方面允许将司徒雷登的骨灰以原燕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安葬于临湖轩。然而不久,有消息传来,北大方面有人发起联名上书,阻挠骨灰归葬之事。
1999年,北大方面再次提出,出于人道主义原则允许安葬,但要求“低调进行”。不久,发生了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一事,中美关系一度紧张,骨灰回葬之事搁浅。
历史学家林孟熹这样评价司徒雷登:“整个20世纪大概没有一个美国人像他那样,曾长期而全面地卷入中国的政治、文化、教育各个领域,并且产生过难以估量的影响。”
在中美关系历史上,司徒雷登是中国最家喻户晓的名字,虽然是以一种奇特的方式被记住的——每一个在1949年后上小学的中国人都能朗朗地背诵上一段:“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
在毛泽东那些广为流传的文章标题中,只有两个外国人的名字曾被提及,一个是“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另一个就是他——“美帝国主义的官方代表”司徒雷登。
“回中国去吧”
光绪二年六月,作为美国传教士长子的司徒雷登就出生在小弄里的一幢二层小楼上。
老杭州人中至今还流传着许多关于他的逸事和段子:他能说一口流利的杭州话,每到清河坊街王润兴饭庄吃饭,会对伙计说:“件儿(五花肉)要瘦,肥了倒胃;木郎豆腐(鱼头)多放胡椒,要烧得入味;响铃儿要熬稍!”
1887年,11岁的司徒雷登被父母带回美国。
大学毕业后,司徒雷登成为一名受学生爱戴的青年教师。他热爱教育事业,爱弗吉尼亚平静而熟悉的生活。可是作为海外传教士的后代,他的耳边总是盘旋着一个摆脱不掉的声音——“去海外布道吧,回中国去吧。”
1905年,司徒雷登带着新婚妻子艾琳,回到了阔别多年的第二故乡——中国。
为了能真正地了解中国文化,司徒雷登专门聘请了一位中文老师,学习汉语和经史子集。他欣赏中国文化中温和的人道主义思想,尤为推崇孟子和王阳明的学说。
在浙北乡村传教时,司徒雷登觉察到父辈传教方式的狭隘与不足。他认为:没有必要让信徒们在新教和尊崇祖先之间左右为难;洗礼只是一种简化了的信教仪式……他的观点逐步为许多在华布道团所采纳。
1908年,司徒雷登被委派任教于南京神学院。为吸引中国民众对基督教的兴趣和关注,他在布道和福音写作中,常常引用儒家的学说来诠释基督教义,以“大同主义”来比喻和描述将福音传遍地球的使命。
这位思想开阔的年轻传教士积极地介入中国人的社会生活,逐渐成为在华传教士中的佼佼者。
自嘲为乞丐的
“燕大之父”
1918年,一封来自北平的邀请信改变了司徒雷登的人生轨迹。他被力邀出任即将合并的两所美国教会在华大学的校长。
一名教员曾这样回忆燕大刚刚合并时的惨淡局面:人事内斗不休,校舍简陋破败,设备缺乏,学生不足百名,多数教员没有大学教授的资格,学校年年财政亏空。
为弥合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差距,司徒雷登主动放弃了不管筹款的就职条件。他先后10次漂洋过海到美国,和副校长鲁斯博士等几位筹款人从一个城市辗转到另一个城市,在任何有可能筹到款的场合演讲,向各种潜在的捐款人做说服动员。
“我每次见到乞丐,就感到我们属于他们这一类。”在一次筹款旅行归来时,司徒雷登如此自嘲。对一个以谨守清贫为荣耀的传教士来说,不得不向有钱人低头是一种痛苦而屈辱的经历。为了从美国铝业大亨霍尔的遗嘱执行人那里得到遗产,他一次又一次接受难堪的拷问,在几年中为燕大争取到150万美元的捐赠。他努力和富豪大亨结交,成为福特和洛克菲勒家族的座上宾,并最终使得洛克菲勒家族成为燕大最重要的资助者。
在他的执著努力下,一笔笔捐赠开始源源不断地流入燕大。截至1937年,燕大所募的款项高达250万美元。这为校舍、设备、日益庞大的维修经费和教学经费奠定了基础。
司徒雷登清醒地意识到:燕京大学若要发展成一流的学府,必须摆脱过于狭隘的宗教意识的束缚。为此,他频频写信,努力争取美国宗教界人士的理解和支持。1922年,燕大废除了学生必须参加主日和教堂礼拜等宗教活动的校规,第二年又做出削减宗教必修课的规定。燕园里活跃着各种形式的宗教讲座与活动,但是,学生有选择的自由;师生无论是基督徒、共产党员还是无政府主义者,都被一视同仁地对待。
几乎是依仗司徒雷登一人之力,燕大从一所无名的小教会学校逐步成长为中国一流、世界著名的大学。1928年,在国民政府对14所私立大学的教育、行政的考核中,燕京大学均名列第一,并被美国加州大学列为亚洲仅有的两所甲级基督教大学之一,其毕业生有资格直接进入美国的研究生院。
曾与他共事多年的燕大末任校长陆志韦曾评价说:“凡是崇拜司徒先生的人,不必褒扬他的长处,也不必为他的短处辩护,而应当体谅他的难处。”
结识每个营垒中的
显要人物
在动荡的中国时局中,为了让燕京大学能在中国站得住脚,赢得人们的善意,也为了能筹到更多钱款,在助手傅泾波的帮助下,司徒雷登开始了“一场广交朋友的活动”。
他和各个时期不同营垒的政坛重要人物,包括北洋军阀、伪满、民国政府、中共、汪伪政权等都有过交往。段祺瑞、孙传芳、蒋介石、孔祥熙、宋子文、张作霖父子、冯玉祥、李宗仁、汪精卫、陈果夫兄弟等军政要人都和他结下了不解之缘。
为购买新校址的地皮,他结交了陕西军阀陈树藩,并以低于市价三分之一的价格买到了土地。当他去拜访军阀孙传芳时,虽然对方怎么也不明白“为什么你们外国人要到中国来教育中国人”,并且用100美元打发走了这个老外,但后来还是加捐了2万美元。在司徒雷登的所有社会关系网中,他和蒋介石的交往是最为引人注目的。20世纪30年代,美国遭遇经济大萧条,燕大陷入财政危机,为此他发起“百万基金运动”。为帮助燕大渡过难关,1934年10月,蒋介石、孔祥熙、汪精卫三人以私人名义在南京举办茶会。随之,燕京大学得到了政府各部的支持。
对于共产主义,司徒雷登在个人信仰角度没有好感。然而,在燕大,他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和信仰一直采取宽容和保护的态度。抗战期间,他曾帮助共产党获得一批军用通讯器材,并通过个人关系网,把决心抗日的燕大学生输送到中共根据地。一度,中共高层对这位在中国享有很高声誉的美籍教育家也非常友好。1940年,司徒雷登意外受伤,毛泽东还特意发去慰问电。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司徒雷登坚守“孤岛”办学。他一边在校园里插上美国国旗,维持正常教学;一边与日本军方周旋,竭力保持燕大的独立性。私底下,他还以各种方式帮助抗战事业。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被日本宪兵抓捕入狱,拘禁长达3年8个月零10天。
正是由于这场监禁,许多中国人心中形成了司徒雷登与他们共存亡、同进退、患难与共的深刻印象。抗战胜利后,他的获释引起了各方的关注。《时代》刊文指出,司徒雷登“有可能是目前中国境内最受敬重的美国人”。
1946年6月,燕大为司徒雷登70寿辰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会。当时中国国内各党派代表,包括以张道藩为首的国府大员,以及由叶剑英领衔的中共高层,都出席了这次庆生。蒋介石特以一块刻有贺词的横匾作为寿礼。国民政府颁发“褒奖令”,赞扬他对中国教育做出的伟大贡献,及在抗日战争中体现出的与中国患难与共的精神。
别了,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在中国极高的个人声誉,以及与各个政治阵营、派别的密切关系,引起当时奉命调停国共矛盾的乔治·马歇尔的极大兴趣。这位杜鲁门总统的特使派出私人飞机把司徒雷登接到南京,游说他出任新一任的美国驻华大使。
1946年7月,司徒雷登出任驻华大使的消息一经传出,处于战火威胁中的中国立刻兴起一场意想不到的舆论热潮,“有如阴云密布的天空突然出现了色彩鲜明的一道长虹”(《新闻晚报》语)。在《最后的演讲》中,闻一多热赞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这一段话却在该文1949年后入选中学教科书时被删得一干二净。
上任伊始,这位“政治生手”对推动和平怀着相当的乐观。1946年的夏秋之交,正是和谈最紧张的时期。当时,蒋介石以避暑之名上了庐山,年逾古稀的司徒雷登只得在烈日下频频奔波于庐山和南京之间。
很快,司徒雷登发现自己低估了国共之间无法化解的矛盾。他不由得想起曾任驻华大使的纳尔逊·约翰逊在日本侵华期间和他说过的一番话,大意为:我们正在观看一场最有决定意义的历史剧,我们的座位在前排,但是除了旁观和接受以外,发挥不了任何作用。“哪想到我们现在就坐在一个豪华的私人包厢,观看一场令人甚为悲伤的演出。”他悲伤地感慨。
1947年1月,调停失败的马歇尔应召回国。启程前,他和司徒雷登进行了一次针对中国局势的谈话。司徒雷登积极主张美国应支持国民政府,并要求它做出内部改革。他的建议得到马歇尔的赞成,华盛顿也采纳了这一意见。
局势在一年里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1948年的圣诞节,炮火已弥漫到北平地区。此时,他还乐观地相信这不是他在中国过的最后一个圣诞节。作为一名信仰自由主义的基督徒,司徒雷登对共产主义有偏见。然而,面对中共接管整个中国的前景,他致电美国国务卿,主张接受现实,积极与共产党接触。
1949年南京解放,司徒雷登留了下来,他在静候着另一种可能。
4月24日清晨,一阵吵闹声惊醒了尚在睡梦中的司徒雷登——他惊诧地发现,十来名配枪的士兵闯进了他的卧室。他们一边好奇地打量着他的家,一边大声呵斥这个美国佬——“所有这一切都是中国人民的,而且很快就会归还给我们”。英、法大使馆也遭到了同样的冲击。
经过数月的漫长等待,司徒雷登逐渐意识到——他和他所代表的美国已是不被欢迎的“人”。8月2日,他黯然离开中国。在日本冲绳转机时,他得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公开发表了《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
这让司徒雷登惊骇万分,因为他所呈报的秘密谈话等全被公之于世。“我越来越不安地想到:这一切将对美国、中国、美中关系产生什么影响呢?那些被提了名字、引用其言论的中国人会有什么后果呢?这对那些发表观察、估计和报告的美国人——其中包括我自己,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不出其所料,蒋介石认为司徒雷登对其“支持不力且背后拆台”,毫不客气地拒绝老朋友到台湾履新。而胜利的一方——毛泽东,在随后的一个多月亲自为新华社撰写了6篇“评白皮书”,其中包括那篇流传甚广的《别了,司徒雷登》。
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司徒雷登不久中风,经抢救后幸免于难,但从此行动不便。一年后,他辞去了大使一职。
燕大的肢解,友人们所遭受的迫害,让晚年的司徒雷登沉浸于巨大的伤痛之中。让他最为痛苦的,是他在那片土地上所承受的污名——“我自己的处境也是一种嘲弄。过去我是美国自由主义和对中国亲善的代表,而现在却被污蔑为美帝国主义政府的官方代表”。
从名利角度衡量,他的晚年近乎窘迫。他一生持守着清教徒的生活方式,没有个人积蓄;由于长期在华工作,他在美国没有医疗保险、住房和养老金。他人生的最后十多年是在傅泾波一家的照顾下度过的,做牧师的独子也很少来探望他。后来,美国基督教高等教育委员会得知他的情况后,每月寄来六百多美元的生活资助。
1962年9月19日8时,86岁的司徒雷登在华盛顿去世。在寥寥数人出席的葬礼上,管风琴奏出的是中国古曲——《阳关三叠》。
(杨柳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11年第2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