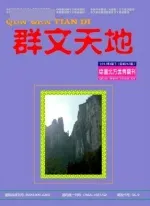一朝品色好 天下皆友之
■刘会彬
这件产于明代宣德年间的青花把莲纹盘(图一),名气非常大,许多著述或文章在谈到明代的青花瓷器时,都把它捧将出来作为例子,有的用它说明当时瓷器的烧造工艺怎样,有的说明胎土怎样,有的说明青花彩料怎样等等。用它来说明明代宣德时期瓷器烧造工艺的高超,主要是把它的大尺寸拿来作为依据,直径有40.5厘米。大就难制作,因为一是制胎难,二是入窑烧造的时候,器物越大就越容易变形,而又制作出来了,所以说明那时的烧造工艺已经并不在于初级。

图一
我们今天在说明古代器物的尺寸时,瓷器也好,铜器也好,玉器也好,木器也好,等等,都普遍采用了“科学”的公制计量单位:毫米、厘米、米什么的。这样做的好处,大概是能够让外国人容易看明白,因为即使不改成公制的而沿用本土的,中国人都能看明白。但是这样一来,好则好矣,用今天的话说,叫作与世界接轨了,但却出来了一个问题,是古人当时之所以将某器制作成为某种尺寸,并不是随意的,而是有讲究的,一改,就把古人的那个讲究改没了。比如这件青花把莲纹盘,40.5厘米换算下来,大体上是十二寸,也就是说是个十二寸盘。
十二这个数字,在中国具有计量以外的含义,虽然最早的发源,据考证不是来自于我国,而是来自于公元前4000年到公元前2000年的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之间的美索不达米亚人。但中国古人也有自己对它的认识,如日晷。我国最早记载日晷的文献,是《隋书·天文志》,书中提到袁充于开皇十四年(公元574年)发明了地平日晷。而日晷将一整天分为十二个时辰,每个时辰为两小时,二十三点到翌日一点为子时,以下依次为丑时、寅时、卯时、辰时、巳时、午时、未时、申时、酉时、戌时、亥时。
十二这个数字,在中国古人的观念中,可能并没有吉凶祸福、是非曲直那样的含义,它仅仅是一个“单位”,一个“单元”,一个“段落”,既没有价值的意义,也没有情感的色彩,但人们在生活中,却的确将它作为事物运行的节奏来看待,是构成整个事件链条中的一环,是构成整个乐曲的一个节拍。我们可以用中国古代的“四大名著”来举例。《三国演义》的第十二回,回目叫作“陶恭祖三让徐州,曹孟德大战吕布”。吕布向有“马中玉兔,人中吕布”的美誉。曹操与吕布此战,而且战而胜之,使得曹操不再是东汉末年诸侯蜂起局面下的一位一般的、普通的诸侯王,而是开始出人头地了,开始显山露水了。因此,第十二回写的曹吕之战,可说是曹孟德完成他事业的转折点,而且此后不久,就“曹孟德移驾幸许都”,挟天子以令诸侯去了。不论《三国演义》作者的情感倾向如何,三分天下以后,实力最为雄厚的一方,其实一直是曹魏。从这个意义上说,曹操此举,为天下后来“三分”的走势,奠定了基础。《水浒》的第十二回,回目是“梁山泊林冲落草,汴京城杨志卖刀”。林冲是整部书基本上贯穿首尾的一个人物,他的上山落草,是一个象征,当时山上虽然已有后来列入一百单八将之内的杜迁、宋万,但梁山真正成为英雄啸聚之所,林冲上山才是开端。而杨志卖刀,又是晁盖等人劫生辰纲的开端,那也是梁山真正走向“繁荣”的肇事。因此,整个《水浒》一部书,至此十二回,才算是序幕结束,正戏开场。《西游记》的第十二回,回目是“玄奘秉诚建大会,观音显像化金蝉”。到西天去取经,是《西游记》故事所要讲述的主旨,也是整个故事串起珠子的那条线,而取经,则由此一回观音菩萨寻到了取经人,方才开始。《红楼梦》第十二回写的是“王熙凤毒设相思局,贾天祥正照风月鉴”。这一回从故事上说,是结束了外围,结束了引子和交代,笔触开始正式进入到荣国府中,进入到荣国府的“社会生活”。从思想意义上说,是揭开了王熙凤所代表的那一类人、一群人的真实内心,这个内心是只可“反看”,不可“正照”,正照的话便是死亡。
总之是十二这个数字,在中国古人那里,虽然不是明面上的色彩,但却是暗中的律动。上面说的四部书,除了十二回以外,十二倍数的回数,也有的可以分析,而且最终是以一百二十回结束。所以像现在这样,将古代遗留物在尺寸方面统统用“科学”的公制法来计量,与西方世界统一是统一了,但却丢掉了中国古代文化中固有的东西,使我们今天看它,没有了文化的温馨感,没有了文化的温暖感,使古物本身的意义、含义,消淡了许多。
题外话说了不少,现在接着说烧造于明代宣德年间的这个青花把莲纹大盘。兹也把它举为例子,是为了说明在中国古代绘画中,有这样一种形式,也就是说,有这样一种画法,称谓上是为“把”,将一些花枝树枝结束起来,可以以手握之。结束为一把的花枝树枝,不限种类,比如说有“把兰”,将几支兰花以索束之,就可以将这幅画题为“把兰”。宋代赵孟坚,有一幅《岁寒三友》传世(图二),这幅画画的不是常见的那样,将松竹梅各一株绘在一起,而是将松竹梅各一枝绘在一起,人看了,除了松竹梅三物在中国古代文人那里所固有的意义外,还给人以优雅、潇洒的审美感受,与常见的画法给人的情感刺激并不相同。这个青花大盘上,画的就是把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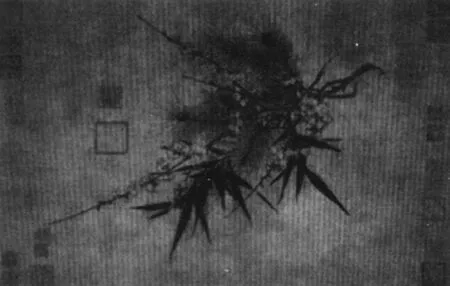
图二
莲荷此物委实可爱,各路人物都喜爱它。例如:有着不同信仰,对世界有着不同认识的各种“教”,在对待莲荷的态度上却格外相同。中国的儒、释、道三家,儒家对待荷花的态度,世人皆知,北宋周敦颐的《爱莲说》一出,荷花简直就成了不与世俗同流合污之高尚品质的象征物,“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成了古代士夫文人追求的崇高的人格境界。可见荷花在儒者那里,差不多已经不再是一种草木花卉了,而是成为了一种精神,一种格调。
中国古代诗歌中,以荷花为题材的,更是数不胜数,而且众口一词的都是把它作为美好情操与事物的化身,或者是志向高洁的人格,或者是纯洁美好的爱情,或者是清雅的情趣,或者是不尘的情怀。早在汉代乐府中,就有这一类诗句,“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到了唐宋时期,直接描写荷花或状荷花之物以抒情的诗词,就更加普遍。当时著名的诗人词家,好像很难找出没写过荷花的来。李白有“涉江玩秋水,爱此红蕖鲜。攀荷弄其珠,荡漾不成圆。”孟浩然有“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李商隐有“世间花叶不相伦,花入金盆叶作尘。唯有绿荷红菡萏,舒卷开合任天真。此荷此叶常相映,翠减红衰愁煞人。”温庭筠有“一夜西风送雨来,粉痕零落愁红浅。船头折藕丝暗牵,藕根莲子相留连。”皮日休有“向日但疑酥滴水,含风浑讶雪生香。吴王台下开多少,遥似西施上素妆。”白居易有“叶展影翻当砌月,花开香散入帘风。不如种在天池上,犹胜生于野水中。”王昌龄有“摘取芙蓉花,莫摘芙蓉叶。将归问夫婿,颜色何如妾。”王维有“日日采莲去,洲长多暮归。开篙莫溅水,畏湿红莲衣。”卢照邻有“浮香绕曲岸,圆影覆华池。常恐秋风早,飘零君不知。”韩愈有“莫道盆池作不成,藕梢初种已齐生,从今有雨君须记,来听萧萧打叶声。”等等,还有宋词元曲,还有古往今来的各种文体,还有至今仍一岁一枯荣于北京大学朗润园荷塘的“季(羡林)荷”,例子真是举不胜举。虽然中国古代的所谓儒者,历代以来所秉承的观念并非单纯的孔孟之道、程朱之学,其间道家的、佛家的,也都多有渗入。但毕竟,士夫文人、诗人词客们的言行,还是更多地反映了儒家的信条理念。因此,当我们举例说明荷花莲藕为儒家所喜爱时,将诗词歌句拿出来作为依据,应无大差。
道教是产生于我国本土的宗教,他们对莲荷也是不吝赞美,并拿来作为自己的神物。道家称莲花为仙花,称藕为灵根。由于莲花在道家那里被赋予了自家的仙气,因此很多道教名山都有莲花山或者莲花峰的称谓,而西岳华山因传说“山顶有池,生千叶莲花”,则干脆就是从莲花(华)山简言而来的。太乙真人是道教之阐教派的十二金仙之一,师尊元始天尊。《拾遗记》说:“汉武时,有人义角……乘一叶红莲,约长丈余,偃卧其中,手持一书,自东海浮来,俄为雾迷,不知所之。东方朔曰:‘此太乙星也。’”到了南宋,《拾遗记》所描述的太乙真人所乘的“一叶红莲”,演化成了“太乙莲舟”。而他的弟子,也是阐派十二金仙之一的哪吒,则干脆就是由莲藕幻化而来的。可见道家对莲花藕荷的钟爱不浅。
至于佛家,我们从许多民间传说故事中,已经早就眼耳都熟而能详了。佛祖释迦牟尼结跏趺坐的是莲花,“西方三圣”之首的阿弥陀佛坐的是莲花,观世音菩萨坐的也是莲花。佛经中把佛国称为“莲界”,把寺庙称为“莲舍”,把袈裟称为“莲服”,把手印称为“莲华(花)合掌”,等等,莲花几乎成了佛教的象征。佛家之所以处处以莲花为伍,据说与佛家的理念有关。佛教将世俗人间视为尘世,而“尘世”是无边的苦海,只有脱离了尘世这个苦海,方才是朗朗乾坤、清明世界,才是幸福的彼岸。而莲花就做到了这一点,它出于淤泥般的尘世,到达了“不染”的“彼岸”。佛家的这个观念,好像与作为儒者,写作了《爱莲说》的周敦颐相当契合,所以说在中国,儒道释三家是很难截然区分开的。
明代洪武时,开国皇帝朱元璋在杀功臣上是有名的。朱元璋这样做,我们作“戏说”式的猜想,可能与他的长子,也是太子的朱标性情太过厚道有关,他担心自己撒手以后,他儿子统摄不住那些因功大而倨傲的功臣们。所以每当上朝,大臣们都惴惴不安,不知道此次上朝会不会有什么祸事,祸事又会降临到谁的头上。马皇后死,在预定的发丧期,天降大雨,雷鸣不止,难以出丧。当此之时,大臣们想,这种情况下皇上的心情恐怕不会好;皇上心情不好,臣子们怕是要倒霉了,所以一班文武,心里都忐忑不安。谁知此时班中走出了一位和尚来,法名唤作宗泐。他对着朱元璋,说出了几句言语,使得朱元璋即使不破涕为笑,心下也颇为安慰了,使得一班臣子们,出了一口长气。宗泐说的是:“雨落天垂泪,雷鸣地举哀。西方诸佛子,同送马如来。”此类言语,佛家称为偈语,但如果我们说它的形式为诗,恐怕也不能算错。这样,佛家弟子与思想观念主要表现为儒家特征的文人所擅长的诗,就发生联系了。宗泐的这几句,如果没有很好的文化功底,一时间应当难以脱口。这也说明在中国,要把儒道释区分的互无瓜葛,怕是难以做到。
既然中国传统文化的表现形态如此,儒道释实际上很难截然分开,那么民间也喜爱荷花这种的确非常美丽的水生植物,也就顺理成章、在所难免了。典型的如杨柳青年画,绘一个胖娃娃抱着一条大鱼,再饰以莲花,谓之“连年有余”(莲年有鱼);把莲花与鹭鸟绘在一起,叫做“一路连升”(一鹭莲升);把莲花和戟(三支)绘在一起,叫做“连升三级”(莲升三戟),等等,不一而足,都反映了在中国民间,莲花为吉祥之物的文化心理。
这件十二寸青花把莲纹大盘,如果将建文和洪熙两朝也计算在内,便是出产于洪武之后四朝的宣德时期。中国的陶瓷史上,尤其是青花,永乐朝和宣德朝是非常重要的时期,人称“永宣时期”。宣德时的政局比较稳定,经济发展较快,天下颇为富足,这为制瓷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因为既有条件发展生产,民间也有条件发生需求。宣德青花成为“鼎盛时期”还有一个原因,是宣德皇帝朱瞻基本人也喜爱艺术,擅长书画。皇帝的喜好,无疑向天下提供了样板,所以天下趋之,并不奇怪。永乐时郑和下西洋,带回来的青花彩料“苏麻离青”,此时仍有存储,因为永乐与宣德虽然中间隔着洪熙一朝,但洪熙朝只存在了一年,这为宣德青花的发展提供了材料上的便利。
这件青花盘的绘画笔法非常流畅而不绵软,劲健有力。画面上除了绘以莲花、莲叶、莲蓬,还绘有茨菰、红寥、蒲棒等其他几样水生植物,使得画面非常丰富,克服了虽然美好却单调的弊端。同时又疏密有致,毫不壅塞凌乱,虽然有图案化的倾向,却又生气盎然、文秀清丽。同时代的纸绢本绘画,如陈淳的《荷花图》,在构图上也有这种思路,应为时代审美倾向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