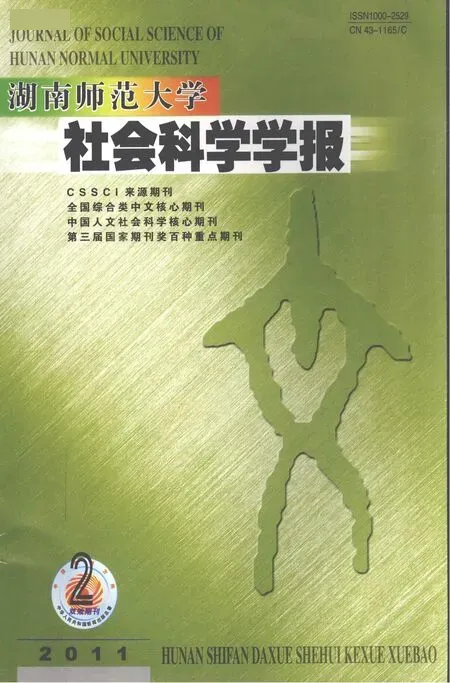庄子“内圣外王”思想的三种形态
陈仁仁
(湖南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庄子“内圣外王”思想的三种形态
陈仁仁
(湖南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庄子通过评判诸子百家之学重提了古代“内圣外王”的思想,并通过转换“圣”、“王”之义将其发展为具有庄子思想特色的“内圣外王”思想。它有三种表现形态,一是作为学问形态,二是作为帝王统治术,三是作为独立个体的人格精神境界。这三种表现形态最终要归结为独立个体人格精神境界这一点上,这也是其为庄子思想之特色所在。
庄子;内圣外王;三种形态
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各家各派大都谈“内圣外王”之道,于是“内圣外王”成为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的最为基本的观念之一。正如梁启超所言:“‘内圣外王之道’一语,包举中国学术之全部,其旨归在于内足以资修养而外足以经世。”[1](P861)大体来说,“内圣”是就修养的成就而言,“外王”是就所成就的事功而言。这是“内圣外王”的基本内涵之一,各家各派大概都不会反对的。但是在内与外,圣与王的具体内涵,以及如何达到“内圣”,如何成就“外王”,“内圣外王”的主体问题与其所反映的更深层的思想观念等具体内容上,就因人而异、因派不同了。无疑,儒家的“内圣外王”思想从《大学》的“修齐治平”论到宋儒重“内圣”而轻“外王”的倾向再到当代新儒家的“老内圣开出新外王”之说,占据了中国思想史上“内圣外王”思想之主流。而“内圣外王”一语与观念之首出于《庄子·天下》,以及它带有道家庄子特有的观念内涵,往往为人忽略。或者人们往往以儒家“内圣外王”观念来理解庄子的“内圣外王”观念,这都是不合适的。实际上先秦儒家文献中虽然有“内圣外王”的观念,但并没有“内圣外王”这一术语。而“内圣外王”自《庄子·天下》提出来后,因其道家庄子义于后世绍述乏人而致渐趋淹没无闻,反被后世儒家袭用而成为儒家的主流思想。本文的目的就在于挖掘出“内圣外王”思想的道家庄子本义,以与儒家义相区别,以明此一思想之源流与分野。我们认为,庄子的“内圣外王”思想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或说有三种形态,这三种形态突出了庄子“内圣外王”思想与其他学派尤其是儒家“内圣外王”思想不同的独特内涵。下面试详述之。
一、作为学问形态的“内圣外王”
《庄子·天下》云:“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这是先秦文献中唯一出现“内圣外王”一语之处。这里并不是从正面阐发来提出“内圣外王”思想,而是从反面表明此道不被人认识和把握。但从这里我们还是可以约略看出“内圣外王”的一些内涵。根据《天下》篇的思路,我们知道,“内圣外王之道”即“道术”。“道术”与“方术”相对。“方术”乃“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的“往而不反”的“百家”之学(《庄子·天下》),也即囿于偏见的关于某一局部或某一领域的学问。《天下》篇讲“道术”“无乎不在”,正表明它与“方术”相对,乃指不含偏见综观全局的关于“无所不在”(《庄子·知北游》)的大全之“道”的学问。因为道无所不在,所以道术也无乎不在。可见,作为“道术”的“内圣外王”之道是一种学问。
就这一学问之为综合而言,并不是指它跟在方术后面作抽象概括与综合,而是在方术之前就存在了,是一种原本就浑沦一体的古代理想的学问形态,所以《天下》篇说它是“古人之大体”,说“古之人其备乎”。各家各派的学问即“方术”都是对“内圣外王”之道即“古之道术”之某一方面的认识、把握、接受和发挥。《天下》篇的主体内容就是评判诸家之学,而在评判诸家之学时有一个相同的表述方式,就是首先引述“古之道术”在某一方面的含义,这方面的含义本与“古之道术”一体无隔,是无可非议的,然后再说“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某某人(即诸家的代表人物)“闻其风而说(悦)之”,接着就进一步评述此家此派的具体主张,而往往在这些具体主张上就可圈可点了。比如《天下》篇这样评述墨家之学:“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不晖于数度,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墨翟、禽滑厘闻其风而说之。为之大过,己之大顺。……以此教人,恐不爱人;以此自行,固不爱己。……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及大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恐其不可以为圣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虽独能任,奈天下何?离于天下,其去王也远矣。”“备世之急”就是“外王”,此语之前的三“不”一“以”句即讲“内圣”,这就是“古之道术”即“内圣外王”之道这种学问的一种体现。墨家喜欢这一方面的学问,于是发挥之。这本无可厚非,亦无不可,但墨家对这一学问实行起来太过苛刻,太顺一己之意,即认为自己能做到,别人也应该做得到,而其实很难做到,于是天下人不乐于追随并实践这种学问。因其学太苛刻,故非圣人之道;又因离于天下无人追随,故去王也远。于是墨家之学既不内圣也不外王了。也就是说墨家的学问本从完美的“古之道术”“内圣外王之道”来,但由于发挥太过而走偏了,成了一种囿于偏见的作为百家之一的“方术”了。
各种“方术”即诸家学问因为都认为自己对“道术”的认识、把握与发挥是绝对正确的,于是就认为只有自己的学问才是真正的“道术”,真正的“内圣外王”之道,是绝对真理,其他诸家之学都是错误的。于是诸家之间就互相争辩,从而形成了战国之时百家争鸣的情形。庄子在《齐物论》中就特别针对这种情形作了批判性考察。他这样说道:“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郭象注云:“儒墨更相是非,而天下皆儒墨也。故百家并起,各私所见,而未始出其方也。”庄子对这种“己是而人非”的狭隘心态是持批判态度的。这种心态会妨碍人们看到其他各种思想的长处,从而妨碍他们对大全之道的理解和把握;这种心态会妨碍人们看到自己思想的不足,从而使他们在自己的狭隘领域内越走越远往而不返。诸家的这种“己是而人非”的狭隘心态是一种思想上的不宽容心态,而与之相对的拥有“内圣外王”之“道术”的“古之人”就应该有一种思想上的宽容精神。这里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庄子所称述的“古之人”的内圣外王之“道术”在古代理想时代是唯一的学问形态,因而不存在思想宽容的问题,但是庄子在“道术为天下裂”之后,针对聚讼纷纭的各家“方术”而重提整体、综合、本原意义上的古之人理想的“内圣外王”的“道术”,显然就赋予了这种“道术”以包容诸家具体思想的能力。诸家具体思想都有其真理性因素,不必互相倾轧、对立,而是可以并存共同回归于实现对“道”以及“道术”的认识。因而,要求不宽容的诸家培养起思想宽容精神,其根据就在于“道术”是一切思想之源和包容一切思想的。
在庄子看来,“内圣外王”之“道术”曾经是天下唯一的学问,后来的诸子百家是对它的割裂,庄子之所以要重新塑造这一理想的“内圣外王”之“道术”的学问形态,其实正是想要现实地再构建一种宽容、包容、涵化诸家之学的大全的学问形态。在庄子的这种学问形态中,诸家相容而不相对立,这正是通过“彼是莫得其偶”(《庄子·齐物论》)而实现的。
二、作为帝王统治术的“内圣外王”
上文还只是从庄子“内圣外王”思想的外在形式和特点来理解其为一种学问形态,但从具体内容上来讲,“内圣外王”是一种什么样的学问呢?它也是一种帝王统治术,这是其“内圣外王”思想的社会政治意义。
张舜徽先生在《周秦道论发微》中认为庄子的“内圣外王之道”是“君人南面之术”。他这样说道:“《天下篇》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此问答之辞也。问者以神明分设,答辞以圣王并举,然则圣王之与神明,同义而殊称耳。董生有言‘人主法天之行,内深藏所以为神,外博观所以为明。’可知神明者,固君人南面之术也。盖圣者,通也,道也。王者,大也,明也。君人者,掩其聪明,深藏而不可测,此之谓‘内圣’。……显其度数,尊高而不可逾,此之谓‘外王’。”[2](P65)张先生从“神”、“明”之义入手来探讨圣王的含义,指出圣王的主体是人君,“内圣外王”是人君的统治术。
庄子“内圣外王”思想确实有作为君人南面之术这方面的内涵,但儒家以及其他诸家的“内圣外王”思想又何尝不是一种君人南面之术?张舜徽先生所谓掩聪明、内深藏之“内圣”,有黄老义;其所谓显度数、外博观,尊高而不可逾之“外王”有儒法义。然则庄子“内圣外王”之说与诸家此说当如何区别之?张先生以“圣”、“王”义同“神”、“明”,却又仅仅以儒家董仲舒之言解“神”、“明”,论证其为君人南面之术,于论证方法言似乎也不太妥当。因而我们有必要对庄子“内圣外王”思想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君人南面之术作出重新思考。
庄子《天下》篇对不同境界和社会阶层的人作过这样的定义与描述:“不离于宗,谓之天人。不离于精,谓之神人。不离于真,谓之至人。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于变化,谓之圣人。以仁为恩,以义为理,以礼为行,以乐为和,薰然慈仁,谓之君子。以法为分,以名为表,以参为验,以稽为决,其数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齿。以事为常,以衣食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为意,皆有以养,民之理也。”(《庄子·天下》)这里区分了七种人:天人、神人、至人、圣人、君子、百官、民。从表述方式来看,前五种人,都是以“谓之”一语以下定义的方式作出界定,而后两种人则显然不是被定义的对象,而只是表示其与某种具体事务有关。从这里可以看出,庄子并不是要简单平列式地将社会人群划出七个阶层来,以表示社会主体有七种人,实际上其所述之主体在以“谓之”一语所定义的由天人至君子五种人。后面的百官与民只不过是前五种人统治安排的对象。从社会阶层之划分来看,其实这里只有君子、百官与民三类人,从天人至圣人这四种人不是某种独立的社会阶层,而是指“君子”的修为境界,此是明“内圣”之旨也。天人、神人、至人、圣人四名异而实一,看似四种人,实则一人而已,正如郭象所注:“凡此四名,一人耳,所自言之异。”尤其明显的是“圣人”乃兼前此三名之义,表示“内圣”需兼天人、神人、至人之义。正如钟泰所指出的:“‘以天为宗’,则圣人即天人也。‘以德为本’,则圣人即真人也。‘以道为门,兆于变化’,则圣人即神人也。……此之圣人,则兼天人、神人、至人而言之,则于天人、神人、至人为集其成。”[3](P757)在“内圣”之义中,所谓宗、精、真、本、门,尚属纯乎其内者,是本体义上的“纯属于道”[4](P3);而所谓“兆于变化”则将入乎变化之域,亦即自然、社会之实然万象之中了,是由“内圣”而“外王”的契机。至于“外王”就是君子、百官与民这一纯然社会领域之事务了。因而很明显,庄子此处的主题就是讲“内圣外王之道”,“内圣”是王者个体的修为境界,“外王”是王者平治天下的社会事功。“内圣”的目的乃在于“外王”,“外王”是“内圣”的外显与延伸。可见,庄子“内圣外王”之道确实有作为君人南面之术这重内涵。但是,在庄子思想中,如何达到“内圣”,如何由“圣”而“王”,需要我们作出进一步的理解。
《庄子·天道》篇有云:“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万物之本也。明此以南乡,尧之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为臣也。以此处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处下,玄圣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闲游,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进为而抚世,则功大名显而天下一也。静而圣,动而王,无为也而尊,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这段话表明庄子“内圣外王”思想有“帝王天子之德”与“玄圣素王之道”两重根本性的意涵。关于“玄圣素王之道”我们将在下节着重论述,这里我们主要来看看庄子“内圣外王”之道如何作为“帝王天子之德”。
“内圣外王”作为帝王天子之德,其主体当然就是帝王天子。帝王天子如何平治天下?根本在于“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虚静、恬淡、寂漠、无为”乃“万物之本”,乃“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庄子·天道》)。成玄英疏曰:“虚静、恬淡、寂漠、无为,四者异名同实者也。”而其根本在“无为”,无为则虚静、恬淡、寂漠矣。所以庄子说“君子不得已而临莅天下,莫若无为”(《庄子·在宥》)。无为是天地之道的根本,人道当效法天地之道,故亦宜无为。所以《庄子·天道》又云:“夫明白于天地之德者,此之谓大本大宗,与天地和者也;所以均调天下,与人和者也。”显然,庄子继承的是老子“无为而治”政治治国理念。《天下》篇曰“配神明,醇天地”,又曰“天地并与,神明往与”,都是以神明与天地相配,所以说“神明即言天地之用也”[3](P756)。王夫之亦云:“神者天之精。”[5](P278)合而言之,可谓圣王法天地神明之道;分而言之,可谓圣法天道之神,王法地道之明。天道“不测”故神而无为,地道容载万物故明而无不为。所以,天地之道即无为而无不为,圣王法之以平治天下。
庄子之以“无为而无不为”作为“内圣外王”的君人南面之术,乃是针对其他各派的帝王统治术以及社会现实状况而发。现实状况是人道往往与天道不一致,庄子云:“悲夫!何谓道?有天道,有人道。无为而尊者,天道也;有为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与人道也,相去远矣,不可不察也。”(《庄子·在宥》)庄子认为,天道无为而人道有为,则人道与天道不一致乃至相去远矣,这是可悲的。这也与老子思想一脉相承,《老子》第七十七章亦曾指出天道与人道在现实生活中的相异,而其目的乃在于使人道效法天道而行。针对儒家等其他学派的统治术,庄子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说:“毁道德以为仁义,圣人之过也。”(《庄子·马蹄》)“及至圣人,屈折礼乐以匡天下之形,悬 仁义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 好知,争归于利,不可止也。此亦圣人之过也。”(《庄子·马蹄》)意思是说儒家等以仁义礼乐等有为之法治理天下是错误的,“偈偈乎揭仁义,若击鼓而求亡子”(《庄子·天道》)。既然有为是“过”,那么在庄子看来,“内圣外王”的君人南面之术必须以天地自然之道的“无为”为根本。所以庄子说:“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黄帝、尧、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为哉?天地而已矣。”(《庄子·天道》)
体天地自然之“无为”即“内圣”的工夫。那么,如何做到“无为”以至“内圣”呢?庄子认为“无心”、“忘”之可以做到“无为”。《庄子·天道》载尧舜问答云:“昔者,舜问于尧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尧曰:‘吾不敖无告,不废穷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妇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则美矣,而未大也。’尧曰:‘然则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宁,日月照而四时行,若昼夜之有经,云行而雨施矣。’”尧之用心可谓美善,但庄子借舜之口表示此等“用心”不若天地之道日月之行昼夜之交替等“不用心”而成就大功。庄子引《记》语“无心得而鬼神服”(《庄子·天地》),鬼神且服而况于人乎?是以无心服人则人治矣。若如天地之无心,必先学会“忘”。庄子云:“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为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谓入于天。”(《庄子·天地》)“忘人,因以为天人矣。”(《庄子·庚桑楚》)“养志者忘形,养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庄子·让王》)“忘仁义”、“忘礼乐”以至于“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而纯然“坐忘”(《庄子·大宗师》)。这都表明要通过“忘”使心虚化而“无心”方能与天地自然之道相合。
“无心”、“忘”、“无为”并不与“有为”、“有得”以及事功截然对立与分割,从无心、无为的角度出发,无为与有为两者之间的关系有两种情形,一是表现为对天地自然规律的遵循与顺应,二是表现为在有为事功活动中的一种不执著的心态。前者如:“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庄子·知北游》)后者如郭象注《大宗师》所言“无心以顺有,故虽终日挥形而神气无变,俯仰万机而淡然自若。”这是无心、忘以及无为的又一种表现。即表现为这使人能顺应世俗之有而不必刻意无之。如庄子借老子之口所云:“圣人遭之而不违,过之而不守。调而应之,德也;偶而应之,道也。帝之所兴,王之所起也。(《庄子·知北游》)这是说圣人遇人事而不违拒,过往而不拘守。调和顺应,便是德;随机适应,便是道。帝王之业就是因之而兴起的。实际上这里涉及的是“内圣”与“外王”之间的关系问题。从“内圣外王”的目的来看,无非是外王即平治天下,而这正是有为、有得与事功。因而“内圣”是工具,“外王”是目的。“内圣”不当排斥“外王”。“内圣”一方面可以是通过遵循天地自然规律而成就“外王”之事功,另一方面可以是在既有之世俗活动中保持一种不执著的心态以顺应万有而成就“外王”之事功。当然从根本意义上讲,“不执著”亦是对天地之道的效法。在“内圣”与“外王”的关系问题上,庄子与后来的儒家一样也有一种重“内圣”而轻“外王”的倾向。其云:“道之真以治身,其绪余以为国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观之,帝王之功,圣人之余事也,非所以完身养生也。”(《庄子·让王》)可见,外王只是内圣之余事,是道之土苴,是可有可无的,内圣必可致外王,而外王对内圣无意义。这与庄子注重个体精神自由的倾向相关。而正是在个体精神自由的人格境界上,庄子的“内圣外王”思想另有一番天地,其“内圣”与“外王”之义当然不同于帝王天子之德意义上的“内圣”与“外王”了。
三、作为个体人格精神境界的“内圣外王”
如果说作为帝王天子之德的“内圣外王”属于庄子“内圣外王”思想的社会政治的意义领域,那么作为玄圣素王之道的“内圣外王”则彰显的是庄子“内圣外王”思想的个体人格精神境界之意义。据《庄子·天道》语:“以此处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处下,玄圣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闲游,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进为而抚世,则功大名显而天下一也。”可知“玄圣素王之道”又分两个行为层次,一是进为抚世,一是退居闲游。两者与帝王“处上”相较,都属于“处下”。其中“进为抚世”是为臣,“退居闲游”是为民。从帝王的“内圣外王”到臣子的“内圣外王”再到一般民众的“内圣外王”,是庄子对“内圣外王”思想所作的一步一步的意义推阐。此意义的核心即是对独立的个体人格的重视。到退居闲游之民的“内圣外王”则纯粹超脱了君民或臣民的对待关系,此民乃逸民而又不执著于隐,是纯然的独立于天地之间的个体人格,其间有一种大境界,鲜明地体现了庄子思想的特色。下面试将此义详述之。
关于“玄圣素王”,郭象注曰:“有其道为天下所归而无其爵者,所谓素王自贵也。”成玄英疏云:“夫有其道而无其爵者,所谓玄圣素王自贵者也,即老君尼父是也。”可见,“玄圣”是指有其道而无其位的圣人,“素王”是指有其道而无其位的王者。有其道”的“道”是什么道?帝王天子平治天下之道也。王的本义是指最高统治者,必是有位者。因而圣人若无王者之位尚且可以理解,而如果说王者也无其位就未免有些强辞夺理了。而素王”之说正是体现庄子思想的特色以及庄子思想转进的一个关键点。
庄子“素王”之称必有其心中所指,其所指可能正如成玄英所言,即老子与孔子。因为两人都是有治国平天下之道而无帝王天子之位的大圣人。尤其是孔子作《春秋》代行王者之事,颇受“知我罪我”之议。所以后世儒者借用庄子“素王”之称来指孔子,算是为孔子正名。于是“素王”之称渐渐地成了孔子之专称,成了孔子为人世立法的天命根据。孔子之称素王是汉初事,此时王其实已经是屈居于皇帝之下的次一级的统治者,而非最高统治者。而春秋战国之世,王依然是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可见,庄子拟“素王”来称处下位者为最高统治者,其勇气与胆量无人能及。如果仅仅将“素王”理解成为帝王天子立言立法的圣人,还不能体现庄子思想的特色,因为先秦各家各派思想的根本目的都在为帝王天子立言立法,先秦诸子饱学深思都想作帝王师。庄子则不然,他超越了作帝王师的企图,我们从《庄子》一书所载庄子不与统治者合作、不应统治者之召的种种行事即可知道这一点。但这并不代表庄子不谈平治天下之道。庄子照样谈论此道,不过他是放在更高的境界上来谈论的。更重要的是他从最高统治者“王”的身上看到了独立个体人格之精神价值,然后将他整个学问都转移到了个体人格境界而非社会人群之治理上。王者是人之大者,他立于天地之间,最能体现人的个体人格之境界。这一点可能是从老子那里继承来的。老子云:“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老子》二十五章)王立于天地之间与天地为叁,故可行参天地赞化育之事。于是庄子的“素王”就不仅仅是治”人,而是应该“治”整个宇宙了。
从上文帝王天子之德意义上的“内圣外王”来看,庄子之治”乃无为而治。“无为”之方乃“无心”而“忘”;“无为”的目的乃无不为而平治天下。天下得以平治的状态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儒道有别焉。在儒家乃将人群导入一个等级秩序中来,使不为乱;而在庄子道家则是使每个人都安其性命之情以体现出各自独立的个体人格来。“无为也,而后安其性命之情”(《庄子·在宥》),这正是从个体内在的存在根据而非外在社会秩序来看待问题的。这个个体内在的存在根据就是“性”、“命”。性命观在庄子哲学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庄子云:“泰初有无,无有无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谓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无间,谓之命;留动而生物,物成生理,谓之形;形体保神,各有仪则,谓之性。性修反德,德至同于初。同乃虚,虚乃大,合喙鸣。喙鸣合,与天地为合。”(《庄子·天地》)可见,万物各有仪则即各有其性,而性之异乃是从源于太初之“无”而来的命份之不同,所以各不相同的物都有其本原形上的根据,因而其物性是自足的,故不必以彼物来评判此物,而应该让万物并存不悖。所谓“物性自足”乃是“长者不为有余,短者不为不足。……性长非所断,性短非所续”(《庄子·骈拇》)之意也。这样才能性修返德,德至而同于初,最后与天地合一。于是,从安其性命之情而来就产生出了一种“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的超越境界。
这样,庄子“玄圣素王”之道意义上的“内圣外王”很清楚地就从为臣者北向事王意义上的“内圣外王”,转入了个体人格意义上的“内圣外王”了。这“内圣”就不仅仅是要求无为而治人群,而且要求与天地精神相往来;这“外王”就不仅仅意味着平治天下,而且意味着平治宇宙,即与天地万物合一。庄子在《天下》篇中自述其学的内涵,即此个体人格意义上的“内圣外王”之精神,其云:“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其于本也,弘大而辟,深闳而肆;其于宗也,可谓稠适而上遂矣。虽然,其应于化而解于物也,其理不竭,其来不蜕,芒乎昧乎,未之尽者。”由此可知,“独与天地精神往来”是内圣,“不敖倪于万物”是外王;“不谴是非”是内圣,“与世俗处”是外王;“上与造物者游”是内圣,“下与外死、无终始者为友”是外王;“其于本……其于宗”是内圣,“其应化解物而无尽者”是外王。
这重意义上的庄子“内圣外王”思想是通过对“圣”与“王”之义作多种转换而实现的。我们先来看“圣”。在这里庄子将“圣”的伦理道德意义上的德性修养的内涵转换成了哲学形上意义上的精神境界之内涵。这种境界的根本表现就是“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精神自由。庄子在很多地方都强调“独”的意义。那为什么要强调“独”呢?因为“道”是独一无对的,所以人心必须先“独”而后方能“见独”(《庄子·大宗师》)而体“道”。所以说,庄子是重视独立个体人格之精神自由的境界的,这个境界与道合一,与宇宙合一,具有哲学形上的超越性。这种“合一”又并没有使个体消融于道与宇宙之中,所以还能“上与造物者游”。而实现这种境界的认识论上的条件就是“不谴是非”,即不卷入是非而超越是非,将是非双方都看作对道的某方面的认识与把握。因而“不谴是非”是一种认识态度、一种思想宽容精神之修养。
然后我们来看“王”义的转换。在这里,庄子对“王”义的转换更多且更重要。首先,王本是对最高统治者的指称,而庄子却把它转换成了指独立个体。也就是说,庄子已经不局限于从外在的“位”上来理解“王”,而是从“王”更为内在的本质特征来理解“王”。这也就把“内圣外王”的主体从“王”转换成了一般个体。王是最高统治者,是主宰者而非被主宰者,因而其独立自主的个体人格义比较好发挥与理解,而其他人都应该像王那样独立自主、自我主宰。施行主宰的不是他人或某物,而是独立个体自身的精神,所以庄子说“物物者非物”(《庄子·在宥》)。于是从精神境界言,一般人与王者都可以同样“逍遥”。现实生活中的王与其他个体虽地位悬殊,但他们都从形上之道那里获得各自之“命”与“性”,因而从“性命之情”上来看他们是同样自足的,都只要“安其性命之情”就可以了。其次,庄子将王所内涵的统治对待关系转换成了平等为友的关系。上下等级秩序主要是一种社会秩序,而平等为友的秩序则可以推扩至宇宙秩序。庄子的“齐物”思想实即走出了人类中心主义而至主张万物平等。在王的原初义上,其统治关系表现为处下者对王的归服。后来王与霸被区别开来,对王者的归服表现为自愿的“心服”(《孟子·公孙丑上》)而非迫于强权与暴力的“力服”(《孟子·公孙丑上》)。庄子也使用了王的“归服”义,如“以此退居而闲游,江海山林之士服”(《庄子·天道》)。庄子这里的“服”当然不是“力服”,因为退居闲游者无武力可恃;甚至也超越了“心服”,因为“服”总有一种屈服独立个体之义,而这是庄子所不取者。所以庄子所谓的“服”乃是认同义,是平等为友义。所以庄子讲“与世俗处”、“不敖倪于万物”,讲“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由此构建出一个和谐的宇宙来。从这里可以看出,庄子走出了关尹老聃的“澹然独与神明居”(《庄子·天下》)式的静止地停留在哲学形上的领域,而是动态地与“天地精神”相往来并进而走向世俗、走向万物以王天下。“神明”即“天地精神”。因而庄子亦是重视“外王”的,只不过这“外王”并非“独治天下百姓而已”(《庄子·在宥》),而是要“出入六合,游乎九州”(《庄子·在宥》),以充分体现独立个体人格之精神自由意义上的王者气概。于是第三,庄子就把王的治百姓、治天下之义转换成了“治身”。所以《庄子》载黄帝向广成子问治天下之道,而广成子不屑,待黄帝不问治天下而问以“治身”时,广成子乃许以“善哉问乎”(《庄子·在宥》)。若人人治身“修形”以把握各自的性命之情与性命之源,即可修性返德以体天地之道,以成宇宙之序。
四、结 语
庄子“内圣外王”思想的这三种表现形态并非截然相分,其实质是合一的。一言以蔽之,庄子的“内圣外王”思想是一种关于帝王统治以及独立个体人格之精神自由境界的学问。其为庄子特色的思想的本质内核在于最终正是归结为独立个体人格之精神自由境界这一点上,其“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内圣”是一种境界,其“不敖倪于万物”、“与世俗处”的“外王”亦是一种境界。于是“内圣”与“外王”在一种超越境界中实现了统一,并使“内圣外王”者在现实生活中做到“以应无穷”(《庄子·齐物论》)而无挂碍。帝王是一独立个体,一般人也是独立个体,两者都可以达到与天地精神往来的精神自由。帝王有帝王天子之德,一般人有玄圣素王之道,两者又都统一于以独立个体的人格精神境界来平天下、友万物、合宇宙。庄子的“内圣外王”思想打破了传统“圣”与“王”的观念,但由于最终将“圣”与“王”合一于超越差别而万物平等的形上的内在精神境界上,所以难免使得庄子“内圣外王”思想有重“内圣”轻“外王”,重个体轻群体,重逍遥轻治理的倾向。庄子的这种“内圣外王”思想也颇有些以“自由个性”为理想以及马克思恩格斯所谓“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味道。但正如段德智教授所指出的,“‘自由个性’虽然是个人发展的最高层次和最高阶段,是理想人格的典型表达式,但是,它不可能是凭空产生出来的,而是以一定的社会条件为基础和前提的”[6](P370),庄子由于认识不到实现它的社会条件,认识不到作为“真实集体”即“能够保障个人利益、个人自由、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真实内涵[6](P374),最终难免使自己的这种思想停留在有些无奈的独立个体人格之精神自由与“虚幻的共同体”上,无法走向真实的社会实践。
[1]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张舜徽.周秦道论发微[M].北京:中华书局,1982.
[3]钟 泰.庄子发微(新1版)[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4]谭戒甫.庄子天下篇校释[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
[5]王夫之.庄子解[M].北京:中华书局,1964.
[6]段德智.主体生成论——对“主体死亡论”之超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Abstract:Through criticizing the thought of several schools,Zhuangzi maintained the ancient idea“be sage within and kingly without”.And through transforming the meaning of the word“sage”and“kingly”,he endowed the idea with Zhuangzi’s characteristics.Zhuangzi’s idea“be sage within and kingly without”has three forms,firstly,it is a kind of knowledge,secondly,it is a kind of methodology of reign,and thirdly,it is a kind of realm of individual spirit.And the three forms will finally return to the point of individual spirit realm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Zhuangzi’s thought.
Keywords:Zhuangzi;be sage within and kingly without;three forms
(责任编校:文 建)
Three Forms of Zhuangzi’s Idea of“Be Sage Within and Kingly Without”
CHEN Ren-ren
(College of Public Adminstration,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Hunan 410081,China)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Hunan 410081,China)
B223
A
1000-2529(2011)02-0017-05
2010-11-20
湖南省教育厅课题“庄子‘内圣外王’思想研究”(07C592);湖南省高校教学改革研究重点项目“中国哲学史类课程体系建构及教学内容改革研究与实践”(湘教通[2009]321号)
陈仁仁(1975-),男,湖南衡东人,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