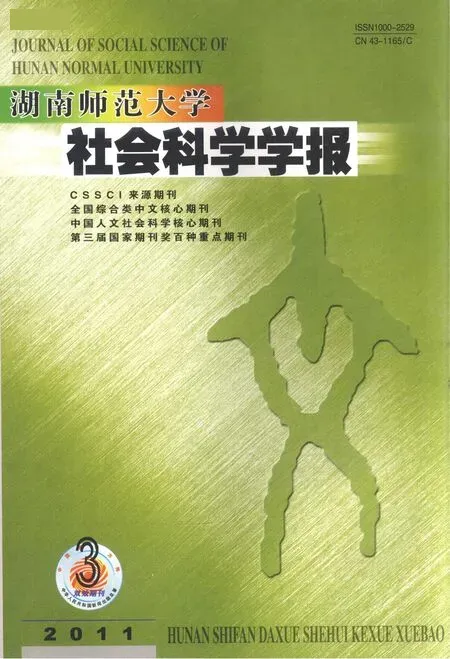梁启超“国学教育”思想研究刍议
朱俊瑞
(杭州师范大学 政治经济学院,浙江 杭州 310036)
梁启超“国学教育”思想研究刍议
朱俊瑞
(杭州师范大学 政治经济学院,浙江 杭州 310036)
“国学教育”虽然是当代学界的流行语,但大多是在一种似乎“不言自明”的模糊状态中使用,很少从史学和教育学的学理层面进行分析。通过对梁启超国学教育思想的探讨,提供一个近代思想家“国学研究”与“国学教育”相关联的分析视角,探索民国时期梁启超“国学教育”的基本内涵和国学研究中的教育意蕴。
梁启超;近代国学;国学教育
国学与国学教育分属两个不同的学科门类。国学已“约定俗成”为传统的“中国学术”[1](P1)。更多地分属于历史学和哲学研究的范围;国学教育则是探索如何把传统学术如何有计划地纳入现代教育体系中,现代教育学学科责无旁贷。现代意义上的国学教育始于20世纪初,到20世纪30年代,“国学教育和研究机构竞相设立”[2](P10),国学教育出现了难得的“少年气象”。因此,从教育史的角度梳理国学教育辉煌时期的合理内核,对于当代的国学教育有重要的启迪。梁启超就是那个时代国学教育的拓荒者。
一
倘若从事中国近现代国学教育史的研究,梁启超无疑是最佳的切入点。教养、学识、才情、勤奋、毅力等各种因素的耦合,促成了梁启超30岁就具备了对传统文化“从头说起”的魄力和胆识,这一年开始写作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贯通今古、旁揽西学,把中国几千年的学术演变写得波澜壮阔、气势恢宏。文章的发端部分更是大气磅礴,如重槌击鼓,催人奋进:
立于五洲中之最大洲而为其洲中之最大国者谁乎?我中华也。人口居全地球三分之一者谁乎?我中华也。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一中断者谁乎?我中华也。我中华有四百兆人公用之语言文字,世界莫能及……吾当草此论之始,吾不得不三薰三沐,仰天百拜,谢其生我于此至美之国,而为此伟大国民之一分子也。
……故合世界史通观之,上世史时代之学术思想,我中华第一也。(泰西虽有希腊梭格拉底、亚里士多德诸贤,然安能及我先秦诸子。)中世史时代之学术思想,我中华第一也。(中世史时代,我国之学术思想,虽稍衰,然欧洲更甚。欧洲所得者,惟基督教及罗马法耳,自余则暗无天日。欧洲以外更不必论。)惟近世史时代,则相形之下,吾汗颜矣!虽然,近世史之前途,未有艾也。又安见此伟大国民,不能恢复乃祖乃宗所处最高尚、最荣誉之位置,而更执牛耳于全世界之学术思想界者?[3](P215)
这篇文章发表时间是1902年,新世纪刚刚开始。
世纪更替,强化了时间流徙和历史变迁在人的心灵中的投影。跨越世纪,常常伴随着人们审视历史、民族和自我角度的重新调整。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对世纪更替的自觉意识首先表现在以“20世纪”命题的文字日益增多①。对近代中国人来说,19世纪中叶以来因战争的失败带来的民族全面危机已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一时间“变动”、“变局”、“变端”、“创事”、“创局”等概括性术语应运而生,体现着一颗颗恐慌不定的心灵。甚至不少人的民族文化自信心的最后防线也被冲破,中国人的文化身份都成了问题。“忧时之士愤神州之不振、哀黄民之多艰,以为中国之弱,弱于中国之学;中国之学必不足以强中国。”[4]于是产生了国学必亡的焦虑②。但梁启超的笔下,一改“老大国”的幕气沉沉和哀伤之语,横扫因战争失利笼罩国人心头的阴霾。尤其是面对刚刚到来的20世纪,梁启超更萌发了一种国学将与之复兴的“世纪更替”意识。
20世纪的钟声刚刚敲响,梁启超就以“少年中国”为题,写就了回肠荡气的《少年中国说》,“少年中国”说一扫“面皴齿尽,白发盈把”的老大帝国形态,展示了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新中国形象。在“少年中国”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创世纪的激情、精神和力量,一种创造生命和“挟山移海”的国家形象③。作为探索“少年中国”生命创造的一部分,梁启超发现了从国学中可以汲取国人自信力和爱国心的力量源泉。因为“学术思想之在一国,犹人之有精神也。而政事、法律、风俗及历史上种种之现象,则其形质也”,“故欲觇其国文野强弱之程度如何,必于学术思想焉求之”。《中国学术思想发展之大势》集中反映了他在国学问题上的最初思考。他引领国人看到的是一个可以与世界之文明相激、相射、相交换、相融合,绽放五光十色之异彩的中国学术文化,看到了区别于“政治世界”的一个学术世界。在学术世界的时空中,梁启超为中国学术的辉煌而鼓舞,抑制不住弘扬国学的兴奋和冲动:
吾欲草此论,吾之热血,如火如焰;吾之希望,如海如潮;吾不自知吾气焰之何以湓涌,吾手足之何以舞蹈也……生此国,为此民,享此学术思想之恩泽,则歌之舞之,发挥之光大之,继长而增高之,吾辈之责也……虽欲歌舞之,乌从而歌舞之?区区小子,于四库著录,十未睹一,于他国文字,初问津焉尔,夫何敢摇笔弄舌,从事于先辈所不敢从事者?虽然,吾爱我国,吾爱我国民,吾不能自已。吾姑就吾所见及之一二,杂写之以为吾将来研究此学之息壤,流布之以为吾同志研究此学者之筚路蓝缕。天如假我数十年乎,我同胞其有联袂而起者乎,伫看近世史中我中华学术思想之位置何如矣?[3](P215)
正是中国学术思想的这种独特魅力,以及梁启超这种对于本国学术的自尊、自爱和自信的态度,推动着他毫不动摇地走上了国学教育之路,承担起“播种之义务”:
顾吾侪今日,只能对于后辈而尽播种之义务,耘之获之,自有人焉,但使国不亡,则新政府建立后二十年,必将有放大光明、持大名誉于全世界学界者,吾诸我先民,吾能信之!……虽然,吾更欲有一言,近顷悲观者流,见新学小生之吐弃国学,惧国学之从此而消灭;吾不此之惧也,但使外学之输入者果昌,则其间接之影响,必使吾国学别添活气,吾敢断言也。但今日欲使外学之真精神,普及于祖国,则当转输之任者,必邃于国学,然后能收其效,以严氏与其他留学欧美之学僮相比较,其明效大验矣!此吾所以汲汲欲以国学为我青年劝也[3](P284)。
不言而喻,民族主义立场和爱国主义情怀,是梁启超从事国学教育的原动力,这原不必需要做太多的解释。
二
承担西学传入者固然应有“邃于国学”的基本功,进行国学研究和从事倡导国学教育更必须具备“邃于国学”的修养。梁启超虽然多以“区区小子”、“难以胜任”自况,也有对自己学术上“病在无恒”自责,但刚刚而立之年的他写就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实第一部有统系之中国学术史,一气呵成,前无凭借,非有绝伟之识力,其曷能与于斯?”[5](P106)世人赞叹这种对中国学术“从头说起”的气魄,也惊叹他学术功力之深厚和笔力之雄健。从1920年欧游归来到1922年双十节前仅仅用两年半的时间,除在清华、南开担任功课及各地巡回讲演外,其著述(主要是国学方面)约有一百万字。他自己曾在《梁任公近著第一辑》的序上统计过:“已印布者,有《清代学术概论》约五万言,《墨子学案》约六万言,《墨经校释》约四万字,《中国历史研究法》约十万言,《大乘起信论考证》约三万言。又三次所辑讲演集约共十余万言。其余未成或待改之稿有《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示的情感》约五万言,《国文教学法》约三万言,《孔子学案》约四万言。又《国学小史稿》,及《中国佛教史稿》全部弃却者各约四万言。其余曾经登载各日报及杂志之文,约三十余万言,辄辑为此论〈编〉,都合不满百万言。两年有半之精神,尽在是矣。”[6](P966)后人评述说,梁启超之著述“势气的阔大,规模的弘博”,堪称是学术上“一位虎视耽耽的野心家”,“他要论中国的学术,便写了一篇《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要论中国的民族,便写了一篇《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要对于‘国学’有所讲述,便动手去写一篇《国学小史》,要对于中国民族的文化有所探究,便又动手去写《中国文化史》。这些都是极浩瀚的工作,然而他却一往无前的做去”;“最可骇人的还有他的《中国文化史》的计划”[7](P93-97)。
在国学教育方面,梁启超也有过创设国学院的宏大计划:
第一,编著国学丛书。以百种为一集。其中分为“校理阐发先哲某家某派之学说为主”的学术思想;以“诠述批评前代作家或作品为主”的文艺;以及各种历史和社会现状方面的著作。第二,编辑近代学术文编及国学海外文编。仿照贺长岭的《经世文编》,广搜清初以来的学者专集及杂志中所发表凡研究国学有价值之文章。第三,编制大辞书。包括百科总辞书和分科专门辞书。第四,校理古籍。拟于五年内将最重要之古籍校理完竣。第五,续辑《四库全书》。搜集(四库)未收书,及乾嘉以后名著,编定目录,撰述提要。第六,重编佛藏。精择各宗派代表之经论,删伪删复,再益以(续藏)中之主要论疏,约列成三千卷,各书附以提要[8](P36-37)。
这种气吞万象的魄力以及在国学方面“绝伟之识力”,在民国初年的教育界“其声望所归如万流仰镜”,使梁启超有足够的理由和勇气宣告:
启超确信我国儒家之人生哲学,为陶养人格至善之鹄,全世界无论何国,无论何派之学说,未见其必在今日有发挥光大之必要。
启超确信先秦诸子及宋明理学,皆能在世界学术上占重要位置,亟宜爬罗其宗别,磨洗其面目。
启超确信佛教为最崇贵最圆满之宗教,其大乘教理,尤为人类最高文化之产物,而现代阐明传播之责任,全在我中国人。
启超确信我国文学美术,在人类文化中有绝大价值,与泰西作品接触后,当发生异彩,今日则蜕变猛进之机运渐将成熟。
启超确信中国历史在人类文化中有绝大意义,其资料之丰,世界罕匹,实亘古未辟之无尽宝藏,今日已到不容扃镢之时代,而开采之须用极大劳费。
启超确信欲创造新中国,非赋予国民以新元气不可,而新元气决非枝枝节节吸受外国物质文明所能养成,必须有内发的心力以为之主。以上五事,实为其芽种。
启超确信当现在全世界怀疑沉闷时代,我国人对于人类宜有精神的贡献,即知识方面,亦宜有所持以与人交换。以上五事之发明整理,实吾侪对世界应负之义务。
启超确信欲从事于发明整理,必须在旧学上积有丰富精勤的修养,而于外来文化亦有相当的了解,乃能胜任。今日正在人才绝续之交,过此以往,益难为力。启超虽不敢自命为胜任,然确信我在今日,最少应为积极负责之一人;我若怠弃,无以谢天下[9](P825-826)。
评述梁启超的国学著作,不是本文的主题,也不是作者笔力所能及。但从梁启超“我若怠弃,无以谢天下”的告白中可以看出,他对国学的“发明整理”含有登高一呼的强烈愿望和执着追求。换言之,梁启超的国学研究带有鲜明的教育和启蒙色彩,甚至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毫不掩饰地和盘托出:
其一,可见我国民确富有“学问的本能”。我国文化史确有研究价值,即一代而已见其概。故我辈虽当一面尽量吸收外来之新文化,一面仍万不可妄自菲薄,蔑弃其遗产。
其二,对于先辈之“学者的人格”,可以生一种观感。所谓“学者的人格”者,为学问而学问,断不以学问供学问以外之手段。故其性耿介,其志专一,虽若不周于世用,然每一时代文化之进展,必赖有此等人。
其三,可以知学问之价值,在善疑,在求真,在创获。所谓研究精神者,归著于此点。不问其所疑、所求、所创者在何部分,亦不问其所得之巨细,要之经一翻研究,即有一翻贡献。必如是始能谓之增加遗产;对于本国之遗产当有然,对于全世界人类之遗产亦当有然。
其四,将现在学风与前辈学风相比照,令吾曹可以发现自己种种缺点。知现代学问上笼统影响凌乱肤浅等等恶现象,实我辈所造成。此等现象,非彻底改造,则学问永无独立之望,且生心害政,其流且及于学问社会以外。吾辈欲为将来之学术界造福耶?抑造罪耶?不可不取鉴前代得失以自策厉。[10](P3108)
一般来说,国学研究偏重考证,与情感洋溢的国学教育似乎冰炭霄壤,但是,梁启超的国学研究著作却让我们看到了二者的水乳交融,看到了国学研究的冷峻理性与国学教育的人文关怀间的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梁启超的国学论著在国学教育热的今天所以能为众所瞩目,就在于在他理性的分析背后通过酣畅淋漓的语言表达出的一种育人的激情[11](P63-64)。阅读《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或《清代学术概论》,我们面对的不是仅仅在这个专题领域有其特长的学者,而在他的著作里,在他非繁复征引和绵密演绎的深处,有着超越于史事论证的对人生、对社会、对中华学术未来的深刻思考,他对学术人格的剖析和对国学中科学精神的礼赞,总会感到一种无形的人格力量,又能受到做学问的一种极难得的启示和陶。这样才使得国学研究蕴含一种“秋冬之际”“、山阴道上”的眷恋情怀,又能有一种“仲春令月,时和气清”的舒朗气息。在这种意义上,不正是一种成功的国学教育文本?显然,研究梁启超的国学思想,以通常的考据学功夫评述梁启超国学研究上的得失固然不失为一种可行的方法,但掠过他特定的“国学教育”意图恐怕难得要旨。发掘梁启超国学研究中的教育内涵应当成为梁启超国学思想研究的重要内容。
梁启超在国学教育的态度上绝不是守旧主义,更不是传统主义。他在对待国学的态度上一直抱有开放的态度,这种开放包括自我批判和对不同文化的传统的开放,既反对保守主义者的固步自封,也时刻防范对本国学术文化上的虚无主义:
凡天下事,必比较然后见其真,无比较则非惟不能知己之所短,并不能知己之所长……今世所称好学深思之士有两种:一则徒为本国学术思想界所窘,而于他国者未尝一涉其樊也;一则徒为外国学术思想所眩,而于本国者不屑一厝其意也。夫我界既如此其博大而深赜也,他界复如此其灿烂而蓬勃也,非竭数十年之力于彼乎,于此乎,一一撷其实,咀其华,融会而贯通焉。[3](P215+216)
三
梁启超是公认的百科全书式国学大师,甚至被誉为20世纪的学者,这并非因为他在这个世纪生活了29年,主要是因为他的学术思想在这个世纪产生了经久不息、无可回避的影响。
现在学术研究分工的精细化促进了对局部问题研究的深入,却也再难见先哲那种“统摄六艺”的通家气象。以当代学者的学术训练研究梁启超这样一个通才型人物也只能使学术成果走向“深刻的片面”。如,论述梁启超教育思想的论著以及国内有关中国教育思想史方面的论著大多紧扣教育原则分析梁启超的教育思想[12](P208),对其学术思想的研究则相对不足;史学界侧重了梁启超的“国学研究”却又冷落了他的“国学教育”思想。目前,对梁启超国学思想研究和国学教育的研究基本上还是被分为两橛。
如果把国学教育与学术研究的不同指向进行合理的联结,“国学教育”可以衍生为一个教育哲学的命题,梁启超“国学教育”思想的基本涵义逐步清晰④。实际上,学术与教育的关系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关注的重要命题。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发展历程中,学术成果要纳入教学内容之中,学术成果经过一定的程序可以选择、组织为“课程”;而教学内容的深度要反映学术的成就,传递学术成果,两者的关系十分密切。“研究中国学术与教学的关系,尤应掌握这一基本精神与基本方法。”[13](P277)所以,如果把中国学术还原为“国学”,传统的“国学教育”的体制,无论是官学还是私学,都是一种教育者把儒家思想(含学术)“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受教育者的身心施加影响的活动”⑤。特别是带有霸权性质的科举制,建立起对圣贤之言的神圣性崇拜。儒家经典,也成为中国读书人主要的教育资源。应该说,近代以前中国学术(“国学”)与教育的关系比较容易厘清,它主要是传统内部学术资源的不同分配问题。
近代以降,中学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中学的命运反复叩动着国人的中枢神经。围绕中学与西学、旧学与新学的百年争论,落实到教育上,大体上可以视为传统学术能否进入、如何进入近代新式学堂中的问题。“国学”最终取代“中学”成为中国学术的代名词,很大程度上也是这种思考、争辩的产物。因此,近代国学教育的基本内涵是思考“中学”能否在新式学堂教育中占有一席⑥。从1898年的几个《大学堂章程》中可以看到,在高等教育课程设置的初始阶段,把“中学”“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进入大学课堂甚至可以占据主导地位并没有多大的困难。但现实的发展证明,这种让“中学”立于新式课堂的愿望无法真正成为现实。其中的原因除了“西学之用”越来越得到“举国上下”的支持外,还源于东西学术自身不同的分类和构成。中国传统的“四部之学”难以与“七科之学”合理嫁接,传统的经史之学强行改装也难以进入西学的学科门类,在新式“大学堂”按照西方分科设学的体制下,“中学”面临的尴尬是个不证自明的事实⑦。如果说科举制的废除标志着“中学”不再拥有作为教育资源的“合法性”基础,那么“分科设学”则使中学在大学体制下失去了学理上的支援⑧。当然,在科举制废除的四年前,实行了一千多年的书院教育制度,已早早被清廷一道旨令强行改制,中国高等教育基本上让重实用的欧美模式一统天下。
不过,教育上的“西学东渐”过程也是被思想家不断反省甚至引起抵抗的过程。与章太炎、马一俘等人排斥新式学堂、坚持书院教育的方式不同,梁启超在中西学术上的一贯立场是“中学为中心”的中西学术并立,在认同、接受近代教育体制的前提下思考中学的位置和未来。从戊戌变法时期主张“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到《新民丛报》时期短暂地“采补其所本无”很快转化成以“淬厉其所本有”为中心;再到辛亥革命前后以“国语”、“国教”、“国俗”论证中国国性之永恒;五四以后更是把主要精力付诸国学教育。究其一生的教育思想和实践,在梁启超的“国学教育”概念中,“中学”始终应该成为学校和社会育人的基础;智、仁、勇“三达德”为中心的传统人格教育始终应该是近代教育的方向;从国学中寻觅医治现代教育弊病的良方是他始终不渝努力的目标。梁启超一生虽然以“善变”闻名,但把“中学”引入近代教育是他一贯的立场。当然,在不同的时期,梁启超国学教育的具体内容有所不同:戊戌变法时期主要是反省洋务过程西学教育的畸形发展,梁启超把“中学”中的“政学”引入到学堂教育中;《新民丛报》时期,梁启超主要反省新学青年对“政学”的误用,把王阳明的德性之教和曾国藩的“内省之学”导入新学教育中;五四后梁启超通过对西方学术文化和中国大学教育的双重反省,把国学中的科学精神和“内省躬行”的人格修养纳入现代大学教育的宗旨和学生的日常行为中。梁启超的“国学教育”思想的主要线索也是随着他对近代教育“西学东渐”后的三次集中反省而次第展开。
四
梁启超不属于有严密理论体系的教育家,即使在后期专心从事国学教育完成的《治国学杂话》、《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等论文和演讲也多为随感而发。换言之,梁启超在国学教育问题上,并没有预先设定理论框架,而后逐步演绎出国学教育的宗旨、原则、内容、关系、方法等等。但有关国学教育的“杂话”,却是出自他对人生、教育的深切领悟,并把这种领悟带入自己擅长的国学研究著作中。因此,从事梁启超“国学教育”思想的研究可以按照“法从例出”的思考方式,从解读梁启超的国学研究的经典著作中,整理出梁启超国学教育思想的丰富内涵。
在民国时期的国学大师中,他不属于那种将生命捻成思辨的或训诂的语丝式的纯粹学者,而是直接用热血去鼓舞时代的教育家,在他国学著作中,始终在坚韧地期待国学的春风:
吾对于我国学术界之前途,实抱非常乐观。盖吾稽诸历史,征诸时势,按诸我国民性,而信其于最近之将来,必能演出数种潮流,各为充量之发展。吾今试为预言于此,吾祝吾观察之不谬,而希望之不虚也。
其一,自经清代考证学派二百余年之训练,成为一种遗传,我国学子之头脑,渐趋于冷静缜密……今后欧美科学,日日输入,我国民用其遗传上极优粹之科学的头脑,凭借此等丰富之资料,瘁精研究,将来必可成为全世界第一等之“科学国民”。
其二,佛教哲学,本为我先民最为珍贵之一遗产……我国民性,对于此种学问,本有特长,前此所以能发达者在此,今后此特性必将复活。
其三,所谓“经世致用”之一学派,其根本观念,传自孔孟……吾敢言我国之生计社会,实为将来新学说最好之试验场;而我国学者,对于此问簿,实有最大之发言权,且尤当自觉悟其对此问题应负最大之任务。
其四,我国文学美术根柢极深厚,气象皆雄伟……今后西洋之文学美术,行将尽量收入,我国民于最近之将来,必有多数之天才家出焉,采纳之而傅益以己之遗产,创成新派,与其他之学术相联络呼应,为趣味极丰富之民众的文化运动。
其五,社会日复杂,应治之学日多,学者断不能如清儒之专研古典。而固有之遗产,又不可蔑弃,则将来必有一派学者焉,用最新的科学方法,将旧学分科整治,撷其粹,存其真,续清儒未竟之绪,而益加以精严,使后之学者既节省精力,而亦不坠其先业。世界人之治中华国学者,亦得有藉焉。[10](P3108-3109)
这种“夹叙夹议”国学研究所彰显的教育命题,是梁启超把原本“为学术而学术”国学研究转化为“学术致用”的通用风格。为了有利于把国学研究转化为教育资源,梁启超把国学分为“文献的学问”和“德性的学问”,主张分别用“客观的科学方法”与“内省的躬行的方法”去研究[14](P3343),把国学教育的视野扩展到几千年中国传统学术领域,以“淬厉其所本有”的姿态,“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通过对国学内涵的重新诠释,梳理出矫正近代以来西学教育畸形发展和挽救道德沦丧学风的营养元素。特别是他后期潜入清代学术不厌其烦地赞美清代学者“非功利”的严谨治学精神,但另一只眼始终不离开生活在现实中的学界文人和青年学子。他未能具备乾嘉学派的治学风格,在学术上或许是梁启超的不幸⑨,但把国学研究和国学教育紧密联合,梁启超出色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从教育学的意义上看梁启超的国学研究,梁启超是成功者,也使他真正走出了“乾嘉时代”。
对于自己过渡时代之人物的定位有清醒意识的梁启超,完好地向我们传递了包孕在20世纪初而影响及于21世纪的学术讯息,以觉世始而以传世终。这便是他在近现代国学教育史上应有的形象和历史地位。所以,以客观的态度整理梁启超的国学教育思想,不应被误解成“为守旧主义者辩护”。同时,梁启超的志气德行、事业文章早已“力透纸背”,如“溪水之自山谷陡降也,气势雄健,一往无前,波跳浪涌,水声雷轰,一切山石悬岩,皆只足助其壮威,而不足以阻其前进”[7](P83),也绝不会因后学的浅薄而损耗其分毫的价值。
注 释:
① 参见《20世纪之支那》第1期。
② 黄节甚至认为“亡吾国学者,不在泰西而在日本”。见黄节,《国粹学报叙》,《国粹学报》第1年第1期。
③ 这一青春创造的时代命题深深地影响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引起了他们的共鸣和回响。尤其是五四时期的少年中国等概念的流行。
④ “国学教育”一词常见诸报端,但何谓“国学教育”,的确需要一种教育哲学的论证。
⑤ 该定义来自对“教育”概念解释的转用。
⑥ 广义上的中学包容了全部的中国文化,梁启超笔下的“中学”(本文中用引号标识),是指狭义上的中国学术,与后来讲的“国学”同义。按照梁启超的行文,在1904年前多用“中学”,以后使用“国学”,有时也用“旧学”,都是指中国学术。
⑦ 不证自明不等于不需要证明。实际上这是个复杂的问题。大学课程的设置恪守西方的学科分类原则,中国哲学、中国历史逐步从传统的经学中剥离出,但中国有无哲学或能否用西学中的方法分解“中学”,这个问题至今仍有争论。
⑧ 对于梁启超学术的不严谨,学者包括梁启超自己多有论述,此勿赘述。
⑨ 刘心龙对此有精当的分析:“中国传统《七略》或四部式的图书分类,虽然不能完全视为一种学科分类系统,但是多少反映了中国传统的知识系谱,只是此一反映中国知识系谱的分类系统,却始终与学堂教科之间存在着严重剥离的现象。就以清代来说,经史子集等内容能被纳入学校教育体制中的毕竟只是少数,八股制艺取士的方式,使大部分的书院学堂只侧重部分经史典籍的研讨,更导致学堂教科的内容只有极少部分能与传统知识叠合,然而可以叠合的这少部分经史典籍,却又因制艺主导的教学方向,逐渐化约为愈趋空洞僵化的教条,终致无法反映中国整体的知识结构。因此当清末新式学堂采行中西学并重的教育方式时,中学基本上便不是以其整体的知识结构来应对西学,以致西式分科的教育内容,得以轻易地顶替传统官学(或书院)笼统而不分科的教学体制。”论文收入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 史学卷(下)》,山东人民出版社)第四编。
[1]张岱年.《国学丛书》序[A].国学今论[C].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
[2]桑 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3]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A].饮冰室文集(点校本)第一集[C].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
[4]邓 实.国学保存论[N].政艺通报,甲辰3号.
[5]张荫麟.近代中国学术史上之梁任公先生[A].夏晓虹.追忆梁启超[C].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
[6]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7]郑振铎.梁任公先生[A].夏晓虹.追忆梁启超[C].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
[8]王森然.梁任公先生评传(节录)[A].夏晓虹.追忆梁启超[C].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
[9]梁启超.为创立文化学院事求助于国中同志[A].梁启超选集[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10]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A].梁启超全集(第五册)[C].北京出版社,1999.
[11]方红梅.关于完整人与趣味人的构想——席勒与梁启超美育思想之比较[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07,(1):63-64.
[12]宋 仁.梁启超教育思想研究[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
[13]黄 济.中国传统教育哲学思想概论[M].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4.
[14]梁启超.治国学的两条大路[A].饮冰室文集(点校本)(第六集)[C].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
(责任编校:文 泉)
On the Thoughts of“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Education”by Liang Qichao
ZHU Jun-rui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Hangzhou,Zhejiang 310036,China)
The technical term“Educ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is now very popular in academic circles,but it’s often used as if the term is self-evident,and it was seldom analyzed in the aspects of both history and education.This paper analyzes the thoughts of“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education”by Liang Qichao,offering a new analyzing angle which is based on not only“the research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but also“the educ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of the thinker in modern history,approaching both the main contents of“Educ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and the education intention in“the research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of Liang’s thoughts.
Liang Qichao;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educ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G40-03
A
1000-2529(2011)03-0119-05
2011-01-20
浙江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民国时期国学大师笔下的‘浙江学派’”(09JDMG003Z);浙江省教育规划重点项目“国学教育资源中的‘浙江学派’”(SB96)
朱俊瑞(1965-),男,山东昌邑人,杭州师范大学教授,历史学博士,教育学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