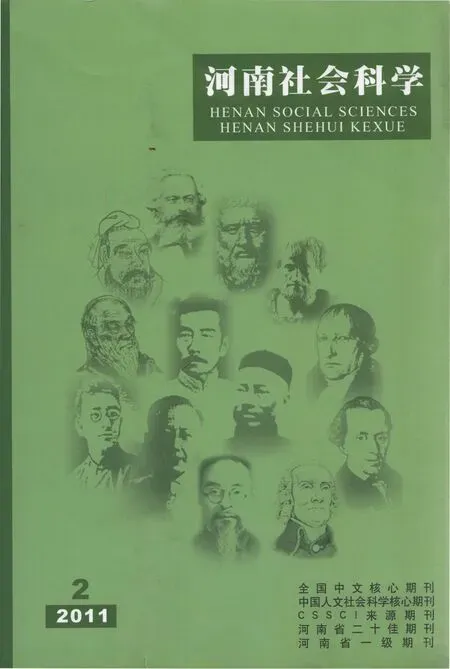钟嵘《诗品》以“品”评诗渊源考
李天道,刘晓萍
(1.四川师范大学,四川 成都 610066;
2.四川大学,四川 成都 610064)
钟嵘《诗品》以“品”评诗渊源考
李天道1,刘晓萍2
(1.四川师范大学,四川 成都 610066;
2.四川大学,四川 成都 610064)
有学者认为,《诗品》以“品”论诗的批评方法,其渊源应该是《汉书·艺文志·诗赋略》的“以品论赋”。笔者认为,这一说法,未免有失精准。应该说,钟嵘的分“品”比较、以“品”评诗的方法的生成根源有多种,究其主要看,既根植于古代文化学术传统,又是当时人物品藻方法与潮流影响的产物。
诗品;品;文化学术传统;人物品藻
一
据《梁书·钟嵘传》、《南史·丘迟传》的记载和隋刘善经《四声论》(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引)、初唐卢照邻《南阳公集序》、唐林宝《元和姓纂》等称引,《诗品》又名《诗评》。如《隋书·经籍志》云:“《诗评》三卷,钟嵘撰。或曰《诗品》。”唐、宋多用《诗评》,宋以后,往往正史艺文志系统称《诗评》,目录学系统和丛书系统称《诗品》,诗话系统则二名混用。由于文化传播方式和流传系统的原因,以及目录学和丛书文化的发展,后世学者遵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尤袤《遂初堂书目》和《吟窗杂录》、《山堂群书考索》的习惯,多称《诗品》。《诗品》所论的范围主要是五言诗。全书共“品”评了两汉至梁代的诗人一百二十二人,计上品十一人,中品三十九人,下品七十二人,把入选的一百二十二人分上、中、下三个等级,以“三品升降”显现优劣。应该说,钟嵘的《诗品》是在刘勰《文心雕龙》以后出现的第一部以“品”评诗的诗学专著。近有学者认为:“《诗品》以品论诗,实渊源于《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以品论赋。”[1]笔者认为,这一说法,未免有失精准。应该说,钟嵘的分“品”比较、以“品”评诗的方法,既根植于古代文化学术传统,又是当时人物品藻潮流影响的产物。为此,这里特就钟嵘以“品”评诗方法的渊源作一考证。
二
在《诗品序》里,钟嵘明言自己的分“品”比较、以“品”评诗方法,来源于“九品论人,七略裁士”。所谓“九品论人”指班固的《汉书·古今人名表》九品论人法,而“七略裁士”则指刘歆的《七略》叙述历代学术源流、追溯士人风格渊源法。
品,其原初义域为物品、物件。所以钟嵘以“品”评诗方法来源之一的“九品论人”与中国古代以“品”论物的传统分不开。在中国古代,很早就有“三品”之说,以分“品”论物。如《周易·巽》云:“六四:悔亡,田获三品。”高亨注云:“品,种也。……行猎将得三种猎物。”又如《尚书·禹贡》云:“厥贡惟金三品。”孔安国传云:“金、银、铜也。”孔颖达疏云:“郑玄以为铜三色也。”《太平广记》卷四○一引宋孙光宪《北梦琐言》云:“巴巫间,民多积黄金,每有聚会,即于席上列三品,以夸尚之。”这些地方所谓的“三品”,其义域为三种、三类。“品”又为等级、等第。《礼记·郊特牲》:“笾豆之荐,水土之品也。”《尚书·舜典》孔颖达疏云:“品,谓品秩也,一家之内尊卑之差。”《汉书·匈奴传上》颜师古注云:“品谓等差也。”《宋书·恩幸传序》:“刘毅所云‘下品无高门,上品无贱族’者也。”这些地方的“品”为地位的尊卑贵贱等差。又如刘向《说苑·政理》云:“政有三品: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强者之政胁之。”《后汉书·循吏传》云:“每于农月,亲度顷亩,分别肥瘠,差为三品。”《隋书·经籍志序》:“炀帝即位,秘阁之书,限写五十副本,分为三品:上品红琉璃轴,中品绀琉璃轴,下品漆轴。”这些地方所谓的“三品”,其义域则为三等级别,即将政绩、田亩、书分为上、中、下三等品级,以“品”评物。显然,这也应该是钟嵘以“品”评诗方法的文化渊源之一。
对人物进行“品”评,有时称为“品鉴”,有时称为“品藻”。就文献资料看,“品藻”一词最早应该出现在《汉书·扬雄传下》。其记载云:“仲尼之后,讫于汉道,德行颜、闵,股肱萧、曹,爰及名将尊卑之条,称述品藻。”对此,颜师古注云:“品藻者,定其差品及文质。”表明所谓“品藻”多针对人的节、品、格而言,以是非长短优劣好恶议事。《颜氏家训·涉务》云:“吾见世中文学之士,品藻古今,若指诸掌,及其试用,多无所堪。”这些地方所谓的“品藻”,就是排列评价、分析鉴别的意思。正由于此,所以即如刘知几在《史通·品藻篇》中指出:“夫能申藻镜,区别流品,使小人君子臭味得朋,上智下愚等差有序,则惩恶扬善,永肃将来,激浊扬清,郁为不朽者矣。”应该说,“品藻”是“世中文学之士”的活动,其目的是辨君子小人。
在中国古代,分“品”论人的传统由来已久。所谓辨小人、君子的以“品”评人在先秦就已经开始,如《诗经》即有“有匪君子,如金如锡,如圭如璧”之说。又如《国语·周语》中记载:“内官不过九御,外官不过九品。”这里的“品”为当官的等级。“品”又为人品。据《逸周书·太子晋》记载,周灵王的太子王子晋,名晋,字子乔,也叫太子晋,王子乔。其时,师旷出使周,赞誉太子晋说:“温恭敦敏,方德不改。”就称赞子晋性情温柔,人品厚道,不改常德[2]。又据《春秋左传注·文公元年》记载,初,楚成王想立商臣为太子,于是征求令尹子上的意见,对此,子上说:“君之齿未也,而又多爱。楚国之举,恒在小者。且是人也,蜂目而豺声,忍人也,不可立也。”这些材料虽然没有出现“品评”、“品藻”、“品鉴”之类的辞藻,但应该也是一种“定其差品及文质”的以“品”评人行为。又如春秋时期的孔子,就是本着当时的审美诉求以及审美标准,从“仁”、“礼”出发,提出了一系列考察和评品人物的品格和才能的方法,如非常有名的“孔门四科”,就是从“文、行、忠、信”四个方面,即德行、政事、文学、言语来品评人物与人才的。同时,孔子还以人的天赋禀性来品评人物,把人划为先天的、生来就“知之”和后天通过学习而“知之”,以及有了困惑而“学之”和有了困惑而“不学”等四类。应该说,这种根据先天禀性与后天习性将人划分为不同类别并针对不同类别分别加以品评的方法对后世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从语义看,“品鉴”与“品藻”都是对人物的精神、气质、风度、才学高下的评论,但两者还有所不同,“品鉴”侧重于才性方面的品评,而“品藻”则侧重用绮丽、优美的辞藻对人的气度风神进行评价。从历史上看,真正意义上的人物品评始自汉代。其时,人物品评已经蔚然成风。汉代在人才选拔方面采用“征辟”和“察举”两种途径。所谓察举,就是由州、郡等地方官,在自己管辖区内进行考察,发现统治阶级需要的人才,以“孝廉”、“茂才异等”、“贤良方正”等名目,推荐给中央政府,经过一定的考核,任以相应的官职;所谓征辟,是由皇帝或地方长官直接进行征聘。这中间就涉及乡间的鉴定和名士的品评。因为关系到士人的升迁提拔,所以这种选才途径受到整个社会的高度重视。到汉末、三国时期这种制度转变为盛行的诸子的谈论。这种诸子型的谈论带有非常浓郁的战国辩士之风,因此,无论是“品藻公卿”还是“激扬声名”,已经和汉代流行的以“孝廉”、“茂才异等”、“贤良方正”为标准、以温柔敦厚为行仪规范的人物品藻不同了。如刘劭《人物志》中对当时人物的品评标准就充斥了刑名法家思想,这应该是当时风气的一种写照。
对汉代人物品评记载得最为翔实的是班固《汉书》中的《古今人表》。班固在该《表》中把上古以来的历史人物分别以上中下等级归类,划入上上品、上中品、上下品、中上品、中中品、中下品、下上品、下中品、下下品等所谓“九品”。到延康元年(220年),汉献帝让位于曹丕。班固的这种对人物进行不同品级划分的方法得到朝廷的重视和进一步推广。朝廷采纳吏部尚书陈群所献的人才选拔策略,承续班固的人物品评法,将士人分别评定为“九品”,以此为基础,供朝廷选拔任用。为了更好地选拔人才,当时还在全国各地设专门进行人物品评的“中正”官。这就是中国人才选拔史上著名的“九品中正制”。这一制度沿袭和发展了东汉以来重观察而不重考试的人才品评方法。不过,在多数情况下,这种将人才分为“九品”的“中正品第”制度只是流于形式而已,并不作为士大夫入仕的主要选拔标准。
到魏晋时期,自给自足的封建大地主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各有其经济力量和政治军事力量的门阀世族的形成,东汉以来日趋僵化、烦琐的儒学影响不断削弱,使得统治阶级士大夫在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识上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生活上和思想上获得了过去所没有的一个相对独立自由的活动天地,文化不再只是朝廷进行伦理教化的工具了,而日益成为上层社会士大夫精神生活的重要部分。先秦以来特别是汉代后期,对个人的才能风貌的讲求以及对人生意义、价值的思索,都被不可分割地联系起来,使人的个性、爱好、趣味等等在封建制度所能容许的范围之内,第一次得到了真正的注意和重视。由此人物品藻也具有了全新的内容。这时的人物品评,逐渐发展为不仅仅是看人物的道德节操如何,而且十分重视才能、智慧、应变的本领等。到了晋代门阀世族大兴之后,人物品藻更演变为对人物的个性气质、风度才华的品评。从《世说新语》一书中可以明显地看到,这种品评不只是政治伦理的,而且更是审美的,后者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种情况深刻地影响到各门文艺和美学思想的发展,使得这一时期的美学思想经常从人的内在的个性、气质、天赋以及独特的心理感受等角度来观察审美与艺术问题,注重于人物的风采神韵。即如宗白华所指出的,中国美学的精神及其整个思想体系的建构,都应该是建立在“人物品藻”的基础之上的,所以中国美学乃是“出发于‘人物品藻’之美学”。中国美学有关“美”的概念、范畴、形容词等,都发源于对人格美的评赏。在宗白华看来,中国人对于人格美的爱赏渊源非常深远,而到魏晋时期,即“世说新语时代”,这种对人格美的爱赏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3]。
可以说,正是受“人物品藻”和对人格美追求的世风及其方法的影响,到六朝时期,人物品评和诗文思想的结合代替经学而成为生成诗文批评的主要途径,对作为审美意识形态的诗文思想的建构发生了重大影响。汉代以来依经学而产生的诗学理论转变为注重从创作者个体的才性出发的分“品”比较、以“品”评人的诗学批评。中国诗学批评的名著,钟嵘《诗品》之前的陆机《文赋》,同时的刘勰《文心雕龙》,应该说,都受品藻人物风气的影响。艺术批评方面,早于《诗品》的赵壹《非草书》、顾恺之《晋代胜流画赞》、谢赫《古画品录》,分品评论书画家;晚于《诗品》的梁庾肩吾《书品》,分三品评论书家,每品之中,又分三等,实际上是九品,与政治上的“九品中正制”正相吻合。此外梁阮孝绪的《高隐传》也分三品评古今高隐之士。可以说,分“品”批评,已是当时评论家的共识,是一种带有时代特征的批评方法。应该说,钟嵘《诗品》以“品”评诗的方法受此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三
钟嵘《诗品》这种分“品”比较的方法还受“七略裁士”,即刘歆的《七略》叙述历代学术源流、追溯诗人的风格渊源方法的影响。刘歆与其父刘向是西汉后期著名的古典文献专家和历史学家。从中国学术史看,刘歆和刘向父子的治学态度是所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即以历史的、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古代学术流派及其文化渊源,注重文献考据、辑佚辨伪,从纷繁复杂的文献之中理清线索,做出明晰的判断。他们注重全面地掌握文献,一方面广泛地收集遗书,一方面对存世典籍进行深入研究,因而其治学方法及其思想又具有学术规范的意义。其《七略》,特别是其中的《诸子略》,在学术思想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方法论上的引领性与规范性意义。根据《汉书·刘向传》的记载,汉成帝时,刘向受命负责校勘皇家馆藏的经书;刘歆则接受朝廷的诏书,与其父一同领校秘书,讲习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数术、方技等,涉及其时文化领域的方方面面,没有他们不考究的。班固《汉书·艺文志》记载,汉武帝时,要求天下的士人献书,到成帝时,朝廷又下诏,要求整个社会都搜寻“遗书”。并且下令,要刘向等人负责整理这些“遗书”。其时每一部书整理以后,刘向都要“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刘向死后,刘歆继承其父的遗业,总揽群书,并向朝廷进献他所撰写的《七略》,由此才“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由于历史变乱,刘歆所撰写的原本的《七略》已经散落,但其中的大部分则通过班固的《汉书·艺文志》承传下来。其基本内容仍然突出地体现了刘向刘歆父子的学术史思想。
按照刘氏父子的说法,《七略》对先秦至汉的学术流派和重要著作,大体均有著录,其著录过程就是一个“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过程,“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本着“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刘氏父子秉承司马迁父子的治史原则,从流派的角度来研究古代学术发展史,对古代的若干学术流派加以划分,分为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等十家。同时,在他们看来,这十家之中,小说只不过是一些街谈巷议、道听途说,缺乏真实性,不足为据,所以“君子”,即士大夫是不会写小说的,因此,“十家”之中只有九家是应该得到重视的。正由于此,才有所谓“诸子十家”其可以看的只不过“九家”之说。对此,班固特别在《汉书·叙传》中加以评论,强调指出:“秦人是灭,汉修其缺,刘向司籍,九流已别。爰着目录,略序洪烈。”也正因为此,后来则称古代学术流派为“十家九流”。
在经书中,刘氏父子对《易》特别推崇。他们不但把《易》列为“群经之首”,而且在《六艺略》中特别表明他们的学术史思想,认为《易》为“五经之原”。他们强调指出:《六艺》之中,《乐》主“和”,以之“和神”,为“仁之表也”;《诗》是用来规范言论的,以之“正言”,为“义之用也”;《礼》是用来“明体”的,“明者着见,故无训也”;《书》是用来“广听”的,为“知之术也”;《春秋》是用来“断事”,为“信之符也”。这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其中,“《易》为之原”。所以说,“《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也就是说,《易》是与天地为终始的。根据《汉书·五行志》的记载,他们的这种观点是有由来的,因为刘歆认为,远古时期的伏羲氏是秉承了“天”的意志而王,接受《河图》,以其为基础而画之,由此始有“八卦”;后来出现了洪灾,大禹治理洪水,获得《洛书》,法而陈之,由此才有《洪范》。刘歆指出:从前,“殷道弛,文王演《周易》;周道敝,孔子述《春秋》。则《乾坤》之阴阳,效《洪范》之咎征,天人之道粲然着矣”。也就是说,在他看来,五经以《易》为其本原,就是以“八卦”为《河图》,以《洪范》为《洛书》。可以说,刘歆是把《周易》、《洪范》和《春秋》都看做是讲天人之道等根本道理的经典著述。
正因为如此,刘氏在对诸子各家著述作评论时,喜欢引用《周易》“经文”与“传文”,以其作为评判各家各派学术思想的标准和依据。如就《七略》来看,其中的《六艺略》和《诸子略》就引征了八条《周易》的“经文”与“传文”,其余的引征了五条。比如:其中品评《易》引了《周易·系辞下》的“伏羲氏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评述《书》则引《周易》中的“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评论《礼》又引用了《周易》中所谓的“有夫妇父子君臣上下,礼义有所错”,评论道家学派则引用“《易》之谦谦”,评论法家学派又引用《周易》的“先王以明罚饬法”,评论天文者流则引《周易》所谓的“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评杂占者流则引《周易》的“占事知来”等等,不一而足。刘氏父子“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方法和思想显然影响到钟嵘,并成为其《诗品》以“品”评人、“裁士”方法的渊源之一。
按照钟嵘自己的说法,他的批评方法主要是“致流别,辨清浊,掎摭病利,显优劣”。所谓“致流别”,即追溯师承宗派、时代源流,实即区分诗歌的风格流派,追溯其渊源;“辨清浊”,在这里则指辨析不同流派及同一流派中风格的一致性和多样性;“掎摭病利”,主要指陈诗歌作品的利病得失;“显优劣”,则为评定诗人地位的优劣高低。几种方法交叉运用,同时出现,又互相交融,形成其“三品升降法”或分“品”评述法。
总之,钟嵘《诗品》以“品”评诗方法的渊源应该是多方面的,不应该简单化。
[1]李士彪.三品论赋——《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前三种分类遗意新说[J].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3):112—114.
[2]卢文晖.古小说辑佚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3]宗白华.宗白华全集(第2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
责任编辑宋淑芳
(E-mail:hnskssf@163.com)
I2
A
1007-905X(2011)02-0173-04
2010-12-2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8BZX068)
1.李天道(1951— ),男,四川彭州人,四川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2.刘晓萍(1981— ),女,四川彭山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