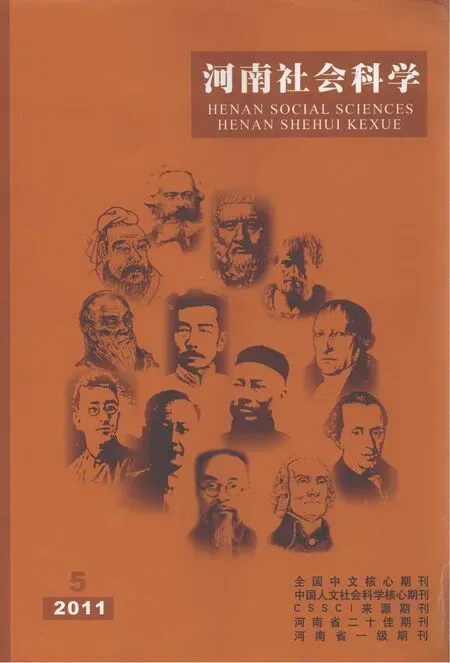文化—心理图式对创作的正负效应
夏 秀
(济南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022)
文化—心理图式对创作的正负效应
夏 秀
(济南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022)
文化—心理图式是积淀着特定文化蕴涵的心理结构,或者说是一种文化无意识。这种文化—心理图式影响着在特定文化中生存群体的思维方式、感知方式和情感模式。文化—心理图式对创作有重要影响:不仅影响着意象选择,还影响着叙述程式和特定主题的形成。文化—心理图式影响创作的方式有“化合式”和“模式化”两种方式。前一种方式会对创作产生正面效应,而后一种方式则会对创作形成负面影响。发挥文化—心理图式正面效应,规避其负面效应的方式的关键在于文学活动主体保持对于“文学”的自觉以及“创新”的自觉。
文化—心理图式;创作;正面效应;负面效应
人格心理学研究指出,为了有效地组织信息,以便灵活地适应外在世界,人类不得不寻找相对经济的方式分门别类地加工信息,而不是对信息进行单个处理。心理图式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种分类方式。研究者进而指出,人类处理信息过程既“有文化上共享的图式,也有个体特有的图式”[1]。我们这里所说的文化—心里图式是指积淀着特定文化蕴涵的心理结构,或者说是一种文化无意识。这种文化—心理图式影响着在特定文化中生存群体的思维方式、感知方式和情感模式。
在艺术创作中,文化—心理图式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不仅影响着创作者对意象的选择和人物的塑造,还在根本上制约着叙述程式的形成、主题的开掘,最终影响着作品意蕴的深浅、境界的高下。但是,文化—心理图式既有正面效应也有负面效应,对于创作来说也是如此。由于它主要是在无意识中发挥作用,让人难以察觉,所以充分认识文化—心理图式的效应并发挥其正面效应、抑制负面效应并非易事。
一、文化—心理图式影响创作的表现和方式
(一)文化—心理图式影响创作的表现
1.影响意象选择
比如中国文化和文学经常把伟人形容为“高山”或“大海”,而德国文化或文学则习惯于把伟人形容为“树”或“森林”。比如德国诗人赫尔曼·黑塞在文章中就曾这样写道:“树木是棵棵独立体,不同于那些这样或那样要避开自身弱点的隐居者,它们是个个孤寂的伟人,它们是贝多芬,是尼采。”而中国文学在赞美伟人时则与之不同,比如范仲淹这样赞美严子陵:“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严子陵祠堂记》)物象描写本身体现出文化选择。中、德文学中的这种差异源于两个民族不同的文化—心理图式。正因为中、德不同的文化精神,中、德作家才会在表达同样的思想时选择不同的物象。而不同的文化—心理图式最终来自中、德原住居民不同的生存环境。农耕文明使中国人更多地关注土地、山和水,而日耳曼民族早先在高原和森林地带的生存让他们更多关注树木和森林。
2.影响叙述程式
在文学,尤其是叙事文学中,在文化—心理图式影响下可能会形成相对比较固定的叙述结构或者人物关系结构。比如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由于男女授受不亲等传统礼教的影响,唐代以后的作品中凡涉及恋爱的主题,其中必会出现一个“红娘”角色,多由作品中小姐的丫鬟担任。
3.影响特定主题(主旨)的形成
这类主旨主要是指作品中相对稳定的、集中或者普遍存在的主题性倾向。每一种文化中都存在着重点关注的主题,比如中国文学,尤其是古典文学中,伤春、悲秋等主题比较普遍,而漂泊、冒险等则是西方文学中常见的主题。再比如爱与恨、生与死等与人类生存密切相关的问题,在各种文化的艺术中都有表现,但是表现形态、处理方式却各有不同。对这些主题的探讨不仅有助于把握处于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人们的审美心理、文化性格和精神形态,而且有助于从根本上理解不同文化系统中文学和艺术的同与异。
(二)文化—心理图式影响创作的方式
在艺术创作中,创作者的文化—心理图式的效应是巨大的,它既可以使作品思想深刻、内蕴厚重,也可能使作品平庸无奇、毫无新意。那么,如何发挥其正效应、避免负效应就成为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我们认为,这主要取决于既定的心理结构如何作用于创作者的心理状态和创作过程。
在创作活动中,既定的心理图式作用于创作者的方式是不同的。受同样的心理图式影响的艺术作品,有的风格突出,魅力四溢,但有的作品就表现平庸,乏善可陈。换言之,即便是蕴涵着丰富文化底蕴的文化—心理图式也不是创作的灵丹妙药,其中的文化韵味能否呈现关键在于创作者如何接受既定心理图式的影响。
从方式和效果角度,可以将文化—心理图式作用于创作的方式分为两类:一类是在既有文化—心理图式影响下充分发挥个体能动性,将个体的禀赋、体悟、经验融汇到创作中,即在判断和分析有关问题或者现象时,主体不是完全受既有思维模式或者感知方式制约的,他会自觉地融合自己的感悟、体验对社会、人生、宇宙进行思考。在这种情况下,主体对问题的判断和处理往往会受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同时又具有创作者自己的个性特征,从而显示出独特的审美韵味,我们姑且称之为“化合式”。另一类则是完全运用既有文化—心理图式“机械地”、“自动地”解决问题,我们称之为“模式化”方式。在“模式化”的作用方式下,作品毫无创新可言。更为严重的是,如果作者的思维方式已经固化,那么他对于作品所涉及的某些社会现象或问题的认识就可能是落后于时代发展的,因而呈现出庸俗化的倾向。这种作用方式既无益于审美特性和价值的呈现,也无益于对社会、个体的深刻认识,基本上是无意义的。
二、文化—心理图式对创作的正面效应
文化—心理图式对创作的效应因其作用方式的不同而不同。“化合式”能够有效地避免“个体化”创作意蕴浅薄的弊端,使作品意蕴厚重深刻,从而有效地推动文学的发展;“程式化”方式则易于使创作流于模式,拘泥于旧有思想框架、旧的思维方式,既可能削弱作品的思想深度,也可能影响到作品自身的现实主义力度。
(一)成就作品之美
首先,在特定文化—心理图式的影响下,创作者对于意象的选择或者对于主题的开掘等有助于形成作品意义的“张力”,增添作品的魅力。心理图式中蕴涵着特定的文化积淀,这些埋藏在人的深层心理结构中的文化因素对于人的影响是持久的,同时也最容易激发人们的深沉情感。美国学者拉里.A.萨莫瓦尔和理查德·E.波特在其《跨文化交流》一书中曾经集中论述过深层心理结构的特点。他们指出,人类感受最深的就是潜藏在心底的深层结构规范,深层结构规范以及由这些规范所产生出来的内容能激起人们心底的激情[2]。换句话说,对于具有适当文化背景的“合格的读者”来说,特定的心理图式就好比是催化剂,能激发起阅读者的特定情感,并以此为契机把与某一图式有关的作品连成一体,丰富作品的内涵和层次。这就是美国现代诗人、文学批评家艾伦·退特所谓的“张力”,也是我国古文论所言“味无穷而炙愈出,钻弥坚而酌不竭”[3]的原因。
文化—心理图式的这一效应揭示了一个原理:只有真正反映了人类那些带有普遍性的美好本性的作品才可以持久,才会具有永久的魅力。当我们从这一角度去反观那些一直影响着读者并使读者向往其所描述世界的作品时,我们就会发现其中蕴涵了很多触及我们人类美好本性的结构性因素,正是这些因素使作品经受住了时间的磨洗,避免了意识形态的淘蚀,影响、引导着一代代的读者。
其次,在创作过程中恰当运用图式性因素有助于表达特定的情感和意义。关于这一点,德国理论家莱辛有过精彩的表述,他说:“诗人如果运用熟悉的故事和熟悉的人物,就是抢先走了一大步。这样,他就可以放过许多枯燥的细节,而在不是用熟悉的故事和人物时,这些细节对于全体的了解就是不能放过的;诗人能愈快地使听众了解,也就能愈快地引起听众的兴趣。”[4]我国古代也有类似的说法,比如“此种结构,不必多费笔墨,固已意无不达”[5]等。图式性要素之所以有如此神奇的功能,是因为在特定文化中所形成的图式性要素具有类似于“符号”的性质,特定的“符号”能够表达特定的含义,因此,在一定语境中,我们倾向于选择用这一种方式而不是其他的方式来反映或表达某些特定含义。对于熟悉某一特定图式要素的人来说,“图式”具有情感的再生性,它能有效地把特定的情感和唤起这种情感的刺激联系起来。特定的心理图式性要素具有与图腾类似的作用,其价值就在于唤起创作者或者接受者的情感,帮助我们在一种既是理性的又是情感的方式中去把握整个的意义,从而获得比具体的符号本身更丰富更全面的意义。
(二)有效地避免个体化创作的肤浅和琐碎
在特定文化—心理图式影响下的文学要素,比如意象、场景、人物等——我们姑且称之为“图式性要素”——是文学中具有相对稳定性的形式性因素。对于常变常新的艺术来说,这种稳定性显然是具有局限性的,但也有其积极的意义。
首先,作品中的“图式性要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作品的厚重感。从人类精神的塑造层面看,肤浅的创作是没有多少意义的,它除了造成作家才情的浪费之外,不会给接受者包括创作者自身精神和心灵以滋养和提升。因此衡量一个作家成就的大小,主要应该看其创作在多大程度上触动了接受者——一个民族甚至整个人类——的神经。而蕴涵特定文化内涵的图式性要素,大多是与人类为何生存、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等终极追问有关的,因此对作家来说,把握住了民族内在的文化—心理图式,也就把握住了社会群体的心理,这将为作家个体的变新求异奠定坚实的基础,使刻意锐变的现代作家的作品因此显得内蕴丰厚、深刻,而不至于轻飘、肤浅,流传不远。从长远看,具有持久感染力和生命力的创作必然是以关注群体人类的生存与命运为己任的。比如《红楼梦》的长久流行就是因为它所表现的不是个人的悲喜和单个人的命运。《红楼梦》流传不衰的案例正说明了作品内蕴深厚的重要性所在,任何一部作品若要经久不衰就必须努力去揭示人的深层精神世界,反映人的至真性情和至深人性,而这恰恰是特定文化—心理图式的优势所在。
其次,对文化—心理图式的“化合式”运用还可以使创作有效地避免陷入琐碎叙事与自我感动的泥淖。诚如上述,特定心理图式是在特定民族文化甚至所有人类共有情感影响下而形成的,其中所蕴涵的特定反应方式,比如审美观念、情感表达方式等,往往能够触动特定“群体”的审美心理,进而引发该群体对于历史与现实、自然与社会、人生与宇宙等问题的追问。如此这般广泛、深邃的内涵,使那些仅仅拘泥于个人琐碎生活的窃窃私语或者沉湎于个人悲欢的个体化写作、身体写作不能望其项背。
关于作家要避免琐碎叙事或作品要有深厚内涵这一观点,许多学者有精辟的论述。比如美国人类学者李亦园曾经说,一个文学家成功与否的一项重要标准就是“他能否体会出并道出一个民族的心声,而一个真正伟大的文学家,不但能道出民族的心声,而且是敢在横逆的境遇下冒着生命的危险道出民族的心声”。李亦园更进一步指出,不仅一个民族有共同的心声,而且整个人类因为同为一个种属并共享着文化创造这一种属的特性,因此也拥有着共同的理想。作家需要用象征的手法表达属于人类的共同理想。不朽的文学家,一个世界性的文学家,“应该是一个真正能道出人类共同理想的文学家”[6]。
诸多经典艺术范例已经证明:创作应反映宽广和深厚的社会生活,要反映出深层的人类情感。这对于我们目前诸多拘泥于个体经验展示的创作等现象来说是不乏警示意义的。
(三)有助于形成独特的创作风格
特定的文化—心理图式性要素的运用还有助于形成特定的创作风格。诚如上述,当心理图式在作品中是以“化合式”呈现时,主体会不自觉地在特定意象或者主题中融入自己的独特体悟和经验,同时,文化—心理图式也会潜在地影响主体的感知,并在一定程度上规约主体对事物的认识,从而形成独特的风格。以沈从文先生的创作为例。沈从文的作品中最常见的一个意象是“水”。“水”不仅是他作品中人物的活动场所和行文背景,也影响着他作品中人物的性格,最终形成了他自己的带有“水”的忧郁、柔韧、柔美、宽容的独特风格。
“水”不仅成为沈从文写作的背景,影响了其独特风格的形成,还因为水那天生的“阻隔”功能,引发了作家对诸多问题的深刻思考和细腻体验,进而影响了他的思想的形成。沈从文自己解释说:“我有我自己的生活与思想,可以说是皆从孤独得来的。我的教育,也是从孤独中得来的。然而这点孤独,与水不能分开。”[7]按照沈从文的说法,他的作品的特性及个体体悟几乎全得自“水”给予他的孤独,因为在很多时候,“水”给了他隔绝与外在世界联系的机会,留给他与自己内心相遇的空间,容许他的想象自由地发挥。
当然,把一个作家独树一帜的风格全部归因于某一独特的图式要素的塑造作用显然失之简单,但总的来看,沈从文的作品风格确实与“水”意象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水”意象与生命有着天然关联,同时又具有柔美、坚韧又略显忧郁的象征意义,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作家文化—心理图式的形成。既有心理图式中对“水”意象的理解与自我独特的经历、气质相契合融汇,最终形成了作家忧郁、柔韧又柔美的独特风格。
由此可见,心理图式独特的情感场和同化力确实对创作风格起着一定的塑造作用。心理图式中所积淀的特定的情感方式、感知方式和情绪色彩若能够与作家独特的个性气质相契合,就可能形成相对稳定的搭配,一再出现在作家的创作中。对于富有创造力的作家来说,心理图式的功能在于启发作家向一个更深入的层次去思考、探索,并将这种思考和探索体现在创作中,从而使作品呈现新的面貌。
以上我们主要讨论了心理图式对于创作的正面效应。不过当我们强调心理图式对于创作的重要意义时,必须注意的问题是不能过分夸大它的作用。原因主要在于:心理图式到底在什么程度以及在什么层面上构建着创作的深层心理,目前尚未有充分研究。而有关心理学研究发现,在实践中,过去的事件究竟能不能起作用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起作用,取决于行动当时的“知觉野”:所有的行为都是行为者在行为当时的“知觉野”的产物。所有过去的、现在的以及将来的信息与观念,都只有呈现在当时的“知觉野”中方可对行为有所影响。正因为此,也有心理学研究者倾向于认为,在具体的行为过程中,过去的事件只起着间接的作用。有学者明确论述说:“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有人的组织和环境之心理的性质,据实验所示,绝对有赖于已往的历史。但在动的心理学之内,已往历史的影响应视为间接的:根据体系的因果关系,过去的事件不能影响现在的事件。历史的因果链的交织造成目前的情境,过去的事件只能在这种因果链中占据一个位置。”[8]若根据这个原理去看待我们所讨论的心理图式对于创作的效应问题,结论就是:心理图式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创作,取决于心理图式能否出现在作家创作时的“知觉野”,以及在“知觉野”中的清晰程度和所占比重。因此我们不能片面夸大心理图式的作用。
三、文化—心理图式对创作的负面效应
当文化—心理图式以“程式化”方式对创作发挥作用时,它不仅起不到应有的正面效应,而且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可能导致创作“程式化”
在一些特殊情形下,特定文化—心理图式可能成为实实在在的模式或框架,使创作缺少创新性,也缺乏足够的吸引力。
1.当创作者失去对生存的“原初感受性”,过于遵循固有的反应“图式”时
既定的文化—心理图式不可避免地带有“模式性”、“结构性”的特征,具有一定的倾向性和稳定性。这难免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创作者对事物或问题的认识。
现代心理学研究发现,心理图式在有利于认知的同时,也会影响人们对事物具体特征的感知和把握,损伤人敏锐的感觉能力。美国俄亥俄大学认知科学中心的科学家进行的一项最新研究显示,成年人记忆虚构动物图片的能力要高于对他们所熟悉的真实动物图片的记忆。这项研究的负责人弗拉迪米尔·斯洛特斯基说,逐字逐句地记忆通常是初学者专有的特征,随着人们越来越聪明,他们会将一些已知事项放入分类目录中,于是就会失去对事物个别差异的准确记忆。这种分类帮助人们记忆和认识事物,但是研究者也发现它们会导致人们忽略一些个别的细节,而且不恰当地分类还会养成墨守成规的坏习惯[9]。
因此,虽然反应的程式化体现了人类生存的“经济原则”,但是这种反应的程式化对创作而言却是有害的。对于创作来说,当某一特定文化—心理图式固定化为认知模式或形成思维定势时,创作者如果不自觉地保持积极求索的心态,也不进行有利于保持思维流畅性的训练以保持灵活、丰富的神经刺激反应的话,心理图式就有可能成为创造的桎梏,束缚创作者的创作。
我们认为,当文化—心理图式失去对现实的超越性,变成对日常现实的程式性反应时,它就已经变成人的思维的束缚,对于创新性思维来说有害无利。这种束缚反映在创作上,主要将导致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若从作品形式上考察,主要表现为作品雷同,失去个性。比如20世纪80年代末获得较高评价、反映农村经济改革的三部作品——《老人仓》、《秋天的愤怒》和《苍生》,不约而同地采用了“才子佳人”的人物结构模式和“清官”原型。这不仅使得这三部作品显得脱离实际,缺乏说服力,而且极易让人联想起中国文学史上众多采用类似结构的作品,从而“产生某种程度的平庸陈旧感与腻烦心理”[10]。二是,若在深层次上对作品价值进行考察,我们就会发现该类作品对重大社会问题往往采取套式化解决思路,缺乏对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和批评性解决的能力。比如当代“反腐败”小说中的“清官”叙述模式,就是把复杂的“反腐败”问题人为地让一个或几个“清官”去解决掉,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和批判的深度,也减弱了作品直面现实的力度。
2.在特定心理图式影响下,某些特定意象的表现方式由隐喻或象征变成“借喻”时
所谓借喻不过是“咏妇人者,必借花为喻,咏花者,必借妇人为喻”,作品的内涵和外延没有扩大,也没有缩小,意义没有增减变化,对人的联想或想象起不到新的激发作用。这类意象的效应仅仅在于传达一种明确的意义,不具有更多的包容性或者统摄性,缺乏意义的“张力”。
在文化—心理图式影响下形成的某种定势,影响着我们的信仰、选择、情感,也影响着我们的行动所表示的意义,相应地,在文学创作活动中则主要表现为影响作者的选材、立意、价值取向等。如果对心理图式的这种定势作用缺乏警惕,创作者就可能在无意中因循传统,沉溺于惯性思维,影响想象力和创造力。就中国文学,尤其是古典文学来说,这一点是很突出的。
由于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限制以及特殊的人才选拔制度,中国古典文学的创作者首先是接受主体,其创作正如同欣赏时那样,每一次都在不同程度地重温、感受着以往阅读的经验。饱读诗书的中国文人,其艺术感受的过程即伴随着对前代经典、精品的尊崇。因而在其创作冲动时精神形态的运动,免不了在某个或某几个“主题”河床中行进,带有着“原型模”的印痕[11]。心理图式的这种制约作用使得中国的古典文学在主题或选材上比较集中,也略显单调。
在现当代文学创作中,也存在惯性思维过于强大、创造力和想象力匮乏的问题。作家李贯通称这种现象为“失语”。他在谈到山东作家的创作状态时指出,山东作家的“作品比较注重对现实的关注,讲求当代精神和对传统文化的承继,作品崇尚厚重,膜拜宏大叙事,溺于惯性思维,经验至上,超验苍白。没有完全从‘失语’状态中解放出来”[12]。实际上,缺乏想象力和失语的问题并不仅仅是山东作家的问题,这种状况在其他作家身上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概而言之,如果不能自觉地和有意识地与思维定势相抗衡的话,那么在创作过程中,心理图式就有可能形成心理定势,成为创作的桎梏。
(二)文化—心理图式有可能导致创作“庸俗化”
文化—心理图式对于创作的负面效应除了有可能导致创作程式化、缺乏创造性以外,还可能导致创作“庸俗化”。
文化—心理图式是特定环境和文化的产物,在其诞生之时可能具有其合理性,但在事过境迁之后,其中所蕴涵的精神可能已经落伍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在创作中意识不到这点,就可能造成作品违背时代潮流、思想僵化落伍的情况。
我们还必须关注的一个现象就是,蕴涵了同样意蕴的作品有些能给我们带来审美的愉悦,有些却只能算是概念化的图解,毫无趣味,原因何在呢?对此我们认为,即便是在创作中运用了特定的文化要素,某一部作品要成为经典的话也还需要作者驾驭文字的能力、巧妙构思的能力等。如果不具备一定的文学能力,即便是创作中有图式性成分恐怕也无法给人们带去审美的愉悦。
在创作中,我们要努力发挥文化—心理图式对于创作的正面影响,避免其负面影响。也就是说要实现心理图式对创作的“化合式”影响。努力的关键在于文学活动主体要保持对于“文学”的自觉以及“创新”的自觉。具体的文学创作活动主要表现为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一是规避公共价值,注重个体的精神价值,专注体验生命感受,留心内心体悟。二是有意识地用专属于艺术的表现形式去表达真切的生命感受。因为艺术的目的本来就是要“传达对某一事物的即时感受,就像这种感受是亲眼看到的,而不是所认同的;艺术手段就是使事物陌生化(的)手段,就是阻碍形式手段,这一手段增加了感知的难度和时间,就像在艺术中,感知过程是自我导向的,必须得到延长一样”[13]。
[1][美]珀文LA.人格科学[M].周榕,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98.
[2]LarryA.Samovarand RichardE.Porter.Com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M].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4.83.
[3][清]何文焕.历代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1.499.
[4][德]莱辛·拉奥孔[M].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67.
[5]王弈清,唐圭璋.词话丛编(第4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3788.
[6]吴光正.中国古代小说的原型与母题(序言)[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7]沈从文.抽象的抒情[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246.
[9]晓健.知识多了伤记忆力[N].齐鲁晚报,2005-05-27(4).
[10]杨守森.审美本体否定论[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59—60.
[11]王立.中国古代文学十大主题——原型与流变[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0.18.
[12]倪自放,张颖.李贯通:清醒的幻象创造者[N].齐鲁晚报,2004-12-06(6).
[13][荷兰]杜威·佛克马.关于比较文学研究的九个命题和三条建议[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4):55—60.
IO5
A
1007-905X(2011)05-0126-04
2011-04-10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08DWXJ10)
夏秀(1973— ),女,山东青岛人,济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西方文论、文艺传播理论研究。
责任编辑 宋淑芳
(E-mail:hnskssf@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