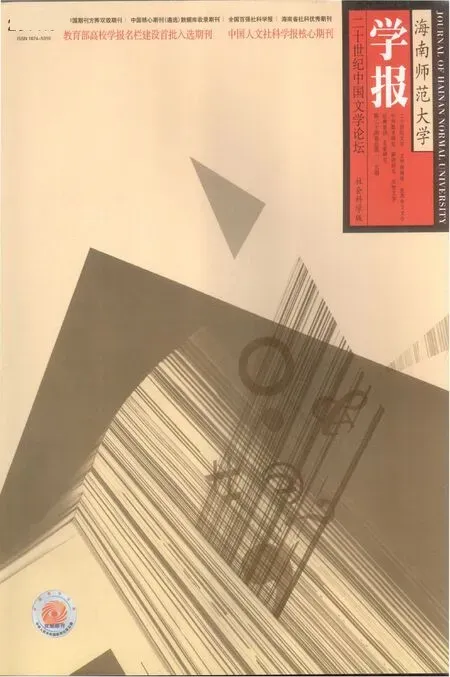郑和形象建构与中国—东南亚国家关系发展
施雪琴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福建厦门 361005)
郑和形象建构与中国—东南亚国家关系发展
施雪琴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福建厦门 361005)
作为中国历史上的航海先驱与外交使臣,郑和所包含的社会文化意义与政治意义已经远远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从社会与文化层面看,在东南亚华人社会,郑和被广泛神化,并演变成为在东南亚华人社会长期流传的“郑和崇拜”,成为凝聚华人社会的粘合剂与强化华人族群文化意识的一种象征。从国家政治层面看,郑和形象的塑造与中国-东南亚关系发展整合在一起,成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发展的纽带与推动力量。东南亚华人社会以及中国对郑和形象的塑造与强化,不仅反映了“文化郑和”在民间社会作为信仰与文化的价值与功能,更凸显了“文化郑和”在新时期中国-东南亚关系中的规范塑造与价值取向方面的角色与影响。
文化郑和;中国-东南亚关系;价值取向
前言
与中国传统的民间信仰相同,东南亚华侨社会传统的民间宗教信仰中不乏从真实的历史事件中演化出来的神祗,如被东南亚华侨华人普遍奉祀的关圣大帝、妈祖、清水祖师、保生大帝、广泽尊王、开漳圣王等,都是真实的历史人物。这些源于中国传统的民间信仰在东南亚华侨社会中的移植与延续,一方面反映了海外华侨华人祈求神灵保佑、消灾纳福的宗教心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海外华侨华人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勇武、慈爱、仁善与孝顺等价值观的认同与继承。这种将历史上的英雄人物神化的现象实质上是一种个人崇拜的极端形式。个人崇拜是人类文明诞生以来普遍存在的社会历史现象,它是将英雄人物神圣化,并将自己的希望、情感、敬慕都付之于崇拜对象。它一般由某个社会群体(或者全社会)共同参与,崇拜者通过利用一些手段、如修建庙宇、举行仪式活动、尊奉遗迹遗址、编撰神话传说等来巩固和强化自己对崇拜对象的虔诚与信仰,并逐渐演变成为一种宗教力量来维护崇拜对象的权威。东南亚华侨华人社会的“郑和崇拜”也是这种从对郑和的个人崇拜发展演变成为信仰崇拜的一个实例。郑和作为封建政府的钦差,他在东南亚的一系列外交活动不仅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与东南亚友好睦邻关系的发展,而且也为广大东南亚华侨在当地创造了一个比较良好的生存发展环境,客观上推动了东南亚华侨社会的发展。因此,东南亚华侨社会的郑和崇拜,从根本上看是对郑和这种历史功德的缅怀和个人英雄行为的崇拜。从文化人类学视野来看,郑和作为一种信仰符号,同东南亚华侨社会其它民间信仰一样,具有整合移民族群、团体与社区以及延续与巩固华人文化认同的功能,成为凝聚华侨社会的粘合剂与强化华人族群文化意识的一种象征。此外,值得指出的是,民间信仰在本质上是下层民众的社会文化心理在宗教上的聚合与反映,同中国传统的民间信仰相同,东南亚华侨华人社会的民间信仰基本分为两类,一类是奉祀本乡本土的神灵,如在海外闽粤移民社群中盛行的大伯公与妈祖等乡土神灵;另一类是中国民间普遍奉祀的神祗,如关帝、观音与玉皇大帝等神灵。而郑和崇拜作为一种流传于东南亚华侨社会的民间信仰,它既不同于闽粤华侨的乡土之神,也不是中国民间普遍奉祀的神灵。它是由华侨在东南亚本土塑造的神灵。早期华侨通过神化具有朝廷使臣、航海家、军事家、政治家与外交家等多种身份的郑和,显示出华侨的民间宗教信仰已经突破了乡土界限,也超越了对中华文化传统价值观的肯定与认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早期华侨的故国情结以及渴望得到封建国家保护的心理。而在国家层面上,有关郑和话语的建构往往与国家形象联系在一起。“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宣德化而柔远人”,“颁中华正朔,宣扬文教”等均显示出郑和话语的国家意义。因此,从社会层面看,郑和崇拜是华人移民文化与社会心理认同的聚合与反映,从国家层面看,郑和崇拜奠定了近代以来中国与东南亚交往的方式以及中国与东南亚关系的基础。而且随着近年来中国与东南亚关系的不断深化,郑和崇拜已经超越华人社会与文化层面,成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发展的纽带与推动力量。可以说,近年来,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郑和崇拜不断在社会(族群)交往、学术交流与国家关系语境中被升华与强化,这凸显出郑和崇拜在中国与东南亚交往中角色及其功能的拓展与嬗变,从族群认同的文化领域延伸到学术话语以及国家关系的政治范畴。国家对郑和话语的强化与升华,不仅折射了新时期中国-东南亚关系的新变化,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崛起中的中国及其外交政策的价值观定位与认同,郑和所体现出的海洋开放意识、开拓精神、和平、包容与尊重对新时期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发展不乏积极而深远的意义。
一 东南亚华侨社会郑和崇拜的建构
一百多年前,中国现代史学的先驱梁启超先生就在其《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一文中充分肯定了郑和的航海伟绩,指出“全世界历史上所号称航海伟人,能与并肩者,何其寡也。”郑和作为中国海洋发展史、乃至世界航海史上的一大伟人,七下西洋,足迹远至非洲东海岸,并多次途经并访问了现今东南亚的越南、柬埔寨、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文莱、等国的一些地区。郑和的西洋之行,一方面,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睦邻友好关系,传播了中华文明,推动了南洋各地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另一方面,对东南亚华侨社会的发展也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今天的东南亚,有许多与郑和有关的山水、建筑与寺庙,记载了郑和当年的足迹与活动,人们在这些山水、建筑与寺庙的前面加上郑和的小名“三保”,(又称“三宝”)便形成了今天东南亚华侨社会的一道独特的文化人文景观。东南亚华侨社会的郑和崇拜主要体现在把郑和物化与神化两个方面。
首先,郑和船队留下的遗迹与遗址上发展起来的山水、建筑与城市是东南亚华侨社会郑和崇拜的物化形式,如马来西亚马六甲的三宝山、三宝井;印度尼西亚中爪哇省省会三宝垄及其附近的三宝港、三宝洞与三宝墩,泰国境内的三宝港、三宝塔等。这些与郑和有关的山水、建筑与城市记载了郑和船队当年的活动,是郑和崇拜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虽然这种纪念与缅怀表明东南亚华侨对郑和的崇拜还停留在对历史人物的敬慕与纪念的层次上,没有上升到神灵崇拜的高度,但这些古迹往往被华侨赋予了灵性,也成为人们膜拜祈求的对象。如1742年,三宝垄的华人在三保洞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庆祝会,以表示感谢三保大人保佑他们能够在此地安居乐业、生意日益兴隆的恩德。并且还对三保洞进行修葺。后来,每逢阴历初一、十五,很多华人前来烧香礼拜,而且还捐献维修三保洞的费用。[1]
第二,东南亚各国华侨为了纪念郑和而广泛修建的三宝庙与三宝寺不仅是郑和崇拜的物化标志,更是华侨神化郑和的一个重要象征。东南亚有许多奉祀郑和的寺庙,如马来西亚马六甲、吉隆坡、槟榔屿、沙捞越、丁加奴,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岛、邦加岛、爪哇岛,泰国的曼谷、大城,以及柬埔寨、文莱等国,都兴建有三宝庙、三宝宫、三宝禅寺、三宝塔等。建于1795年的马六甲三宝山的三宝亭,曾供奉有郑和的神位,与福德正神(大伯公)和妈祖并立。三宝寺庙在东南亚地区的广泛建立和郑和神位的出现,说明郑和在东南亚华侨移民中的形象已经发生转变,从历史人物转变成为具有超自然能力的保护神,甚至与东南亚华侨信奉的航海女神妈祖并列。郑和形象的这种演变是华侨对郑和的神化。而这种神化,有助于郑和崇拜的延续和强化,也推动了郑和信仰在东南亚的传播与发展。郑和形象的转变与神化,使得郑和在东南亚颇受尊重。如许云樵在《三宝公在南洋的传说》一文中所说那样:“华侨的信仰三宝公,的确较国内吃食店之敬关公,读书人的尊孔子,尤为热烈。他的地位,简直可以和基督教的耶稣,回教的谟罕默德相当,几成为一个宗教主了;所以在传说中,他是法力无边,万物听命的。”[2]94东南亚华侨对郑和的敬畏甚至发展到可笑荒谬的程度,“大抵凡事物之不明其理者,不曰三保公所教,则称三保公所为,敬信之深,于此可见矣。此种信心,牢不可破。甚有谓三保公圣口者,好害凭其言。”[2]94
第三,东南亚华侨社会一些已经形成并固化的节日与民俗仪式对延续与强化郑和崇拜有重要的意义。如印尼爪哇华侨每逢中国农历六月三十日都要举行盛大的祭祀郑和的迎神出巡庆祝活动,该节日是纪念郑和船队首次在爪哇登陆。活动期间,人们抬着郑和的神像,一路锣鼓喧天,爆竹齐鸣,人山人海,热闹非凡。马来西亚丁加奴每年农历六月二十九也要举办盛大的庆祝活动来纪念郑和的诞辰。文化人类学通常将仪式界定为象征性的、表演性的一整套行为方式,具有强化秩序与整合社会的功能。东南亚华侨社会这些固化的纪念郑和的活动与仪式,一方面有助于强化郑和的神圣地位,另一方面也借助华人对郑和的崇拜来加强华人族群文化意识的认同,增强华侨社会的凝聚力。
第四,东南亚华侨神化郑和还体现在东南亚各地盛行的关于郑和的灵迹传说。在东南亚华侨社会,有许多与郑和有关的神话传说,如关于三指鱼的传说、暹罗北大年卧佛的传说、豆芽变巫文的传说、印尼邦加岛脚印的传说、马来虎叫声的传说、大鲸鱼迎宝船的传说、榴莲果的传说等。此外,还有一些与郑和有关的民俗习惯与禁忌,如水浴(牛尿)治病、禁食节、烧稻草作肥料、火葬等,以及在华侨航海者中广为流传的一种汲天方井水藏于船边以备降风浪等风俗在东南亚华侨社会中也得到保持与延续。这些灵迹传说虽然是一种宗教幻想,但郑和崇拜的“生活化”与“民俗化”却有助于郑和崇拜在东南亚华侨社会的延续,因为“与‘文化创造物’的制度不同,民间宗教一类的‘传统’的继承,更重要的是植根于普通百姓一代又一代的日常生活经历中的‘言传身教’,……来自于‘非制度化’的家庭与社区内部的‘耳濡目染’。”[3]
二 郑和崇拜产生的社会文化心理
民间信仰是普通大众社会文化心理的长期积淀,它的形成有深刻的历史文化与社会经济等方面的根源。郑和崇拜在东南亚华侨社会的生成和发展,是华侨社会文化心理的集体反映与聚合。早期华侨出海,须得乘槎浮海,跨越大洋,生命维系于茫茫无际的惊涛骇浪中,只能在冥冥之中祈求神灵保护,这也是郑和崇拜产生的一个根本原因。正如克劳福所言:“在无知识的人民当中,三宝公显然是一个有魅力的名字。传说当其国人在异地旅途中遭受危险时,他曾加以救援。这种奇迹是虚构的奇事,它明显说明了神话起源的一个因素。”[4]所以,华侨对郑和神性的塑造,如同对其它民间神灵的奉祀一样,反映了华侨祈求旅途平安、希望神灵保护的心理。但同其它民间信仰的不同,郑和崇拜在东南亚华侨社会的产生还有特殊的历史文化因素。
第一,郑和七下西洋推动了东南亚华侨社会的发展。郑和下西洋为东南亚的华侨移民营造了良好的生存与发展环境。自古以来,中国人移居海外,都是自发移民,有的为生计所迫而流寓海外,有的为逃避战乱而流落异邦,没有祖国的保护,不仅要与严酷、陌生的自然环境作斗争,而且还时常遭受当地统治者的凌辱与虐待,苦不堪言。但郑和船队“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其浩大气势与“二万七八千人”的精锐部队,不仅迅速结束了东南亚国家之间的纠纷与动乱,平定了骚扰海上贸易的匪盗海贼,而且显示了华侨祖国的强大威力,足以对东南亚各国形成强大的威慑力,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改善华侨被欺负、凌辱的地位,为东南亚华侨的生存和发展创造了一个空前有利的国际环境。以至于在郑和下西洋之后的岁月里,一些郑和使团访问过的国家,如渤泥国,“凡见唐人至其国,甚有爱敬。有醉者则扶归家寝宿,以礼待之若故旧。”[5]在真腊国,“其见唐人,亦颇加敬畏,呼之曰‘佛’云。”“余观《通典》、《通考》、各代史、《异域志》诸书,所载未有如此之异者”[6]郑和在南洋各地访问时,郑和船队所到之处“宣德化而柔远人”,“颁中华正朔,宣扬文教”,以礼待人,尊重各国的主权与当地风俗,公平地进行经济贸易,传播中国先进的生产技术、医药方法、传播友谊、积德积善,深受南洋诸国人民敬佩。连印尼学者也认为,郑和下西洋的航海事业对促进南洋各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和对航海科学知识的充实等等,都作出了伟大的贡献。这样卓越的成就是“无可比拟的”。[7]因此郑和也受到南洋各国人民的爱戴。在东南亚各地原住民中,至今还也流传着许多与郑和有关的传说。如在印尼,流传着郑和与满者伯夷帝国的伯罗威佐国王(Browijoyo)的女儿蒂维·基利苏西公主柏拉图式恋爱的故事,以及与郑和随从瑞和、江厨师等有关的三宝瑞和庙与三宝灶婆公庙的传说。[8]当地人甚至把郑和写进他们的历史、文学作品中。如马来历史名著《马来纪年》中就记载了郑和护送明朝汉丽宝公主远嫁马六甲国王的故事。这些故事虽然都是传说,但从中反映了郑和在马来民族人民心目中的形象与地位。郑和在当地人民心目中的良好形象与崇高的地位无疑有助于推动华侨移民与当地民族之间的关系发展,有利于改善华侨在南洋的生存与发展环境。生存环境的改善必然招致更多的华侨移民。郑和下西洋后,华侨移居南洋的人数激增。“惟中国之南洋,万岛环列,星罗其布,或断或续,……明初,遣太监郑和等航海招致之,来者益众。迨中叶以后,欧罗巴诸国东来,据各岛口岸,建立埔头,流通百货。于是诸岛之物产,充溢中华。而闽广之民,造舟涉海,趋之若鹜,或竟有买田娶妇,留而不归者,如吕宋、葛罗巴诸岛,闽广流寓,殆不下数十万人。”[9]后有人评价说“西洋之迹,著自郑和。”[10]由此可见,郑和下西洋推动了东南亚华侨社会的发展,自然受到华侨的敬仰与崇拜。
第二,郑和崇拜能在东南亚华侨社会产生与发展,这与郑和多元的宗教信仰有一定关系。郑和出生于伊斯兰教家庭,伊斯兰教是他的基本信仰,但他对其它宗教如佛教、道教并不排斥。他自称奉佛,并有法名。如在明初刻本《伏婆塞戒经》卷七所附《题记》中,郑和自称“大明奉佛信官内宫太监郑和,法称速南吒释,即福吉祥”。①转引自林松:《论郑和的伊斯兰教信仰—兼评郑氏“奉佛”、“崇道”说》,载《郑和下西洋论文集》(2),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85,第116页。此外,他在七下西洋之前和下西洋之间,都祷祝过海神天妃(有学者认为天妃属于道教)。天妃娘娘庇佑郑和下西洋的神话在民间流传甚广,这极有助于信仰天妃的东南亚华侨把郑和与天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加以奉祀,马六甲三宝山的三宝亭曾把郑和的神位与天妃一并奉祀便可为证。此外,郑和的伊斯兰教背景也有利于郑和崇拜在以伊斯兰教为主要信仰的南洋群岛等地的流传。如马来西亚丁加奴州的三宝公庙坐落在信奉伊斯兰教的马来人的村子里,又请马来人看管,三宝公庙所在的村落又属于伊斯兰教党执政之地,三宝庙作为华侨的民间信仰的象征能建立在马来人的村落中,这和郑和的伊斯兰背景以及郑和下西洋推动伊斯兰教在东南亚的传播不无关系。值得指出的是,郑和崇拜在东南亚华侨社会的生成还有其特殊的含义。从郑和崇拜的产生来看,郑和既不是华侨的乡土之神,也不同于中国民间普遍奉祀的神祗,他完全是东南亚华侨在当地建构并奉祀的神祗。在东南亚华侨心目中,郑和具有多种身份,华侨社会对郑和的崇拜实际上已经突破了华侨传统民间宗教信仰中的乡土界限,也超越了对中华文化传统价值观的肯定与认同,东南亚华侨华人对郑和多重身份的认同,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早期华侨对郑和代表的国家权威的膜拜以及企盼得到封建国家保护的心理。
三 郑和崇拜与东南亚华族文化意识
同信仰妈祖等其它民间神灵一样,郑和崇拜一方面是早期东南亚华侨祈求平安与保护的心理需求的一种体现,另一方面,也成为东南亚华侨保持与强化族群文化意识的一种象征。随着二战以来东南亚华侨社会变化的巨大变化,传统的华侨社会由落叶归根转变成为落地生根,华侨转变为华人并成为当地多元民族的组成部分。在这种情况下,东南亚华侨华人不可避免地在政治、经济、文化与风俗习惯等方面不同程度地表现出认同当地主体民族的趋势。但在族群意识认同这个层面上,二战以来以后东南亚各地的华人仍不同程度地坚守华人的族群意识。在东南亚的华人族群认同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族群文化意识,这种文化意识是族群的群体行为特性的概括,高度表现为自我“华人意识”。[11]这种族群文化意识是由“一系列重要的价值观与习俗所组成,常在不知不觉中由个人或群体表现出来,构成华人的日常生活,这也是中国移民带来的文化包袱。”①Edgar Wickbery,Ethnicity,载Lynn Pan.Chinese Encyclopedia.Singapore:Archipelago Press,1998。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华人社会传统的民间信仰不仅是华人族群文化意识的重要组成,而且成为华人进行“自我分类”以及与其它族群相区分的一个重要标准。民间信仰的这种意义转换不仅没有削弱它作为华人宗教信仰的本质,反而强化了其作为族群文化象征与族群粘和纽带的功能。马来西亚华人数百年来为保护马六甲三宝山而进行不懈斗争的历史可以说是东南亚华人社会维护族群文化象征的一个典型事例。三宝山位于马六甲市中心,它因郑和曾驻扎在此而得名,传说郑和在马六甲身故的部下也安葬于此山。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极重丧祭。华人流寓海外,远离故土亲人,无不希望身故之后能按照中国的传统安葬,入土为安,魂有所归,并为后人所祭。“清初年间,幸有仁人君子李君②李君,即马六甲第二任华人甲必丹李为经(1614-1688)。他从荷兰殖民当局处买下三宝山,献给华人社会作公墓。发出一片慈悲,乃对众布告,献其葬地,名曰三宝井山。”(重修宝山亭碑记)[12]281三宝山从此开始作为马六甲华人社会的公共墓地。1795年,马六甲华人社会有感于三宝山华人墓地“少立祀坛,逐年致祭,常为风雨所阻,不能表尽寸诚”,在第八任甲必丹蔡士章的首倡下,“爰诸老捐金,建造祀坛于三宝山下”。(建造祠坛功德碑记)[12]271为纪念郑和,该亭取名为“三宝亭”,供扫墓者休息之用。1824年,英国从荷兰手中夺得马六甲的统治权,在三宝山的所有权问题上,华人与英国东印度公司发生了纠纷。英国殖民当局拟在三宝山开路取土,马六甲华人认为,“地脉动摇,势必至坟陇有所损害,死者有知?其不能旦夕之安于窀穸也明矣。”于是有“华人之巨擘”——青云亭亭主陈宪章“谋于众,敛赀一千八百元,于同治丙寅年,助公班衙(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修葺之费,并购送武格峇汝山一所,与公班衙立约,不得妄取此山一杯土,以永妥华人义塚焉。”(保三宝井山义塚资助公班衙碑记)[12]278在马六甲华人社会的共同努力下,三宝山华人义塚终于完整地保存下来。在马六甲华人维护三宝山的历史上,除了与殖民政府交涉外,还要与其它个人或族群交涉。马来西亚为多民族聚居之地,除华人外,尚有马来人与印度族裔,其中不乏以放牧牛羊为业者,一些人将牛羊放牧三宝山,牛羊喧闹嘈杂,啃食草木,不仅严重破坏陵区清幽的环境,而且违背了华人墓地风水切勿妄动的传统风俗。1906年,三宝山的管理机构青云亭颁布告示,上书“立字示各色人等知悉,如有饲牛羊者,不准放在三宝山食草,致践踏伤戕风水。倘敢弗遵,仍将牛羊放上山者,即令人拿交玛礁厝照官惩治。”(禁止放牧牛羊碑)[12]282此外,马六甲华人社会还注意三宝山的日常修缮维护。1924年,鉴于三宝山“树木阴翳,蔓草滋生,乱杂争植,满山皆是,”华人张长才“慷慨解囊,输出巨资,雇工剪伐芟除……厥后呷坡诸善士,奋然兴起,见义勇为,当仁不让,亲自乐捐金钱,共相赞助……”18位华人贤达共捐献银11,667元,历经四年,对三宝山的环境进行了比较彻底的整治。(兰城三宝山剪除草木碑记)[12]283-284马来西亚独立后,马六甲巫统以及马六甲州政府曾多次拟征用三宝山,但都遭到了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反对,其中以1984年的三宝山事件最为轰动。该事件的起因是1984年马六甲州政府计划将三宝山发展为商业和住宅中心,希望迁移山上的华人坟茔。此计划遭到以青云亭、人民行动党以及马来西亚最大华人青年组织—青团运等为首的华人社团、政党的坚决反对。他们不仅取得数十万马来西亚华人的签名,而且行动党还组织了抗议示威。经过与马六甲州政府长达两年多的抗争与协商,三宝山最终作为华族历史文化遗产而保留下来,1986年,马六甲州政府宣布将三宝山列为历史文化区,同时兴建亚洲缩影村,以发展新的旅游。至此,1984年的三宝山事件终于获得圆满解决。从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保护三宝山的历史,我们看到三宝山对于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保存郑和遗迹与郑和崇拜的意义。作为历史悠久的华人义塚,三宝山有12,500座坟茔,其中一些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马六甲华人社会的领袖人物诸如甲必丹郑芳扬、李为经、李正壕、曾其禄和陈承阳死后皆葬于三宝山。此外,宝山亭旁还建有华人抗日义士纪念碑,以纪念二战期间为保卫马六甲而与日军战死的华人勇士。可见,三宝山不仅与马来西亚华人的宗教礼俗密切相关,而且是华人先贤开拓创业与英勇无畏的民族精神的记载与象征。它作为马来西亚华人历史文化的载体与华人族群文化象征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强化马来西亚华人的族群意识与整合马来西亚华人社会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鉴于三宝山在马来西亚华人历史文化上的地位与影响,从1984年起,马来西亚每年由各州轮流主办“全国华人文化节”,每届都由各州的领导人在文化节开幕的头一天齐集三宝山上举行升旗礼后,燃起圣火,并由青年团把火炬高高举起跑几十或几百公里回到本州,从而揭开这一届文化节的序幕,由此象征着把郑和带来的华族传统文化世代相传。
四 “文化郑和”与当代中国与东南亚关系
可以说,郑和崇拜源于东南亚华侨社会,但其影响力已经超越东南亚地域,并演变发展成为为连接中国与东南亚的文化纽带。这种文化纽带不仅表现在中国华南侨乡民间信仰中的“郑和记忆”中,①曾玲在《一个闽南侨乡的郑和传说、习俗与崇拜形态及其社会文化意义:福建省漳州市角尾镇鸿渐村“太保公”庙的田野调查》一文中,考察了闽南侨乡鸿渐村的郑和传说、习俗与崇拜形态与东南亚华人有密切关系,认为福建闽南侨乡的郑和崇拜有可能源自东南亚而非产生于本土,并指出在东南亚华人与祖籍地的关系中,“郑和记忆”作为一条文化纽带,它不仅承载中国华南移民东南亚的历史记忆,也维系着东南亚华人与祖籍地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参见《一个闽南侨乡的郑和传说、习俗与崇拜形态及其社会文化意义:福建省漳州市角尾镇鸿渐村“太保公”庙的田野调查》,载曾玲主编:《东南亚的“郑和记忆”与文化诠释》,合肥:黄山书社,2008年,第92-108。而且更升华为国家话语中的“文化郑和”,成为连接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文化桥梁。与作为东南亚华人社会民间信仰的郑和崇拜相比,“文化郑和”作为在内涵与形式上超越了民间信仰的层面,在国家力量的推动下,正演绎成为一种展示国家文化外交价值观念与认同的形象。郑和作为中国历史上堪与哥伦布相比的大航海家,展现了近代中国人走向海洋的开拓冒险精神,而他所包含的和平精神、包容与尊重不同民族与文化传统的品质又超越了殖民探险家哥伦布,因而奠定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与民族关系的基础。从近年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发展与郑和话语在中国与东南亚关系中的再次强化与延伸来看,可以说,郑和已经从民间信仰的层面延伸到国家话语的范畴。2005年以来,中国从中央到相关地方政府隆重举办的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的各种纪念活动以及学术界兴起的郑和研究热与郑和航海的宣传展览,都集中体现了中国政府对郑和精神的追溯以及对郑和崇拜的国家塑造,郑和成为当代中国实现海洋梦想、民族复兴与中国外交文化观念与价值认同的载体。新时期中国政府对郑和的追溯与塑造,无疑是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谋求复兴崛起以及中国实行睦邻安邻富邻外交政策下对中国与东南亚关系的一次新解读。
首先,改革开放是国家建构郑和话语的一个重要因素。1978年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这不仅是一次经济领域的改革开发运动,而且也是现代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革命,中国社会开始集体思考中国从农耕文明为基础的“黄色文明”向以工商业为主的“蓝色文明”的转变之路。在这种话语下,郑和作为中华民族走向海洋的,开创中华文化“蓝色文明”之路的先驱与代表,成为改革开放时期中国急需树立的开放与进取精神的象征。因此,另一种不同于东南亚华人社会保护神的郑和崇拜,在改革开放的中国,在国家意识形态视野中被构建起来。
其次,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中国国家综合国力的全面提升,“中国威胁论”也随之成为国际政治经济论坛的热门话题,尤其是与中国山水相连的东南亚国家,长期以来纠结于与中国恩怨交集的历史与不可分离的现实,在“中国威胁论”的推动下也催生了各种对中国的复杂情感:既包含欣羡与需要、又深怀猜忌与恐惧,这些情感在边界、领土、贸易、移民等问题的推动下,成为影响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快速稳定发展的不可忽视的因素。如何破除“中国威胁论”这一魔障,以及消除它对中国-东南亚发展带来的潜在的消极影响,成为摆在中国政府与学术界的重要课题。
第三,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政治格局进入一个多极化时代。中国作为新兴经济大国,也成为重要的一极,中国在国际舞台积极推行多边外交,尤其重视在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上推动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与经济关系。非洲在21世纪成为中国外交的一个新方向与新重点。作为郑和航海船队的多次所到之处,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政治伙伴,大多数非洲国家与中国拥有传统的友谊与现实的共同利益,如何在多极化的世界共同发展,成为中国加强与非洲关系的重要话题,而郑和西行访问非洲留下的中国外交文化遗产如和平、平等与互利等价值观念成为新时期处理中非关系的宝贵财富。
第四,软实力与文化外交成为近年来中国外交的主题词,而郑和下西洋奉行的“宣德化而柔远人”,“颁中华正朔,宣扬文教”无疑是软实力与文化外交的最好注脚。新时期中国政府对郑和的追溯与再塑造,明显在昭示中国外交强调和平与友谊的传统以及国力强大不忘睦邻友好的诺言。
因此,我们看到,自1980年代以来,有关郑和的话语开始被国家所强化。1987年,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艘远洋航海训练舰被命名为“郑和号”。服役22年以来,该舰先后完成了学员实习、军事训练、出国访问等各项重大任务二百余次,总航程达28万多海里。开创了人民海军单舰航程最远、在航率最高、所经航区和出国次数最多4项记录。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对郑和的学术研究也进入了一个高潮期。据相关学者的统计,在1904-2003年来百年郑和研究的学术论著中,1985年至2003年共有1968部或篇,占百年论著总数的72.6%。1985至2005年,国内举办郑和研讨会、座谈会共有48个。1985至2005年海峡两岸举办的郑和展重大活动共有29个。1981至2005年,海峡两岸建立的纪念郑和的馆所、公园共有8个。随着国家对郑和的推崇,以及2005年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的到来,2004至2005年,中国大陆共出版关于郑和的书籍51部,单2005年就出版了45部。①转引自孔远志、郑一均著《东南亚考察论郑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25页。
2005年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活动在北京的隆重召开将国家对郑和话语的建构推向了高潮。这次高规格的纪念大会于2005年7月11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黄菊出席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出席会议。黄菊在纪念大会上高度评价了郑和下西洋的光辉业绩和重大历史意义,并宣布将每年的7月11日定为“国家航海日”。除中央政府外,一些相关的地方政府也隆重地举办了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的纪念活动,这种自上而下的国家建构模式无疑对强化与升华郑和话语有积极的推动意义。
中国对郑和话语的升华与强化,也得到了东南亚国家的呼应,双方都意识到在中国崛起形势下,必须有一个规范来保障中国-东南亚关系的健康发展,那就是和平、尊敬、合作与互利。尤其是马来西亚,作为郑和下西洋五次到访的国家,郑和船队在马来西亚的马六甲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郑和穆斯林的身份,更加强了马来西亚这个伊斯兰教国家对郑和的认同与亲近感。近年来,马来西亚作为中国在东南亚的重要政治与经贸伙伴,从华人社会到马来西亚政府都在积极寻求与中国的合作,郑和自然成为强化双方关系的纽带。1993年8月,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曾率领500人的工商代表团访问中国,在百忙中到与郑和有密切关系的西安大清真寺做礼拜。1994年9月,马来西亚副首相安华访华时特访南京,参观郑和衣冠冢墓园,向这位马中共仰的伟人致敬。面对中国的发展以及“中国威胁论”的泛滥,2003年7月底,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在第七届世界华商大会上说:“我们离中国很近,但中国从来没有占领过我们的,我们并不担心中国变成军事强国,把我们吞并,因为这不是中国的传统。”②Eddie Leung:Southeast Asia-China:Threats,Opportunities,http://www.atimes.com/atimes/China/EH02Ad01.html
马哈蒂尔首相的言辞反映出马来西亚政府更看重与珍惜中国发展所带来的历史机遇,这种观念得到马来西亚社会的普遍认同,并从郑和开创的中马友好关系的历史中追寻两国关系的未来。如马六甲首席部长拿督里莫哈末阿里认为,郑和舰队下西洋到马六甲,可以说对马来西亚及马六甲人民带来深远的影响,包括宗教、文学、贸易及外交关系,并且丰富了马六甲的多元文化。因此,2005年是中马建交30周年的“中马友好年”,又恰逢郑和下西洋600周年,马六甲举行了一系列庆祝和纪念活动。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也将郑和视为华人文化的重要部分,如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会长林玉唐在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之际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中指出,“郑和船队代表的和平与亲善”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中心点。马来西亚华人穆斯林也发扬郑和精神来促进中国与马来西亚以及其它伊斯兰国家的经济贸易与文化交流。如2009年12月27日至31日,应马来西亚著名华人企业家李金友公爵和的邀请,来自马来西亚、文莱、泰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阿联酋和中国等七个国家的华人穆斯林企业家和文化人士齐聚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发起成立“郑和国际经济文化发展联合会”,探讨在新的历史时期穆斯林经济文化人士所肩负的使命,以及如何为构建“和谐世界”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马哈蒂尔出席了这次华人穆斯林企业家盛会并致辞。这一系列的活动表明,关于郑和话语的建构不仅被中国所重视,也被东南亚国家与社会所重视,甚至被国际化,表达出新形势下国家在积极参与建构郑和精神的时代意义。
结语
郑和,作为中国航海事业的先驱与开拓者,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文化交流的推动者以及近代中国与东南亚外交政策的主要实践者,在东南亚华人社会与当代中国政治经济的不同语境中有着不同的形象。在东南亚华人社会与华南侨乡社会,郑和从一个历史人物演变为东南亚华侨华人的保护神与华人族群文化意识的象征以及联系东南亚华社与祖籍地的文化纽带,充分显示了作为“非制度文化”的民间信仰在延续华人历史文化传统方面的生命力及其对巩固华人族群意识、加强华人社会凝聚力等方面的重要意义。而在当代中国迅速变迁的政治经济环境下,郑和话语被国家所强化与升华,成为中华民族精神与中国外交理论的价值观念与认同的重要构成。华人社会、侨乡社会与国家层面对郑和的不同解读,都反映了郑和作为一种信仰与文化的生命力。
[1]林天佑.三宝垄历史:自三保时代至华人公馆的撤销[M].李学民陈巺华,译.广州:暨南大学华侨研究所,1984,46.
[2]许云樵.三宝公在南洋的传说[G]//郑鹤声,郑一均.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M].济南:齐鲁书社,1989.
[3]郑振满,陈春声.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1-2.
[4]布赛尔.南亚的中国人—总论[J].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57,(4):1-23.
[5](明)费信.星槎胜览校注(后集)[M].冯承均,校.北京:中华书局,1954:4.
[6](明)罗曰褧.咸宾录·真腊传[M].余思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141.
[7]孔远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文化探析[M].香港:南岛出版社,2000:158.
[8]李炯才.印尼——神话与现实[M].新加坡: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79:88-89.
[9](清)徐继畲.瀛环志略·亚细亚南洋各岛[M].宋大川,校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27.
[10](明)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M].谢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2:7.
[11]庄国土.闽南海商的兴起与妈祖信仰的传播—兼论妈祖信仰与华人族群意识的关系[M]//郝时远.海外华人研究论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295-312.
[12]陈铁凡,傅吾康.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G].吉隆坡:马来亚大学出版部,1985.
The Establishment of Zheng He Imag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SHI Xue-qin
(Research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Xiamen University,Xiamen361005,China)
As a great navigator and a diplomat in Chinese history,Admiral Zheng He has produced far-reaching impact on China-foreign relations.In terms of socio-cultural aspect,Zheng He is revered as the protector of Chinese community in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in which the shaping of Zheng He cult reflects the influence of Zheng He who has been transformed into a symbol of Chinese identity reinforcing coherence and solidarity of Chinese community.At the level of national politics,the reshaping of Zheng He’s image is increasingly integrated into the narrative of Sino-southeast Asian relationship in the new era,being honored as an effective dynamic of the development of Sino-southeast Asian relationship.The multi-narration of Zheng He in the ethnic Chinese community and at a national level demonstrates the vitality of Zheng He,as a belief,a value and an identity.
the cultural image of Zheng He;Sino-Southeast Asian relationship;value orientation
K203 < class="emphasis_bold">文献标识码:A
A
1674-5310(2011)-05-0046-07
本文系国务院侨办课题“多元文化视野下的族群关系;印尼华人的文化调适与和谐侨社研究”(编号:GQBY2011048)阶段性成果。
2011-04-23
施雪琴(1968-),女,重庆人,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东南亚历史、社会与文化研究。
(责任编辑:胡素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