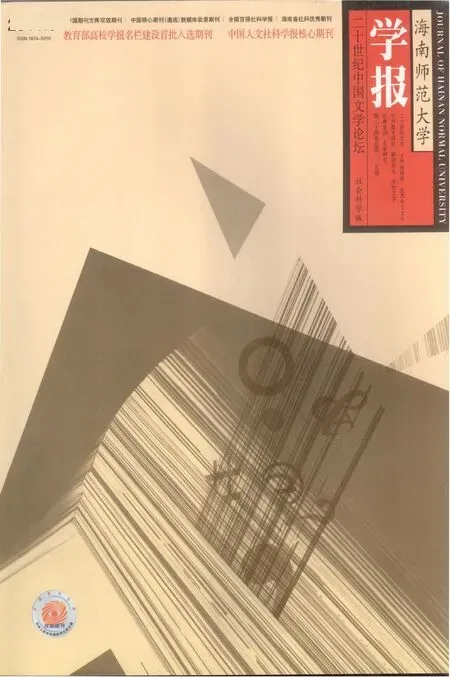巴尔加斯·略萨:一只啄食腐肉的“兀鹫”
陈春生,张意薇
(1.赣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江西赣州 341000;2.海南工商职业学院海南海口 570203)
巴尔加斯·略萨:一只啄食腐肉的“兀鹫”
陈春生1,张意薇2
(1.赣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江西赣州 341000;2.海南工商职业学院海南海口 570203)
巴尔加斯·略萨获得2010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对人们重新聚焦拉美文学具有重要的意义。略萨以文学介入生活、介入政治,具有小说家与政治家的双重文化身份。他如一只啄食社会腐肉的兀鹫,用文学对抗社会黑暗、腐朽的独裁政治。在对拉美社会权力结构精细的描绘中,他以虚构小说的方式将理想与现实两个世界对举连通;从而在立体的艺术世界中,扫荡着现实社会生活的荒谬,呼唤人类的尊严。
略萨;拉美文学;政治美学;结构现实主义
一 摘得桂冠:拉美文学的又一奇葩
2010年度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巴尔加斯·略萨,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这个具有秘鲁与西班牙双重国籍的拉美作家与09年获奖的赫塔·梅勒带给人们的陌生感大不相同,略萨获奖前不仅是一位具有世界性声誉的作家,而且在中国也是较早引起了学术界关注的拉美作家之一。20世纪70年代末,略萨就被介绍到中国,90年代大陆有两家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文集,对他人生经历与小说创作的关系,他的小说美学思想的追求以及独特的艺术创新精神的研究达到了一定的深度。略萨开创的“结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他自称“通管法”)对中国寻根文学以及后来的先锋文学思潮都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
从新世纪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史的角度审视略萨获奖,可以看出2010年度诺贝尔文学奖颁奖意义非同一般。
首先,在文学全球化日益明显的今天,瑞典文学院的评委们再次以世界性的眼光关注欧洲以外国家和民族的文学,自1945年始,拉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有:米斯特拉尔(智利,1945)、阿斯图里亚斯(危地马拉,1967)、聂鲁达(智利,1971)、马尔克斯(哥伦比亚,1982)、帕斯(墨西哥,1990),加上略萨,共有6位。略萨的获奖使诺贝尔文学奖在间隔二十年后,人们再次将目光聚焦于拉丁美洲文学,这些不同风格和流派的作家,构成了不同时期拉丁美洲文学史的典型个案,将这些作家连接在一起,就能从“世界文学”或“总体文学”的高度来了解拉美大陆的文学史,也可以完整地了解拉美的社会史、政治史。
其次,新世纪以来,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往往爆出“冷门”,很多作家在获奖前,其作品只是在较小范围内传播,一般读者很少关注作家的创作以及他们作品中对社会、人生的深刻思考。而略萨是一位被诺奖多次提名的作家,他的作品在世界范围内拥有广大的读者,因此略萨进入诺贝尔文学奖圣殿最重要的意义是,它使得最近几年争议不断的颁奖得到了更多的正面评价,略萨的获奖是诺贝尔评选委员会对最近几年选择颁奖作家视域狭隘、作家冷僻以及委员们自身趣味偏狭的一种纠正。
再次,略萨的获奖表明瑞典文学院不会忽略那些在文学上不断锐意创新的作家,也不会忽略经历时间洗礼依然闪耀着艺术光芒并具有艺术生命力的作品。它增加了一般读者对诺贝尔文学“理想主义倾向和最出色的”颁奖标准的深切了解,在诺贝尔文学奖在文学与大众之间架构了一座相互沟通的桥梁。
作为拉美文学两巨匠的马尔克斯和略萨是研究拉美文学不可回避的两座高峰。当1982年瑞典文学院通过对马尔克斯的授奖而从世界文学视野肯定了魔幻现实主义的时候,结构现实主义文学虽为人关注,但还未进入诺贝尔文学奖的视野。这次略萨获奖,可以说是对20世纪拉丁美洲文学创新的另一具有影响流派——“结构现实主义”的肯定,有助于人们在探究拉丁美洲文学全貌时获得一个更加完整的印象。马尔克斯听闻略萨获奖,高兴地说:“我们终于一样了!”
略萨虽比马尔克斯小九岁,但成名的时间较早,风头也一度盖过马尔克斯。两人是1967年略萨去委内瑞拉领取第一届加列戈斯文学奖(拉美最高文学奖)时相识的。此时《百年孤独》才刚出版两个月,尽管该书出版引起拉美文坛轰动,但进入欧洲读者的视界尚需时日。略萨结识马尔克斯后,决定放下手中工作,研究比他名气小的作家。略萨将1967年以前马尔克斯全部创作作为一个系统进行整体性的考察,并用一个专有名词称作家为“拉丁美洲的弑神者”。1971年,略萨完成了40万字的博士论文《加西亚·马尔克斯:一个弑神者的故事》。在《虚构的现实》这一部分,对作家人生经历与创作心理之间隐秘联系的分析,几乎达到了心理学分析批评的高度。
略萨从世界文学的角度对这位刚刚走红作家的未来进行了准确的预言。略萨认为马尔克斯小说中那种超越民族、超越地域的世界性主题,即专制、独裁、贪腐给人类精神和心灵带来的伤害深刻而准确的描绘,将会使之成为一位具有世界性影响的作家,略萨进而指出,独裁的结果便是导致整个拉美民族游离于世界主流价值之外,陷入永远无法摆脱的孤独之中。独裁、专制、腐败不仅是拉丁美洲的病症,也几乎是整个人类社会必须警惕的公害。
略萨曾问马尔克斯“我们为什么写作?”马尔克斯说从事写作除了因为不会做别的事并且想让自己的朋友更加喜欢自己外,小说还承担着一种职能,这种职能就是对现状的一种破坏性力量,“我不知道有哪种优秀文学作品是用来赞颂已经确立的价值的,在优秀文学作品里,我发现总有推毁已被确立的、被强加的东西和促进建立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社会制度的趋势。总之,是改善人们生活的趋势。”[1]略萨肯定了这种立场:既然拉美大陆到处是苦难,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作家,就应该理直气壮地撕破面纱,充当现实的弑神者。对加西亚·马尔克斯小说中那种与众不同的重复:重复的人物、情节、人名、地点、举止和行为等等,略萨以一个作家的体验和思考,令人信服地指出:这是“对生活的一种循环的、渐进地、强化的审视”,而这种孤独和死的循环往复,是人类遭受的一种可笑的、可悲的因而也是一种可怕的折磨,恰似普罗米修斯的五脏六腑被兀鹫啄食,痛苦异常,且永无休止。这种描写的意义何在?略萨指出,这是对人类多舛命运的深刻揭示。其实,弑神者,也是略萨自身的写照,正因为他和加西亚·马尔克斯在精神气韵上的相同之处,才能如此独到地感受加西亚·马尔克斯作品后面蕴含的深意。其实,除了潜心文学外,略萨也直接参与政治生活。1989年,他参加秘鲁总统竞选,遗憾的是败给了日裔人藤森。
二 多重文化身份:政治性作家的文学生涯
略萨全名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Mario Vargas Llosa)。1936年生于秘鲁阿列基帕市,父母离异后,略萨与母亲随外祖父在玻利维亚的柯恰潘巴生活。1945年回到秘鲁,定居在皮乌拉。1946年,父母复婚后又迁往秘鲁首都利马。1950年,青春年少的略萨奉父命进入了普拉多军校。1953年,进入圣马科斯大学,在求学期间,他深深地迷上了文学,广泛涉猎世界文学名著,毕业后还和别人合作编辑出版了《写作手册》和《文学》两本杂志,且开始涉足戏剧,曾创作神话剧《逃亡》。在皮乌拉地方民间艺术节小范围演出后很受欢迎。1958年,他创作了短篇小说《挑战》,获得《法国杂志》在秘鲁举办的短篇小说竞赛奖,同年出版了短篇小说集《首领们》,小说反思了心智健全的少年为何在斗殴和残杀中浪费青春,将矛头直指社会。同年,略萨获得了西班牙马德里大学奖学金,可惜进校不久,便因经济原因辍学。随即前往法国并在法新社和法国电视台谋得职位。可以说,如果不离开马德里大学,略萨可能是一个优秀的学者,但富有浓厚艺术气息的巴黎,成了他作为一个优秀文学家以及评论家的重要机缘。略萨在巴黎大量阅读了雨果、巴尔扎克、大仲马、萨特等人的著作,并结识了一批侨居巴黎的拉美作家,如古巴的卡彭铁尔、危地马拉的阿斯图里亚斯、阿根廷的博尔赫斯等。之后,略萨又侨居伦敦、巴塞罗那等地。
略萨真正成名作是1962年完成的《城市与狗》,小说开始展示了作家独树一帜的“结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小说以秘鲁的莱昂西奥·普拉多军校生活为题材,不断转换视角,打破时间线索,自由拼接故事情节,似乎眼花缭乱,但又精彩纷呈。小说语言的意象简洁而深刻,充满智慧,一出版就获得了“小丛书奖”(一种给予西班牙语小说的最佳奖)和批评奖(1963)。由于小说对军政当局的大胆揭露和批判,激怒了军方,他们在军校组织烧毁了刚出版的1000本小说,并宣布略萨是学校和秘鲁政府的敌人。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军政府的禁戒反而加大了这本书的传播速度和范围,也让略萨更加有名气了。
1964年,尽管《城市与狗》引发的政治风波还没有平息,略萨还是回到秘鲁。他在落后的的丛林地区考察生活,欧洲都市的繁华与秘鲁乡野的贫苦,两相对比中呈现的巨大反差强烈震撼了他的心灵:“秘鲁有一个比我通过普拉多军校看到的更为广阔的、更为可怖的世界。”对现实认识的深化加强了作品的现实干预力度。为此创作了小说《绿房子》(1966年),小说以丛林地区一个叫“绿房子”妓院的兴衰变化为描写主线,构思独特,反映了拉美社会“虚假的、恶毒的、将要腐烂的社会结构”,这个社会“放散着一种致命的毒气”。“绿房子”是一个时代发展变化的缩影,折射了20世纪20年代以来秘鲁的社会现实。小说的处理手法类似塞尔维亚作家安德里奇的《德里纳河上的桥》,即以一个与我们生活密切相联系的事物为载体,展示不同时代的不同风俗以及时代变化发展的轨迹。小说中蕴含着强烈的政治批判意识,考虑到第一部小说带来的麻烦,略萨将小说送到西班牙出版,并受到了西班牙语文学界的好评。
略萨是一个勤奋而多产的作家,几乎每隔三年就有小说问世,而且都能产生较大的影响。他主要创作的小说如下:长篇小说《酒吧长谈》(1969),《胡利亚姨妈与作家》(1977),《世界末日之战》(1981),《马伊塔的故事》(1984),《谁杀死了帕罗米罗》(1986),《安第斯山的利图玛》(1993),《堂里格维托的笔记本》(1997),《另一个街角的天堂》(2002),此外他还有大量的剧本、散文、谈话录等。1992年,他加入了西班牙国籍,1994年因为其创作的出色成就,获得了西班牙最高文学奖——塞万提斯文学奖。晚年的略萨一直笔耕不辍,直到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略萨丰富的履历,成为我们研究他多重文化身份和小说主题、艺术技巧相互联系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在他的创作历程中,主动接受其他民族文化和文学的滋养,感受多种文化的冲击,与本民族的文化底色相融合,思考人类的前途。从文化养成上讲,他深受西班牙文学传统的影响,而旅居欧洲多国的经历,又让他具有更为宽阔的文学视野。他的创作既扎根拉美大地,又能超越本民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和制约,能在全球化视野中审视民族的命运和人类的未来。正是在多元文化的熏陶,略萨评价生活的尺度,不再是局限于本国的现实,而是从人类社会发展的高度,思考积弱的祖国如何摆脱专制奴役,如何在民主、自由、独立的价值观念之下,融合到世界文明进步的大潮之中。
三 挺身弑神:以创新的理念反叛现实
略萨漫长的创作生涯中,涉及的文学体裁非常广泛,如小说、诗歌、散文随笔、戏剧、文学评论、政论杂文等。在迄今为止出版的十部小说中,《城市与狗》、《绿房子》和《潘上尉与劳军女郎》等尤具代表性。从创作技法以及艺术风格上说,他用所开创的“结构现实主义”方法营造了一种相当独特的叙事风格。一个杰出的作家,他同时是一个思想家,一个具有独特美学追求的艺术革新意识的大师。略萨能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主要取决于他所坚守的理想和追求,和劳苦大众站在一起,和世界文明发展的潮流站在一起。略萨提倡“不妥协”的文学,主张“文学要抗议,要控诉,要批判”,其小说批判的锋芒直指独裁统治、教会和贪赃枉法的官僚。但是,他的小说与传统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给我们的审美感受是不一样的,他用一种陌生化的处理方法带给我们一种别样的审美感受。
略萨进入拉美文坛的时候,正是拉丁美洲文学以“爆炸性”姿态引起全世界读者关注的年代,他成了推动拉丁美洲文学进入世界主流文学的重要作家之一。由于殖民的原因,拉丁美洲文学引渡自欧洲大陆,确切地说,其美学准则受西班牙文学、尤其是塞万提斯的影响很大。
塞万提斯认为,现实主义就是要模仿自然和反映现实,但要把模仿建立在想象与历史真实的基础上,也就是说作家在摹写客观现实的同时,不能忽略作家的主观想象。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虽在历史真实中混入大量的想象,但我们依然认为它是现实主义的作品。也就是说,这种现实主义并不强调典型环境、典型人物以及细节的真实性,而是注重是否能在细节的的背后发掘出象征意义,这才是更高层次的真实。在1995年获塞万提斯奖的演讲中,略萨通过盛赞塞万提斯及其代表作《堂吉诃德》阐释艺术创作中想象与真实间存在的张力:“通过艺术创作,人类可以冲破自身条件的限制,找到一种永生的形式;但与此同时它又把我们打得粉碎,因为它让我们意识到与构思出这样英雄伟业的巨人相比是何等渺小。如何能犯下如此弑神之罪呢?怎么可能以这样的方式向神的创造挑战呢?由于塞万提斯写出了这个奇情异想的绅士故事,就使得西班牙语有可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为我们用这一语言写作的人设立了最高标志,他还革新了小说这个种类,赋予小说以复杂性和细微的特点,其范围之广阔如同给小说以生命的这个世界那样具有破坏性和建设性。”[2]
“结构现实主义”的美学原则发源于塞万提斯,而其近源则可追溯到1911年西班牙画家毕加索所创造的“立体主义”。这个美术流派主张,将一切物体的形状加以解体,再由艺术家凭自己的主观真实观念重新组合,画家可以在画面上表现事物的不同侧面。略萨以及结构现实主义作家就是将这种绘画理论移植到小说创作当中来,就形成了非常独特的“结构零件说”:“现今小说总想用一条渠道、一个角度去表现现实,而我却相反,我主张创作总体小说,即雄心勃勃地从现实的一切方面、一切表现上来反映它。”他的美学追求是,“观察现实的角度是无限的。尽管不可能一切角度都涉及,但是表现现实的角度愈多,小说就愈出色。”秘鲁知名批评家桑切斯在谈到结构现实主义的特点时,概括性地指出,“现实的再创造就是指作者的再创造,作家在认识和体验了现实之后,把现实中合适的成份(零件)和令人感兴趣的成份(零件)提炼出来,在不歪曲原素材的前提下,重新组合一个世界、社会或者人物,这种方法既取材于现实又区别于现实。”
略萨从塞万提斯那里获得思想资源,打破旧有的艺术程式;在艺术革新的呼声中,置换文学作品的陈旧内核也成为必然要求。在略萨对马尔克斯的研究中,指出“弑神者”首先要揭下拉丁美洲独裁者的虚伪面具。为了维护独裁统治,统治者将自己装扮成超越世俗的神——冷漠、傲慢,高高在上地睥睨万物,但是独裁者傲慢且不近人性的背后是凶狠残暴、昏聩无能,他们虚弱却装出强大,他们胆怯却沉醉在虚幻辉煌的历史中。独裁的形成与殖民统治密切相关,略萨将独裁极权等拉丁美洲大为流行的政治文化现象与殖民灾难联系在一起批判——恰恰是殖民者对拉丁美洲大陆巧取豪夺、胡作非为才使得拉丁美洲陷入了持续的动荡之中。极权者的暴虐带来了社会的灾难,正是统治者独裁贪腐,人民的权利才无法得到保障。那么作为一个作家,就应该义不容辞地将民众的这种社会处境和苦难根源进行披露,以呼吁人民起来反抗,打碎这种不合理的制度。——这是真正的文学作品所应具备的内涵,这种对统治者横征暴敛、独裁专制的揭露,无疑是弑神精神的另一面。略萨赋予了马尔克斯弑神者的意义和并成为拉丁美洲的这场弑神活动的声援者,意味着他对文学与政治的双重反叛。
其实,略萨在巴黎即已接受了萨特等人的存在主义的观念,即文学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干预社会。如何达到干预的目的呢?就要对社会生活进行全景式的、总体上的勾勒。既然是多角度、多层面的描写,每一个侧面可能有不同命运遭际的人物,也就是没有一个人具有总体上的代表性和典型意义,因此略萨小说中的人物,往往只是作家描写复杂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只有不同层面、不同人物的命运和生活经过作家的扭结才能实现这种立体感。由此,结构现实主义很少设置贯穿小说全篇的主人公,也很少安排类似的人物活动在同一个层面上,而是让人物活动在不同的侧面上或者一个集团、一个群体之中。略萨自己也说,“我塑造的是一群人物的故事而不是一个人物的故事,主要角色是以小集团出现的。”
因此,略萨的结构现实主义,可以理解为:既然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复杂多变的,文学作品也应该表现这种丰富多彩、复杂多变,否则就无法反映现实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多样性。小说表现现实的角度和层次愈多,就越真实,要想写出伟大的小说,就应该尽可能多层次、多角度去把握现实,表现现实。了解了结构现实主义以及略萨的美学追求,我们对他小说中纷乱的线索和多层面的情节就能理解了,也能感受那种总体结构带给我们的艺术冲击力。
以《胡丽亚姨妈与作家》(1977)为例,小说共20章,作家别出心裁地以单数和双数来结撰小说的构架,单数各章讲述胡丽亚姨妈和作家的恋爱故事,以及剧作家卡玛乔在利马电台积劳成疾的遭遇,而双数章节则选择了故事发生过程中的一些不相关的故事,表面上看写富人的奢侈,穷人的痛苦,但是将这些独立的小故事和姨妈的故事连接在一起,就能看到一个时代的生活概貌和人物悲剧性命运的场景。这些故事、场景作为另外的叙事线索和时代背景出现,就构成了总体小说的特征。
四 如椽大笔:美学理想的文学样态与艺术实现
在《城市与狗》中,略萨开始用一种独到的眼光审视专制制度如何将人培养成狗的尖锐现实。军校学员偷窃试卷行为败露,校方对全体学生进行严密的监控,终于一个绰号叫“奴隶”的学员用告密换取了一次外出自由,偷窃者事件的主谋“美洲豹”为了报复“奴隶”,竟寻机将其打死,学生诗人阿尔贝托出于正义,向学校当局检举了“美洲豹”,但严酷的现实让正义者体验到了专制社会的冷酷与黑暗,学校当局将真相彻底遮蔽。阿尔贝托基于人善良的天性所做出的微弱的反抗,在强大的专制权力面前不堪一击。
从创作手法上讲,由偷试卷引发的学员之间的分裂、猜忌和报复等情节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情节延展,而是起到串连各生活片段和场景的“部件”作用,这些“情节”魔方一样镶嵌在小说总体框架中。也就是说,传统小说技法中将事件本身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作为推进小说情节延展的结构程式虽然在小说布局中依然存在,但是已经化为拉开情节背后日常生活场景的帷幔,帷幔之后的广阔社会舞台和生活百态才是作者的用意所在。
略萨自己那段军校生活的青春岁月无疑使作家对专制的暴虐记忆深刻,在对军校生活的表现中,他细致地展示专制制度如何让本性纯良的青年逐步失去理想、信念和独立思考的能力,成为听命专制统治者的工具。小说中的教官并不多,但他们每天像幽灵一样到处游走,对人对事冷漠无情,除了凶狠的吼叫,就是无处不在的惩罚。对他们的刻画,看似浮光掠影,但让人感到校园内无孔不入的监控。除了表现这种压抑窒息的校内养成环境,校外活动则是对学校专制文化氛围的补充,而相对单纯的家庭关系和天然纯真的爱恋,军政统治下人们生活压抑,家庭破碎的窘境就被凸显出来。本应最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年轻人感受不到青春的欢乐,即使遭遇冤屈,也无法申诉。这种生存图景传达给我们的是看不到出路的痛苦、绝望。
略萨的另一部长篇小说《潘塔莱昂上尉和劳军女郎》,则不是一首青春和正义的挽歌,他将主人公替换为统治阶级内部中的一位“模范人物”——潘塔莱昂上尉。这位忠于职守军人,从不吃喝嫖赌。但是愈是靠近统治核心的人愈容易物化专制机器一个部件,而成为没有思想的躯壳。这是一部融合了西班牙文学传统的小说,在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西班牙塞万提斯式的表现手法,在崇高庄严的故事叙述中,充斥着社会的荒诞、人生的无聊和命运的乖戾。由于边疆区驻军条件艰苦,士兵纪律松弛,强奸事件屡发不止。为了平息士兵的欲火,潘上尉不得不接受一个荒谬的政治任务,上级要他以商人的身份组织军中慰安所。潘上尉以一种军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尽职尽责履行任务。他一脸正气地穿梭于风月场所,遴选具备资质的妇女,用科学统计方法计算服务队的规模,并严格按章办事、及时上报情况、统筹管理经费。但潘上尉最终成了军中丑闻的牺牲品,被发配到北部高寒地区工作,而服务队的妓女则被将军和神父据为己有。在这里,劳军情节既是象征的,也是现实的。潘上尉的越是认真负责就越滑稽荒诞,这种艺术表现上的张力寄予着略萨对军界的腐败、荒唐的尖锐的讽刺;这种军中见不得光的丑恶正是整个秘鲁社会腐败、堕落的真实缩影。略萨一辈子痛恨专制威权政权,在1993年自传《水中鱼》尖锐地指出,威权政府是一个专断而愚蠢的“政父”,秘鲁在这样专制独裁的威权统治下,“政府就是国家,执政者管理国家如同管理自己的私人物品,更确切地说是战利品”,[3]48而且在“政父”的统治下,全体民众都失去了信心,“人们生活在互不信任、互不了解之中,生活在不满与偏见之中,生活在暴力的漩涡里。”[3]223
略萨的这种颇具创新现代意味的手法催生了人们对目前政治体制带给人的痛苦和灾难的深刻思索。他所展现的丰富的秘鲁当代社会生活的多彩画卷,传达出一种鲜明的政治倾向。他意在与军政当局进行彻底的“决裂和反抗”,对秘鲁政府进行“抗议揭露和批判”。小说中,军政独裁的秘鲁已经成为扭曲人性的强大异己力量,作为一个具有民主精神的作家,略萨站在世界潮流面前揭露了这种政治体制的荒谬,以文学创新的方式,完成了政治上的与专制政权的不合作,高扬着自由的旗帜。
略萨曾在其政治性论文《顶风破浪》中指出,“小说的任务就是要抓住现实中的丑恶现象加以揭露和抨击,以便加速旧世界的崩溃。”“文学作品是对社会现象不妥协的武器,是预言旧世界行将崩溃、新世界即将到来的先声。”他认为“作家的天职就是反抗,在道义上有义务成为社会的反抗者。”[4]
五 小结:文学与政治联姻的启示
我们一度倡导文学的“去政治化”,即文学要摆脱政治的干扰从而获得艺术上的自主性,让文学性或艺术性成为文学作品的价值所在。但是略萨以其创作实绩告诉我们,真正具有价值的文艺作品往往和政治扭结在一起,联结文学与政治的纽带不是强制律令,而是作家的人道精神和对现代社会价值的追求。也就是说,只要不将文学叙事单纯化为“政治正确”之类的宏大叙事,将文学虚构简化为图解政治的苍白模式,文学不应该拒斥和政治的“联姻”。
在略萨的作品中,他激发起文学承担社会使命的这一重要职能,将民主政治的意识置于文艺作品的中心,没有简单构筑理想社会的乌托邦幻景,却一直前进在追逐自由理想的路上。诺贝尔文学奖给略萨的颁奖词是赞誉他“对权力结构制图学般的细腻描述和他对个人的抵制、反抗和挫败形象的尖锐刻画”。政治追求是人类群体生活中一个重要向度,政治美学是人对自身生存的这一向度的美学观照。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形式漂浮在人类精神领域的上空,在被一定的历史结构决定和制约的同时并未放弃自身的改变历史的雄心,而只有具有思想深度和历史内容的作品,才能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历史的转折。
略萨富有时代感和现实意义的艺术描写,揭露了秘鲁社会现存秩序的非人性质,表现了他所处的社会的专制腐朽以及荒谬怪诞,这种对非人化历史的批判,不是从形而上的艺术理念中派生,而是和现实的政治斗争相关联,因而兼具历史的和时代的精神。他以其文学创作的实绩,将自己对现代社会理想的诉求融入艺术的典型和“虚构的真实”中,指出独裁的军政府无法成为秘鲁国家未来的担纲者,并希图据此引导一场大范围社会政治的变革。处于军政府独裁统治下的拉美社会,利益归属无限向军政府倾斜,于是,统治阶层处在毫无监管机制的运作之下,不仅腐朽堕落、滥施淫威,甚至到了荒谬、离奇的程度。基于这种社会状况以及略萨对时代精神的精准把握,他将复杂的历史事件进行形象化、艺术化的处理,试图追寻历史事件的背后的深层动因,在艺术的世界中重建时代话语的意义维度,并通过一种塞万提斯式的庄严中的反讽,对人们进行一种政治的、伦理的暗示,历史是毁灭与文明的双向过程,对丑恶以及荒谬的鞭挞和超越,沉重的现实终将指向更为理想的彼岸。“个人的抵制、反抗”将并非仅以“挫败形象”徒劳地湮灭在历史进程中,他们成为促成旧有的权力结构坍塌、阶级关系更替乃至整个社会历史转型的重要力量。
[1]林一安.加西亚·马尔克斯研究[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154.
[2]巴尔加斯·略萨.巴尔加斯·略萨在接受1995年塞万提斯文学奖时的演说词(选登)[J].赵德明,译.外国文学动态,1996(10):37.
[3]略萨.水中鱼[M].赵德明,译,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6:48.
[4]孙家孟.结构上的美学实验——论略萨的创作技巧[M].北京:北京旅游出版社,1989:287.
Mario Vargas Llosa:A“Vulture”Pecking at the Carrion of Society
CHEN Chun-sheng1,ZHANG Yi-wei2
(1.Department of Chinese,Gangan Normal College,Gangzhou341000,China; 2.Hainan Vocational Institute of Industry and Commerce,Haikou570203,China)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in 2010 is awarded to Vargas Llosa,which is greatly significant for people to refocus on Latin American literature.As Llosa’s literature involves life and politics,he has the dual cultural identity of both a novelist and a statesman.He is like a vulture pecking at the carrion of society,fighting against social darkness and corrupt dictatorship by means of his literature.In his vivid description of the social power structure in Latin America,Llosa manages to connect the worlds of idealism and reality in a fictional manner,thus having swept the social absurdity and called for human dignity in the stereoscopic world of art.
Llosa;Latin American literature;political aesthetics;structural realism
I3/06 < class="emphasis_bold">文献标识码:A
A
1674-5310(2011)-05-0024-05
2011-05-16
陈春生(1963-),男,湖北罗田人,文学博士,赣南师范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张意薇(1984-),女,黑龙江海伦人,文学硕士,海南工商职业学院教师,主要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责任编辑:胡素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