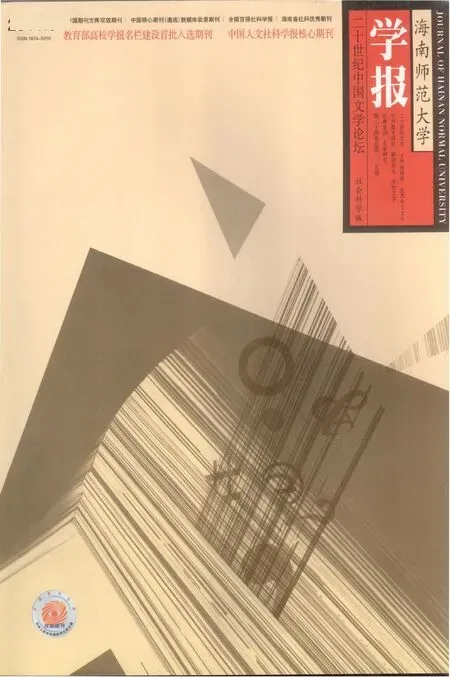作家如何“读史”——刍议新时期作家对“文革”历史的文学叙述
沈杏培,姜 瑜
(1.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210097;2.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江苏南京 211172)
作家如何“读史”
——刍议新时期作家对“文革”历史的文学叙述
沈杏培1,姜 瑜2
(1.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210097;2.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江苏南京 211172)
“文革”是新时期以来的中国作家面对的最近也最压抑的历史,对这段历史的描述,不同作家的叙述与书写也呈现出不同的风格与形态。论文考察新时期以来的知识分子作家,面对文革这段历史时,这些读史者是如何去“读”和“叙”,对文革的历史叙述存在哪些历史误区与困境,如何建立关于文革的历史叙述的有效而丰富的生态。
新时期作家;“文革”历史;文学叙述
“文革”被当代作家视为中国的奥斯维辛,[1]被一些作家视为创作的母题和终身要表达的命题。[2]而在新时期以来的30余年的文学天地里,以文革作为题材的小说确实蔚为大观,无论是“伤痕”、“反思”文学、先锋文学、新生代创作,或是所谓老中青几代作家、体制内与体制外的作家,都染指过此领域,为三十年的新时期文学留下了大量“文革”叙事小说文本。文革叙事可以在多个层面解释、书写,文革可以作为心理范畴的创伤记忆或集体记忆,可以在历史视域作为对中国社会进程进行书写的历史叙述,可以作为文学母题或独特题材,甚至可以作为反观民族文化心理与民族人格的文化原型。那么,作为历史叙述的文革,在三十多年的小说叙事中究竟是在不断增殖还是不断被遮蔽?按照“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命题逻辑,克罗齐由此还得出了历史是愈来愈丰富、愈来愈深刻的结论,他觉得人的精神是不断发展的,因而人的历史视野和历史认识也在深化,历史不断地被重写着,在新的解释和书写中不断丰富和完善。[3]17因而,笔者将追问的是:文革作为近百余年中最为悲壮和缠绕的一段历史,在新时期以来文学知识分子和作家那儿以小说的形式清理、阅读、审视、书写时,究竟呈现出怎样的话语和叙事特征,当代的历史叙述是在还原文革的真实历史还是建构动态的“当代史”视野里的文革,这种还原或建构的努力彰显了什么,遮蔽了什么?对此,我们又应以何种精神姿态和文学策略去建立历史叙述的生态?
一
黄子平在《灰阑中的叙述》的前言中提及50-70年代的讲述历史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时,认为这种题材在出现和走向经典的过程中承载着巨大的意识形态性,“它们承担了将刚刚过去的‘革命历史’经典化的功能,讲述革命的起源神话、英雄传奇和终极承诺,以此维系当代国人的大希望与大恐惧,证明当代现实的合理性,通过全国范围内的讲述与阅读实践,建构国人在这革命所建立的新秩序中的主体意识。”因而,对于他来说,在对这些革命历史小说重新解读时,他的目的便是“回到历史深处去揭示它们的生产机制和意义架构,去暴露现存文本中被遗忘、被遮掩、被涂饰的历史多元复杂性。”[4]2-3历史是一个巨大而复杂的存在,既散逸在已逝的时光隧道里,又被刻在了典籍木牍石碑上,既指官修正史,又包含民间野史趣闻。历史是一副丰富而多义的画卷,任何试图对它的描述都充满了陷阱和困难。那么,面对历史这种模糊而暧昧的面孔,历史叙述何为?文学性的文革叙事又能何为?
提到历史叙述不能不说到旧历史主义与新历史主义的两种历史叙述。前者认为历史是确证与实存的,是客观、连续、整体的实存,而他们的历史叙述认为通过语言和叙事可以触摸、勾勒和恢复这一历史情境。而新历史主义则认为历史是一种文本和话语,具有偶然性、临时性,只能通过文学技巧和“想像的建构力”[5]419获得,“利用真实事件和虚构中的常规结构之间的隐喻式的类似性来使过去的事件产生意义”便形成了所谓的历史叙事。[6]171历史学或历史哲学视野里的历史叙述通常包含事实的意义层(数据或资料)与阐释的意义层(解释或关于事实的故事),[6]186而后者的获得在怀特和科林伍德这儿通常是通过建构的想象力和文学的手段如隐喻、象征去获得,正是在这一点上,历史叙述在史学和文学这两个学科间找到了共同的交汇点,“如何组合一个历史境遇取决于历史学家如何把具体的情节结构和他所希望赋予某种意义的历史事件相结合。这个作法从根本上是文学操作,也就是说,是小说创造的运作。”“事实上,历史……是按照诗人或小说家所描写的那样使人理解的……不管我们把世界看成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解释世界的方式都一样。”①需要说明的是,指出历史叙述在小说与历史领域二者的类同是为了从方法论上借鉴史学中的历史叙述,进一步拓宽文革叙事的研究,而且,小说的历史叙述首先也涉及到作家如何看待历史的问题,这也涉及到作家的历史观和历史哲学等问题,因而,对照历史与历史哲学这一参照系理应会便于本论文的研究。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历史叙述在两个不同学科间的差异也是很明显的,坚持这种差异的主要还是旧历史主义者们,这点怀特在《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本文》中简略提及过。有学者指出,史学与文学的历史叙述在创作态度、选择事件和故事组合方式上不同(分别参见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65、178页;李纪祥:《时间·历史·叙事》,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7页)。
由于历史是复杂而多面的,对历史的认识与叙述便处于一种变化之中,这就涉及到历史叙述的发展性和变化性问题,指出这点很重要,历史叙述的变化也直接可以解释中国三十年来文革叙事发生变迁和叙述重心转移的原因。那么,历史叙述缘何而变?历史之所以能存在,用汤因比的话讲是基于一种假设,这种假设是“现实具有某种意义,而且是我们在解释活动中能够把握的意义……在千变万化的现象之间至少存在着某些秩序或规律。”[7]425于是,认识历史与理解历史便包含在一种动态的过程以及过去与现在相互影响的二维交互之中了,“实际上,当前的理解处于不断地形成过程中,当前的现实也不可能完全摆脱过去。过去规定着现在,现在也重新理解着过去。理性反思到人类知识是有局限的,从而确证了理性的历史性。”[3]136-137对此,爱德华·卡尔在《什么是历史》一书中指出历史就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无终止的对话。因此,对历史的理解在作家这儿是个历史过程,理性反思在现在和过去两重关系间是个历史性的过程,历史理解和历史叙述也便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了。
历史叙述的历史性和变化性带来了历史叙述的多样性,中国当代文革叙事的多样性在这儿也找到了部分原因。文革是新时期以来作家面对的最近也最压抑的历史,对这段历史的描述,不同作家的叙述与书写也呈现出不同的风格与形态。一段文革演绎几多伤心事,一段往事又带出多少悲喜剧。围绕文革,在近三十年产生了大量的小说文本以及多姿的叙事风格。围绕文革何以会形成这么多的历史叙述?海登·怀特在《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本文》中的论述部分地揭示了其中原委。“在历史上,从一个角度看是悲剧性的事情也许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就是喜剧性的。在同一个社会里从某一阶级立场来看似乎是悲剧性事件,但另一个阶级则可以把它看成是一场滑稽戏。”怀特认为历史事件本身在价值判断上是中立的,最终成为悲剧、喜剧、传奇或讽喻中的哪种范畴,取决于按照何种情节结构或神话组合,关键是如何排列事件顺序、如何编织历史片段,“以便提供关于事件的不同解释和赋予事件不同的意义。”[6]163-164怀特继而以法国大革命为例,指出米歇利特将之描写成浪漫主义超验论的一个戏剧,同代人托奎维利则将它写成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悲剧。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面对同一历史故事,两人“不同编排故事的方式”和“采取的不同叙事视点”导致风格迥异的历史叙事。在一些历史学家看来,历史是由异质性与间断性构成的,由一个事情,一个人物,一个结构,悲欢离合或典章古籍构成了这个社会的“殊相”,每一个“殊相”都是一个存在的点,对应着一个“视点”,由于人们视点的不同导致了视物时“殊相”的差异,这便造成了我们在研究历史时有时强调的是政治,有时是经济或是思想,这来源于时代、环境的影响,来源于视者的不同。不同环境的不同视点造成了侧重生产方式、政治因素或地理因素、人伦关系的不同,因而历史叙述呈现出不同。[8]9这对我们从宏观上理解三十年来当代小说家书写文革题材小说呈现出的丰富驳杂、参差多姿的现状有一定的启示性。作家的不同生命历程与历史体验(亲历文革,还是想像文革)、不同历史观念(乐观的进化论史观,还是怀疑的解构的历史观)、不同的地域环境与教育背景、不同创作目的(印证主流意识形态规定的历史讲述,还是反抗主流叙事),等等的差异导致了叙述文革的“视点”不同,视点的不同以及作家“排列事件顺序”的不同便导致了文革叙述风貌与形态的差异。客观地讲,文革叙述的悲剧性、喜剧化;主流化,民间化;启蒙式,游戏化书写除了与作家采取的不同视点和编排故事的方式有关,还与不同时期的主流文化、意识形态规约、读者审美文化心理、作家的历史意识和文学观念等相关,这些因素合力导致文革叙述呈现出多元芜杂的现状。
二
从宏观上分析了历史叙述的内涵、功能以及文革叙述的多样性和发展性后,接下来我们会将目光聚焦到文革叙述的现状、困境和出路上来。
孟悦在《历史与叙述》中将康有为、梁启超以及“五四”一代文化先驱称为观照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读史者”,“(他们的)‘读史’行为乃是一种象征行动,它在文化领域完成了生产方式领域、社会政治领域所没有完成的‘革命’任务。”而他们“读史”形成的小说叙事“一直是关于历史、关于民族生存的叙事”。[9]18那么,新时期以来的知识分子作家,面对文革这段历史时,这些读史者又是如何去读和叙的呢?面对文革,如何阅读,如何叙述,应该是新时期以来作家的集体焦虑,如同芒刺在背,不拔不行,想拔除却不知道如何痛快淋漓地施展手脚。
尤其对于亲历文革或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作家,文革如梦魇一样如影随形,出生于上世纪30-50年代作为历史亲历者的作家们对文革有着切肤的体验,正如叶兆言所言:“毫无疑问,我属于那个时代里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世界观不可能不带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刻烙印,也许是烙印太深了,时至今日,我总有一种疑惑,那就是‘文化大革命’究竟有没有结束。”[10]62这种深刻烙印和历史震惊形成的文化记忆即使在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那儿依然顽强,他们同样留存着对文革的或清晰或模糊的印记,“可以这样说,在我的创作中,有关‘文革’的部分更能体现我的写作。我生于1964年,其实,对‘文革’我有切肤的认识,也就是说,不只是记忆。”[2]对于当代作家而言,这种强烈的文化记忆与历史体验必然要诉诸创作和历史叙述,尽管新时期三十余年已经产生了林林总总的关于文革的小说叙述,显示出追求历史还原或历史建构的雄心,但过于共识化的意识形态性的书写或是一味个人化、民间化的文革叙事使这种历史叙述显得粗疏、表象而无序,这种讲述民族往事的历史叙事还是呈现出它的集体焦虑,正如研究者指出的,“到现在,我们拥有了多重经验以后怎么讲述自己、讲述这个民族一百年来的遭遇,这个问题就没有解决,一大批作家为此寝食不安,他们想为此做出自己的表述。”[11]万之在介绍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罗马尼亚的“知青作家”作家缪勒时,盛赞她固执而顽强地书写齐奥塞斯库统治下的重负,而形成了“无家可归状态的风景”,对比中国的知青作家,“(他们)大多数在写了几本过去的底层生活之后,就开始‘与时俱进’,追求时尚,随波逐流,或者玩弄写作技巧,翻点‘现代派’的新花样,但是他们对苦难的记忆却日益模糊,感情日益麻木,不用说鲁迅式的‘呐喊’,甚至连‘呻吟’都听不见。”[12]288没有对民族苦难执着的表述与书写,忙于对新潮与文学技艺的追新逐异,过早地放逐了对文革的历史记忆与叙述,这是知青一代受到责难的原因,这种批评还是很有道理的。其实,在中国文学界或知识界,不乏这样的知识分子或作家:他们对民族苦难的历史从未相忘,执着于用手中的笔去书写,去叙述,去延续记忆,去建构历史,去追问或反思,比如韩少功、李锐等作家。极富思想家气质的韩少功不仅创作了大量文革题材小说,在大量的思想性随笔、访谈、对话录中表达了对文革的深邃性思考。在和王尧的对话录中他提出在反思文革时要杜绝“妖化文革和美化文革”[13]21、9-10两种倾向,同时也不应对文革作简单想像和判断,文革首先要靠中国知识分子和知识界来反思,不能像西方学者那样审视文革。丁帆等学者指出用现代和后现代文化理论在反思、书写文革与文革文学虽然带来了很高的理论切入,但也要防止文化思想理论与文学事实之间的错位。[14]138
知识界的这种声音对于文革叙述有着很好的匡正和补充作用。但创作与理论毕竟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创作领域中的对于文革的历史讲述不容乐观。新时期之初的文革叙述在表述文革经验和时代创伤上显示出正面强攻的直面姿态,无论是真诚而有责任感的态度还是现实主义创作手法,都显示出“亲历者”们对文革的真诚反思,但此时由于特定的政治文化和主流话语的规约,此时的文革叙述无论在艺术还是在思想深度上都处于文革叙述的起步阶段。1985年后,随着社会语境的开放和文学主体性的自觉,文学开始疏离历史,大历史逐渐淡出作家的书写,“历史”开始从叙述中滑脱。[9]27洪子诚先生认为新时期之初的作家在叙述文革时将文革处理成了历史进程中的偶然、暂时的事件,这种概念化、主观化的文革叙述简化了历史的复杂性。在这篇谈《鼠疫》的阅读笔记中,[15]214-216他对比中国伤痕、反思小说,通过灾难(灾变)主题对比加缪和新时期的作家处理的不同态度与方式,认为中国作家太过乐观与光明地对待灾难与创伤,这些看似明亮、快慰的结尾缺乏的是“对于灾难的绝不屈膝投降的态度和行动”,中国作家过早地将自己的叙述当作了胜利的证词,而《鼠疫》的差别在于:在一些人止步的地方,另一些人却继续他们的追问与思考。
三
那么,该如何想像和叙述文革的历史呢?
对于小说家而言,该如何进行历史叙述才是有效而有意义的,这个问题是作家进行历史题材创作不容回避的问题,或者说,这也是研究者或批评者应该提醒作家的地方。彼得·盖伊在《小说的真理》中认为伟大的小说家通过完美的虚构可能创造出真正的历史。盖伊以拉美马尔克斯出版于1975年的《独裁者的秋天》为例,细致分析了马尔克斯这部书写历史暴政和暴君的历史作品是如何利用历史、如何处理文学想象、历史真实与小说真理的关系。盖伊指出马尔克斯在处理独裁主题时并没有简单地把事实和虚构加以截然区分,让历史成为人物心灵世界的背景,同时通过多个叙述者轮流讲故事、模棱两可的叙述方式故意切断可能说明事实的蛛丝马迹,从而让小说带有了寓言性质,在对专制和暴君的描写中,对极权下人的生存境遇的怜悯,人类孤独等主题呼之欲出。因而,“他利用文学的想像手法做到了历史学家想做或应该做却做不到的事情,他写了一本极具历史意义的小说……这本小说以最戏剧的形式提出了小说中的真理此一问题。”[16]153以小说探讨历史的真相,或在历史叙述中用完美的虚构创造出真正的历史,这是彼得·盖伊苦心追问的真理所在。
追寻历史的真理也好,建构历史的本质也好,这毕竟是历史叙述力图要达到的理想目标。那么究竟用什么形式或方式去呈现呢?费里德兰德对于电影和小说中处理纳粹第三帝国和最终判决时存在的美化现象曾给予了严厉的批评,这种把第三帝国的事件建构为喜剧或田园牧歌的美化式叙事在费里德兰德这儿是不可接受的。然而对于如何表述诸如革命、灾难、战争浩劫,不同流派的人各执一词。乔治·斯坦纳和A.R.艾克哈德都认为这些领域的讲述是在“语言”之外的。兰格认为除了用沉默对待之外,大屠杀和灾难叙事应杜绝使用比喻性语言和比喻性表达。在兰格看来,这种比喻性语言对真实历史会发生增添或篡改,容易将事件中的行为者和行为人格化,影响历史真实和对历史的理解。因而,兰格的理想是杜绝比喻性语言,防止造成或揭示真相上的歪曲,而依赖字面语言来揭示历史与政治的真实本质,因而,这可视为兰格式的从事实或字面意义的角度阐释和叙述历史的范式。王安忆和张旭东在近年的一次题为《理论与实践:文学如何呈现历史?》的对话中探讨了在叙述和想像历史中的“纪实与虚构”、“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等理论问题,他们认为真实性的纪实与现实经验固然便于历史叙述的操作,但过于直接和真实的经验有时往往会限制历史叙述和艺术想像,他们以史铁生为例说,“在他的写作里边,当他书写他的经验的时候,比如插队、生病、回城、街道厂、画彩蛋,他不大虚构,都是写实,而他一旦进入到抽象的领域……都是虚构的,就是说,现实经验反而限制他想象了。他从现实经验出来以后,他进入抽象的、玄思的一种写作的时候,他开始虚构了。”[17]从这一角度就容易理解新时期之初刚刚走出文革阴霾的作家们的历史叙述和特点了:他们大都是文革的亲历者,当他们开始用笔书写时,首先复苏和召唤的便是他们的文革经验和文革情感,由于缺少一种必要的审美距离和情感积淀,他们的写作都拘囿于这种太过直接的“现实经验”,想象力没法进入,只能是现实主义的写实和直面进入,在情感上也表现出不加节制的滥情(如写作时太多的泪水)。在内容上,他们的历史叙述具有书写共识性经验的特点,在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上有着“共谋”与“合流”的特性。
因而,讲述文革时选择怎样的叙述视点,选用写实的还是虚构的创作方法,采用隐喻象征的语言还是客观描绘的语言都影响着历史叙述的形态和风格,以及叙述意图和思想意义的表达。200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匈牙利籍犹太小说家凯尔泰斯,这个据一项在瑞典进行的调查显示96.4%的受访者从来没有听过的作家,当年成为了世界文坛的一匹黑马,那么,这个终身执着书写奥斯维辛经历的文坛“灰姑娘”在一夜之间如何声名鹊起,他以什么征服了严明而又挑剔的瑞典学院的评审委员的? 2001年纪念诺贝尔奖一百周年时瑞典学院举办的一个特别的研讨会,题目是《见证的文学》,这个研讨会为第二年凯尔泰斯获奖埋下了伏笔,因为瑞典学院向来是表扬特殊而独特的文学,而当年凯尔泰斯正好是这种特殊文学的代表,这就是给历史作见证的文学。何谓“见证的文学”,“就是文学能够起到为历史作见证的作用,作家应该记录个人在历史中的深切和真实的感受,用自己的语言去对抗以意识形态来叙述的历史和政治谎言,也就是给凯尔泰斯的颁奖词清楚地说明的,‘支持个人脆弱经验而反对历史的野蛮专横’。”[12]116-117凯尔泰斯一生创作并不多,他的获奖也不因为他在艺术风格和语言叙事上有所突破,正是因为他直面奥斯维辛,否弃了阿多诺“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的论断,坚持认为“奥斯维辛之后,只有写奥斯维辛”、“奥斯维辛通过我说话”,以其非凡的勇气在历史审判台上用脆弱的个体经验为历史作证。在我看来,凯尔泰斯提供了一种面对历史的不屈的精神姿态,更提供了一种叙述历史的基点与视角,而这正是他区别于很多描写奥斯维辛的作家的地方。那么作为一种见证者的叙述和见证的姿态,究竟是何意呢?面对历史时作为一个见证人,“在再现个人经验的历史时,作家只能是见证人而不是其他。他首先不能把自己当做法官,或者当做陪审团的成员,他不需要作出判决,或者干预判决,对谁有罪或者历史功过做出超越见证人立场的判决。因此,作家就只是一个当事的见证人,一个个人,而不代表法律,不代表任何意识形态,不代表道德标准,不代表任何政党、集团和政权。”[12]120而且从叙述的姿态和角度来看,“见证人必须有原本的当事人的立场和叙述方式,而不是脱离了时代背景的历史回顾的立场和方式。”[12]123以“原本的当事人的立场和叙述方式”进入到历史的书写和叙述时便会开启历史的原初情境,在这一原初情境中展开和历史的对话,在这种对话中不是单纯去声讨和暴露,甚至可以像凯尔泰斯在《无形的命运》中那样书写苦难中的温馨和快活,在这种对原初历史情境的重造与生活场景的原本再现以及人在苦难情境中痛与乐、恐惧与幸福的逼真复呈中,历史鲜活而有张力地通过作家的语言和叙述呈现出来。这种历史叙述相对于中国新时期初文革叙述中的控诉批判以及后来的夸张变形等种种叙述要独特得多,对于我们有较大的启发意义。
[1]李锐.重新叙述的故事[J].文学评论,1995(5).
[2]毕飞宇,汪政.语言的宿命[J].南方文坛.2002(4);李锐.“文革”是我终身要表达的命题[J].凤凰周刊,2006(35).
[3]韩震,孟鸣歧.历史·理解·意义——历史诠释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
[4]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5]南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99个词.[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
[6]海登·怀特.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本文[M]//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7]〔英〕汤因比.历史研究(插图本)[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8]李纪祥.时间·历史·叙事[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
[9]孟悦.历史与叙述[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
[10]叶兆言.记忆中的“文革”开始[M]//张贤亮,杨宪益,等.亲历历史.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
[11]张未民,等.追求历史的还原或建构——《圣西门口》座谈会纪要[J].文艺争鸣,2007(4).
[12]万之.诺贝尔文学奖传奇[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13]韩少功,王尧.韩少功王尧对话录[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
[14]丁帆,等.用现代和后现代文化理论解析“文革文学”的错位[M]//乐黛云,等.跨文化对话(13).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
[15]洪子诚.文学与历史叙述[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
[16]〔美〕彼得·盖伊.历史学家的三堂小说课[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17]陈婧祾.理论与实践:文学如何呈现历史?——王安忆、张旭东对话(上)[J].文艺研究,2005(1).
A Talk on the Literary Narrative of the“Cultural Revolution”History in the New Period
SHEN Xing-pei1,JIANG Yu2
(1.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Nanjing210097,China; 2.Nanguang School,Comm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Nanjing211172,China)
As the“Cultural Revolution”is the most recent and repressive history that Chinese writers of the new period are faced with,different writers’narration of and writing about the specific period are of different styles and forms.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how writers of the new period have“read”and“narrated”the“Cultural Revolution”,what historical errors and plights have occurred in its historical narration,and how they have found the approach to establishing an effective and ample platform for narrating the“Cultural Revolution”.
writers in the new period;a history of the“Cultural Revolution”;literary narration
I206.7 < class="emphasis_bold">文献标识码:A
A
1674-5310(2011)-05-0001-05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小说对‘文革’的叙事流变史(1977-2010)”(项目编号11CZW073),2010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新时期小说的文革叙事演进研究(1977-2009)”(项目号10VJC751066)的阶段研究成果。
2010-11-20
沈杏培(1980-),男,江苏泰州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姜瑜(1979-),女,江苏镇江人,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欧美文学。
(责任编辑:胡素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