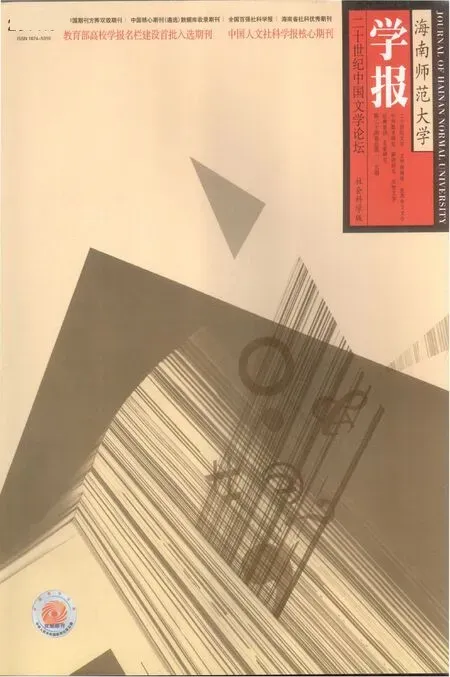诗乐合论:宋代“诗论”与“乐论”关系发微
韩 伟,吴铁柱
(1.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黑龙江哈尔滨 150025;2.黑龙江大学中文系,黑龙江哈尔滨 150080)
诗乐合论:宋代“诗论”与“乐论”关系发微
韩 伟1,吴铁柱2
(1.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黑龙江哈尔滨 150025;2.黑龙江大学中文系,黑龙江哈尔滨 150080)
宋代是继汉代诗、乐分途之后,两者融合的重要时期,其主要表现在于理论层面的诗乐合论。这种关系既表现在沈括、郑樵、王灼等人概论式的论说之中,亦有很多具体而微的表现,在宋诗话涉及的众多内容中对乐器、乐曲以及历代乐诗的评点占有一席之地,诗话中论乐成了宋诗话的重要特色。与此同时,对乐器、乐曲、乐诗的言说也使宋诗话对“诗”与“文”的分析更为形象而具体。
诗论;乐论;乐器;乐曲;乐诗
自《尚书·尧典》“诗言志,歌永言”始,诗与乐在理论上便被放在一起言说,尔后《乐记》、《毛诗序》中“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则从发生学角度看待两者的关系。这表明在先秦时期,与诗乐舞的浑融一致,诗与乐是合论的。虽然两汉、魏晋以后诗、乐开始分途,但这并未使两种艺术在理论层面彻底决裂。如《文心雕龙》中《乐府》篇便同样可以视为乐论,“诗为乐心,声为乐体”观念基本沿袭前说,除此之外《声律》、《时序》两篇也涉及音乐。与这种概论式的诗乐合论不同,《诗品》则试图在具体个案分析中将诗与乐相结合,如对曹植的评点便说:“陈思王之于文章,譬如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这同时也表明诗论与乐论的关系开始由显而入隐,到了唐代除了白居易等少数几人之外几乎无人在理论层面对二者的关系进行言说。而宋代文人则恰恰相反,在诗与乐深度融合的基础上,①对宋代诗、乐的深度融合之考察,笔者将另作文专论。诗论与乐论也表现出向传统模式复归之势。欧阳修、苏轼、黄庭坚、周惇颐、朱熹、李清照、沈括、王灼等人都已经将诗论与乐论等而视之,而南宋郑樵在《通志·乐略·正声序论》中的总结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宋人的基本倾向:
凡律其辞则谓之诗,声其诗则谓之歌,作诗未有不歌者也。诗者乐章也,或形之歌咏,或散之律吕,各随所主而命。主于人之声者,则有行,有曲。散歌谓之行,入乐谓之曲。主于丝竹之音者,则有引,有操,有吟,有弄。各有调以主之,摄其音谓之调,总其调亦谓之曲。凡歌、行虽主人声,其中调者皆可以被之丝竹。凡引、操、吟、弄虽主丝竹,其有辞者皆可以形之歌咏。[1]
可见宋人的普遍观念是将诗与乐章等而视之,认为不同之处仅是外在表现形态上存在差异而已,所以尽管郑樵名之为《乐略》,并且分目为“正声”、“别声”、“遗声”,但其中则是诗、乐并举的,从这个意义上看,宋代诗论与乐论关系变得更为密切。而本文认为,这种密切关系既表现为沈括、郑樵、王灼等人概论式的论说之中,亦有很多具体而微的表现,故拟以宋代大量存在的诗话、词话为基点,具体考察两者的融合状况进而为更深层次的理论言说打下基础。
一 宋诗话与乐器
宋人诗话极为浩博,据考证仅宋代单独成书的诗话便有一百七十余种。[2]散佚之作尚有数百万字,而这些诗话的突出特点是多以片段评点形式出现,其中涉及的内容十分丰富,因此不免有芜杂之感,在众多内容中对乐器、乐曲以及历来乐诗的评点占有一席之地。这是前代文论很少涉及的层面,而宋诗话往往对这几方面进行十分周详的考证。
就乐器言之,宋人诗话、词话亦有对乐器及弹奏技巧的介绍。琴、笛、琵琶是宋人较为欣赏的几种乐器,其中琴属雅乐器,多出现在文人的诗歌酬唱之中,而笛与琵琶由于源自西域,所以多在俗乐中出现。总体上,宋诗话也是沿着这一分野而进行论述的。《渔隐丛话》辑《复斋漫录》、《西清诗话》言鼓琴之事曰:
《复斋漫录》云:元微之诗:“尔生不我待,我愿裁为琴。宫弦春似君,君若春日临。商弦廉似臣,臣作旱天霖。”盖取《史记》:“驺忌子闻齐威王鼓琴而为说曰:大弦浊以春温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西清诗话》乃云:“吴僧义海琴妙天下,而东坡听惟贤琴,有大弦春温和且平,小弦廉折亮以清之句。”至谓东坡未知琴趣,不独琴为然;殊不知亦取驺琴之事耳,可谓不学。
自魏晋以来文人一直对琴情有独钟,并将琴弦音响赋予道德意味,有意识地将琴乐人格化、道德化,这自然便成为了宋诗话的言说对象,并且对咏琴之诗进行考证和品评(见下文)。蔡正孙在《诗林广记》中亦谈及羌笛,“《春夜洛城闻笛》:‘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胡苕溪云‘《乐府杂录》云:笛者,羌乐也。古曲有《折杨柳落梅花》之名,故杜少陵亦有《吹笛诗》云:故园杨柳今摇落,何得愁中曲尽生。王涣之亦云: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此皆言折杨柳曲也。”[3]其中不仅列举含有羌笛的诗句,更为重要的是对唐宋以来的竹笛缘起进行考证,并指出了羌笛音色上的特点,以其苍凉的音色经常与离愁别绪相得益彰。事实上,宋代无论是宫廷雅乐还是民间俗乐中羌笛都是必不可少的乐器,笛、筚篥、琵琶等乐器早在唐代就已经十分盛行,《隋书·音乐志》中龟兹部(胡部)所载乐器包括:琵琶、五弦、笙、笛、箫、觱篥、毛员鼓、都昙鼓、答腊鼓、腰鼓、羯鼓、鸡娄鼓、铜钹、贝等等,到了宋代教坊乐与民间音乐更进一步吸收这些乐器,弦乐与管吹乐的应用范围甚至超过了传统的金石之声。在宋代歌诗盛行的大背景下,诗论与文论中涉及这些乐器就不足为怪了。
如上述,胡乐器中除了羌笛在宋人诗话中经常出现之外,琵琶也被经常谈及。在《韵语阳秋》卷十五中葛立方整理了众多关于琵琶的诗话片段。[4]其中既有对“昭君自弹琵琶”之遗事的考订,认为“马上弹琵琶非昭君自弹”,亦有对五弦与琵琶关系的考证,认为“五弦之制亦出于琵琶也”,并进一步称:
乐天有《五弦弹》诗云“赵璧知君入骨爱,五弦一一为君调”,又云“惟忧赵璧白发生,老死人间无此声”,想其搊弹之妙冠古绝今,人未易企及也。尝观《国史补》云“人问璧弹五弦之术,璧曰吾之于五弦也,始则神遇之,终则天随之,眼如耳,耳如鼻,不知五弦之为璧,璧之为五弦也”,其庄周所谓用志不分乃凝于神者乎。韦应物云“古刀幽磬初相触,千珠贯断落寒玉。”张祜云“小小月轮中,斜抽半袖红”元稹云“促节频催渐繁拨,珠幢斗绝金铃掉”亦可见五弦声韵制作之仿佛矣。
通过对五弦、琵琶两种乐器形制的考订,进而分析两种乐器的渊源关系以及五弦的声韵特点。除此之外,《韵语阳秋》还十分详细地记载了琵琶的弹奏技巧,“弹丝之法妙在左手脱,右优而左劣,亦何足论乎?尝观《琵琶录》云‘元和中曹保有子善才,善才有子纲,皆能琵琶,又有裴兴奴,长于拢捻,时人谓纲有右手,兴有左手,盖拢捻在左手也,纲劣于左手,则琵琶之妙处逝矣’白乐天有《听弹琵琶示重莲》诗云:‘谁能截此曹纲手,插向重莲红袖中’。惜乎乐天未知截兴奴手之妙也。”琵琶在不断汉化的过程中逐渐在文人的日常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其形制及演奏技巧已发生了不少变化,据郑祖襄先生考证:“胡琵琶原本没有品,汉化以后的俗琵琶使用了品。有品的琵琶图像在宋代还能见到,如河南禹州白沙北宋墓散乐壁画中的琵琶、山西平定县姜家沟1号宋墓乐舞壁画中的琵琶。”[5]汉化的过程就是不断被使用的过程,如此情况,说明琵琶在宋诗话中出现绝非偶然。
除了上述三种主要乐器之外,钟、鼓、筚篥、竽、笙等乐器在宋人诗话中亦经常出现,虽然不像《乐书》、《文献通考》、《通志》那样着重对形制、源流的考订,但往往能从文学角度看待各种乐器的变迁,从一个层面反映了各个时代音乐与文学相结合的状态,不仅对考察诗歌题材特点有所帮助,也对音乐史有着重要贡献。
二 宋诗话与乐曲
就乐曲而言,宋诗话中谈及最多者当是对唐大曲《霓裳羽衣曲》的考证。《西清诗话》、《蔡宽夫诗话》、[6]《苕溪渔隐丛话》、《韵语阳秋》、[7]602—603《碧鸡漫志》等都谈及此曲,其中主要问题是考证《霓裳羽衣曲》的产生过程及基本特色。宋人普遍认为此曲源自西域,经唐玄宗改造而成。《西清诗话》载:
余尝观唐人《西域记》云:“龟兹国王与臣庶知乐者,于大山间听风水之声,均节成音,后翻入中国,如《伊州》《凉州》《甘州》,皆自龟兹至也。”此说近之,但不及《霓裳》耳。郑嵎《津阳门诗注》:“叶法善引明皇入月宫,闻乐归,留写其半。会西凉府杨敬远进《婆罗门曲》,声调吻合,按之便韵,乃合二者,制《霓裳羽衣曲》”,则知《霓裳》亦来自西域云。[8]176
从中不难看出一直以来在《霓裳羽衣曲》的产生问题上,存在虚与实两种看法,“明皇入乐宫”事为虚,“杨敬远进《婆罗门曲》”事为实。而历来文献中多以前者为据,《苕溪渔隐丛话》曰:“明皇游月宫事,凡见于五书。郑嵎《津阳门诗注》、《明皇杂录》、《高道传》,此三书皆云:‘叶法善引明皇游月宫,闻乐,归作《霓裳羽衣曲》。’《唐逸史》云:‘与罗公远同游。’《异人录》云:‘与申天师同游。’惟此二书为异。余尝考《高道传》,亦有《罗公远列传》,无游月宫事,则知《唐逸史》之误无疑。若《异人录》别无以证之,未遽以为误也。”[9]所以《霓裳羽衣曲》在唐代是带有浓重神秘色彩的,这种说法在开元、天宝年间十分盛行,一方面源于野史之杜撰,而另一方面则源于文学家的文学想象,而后世往往据之以为事实。其中白居易《长恨歌》最早提及《霓裳羽衣曲》,《长恨歌》演绎明皇游仙宫与玉环相见之事,其中帝王日常玩乐多奏《霓裳羽衣曲》,待到明皇游仙宫两人重逢,玉环的姿态则是“风吹仙袂飘飘举,犹似《霓裳羽衣舞》”,这样的描述自然使这个舞曲带有了神秘而浪漫色彩。故后世注家及野史作者多从浪漫角度言及该舞曲的产生。
宋人对《霓裳》之产生的另一种认识,则属于“实”的层面。即认为各种野史、遗事中记载的明皇游仙宫,归而作《霓裳》事为荒诞杜撰。王灼在《碧鸡漫志》中便持这种观点,称:
《霓裳羽衣曲》,说者多异。予断之曰:“西凉创作,明皇润色,又为易美名。其它饰以神怪者,皆不足信也。《唐史》云:‘河西节度使杨敬忠献,凡十二遍。’白乐天《和元微之霓裳羽衣曲歌》云:‘由来能事各有主,杨氏创声君造谱。”自注云:“开元中,西凉节度使杨敬述造。’郑嵎《津阳门诗》注亦称西凉府都督杨敬述进。”予又考《唐史·突厥传》,开元间,凉州都督杨敬述为暾欲谷所败,白衣检校凉州事。乐天、郑嵎之说是也。[10]51
王灼认为《霓裳羽衣曲》当源于西凉《婆罗门曲》,传入中土以后经唐玄宗润色进而本土化,王灼为南宋高宗时人,其时各种材料已经较为详备,在考证《唐史·突厥传》、杜佑《理道要诀》、郑嵎《津阳门诗注》及白乐天、刘梦得等数人诗作之后,明确指出:“月宫事荒诞,惟西凉进《婆罗门曲》,明皇润色,又为易美名,最明白无疑。”可以说,这种观点代表了宋人对《霓裳羽衣曲》的成熟认识。
与对起源问题的考证相应,宋人亦对《霓裳》的音乐特色进行考察。在《霓裳曲》所属宫调问题上,时人多将其归为道调法曲。所谓道调,为宫调之胡名,“二十八调之中,调多胡名,如宫调,胡名道调。商调,胡名大食调,又名越调”。[11]如上述,《霓裳曲》源于西域《婆罗门曲》,而该曲则属于商调,郭茂倩《乐府诗集》引《乐苑》语称:“《婆罗门》,商调曲。开元中,西凉府节度杨敬述进。”[12]基于这种认识,葛立方在《韵语阳秋》中纠正了宋人的错误,称:“若以为道调,则误矣。乐天《高阳观夜奏霓裳》云:‘开元遗曲自凄凉,况近秋天调是商。’则《霓裳》用商调,非道调明矣。”[7]603与其相似,王灼《碧鸡漫志》亦考证称:“明皇改《婆罗门》为《霓裳羽衣》,属黄钟商。云:时号越调,即今之越调是也。白乐天《嵩阳观夜奏霓裳》诗云:‘开元遗曲自凄凉,况近秋天调是商。’又知其为黄钟商无疑。”[10]54由这些考证可知,虽然到了宋代《霓裳》大曲全貌已经难以见到,①《宋史·乐志》载:“庆节上寿,及将相入辞……所奏凡十八调四十曲:一曰正宫调,其曲三,曰《梁州》、《瀛府》、《齐天乐》;二曰中吕宫,其曲二,曰《万年欢》、《剑器》;三曰道调宫,其曲三,曰《梁州》、《薄媚》、《大圣乐》;四曰南吕宫,其曲二,曰《瀛府》、《薄媚》;五曰仙吕宫,其曲三,曰《梁州》、《保金枝》、《延寿乐》;六曰黄钟宫,其曲三,曰《梁州》、《中和乐》、《剑器》;七曰越调,其曲二,曰《伊州》、《石州》;八曰大石调,其曲二,曰《清平乐》、《大明乐》;九曰双调,其曲三,曰《降圣乐》、《新水调》、《采莲》;十曰小石调,其曲二,《曰《胡渭州》、《嘉庆乐》;十一曰歇指调,其曲三,曰《伊州》、《君臣相遇乐》、《庆云乐》;十二曰林钟商,其曲三,曰《贺皇恩》、《泛清波》、胡渭州》;十三曰中吕调,其曲二,曰《绿腰》、《道人欢》;十四曰南吕调,其曲二,曰《绿腰》《罢金钲》;十五曰仙吕调,其曲二,曰《绿腰》、《采云归》;十六曰黄钟羽,其曲一,曰《千春乐》;十七曰般涉调,其曲二,曰《长寿仙》、《满宫春》;十八曰正平调,无大曲,小曲无定数。”(见脱脱等:《宋史》卷一百四十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239页)可知,宋时《霓裳》大曲已经不在庙堂之上存在。只见其谱难见其容,但是宋代诗论、文论仍对其十分重视。一方面,说明宋人并没有严格将诗论与乐论进行界限区分,诗论中谈及乐曲是作为一种十分正常现象出现的。另一方面,亦表明在实践层面诗与乐也应该是共存的,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宋代歌诗的实际情况。详考宋人诗话,会发现除了《霓裳》曲之外,对《三台》、②(宋)张表臣《珊瑚钩诗话》卷二载:“乐部中有促拍催酒,谓之‘三台’,唐士云:蔡邕自持书,御史累迁尚书,不数日间遍历‘三台’,乐工以邕洞晓音律,故制曲以悦之,又始作乐,必曰‘丝抹将来!’盖丝竹在上,钟鼓在下,丝以起之,乐乃作。唐以来如是,非古所谓合止柷敔也。”按,为唐代教坊舞曲,玄宗开元以前人作。据《乐府诗集》引《乐苑》称“天宝中,羽调曲有三台,又有急三台”急曲凡三十拍,自唐至宋,均入酒令,用以催酒。《凤将雏》③《 韵语阳秋》卷十五载:“《凤将雏曲》,吴兢乐府题要云‘汉世乐曲名也’而郭茂倩《乐府诗集》中无此词,独《通典》载应璩百一诗云‘为作陌上桑及言凤将雏’张正见置酒高殿上云‘琴挑凤将雏,当是用相如鼓琴,挑云凤兮归故乡,四海求其凰之义’则此曲其来久矣。按《晋书·乐志》吴声十曲:一曰《子夜》,二曰《上柱》,三曰《凤将雏》,此三曲自汉至梁有歌,今不传矣。”等舞曲亦多有考证,那么下面的问题是,宋人诗话中对这些大曲或教坊曲的考证具有什么样的深层意义呢?
宋诗话中对这些舞曲多以考证为主,这与唐代以前诗论、文论侧重对舞姿、曲调的感性描绘明显不同。本文认为,考证除了表明宋人致力于恢复舞曲原貌,恢复诗、乐融合传统之外,更彰显了宋人的独特审美风尚。具体言之,可以分作两个层面:其一,对舞曲的考证开始由虚而入实,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唐宋两代审美倾向的变化。以《霓裳》曲为例,唐代提及此曲多见于诗歌之中,据考证多达九十余篇。[13]这些诗作多从浪漫角度进行取材,往往倾向于明皇游月宫事。与此同时,与其它大曲相比,《霓裳》也是在唐人诗作中被提及最多者,这也符合唐代天真浪漫的整体审美风尚。而宋人诗作中虽多涉及《霓裳》者,但多复归理性的反思。如徐铉《又听霓裳羽衣曲送陈君》“清商一曲远人行,桃叶津头月正明。此是开元太平曲,莫教偏作别离声”、韩琦《初会醉白堂》“自向酒中知有德,更于琴外晓无弦。霓裳百指非吾事,只学醺酣石上眠”、祖无择《琵琶亭》“晚泊湓江半客舟,琵琶亭下动闲愁。霓裳绿腰杳何许,枫叶荻花空自秋”等等。除了具体诗作之外,宋诗话则更能体现宋人“尚实”审美风尚的,上文所列对各舞曲的产生、特色的考证便可说明问题。不赘述。其二,宋代诗话、文论的基本倾向开始重视客观言说。自欧阳修《六一诗话》始,宋代诗话表面看来以片段性的语录为主,似乎并不执迷对某一问题的深入探究,但实际上宋人所下断语是建立在深厚的学养基础上的,某些内容是作为一种共识性知识而被有意隐去的,而对于某些存在歧义性的问题,则以考证为主。上文提到的各种诗话对《霓裳》舞曲的考证恰属于后者,这样做的目的无疑是为了追求知识的准确性,并希望达成某种共识,为进一步的断语性言说提供普适性材料。所以本文认为宋代诗话的突出特点便是建构了一种高度抽象式的理论模式,以直达本质的方式对现象进行抽离和超越,简短的断语背后往往以丰富的实证材料作为支撑。从对《霓裳》等舞曲的考证足见一般。
三 宋诗话与乐诗
就乐诗而言,相比于乐器、乐曲,宋诗话对乐诗的关注是最为突出的,宋及宋前的各种反映音乐题材的作品经常成为宋诗话论说和考订的对象,构成了宋诗话的重要特色。《西清诗话》[8]192-193和《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六)中都有下面记载:
三吴僧义海以琴名世。六一居士尝问东坡:“琴诗孰优?”东坡答以退之《听颖师琴》,公曰:“此只是听琵琶耳。”或以问海,海曰:“欧阳公一代英伟,然斯语误矣。昵昵儿女语,恩怨相尔汝。……皆指下丝声妙处,惟琴为然。琵琶格上声,乌能尔邪?退之深得其趣,未易讥评也。”东坡后有《听惟贤琴诗》……诗成欲寄欧公而公亡,每以为恨。客复以问海,海曰:“东坡词气倒山倾海,然亦未知琴。春温和且平,廉折亮以清。丝声皆然,何独琴也?又特言大小弦声,不及指下之韵。牛鸣盎中雉登木,概言宫角耳,八音宫角皆然,何独丝也。”闻者以海为知言。余尝考今昔琴谱,谓宫者非宫,角者非角,又五调迭犯,特宫声为多,与五音之正者异,此又坡所未知也。
即是说在僧义海看来,欧阳修、苏轼对韩愈《听颖师弹琴》的理解都是存在问题的,而将其视为咏琵琶诗更是谬之千里,甚至后来苏轼《听惟贤琴诗》的词句亦是不够准确,多少受到了当时“五音迭犯”整体环境的影响。宋人包括苏轼、欧阳修等人经常赋诗,或描摹乐器,或描写听乐感受,形成了题材非常独特的一类诗歌,本文权称之为“乐诗”,与这些乐诗创作相呼应,文人之间亦经常进行相关讨论,上述对韩愈《听颖师弹琴》的讨论便是很好的例证。宋诗话中记载的这些片段不仅能帮助还原当时社会文人以乐诗相互唱和、切磋的事实,亦展示出了当时的文艺思想状况,构成了宋代诗话的独特风貌。除了上面的例子,类似诗话中的记载还有很多,兹举数例:
《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六:“东坡《听琵琶诗》云:‘何异乌孙送公主,碧天无际雁行高。’乃用《文选·王明君辞序》云:‘昔公主嫁乌孙,令琵琶马上作乐,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尔。’则琵琶非起于明君,盖前已有也。《释名》云:‘琵琶本胡中马上所鼓也,四弦象四时也。推手向前曰琵,却手向后曰琶,因以为名焉。’”
《彦周诗话》:“韩退之《听颖师弹琴诗》云:‘浮云柳絮无根蒂,天地阔远随飞扬。’此泛声也,谓轻非丝、重非木也;‘喧啾百鸟群忽见,孤凤皇泛声中寄。’指声也;‘跻攀分寸不可上’,吟绎声也;‘失势一落千丈强’,顺下声也。仆不晓琴,闻之善琴者云:‘此数声最难工’,自文忠公与东坡论此诗,作听琵琶诗之后,后生随例云云,柳下惠则可,吾则不可,故论之少,为退之雪冤。”
《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十:“《后山诗话》谓:‘六一居士闻杜彬弹琵琶,作诗云:坐中醉客谁最贤?杜彬琵琶皮作弦。自从彬死世莫传,皮弦世未有也。’丙戍岁,居苕溪,暇日因阅《酉阳杂俎》,云:‘开元中,段师能弹琵琶用皮弦,贺怀智破拨弹之,不能成声。’因思永叔、无已皆不见此说,何也?”
《诗话总龟》卷六:“昔苏子美言乐天《琵琶行》中云‘夜深忽梦少年事,觉来粉泪红阑干’此联有佳句。余谓梦得《武昌老人吹笛歌》云‘如今老去语犹迟,音韵高低耳不知。气力已无声尚在,时时一曲梦中吹。’不减乐天。”
《诗话总龟》卷二十:“刘仲几饯饮东坡,中觞闻笙箫声杳杳在云霄间,抑扬往返,粗中音节,徐而察之,则出于双瓶,水火相搏自然吟啸,食顷乃已。坐客惊叹请作《瓶笙诗》以记云‘孤松吟风细冷冷,独蠒长缫女娲笙。陋哉石鼎逢弥明,蚯蚓窍作苍蝇声。瓶中宫商自相赓,昭文无亏亦无成。东坡醉熟呼不醒,但云作劳吾耳鸣’。(辑自《百斛明珠》)”
《韵语阳秋》卷十五:“《后庭花》,陈后主之所作也。主与幸臣各制歌辞,极于轻荡,男女唱和,其音甚哀,故杜牧之诗云‘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阿滥堆》唐明皇之所作也。骊山有禽名‘阿滥堆’,明皇御玉笛将其声翻为曲,左右皆能传唱,故张祜诗云‘红叶萧萧阁半开,玉皇曾幸此宫来,至今风俗骊山下,村笛犹吹阿滥堆’二君骄淫侈靡耽嗜歌曲,以至于亡乱,世代虽异,声音犹存,故诗人怀古皆有犹唱犹吹之句,呜呼,声音之入人深矣。”
综上可知,宋代诗话中蕴含大量关于乐器、乐曲、乐诗的内容,诗话中论乐也成了宋诗话的重要特色。但这只是诗话与乐论关系之一维,与此同时,乐在诗话中亦并非处于被动的被描述和被阐释的地位,它反过来也对诗论、文论的进一步深入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文认为这种作用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得以实现,一是以乐评诗,一是以乐论文。①限于篇幅,对“以乐评诗”及“以乐论文”将另作专文论述之。
[1](宋)郑樵.通志二十略[M].王树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5:887.
[2]吴文治.前言[M]//宋诗话全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3](宋)蔡正孙.诗林广记:卷三[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482册:34.
[4](宋)葛立方.韵语阳秋:卷十五[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201-203.
[5]郑祖襄.宋元明琵琶图像考——琵琶乐器汉化过程的图像分析[J],中国音乐学,2008(4).
[6]郭绍虞.宋诗话辑佚[M].北京:中华书局,1980:401.
[7](清)何文焕.历代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1:602-603.
[8]张伯伟.稀见本宋人诗话四种[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176.
[9](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十四[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159-160.
[10]岳珍.碧鸡漫志校正:卷三[M].成都:巴蜀书社,2000:51.
[11](明)倪复.钟律通考:卷六[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12册:743.
[12](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八十[M].北京:中华书局,1979:1128.
[13]王安潮.《霓裳羽衣曲》考[J].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学报,2007(4).
A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Poetic Theories”and“Music Theories”
HAN Wei1,WU Tie-zhu2
(1.Department of Chinese,Harbin Normal University,Harbin150025,China; 2.Department of Chinese,Heilongjiang University,Harbin150080,China)
The Song Dynasty is a significant period of integration for peotry and muisc since their detachment in the Han Dynasty,as is evident in the combined exposition on peotry and music at the theoretic level,which is embodied not only in sketchy comments by Shen Kuo,Zheng Qiao and Wang Zhuo,et al but also in many concrete and profound discussions.As notes on the poets and poetry in the Song Dyansty involved musical instruments,musical compositions and previous commentaries on the msuic theory,the exposition on poets and poetry in the Song Dynasty is characterized by its incluison of discussions on music.Meanwhile,the exposition on muiscal instruments,musical compositions and musical poems has also led to a more vivid and concrete analysis of“verse”and“prose”in the poetic discussion of the Song Dynasty.
poetic theories;music theories;musical instruments;music compositions;musical poems
I207 < class="emphasis_bold">文献标识码:A
A
1674-5310(2011)-05-0034-05
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宋代乐论研究”(编号:10YJC751024)阶段性成果;黑龙江省教育厅项目“中国古代乐论美学思想研究”(编号:11552086)阶段性成果。
2011-06-11
韩伟(1981-),黑龙江海伦人,博士,哈尔滨师范大学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论、文艺美学;吴铁柱(1977-),黑龙江克山人,黑龙江省委宣传部科员,黑龙江大学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李 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