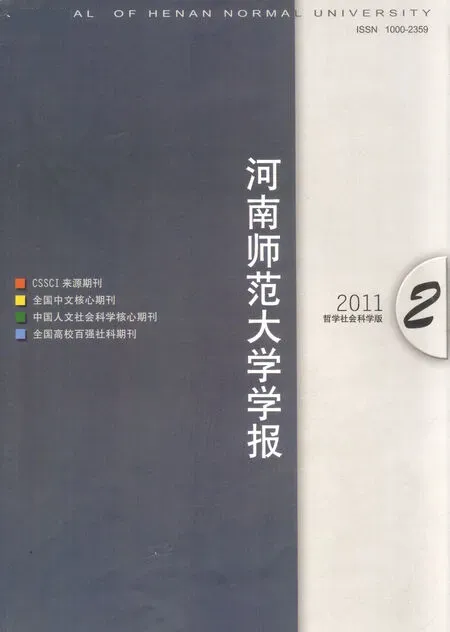批判与探索:思想政治教育人学范式分析
陶 磊
(河海大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江苏 南京 210098)
批判与探索:思想政治教育人学范式分析
陶 磊
(河海大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江苏 南京 210098)
思想政治教育人学范式的提出反映了社会转型中对“人”的重视,但现有的思想政治教育人学范式的研究将思想政治教育最终视为一种教育活动,从而遮蔽了思想政治教育自身的存在。不仅如此,思想政治教育人学范式所隐含的预成论式的人的价值悬设,实质上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只有在新的历史地平线上,使用马克思的“从后思索法”,重新厘清思想政治教育的起源,才可能有效避免当前思想政治教育人学范式研究中的“人学陷阱”。
思想政治教育;人学范式;思想政治教育人学范式;批判;探索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门由人开展并以人为对象的社会实践活动,重视人自然是题中之义。思想政治教育人学范式的提出正是彰显了社会转型过程中对人的重视。目前思想政治教育人学范式的研究,似乎大大推进了思想政治教育人学的深入发展。近年来,随着思想政治教育人学研究的兴起,思想政治教育人学范式逐渐成为人们所熟知的一个研究范式,但“熟知并非真知”,人们在不断重复这一研究范式的时候,对其真实内核却大多未能进行深入追究,致使思想政治教育人学范式研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被遮蔽了,思想政治教育人学范式讨论中的核心内容被人为地空挂起来,思想政治教育被人学范式研究所架空,这就使人们不能从根本上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核,从而造成思想政治教育人学范式研究的虚无化、空洞化,导致思想政治教育人学范式研究和建设的表象化。因此,回顾和省思思想政治教育人学范式的研究,对于思想政治教育人学范式的深入研究和工作实践的发展都是很有必要的。
一
关于为何要“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的人学转换”,思想政治教育人学范式研究者们提出的理由,可大致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需要。革命战争时期夺取政权的中心任务致使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哲学范式得以形成。社会哲学范式侧重强调思想政治教育服从于社会的需要,这一范式在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并没有及时加以转换。相反,在计划经济体制制约和“左”的思想影响下,社会哲学范式不断得以强化[1]。社会哲学范式过于强调思想政治教育为社会需要服务,使人们普遍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再重要也是党和国家的事情,是社会的事情,与个人无关,从而造成人们远离、漠视甚至拒斥思想政治教育[2]。二是时代的召唤。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民主政治的发展,以及哲学从认识论向生存论的范式转向,时代呼唤着思想政治教育及其研究范式的人学转换[1]。三是从本源和最一般意义上讲,思想政治教育是人的一种实践活动[3]。思想政治教育人学范式研究者们认为,已有的研究通常只从政治性、社会性、工具性的角度来讨论思想政治教育何以存在,却忽视了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根本依据。正是思想政治教育对人的生存、发展活动的保障、提升以及使人成为“人”等方面的重要意义,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得以存在的根本依据。
人学范式作为反映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特殊历史阶段与现实环境的共同研究纲领,与社会哲学范式这一研究纲领有着本质区别。伊莫尔·拉卡托斯(Imre Lakatos)认为:“一切科学研究纲领都在其‘内核’上有明显的区别。”[4]相比较于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哲学范式的“内核”强调社会的需要而言,思想政治教育人学范式研究者们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真正目的是提升人性,促进人的发展[5]174。政治性、社会性都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工具性理解,对人进行精神牵引和生存关怀,构筑人的精神世界,引领、提升人之生存,才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之所以存在的内在依据[6]。
二
思想政治教育由社会哲学范式向人学范式转换体现了对人的重视,也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对社会转型中人的精神失落、精神价值的迷失等现象的关注。现代人存在的诸多问题似乎在思想政治教育人学范式中得到了有效缓解。但这种表面的缓解让人们不但很容易忽视思想政治教育和教育的实质性差异,而且对思想政治教育人学范式背后所隐藏着的“人学陷阱”难以察觉。具体来说,其集中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1)现有的思想政治教育人学范式研究恰恰遮蔽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存在。现有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人学范式的研究者几乎无一例外地认为,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目的“不但要看到思想政治教育满足了统治阶级维护统治”的需要,“而且更要清醒地意识到思想政治教育是人的教育,在教育过程中满足人的需要,促进或实现人的发展与完善才是最根本的事情。这种以人为目的,为人的发展和完善服务的内在价值,方是思想政治教育目的之所在”[5]156-157。问题是,这样的思想政治教育目的和一般的教育目的又有何不同?教育难道不也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促进或实现人的发展与完善吗?当然,思想政治教育人学范式的研究者也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性,但他们却始终将政治性看作思想政治教育的工具性目的,由于工具性(政治性)终究受目的性(属人性)的制约,思想政治教育和教育之间的差别被最终磨平就是必然的了[7]。追本溯源,是因为人学范式的研究者将思想政治教育看成“一定阶级、社会、组织、群体、群体与其成员,通过多种方式开展思想、情感交流的互动,引导其成员吸纳、认同一定社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促进其知、情、意、信、行均衡协调发展和思想品德自主建构的社会实践活动”[1]。虽然这里的思想政治教育充满着人文关怀,但不难看出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矛盾依然是“一定社会、一定阶级对人们思想品德要求与人们实际的思想品德水准的矛盾”[8]。而这一基本矛盾事实上是对教育的基本矛盾稍加修改后的移用。因为教育学上一般把教育定义为“教育者按照一定的社会或阶级要求,有目的、有计划地对受教育者身心施加系统的影响,以使受教育者发生预期变化的活动”[9]。而且这种人学范式看待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正好落入了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曾经批判过的旧教育观的窠臼:“这种学说忘记了”“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这种学说必然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凌驾于社会之上”[10]59。由此看来,思想政治教育人学范式不过是一部分人采用了充满人文关怀的方式对另一部分人进行教育,但问题是一部分人何以能教育另一部分人呢?是因为这一部分人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先知先觉,还是因为他们率先掌握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钥匙?
(2)现有的思想政治教育人学范式研究实质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在现有的思想政治教育人学范式的提出者视野中,“思想政治教育是由人的生存、发展活动所催生”,“思想政治教育是人之存在的一种表现形式”,“思想政治教育导向人的解放和全面而自由地发展”[3]。或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以使人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存在为指向,它致力于通过促进人之崇高精神境界的自我塑造和生成而提升人的存在,这是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的本真性回归”[11]。在这种思想政治教育人学范式的逻辑建构中,实际上有一个基本的立足点——关于人的本质的本真状态设定,这是思想政治教育人学范式的立论基础。在本真状态中,人是完美的统一体,思想政治教育就是让“人从自在自发状态到异化受动状态再到自由自觉状态的否定之否定过程”[11]。不难看出,虽然这种人学范式研究提出了要以现实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来消除异化问题,但如果这种活动是以一种伦理原则为依据,那么这种活动说到底还是一种以价值悬设为取向的价值观念,而不是从现实生活本身出发的现实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
现有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人学范式归根结底是一种人本主义的价值悬设,这种人本主义的价值悬设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主体性人学,另一类是生存论人学。但不论是主体性人学还是生存论人学,实质上都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因为它们都预设了一个前提。“在主体性人学中,人的自由自觉的主体状态,构成了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在生存论人学中,存在的澄明之境则是人的本真生存状态的根基”[12]。显然,这种形而上学(预成论式)的思想政治教育人学范式是我们需要扬弃的。事实上,马克思早年就对这种形而上学作了深刻的批判:“形而上学的全部财富只剩下想象的本质和神灵的事物了,形而上学变得枯燥乏味了。”[13]因为形而上学者“还从来没有看到现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于抽象的‘人’”[10]60。
三
思想政治教育人学范式不但磨平了思想政治教育和一般教育之间的差别,而且没能真正解放人、发展人、提升人,使人彰显其生命和个性,相反,它只能束缚人、限制人、压抑人,最后扼杀人的个性和价值,因为形而上学的思想政治教育人学思维方式造成了对人的理解是抽象的,即把人理解为抽象的外在的研究对象,以对物的方式去理解和把握人。同时这种对人的把握又是凝固性的,即往往从“是什么”的意义对人性给予规定。思想政治教育人学范式的前提虽然也是人,但这个人却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这正是因为思想政治教育人学范式“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10]58。什么叫感性活动?我们以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就可看作一种人的感性活动,在这种感性活动里,它既有主观环节,也有客观环节,通过它的主观环节和客观环节之间的关系,我们从中可以推出思想政治教育人的世界的客观存在,这个客观存在就是像它在这个关系中、在感性中那样存在着。质言之,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不能理解为一种媒介、一个桥梁,而是全体。
但需要进一步明确的是,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这一“全体”的首要性质是什么。要厘清这一思想政治教育元问题,需要用历史的方法搞清楚思想政治教育的起源。问题是历史是已经过去的存在,在认识历史的活动中,认识主体不可能直接接触认识客体。认识对象的这种特殊性造成了历史认识的特殊性,并使历史认识论的研究遇到了一系列特殊的困难。然而,马克思的“从后思索法”的提出解决了这一特殊的困难。马克思认为:“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结果开始的。”[14]“从后思索法”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历史虽然已经过去,但它并没有消失,化为无,而是以浓缩、变形的方式,或者以萎缩、发展的形式被包含在现实社会中。现实是历史的延伸,历史往往平铺在一个社会截面上。因此,透过现实社会,我们便可以看到过去的历史[15]。“从后思索法”之所以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出发,是因为“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16]43。那么,马克思的“从后思索法”是否受一定条件制约呢?那是毫无疑问的。这个条件就是要先行地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意识获得批判性的识见。马克思认为:“基督教只有在它的自我批判在一定程度上,可说是可能范围内准备好时,才有助于对早期神话作客观的理解。”[16]44
“从后思索法”启示我们,考察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起源,不仅要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出发,更要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历史认识的前沿性观点持有批判的态度。只有如此,才能更好地“阐思想政治教育之今”,而不是“叙思想政治教育之古”。目前学界对思想政治教育历史的起源的前沿性观点有:思想政治教育并非人类社会先天具有的,而是伴随着阶级、国家的产生而产生;思想政治教育在人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中产生的,既是满足人的政治社会化的需要,也是实现或维护阶级统治的必然结果;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有意识的教育,其产生之时基本掩藏于其他教育之中。这里,思想政治教育不同于教育这样一种有意识的活动是:“思想政治教育更是人类一种有意识的政治教育活动,只有当社会有意识地灌输或人们有意识地接受阶级思想、阶级观念之时,教育才能转化为思想政治教育,否则只是萌芽中的政治教育。”[5]57-58这是关于思想政治教育起源中很有启发性的观点,因为它已经敏锐地捕捉到了思想政治教育同一般教育之间的区别,即有意识的政治教育活动。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将这种有意识=社会有意识地灌输或人们有意识地接受阶级思想、阶级观念,使得思想政治教育起源再次和国家和阶级的产生等同起来。问题是,思想政治教育虽然是关于人的政治思想活动,但显然并不能将所有影响人的政治思想活动等同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如将二者等同,实际上是混淆了政治的意识和意识的政治的区别,即“把所有具有政治影响性活动等同于具有高度自觉性的针对人的思想意识的政治实践活动”[17]。但是,现有的思想政治教育起源的认识却可以构成我们对思想政治教育起源的重新认识的出发点,因为“从后思索法”出发点是在“完成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因此,“有意识”“政治性”“教育性”都是思想政治教育历史起源的“抽象的规定”,要获得思想政治教育起源的理性认识,还需要要将这些“抽象的规定”上升到“理性的具体”。在这个意义上,思想政治教育起源于意识形态政治。
意识形态这个概念最早由特拉西提出的,他将意识形态定位为对思想的要素及其来源的分析,意识形态是理念的科学,以使思想摆脱封建神学及形而上学的桎梏,达到理性层面,并将情感、意志置于理性的制约下,以此重构政治学、伦理学、经济学,反对政治权威。可见,意识形态这个概念最初体现了资产阶级的诉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将意识形态定位为资产阶级思想,从这一概念发生学意义上看是极为准确的。我们知道,思想政治教育是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来影响人、教育人,这里的“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显然是一种阶级意识形态,但并不能因此将意识形态性看作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规定。因为意识形态包括政治思想、法律思想、经济思想,还包括社会思想、教育、伦理、艺术,甚至宗教等,因此,意识形态性作为思想政治教育本质规定可能导致使思想政治教育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学科。更重要的是,意识形态归根结底是一种观念的活动,而思想政治教育不仅是一种观念的存在,更是一种社会实践活动。但是意识形态政治不同于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政治反映了思想政治教育不仅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物,而且是现代社会所特有的一种社会实践活动。意识形态政治“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实际的起点。……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18]18。
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这一“全体”的首要价值并不在于培养和教育人,它根本上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政治活动而存在的。但要准确把握这种意识形态政治活动,还需要结合马克思所说的“现实的个人”进行。只有立足于“现实的个人”,我们才能超越现有的思想政治教育人学范式中对人的非历史的理解。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10]66-67人的“思想、观念、意识的产生最初是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产物”[10]72。这决定了考察现实的个人必须置于具体的社会历史情境中。意识形态政治是随着现代性的出现而出现的,“现代性意味着以下两种全新价值在人类社会中涌现:第一为‘工具理性’成为社会行动(制度)正当性的最终根据;第二是个人权利观念的兴起”[19]。而我们今天所说的现实的个人,就是在现代性的历史情境中进行的物质生产劳动的个人,当代中国的这场“总体性”社会转型,使长期以来的以农业为主的生产劳动方式渐已被以工业化为主的生产劳动方式所取代,市场经济取代了计划经济,原先同质化的社会秩序的瓦解使离散化的社会群体从一元化的“实体”中解脱出来……组成现代社会的最基本单元的个人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他们在现代社会中借助主体性原则表达着自己的利益取向和价值立场。人们的思想观念领域发生了巨大变化,价值领域出现了“诸神竞争”,不同的政治集团为了获得并维护各自的政治权利(力)展开了激烈的意识形态竞争,作为意识形态政治活动的思想政治教育正是在此时才得以真正出场。历史也已经证明,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我们党的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正是意识形态政治活动和现实的个人完美结合的体现。
[1]张耀灿.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的人学转换[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0(7).
[2]万光侠,等.思想政治教育的人学基础[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50.
[3]曹清燕.思想政治教育存在根据的人学追问[J].理论与改革,2008(5).
[4]伊莫尔·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的纲领[M].蓝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67.
[5]李合亮.思想政治教育探本——关于其源起及本质的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6]曹清燕.引领人之生存: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关怀[J].探索,2010(6).
[7]陶磊,孙其昂.回顾与评价:思想政治教育本质问题的研究进展[J].探索,2010(6).
[8]张耀灿,郑永廷,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6.
[9]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编写组.教育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19.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1]曹清燕.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的人学阐释——基于人之存在论维度[J].理论与改革,2010(3).
[12]仰海峰.形而上学批判——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前提及当代效应[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110.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161.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92.
[15]杨耕.为马克思辩护——对马克思哲学的一种新解读(修订本)[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297.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7]金林南.从政治的意识到意识的政治——思想政治教育起源的政治哲学分析[J].思想理论教育,2010(19).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8.
[19]金观涛.探索现代社会的起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6.
[责任编辑孙景峰]
CriticismandExploration: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HumanParadigmAnalysis
TAO Lei
(Hehai University,Nanjing 210098,China)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human paradigm proposed to reflect the “human” attention in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but because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human existing in the paradigm of research will eventually as a kind of education activity to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tself covered the existence. Not only suc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human paradigm of implied who gets into the value of suspending hypotheses, is in essence a kind of metaphysical thinking. Get rid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study of human paradigm this “humanistic trap”, need in the new historical horizon, use of Marx's “thinking from now” method , to clarify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rigin, it is possible to avoid effectively curren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study of human paradigm “humanistic trap”.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human paradigm;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human paradigm;criticism;exploration
D64
A
1000-2359(2011)02-0239-04
陶磊(1979-),安徽当涂人,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10YJA710055)
2010-1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