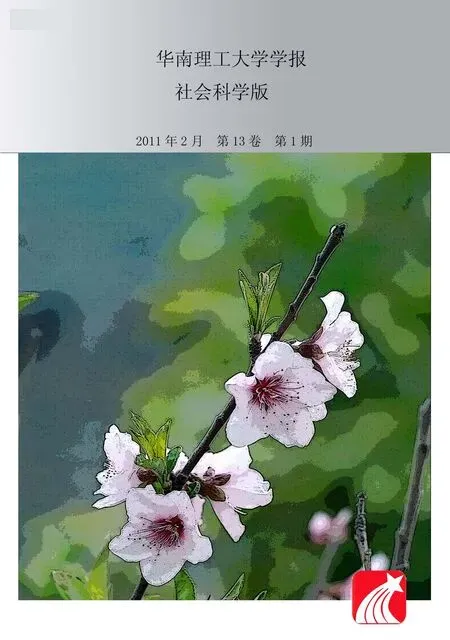从现代客家小说观照客家女性文化
刘小妮
(华南理工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现当代客家小说充分地展现客家的地方风情和地域文化,弥漫着浓郁的特定的地域气氛,并为读者提供了显示这一地域文化精神的多姿多彩的艺术图景,从而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客家文化的若干方面。对客家女性的描写,集中展现两个方面: 一为愚昧乡村女性的婚恋贞节观,二为知识女性的精神境界,客家女性身上既有传统因袭的婚恋苦难,又有集体无意识传承的优秀品质,本文通过对小说的解读,对客家女性文化进行现代审视。
一、 传统文化影响下的客家女性婚恋观
(一)重学问的择偶观
客家文化,本质上传承了中原文化,信奉儒家传统。在客家地区,即便一般家庭,也以能培养出读书人为骄傲和自豪。所以,为人父母者,勒紧裤带,节衣缩食也决不敢在子弟的学业前途方面疏忽大意。这种客家文化进取情怀,张资平在《资平自传》、《脱了轨道的星球》、《冲积期化石》等小说中都有表现。《冲积期化石》中的天厂,就是一位望子成龙的慈父,他为了能让儿子出国留学,实现文化治贫的人生理想,其良苦用心真可以说到了万死不辞的地步。他弥留之际给远在日本求学的儿子留下的临终嘱咐就是好好用功,学有所成之后再回来报答亲恩,还特别叮嘱: 父亲死后也不必回家奔丧服孝,“如遗父命,便为不孝”。在这里,孝和不孝的内涵有了新的特定内容。小说中的韦天厂的原型正是张资平自己的父亲——一位中年丧偶,家道中落,但又文明开通,思想进步的穷秀才。
在客家人看来,一个姑娘如果能够和一位斯斯文文经由读书走出大山的书生结成佳偶,不啻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因为这意味着其一生的命运将由此发生改变。故在张资平小说中的人物,如黄广勋、谢克欧、刘文如、宗礼江、吕广、吴梅等文化人身份的先生和书生,是小说中最受年轻女性青睐爱慕的美少年。
以农业为主要特征的古代社会,女子嫁人,首要选择是“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女子对丈夫具有强烈的依附色彩,这种经济与地位决定的依从关系,导致现实生活中的男尊女卑。客家女性具有独立的经济能力,嫁学问人并非仅仅功利地为“穿衣吃饭”。这里体现的是儒家文化“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的理想,女性的选择更在于社会价值观念的认同。
(二)严苛的贞操束缚
张资平在小说中也展现了童养媳的悲惨命运。客家人日常所说的“等郎妹”、“细薪舅”,指的就是童养媳。客家人娶童养媳一般是在女婴很小的时候把她抱回领养,婆婆像对待自己的女儿一样调教儿媳。待童养媳稍大,她就成为这个家庭重要的劳动力,必须承担大量的家务活,甚至像成年人一样参加各种生产劳动。张资平作品的意义在于,他对于客家妇女的命运和不幸人生还有更进一步的挖掘和表现。
在张资平早期小说中可以看到,20世纪初期,童养媳的风俗习惯在客家人最集中的梅县依然被完整地保存着,而且极为盛行。尽管张资平没有直接描写以童养媳的生活、命运为内容的小说,但作品中许多人物的身份底色却是童养媳,像《冲积期化石》中的刘四妹,三岁就到舅母家和刚满三个月的表弟结婚; 《梅岭之春》中才周岁的保瑛嫁了一个三岁多的丈夫; 《双曲线与渐近线》中的女主人公梅茵,七岁的时候就被父亲送给了一个商人做媳妇; 《性的屈服者》中的馨儿,《最后的幸福》中美瑛的嫂子(在作品中未曾露过面的角色)等也是童养媳。童养媳的买卖是充满着罪恶和血腥的野蛮行为,无视女性生命的独立性及情感选择的自主,其实质是将女人看作个人或家族的私有财产。张资平用写实手法真实、清晰地记录下了历史上客家妇女的不幸。他笔下那些童养媳出身的女性形象,几乎没有一个不是悲剧人物。她们的痛苦与不幸,就是客家妇女的痛苦与不幸; 她们的命运就是无数客家妇女不平命运与苦难人生的缩影。
青壮男子长期在外谋生,带来的另一问题是,男女之间正当的基本感情需求和原始欲望得不到应有的满足。有的男人一去长年不回,夫妻之间常常音讯不通,夫妻关系名存实亡。有些外出的男人或已客死他乡,或者另娶新妇,另筑家室,也未可知。张资平的一位堂伯父张淑皋就是这样的典型。他因为长期住在日本而另娶日本妇人,重新组织了家庭,结果新妇旧人互相仇视,两方儿女形同敌人。小说《她怅望着祖国的田野》就是以这位堂伯父的生活故事为原型创作的。
长期在外的男人,只要条件许可,自然不会拘于纲常名教等道德戒律,而留在乡里的女人却只能苦苦守候,任青春老去,红颜消损。但也有因耐不住寂寞而大胆僭越陈规去寻求个人幸福的女性。在现实中,那些试图超越古老礼制秩序去寻求感情和欲望满足的女性,一旦被“捉拿归案”则身败名裂,性命不保。族人对犯了“罪”的女人的惩处办法是: 把女的裸体缚在柱上,任族人鞭打,最后用锥钻刺死她(《梅岭之春》)。如《最后的幸福》里,美瑛不得不屈服于阿和,因为阿和掌握了她和黄广勋偷情的证据,如泄漏出去,后果则如村中邻屋的那个女人,按习惯被捆缚在石柱上,族人都可以提起藤鞭子抽她,恨她的甚至拿锥子刺她。美瑛曾目击过这样的情形,她看见那个女人被残毒的几个老妇人用锥刺得周身鲜血淋漓。同样是出于这个原因,《梅岭之春》中的段吉叔父不得不离家出走。
无独有偶,李金发的小说《一个少女的三部曲》亦描写了客家女性所受的贞节压迫。小说揭示了粤东山区这个闭塞的地方,由于交通阻隔,形成独特的旧俗,实行盲婚制度,包办婚姻严重,贞节观念严苛。小说的主人公菊英,16岁被父母媒人包办嫁给患痨病的陈少康。不久,陈少康病逝,留下年轻的菊英守寡。此后,菊英被婆婆视作不祥之物,周围人的目光也充满仇恨,窒息的氛围使菊英不能自由呼吸。终于耐不住跑回娘家,不料却引来大祸。一些好事之徒造谣说菊英是跟奸夫逃回娘家窝藏的,于是三十个男女,甚至藏着铁锥子来了。当躲在邻家的菊英,被一群如狼似虎的“陈姓人”拉出来时,娘家的父老,没有一个敢出来讲一句公道话。菊英被带回陈家,两手被反绑在后面,那些失去人性的暴徒把菊英的上衣除掉,实施暴打。在这个闭塞的山乡,这种野蛮的陋俗被看成天经地义的,那些愚昧的观众竟以此寻找刺激,变态的施虐的快乐。李金发在小说中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闭塞和愚昧,对被迫害者寄予了深刻的同情。
二、客家女性的神性品质
客家女性身上体现的是典型的客家精神,于社会、经济、家庭中体现的其卓绝的风范、情操和品格。美国传教士罗伯特·史密斯在《中国的客家》中说过: “客家人是中华民族牛乳上的奶酪,而这光辉,至少有百分之七十是应该属于客家妇女的。”[1]228大诗人黄遵宪曾这样评价: “无论是为人女,为人妇,为人母,为人太母,操作亦与少幼等。举史籍所称纯德懿行,人人优为之而习安之。”[2]205
《客家文化审美导论》中提到,客家女性相对比其他汉族女性,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客家女子不缠足,二是客家女子不像其他汉族女子那样被锁在深闺,而是走出家门,承担繁重的劳作,还有不少是知书识礼的。谭元亨的《客家魂》中作为知识分子的客家女性在特殊年代里,身上体现的是集体无意识传承的美好品性。
(一)博爱的母性
客家女性具有宽广的胸怀,博爱,是其最本质的爱。女性之爱在这里是全身心地投入,是无私地奉献而不求回报,是慷慨地给予,是恒久的忍耐。在人类文化史上远古的母系文化所提供的文化原则既是初始的,又是永恒的,那是以“母爱”为生存基点而衍生出的爱的原则。女性在孕育生命、维系生命的过程中,实际上也孕育了一种绝对不可忽视的“女性精神”,就是源自生命崇拜的“唯爱”精神。
客家关于“葛藤坑”的传说体现的是客家女性的宽广的胸襟,博爱的精神。黄巢军队肆虐之时,一位母亲牵着自己的儿子逃难,而背负着侄子。这位母亲的回答是: “长者先兄遗孤,父母双亡,惧为贼人所获,至断血食,故负于背,幼者固吾所生,不敢置侄而负之,故携行也。”[3]76危难之前,顾他人而忘自我,是一种淳厚的人道精神,一种哀悯苍生的仁厚之心。
启慧(《客家魂》之二《客家女》)文革被下放到农村,在进村的途中产下儿子,自己为自己接生,这在一般人看来是很难想象的,但是客家女由于长期迁徙的缘故,为自己接生亦属平常,是出于对生命的顶礼膜拜,是作为母亲的天性使然。之后“她有点认不出自己了,因为一路已好些日子没照镜子了,分明瘦削了一些,但仍炯炯有神,而且添上了疑惑与慈祥。和蔼的圣洁神采。她猛地醒悟,可不,自己是母亲了,能不添上母亲的慈容吗?迈进了人生又一神圣阶段!她胸中充盈了温柔与仁爱。过去,是老师,今日,又添上母亲的身份,为人师,为人母,都是至圣至美的。”[2]41此后,启慧就在那小小的村庄建立了学校做了老师,将所有的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倾注了所有的爱,并为了救落水的学生而献出自己的生命。这是由“母爱”而衍生的博爱精神。
远晴是一个柔弱的客家知识女性,在她身上却体现了母爱的强大。被解除公职回乡下后,为了女儿萱龄和侄子元戎的学业,不惜卖血; 自己的冤情无处诉说,却为女儿的被冤而四处奔走; 在武斗场合冒着被流弹射中的危险去救女儿,逼使所有的枪口都垂了下来; 直至丈夫和另外一个女人石萝生下的孩子伟龄,远晴都是视为己出,倾注真诚的母爱,将其教育成有文化有知识的人;在生命的最后又将辛苦抚养的儿子伟龄还给其生母,无不显示她伟大而宽广的胸怀和深沉无私的母爱。
客家女性的母性,还表现在作为精神家园的象征。“女人们则是家园的守望者,给男人创造根基、慰藉、希望,在漫长的岁月里,是她们永不竭尽的奉献支持了男人的生存、家族的荣誉、历史的精神。”[5]214只要有女性的存在,就有“家”的存在。所以《客家魂》中郭家在远晴死后,还有石萝的身影出现,她是作为“家”的隐喻存在,有女性的存在就有家族的存在,就有希望的存在,就能让远行的人,“处处无家处处家”的民系心中有归宿感。
(二)自强不息的独立精神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女性在社会及家庭伦理秩序中是被统驭的对象,在经济秩序中是依附在男人身上的寄生者。而客家女性相对其他汉族女性,具有自强不息的独立精神。客家女性是家庭的中心,主持家政,她们承担了比男人更繁重的农耕。 黄遵宪道: “吾行天下者多矣,五洲游其四,二十二省历其九,未见其有妇女劳动如此者。”[2]205有文撰道: “一家妇女所得,不但以维持一家生活费用,甚至可供给子女受中小学教育; 而男子在外地寄回之金钱,则涓滴不漏,储积以生息,及购置天屋; 故各家家庭之支柱是妇女……”[3]99可见客家女性在经济上是独立自主的。
著名美国作家A·米切纳的代表作《夏威夷》中,有关客家人的内容的一章《哀鸿遍野的农村》,作品的主人是客家女性谢玉珍,她从出生开始就是不幸的,最后被带到檀香山,经历了常人无法忍受的艰难到达夏威夷,因为玉珍的克勤克俭,成为华人们的道德楷模。玉珍舍身陪患麻风病的丈夫去孤岛生活,历尽艰辛。丈夫死后玉珍重返夏威夷,将五个孩子送去读书皆有出息。此后发生了火烧唐人街的事,玉珍肩负起复兴家族的重任,开始第二次创业,又经历种族歧视、地震、飓风等天灾人祸,最终终于成功。在玉珍身上集中了客家女性的品性,近乎神性的品性。
在《客家魂》中,远晴和石萝体现的是一种韧性生存。 当远晴被学校除职回乡,她还担心自己不能适应,但是她还是坚强地挺过来了,“一个当了近十年女教师的弱女子,就这么成了把犁、砍樵、种田的健妇,而且是几乎短短几个月中变成的。”[4]203于是远晴在丈夫长期不在家的境况下担负全家的重任。石萝则长期照顾身残的丈夫和孩子,同时还要忍受内心的痛苦的煎熬、良心的谴责,在这种境地下还是坚强地生存下来,并在远晴死后成了郭家家园的守望者,继续家族的精神支持。
萱龄是一个非常独立的现代女性,她未足十岁就不忍母亲远晴的艰辛,跟母亲约法三章,自己挣学费上学。她给队里放鸭子,去河边挑沙,尝尽了艰辛。“正是在这千年的磨砺中,使他们有着罕见的生命力,能经受住生活中非常人能经受住的痛苦、疾病与灾难,每每能从余烬中再度站立,显示其健壮的体魄。”[4]318在她们身上流的是千年迁徙而艰难生存的强者血液,体现的是自强不息的精神。
(三)坚定的婚姻爱情观
客家女性对爱情婚姻是很坚定的,敢爱敢恨,情感表达形式刚烈,天崩地裂亦不后悔,是一种生死相许的决然,正如在客家山歌里所唱:
生爱连来死爱连,两人相好一百年。
曼人(哪个)九十七岁死,奈何桥上等三年。
入山看到藤缠树,出山看到树缠藤。
树死藤缠缠到死,藤死树生死也缠。[3]176
在《客家魂》中,启慧、远晴、萱龄、余恬以及石萝,都是固守爱情的女性。启慧在特殊的年代里,为了保住爱人杨双渔,不惜牺牲自己的幸福,独自承担痛苦,在农村独自抚养儿子,而且从不曾后悔自己的爱情选择,对杨双渔的感情生死不渝。远晴一生等待远离的丈夫,无怨无悔,最后对丈夫的选择表示谅解,还接受了石萝。还有萱龄之于大鸿,余恬之于元戎,都是一往情深,甚至石萝之于启兴,也是不带任何功利色彩的纯粹的爱。
她们的爱,无论是对家族,对后代,抑或是对爱情,都是至情至性,默默奉献、牺牲,对家族、历史带来的灾难和苦难勇敢承担。惟其是主动承担,更显示客家女性的坚强和伟大,从而成为文化的隐喻,在精神上起着抗击困难的支持力量。
三、 客家女性文化的现代审视
客家女性身上集中了大量优秀的传统美德,然而将客家女性置于现代位置进行审视,将发现许多不合理的地方。
(一) 个体生命的存在价值的缺失
自古,女性一直处于对象化的位置,是欲望的对象,是审美的对象,是男性理想的载体。她是她之外的一切,女性的这种对象性的地位是由男性造成的,男性将自己的要求加诸女性身上。客家女性身上的种种美德,如母性、独立,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缺乏个体精神,其人生价值在于奉献,在女性的心中有所有,为人女,为人妇,为人母,直至为人太母,唯独没有自我,将自我的价值转嫁到丈夫、后代以及家族荣誉上,实现的自我只是社会角色关系中的自我,是缺乏主体意识的“无我之我”,则个体生命存在价值无从说起,女人作为女人的价值也无从说起。女性为家族辛劳,在经济上是独立的,不是依附于男性的寄生者。然而在社会地位上,虽然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将全部精力用于支持夫家生计,任劳任怨,默默奉献,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却是一副沉重的枷锁,依然是作为男性中心文化的“物”的存在,是作为传宗接代的工具,作为家务劳动的工具。女性始终没有作为历史的主体而存在,只是作为一种客体,一种物,或者说是一种需要而存在于男性社会。
即使是太平天国,虽使得女性地位得到提高,像洪宣娇等人,是太平天国的将领,和男人一样承担着攻池掠地、坚守要塞的种种艰巨的战斗任务。但战后,无论是否封了女官,论功行赏,依然是返回家庭。她们只是特殊时期的需要,没有战争则退回家庭,继续作为男性社会背后被置换的风景或者是工具,无法发出一己的声音。
《客家魂》中的众多女性,虽然是作为知识女性,自尊自立自强,但是置放在历史文化背景中,仅仅是社会的人,集体的人,固然是一个大写的“我”,毕竟不是自我。她们的生存方式固然是坚强韧性的,毕竟是为了集体的、家族的、他人的,而非女性自身的。女性要脱离这种非主体性的存在方式,就必须去寻找经验世界中的真我,即是建立自我意识,塑造自我。惟其是自觉纳入文化体制中,承担所有的美德,才愈发显得女性角色的沉重;自由放旷的“天放”个性色彩在这群女性身上并不明显,情感压抑在文化与道德之下。
(二) 爱情婚姻的现世幸福思考
女性若太强调对爱情和婚姻的忠贞,则必然陷进男性文化设置的从一而终的陷阱。毕竟女性有权像男性一样发展自我,拥有幸福的生活。在爱情的天地里,忠贞的爱无疑是美好的,但成为一种理念绳索却捆绑着人的灵魂,勇敢地背叛定型的理念,获得灵与肉的自由,这种短暂却真实的爱比长久地在信仰中承受精神的折磨要好。
经过十年留学生活,接受过现代科学文明洗礼,有了异质文化作参照之后的张资平,以新文化运动亲历者和先驱者的姿态,对不幸女性命运倾注无限的同情和怜爱,有意识地将它艺术地摄入小说文本,暴露出封建宗法制度的不合理性和罪恶性,显示出作者对客家文化中野蛮残忍的落后成份所持的批判态度,成为“五四”时期国民性批判的时代主旋律中一个响亮的音符。
因而,张资平在包括《双曲线与渐进线》、《回归线上》、《圣诞节前夜》、《性的屈服者》、《梅岭之春》、《苔莉》、《飞絮》、《最后的幸福》等小说中,主题重复对“五四”反封建礼教的描写,表现青年男女对婚恋自由的追求,对理想爱情和幸福婚姻的向往,对女性柔弱无依和任传统摆布命运的同情,这些都在当时青年中产生极大共鸣。他的小说曾连续再版,例如《爱之涡流》出版半年就再版3次,《飞絮》不到3年就再版8次,可见其欢迎程度。“五四”时期,提倡个性解放、婚姻自主,冲破封建罗网,张资平无疑是挺立在潮头上的。所以,他的情爱小说受一代青年的热烈欢迎,并产生极大的反响。即便是他的性描写,倡导自然主义,也是一样有惊世骇俗的积极意义。而实际上,他的性描写亦是浅尝辄止,与今天的某些性爱书写小说相比,更是小巫见大巫。
张资平一反常规模式,传统文学中的情爱小说流行的是一种“男求女”的模式,双方千回百转终于成功或终归失败,而在他笔下,女性总是主动的、勇敢的,而男性多是被动的、懦弱的。这首先在构思上打破了以往情爱小说的僵死的模式,有新鲜感,为以后情爱小说的构思开拓了一条新的路;其次,这样的描写还具有反封建的色彩,有“开风气之先”的意味。众所周知,男尊女卑是一个旷日持久的社会现象,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女性是最深重的受害者,封建礼教扼杀了她们的爱情幸福,她们被不幸的婚姻残害,被畸形的家庭扭曲,在无爱的苦海里挣扎,在世人的冷眼中沉沦,她们作为“人”的自我价值的实现,自然要比男性困难得多。然而,压迫愈重,反抗亦愈烈,一旦打破了礼教的枷锁,冲破了家庭的罗网,她们将会比男子更为激进,情欲使她们不顾一切,被动的承欢变成了主动的追求。因而,其女性形象便有了冲破封建婚姻的意义。
正如钱杏邨所说: “张资平先生的恋爱小说的产生是与他的时代有密切的关系,他的创作的确是时代的产儿。我们只要了然于五四运动以后的情况,我们就可以不加思索地指将出来,张资平先生的恋爱小说完全是五四期间女子解放运动起后必然地要产生出来的创作。张资平先生的创作的内容完全是五四时期两性解放运动的事件对于文学上的反映。”[6]135正是在张资平的情爱小说中,张扬了个性,张扬了人的解放。没有个人的自由发展作为条件,人类的自我解放便是一句空话。
四、 结 语
客家文化是儒家文化的一部分,客家女性文化也应该属于儒家文化,因而客家女性有着中华民族种种传统美德以及客家女子特有的品性。然而,处于偏远的山区,客家女性所受的苦难与因袭的传统也较多。在当代研究客家女性文化,不应再强调文化传统赋予的女性品德,而是应该关注女性的生存境况,使女性真正具有女性自觉意识和主体意识。
参考文献:
[1] (英)爱德尔.中国访问纪录[M]//.胡希张,莫日芬.客家风华.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
[2] (清)黄遵宪. 李母钟太安人百龄寿序[M]//黄遵宪研究资料选编. 香港: 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5.
[3] 谭元亨, 黄鹤. 客家文化审美导论[M]. 广州: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1.
[4] 谭元亨. 客家魂之二:客家女[M]. 北京: 十月文艺出版社,1997.
[5] 徐肖楠. 走向世界的客家文学[M]. 广州: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1
[6] 钱杏邨.张资平的恋爱小说[M]//史秉慧. 张资平评传. 上海: 上海现代书局,19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