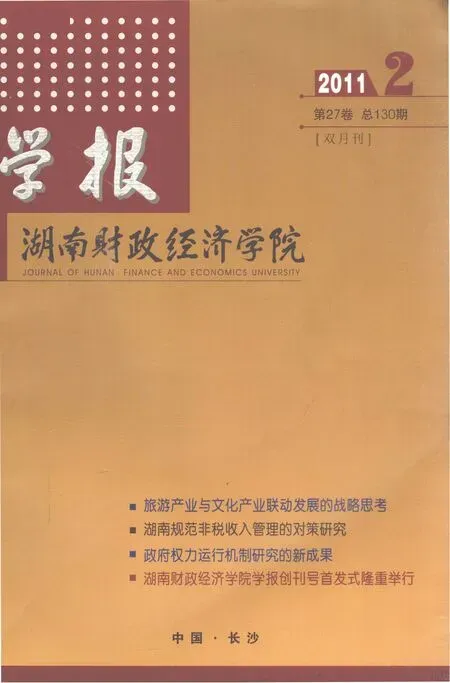从 《还乡》中的荒原看哈代的生态思想
胡 敏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湖南长沙 410205)
从 《还乡》中的荒原看哈代的生态思想
胡 敏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湖南长沙 410205)
荒原在不同时代的文学作品中被赋予了不同的象征意义。在哈代的小说《还乡》中亦多次出现荒原主题,荒原是《还乡》的灵魂。哈代通过小说《还乡》表达了回归荒原、回归自然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思想。
哈代;《还乡》;荒原;生态思想
荒原常指“荒凉的”或未驯化的荒野地区,在不同时代的文学作品中,荒原被赋予了不同的象征意义。上古时代的先民们敬畏自然,在古老的观点中荒原威胁人类的生存,是荒蛮野性、贫瘠残酷的地域所在。旧约和新约都将荒野描述为贫瘠和荒凉之处。圣经上说,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来到“受诅咒”的荒野,“那儿长满荆棘,只能吃荒野上的植物”。在新约中,只是受到撒旦的诱惑后基督耶稣才进入荒野并在那里禁食40天。荒野不仅危险,而且是邪恶所在,是伊甸园和福地的对立面[1]。人类中心主义形成以后,人类渴望拥有对世界至高无上的权力,妄图征服自然、统治自然,自然成了人类支配和利用的对象,自然的野性、美好不再令人类敬畏热爱,荒原被看作可供使用的工具或资产,被人类开发利用的资源,自然遭到了人类文明的破坏。18世纪伟大的生态思想家卢梭率先提出“回归自然”,呼吁人们回归自然环境,回归人类的自然本性,“在他看来,自然状态能够恢复人的本性,唤回人的德行,而理性状态却使人虚伪奸诈、残忍好恶”[2]。“回归自然”的理想在浪漫主义时期达到高潮,在18-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运动的影响下,人们对荒原有了新的理解,荒原象征着纯真和美好,浪漫主义文学寄情于自然荒原,抒写从文明的破坏性影响的逃离和向自然的回归。
哈代从青年时代开始就崇拜达尔文,受到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是《物种的起源》最早拥护者之一。达尔文主义将人类看做自然一部分,认识到人类与其他生物有着生物学意义上的共同的根,人类不能超越自然,与自然没有根本区别。达尔文主义推动人们把人类的伦理扩大到所有生物,把对人的关怀扩大到所有生命。哈代在1910年写到:“似乎极少有人认识到,确认物种的共同起源的最深刻的影响是道德上的,也极少有人认识到,这种确认涉及到一种无私的道德再调整……从只适用于人类到适用于整个动物王国”[3]。哈代的全部创作和思想发展过程中,进化论学说都贯穿始终,是哈代的社会观念、伦理道德观念和文艺思想的基础。进化论学说是哈代的宇宙观和世界观的基础,也是他的现实主义的理论基础[4]。《还乡》是“性格与环境小说”中具有代表性的一部,荒原主题多次出现其中,是小说的灵魂,哈代通过小说表达了回归荒原、回归自然的思想,使得小说具有深刻的生态内涵。
一、荒原:自然的始初
荒原存在于自然之中,是自然的一部分,是原始状态的自然。霍尔姆斯·罗尔斯顿说过:“每一个荒野地区都是一处独特的大自然”[5]。哈代是土生土长的英格兰人,从小就对荒原、林地等自然的世界有着特别的亲切感,《还乡》开头几句话就给读者呈现了一片气势磅礴的荒原,“十一月的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已近黄昏,埃格敦荒原这片尚未圈地的广袤原野上,天色随着一分一秒过去而暗下去了。头顶一片灰白色的宝盖云,将天空遮住,变成了帐篷顶,于是整个荒原就当做了地铺”[6]。埃格敦荒原与天空融为一体,展现了人与世界、与天地自然交相融合的原初境界,“这一大片默默无闻、无人问津而荒废的乡野,《末日审判书》(英国11世纪钦定的田亩册)上却赫然在目。那部最终税册上记载着,它是一片石南丛生、荆豆棘蔓延,长着野蔷薇、金刚藤的原野……古代一里格的计量单位到底有多长,无从查考确定,但是从那数字来看,埃格敦的面积,到现在为止,不见得缩小多少。”[6]由此得知,荒原从史前时代开始就丝毫没有改变,从古至今依然保留着大自然最原始的状态。英国作家劳伦斯认为荒原“是本能的生命得以出现的原生的、最初的土地”,“这一片圣洁的大地方,有一种古老的持久性,这是大海所没有的。谁能指出一片海洋来,说它古老?大海受太阳的蒸发,受月亮的搓捏,面貌日新月异,说变就变。沧海易容,田野变迁,江河、村落、人物,全有变化,唯有埃格敦荒原一成不变”。[6]灰暗的天空、苍茫的大地、呼啸的风声、阴沉的夜色都呈现出浑厚质朴、深沉粗犷、苍凉奇特的自然风貌。
哈代的作品中,大自然高深莫测、不可变化,然而大自然总是和人的活动交织在一起,似乎和人结成了一个有机整体。那些与自然和谐相处,承认大自然不可变的乡亲们驯服地遵照生活中的规则和礼仪来适应自然亲近自然,终日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古朴的民风,古老的传统在他们身上一直流传,寒冬临近,埃格敦荒原附近一带小村庄的老少爷们挑着沉重的荆豆柴担爬上荒原上的古冢,他们将柴担堆在一起,垒成一个荆棘金字塔,在荒原上远远近近点起了许多篝火“这些老少爷们仿佛一下子又投身到了古代,从中挖掘出了这块地方从前熟视无睹的一段时光和事迹。原始不列颠人在山顶火葬的骨灰,仍旧埋在他们家下的古冢里,清新依旧,不受打扰。很久以前在那里点燃的火葬堆火光,也和现在的篝火一样,曾照耀到下面的低地上。后来,此地出现了祭祀托尔和沃登的欢庆篝火,也盛极一时。其实,众所周知,如今荒原居民玩的这种篝火,就是德鲁伊特礼仪和撒克逊典礼混杂后的直系传承”。[6]这是大家在庆祝十一月五日的篝火节,“严冬将至,自然界里到处都敲响了熄灯的钟声,点篝火就是人类出于本能的抗拒行为。一年一度的冬季把恶劣天气、阴冷黑暗、悲愁死亡带到人间,篝火就是一种自发的普罗米修斯式叛逆习俗,来反抗这种节令。黑暗的混沌降临时,地球上被囚的诸神就跟着说:‘应该有光’”。[6]哈代小说中的乡土世界是远离工业文明的净土,它依旧保持着宗法制传统生活,洋溢着古朴的生活情调,回荡着远古历史的声音。大自然体现了原始的、恒久的生命力,是人类诗意栖居的环境。
二、荒原:文明的死敌
19世纪始于英国的工业革命使资本主义势力向农村不断渗透,此时的农村,机器取代了人工,资本左右了市场,乡间荒原上和谐的民俗风情、宁静的生活方式等都受到了冲击。哈代的小说开始记录了作者从早期的眷恋乡土到忧心故乡前途的心绪转变,《还乡》中尤为凸显了文明与自然对立的主题。哈代笔下的埃格敦荒原自古以来桀骜不驯,“文明是它的死敌,从有植被那天起,它的土壤就披上了这件古老的褐色衣服;这本是那种地层上的自然服饰,亘古不变。它那资深的衣裳只此一件,这对于人类在服饰方面的虚荣心有某种讽刺意味。一个人穿着颜色和样式都摩登的服装,跑到荒原,总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大地的服装既是这样原始,我们仿佛也要穿最古老、最朴素的衣服呀”。[6]资深的褐色服装意指朴实自然的荒原生活,古老传统的观念习俗,它与摩登的都市文明格格不入。哈代追求自然与人类整体的和谐生存方式,认为人类与自然是浑然不分的。19世纪中期的维多利亚时代正是资本主义文明大举侵袭的时代,在哈代看来,这种非理想的近代文明形态导致了自然和谐的破裂:大自然遭到大工业无情的破坏,传统的伦理关系和价值观念遭到文明的践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状态不复存在。
哈代作品中常以宇宙空间的广袤无垠来对照人类的微不足道,表现人类在宇宙空间的极其渺小和无足重轻的思想,埃格敦荒原原始古老,粗犷质朴,保守落后,多少个世纪一成不变。它把现代文明看成它的对头,用讥笑敌视的态度看待世事的变迁,并因此同企图改变它的居民发生了尖锐冲突,在《还乡》中文明与自然,文明人与荒原的对立通常以文明人的失败而告终。游苔莎羡慕巴黎浮华的生活,讨厌荒原的孤寂,认为荒原是她苦难的深渊,“是她的冥土”,[6]“她身处荒原却不研究荒原的意义,就仿佛嫁给外国人却不学外语。荒原微妙的美,游苔莎并未领略,所能抓到的,仅仅是荒原的缥缈云雾。荒原的环境,能让知足的女人赋诗,能让受罪的女人虔心礼拜,能叫虔诚的女人写圣歌,甚至能叫轻佻女人的沉思,现在却叫桀骜不驯的女人忧郁不合群”[6]。游苔莎出生在时髦的海滨胜地蓓蕾嘴,父亲是一名乐师,她曾受过很好的教育,父母过世后随外公来到荒原,她对于这一变动耿耿于怀,觉得被流放了一样,她向往诗歌与音乐,向往资本主义文明,时时刻刻想离开荒原去巴黎,但每一次挣扎,给她带来的只是更深重的悲剧命运。克林是荒原上的另一个文明人,他虽然出生在荒原,但从小被送到巴黎珠宝店当学徒,而后成了珠宝商人,受到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后“厌恶华而不实的生意”,毅然回到了荒原,荒原的苍茫雄伟和冷漠严峻令他陶醉,荒原上寄托了他美丽善良的梦想,他无法“眼睁睁看着世界上有一半人走向沉沦,缺少热心人倾全力教诲他们同与生俱来的苦难进行搏斗”,“坚信大多数人缺少的是那种给他们启智的知识,而不是致富的知识”,他想“为那些穷人和愚昧的人当一名教师”。[6]但是克林不了解荒原的乡亲们,他们还没有成熟到接受他的程度,沉睡在古老宗法习俗里的荒原人安逸于荒原上的简朴生活,对他的办学计划并不热心,觉得没有什么实际价值,认为“他永远都不会实现那个计划的”,“他还是多管管自己的事吧。”克林的办学计划最终落空。他经常一个人在荒原散步,发现荒原上的一切还和原来一模一样,“这不禁使他想到,千古不朽的历史演化是由未可预知的因素控制的”。[6]游苔莎和克林的结局反映了作者的生态思想,哈代认为理想的生活状态就是在亲近自然中悠闲地生活,亲近自然,就能够与大自然融为一体,领略到自然的雄壮奇美;背离自然,则不懂自然的内在规律和价值,将遭到大自然的抛弃。
三、荒原:生态的回归
19世纪的工业文明给自然生态带来了严重的破坏,哈代意识到现代文明在摧毁了自然本性的同时还给人们带来的严重的心理创伤。《还乡》中的埃格敦荒原未曾受过现代文明的侵蚀和浸染,历经千万年依旧保留了它的原始面貌。背离荒原的游苔莎促成了自己的毁灭,企图改造荒原的克林则失败告终。只有维恩和托马辛忠实于爱敦荒原这个古老的世界,他们热爱荒原、亲近自然,因此能够适应自己的环境并最终得到幸福。哈代通过刻画这些自然人表达了回归自然、尊重自然,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思想。维恩是红土贩子,成年累月在荒原上的农场游历,天空为被,大地为床,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常年在荒原上奔走已使得维恩与荒原浑然一体,“红土贩趴到地上,拖过两块泥炭,一块盖住头部和肩膀,一块盖住脊背和两腿。这样就是大白天,也很难被看见;泥炭的石南一面朝上,贴在身上,看着和长在地上一样”。[6]托马辛是个天真善良的姑娘“小媳妇走进房间,身后跟进一道斜阳,和她的体态很配,把她照耀得夺目生辉,就跟她的到来给荒原带来了光明一样。她的一举一动,一颦一蹙,都让人回想起栖息在她家四周的羽毛族。形容她的象征比喻无不以鸟儿开始,到鸟儿结束。她的举止婀娜多姿,就像鸟儿飞翔时多姿多彩。沉思默想时,就像红隼,张开翅膀,以无形的动作飘浮在空中;狂风中,就像轻巧的苍鹭,向着树林和山坡飘动,任凭劲风吹荡;惊骇时,就像悄然疾飞的翠鸟;宁静时,恰似飞掠而过的燕子”。[6]美国学者费尔普斯说过:“由于哈代先生心目中没有上帝,因此他就和树木、平原和江河等这个自然世界亲近起来。他和自然的亲热劲头几乎令人不能相信”。[7]哈代把维恩比作荒原上的石南,托马辛喻为荒原上的小鸟既使人物栩栩如生,又表述了人物的自然属性:人类和动植物一样是巨大的宇宙中的一个小小的部分。
哈代的小说使读者意识到大自然是一个生物圈共同体,山峦、河流、植物、动物及人都是这个共同体的成员,哈代把大自然理解为一种神秘的力量,能对人类的命运或者同情、或者嘲笑、或者无动于衷、或者袖手旁观。 《还乡》中的荒原就是一种保持得最完整的未被人类改造的自然状态,是不可控制的、野性的自然的象征,人类无法控制和支配它,它牢牢控制着人的行动和命运,哈代通过荒原的主题表达了他的生态思想:只有敬畏生命、回归自然,人类才能在大自然诗意地栖居。
(编辑:惠斌;校对:朱恒)
[1][美]戴斯·贾丁斯 (著),林官明,杨爱民 (译).环境伦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77-178.
[2]曾建平.自然之思:西方生态伦理思想探究 [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14.
[3][美]唐纳德·沃斯特.自然的经济体系[M].候文慧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79.
[4]聂珍钊.哈代的小说创作与达尔文主义[J].外国文学评论,2002,(2):91.
[5][美]霍尔姆斯·罗尔斯顿 (著),杨通进 (译).环境伦理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28.
[6]托马斯·哈代 (著),王之光 (译).还乡 [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1.5.6.14.15.67.70.177.381.81.214.
[7][美]W.费尔普斯.论托马斯哈代 [A].陈焘宇.哈代创作论集[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20-21.
Hardy's Ecological Ideas Perceived through the Heath in the Return of the Native
HU Min
(Foreign Language Department of Hun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Changsha Hunan 410205)
Wasteland has been given different symbolic meanings in literature in different times,and heath is the soul of the Return of the Native.This novel reveals Hardy’s ecological ideas:man should return to heath and return to nature,and keep a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with nature.
Thomas Hardy;the Return of the Native;heath;ecological ideas
I106
A
2095-1361(2011)02-0156-03
2010-11-19
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生态批评视角下的哈代经典作品研究”(项目编号:2010YBB053)阶段研究成果
胡 敏 (1971- ),女,湖南长沙人,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副教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英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