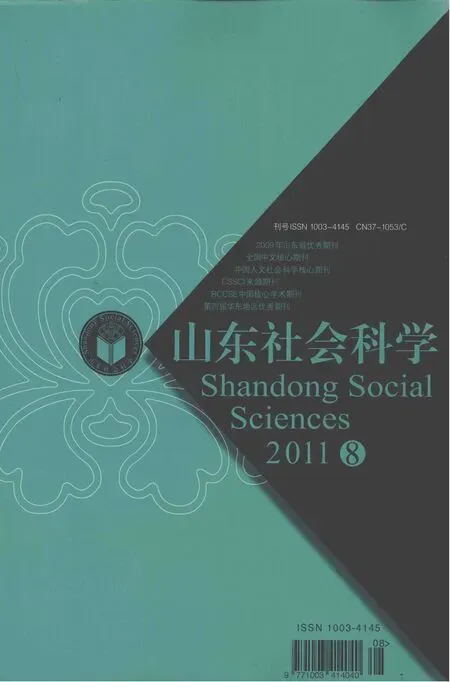论张洁小说的心理描写
周志雄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济南 250014)
论张洁小说的心理描写
周志雄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济南 250014)
张洁的小说注重对人物心理的刻画,这使张洁的小说一面指向生存的现实问题,一面指向精神世界的叩问。心理描写的恰当运用形成了张洁小说特有的心理化叙述风格,摇曳多姿的结构特点,水墨画和音乐抒情曲般的阅读效果,造就了张洁小说特有的人性内涵和精神深度。张洁的艺术选择与新时期的历史语境密切相关,是受外国小说影响的结果,也是与她独特的精神个性相适应的。张洁以丰富的心理描写,让我们见证了生命书写的力量感。
张洁;小说;心理描写;生命书写
张洁的小说很注重人物的心理描写,这不仅仅是一个小说写什么的问题,也是小说如何写的问题。心理描写是一种古老的文学手法,在我国古典文学中常用心理描写,现代西洋小说更擅长大篇幅的心理描写,但二者还是有很大差别的,前者更似蜻蜓点水的水墨画,而后者是浓墨重彩的油画制作,张洁小说的心理描写显然不是前者,但也不是后者,而是介乎二者之间,有着“比中国小说略细一些,比西洋小说略粗一些”的特点。弗洛伊德关于心理结构的理论对文学写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文学家在弗洛伊德之前就表现了潜意识,现代小说对非理性的潜意识的心理表现开拓了文学的表现疆域,正如福斯特所说的:“小说的特点在于:作家可以大谈人物的性格,可以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让读者听到人物的内心独白。他还能接触到人物的冥思默想,甚至进入他们的潜意识领域。”①[英]爱·摩·福斯特:《小说面面观》,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苏炳文译,第74页。20世纪80年代以王蒙为代表的中国当代作家对西方“意识流”进行了中国式的改造,去除了非理性的心理表现,而吸收了意识流动的心理描写方式,张洁小说的心理描写也多是在理性的层面上展开。张洁的小说写作跨越了30年的历程,其小说艺术的成就与心理化的表现手法有着紧密的关系。
一
“对于人性的任何深刻见解都是心理分析式的”,②[美]莫达尔:《爱与文学》,郑秋水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1页。心理描写是表现人物性格的重要方法。在现代小说中,心理描写之所以被广泛采用,是与文学的现代意识紧密联系的,即如鲁迅所说的要打破“瞒”和“骗”的文艺,写出世界的真实底色来。在写人物上要表现人物真实的灵魂,而不是重复一种简单化的人物类型,在具体的写法上不只是通过人物的言语和行动来表现人物,还要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展现人物独特的精神个性。张洁对人物心理的表现形成了作者特有的写作视角,这使作者总是积极地通过故事去审视人物的内宇宙,他们是高雅的钟雨、高尚的梁启明、自私自利的岳拓夫、为爱而疯狂的吴为、探索生命真谛的叶楷文,还有在世俗的白眼中艰难度日的荆华、梁倩等等。《从森林里来的孩子》中对梁启明形象的塑造笔墨并不多,但作者较好地运用了心理描写,将一个有高尚情操的右派塑造了出来。“他知道,生命留给他的时日已经不多了,他争分夺秒地把留在世上的最后时光全都用在孙长宁的身上。他相信乌云会散去,真理会胜利,真正的艺术将会流传下去。这个生长在遥远的林区里的孩子,一定会成为一个出色的音乐家,会的。”(《从森林里来的孩子》)这样的描写还显得有些简单,但几笔之中一个人物的精神灵魂被画了出来。这样的表现手法近似于白描,与古典文学中常见的心理表现手法是相似的。在《方舟》中,白复山的丑恶形象是通过其心理描写来表现的:“知道了又怎么样?狗屁!这些奶子已经像空布袋一样吊着的老母狗,牙口都不顶用了,还敢上来咬一口?白复山恨不得踹她们一人一脚,像踹开一切路障。”这一段心理描写多少有些丑化人物的意味,寥寥数语之中一个对女人怀着仇恨的“坏男人”就站在了读者的面前。如果说在这样的心理描写中,叙述人的感情倾向是明确的,人物的心理描写对人物性格的刻画是直接的、粗线条的,在另一些作品中,张洁对人物的心理描写则要深入、细致得多。如在《雨中》、《忏悔》、《无字》等小说中,心理描写也大多有烘托人物性格的作用,但这种表现是总体性的、无处不在的,作品的主要内容写的就是人物的心理流动过程,整部作品笼罩在一种心理化的叙述之中,人物的孤独、哀伤、忏悔等心情被表现得淋漓尽致。按照刘再复性格组合原理的观点,对人物性格多重性的表现是一部作品人物刻画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在张洁的小说中似乎还很少塑造出有多重性格的人物形象,但因为作者较好地运用了心理描写的方法,在不复杂的故事中写出了有着复杂内心世界的人物形象。比如在《条件尚不成熟》中,通篇小说贴着岳拓夫的个人心理展开,这是个行政官僚式的人物,对局里即将培育的第三领导梯队极为热衷,极力阻止自己的大学同学蔡德培入党,最终因为蔡德培提为副局长的事不需要党员条件,感觉自己处心积虑的做法是多余的,迅速采取行动开会讨论蔡德培的入党问题。一个内心打着“小九九”的自私自利、圆滑世故的官僚形象通过作者对其内心心理过程的层层解剖、放大,被入木三分地呈现了出来。
张洁的小说有着真切的现实关怀,作者写小说多是针对现实有感而发,小说所引起的轰动和争议也与题材效应有紧密的关系。在作者所写的“问题小说”中,通过人物的心理活动表现了对所讨论的问题的看法,心理描写很好地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如《爱,是不能忘记的》通过女儿姗姗(“我”)的心理描写提出问题:“我不由地想:当他成为我的丈夫,我也成为他的妻子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把妻子和丈夫的责任和义务承担到底呢?也许能够。因为法律和道义已经紧紧地把我们拴在一起。而如果我们仅仅是遵从着法律和道义来承担彼此的责任和义务,那又是多么悲哀啊,那么有没有比法律和道义更坚固、更坚实的东西把我们联系在一起呢?”“到了共产主义,还会不会发生这种婚姻和爱情分离着的事情呢?”这样的问题是由钟雨的爱情故事延伸而来的,小说通过女儿对母亲爱情历程的温习和审视思考爱情问题,并通过人物的心理活动作出了解答:“让我们耐心地等待,等着那呼唤我们的人,即使等不到也不要稀里糊涂地结婚。不要担心这么一来独身生活会变成一种可怕的灾难。”这篇小说有针对性地提出社会问题,通过人物的心理描写来深思问题并作出解答,人物的心理描写相当于作品中的“题眼”。
张洁的小说有对生存本质的追寻,这种追寻是哲学化的,作者力图追思人生、爱情的真相,这是带有终极性的精神追问,心理描写正是表现主人公对生命体验的凝思过程,往往带有人物个体的情感体温。《灵魂是用来流浪的》中最有意味的一段人物心理描写是秦不已与继父同归于尽的绝望心理:“秦不已的心,毫无规律,随心所欲地跳动着,时不时还停顿下来,仿佛在思考:继续跳动下去,还是就此罢手?出现在眼前的景象却十分错落、复杂。旺盛,强烈,活跃;或景物,或事件,或人物……浮动上下,浑然一片,深刻难忘而又无法确辨。只有一双眼睛比较清晰,距离也很近,那是谁?……好像是旅伴墨非,正睁睁地俯视着她。除此,什么也没有了。”在这段矛盾、模糊、冲动相互交织的主人公的内心描绘中,女子对男人的仇恨与审判被深度地表现了出来,心理描写写出了主人公“灵魂流浪”的过程。
张洁的心理分析是一种叙述的方式,在叙述中有意识地展示人物的心理,或者是人物自述,或者是叙述人对人物心理进行分析。当叙述人不时地跳出单纯的故事叙述而解剖人物的内心时,叙事不再纯净,而是很混杂,交织着多重声音。《无字》的心理分析化到叙述之中,小说以吴为的发疯开篇,叙述吴为发疯前的状态,叙述是概览性的,有待继续填充的。在发疯前有个记者打电话羞辱她:“听说你有个私生子?”小说由此展开对人物内心的描绘:“这种电话算得了什么?比这更惨绝的羞辱她忍受了几十年,可她的灵魂从未感到轻松,没有,一点也没有。不但没有,反倒越来越往深处潜去。……每当想起这些,她的眼前就漫起一片冥暗、混沌。在那冥暗混沌之后,一道咫尺天涯、巨无尽头、厚不可透的石墙就会显现,渐渐地,又会有一束微光射向那石墙的墙面。”这样的心理描写在小说中随处可见,它与小说中跳跃的事件叙述形成了映衬,共同完成了对人物灵魂的刻画。《无字》在总体结构上是一部回忆性的小说,它是吴为、叶莲子的回忆录,也是胡秉宸、顾秋水的回忆录。“出于对历史的爱好,他禁不住把纵横上下几十年的经历,做一个宏阔的题目来温习。……或许他本就是那疑惑中的一部分,这温习也就始于疑惑,止于疑惑,终究不得其解,长期处在‘剪不断,理还乱’的状态。”(《无字》)这种反复温习往事的方式形成了小说强烈的心理化叙述风格,形成了交响乐般的叙述效果。
二
侧重表现人物心理还是侧重叙述故事是现代小说与传统小说的重要分水岭。在18世纪中期劳伦斯·斯特恩的小说《项狄传》和《伤感旅行》中就表现了人物意识的流动,19世纪后出现了乔治·艾略特、戴维·赫伯特·劳伦斯、詹姆斯·乔伊斯、维吉尼亚·伍尔芙等著名的心理小说家。在现实主义的领域,心理描写被提到了新的高度,莎士比亚的戏剧因为表现人物内心的徘徊,塑造了著名的哈姆雷特形象,“生存还是死亡”成为富有典型意义的内心挣扎。托尔斯泰善于表现人物内心情感的微妙变化,把握人物心灵的辩证发展过程,其心理描写的方法被车尔尼雪夫斯基称为“心灵辩证法”。这些作家的艺术探索极大地拓宽了小说的表现疆域,也对我国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陈平原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一书中,陈平原认为中国小说有两个传统,一个是“史传”,一个是“诗骚”,五四时期的小说更注重“诗骚”,而淡化“史传”,即小说注重对“情调”和“意境”的表现,重视心理描写,从而突破了中国传统小说的情节结构模式。小说的心理化趋势是现代小说转型的重要方面,《狂人日记》、《沉沦》、《莎菲女士的日记》、《腐蚀》等现代文学名篇正是以人物灵魂的展现而具有现代小说的特色。
新时期小说在艺术上也承续了现代小说的这种“诗骚”传统,张洁的写作选择与新时期初特别的历史语境密切相关。有人统计1983年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18篇短篇小说中比较明显地带有心理化趋向的只有2篇;到1984年,获奖的18个短篇中有13篇出现程度不同的心理化趋向。①黄健民:《当代小说心理化趋向》,《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选择心理化的表现手法,体现了摆脱政治化时代思维僵化的文学模式的审美追求,心理化的写法让文学不再只是表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而是要正确地理解文学的内宇宙,心理化描写体现对人性的深层挖掘,是一种新的美学规范的寻找。对此,有人提出“心态小说”的概念,认为:“心态小说是一个更为宽泛的概念,它包括意识流小说,也包括一般的心理小说。它的特点是以主要笔墨展示、刻画人的复杂多变的意绪心态,故又被称作心灵剖析小说。张洁、张辛欣、刘亚洲等,均是新时期心态小说的代表性作家。”②张学正:《缤纷的小说世界:新潮小说选评(一)》,花山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3页。这在“伤痕小说”的发轫之作卢新华的《伤痕》中体现得十分鲜明,这篇小说采取了心理化的倾诉方式,以淡淡的哀伤和内心伤痕的抒发,激起了读者强烈的情绪反应,引起了文学界讨论的热潮。在这样的文学语境之中,一大批作家纷纷实验心理化的表现手法。张辛欣、谌容、张抗抗、李国文、茹志鹃、宗璞等一大批作家纷纷在作品中加大心理描写的力度,出现了《人到中年》、《北极光》、《南方的岸》、《我是谁》、《雨,沙沙沙》等注重心理描写的作品。在一个时期,是否有深度的心理描写几乎成为一个作家是否有创新性的标志。对这一现象,王蒙解释说:“为什么粉碎‘四人帮’以后写心理活动的作品多起来了?原因很多。一是我们突破了很多禁区,敢写心理活动。……其中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每个人在心理活动上所受到的考验,有时超过了他的肉体,我们要表现它。”③王蒙:《在探索的道路上》,《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4期。这样的创作潮流形成了评论家们所总结的文学“向内转”,并在八九十年代之交引发一场关于“向内转”的争论。“向内转”的提出者鲁枢元认为“向内转”是从19世纪末以来文学的一个世界性的走向,是“一种人类审美意识的时代变迁,是一个新文学创世纪的开始”。④鲁枢元:《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文艺报》1986年10月18日。对心理化写法的积极吸取,张贤亮曾有个概括:“中国式的意识流加中国式的拼贴画。也就是说,意识流要流成情节,拼贴画之间又要有故事的联系。”⑤张贤亮:《心灵和肉体的变化——关于短篇〈灵与肉〉的通讯》,《鸭绿江》1981年第4期。在我们所读到的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戴厚英的《人啊,人》、邓刚的《迷人的海》、张贤亮的《绿化树》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张承志的《黑骏马》、谌容的《人到中年》等作品中都具有张贤亮所说的“中国式的意识流加中国式的拼贴画”的特点。张洁小说的心理描写显然也具有这样的特点。
根据张洁的回忆,她从小喜欢阅读的书多是外国小说,“文学作品呢,她喜欢契诃夫、普宁、雨果、托尔斯泰的,中国的则最佩服鲁迅、老舍、冰心等老一辈的作品”。⑥邓国治:《我所认识的张洁》,见何火任编《张洁研究专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页。在这样的阅读背景下,张洁的艺术选择显然更注重对人物灵魂的写照。托尔斯泰的心灵辩证法、契诃夫的心理抒情化都是张洁写作起步时的摹写对象。“如果我们想了解灵魂和内心,那末除了俄国小说之外,我们还能在什么别的地方找到能与它相比的深刻性呢?”①[英]弗吉尼亚·伍尔芙:《论小说与小说家》,瞿世镜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12页。作为深受俄国文学影响的张洁,也吸收了外国小说重心理描写的特点。
莫达尔认为:“诉出悲伤的伟大作品,作者一定经历过其中的悲哀。像乔治·桑这样婚姻不幸的作家才会写出有关婚姻问题的小说。像海涅和谬塞这样失意的恋人才会写出最伤心的情诗。生命充满了哀愁,作者不需要费心去创造。”②[美]莫达尔:《爱与文学》,郑秋水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58页。在当代女性文学的历史上,女性作家的个人经验被女性作家们重视起来,自我成长的经验被作家们视为是女性话语表达的重要领域。心理描写与这种表现相适应,推进了女性特有的性别自我展现,张扬了独特的生命意识。“张洁的作品开创了一条通往中国当代知识妇女内心深处的道路。”③李子云:《女作家在当代文学史所起的先锋作用》,《当代作家评论》1987年第6期。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祖母绿》、《七巧板》、《方舟》都是表现女性情感世界的作品,其耗费了12年心血的《无字》也是一部表现女性命运的力作,选择心理化的写作方式有力地将女性内心的精神世界展现了出来。《爱,是不能忘记的》即便是在今天,读起来仍然有打动人的力量,倒不在于作品所提出的问题多么深刻,诚如作者所言,这不过是学习恩格斯著作的一篇读书笔记式的小说,但作品中所蕴涵的一种优雅的情调,一种含蓄、微妙的心理体验,一种对爱情执守的精神力量通过作品中日记本内容的展现深深地叩击着读者的心弦。《方舟》中对男性的丑化甚至带有一些偏激,对三个“寡妇俱乐部”的女性的命运表现也很难说就有社会普遍性,但小说通过人物内心世界的切入,说出了离婚女性的真实生活感受,深得一些女性读者的认同。表现女性内心世界的最高成就体现在《无字》上,这篇小说将心理回忆和大的历史风云相结合,以心理描写为纲串起一个家族四代女性的命运,以回环复沓的方式表现了在情感世界中纠缠、挣扎的女性内心世界,复调式的叙述结构形成了作品交响乐般的效果。张洁的作品是可以和她自身的经历相互对位阅读的,批评家雷达说:“张洁曾写过一篇很动情的散文《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我觉得长篇小说《无字》中最动人的部分是从那篇散文来的,一种刻骨铭心的依恋。她还写过一篇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写的是一种柏拉图式的爱,手都没有拉过,爱了几十年,只是远远地望着,默默地想着;《无字》当中,那个梦中的爱人似乎变成了生活中的伴侣,但现实中的那个叫胡秉宸的人就显得很丑陋了。我觉得张洁在这部小说里倾诉了女性特有的痛苦,有人说这部作品是以血代笔,也有人觉得作品有点儿累赘,太长了。”④雷达:《我所知道的茅盾文学奖》,《小说评论》2009年第3期。雷达的看法道出了张洁小说与自身生命情感的共振性,作为“以血写书”的作家,张洁选择心理化写法无疑具有通过写作“拯救”被伤害的灵魂的意味,虽然不是完全如同伍尔芙所说的“女作家的作品都是写她自己”,⑤[法]西蒙·波娃:《第二性——女人》,桑竹影、南珊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500页。但作品中明显带有个人情感的强烈体验,这是因为:“如果一个作家的作品中常常出现同一主旨,或继续维持某一口气,他个人生活中一定可找到某些原因。”⑥[美]莫达尔:《爱与文学》,郑秋水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62页。心理描写的恰当运用,造就了张洁小说的人性内涵和精神深度。
三
张洁的艺术选择与其自身的精神个性是相适应的。“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的生活印象都会影响、改变艺术家的心理构成。一般而言,生活积累的材料只影响到作品的形象外貌,深刻的人生体验才构成作品的灵魂。”⑦童庆炳:《文艺心理学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89页。张洁是一个敏感、独立、自尊的女性,在缺乏父爱的环境中长大,后来又经历婚姻的曲折,这些都促使张洁用艺术的方式去关注自我以及同类人的精神问题,不仅仅写出故事,更重要的是揭示他们的内心世界,表现他们的灵魂所饱经的折磨和伤害。心理化倾向只是张洁小说总体上的写作思路,如果不与坚实厚重的作品内容结合起来,也只是一个轻飘的外在之壳。张洁的写作一面指向生存的现实和问题,一面指向对精神世界的叩问。这种致力于思想深度的写作思路,必然使张洁作品中的心理描写总是和议论相关。张洁小说中经常出现站在不同视角的议论片段,这些片段与心理描写的内容构成了互文和参照的关系,共同将作品的意蕴推向哲学层面。当然张洁小说中的议论也会有一些负面的阅读效果,沈从文在谈到张洁的小说时认为:“张洁文中弱点,似有意从‘意识流’方式上用了些心,在对话中附加了些‘感想’或‘解释’,不善于直接从对话中加以安排处理,因此对读者反而发生不连贯印象。”⑧任葆:《深情的关注与希望——沈从文谈古华、张洁》,《作家》2008年第8期。
心理化写法形成了张洁小说摇曳多姿的结构特点。由于心理小说所带来的叙述方式的多样,既可以是外视角的透视,也可以是内聚焦的深入探查,还可以自由变换叙述的角度,依次展开人物的内心世界。《沉重的翅膀》中的主线是正派和风派人物之间的斗争,小说间所穿插的人物心理描写使小说张弛有度。而在《雨中》、《忏悔》等作品中,心理描写构成了人物的内心情绪流动,围绕人物展开的心理情感的描写有结构小说的作用,甚至就是小说结构本身。《无字》通过人物的回忆,将历史与现实交织展开,通过不同时段、不同主体的视角自由展开,纵横驰骋、上下求索,可谓是“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形成了典型的复调小说结构。在新世纪以来的作品《知在》、《灵魂是用来流浪的》、《一生太长了》中,心理描写化入故事的叙述之中,形成故事结构的“灵魂”。
重心理描写的小说因写作的笔力不在故事的讲述上,其写作超越表层意义的叙事倾向十分明确,最终要在意蕴上进入心灵的深层,力图揭示生活的本质。因此心理描写往往作为修辞方式进入象征层面,形成特有的精神指向。张洁的《方舟》、《祖母绿》、《七巧板》、《无字》、《知在》、《灵魂是用来流浪的》、《一生太长了》等小说无不带有这样的设计,作者在构思这些小说的时候,其生活的本质论意味很鲜明,意在通过这些故事对读者形成启迪。作者为揭示自己的精神探索,还设置了一些有隐喻意味的意象,如《知在》中的“画”、《灵魂是用来流浪的》中的“公式”、《祖母绿》中的“宝石”、《无字》中的“塬”等,借助这些意象,小说拓展了作品的意蕴空间。因这样的构思,作品形成了传神尚意、简约澹远的抽象诗化风格,有一种象外之境的精神飞跃,蕴涵着一种超然物外的哲思,给读者以精神的启迪。《一生太长了》以狼的内心活动为线,审视人性的贪婪与纷争,思索生命、死亡等终极性问题,由心理描写出发,小说已经进入文化象征意蕴层面。小说以狼的内心独白开篇,将读者带到一个假定的艺术世界之中。
作为一只狼,我真不该没完没了地琢磨这个问题:这条河是从哪里来的?
如果老执着在这个问题上,紧接着就会想:它往哪里去?
世界上有很多问题,其实是永远不可能找到答案的,如果不明白这一点,即便作为一只狼,也会使自己的一生充满烦恼。
可我偏偏就是这样一只十分明白却又执迷不悟的狼。
不论谁,在他的一生中,总得有一处可以随心所欲说话的地方,一个可以随心所欲说话的对象,是不是?
尽管狼的一生并不长久,不过十几年的样子,但在这个从来不易施舍的世界上,如果找不到这样一个对象或去处,那一生的日子就会显得太长、太长了。
不过我觉得,一个可以随心所欲说话的对象,无论如何也比不上一处可以随心所欲说话的地方。
应该说,作为一只狼,我是幸运的,在这深山老林里,能遇到这么一条苍茫的大河。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属于我,也不知道其他的狼各自拥有什么,然而我知道这条河是属于我的,仅仅属于我。
在缓慢的语速中,作者将狼拟人化,以狼内心独白的方式呈现对生命意义的思索。这是一只头狼,正处于生命的旺盛时期,它回首自己的一生,对自己为了生存而丧失颜面而难过,它主动离开了自己的狼群,只为按照自己的内心来作一次自己的选择。这是一只“哲学”的狼,“对‘后面’有一种不可理喻的固执”,狼的思索中寄寓着作者按照内心自由生活的渴望。小说中还以狼与人的关系审判人,狼试图与人友好,人却无法理解狼的善意,“即便生命垂危,他仍然没有放弃对我们与生俱来的恶意,还有嫌恶、拒绝、恐惧——千真万确的、毫无道理的恐惧。”狼是高洁的,令人起敬的,它选择了高贵地死去,而人是贪婪、丑陋的,这个假定性的叙述中,小说指向对人性阴暗面的批判。对于狼来说,选择高贵的、有尊严的死,还寄寓了作者对生存本质的沉思,狼离世前的最后思绪蕴涵着深刻的哲理:“我最后扫了一眼我生活过的这个世界,想起初生时才有的那种不明就里,为自己能来到这个世界而生出的感动和期待……可我们谁没有犯过这样的傻?”如果联系作者一生坎坷的人生经历,这篇小说与《知在》、《灵魂是用来流浪的》等作品一脉相承,表现了作者超然人世功利纷争的思想境界,这样的哲理性思索通过小说流水般的心理描写呈现出来,直切本质,酣畅淋漓。
张洁作品所隐含的水墨画般的效果,音乐乐曲般的抒情和情感表达,带有女性立场的偏激和痛切,抒情诗般的自由畅达,沉思生命本质的哲理追问,等等,无不与心理化的视角展开有关。张洁以深入细致的心理描写,让我们见证了生命写作的力量感,这样的写作是厚重的,也是令人敬重的。
I206.7
A
1003-4145[2011]08-0087-05
2011-04-08
周志雄(1973—),男,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责任编辑:陆晓芳sdluxiaofang@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