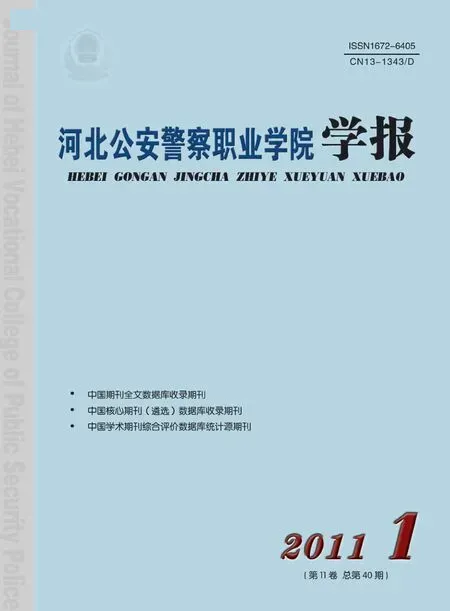信息时代商业秘密犯罪治理研究
周 舟
(华东政法大学,上海 200042)
信息时代商业秘密犯罪治理研究
周 舟
(华东政法大学,上海 200042)
根据我国刑法对商业秘密的定义,商业秘密具有秘密性、经济性、实用性、管理性等特点。应删去其中有关实用性的表述,实现与TRIPS协议对商业秘密定义的对接。商业秘密的重要性及侵犯商业秘密犯罪形势的严峻性决定了对其刑事保护的必然性。信息时代商业秘密犯罪治理存在诸多现实困境,理应从这些困境出发,完善相关法律规定与制度,建构信息时代完善的商业秘密犯罪治理机制。
信息时代;商业秘密;侵犯商业秘密罪;现实困境;治理机制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网络普及到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电子商务蓬勃兴起,信息犯罪、网络犯罪和经济犯罪交融在一起,商业秘密犯罪也呈现出新的样态。在当前这种信息网络社会的新形势下,治理商业秘密犯罪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结合民事、行政、刑事等多方面的手段进行。刑事法治保护体系作为保护商业秘密的最后一道防线,是商业秘密犯罪打击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屏障,在整个商业秘密犯罪治理体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加强商业秘密犯罪治理研究,不仅是现实的需要,是市场经济理论和经济快速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商业秘密国际保护的必然趋势。
一、信息时代商业秘密犯罪治理的理论基础
(一)商业秘密的概念
根据我国《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按照刑法的这一规定,作为商业秘密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应当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1.秘密性
秘密性是指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不为公众所知悉、尚未公开的特点。这是商业秘密的本质特征所在,也是商业秘密区别于专利以及其他知识产权的显著标志。根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禁止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二款的规定:“不为公众所知悉,是指该信息是不能从公开渠道直接获取的。”如果是公众周知或者公用的通用技术及技术方法,则不是秘密。
2.经济性
经济性是指通过对商业秘密的使用,能够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或为其获得竞争优势。这一特征是商业秘密的价值所在,也是商业秘密受到法律保护的根本原因。根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禁止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三款的规定,商业秘密的价值性包括“现实的或者潜在的经济利益或者竞争优势”。
3.实用性
实用性是指商业秘密具有确定的可应用性,即通过运用商业秘密能够为所有人创造出经济上的价值。它不限于目前可以在商业中运用,也包括将来可以在商业中运用的信息。没有实用性的技术信息或经营信息不能成为商业秘密,如一些不能转化为具体、可操作方案的抽象的原理、原则等。
4.管理性
管理性是指权利人为保障自己取得和拥有的某项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不被公众所知悉的主观愿望和实际上采取的控制性措施。控制性措施既包括各种“硬件”措施,如将有关文件放置在保险柜中、架设电子眼监控等,还包括各种“软件”措施,如建立保密制度、与员工签订保密协议等。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简称TRIPS)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商业秘密属于一种“未披露的信息”,它“在某种意义上属于秘密,即其整体或内容的确切体现或组合,未被通常从事有关信息工作的人普遍所知或容易获得;由于秘密具有商业价值,在特定情势下合法的信息控制人已经采取了保密措施”。概括而言,商业秘密需具备秘密性、价值性和管理性的特点。此外,在英美法系国家,对于商业秘密也都强调秘密性、价值性和管理性的特点。相比之下,我国刑法中规定的商业秘密除要具备秘密性、经济性和管理性外,还要具备实用性。对此,笔者认为,应删去我国刑法对商业秘密的定义中有关实用性的表述,从而实现我国刑法与TRIPS协议对商业秘密定义的对接。这是因为,实用性和经济性实际上都是商业秘密价值性的表现形式,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肯定经济性,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则肯定具有实用性,即从本质上来说,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与具有实用性可以归结为一个要件,均体现了商业秘密的价值性。
(二)信息时代商业秘密刑事保护的理论依据
在知识经济的大背景下,商业秘密已成为企业生存、竞争的极其重要的手段,加强对商业秘密的刑事保护已经成为国内外知识产权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
1.商业秘密的重要性决定了对其刑事保护的必然性
国家的发展主要取决于工业效率,而工业效率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知识产权的保护。在信息时代,知识产权是企业的灵魂,国际知名公司其知识产权资产的比重都远远超过实物资产。据此,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充分运用刑事法律武器严厉打击各种形式的侵犯商业秘密的犯罪活动,实现对商业秘密的刑事保护,既有利于维护商业秘密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有利于公平竞争市场环境的形成和实现,同时也是参与国际竞争、与世界经济接轨的需要。
2.侵犯商业秘密犯罪形势的严峻性决定了对其刑事保护的必然性
2004年至2008年,全国公安机关共立侵犯商业秘密犯罪案近600起,占全部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立案总数的6%;涉案金额逾20亿元,所占比例达到了32%。而2009年发生的“力拓商业间谍案”则以其涉案金额之巨、危害之重冠绝全球,再次引起了人们对侵犯商业秘密犯罪的关注。对商业秘密进行周密的刑事保护,以刑罚利器严惩侵犯商业秘密的犯罪行为再次成为世界各国的普遍共识。据此,我们理应完善相关刑事立法,从刑事法制的层面有效控制与预防侵犯商业秘密的犯罪行为,进而形成商业秘密刑事保护的有效机制。
二、信息时代商业秘密犯罪治理的现实困境
(一)罪名及刑罚设置不合理
我国刑法对于侵犯商业秘密罪客观方面的行为表现形式的规定,与世界各国刑法或者《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大致相同,都包括盗窃、利用、胁迫等不同手段。但是,除了我国将侵犯商业秘密罪作为一个单一罪名予以规定外,世界各国无不把侵犯商业秘密罪作为一个类罪名予以规定,在其之下,根据侵犯商业秘密的具体手段的不同,再设置若干具体的商业秘密犯罪,例如泄露工商秘密罪、刺探商业秘密罪等。应当看到,这种将各种性质不同、主体身份不同、社会危害性不同的行为规定在一个口袋罪名之下并设置相同法定刑的立法形式使得侵犯商业秘密罪的犯罪构成及行为特征过于宽泛,不利于罪名的细化、操作与认定,也有违罪名设置的一般原则和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难以充分发挥刑事制裁在惩治商业秘密犯罪行为、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方面的应有作用。
(二)刑事打击标准模糊
根据《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行为人的行为只有达到已经或者可能给商业秘密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的程度才可能构成犯罪,否则应当按照一般的侵权行为处理。应当看到,虽然我国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明确了“重大损失”以及“特别严重后果”的含义,但就侵犯商业秘密罪而言,在这些规定中对于如何计算商业秘密权利人的损失却没有明确的可操作性的规定。在办案过程中,计算商业秘密权利人的损失通常有以下几种方法:1.商业秘密权利人收入的减少额;2.侵权人因侵权行为获得的利益额;3.商业秘密的研发费用;4.商业秘密的自身价值。由此可见,在办案过程中,“重大损失”的认定标准是千差万别,很不统一的。刑事打击标准的这种不确定性,不利于司法实践中对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准确认定,也反映出侵犯商业秘密罪罪与非罪之间的模糊性。
(三)侵犯商业秘密罪结果犯的立法模式不科学
根据《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在客观上要求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但以非法手段获取商业秘密的行为,如果行为人不使用、不披露,只是自己持有,该商业秘密仍处在秘密状态,无论如何不会给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因此,单独以第二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行为构成犯罪的情况几乎不可能发生。同时,该条第二款规定的以侵犯商业秘密论的获取行为,如果行为人不使用、不披露,同样也不会给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可见,将非法获取行为与非法使用、非法披露行为并列分别作为构成犯罪的行为要件是不妥的,在构成要件上缺乏科学性。
(四)侵犯商业秘密罪主观方面的规定不明确
我国《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第二款规定:“明知或应知前款所列行为,获取、使用或者披露使用他人的商业秘密的,以侵犯商业秘密论。”理论上一般将这种行为方式称为间接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而将其他几种行为方式称为直接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对于直接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主观上是出于故意,理论上并不存在太大争议。但对于间接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主观方面,有学者认为,“明知”前款所列行为而实施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是一种故意的犯罪行为;“应知”前款所列行为而实施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则是一种过失的犯罪行为。也有学者认为,侵犯商业秘密罪是一种故意犯罪,其主观方面只能由故意构成,过失不能构成本罪。作为刑法分则中侵犯商业秘密罪中的“应知”是对具体犯罪对象的理解内容,其应理解为“应可推为明知”,是一种推定故意的心理态度,而不应包括犯罪过失,亦即间接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也只能由故意构成。由这些争议可以看出,我国刑法对侵犯商业秘密罪主观方面的规定还不够明确。
(五)诉讼证明责任机制不完善
商业秘密不同于商标、专利、著作权,它没有向国家特定机关申请注册,而且同一行业内很可能存在很多人拥有与其相同和相近的商业秘密。由于商业秘密具有的这种秘密性,侵犯商业秘密的犯罪行为也往往是秘密实施的,这就使得商业秘密的权利人在提起刑事自诉时,举证非常困难,而且行为人一旦得知自诉人开始调查取证时,极有可能转移或销毁证据。因此,许多被害人往往会通过其他途径解决,这就使得许多侵犯商业秘密的犯罪行为得不到有效惩处。
(六)案件审理方式不合理
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确定的不公开审理的案件仅仅限于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和个人隐私的案件,而没有涉及侵犯商业秘密的犯罪案件。鉴于商业秘密的特殊性,只要公开审理,就有可能造成商业秘密在更大范围内的扩散,给权利人造成更大的利益损失,如此行事也将与权利人的诉讼初衷完全相背。此外,在进行侵犯商业秘密罪的侦查和诉讼时,不可避免地会有许多人介入并知悉该商业秘密,如侦查人员、审判人员、代理人、辩护人、当事人、鉴定人、证人、书记员、法警等,这些人员一旦擅自披露或使用该商业秘密,同样会造成对商业秘密的第二次侵犯,而现行刑事立法中对诉讼参与人及相关人员的保密义务和失密责任也还没有专门规定。
三、信息时代商业秘密犯罪治理机制的建构
(一)细化罪名体系
就我国刑法对侵犯商业秘密犯罪的罪名设置而言,笔者认为,应将侵犯商业秘密罪确定为一个类罪名,在此类罪名之下,根据各种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性质的不同,具体设定成不同的个罪名。具体而言,我国刑法可在侵犯商业秘密罪之下,再分别设立窃取商业秘密罪、泄露商业秘密罪、侵占商业秘密罪和以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商业秘密罪等四个罪名,并根据行为不同的社会危害性分别规定相应幅度的法定刑。这样既有利于贯彻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也有利于司法操作。
(二)统一侵犯商业秘密罪中“重大损失”的计算标准
对于如何计算商业秘密权利人的损失,我国目前还没有明确的可操作性的规定。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的规定:“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给被侵害的经营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被侵害的经营者的损失难以计算的,赔偿额为侵权人在侵权期间因侵权所获得的利润;并应当承担被侵害的经营者因调查该经营者侵害其合法权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所支付的合理费用。”该款规定了权利人损失的计算方法,即损失额=损失+调查费;被侵害人的损失难以计算时,则损失额=侵权者的获利+调查费。也就是说,这里规定的赔偿额有两种计算方法,即权利人的所失或侵权人的所得(利润)。笔者认为,虽然该款本来是针对“经营者”所作的规定,但因为有关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给权利人造成的损失尚没有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故可以将该款确立的原则适用于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场合,进而统一侵犯商业秘密罪中“重大损失”的计算标准,即以权利人的损失额或者侵权人的利润作为计算的标准。
(三)在侵犯商业秘密罪中增设“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要件
正如前文所述,“造成重大损失”并不是影响所有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情节,在非法获取商业秘密这一行为中,就不可能存在造成重大损失的情况。因而,将“造成重大损失”同时作为非法获取商业秘密的行为与非法使用、非法披露商业秘密的行为成立犯罪的构成要件显然有所不妥。应当看到,非法使用、非法披露商业秘密的行为要比单纯地非法获取商业秘密的行为社会危害性要大,根据举重以明轻的原则,既然非法使用、非法披露商业秘密的行为只有给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才能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那么,非法获取商业秘密的行为也应当具有一定的严重情节才能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因此,我们在将“造成重大损失”作为侵犯商业秘密罪定罪情节的同时,理应增设“具有其他严重情节”作为与“造成重大损失”并列的可予选择的定罪情节。
(四)在刑法条文中明确侵犯商业秘密罪中“应知”的含义
根据《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直接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人主观上只有出自故意才能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过失不能构成本罪,而出于过失直接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又显然大于出于过失而间接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据此,在对过失直接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不作为犯罪论处的情况下,认为《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第二款规定的第三人间接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可以由过失构成,显然不尽合理。根据刑法的基本理论,刑法分则中的“应知”是不同于刑法总则有关疏忽大意过失中的“应当预见而没有预见”的。“应当预见而没有预见”反映的是行为人对危害结果在负有预见义务和预见可能的情况下,主观和客观上均没有预见。而“应知”则反映的是行为人对于某种危害行为的对象实际上是认识到的,从犯罪的故意内容来讲实际上具备了认识因素,体现为一种客观上的预见性,其本质上是属于“明知”的一种表现形式,只是在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其主观上对犯罪对象是“明知”的情况下,法律使用“应知”这一用语从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司法机关的证明义务,因为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对犯罪对象“明知”是非常难以证明的。正如有学者指出,两高在刑法分则中对于部分犯罪对象用“应知”来解释“明知”,其目的是通过简化的证明过程来提高诉讼的效率,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指导思想在刑事领域的体现。由此可见,理论上之所以对间接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主观方面存在争议,其原因就在于对侵犯商业秘密罪中“应知”的含义的理解存在偏差。据此,笔者认为,理应在刑法条文中明确侵犯商业秘密罪中“应知”的含义,进而明确侵犯商业秘密罪的主观要件。
(五)实行举证责任的适度转移
在侵犯商业秘密犯罪的自诉案件中,笔者认为,应实行举证责任的适度转移,从而减轻商业秘密权利人选择刑事途径打击犯罪的难度。具体而言,在侵犯商业秘密犯罪的自诉案件中,自诉人只要能够举证自己合法拥有某种商业秘密,而被告人拥有与自己相同或者非常相似的商业秘密,且其与自己的商业秘密有过某种接触(具有实施盗窃、利诱、胁迫以及非法占有等条件),权利人的举证责任便告完成。而获取、泄露或使用他人商业秘密的被告人,则有义务举证证明其利用的商业秘密来自正当合法的途径,否则,法院可推定被告人属于侵犯他人的商业秘密。
(六)采取不公开审理方式并明确诉讼过程中相关人员的保密责任
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一条第二款中规定:“对于当事人提出申请的确属涉及商业秘密的案件,法庭应当决定不公开审理。”但笔者认为,还应在《刑事诉讼法》中对侵犯商业秘密案件明确作出统一不予以公开审理的规定,如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涉及商业秘密的刑事案件一律不得公开审理”等。此外,还应在刑事诉讼中引入临时禁令制度,并明确诉讼过程中相关司法人员的保密责任。其中,引入临时禁令制度,能够及时制止侵犯商业秘密的违法犯罪行为,防止犯罪行为人在诉讼中继续侵犯商业秘密权利人的合法权益。而明确相关司法人员的保密义务与法律责任,则可以防止商业秘密在诉讼过程中受到二度伤害。
[1]王志广,吕伟,李春雷.侵犯商业秘密罪探析[J].人民检察,2009,(12).
[2]赵艳.论侵犯商业秘密犯罪的刑法调整[J].潍坊学院学报,2007,(3).
[3]夏菲.论商业秘密犯罪的认定——兼与美国相关制度比较研究[J].犯罪研究,2005,(1).
[4]李文燕,田宏杰.全球化背景下完善我国商业秘密法律保护之构想[J].山东公安专科学校学报,2002,(3).
[5]刘宪权,吴允锋.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理论与实务[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6]肖函,张振.关于侵犯商业秘密犯罪的认定与立法界定[J].商业经济,2006,(7).
[7]赵秉志.当代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
[8]刘宪权,吴允锋.侵犯商业秘密罪若干争议问题研究[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6,(4).
[9]游伟,张本勇.侵犯商业秘密罪的认定及诉讼问题[J].人民司法,2000,(3).
[10]何正泉.论间接侵犯商业秘密罪的主观方面[J].中南民族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9).
[11]陈龙鑫.侵犯商业秘密犯罪成因与抗制对策[J].吉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1).
Research on Management of the Business Secret Crime in Information Age
Zhou Zhou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Shanghai,200042)
According to the definition of business secrets in criminal law of china,privacy,economy,practicality and manageability are the characters of business secrets.But in order to conform to the definition of business secrets in TRIPS agreement,the expression on practicality in our criminal law should be deleted.The importance of business secrets and the serious situation of the crime of infringing upon business secrets determine the necessity of criminal protection.There are many practical difficulties in the management of the crime in information age.We should improve provisions of relevant laws and systems to construct sound management mechanisms of the business secret crime.
information age;business secret;crime of infringing upon business secret;practical difficulties;management mechanisms
D924
A
1672-6405(2011)01-0034-04
周舟(1987-),男,江苏东台人,华东政法大学刑法学研究中心学术秘书,主任助教,刑法学硕士研究生。
2011-02-17
王凤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