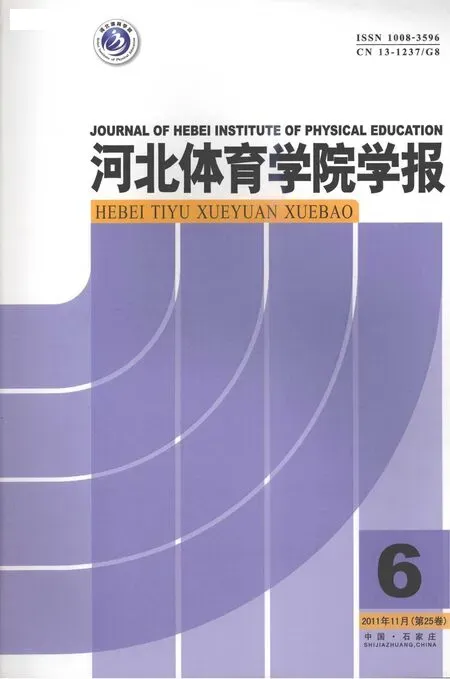史前时期武术的萌芽探究
王 震,周广瑞,张继合,王军伟
(1.上海体育学院 武术学院,上海 200438;2.上海体育学院 研究生处,上海 200438)
史前时期武术的萌芽探究
王 震1,周广瑞1,张继合2,王军伟2
(1.上海体育学院 武术学院,上海 200438;2.上海体育学院 研究生处,上海 200438)
采用文献法、历史与逻辑分析法对史前时期的武术萌芽进行了深入探究。认为:原始人进化完成、手足分工,是武术萌芽产生的契机;由本能到自觉再到自保意识的演进是武术萌芽产生的内在诉求;原始战争频发成为推动武术萌芽的轴心力量;武与舞 “联姻”的运动形式,实现了萌芽期武术的发展历程。
史前时期;武术;萌芽;进化;意识演进;原始战争;舞蹈
有历史记载以前的时期称为史前时期[1],中国的史前时期主要指商代以前。该时期跨度非常大,前后经历了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在这段漫长而艰辛的历史中,人类及人类社会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进化过程,与此同时也萌生、发展出了诸多社会文化现象,形成了璀璨的中华文明。武术作为中华民族创造出的一种特定的社会文化现象和身体运动形式,其萌芽可以追溯到史前的原始社会之中。
武术的起源是武术史研究无法回避的问题,对此诸多专家学者纷纷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一般认为武术的起源与原始先民的生产实践、原始战争、原始舞蹈、宗教娱乐等活动有着密切联系[2]。也有学者提出武术起源于夏朝时期的器械技艺[3]。这些研究成果无疑对厘清武术起源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从事物起源的特性来考察,武术的萌芽应该属于人类文化起源进程中发生学的范畴,而 “发生”永远是一个过程,“从研究起源引出来的重要教训是,从来就没有什么绝对的开端……起源是无限地往回延伸的,因为一些最原始的阶段本身,也总是以多少属于机体发生的一些阶段为其先导的。”[4]因此,武术作为原始人类为争取生存权而创造的身体运动形式,在原始社会萌芽过程中的每个阶段,必定是以前一阶段的发展为基础的,同时又成为其下一阶段发展的契机,整个过程呈现一种 “螺旋式上升”的图景,最终从生活实践中脱离出来,成为了一种特定的社会文化现象。
1 手足分工——武术萌芽的契机
武术作为中华民族创造的独特身体文化现象,从表现形式看就是手与足的运使文化。握拳作为人类应对危险的本能反应行为,成为人类在自保求生中使用的基本搏击方法,因此在中国武术中就形成了风格多样的 “拳”文化,如 “握拳如卷饼”的 “四平拳”、太极拳虚握的 “空心拳”、通背拳中指突出形若鸡心的 “尖拳”或曰 “中拳”或曰 “透骨拳”或曰 “凤眼拳”、醉拳的 “端杯拳”、蝗螂拳的 “刁手拳”等形状,也产生了拳之冲、贯、撩、劈、扣等方法,以及配合不同身体姿势的各式各样的打法[5]。除此之外,还有因地域文化差异形成的 “腿”文化,如有以弹、蹬、踹、勾、箭弹等屈伸性腿法为主的潭腿,“三只手”打人的戳脚等以腿为主要技击特点的武术流派。因此,原始人类独立行走和手的解放,就成为了原始武术萌芽的契机。
约500万年前,在蛮荒的中华大地上第一批像人的古猿出现,生物进化有了新的转折,它们的特征更像今天的人类一样双腿直立行走,因此它们被称为类人猿[6]。300万—4万年前是人和人类社会形成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原始人被称为 “正在形成中的人”或 “猿人”,其主要代表是“直立人”和 “早期智人”。“正在形成中的人”手足分工和直立行走基本完成,同时脑的重组和扩大更是其体质形态变化的重要一环。手足分工后的原始人类,正式与猿类划清了界限,虽然在智力、外貌形态上与现代人存在较大差距,但是从身体结构上看已经与现代人没有差别了。更重要的是,手的解放成为人类向现代人进化的 “催化剂”,成为了人类创造文明和无数因子发生的肇始。恩格斯在评价工具制造的发生时这样说道:“在人用手把第一块石头做成刀子之前,可能已经经过了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但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完成了:手变得自由了,能够不断地获得新的技巧,而这样获得的较大灵活性便遗传了下来,一代一代地增加着。”手的灵活运使,促发了工具制造的产生,这也使人从动物的 “身份”中脱离出来。随着手足分工的形成,原始人类在采集生活中,逐渐掌握了走、蹬、爬、攀、摘、抓、掰等生活技能,这不但能让他们获得更多的生活资料,同时能更好地逃避巨兽的袭击。这时原始人类使用的器具还极为简陋,有尖状器、砍砸器、刮削器等类型,渐渐他们也学会了一些砸、砍、挥、削、刻等简单的动作。无论是在改变自然还是改变自身的活动上,都不再像以前那样仅仅是本能行为的结果,而是已经初步开始了的有目的、有意识地通过劳动开始改造自然、改造自身、创造文明的伟大进程。
2 思维意识的演进——武术萌芽的内在诉求
武术作为人创造的一种文化形式,其发展史犹如人的进化史一样,都经历了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 “进化”过程,这与人自身,尤其是人类思维意识的发展息息相关,因为从一定程度上说,武术也是人类思维与客观现实相互作用的产物。“随着手的发展,头脑也一步一步地发展起来,首先产生了对个别实际效益的产生条件的意识,而后来在处境较好的民族中间,则产生了对制约着这些效益的自然规律的理解。随着自然规律知识的迅速增加,人对自然界施加反作用的手段也增加了。”手的解放和自由运使,推动了原始人类大脑的不断发展,从而促使人类的思维意识不断演进,随之对自然规律的认识也不断深化。“我们的意识和思维,不论它看起来是多么超感觉的,总是物质的、肉体的器官即人脑的产物。”即人脑是意识和思维的物质基础。在原始人类长期的进化发展中,“人脑的脑量变大,绝对脑重增加”,“人脑皮质层有了语言功能区的分化,视、听觉的发达,第二信号系统的出现构成了人类特有的思维活动”,并 “在劳动过程中由于人手部的灵活和使用工具,脑部也发生相应的变化,思维发展,手脑结合,人类逐渐学会制造简单的木器和石器工具”[7]。制造工具的劳动行为,真正标志着人类意识的出现。只有在以制造工具为开端的劳动实践中,自然意识才进化为自我意识,真正的创造性劳动才从这里开始,人类的全部文化才从这里发端。
意识和思维是人脑对客观存在的观念的、心理的反映,是客观存在在人脑中的主观观念、心理映象。这种主观观念与心理映象,只有在人与客观存在发生作用时才形成。原始先民 “日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生存于 “人民少而禽兽众”、“鸷鸟攫老弱,猛兽食颛民”的恶劣环境中,为生存而斗争成为 “适者生存”的不二法则。正是基于对自身生存状况和自然规律的初步认识和把握,原始人类进行了创造性的生产活动,日益改造着劳动工具,使之更加精细、锋利、多样,以适应生存的需要。从现有的考古发现中我们可以发现,在旧石器时代,已出现了尖状石器、石球、石手斧、骨角加工的矛,以及对当时生存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弓箭,而到了新石器时代末期,则出现了大量的石斧、石铲、石刀和骨制的鱼叉、鱼镖,甚至还有铜钺、铜斧等多样化的器具。这表明在恶劣生存环境的激发下,原始人类实现了本能到自觉意识的全面转化,他们制作的多样化的生产器具,成为了战争中军事武器的雏形。他们还学会在生存的部落周围利用地势挖掘围沟防止野兽或外族侵袭等。在这种自保意识的促动下,原始人产生了如何在人与人战斗中取胜 (技击方法)的内在诉求,武术因子也在这样的思维下逐渐萌芽。
3 原始战争——武术萌芽的轴心动力
据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的研究,人类生活在地球上已经有300多万年的历史。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原始人类 “发明”了诸多运动形式,如跑、跳、投掷、攀登、游泳等,以便能够在恶劣的环境中争取生存权,同时这也成为最原始的“体育活动”,也是今天诸多体育项目的源头。武术作为一种特定的身体活动形式,其萌芽因子也蕴含于其中。然而,推动武术从原始 “体育活动”中脱离出来,成为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技击术的轴心力却是原始战争。因为在原始的生存斗争中,人类与猛兽抗衡固然是萌生搏杀技能的因素之一,而人与人之间的搏杀格斗对武术 “催生”则起了更为直接的作用[8]。《易经》说:“民物相攫,而有武矣。”《吕氏春秋·荡兵》说:“未有蚩尤之时,民固剥林木以战矣。”又说:“争斗之所自来者久矣,不可禁,不可止。”这反映出原始先民好勇争胜的强悍性格,而正是这种性格 “构成了与武术萌芽极其紧密的文化渊源关系。”[9]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法·拉法格也指出:“力量和勇敢是处于经常不断的彼此斗争和同自然斗争的原始人的首要的和最必需的美德。”正因如此,原始人逐渐将搏斗技能作为自身的基本素质而加以严格训练。“从儿童时代起,他们的身体靠体操而变得灵活和健壮,靠斋戒和拳击来练强身体。他们常常因拳击而毙命。”[10]
原始社会后期,私有制出现,社会等级分化,当生存资源的稀缺性与人类的自私性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时,各部族为了繁衍生息,就爆发了原始的部落战争。《史记》载:“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山海经》载:“蚩尤作兵伐黄帝。”《中庸》记载了史前以尧、舜、禹为代表的北方华夏集团向南征讨以蛮苗为代表的三苗部落集团的战争,这也是我国最早的南北军事对峙[11]。 《墨子·非攻下》对 “禹伐三苗”的战争作了详尽描写:“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龙生于庙,犬哭于市,夏冰,地坼及泉,五谷变化,民乃大振”,展现了原始战争的惨烈。伴随这样残酷的战争,原始人手中的劳动工具转变为战场杀敌的兵器,还进一步出现了用于作战的专门器械,如 “蚩尤作五兵”和蚩尤 “以角抵人,人不能向”的记载,这表明原始战争不仅有力地促进了器械制作的发生、发展,对徒手的擒、拿、摔、打等战斗技能的产生也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12]。尽管在原始社会,尤其是原始社会后期出现的这些充满格杀搏斗的武力活动还不能称之为“武术”,但是这种生产活动与军事活动对武术的萌生奠定了基石。
4 舞武 “联姻”——武术萌芽的表征
原始社会初期,人类的生存环境是极其恶劣的,这时人与自然之间基本上是一种对立的关系,人只能被动地适应自然,正如马克思所说:“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存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它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13]然而即使是在这样艰苦的生存条件下,原始人类跟其他动物一样也有着追求快感的 “本能嬉戏”行为。这种行为不直接指向外在的功利目的,而是与运动系统和高级神经系统生命运动的内在功利目的相符,即满足了动物本身的运动欲,有学者称这种 “本能嬉戏”的行为为 “娱乐原欲”[14]。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自身的进化,人的各种感觉和意识变得丰富和深化起来。一方面,“人离开动物愈远,他们对自然界的作用就愈带有经过思考的、有计划的、向着一定的和事先知道的目标前进的特征”,另一方面,“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人类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运用,使人类掌握客观世界的活动上升为一种 “自由自觉的活动”和 “有意识的生命活动”[15]。随着人类对客观世界和自我认识的不断加深,人的身体活动更加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如原始人 “创编”了宣导 “筋骨瑟缩不达”之症的 “消肿舞”,有表达喜怒哀乐情绪的 “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原始舞蹈的产生对与原始人的生活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它不但让原始人类有了保持健康、延长寿命的运动形式,而且成为萌芽期 “武术”技能得以总结的重要表现形式。
著名学者闻一多先生曾说:“除战争外,恐怕跳舞对于原始部落的人,是惟一的使他们觉得休戚相关的时机,它也是对于战争最好的准备之一。因为操练式的跳舞有许多地方相当于我们的军事训练。”表明了舞蹈与武术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武、舞在原始状态下是合一的,如 《诗经》中为 “象舞”而 《礼记》中则作为 “象武”;《春秋》中的“以蔡候献舞归”在 《谷梁传》的解释中却改为 “献武归”等。舞就是武、武就是舞,武舞同源,舞武难分[16]。原始先民通过 “舞”的形式进行格杀技能的训练即 “武舞”,也称 “战舞”[17],据 《韩非子·五蠹》记载,“当舜之时,有苗不服,……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显然这种 “干戚舞”既是军事操练,又带有某种武力炫耀,即“用武力威逼有苗臣服的意思”[18]。原始先民还将舞作为军事训练的形式,《山海经》记载 “大乐之野,夏后启于此舞九伐。”《礼记》载:“一击一刺为一伐”,这说明当时的军事训练不仅有简单的单个技术,而且有一击一刺的连续演练。这种 “武舞合一”的现象,在今天的民俗活动中仍未分离,如永新盾牌舞、湛江舞鹰雄、闽南宋江阵、潮汕英歌舞等,在这些民俗舞蹈活动形式中均有武术的活动内容。由此看出,原始的娱乐活动 “舞”对武术萌芽起着重要的载体作用,原始人类通过 “舞”使得在战斗中积累下来的实用技击动作便于记忆,舞本身也成为军事训练的重要形式,并进一步衍化出了简单的 “套路”练习,这也成为传统武术套路的滥觞。至原始社会末期,历史文明的曙光来临之际,武术作为原始人类在实践中总结出的技击形式和方法,逐渐从原始社会生活中脱离出来,技击实用性成为这种活动的主要属性,完成了史前时期武术萌芽的艰辛历程。
5 结语
作为舶来品的 “体育”一词,意指人类社会中的各种身体活动形式。在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由于传统文化和不同地域文化的滋养,形成了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其萌生渊源均可追溯至史前原始人类的生活实践中。武术作为中华民族独特的智慧创造,从远古人类的生产生活中萌生,经历百万年演变而发展至今,薪火相传,连绵不绝,最终形成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体系。久远的历史赋予了武术深厚的文化内涵,其形成是许多复杂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但诸多因素中在武术发生、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尽相同,在我们探讨武术起源时,应该将其中最主要和起决定性的要素剥离出来,以真正揭示武术产生、发展的规律。本文就是基于此种思考进行的初步探讨,旨在为重新梳理史前时期武术萌芽的路径起抛砖引玉之功。
[1] 王树民.文字记载中的史前历史时期[J].河北学刊,2005(1):148.
[2] 蔡建,李海停.浅析武术的起源与技术演进的特点[J].山西师大体育学院学报,2005(3):54.
[3] 于志钧.中国传统武术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4] 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5] 戴国斌.武术的文化生产[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8.
[6] 郭克建,孙志华,范丽珺.石器时代:体育运动原始形成期的本质过程及其概念框架[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0(4):95.
[7] 耿业进.从人类劳动方式演进审视体育的发展[D].广州:华南师范大学,2003.
[8] 周伟良.中国武术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10.
[9] 旷文楠.中国武术文化概论[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0.
[10] 旷文楠.体育起源论略[J].四川体育科学,1984(3):13.
[11] 徐祖祥.中国史前时期的南北对峙[J].华夏文化,2007(4):17.
[12] 周军,郭敏.论我国古代战争对体育的促进作用[J].河北体育学院学报,2006(1):81-82.
[1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5.
[14] 熊志冲.从本能的嬉戏到文化的体育——体育起源新论[J].体育与科学,1988,9(4):14-17.
[1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50.
[16] 张洪安.论传统武术套路形成的渊源[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05:14.
[17] 段丽梅,徐健.夏代干戚舞研究[J].河北体育学院学报,2010(6):80-83.
[18] 郭沫若.中国史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The Study on Beginning of Martial Arts during the Prehistoric Period
WANG Zhen1,ZHOU Guang-rui1,ZHANG Ji-he2,WANG Jun-wei2
(1.College of Martial Arts,Shanghai University of Sport,Shanghai 200438,China;2.Postgraduate Department,Shanghai University of Sport,Shanghai 200438,China)
With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view and history and logic analysis,this paper made deep research on the beginning of martial arts during the prehistoric period and concludes that the completion of primitive evolution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ur for hand and foot provide the martial arts an opportunity to sprout;The evolution from instinctive self-protection to the conscious self-protection to self-protection is the martial arts’intrinsic appeal;The breakout of the original wars is the axis force to promote the beginning of martial arts;The martial arts and dance’s“marriage”form of exercise achiev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artial arts.
prehistoric period;martial arts;beginning;evolution;the evolution of consciousness;primitive wars;dance
G852
A
1008-3596(2011)06-0090-04
2011-05-12
上海市第三批重点学科建设资助项目 (S30803)
王 震 (1972-),男,河南鹤壁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武术历史、传统体育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