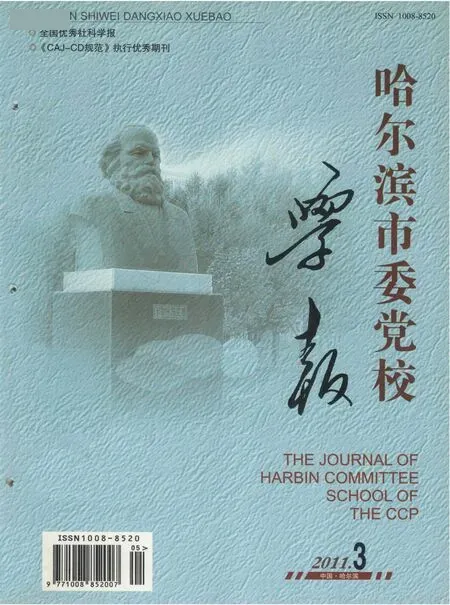《正义论》的基本原则及对我国完善社会制度的启示
郝姝媛
(黑龙江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哈尔滨 150080)
·科社新探·
《正义论》的基本原则及对我国完善社会制度的启示
郝姝媛
(黑龙江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哈尔滨 150080)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中国的社会体制和社会面貌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社会经济的快速增长使中国在国际竞争中的能力和地位有了重大的提升,与此同时,国家也面临着更多挑战,如如何公平分配国民利益以及公民的道德培养等都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罗尔斯的《正义论》,对我国完善社会制度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正义论;基本原则;社会制度
一、罗尔斯《正义论》所阐发的基本原则
约翰·罗尔斯,普林斯顿大学哲学博士,哈佛大学教授,是20世纪英语世界最著名的政治哲学家之一,主要著作有《正义论》、《政治自由主义》、《万民法》等名著。罗尔斯主要研究政治哲学范畴内的正义理论,几乎耗尽毕生的经历偏执于捍卫自由、平等和对弱者的关怀上,却极少涉足政治运动。
《正义论》这本著作是罗尔斯终生思想的围绕点和基础,主要研究的是社会基本机构在分配利益、划分负担方面的正义问题。但罗尔斯于本书中只是在很抽象的层次上探讨社会制度中的正义原则,这种抽象来自于他的探讨范围仅限于一种”法律被严格服从的状况”以及一个“组织良好的社会”。这个社会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相对封闭的社会,社会中的规范被人们大致遵循,人和人之间是一种为了推进共同利益的合作关系并且存在于这样一个组织良好的社会之中。也就是说他的理论所形成的条件是带有一定理想性质的,因而他的理论又被人称为一种“乌托邦”理论。但是,这种“乌托邦”形式的理论不但没有被忽略,反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肯定。
1.第一原则:自由平等原则
当今时代,人民在享受日益丰富的物质文化生活的同时,自由一词开始受到更多的关注和思考。自由,在政治领域内可以解释为:公民依法享有的某些行为不受干涉的权利。这一概念中重点强调的是“依法”。由此可见,自由不但不是为所欲为的行事,而是紧密地同法律和约束联系在一起的。人民在国家中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人身自由、通信自由等权利,都必须在法律界定的范围内才能得以实行。例如,一个城市居民在宗教信仰上选择了基督教,他参与教会活动、购买的相关书籍等行为都是受到法律保护和国家允许的,由于宗教的信仰自由恰恰是源于国家承认或者允许公民对宗教有信仰自由的权利,公民才得以去自由的选择自己的宗教信仰。因此可以说,自由和纪律密不可分,二者缺一不可。如果没有社会“限制”,自由与个性都相对成为虚无;正因为有了社会中法的限制,它们才显的特别美好而具有实在意义。社会限制——或者最好是说社会影响——是人类所拥有真正自由的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它也是人类发展的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1]9。
在《正义论》中,罗尔斯提出的两条正义原则,其中第一条被表述为:每个人对与所有人拥有的充分恰当的、平等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自由平等原则)。按照罗尔斯的理解,如果一个人的自由行为影响了他人的自由程度,或者说一个人在行使自己的自由权利时损害了国家的、集体的、其他公民的利益或者自由权利,这也就造就了一种不平等的社会意境。因此可以说,一个人的自由必然要以另一个人的同等自由的程度为限制。由此我们应该正确地认识到,在社会领域中的自由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为所欲为。罗尔斯总是联系社会制度的规范体系、宪法和法律来谈论自由。这是他的一个理论特点,也是他带给社会体制下人们的自由观念和意识的一种进步。
2.第二原则:机会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
在近现代西方学者眼中,“正义”一词被越来越多地作为一种道德标准来评价社会制度。罗尔斯认为,不同的政治体制、社会条件、出身背景和自然禀赋限制和影响着一个人的生活状况和命运前途,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出身决定命运”[2]60。罗尔斯正义原则的另外一种表述为: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他们:(1)在于正义的储存原则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差别原则);(2)依系于在机会公平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机会的公正平等原则)。即从一般正义观的“呵护每一个人的利益”到两个正义原则最后陈述的“呵护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这是罗尔斯正义论的一个关键[2]60。
“社会基本结构对人们的影响十分深刻、广泛且自始至终,决定着人们的生活前景,决定着人们的最初机会或出发点,这种深刻和重大影响又是个人所无法选择的,故而需要有有关制度的正义原则来进行调整和处理[3]50。罗尔斯的机会公平原则深刻反映出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深刻的不平等问题。人们的自然因素(如天赋)与社会因素(家庭状况),在相当程度上深刻地影响着个人的成长与成功的机会。这种情况我国的当代社会更为明显。事实上,这种不平等也确实是个人无法进行自我选择的。在中国,例如一个出生在富裕的城市中产阶级家庭中的孩子与一个出生在乡村农民家庭中的孩子,从出生伊始,他们所承受的家庭文化熏陶、生活条件和教学质量是没有任何可比性的。大城市中的文化教育水准和条件远比乡村更优越,更多元化;而孩子父母的文化程度以及对世界人生的看法也会深入影响孩子的成长。不同观念下造就的孩子对人生的需求、看法和对未来的选择也不尽相同。于是就注定了这样一种情况,即农村贫困家庭中的孩子所追求的物质和文化更基本,而城市或富裕家庭中的孩子可以不必考虑生活中基本的物质追求而有更高层次的理想。正义原则的目的就是要通过调节社会制度,从全社会的角度来处理这种基础上的不平等,力求做到尽量排除由于社会历史或者自然方面的偶然因素对于人们生活及前途的影响。正义所包含的概念很广泛,例如法律完善、制度健全、提高道德等,并不是一种公平就能涵盖的,但是公平却是正义不可或缺的内涵,这就是正义与公平二者之间的关系。因此,我们要从公平的角度来审视正义,更完善地体现集合正义的内涵。
二、《正义论》对完善我国社会制度的启示
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曾说:“一个社会的改变有三个方面,人心、政令、物质。依这个顺序,开头困难,但终能成功;顺序反过来,看似捷径,但最后走不通。”以人心所向为基本出发点,才能使国家在成熟的道路中少走弯路,相反地,如果一昧只追求经济效率带来的高收益,而忽略了民众作为国家改革的主体性,就只会离共产主义的目标南辕北辙,背道而驰。
1.重视国民的道德培养是促进社会进步的有效途径
对于道德感的重视,是罗尔斯正义理论中非常有特点的一部分。“高尚的道德不可能由国家来规定,单纯地用强制手段来推行,强制或利诱只会使本来高尚的事情改变味道。国家伦理不是国家发展到高级阶段的终极目的,也并不是每个人都要为达到它去创造条件,相反,是它要为个人道德的发展创造条件。”[3]58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生产现代化和经济的飞速发展,我国国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文化生活日益丰富。但同时,也带来一些消极的影响。各地区之间进行激烈的商品贸易竞争,全力以赴发展经济的同时已经很少去顾及国民素质及道德的提高和培养。就在这个以效率、利益为先导的大背景下,一部分国民开始加入了“商品拜物教”的行列,开始走向了的道德缺失的领域,而最终导致了商品的异化。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人性不是固有的也不是普遍相同的,它是随着社会历史发展变化而变化的,它是受历史的规律支配的。社会的大氛围对国民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只有强调执政者的道德,也只有强调道德的执政者即以官员廉洁奉公、忠诚负责,率先成为道德楷模作为前提去感化国民;以国民团结互助、诚信友爱的奉献精神为主体倡导,才能达到一个政治清明、风俗淳美的和谐社会标准。对于国民素质的培养不单是一个文化层面的问题,它更关系到国家未来的发展趋势。社会的当下与未来都与政治体制有着必然的联系:一个国家的国民面貌是由国家的政体决定的,一个国家的发展和进步又与国民的整体面貌和素养有着密切的关联,二者的关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虽然社会制度的制定和执行总是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只会做到公正、平等,而无法达到感情上的慈爱友善,但国家的文化熏陶和道德培养却可以促进公民走向一条自我完善的道路,从而在人人有爱、家家和谐的氛围下取得社会的长足的进步。
2.缩小贫富差距是国家向更高目标发展的必由之路
随着我国逐年将贫困线水平不断提高,贫困线以下人群逐年减少,但是与各地频出的富豪相对而言的贫困现象越来越成为改革开放后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据统计,在2010年,中国仍然有约4 000万左右的人口处于年均收入1 300元以下的状况。资料显示,中国基尼系数已超过了0.4这一警戒线,贫富差距持续扩大会加剧经济及秩序的混乱,激化社会矛盾,不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甚至将影响社会的政治稳定、民族团结和国家安全。
“十二五”规划着重强调了在社会保障和民生问题方面,应提高人均收入,增加市民可支配收入,缩小贫富差距。目前中国的低收入人群及贫困线以下人群作为这种“最少受惠者”恰恰应该成为重点补偿对象,在形成社会利益公平分配的模式时要注重向最少受惠者获得更大利益方面转变。正义虽然不完全等同于公平,但是公平是正义的基础,一个正义的制度并不是仅仅达到平均,但绝对是要以实现公平的目标为出发点,以看似不公平实则公平的模式逐渐取代绝对公平下所带来的不公平现象。罗尔斯的差别原则理论,也强调了对最少受惠者的关切,这是其理论中最具特色的部分。他认为,自己理论的主要力量就在这里。《正义论》中所探讨的自由平等和差别原则,以一种理论的方式提出了一些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在缩小贫富差距方面,一方面在国家政策上要积极培养社会成员的创富意图、鼓励创富方法;另一方面要深切地关心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使他们也能享受到改革开放、经济增长带来的丰富成果;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不断优化养老、医疗保险制度和社会救济制度,在使大家均享有平等的权利和机会的同时,兼顾“最少受惠者的利益”,最终达到消除两极分化。
马克思从生产的角度来分析社会中的正义问题,他主张要实现社会正义要从分配的基础,即生产上来消灭异化劳动,实现人自身的自由和解放,这才是社会的正义之本。罗尔斯的“正义原则”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上的,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调和资本主义制度下日益激化的矛盾。“马克思把社会主义看成是比资本主义社会‘更高级的’社会形式,也是因为社会主义社会更公平更公正。”[1]181在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我们的国家之所以有条件走向更高级的形式,是因为执政者始终在不断坚持改进和完善政治体制,深究我们的社会制度姓“资”还是姓“社”已经没有意义,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地走民主政治的道路,始终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行动的指南,同时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国家就一定会在稳定和谐的氛围中创造更大的辉煌。
[1]肖恩·塞耶斯.马克思主义与人性[M].冯颜利,译.上海:东方出版社,2008.
[2]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3]何怀宏.公平的正义[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
D08
A
1008-8520(2011)03-0058-03
2011-03-10
郝姝媛(1984-),女,黑龙江哈尔滨人,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赵延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