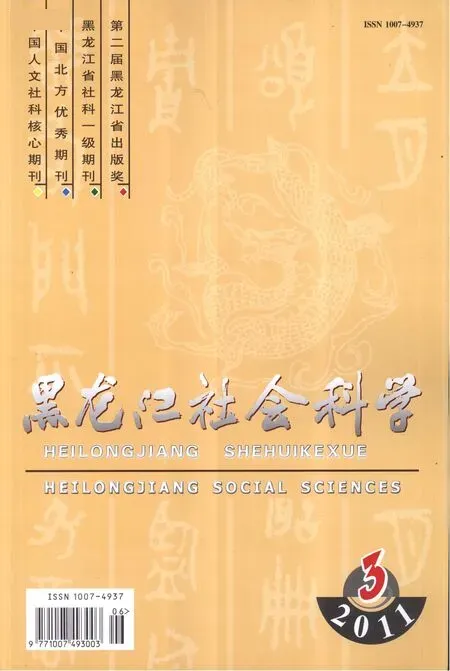从“民族情感论”到“国家利益论”——当代日韩关系新解
隋竹丽
(佳木斯大学,黑龙江 佳木斯 154007)
从“民族情感论”到“国家利益论”
——当代日韩关系新解
隋竹丽
(佳木斯大学,黑龙江 佳木斯 154007)
在冷战体制下,朝鲜半岛是东西方冷战的重要舞台,日韩关系研究历来都是当代东亚区域史研究中的一大热点和难点。《当代日韩关系研究 (1945—1965)》以二战后日韩围绕战争赔款及财产请求权、渔业及日本和韩国有主权争议的水域“李承晚线”、在日韩国人的法律地位等两国之间悬案问题展开的七次会谈为主线,利用日、韩、美新近公布的一手资料,并跨越传统外交史的局限,以东亚区域国际关系史的视角对1945—1965年的日韩关系进行了系统研究。该书不仅弥补了国内日韩关系研究中的不足,也开辟了基于第一手资料研究当代日韩问题的先河。
《当代日韩关系研究》;日韩关系;“民族情感论”;“国家利益论”
在冷战思维下,国内外诸多研究当代日韩关系问题的学者大多从日韩之间长期的侵略与被侵略、压迫与反抗的历史造成的民族感情冲突的角度把握当代日韩关系,但这似乎并不能理性地、正确地认知当代日韩关系的发展变化。我国国内的韩国研究虽然发轫于改革开放之后,但是直到 1992年中韩建交以后才有了较有分量的研究成果问世。综观其研究,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国内大多数学者的研究均基于国外学者研究成果的二手资料,鲜有利用与韩、日、美等国相关的第一手资料进行的研究。
黑龙江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系教授、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安成日博士出版的《当代日韩关系研究 (1945—1965)》(以下简称《安著》)一书,恰恰弥补了国内日韩研究中的这一不足。该著作以二战后日韩围绕战争赔款及财产请求权、渔业及李承晚线、在日韩国人的法律地位等两国之间的悬案问题展开的七次会谈为主线,并以东亚区域国际关系史的视角对 1945年二战结束后到 1965年日韩实现邦交正常化为止的日韩关系进行了系统研究。综观全书有以下几方面特点。
第一,《安著》在研究视角和理论上有新的突破,并提出了新的观点。在国外,有关当代日韩关系研究虽不能说“汗牛充栋”,但也有多部著作问世。不过这些著作多拘泥于“民族情感论”或“美国导演论”,未能深入解析制约或推动当代日韩关系发展的根本动因。如美国学者李庭植、韩国学者李元德、日本学者高崎宗司等,把二战后日韩关系长期处于不睦状态的原因归咎于“对朝鲜殖民统治的认识问题”和“民族感情冲突”。他们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韩迟迟不能顺利解决两国之间的各种悬案,建立邦交的根本原因在于日本拒不承认过去对朝鲜殖民统治的错误,这导致了日韩两国对过去历史认识上的严重对立,两国民族感情发生激烈冲突,导致两国战后处理谈判,久拖不决。这些学者在著述中,对日本在过去朝鲜殖民统治问题上的错误认识,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1]6其学术研究角度,以“认识 (知)论”和民族主义为视角,注重决策者“认识 (知)”对一国对外政策的影响,盯住日韩民族仇恨问题,其研究视角基本停留在 20世纪初期的外交史纬度内[2]100。还有一些学者,如李钟元等力主日韩会谈“美国导演说”,把影响当代日韩关系发展的原因归结为“东西冷战”和美国的“冷战战略”,强调“美国因素”,提出在处理日韩各项悬案以及实现两国邦交正常化的进程中,美国发挥了重要作用[1]6。
《安著》则以国际关系史研究取代传统的外交史研究,主张破除民族主义狭隘的偏见,强调多国档案的对比研究,研究范围由传统的谈判,扩大到国与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层次的往来,并深入外交决策的内层,如决策过程、压力团体等内政外交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2]100。其认为:“冷战”体制是一个大系统,它内部存在东西两个“相互对立两大子系统”,并指出“日韩关系是西方子系统内部次元体之间的双边关系。”同时“从地缘政治上讲,日韩关系是东亚地区邻国之间的关系;从经济发展层次的角度来说,日韩关系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从历史角度来说,日韩关系是殖民国家与被殖民国家的关系。因此,日韩关系既有东亚邻国关系的特点,又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关系的特点和亚洲侵略国家和被侵略国家、殖民国家和被殖民国家关系的特点。这些构成了当代日韩关系的复杂性和特殊性。”[1]23据此,安成日博士摒弃传统外交史研究中的“认识 (知)论”、“民族感情冲突论”、“美国导演论”等,结合日、韩、美等国的大量第一手资料分析,以“国家利益论”阐释了当代日韩关系的发展演变根本动因。《安著》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韩两国之间的各项悬案久拖不决的根本原因,在于“日韩两国在财产请求权问题和渔业问题上的国家利益的根本对立”;同样,20世纪 60年代中期日韩会谈之所以达成协议、建立邦交的根本原因,也在于“两国在‘经济合作’和‘安全保障’方面的国家利益上的相互吸引”[1]6。从而在当代日韩关系研究方面不仅为我们提供新的研究视角,而且实现了理论上的新突破,得出了新的研究结论。
第二,在历史研究的观念上有新的突破。从传统的外交史到国际关系史发展过程,实际上也是实证史学和理性史学的结合和发展过程。二战后,美国外交史研究的演变印证了这种转变过程。二战后,美国的外交史学发展经历了从理想主义到现实主义的国家利益说,再到修正学派、后修正学派的转变。
二战前的以比米斯、格里斯沃德等为代表的理想主义学派强调“人类理性”,主张自由、民主、自决等原则,认为衡量一个国家外交决策正确与否的尺度只能是道德标准和国际法[3]92。二战后兴起的以汉斯·摩尔根索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学派,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认为用传统理想主义所诉诸的“人类理性”远不能说明复杂的国际关系,进而提出“美国的外交行为无须用道德准则和国际公法来规范,而应以是否符合本国的国家利益为尺度做出选择”[3]93。
20世纪 60年代,以威廉斯为代表的“修正学派”(或“新左派”)现代外交史学兴起。“修正学派”反对传统外交史学只描述外交过程的治学风格和方法,也不赞同现实主义学派“只从国际均势和国家利益的角度研究外交史的做法,改从研究国内社会经济入手,探寻美国外交的历史渊源、主流和动力。”但是“修正学派”片面强调经济因素,而忽视其他社会因素对外交作用,不加区分对立的利益集团之间差异及其对外交政策不同影响的做法也招致了各种批判和挑战。
20世纪 70年代之后,对“修正学派”的批评之声逐渐汇集成“后修正学派”。“后修正学派”在外交史研究中总体上强调两点:其一,主张对“外交进行综合研究”。“后修正学派”呼吁“从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国家实力、决策精英、官僚体制、企业集团、社团组织、宗教信仰、思想意识、传播媒介、公众舆论、地理环境等视角对外交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其二,“站在美国之外的世界观察美国的外交”。“后修正学派”还抨击以往外交史学单纯地从国内背景出发“由内向外”地考察外交的方法,“呼吁从外部世界或从国际的宏观舞台来俯瞰美国外交”,主张“美国外交史从美国史的一个分支变为‘国际史’”。“后修正学派”“批评传统史学仅把美国外交作为美国的民族经验的外延来解释,他们认为要考察 X国对 Y国的影响最说明问题的材料应到 Y国去找,因此必须从美国以外国家的历史档案中发掘材料”[3]95-97。
同样,日韩关系也需要“进行综合研究”,要站在“国际史”的角度研究当代日韩关系。《安著》从国家利益入手,以东亚国际关系史的纬度,从日韩两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国家实力、决策精英、官僚体制、企业集团、思想意识、群众心理、传播媒介、公众舆论、地理环境等不同的视角综合考察了当代日韩关系,从而实现了历史研究观念上的新突破。另外,国际关系史的研究,要求作者具有理性历史观念。从民族情感到国际关系史中的国家利益,需要突破民族情感的约束,因此,不仅要资料真实,还要从历史规律的理性角度来认识人和社会,以及认识国际关系,反映出柯林武德所说的:在历史行动者,历史事件之上的历史观念[4]51。这要求叙事者必须把握好宏大叙事结构和细节传神之间的关系。叙事者作为一个客观观察者,确立合适观察点,把握时代精神,通过历史事件和行动者反映历史观念,国外学者称之为“移情”,而对于具有美学底蕴的克罗奇和柯林武德而言,历史是完成人由恶到善的转变,历史女神克丽奥美育的历史,当然不应该凸显民族仇恨。这对于任何一位史学家都是一种挑战。国外日韩关系研究,日、韩学者之所以演绎出“民族情感冲突说”和“美国导演说”,正是这样一种历史观念的缺失。因此,“当代日韩关系”对于安成日这样一个具有韩国血统的历史学者而言,不亚于一场心灵战争。可贵的是,在民族情感的波澜中,安成日奉献给我们的是一部历史理性的日韩关系研究著作。
这并不等于说安成日比国外研究者聪明,而是说他完成了理性智慧的历练。安成日以民族情感入境,以理性史学观念出境,唯此才有了由“民族情感论”到“国家利益论”的国际关系史研究著作。从这个意义上讲,《安著》既是世界史研究的突破,更是作者历史观念上的突破。
第三,细节上为历史行动者以传神写照,凸显历史观念。作为国际关系史的研究,详细列表、考据分析的 Seminar(研究、讨论、提高)是必需的过程。这主要体现在对于资料的运用方面。《安著》大量运用了韩国和日本的各种统计资料,通过数据说话及列表分析,给人一目了然的直观感觉。对于翔实的资料,安成日博士仍审慎地核实,如对日文中的“瓦”,提出了自己的考证[1]28。《安著》在资料的运用方面,除对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档案、回忆录、论著、报刊予以关注外,还对那些不直接相关但是反映了两国政治动态、社会风情、国际国内背景的民情、民意、民风的著作,同样予以了应有的关注[1]6。历史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文本的阐释,语言是把握细节的第一关。许多历史思想、观念往往蕴涵在本民族凝练的语言中,决策者的会意传神的语言尽显其思想、观念,如吉田茂鼓励池田勇人改善日韩关系的“勇往直前”,经作者注释方知实为一语双关[1]283,读后释然一笑。这当然取决于作者精通日语和韩语的功底。实际上,安成日潜心日本研究二十余年,悉观日韩民俗,始能做到细节上为行动者传神写照。
《安著》谈到“李承晚的下台”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时,则用“李承晚是权欲极其强烈的男人”的寥寥数语,勾画出了李承晚的性格、品行,如见真人,也说明了事件的本质[1]241。对学生运动,反对李承晚选举舞弊谋求第四届连任的游行示威,则情深义重[1]243,反映了社情民意。对于朴正熙军事政变美国导演说,直言没有资料,证据不足,存此一说[1]280。另外,通过对著书宣称“日本侵略战争是‘圣战’”的日本外相椎悦三郎,在韩国机场上临时写上“道歉语”的这一“灵活外交”典型细节的把握,把日本外相的随机应变能力和日本对韩外交的本质跃然纸上[1]346。《安著》还分析了韩国在野党最终妥协的原因称:“中国连续举行了两次核试验,越战爆发等紧张的远东局势下,韩国有被孤立的担忧。”[1]363一语道出了民族情感与国家利益的心灵之战。还有对于不同社会的反响,中国和朝鲜的否定声明,其也一一加以记述[1]360。
总之,通过对日韩七次会谈中典型细节的分析,《安著》从政治、经济、文化各层面论证了国家利益对于决策者的影响,反映了各种利益阶层与决策者之间的压力互动,为我们理性认识资本主义世界的自由、平等提供了难得的历史范本。作为一部开拓性的研究著作,《安著》以国家利益论重新审视了当代日韩关系,但其研究实证分析有余,最后的理性展开却略显不足,读来使人有言犹未尽的感觉。
当代日韩关系的研究,折射了人类历史所遇到的共同问题:民族、战争、仇恨、邦交。《安著》在研究视角和理论以及历史观念上已经有了超越,主张不能只盯住民族仇恨。在分析日本对朝鲜半岛殖民统治的认识问题和日韩邦交正常化的问题时认为,日本“否定侵略”、“美化殖民统治”的态度和立场曾经对日韩会谈和日韩关系的发展产生了不良影响。尽管如此,在实现日韩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日韩双方在现实国家利益的诱惑下,搁置日韩在殖民统治认识问题上的争议,实现了邦交正常化[1]375。这里,“诱惑”一词不确,如果改成“做出了理性的历史选择”则更符合民族理性,更符合不能只盯住民族仇恨的国际关系史研究。人类历史上的这种情感,每个民族都有,只有着眼未来,才能避免盯住仇恨不放。这种情感的超越,就是人类伟大的理性。《安著》对此有哲学概括,“日韩关系的正常化,说明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思想认识和意识形态上的对立的国家,为实现各自更加现实的,更加重要的国家利益是有可能超越思想认识和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就某些问题达成妥协的”[1]6。
笔者认为,《安著》提出的日韩两国“思想认识和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可能是从广义上而言的。自1910年韩国被日本吞并,就两国在人权、主权、侵略与被侵略、殖民与被殖民的社会地位而言,它们的认识和情感是对立的。但是,就 1945—1965年而言,笔者认为日韩之间狭义上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价值观念等并不存在根本对立。因为它们同属于一种政治阵营,政体上一个是君主立宪的内阁制、一个是总统制;它们同属于美国自由观念的国家,对立的是对过去的历史认识和民族情感。日韩之所以能超越历史认识和民族情感的对立,实现日韩关系的正常化,是民族情感向民族理性的回归,执政者以国家利益为重做出理性的历史选择的结果。至于思想认识和意识形态上的对立,笔者认为应该是中美、东西两大阵营等之间的事情。对于中美而言,超越思想认识和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建立邦交,同样是执政者以国家利益为重的历史选择。因此,从民族情感到国家利益实质是民族理性的体现。
[1] 安成日.当代日韩关系研究 (1945—1965)[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2] 唐启华.“北洋外交”研究评介 [J].历史研究,2004,(1).
[3] 王玮.美国史学对 19、20世纪之交美国海外扩张的思考与认识[J].史学理论研究,2004,(2).
[4] 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D7
A
1007-4937(2011)03-0118-03
2011-02-12
隋竹丽 (1965-),女,山东文登人,副教授,从事古希腊、古罗马历史文化研究。
王雅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