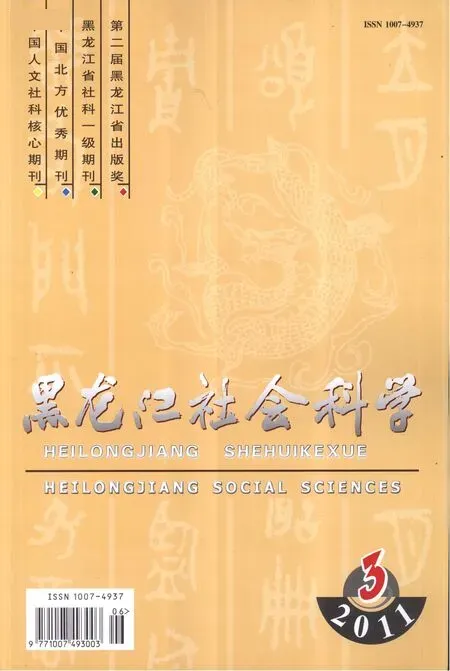消费文化时代的文学理想重构
范玉刚
(中共中央党校文史部,北京 100091)
消费文化时代的文学理想重构
范玉刚
(中共中央党校文史部,北京 100091)
消费文化时代文学理想的危机,其实是人的危机。文学理想赋予作品以生命而使作品有了“精神”。文学理想离不开正面价值的贞立,离不开对真善美的追求,离不开对人生“至善”的价值祈向。这种祈向应成为走在文化复兴途中的创作者的自觉!文学理想的重构要向经典美学寻求资源,以获得美的理想的烛照和审美表达的润泽。真正的文学是在对时代深刻感悟和对生活深厚积淀中从内心深处流出的文字,而不是凭借多少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技巧”弄出一些无病呻吟的技术性码字。
消费文化时代;文学理想;美;价值祈向;审美表达
文学理想缺失的时代
一个时期以来,各种“终结论”盛行,“艺术的终结”、“文学的终结”、“美学的终结”、“人的终结”、“意识形态的终结”、“历史的终结”等等,甚嚣尘上,如果人不存在了,文学终结了,还有文学理想可谈吗?这是一个理想缺失的时代。英国左派理论家伊格尔顿更是在《理论之后》宣布“理论的终结”,意在警醒人们要对后现代理论的局限性有所反思,风靡一时全球理论旅行的“文化理论”不能终结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也就是说,在多元文化景观中,现代性的诉求依旧有效,崇高、理想、审美依然是当下生活要切近的语汇,“宏大叙事”在后现代景观中依然存在,这不仅显现于北京奥运会的宏大场景,也显现于上海世博会的空间设计和对审美现代性的诉求。理想的缺失不意味着不需要理想,不意味着文学不再书写理想,恰是在缺失理想的消费时代,文学理想显得弥足珍贵。
如果文学消亡了,谈文学理想和审美表达还有意义吗?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是尴尬的。现在有学者开始谈论“后文学时代的来临”,未来的文学家靠电子书写、数字化操作生产文学。超级电脑的研发和广泛应用,人是否会变成傻瓜?书面文字和纸版印刷的消亡是否就是人类文化进步的表征?似乎每一次介质的更新都给既有的文学和文化存在以极大的冲击,都给人们带来恐慌和新鲜体验。对于这种技术进步带来的深刻变化,我们如何有效应对?只要人不消亡 (非肉体上的),文学就不会死。但问题依旧存在,文字是单纯的介质吗?若是,图像不是更有视觉冲击、感官刺激和审美意味吗?那还何来恐慌?其实,我们看到网络电子视像在深刻地改写文学发展格局的同时,带来的不单是文学的分层、分化和文化化,人们感受到的是精神深度的平面化和文学理想的消逝。在视像流行的时代,另一股潜流在生长,那就是本真的文学的回归,分化给文学回归自身守护审美理想提供了机遇和空间,一种回归自身的张扬文学理想的文学正在生成。在大众文化的流行中,既播撒了文学理想和审美泛化的碎片,在娱乐化中慰藉身心疲惫的大众;同时,在小众的传播中依然守护着文学理想和审美意蕴,希冀着文学力量的生成,期望文学语言重新对图像发起冲击!
固然大师的时代一去难返,文学作为聚焦社会中心的时刻也成为历史记忆,但文学在卸掉试图干预社会现实而奔走呼号的外在重负时,也放逐了理想,这才有近年来不断关于“当代文学价值”的论争。我们不回避文学在回归自身的文字叙述技巧上的愈益成熟,但也深刻感受到文学在玩转花样翻新中的空洞沉沦。当下很多文学犹如韩少功先生在《小说选刊》2004年第一期中的不屑:第一,没有信息,或者说信息重复。吃喝拉撒,衣食住行,鸡零狗碎,家长里短,再加点男盗女娼,一百零一个贪官还是贪官,一百零一次调情还是调情,无非就是这些玩意儿。第二,信息低劣,信息毒化,可以说是“叙事的失禁”。很多小说成了精神上的随地大小便,成了恶俗思想和情绪的垃圾场。这不单是文学的现实,也是社会的一种普遍心态,而文学之为文学不是描摹生活的“原生态”,而是有所警醒和鞭策;不是与生活同流合污或“合谋”,以捞取一杯羹,而是以理想烛照现实的不足,给生活以温暖和亮色。文学的不作为和漠视这种心态蔓延,才是文学最大的危机。危而及之的是精神上的侏儒化和庸俗化,行为上的低俗化和恶俗化,道德上的乡愿化和无谓化,这不但是很多国人的精神现状,也是很多知识生产者、文化工作者的精神写照,普遍的冷漠和自我放逐严重侵蚀了社会主流价值的肌体,在集体的逃避和无力承担中使之变得千疮百孔,而无力烛照社会。思想的滑坡、浅薄和文艺审美表达能力的同步下滑,造成作品精神深度的缺失和粗鄙产品的流行,看似文化繁荣、景观炫目,实则经典阙如,精品如沙下之珠。
文学守护的价值一再退却,甚至到了无“线”可守的边缘。“理想主义”的一度盛行是否耗尽了当下的资源和动力,以至于人们耻于谈“理想”?还是我们得了矮化症或萎缩症而撑不起“理想”的骨架?哪里是文学理想远遁的足迹?失去了对未来的想象和文学的激情,文学将何以堪?海德格尔以思之强力洞察到,存在的被遗忘,理想的丧失,是时代精神的沉沦,是诸神不在的夜半的贫乏时代。当下流行的是功利主义,看重的是文学的产业化运作和市场效应,经济维度成了评价作品是否成功的有效尺度。文学批评也是顺着市场逻辑,变成快餐式的新闻媒体批评,一同随着文学沉沦。
这个时代凸显的是人的“肉身”狂欢,情色文学、玄幻小说、穿越、盗墓古装戏吸引眼球,低幼化阅读、浅阅读成为时尚,甚至是全媒体时代“数字身体”的喧嚣。理想生成的土壤正在沙化,理想的根荄正被置于荒凉的暗夜。这是把整个社会的文化品位和审美趣味往下坠,是无聊的噱头在招摇,人被降到“物”,或者动物性的本能层次,属人的品质、品格就越来越少。身体不仅成为“交换”的筹码和潜规则的“道具”,也成为对抗审美心理和衡量艺术的法器,这是文艺的悲哀,更是对民族未来的戕害!这与我们五千年悠久的历史不匹配,与在世界上的经济大国地位不匹配,与在社会上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初衷不匹配。
文学是民族良心的承载者,是民族文化理想的传播者,怎能缺失理想之维?文学要高扬理想就必须关注人生的价值、生活的意义,要有心灵的眷注,而不是身体的贪欢。遗憾的是,当下大多数文学作品在人性探寻上往往浅尝辄止,灵魂的刻画很肤浅。马克思曾指出人的感觉成为人的,而非止于本能层面的饮食男女——当下的某些文学恰恰追逐的是感官欲望的刺激,流行的是身体写作、私人写作、美女作家和口水诗、梨花体,渲染穿越和盗墓的玄幻文学,有着情色萌动的青春文学。嬉戏于人性的肤浅,缺失灵魂映照的深刻性,表征着当下的文学创作缺少走向经典化的冲动,固然有着各种奖的激励与鞭策。但真正能进入火热的生活、又能有所超越和有着人生价值祈向的人物形象,少之又少。注重人的感性不是引向“下半身写作”,去张扬人的感官欲望和趋向动物本能。被现实五彩缤纷之相迷失双眼的作家,对人的理解不是肤浅、片面化、抽象化、理论化,就是太近于写实而缺乏超越性和理想化,而难以企及时代精神。正是因为马克思注重人的感性活动,没有把人抽象化,他才在 1859年给拉萨尔的信中提出“你就得更加莎士比亚化,而我认为,你的最大缺点就是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这要求文学在贴近生活实际中展示出人性的丰富,刻画出人的本质。
文学眼光的缺失,是时代的问题?还是文学的问题?伟大的文学、伟大的作家都不可缺失理想的维度,都有一种“至善”的境界祈向,这祈向是一种向上的力量,这力量引导文学去发掘人性的光辉和高扬理想主义旗帜!对生活中阳光的讴歌、对人生幽暗的同情,甚至日常生活中淡淡的忧伤,都蕴含着文学理想的种子。海明威对人生勇气的肯定,茨威格对人物内心美好力量的追求,罗曼·罗兰、高尔基等对人类崇高理想的高扬,鲁迅对人性灵魂的拷问,女作家萧红对故乡呼兰河深沉的爱,史铁生创作的顽强和不妥协,迟子建对寻常故事伦理情怀的执著,还有张承志、张炜对“道德理想主义”的赞颂!这些都是文学的力量和生活的暖色,是文学中的清朗刚健之气。鲁迅先生在杂文《论睁了眼看》中说:“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后现代的平面价值观解构深度和消解理想,现代主义则过度专注于人的阴暗心理和灰色人生,在文学技巧上玩花样。何谓文学需要当头棒喝!文学对理想的守护是本然的希冀,并非什么外在的点缀。请给文学以自尊,她会给行走在暗夜的人以光亮,在其内蕴的理想指引下穿越黑暗,走向光明。甚至在多年以后的记忆中,会深刻感受到文学的温情,给人以勇气和力量。文学理想离不开正面价值的贞立,离不开对真善美的追求,离不开对人生“至善”的价值祈向。文学过于娱乐化吸引眼球,追逐利润,必然会迎合低级趣味、矮化英雄、嘲弄经典,这就是当下流行的“大话文学”、“恶搞文学”生成的语境,缺失理想主义的烛照,文学还有精气神吗?其实,真正打动人心的是精神的温度,是灵魂的震撼!自上世纪 9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文学总体上已成萎靡之相,大多流露出的是失望、无聊、琐屑,甚至是颓废和阴暗,其格调和趣味多是病态的,始终缺失一种“应当的”文学伦理维度。在身体欲望泛滥、扮饰美的流行中,高扬文学理想并不是一件多余的事。
文学理想重构的美学底蕴
对于当下的文学状况,唯有经典才能纠偏鄙俗之气,才能荡开文学思维的板结化,才能缝合文学话语的碎片化,才能重整文学的山河,注入审美之力才能使文学强身健体,给粗糙的文学以审美表达。此处所谓经典不单指文学经典,还包括学术经典。有经典的民族,才是文化成熟和文化自觉的民族,才是弘扬理想和产生英雄的民族。这样的民族才会用文学滋润心灵、提升境界。正是在此意义上,文学理想的重构要向经典美学寻求资源。
在精神的王国中,文学很难用进步来评说,它自有其高蹈的意识,文学写作当然离不开感官的调动和参与,但绝不是用身体写作,而是心灵的诉求与主导,它指向的是一种应当的价值。“随着我们的科学和艺术进于完善,我们的灵魂败坏了”,“我们已经看到美德随着科学和艺术的光芒在我们的地平线上升起而逝去”,卢梭曲尽心曲的申说,意在以理性反显良心,他诉诸的是心灵的眷注。卢梭的良心是对本能的超越,不委落于利害得失的判断,只是作为一种美好的情致把人引向道德的高尚,为时代的文艺树立应当的维度。而在康德,“真正的崇高只能在评判者的心情里寻找,不是在自然对象里。对于自然对象的评判引起了对于它的情调”[1]95。他寄希望的不是外物——哪怕再大的“客观属性”,而是那端直纳入直观中的外物时的一种内心的情调。情调、美、道德律,在康德“美才能被当作道德秩序的象征,而这是他的使心灵‘意识到自己的某种高贵化和超升于感官印象愉快的单纯感受性之上’的能力的真正源泉。”[2]唯此,审美趣味才能在更大的理性系统中发挥作用。康德在论析“美的理想”时说,最高的范本,鉴赏的原型,只是一个观念,这必须每人在自己的内心里产生出来,而一切鉴赏的对象、一切鉴赏判断范例以及每个人的鉴赏,都必须依照着它来评定。观念本来意味着一个理性概念,而理想本来意味着一个符合观念的个体的表象[1]70。所谓“审美观念”,也就是生自每个人内心的审美理想,它来自人的心灵和想象。这理想作为圆满意义上的美,为有着“共通感”的每个人的心灵凭着想象力塑造出来,故而落在“主观的”维度上。但在对审美和道德判断的反省中,可直观的“美”在“使人愉快并提出人人同意的要求”和“超越着单纯对于感官印象的愉快感受”方面表现的精神性状可以向着“道德”作一种“类比”,故而,“美”由主观而客观,乃源自判断力的情感机能向理性的欲求机能的“转译”,由于这“转译”,道德欲求被象征式地直观,从而显现出一种直抵人心的力量。就理想生成而言,文学是这“转译”的方式,通过文学的审美表达可以感受到美的力量。文学也因理想的守护而位于精神的高格,依照“范本”“原型”美的艺术从作为理想的审美观念那里汲取灵感,创造出使自然的美的形式相形见绌的美,尽管它并不是——也不可能是——审美理想的全然实现,但它借着审美表达已全力逼近审美理想。这就是文学何以要高于现实,高扬文学理想的用意,正是文学理想赋予作品以生命而使作品有了“灵魂”。这灵魂作为审美理想“必须每人在自己的内心里产生出来”,却又不是每个经验的个人都可以使这应当的“必须”成为现实的“能够”。只有天才人物才能在自己的内心里生出这审美观念或“灵魂”,并把它表现出来,且一旦被表现出来总会作为一种审美的公意或迟或早地获得认可。审美理想须通过审美表达即想象力的自由显现,成就文学艺术作品。“没有自由就没有美的艺术,甚至于不可能有对于它正确评判的鉴赏”[1]203-204。作为审美理想永难企及的“原型”——“最高的范本”是一种虚灵的真实,恰恰构成文学理想的底蕴,它作为心灵的内在之光烛照人们借着既有范例创造又一个范例,这实际上就构成文学史上的经典序列。
对于如何实现审美理想与审美表达的统一,黑格尔指出,所谓“美”的要素可分为两重:一重是内在的意蕴,一重是外在的形状。他把意蕴或内容称作内在要素,把形状或表现形式称作外在要素,强调二者在艺术品中的“相互融贯”。“美”这个概念里有两重因素:首先是一种内容、目的、意蕴;其次是表现,即这种内容的现象与实在——第三,这两方面是互相融贯的,外在的特殊的因素只显现为内在因素的表现[3]12。“美就是理念的感性显现”,是黑格尔对“美”的界定。所谓“理想就是从一大堆个别偶然的东西之中所拣回来的现实,因为内在因素 (心灵或灵魂)在这种与抽象普遍形象对立的外在形象里显现为活的个性”[3]201。而理想美的生成“就在于所要表现的那种心灵性的基本意蕴 (即美的理念)是通过外在现象的一切个别方面完全体现出来的,例如仪表、姿势、运动、面貌、四肢形状等等,无一不渗透这种意蕴,不剩下丝毫空洞的无意义的东西”[3]221。真正艺术作品的生成,其现实性的契机在于艺术家的创造活动即审美表达。在最高意义上,美的艺术、美的理想与真理相通,是心灵的最深广的真理的一种方式。艺术之成为艺术就在于心灵灌注给它的生气,心灵不仅能把它的内在生活纳入艺术作品,它还能使纳入艺术作品的东西,作为一种外在事物,能具有永久性 (形式美)。也就是说,文学理想的重构必须经由作家心灵的催发,通过对心灵的涵养焕发出一种超越性力量,穿越现实的迷雾,又深刻解读现实,在审美理想与审美表达的统一中成全一部完美的艺术作品。譬如,《浮士德》作为德意志民族寻求光明和力量的“集体无意识”,全然相契于歌德的人生祈向,不仅彰显出人性理想的光辉和普遍性的意义,还创造出与之相契合的完美形式。他说:“希腊人的理想和追求是把人神性化,而不是把神人性化。那是神本主义,而非人本主义!”[4]歌德的话语,给我们以深刻启迪。同样,席勒的美学思想和创作也给人以启发,诚如黑格尔所言:“席勒在表达情致时,就把他的整个灵魂而且是伟大的灵魂摆进去,这种灵魂对于事物的本质能体验入微,而且能尽量用丰富而和谐的语言自由地光彩焕发地把事物本质的深微处表现出来。”[3]368唯此,他高度赞扬席勒塑造的那些道德高尚的理想化人物。可见,文学理想重构的底蕴是对美的诉求和应当的价值祈向。
重构文学理想关乎对人的理解,当下消费时代文学理想的危机,其实是人学的危机,文学作为乌托邦的守护神,其功用在于为人类建构良好的人性基础,弘扬人的尊严。人的尊严就是文学的尊严,文学要正视人,守护人的理想。但它守护的不是人的自然属性,而是人的超自然的人文社会属性。人是谁?马克思所理解的“人”是“现实中的人”,是特定历史语境下社会存在的人,它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对其内涵的理解,要回到马克思的原初视野中去领会。马克思批判了费尔巴哈对人的抽象的自然人性论的理解,使之回到历史的社会的进程中看一般的人性,马克思视野中的人是自然性与社会性、个人与社会相统一的人,其普遍的人性是指自然性与社会性、个体性与社会性的统一,与费尔巴哈所说的作为“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的普遍人性有着本质的区别。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进一步提出“内在尺度”和“人按照美的规律来造型”的理论。基于人的实践性活动,提出只有人,只有有意识的、自由对待自己的生产活动和产品的人,才能按照美的规律造型,进行美的创造,这就在美学史上首次将审美和美的规律奠基于人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即实践活动上,为美学、文艺学理论确立了实践存在论的基础。“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本质”[5],才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的本意,这是对人的异化的扬弃和对人的完整性的肯定。
大众文化时代文学理想何为
当下文学生产中的低俗和恶俗创作不但颠覆了文学的审美特性,而且向文学提升人生境界、塑造美好心灵、构筑人性家园的本性发起挑战,试图把无限扩张感官欲望的文艺现象美化为“回归”美学的感性学本义。这既是对美学的扭曲,也是对文学理想的践踏。回顾中外文学史,文学的理想主义情怀始终是其底蕴,不但浪漫主义文学闪耀着理想的光辉,即使批判现实主义在对现实的深情拥抱中,也从未丧失理想的高蹈,全然不是当下丧失价值追求的无聊。不经意间,似乎也是不期然,当下的某些文学越来越迷恋于生活的表象,迷恋于“物”,迷恋于“下半身”,迷恋于丛林法则,张扬着无耻并为无耻辩护,决然地从本应关注的城乡之别、底层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冷漠地转开眼去,为新兴的中产阶级鼓与呼,全然没有了深刻的思考和道德的关怀。
随着文学理想的失落和文学的碎片化,我们似乎到处遭遇文学,可我们却越来越缺失文学,有的只是文学性的话语和修辞。面对文学的危机,文学要重拾信心和理想,并以美好的情致表达理想,重构一个纯净的文学世界。今天重构文学理想,不是让个体在大话语的空洞中淹没个性,让血肉丰满的个体充当时代精神的传声筒;也不是让作家沉浸在自我情史的喃喃自语中,更不是陷入阴暗的钩心斗角中难得透视阳光的罅隙。而是在“大我”的豪迈旷达与“小我”的真挚高尚中塑造出不负时代的人物形象,在历史理性与人文价值的张力场中书写时代的真实,既可触动心底的微澜,也可凸显出时代的波澜壮阔。这其实就是有着人间情怀和道德情怀与终极关怀的文学理想的自觉,有着脱俗的审美表达的创作者的自觉。
就文学之为文学而言,应该说文学最不缺的就是理想,应该说这是文学与生俱来的要素,现在却成了写文章鼓与呼的话题,可见文学的当下境遇和时代的境况。高扬文学理想的维度,不是说文学不食人间烟火,恰恰相反,而是要求文学更加关注人生的真实境遇,关注人间的苦难和悲欢离合,关注人间的阳光和情感的美好,即关注“现实中的人”——马克思经典作家视野中的“人”。在大众文化流行并作为主要消费对象的时代,文学和文学研究不能再回到僵化的一体化时代去塑造人物的高大全,更不能企望精雕细琢的八亿人看八部样板戏的文化沙化时代;也不会重现上世纪 80年代文化热、美学热氛围中的文学胜景,以及文学主体性、审美自律性主导研究范式的时代;而是在消费时代,在文化景观此起彼伏的换场中为文学守护一方净土,在回归自身的完整性中守护文学理想,而不是在碎片化中成为景观的点缀;在多元文化的合唱中,为大众提供更多的文艺欣赏和消费的机会;在文学形态多样化中,为心仪文学、敬畏文学的人留下时代精品,毋忘文学走向经典的使命。这需要文学、作者、读者、社会文化环境的多方契合,尤其在浅阅读的电子时代,文学理想需要培育,大众的审美趣味需要引导。随着文化市场的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主要矛盾并非文化产品的短缺,而是一元和多元之间的关系,就文学而言,是如何引导文学发展和提升的问题。其中文学理想的价值祈向和重构,应该成为走在文化复兴途中的创作者的自觉。
今年秘鲁作家略萨获诺贝尔文学奖,其颁奖辞是:略萨对权力结构进行了细致的描绘,对个人的抵抗、反抗和失败给予了犀利的叙述。略萨自己说:“我是作家,同时也是公民。在拉丁美洲,许多基本的问题如公民自由、宽容、多元化的共处等都未得到解决。要拉丁美洲的作家忽略生活里的政治,根本不可能。”“作家有义务介入公共事务”,这不只是略萨的文学口号,也是他的文学行为。正是这行动证实了文学的精神力量,坚信文学需要信仰,对文学的坚定信念,是文学的持久动力。介入社会,介入现实,是文学的使命,文学说到底是一种精神形式的社会实践。作家对现实事务是否有热情、有勇气、有理想,直接影响着文学的成败。略萨的成功在于保持了一种文学的批判精神和社会关怀,其作品有着理想主义的信念和维度,从中展示出以“小我”拥抱“大我”的民族良心和社会良知。这契合了当年的福克纳的诺贝尔获奖感言:“今天从事写作的男女青年已经忘记了人类内心的挣扎。然而只有这一主题才能成就好作品,因为唯有它值得写、值得为之付出艰辛和汗水。”“这些永恒的主题是:爱、荣誉、怜悯、自尊、同情与牺牲精神等。如果缺乏这些,任何小说都只能昙花一现,注定要失败。”“人类不朽不是因为在万物中唯有人拥有永不消逝的声音,而是因为人有灵魂,有同情心、有牺牲奉献和坚韧忍耐的精神。诗人和作家的责任就是把这些写出来。升华人类的心灵,唤醒人类曾经引以为荣的勇气、荣誉、希望、自尊、同情、怜悯与奉献精神,从而使人类真正永生,这正是诗人和作家的殊荣。”这些带着文学理想的声音至今振聋发聩。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学固然不必全力去拼杀、呐喊,但要在对消极自由的守护中学会“拒绝”和“抗争”,拒绝媚俗,抗争无耻。以文学的审美表达展示出文学的美好!在消费文化时代,当代文艺学既应回答“文学是什么”,又应回答“好文学是什么”,并阐释清楚“文学”与“好文学”的价值关系。真正的文学是在对时代深刻感悟和对生活深厚积淀中从内心深处流出的文字,而不是凭借多少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技巧”弄出一些无病呻吟的技术性码字。讲究审美表达,就是要真诚,不虚伪不做作,把人类的情感、人生的体悟和美好的追求熔铸到文字中,以文学的笔调和情致,塑造“有意味的形式”,而不是在作品中曝粗口、下流和歇斯底里般的啼哭,文学形式要给人以美感,而不是粗俗、刺目!
当下,电影作为文学叙事、高扬文学理想的主要方式之一,往往成为受众消费最多的文本。电影《山楂树之恋》作为一部文艺片,它通过电影的语言、形式和手法讲述了一个“纯粹”的爱情故事。如若细读文本,则会发现文学理想与审美表达之间并未充分交融。故事中的人物并未真正走进历史,融入现实,融入时代。影片固然堆积了特定时代的文化符号,但这些历史标志只是浮在地表上的点缀,尚未构成人物生活的真实环境,未能渗入故事的肌理层面。使人难以体会到特定文化环境在人物心灵上的激荡、压抑与折射,似乎一切都是“拼凑”。影片固然有着唯美的诉求,但因缺乏深刻的内涵支撑,人物形象与时代精神产生隔膜,夺目的是空洞的能指的喧哗。文学理想只有浸入时代意识与人物的心灵和肉体,才能成为有效的思想力量,才能在历史与美学的统一中使能指与所指之间保持审美的张力。电影有意识地使故事过于“纯净”,而降解了“理想”的高度与内涵的丰富性,缺失了历史的深度与现实的力度,虽然在电影技巧表达上、细节上有一些追求,催人泪下,但二者无疑是分裂的而非相融的。与之不同,电影《康定情歌》把文学理想融入历史的厚重中,高扬了李苏杰与达娃心中怀着的信念,他们以各自的方式用一生时间守护自己的承诺,信守承诺就是他们人生的理想和革命激情。电影的叙述方式和所展现的时代场景,虽然有些单薄,但与故事所烘托的理想信念相契合,成为影片打动观众的力量所在。可见,文学理想是人类心灵的寄托,是人类心底的光荣与梦想,是身处困厄逆境永不丧失的信念。理想经由文艺的审美表达焕发出抗争苦难的勇气,摆脱内心的焦虑,展示灵魂的自由从容,给人以确证生命价值的光源,从而值得一代又一代文学艺术家去守护,去执著地追求。在文学理想的烛照下,让我们珍惜文字,回到经典阅读的朗朗书声和豁然开朗的会心微笑中,守护穿越浮躁的灵府中那不息的诗意!
[1] 康德 .判断力批判:上卷[M].宗白华,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2] 门罗·C·比厄斯利 .西方美学简史 [M].高建平,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98.
[3] 黑格尔 .美学:第 1卷 [M].朱光潜,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4] 歌德 .歌德文集:第 10卷 [M].范大灿,等,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202.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23.
J1
A
1007-4937(2011)03-0072-05
2011-02-20
范玉刚 (1969-),男,山东临邑人,教授,从事文艺学、美学与文化研究。
李 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