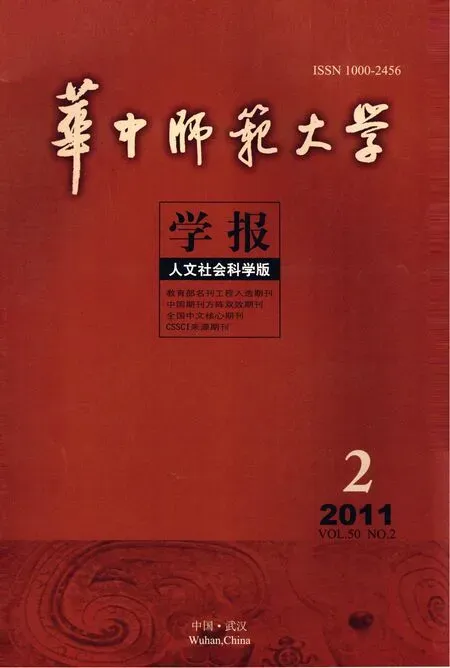甲午战前士大夫的“革新”意识探析
申祖胜
(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院哲学系,北京102488)
甲午战前士大夫的“革新”意识探析
申祖胜
(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院哲学系,北京102488)
在晚清士大夫的对外观念中,经济、政治、文化是三个最受关注与重视的方面,他们由于受到日本等外来影响,在这三个方面都显现出一些看似偏离传统的言论倾向来。但事实上,他们既保守着传统的士大夫身份未曾改变,而在社会大变动局势下的文化心理及其种种事功也未能超出传统的藩篱。外患的加剧固然是加重了他们的忧患意识,促使他们急切地寻求一条强国富民之路,但是士大夫精英们在此形势下的思想并未能超脱出历代王朝变革意识层面之外,他们的社会变革意识依然不过是传统的翻版,并未能做到与近代接轨,真正的近代式变革思想要等到甲午战争以后方才出现。
甲午战前;对外观;士大夫;革新意识;传统
一 、绪论
关于甲午战前士大夫精英阶层的对外观,学界已有了相当研究①,然而却大都停留在简单的分类介绍上,并未对其社会变革意识的性质分属进行深入的研究。本文试图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分析士大夫精英们的社会革新意识,以期说明晚清社会变革一直未能有实质进展的深层次原因。以往的研究一般认为晚清改良派思想家如郑观应的商战思想已经属于资本主义范畴的经济思想②,本文则认为他们这些思想依然不过是传统形式的现代翻版,其传统实质并没有发生改变,他们虽然在经济政治等层面表现出了一些偏离传统的倾向来,但在根本信仰上则并未有所新变化。他们的社会革新意识实质上是继承历来王朝危机时刻所做的自我革新。甲午战前的中国虽处于世界大变革时期,却未能实现同近代意识接轨。其间深层原因即是本文试图要探讨的。
二 、经济、政治层面下的士大夫变革意识
儒教中国的传统经济思想并不拒绝人们对物质的追求,相反,国民的富足才是施政治民的关键所在,正如《管子·治国》所谓:“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
《孟子·梁惠王上》谓:“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於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只是物质的满足必定是有一个限度的,因为生命的追求在物质之上尚有道德。儒家传统教导人们要求以礼来节制欲望,故《荀子·礼论》谓:“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於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儒家的义利之辩很大程度上着眼处,不是片面的否定利而要求义,而主要反对的是对个人私利的追求,并不是任何层面的“利”都一概否定。中国古代信奉着“贫而乐,富而好礼”,礼的着眼处是“和”的境界,即政平人和,在儒教中国的传统社会,经济和政治、文化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为人生”的道德理想追求使得“德”成为儒家信众们永恒的持守。
古代中国一直重视发展经济,并处处以“民生”为外在事功的施定基准,儒家士大夫激烈的反对苛敛,无论是来自官府的还是私人的。商业之不受重视,也多是因为在儒家士人们眼中,它属于末技枝流,只会引起社会的奢靡,造成浮华的风尚。在一个社会经济普遍低下的传统社会,人生的满足主要靠的是减低欲望,节制需求。商人们常被看作是不劳而获,只是在商品转运买卖中聚敛财富。他们浮奢的作风使他们始终被正统士大夫们拒绝于官场之外。
爱民施仁是立国的根本,《孟子·离娄上》谓:“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
正因为此“民为邦本”的思想意识,因而经济的发展要一切以“民生”为根据,政治国家的运行也要以“民生”为根本。《大学》谓:“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中国传统的经济体制奉行的是“藏富于民”,传统政治体制奉行的则是“以民为本”。
基于此点我们就可以来重新审视晚清士大夫精英们的经济政治革新意识了。
在近代世界,中、日同遭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但日本却能抓住时机,并极具战略眼光的仿效了西方,得以迅速崛起,这渐渐吸引了一批精英士大夫对它的关注。晚清士大夫的对日观经由了从轻视到师法,其间的评判得失标准一直是传统的“民生”标准,未曾有新的改变。以是否有助于“民生”作变法革新优劣的评判基准,很能说明晚清士大夫精英们在此层面并未具有近代社会的变革意识。
日本在1880年以前,外贸有大量逆差,金银不断外流。这让对日本开始关注的中国士大夫不断增加对日本明治维新成效的怀疑,这种状况极大影响了士大夫的对日观。
曾任江西吉安府莲花厅同知的李莜圃指责日本维新改革后“非但不能拒绝远人,且极力效用西法,国日以贫,聚敛苛急,民复讴思德川氏之深仁厚泽矣。”③除此之外,有人认为日本“复用西法勤练军士,自以为富强可以立待。殊不知慕西法而无生财之道,适足以自耗其财。今自通商改用西法之后,国用不继,不得不苛敛于民。”“西人见其各事皆效西法交相夸誉,不知其正以此而致贫,慕虚名而难收实效,富强二字恐不易言也。”④很明显,他们都认为日本的明治维新并未使得日本富强,现反却加重了政府对人民的苛敛。在这些自来就信奉“民为邦本”的士大夫文人看来,日本明治维新自然是无足取了。因而他们不免对日本加以嘲弄与讥讽。他们讽刺日本“东头西脚,西头东脚,不成东西”⑤。既然维新造成了民生困乏,那么对他们更不易接受的易衣冠,改岁历就更不可理解了,这些都大大背离了传统,日本的“失败”证明了他们的正确——坚持传统。
不过,目光有长远与浅近之分,还有一些士人对日本并不一味的否定,他们虽说仍然以日本的维新造成民生困乏不以为然,但认为只要搞好了民生,日本还是有希望的。“自效西法,废封建为郡县,前后旧职去爵去禄不知凡几,此乱萌隐伏也。且国计日蹙,不得不多取之于民,而民怨,此亦乱萌隐伏也。”不过他还是说道:“诚能如当道之言,将所揭一千二百五十万元为开垦费用以尽地力,用织绒织布等物以夺外利,设国会以收民心。十余年间,日本可转贫为富,转弱为强国”⑥。
1880年以后,日本的经济形势出现了好转,逆差变为顺差,这种状况维持了大约十年之久。明治维新的诸多实效到此时方渐渐显现了出来。中国士大夫在感叹之余开始着力探求日本商务勃兴的根源。他们的对日观也已不再是轻视嘲讽了,而是师法仿效了。
中国自鸦片战争后不断面临外来列强的侵略,既有军事层面也有经济层面,中国逐渐被纳入世界市场之中,很显然,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必须在新形势下改变了,一些士大夫已经认识到了商业的重要,“夫商务未兴之时,各国闭关而治,享其地利而有余,及天下既以此为务,设或此衰彼旺,则此国之利,源源而往,彼国之利,不能源源而来,无久而不贫之理。所以地球各国,居今日而竞事通商,亦势有不可得已也。”⑦商业在一国发展中已经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故论一国之贫富强弱,必以商务为衡。商务盛则利之来如水之就下而不能止也,商务衰则利之去如水之日泄而不自觉也。”⑧“盖有商则士可行其所学而学益精,农可通其所植而植益盛,工可售其所作而作益勤,是握四民之纲者,商也。”⑨他们看到了日本商务的重大成就,认为日本商务勃兴的一个根源在于其政府的大力扶持,“日本农务商务……有农商务省以管摄之,保护之。”⑩因而郑观应等改良派认为国家政权应该为商业作庇护,国家政须实行“保商之法”,要革出“困商之政”。他们的目的是要“初学商战于外人,继则与外人商战。”⑪
很明显,这些士大夫的重商思想是有感于外来的经济侵略,他们鼓吹兴商的重点是要与外人商战,维护中国经济自主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抛弃了(更确切的数是扬弃了)传统的重农抑商。以往的学术研究往往以此来论定他们的重商思想已经属于一种资本主义范畴,其实这种看法忽略了对这些士大夫的目的论与方法论考察。更确切的说他们是扬弃了中国传统的重农抑商的经济体制形式,但根本的经济思想内涵——即以“民生”为基准——并未有根本改变,他们只是吸收新兴的更符合时代潮流的经济体制形式来继续维持传统的经济思想。形式改变了,但实质未变。西方的重商主义,即资本主义的重商主义,崇尚的是自由竞争,他们鼓励私人商业的竞争并谋求个人财富的聚集。而晚清士大夫的商业思想很明显是要以发展商业与外人商战,商业的主宰权归国家,因为也只有国家才能更大效益的组织力量与外国商战,而在此背景下的所谓“励商”也基本上是为了这一个目的。他们反对经商以聚敛个人财富,无论是官还是民都如此。这就是为什么,如郑观应等改良思想家初始时极力推崇洋务派的“官督商办”政策,认为这样能更有效的筹措经费以及发展商务,只是后来看到很多弊病,中饱私囊,专擅其事,调剂私人等,这些都严重违背了他们的初衷,兴商的目的不是为了国家的富强,民生的安泰,却用来为个人谋求私利,这是他们不能接受的。因而从此点来看,他们并未接受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商业精神。事实上,发展商业是必然要走上自由竞争这一步的,因而不能认为他们的商业思想属于近代资本主义的经济范畴。
事实上,非但经济层面如此,在政治层面他们也未脱离传统的意识藩篱。
晚清士大夫很是赞扬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器物技艺等的巨大进步,却很少去触及它的社会政体等层面,即使偶有触及,也是浅尝辄止。而这些人又大都是游离于封建政权中心地带的少数士大夫,他们在这种封建政权网络中居于一种令人尴尬的边缘境地,大抵只相当于幕僚一级。他们虽秉承了儒家的“济世情怀”却人微言轻,无力扭转最高权力中心的决策。
通过对日本的观察与了解,一些士大夫在很深程度上被西方的议院制吸引。他们做了一些详尽的介绍,称“其都城设有上下议政院。上院以国之宗室,勋戚及各大员当之,以其近于君也。下院以绅耆士商,才优望重者充之,以其迎于民也。凡有国事,先令下院议定,详达之上院。上院议定,奏闻国主。若两院意议符合,则国主决其从违。倘违此参差,则或令停止不议,或覆议而后定。”⑫议院制让他们找到一种新型的制度可以更好的联络君民,中国的传统是信奉“民为邦本”的,君主要时时注意体察民情,值当近代多事之秋,不更应该如此吗?他们宣称“盖闻立国之本在乎得众;得众之要在乎见情。故夫子谓:人情者圣人之田,言理道所由生也。此其说谁能行之,其惟泰西之议院。议院者,公议政事之院也。集众思,广众益,用人行政一秉至公,法诚良,意诚美矣。无议院,则君民之间事多隔阂,志必乖违。”⑬很明显,在这些士大夫看来,议院制不仅能更好的联络君民,而且能很好的团结维系国人一起对外。“中国户口不下四万万,国能设立议院,联络众情,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合四万万之众如一人,虽以并吞四海无难也。何至坐视彼族越九万里而逞披猖?”⑭
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改良派士大夫虽有这种比较新型的观念,实则还是在传统思想范围之内思考,他们从传统出发最后还是回到了传统。他们并不要根本革新,他们更不会要兴民权以削君权。他们既无此能力,更无此思想。他们只是放言:“中国两千年来专制政体,素主帝天下无可逃神圣不可犯之说。平生所最希望,专欲尊主权以导民权,以其势较顺,其事稍异。”⑮且更申明其志“近年以来,民权自由之说遍海内外,其势长驱直进,不可遏止,而或唱革命,或称类族,或主分治,亦嚣嚣然盈于耳矣。而仆仍欲奉王权以开民智,分官权以保民生,及其成功则君权民权两得其平。仆终守此说不变。”⑯
因此,我们不难看出,无论在经济还是政治层面,晚清士大夫都始终局限于传统的意识藩篱,未能摆脱,而与近代接轨。相比于历来的王朝变革,不同的是,他们深受新世界外来形势的刺激,试图以变革外在形式来更好的传承传统。他们是不可能带领中国走向一个新时代的。
三 、思想文化层面下的士大夫革新意识
小岛佑马称中国旧体制的特质为“知识分子支配”(《中国的革命思想》)正是这些士大夫在政治文化两方面构成了中国旧体制的支配层⑰。官僚士大夫们的心态恰反映了中国社会思想的方向和主流。
这些官僚士大夫正如佐藤慎一所指:“从小开始就致力于学术,通过突破科举各个阶段的狭窄门槛而使出类拔萃的能力得到客观的证实之后,成为官僚以辅佐皇帝的统治。”⑱
中国士大夫的知识伦理是“学而优则仕”,他们已经长时间的濡染了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道德情怀,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最高理想,他们不乏渴念“为君师”这样便可以“致君尧舜上”。“内圣外王”之道是他们的处世准则。科举入仕联接了士与君,入仕带给了他们荣耀的身份与地位,然而一旦入仕,他们即被囊括进了庞大的官僚网络体系,并以此附着上了君王国家政体。他们不能够再肆无忌惮的放言高论,相反却需在合乎官僚政体利益的“合法范围”内思考与行动。
当然,这只是士大夫立身行世的外在方面,单凭这点是无法解释他们思想意识及外在事功取向的根本原因的。倘没有一套系统完整的价值认同,士大夫阶层要保持如此一种“似疏又密”的组织体系,且维持长久的和谐度,实在很难。他们必得有一套基本的认识论哲学,且对之须有着虔诚的崇信⑲。当然时日长久这种信仰意识也难免发生松弛,晚清士大夫事实上也正是在这种对传统信仰意识的逐渐松弛中渐渐展现出其变革思想的。
外来的危机越发刺激了精英士大夫们的忧患意识,他们身遭变局,不满眼前的社会格局,想要革新却又无法甚或“不愿”根本革新,他们只是在尽力的做些“修缺补漏”的工作,因为在他们眼中,眼前的危机跟历朝历代的王朝危机并未有根本的区别,只要王朝管理者澄清政治,变革自强就依然能维持强大不倒的地位。他们的革新意识并未能深入到近代社会变革意识层面。
美国学者列文森的《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对士大夫的文化矛盾心理做了细致探讨,该书关注的核心之点在于历史与价值的张力,他宣称儒教中国的知识分子处于一种难言的窘境:他们在情感上执着于自家的历史,在理智上却又献身于外来的价值⑳。
相较于列文森单一的“冲击”论,墨子刻注意到了是儒教中国固有的思想脉络与问题,而不仅仅是西方的“冲击”,决定着中国近现代思想的发展与中国思想家对于西方思想的选择及其回应方式,他宣称:“文化传播是一条双轨线,它同时取决于输入的观念的有效性和促成这种输入的内部刺激的广泛性。二者中任何一方都不可或缺。”他看到了儒教传统内部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困境意识”㉒。
同样针对列文森用“文化认同危机”来阐释中国近现代思想,张灏则认为,普遍性层面的“意义危机”较之特殊的“文化认同”更能体现中国现代思想的深层结构,他认为:“中国的文化认同危机出现了非西方国家所共有的典型特征,其特色即是,因西方而产生的屈辱形成了情意综,这种情意综使中国知识分子在潜意识中去寻求心理上的补偿,宣称中国文化可与西方文化并驾齐驱,甚或较之优越。”㉒
虽说这三种观点对理解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的思想不无裨益,但需指出的是,在甲午战前的精英士大夫阶层(在此更多的是指具改良思想的精英士大夫),这种深层次的意识危机尚未有呈现于他们的心中,或者是占据他们意识的主流,根本的文化冲突,在此时期尚未明显的出现,只有等到甲午海战,蕞尔小国的日本战胜古来强大的中国,士大夫群体方才在极大的屈辱中激发出了上述种种的文化心理认同危机。而在中日海战之前的很长时期,士大夫的革新意识却并未能突破传统王朝变革意识的藩篱,其变革意识不属于近代性质范畴。
事实上,“因屈辱而产生的情意综”极明显的出现在了甲午战后的士大夫守旧派思想中。他们虔诚宣称着:“夫学以框时为急,士以立志为先,四郊多垒,而不思卧薪尝胆以雪国耻者,卿大夫之辱也,邪说诬民而不思正谊明道以挽颓流者,士君子之辱也。”㉓他们认为:“闻日新其德矣,未闻日新其义理也。乾嘉诸儒以义理为大禁,今欲挽其流失,乃不求复义理之常,而徒备言义理之变。彼戎狄者,无君臣,无父子,无兄弟,无夫妇,是乃义理之变也。将以我圣经贤传为平淡不足法,而必以其变者为新奇乎?有义理而后有制度,戎翟之制度,戎翟之义理所曲寓也,义理殊斯风俗殊,风俗殊斯制度殊。今不揣其本而曼云改制,制则改矣,将毋义理亦与之俱改乎?”㉔列文森等的文化探讨,在此时期方才显示出极大的关联性和针对性。
传统儒教中国“士大夫的学问对象局限于按经史子集分类的中国古典世界,但是这并不是由于他们的偏狭。中国古典世界本身就是一个宏伟的知识体系,”“值得一学的都应该包含在其中,关于人与社会各种问题的解答都应该包含在其中。关于人与社会的真理记述在经书中,解决问题的先例则积蓄在史书中。士大夫的任务就是正确地解释这些书籍,发现确切的答案。19世纪后半期的士大夫尽其所能,倾其所学而为的正是这些。他们虽然提出了无数的对策案,但是终究不能找到确切的解答,这是因为经过产业革命与政治革命而成长起来的西方诸国的力量——政治力经济力与军事力——在人类历史上本身就是前所未有的。如何翻阅中国的古典也不可能找出确切的解答来。不能找出确切的解答,并不是因为各个士大夫的个人能力不足。”㉕
这段话较深入的揭示了精英士大夫们身处危机下凸显出的革新意识,为何终究未能摆脱传统藩篱。关键点在于他们长久的身处于古典世界的模式中,未能深切体会出近代社会的层层意识。
这种状况的养成跟士大夫精英阶层的科举制度关系紧密,士大夫们内在的自由思想转被官方政治形态外化,这样便由原来的灵动活泼走向了沉滞僵化。
我们须得重新审视传统中国下的科举制度。
科举制在中国的封建官僚体系建设与完善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它是联接学者与官僚,以及在两者之间画等号为媒介的制度,是士大夫社会再生产得以成为可能的制度。它维系了庞大官僚体系的正常运转,不断地为它“造血”与“输血”,是维系千年以上中国社会的根本构架。
在传统中国,区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标准是有无文化能力和道德能力。科举所要求的正是这两项能力:一是固定的诗文的写作能力;一是关于儒教经书的知识。前者考察其有无文化能力,后者则考察其有无道德能力。这样的科举考察很明显忽略了官员们所应当具备的专门知识(如法律知识)的有无。在封建中国,官员政绩的考察点着眼于是否人口富足,民生安乐,官员们所需做的只是对人民用道德加以维系并用文化加以教育。传统中国是一个重情更甚于重法的社会,官员们并没要求要拥有多么深切的法律知识,“城池钱谷”之类的俗事又多委托给了幕僚或胥吏。这些官僚士大夫实质是处于一种既深入政治又远离政治,似仕又隐的状态。只是,在事实上,这些士人出身的官员除了通过科举成为官吏而起家之外,既无别的立身之途,又一般没有作为维持作为一个有教养人生活的手段,于是即便他们不关心政治也要依靠它来维系自己的存在了。只是作为官僚又必得具有一定的“为政手段”,这些需求很幸运的他们通过对儒家经典的学习获得了。如前所述:关于人与社会的真理记述在经书中,解决问题的先例则积蓄在史书中。在这种情况下,对儒家经典的解读与释义就成了官僚士大夫群体维系自身权威的保障,获得对经典的解读权即获得了为官的保障,这样也就保障了他们的荣耀,身份地位与财富。
巨大的政治利益是不可能让这些士大夫如同现代知识分子一般游离超乎于社会之上,做无顾虑的批评的。他们的利益附着于整个传统社会之上,这也使得他们都无形中附着于传统之中,无法超脱。
事实上,此时期的士大夫精英们几乎都有意无意地奉行着“古体今用”的模式,尽管所信奉的这个模式的内涵不尽相同,但无疑都不离“古体”的意识内涵。
中国古代的“体用”常常是合而不分的,有何“体”必有何“用”。晚清士大夫们危机意识下的“革新”观,虽是瞩目于西方或日本的近代化层面,但他们期望的常常是在“古体”上的“今用”“嫁接”,都有意无意的造成了“体用”两割,实质依然未变。
这种主观性的理想化设计思路,使他们看不出中外的根本差异,面对外来时,始终摆脱不了“崇古”情绪。只是,这并不等同于列文森的“文化认同危机”下的“情感上的执着”,这种心理更大层面上是一种“混沌式的盲目自信”。
在这种心理下,他们坚信“西学中源”,西方现在优越于中国的都是我原来具有的,这种意识取向极大的盛行于晚清士大夫之中,如冯桂芬即认为“中华扶舆灵秀,磅礴而郁结,巢燧羲轩数神圣,前民利用所创造,诸夷晚出,何尝不窃我绪余。”㉖就连极为开明的黄遵宪也未能脱此窠臼。他说:“其(指西方)谓人人有自主权利,则墨子之尚同也;其谓爱汝邻如己,则墨子之兼爱也;其谓独尊上帝,保汝灵魂,则墨子之尊天明鬼也;至于机器之精,攻守之能,则墨子备攻备实,削鸢能飞之绪余也;而格致之学,无不因其端于墨子《经》上下篇。”㉗
这种状况下的士大夫们注定是王朝历史的悲剧者,他们的命运丝丝连接于旧王朝,同生同死,科举的废除,其后跟随着清朝的灭亡,也伴随着传统士大夫的消失。
四、小结
从总体上讲,晚清士大夫正在逐渐地从封建政权中心游离出来,甲午战后,精英士大夫们更多的是以知识层面的身份参与言论,较之战前的士大夫们少了些政治场上的顾虑,他们受空前的思想意识危机影响,提出的口号更为强烈,变革也更为深刻。在此前提下的变革意识,方才逐渐向近代意识层面迈进。
总体上讲,甲午战前的中国士大夫只是处于一个特定的转型时期,他们逐渐从传统中游离出来,并向近代知识人蜕变,处于这一时期的传统士大夫开始呈现出一些近代化的形式倾向,且具备一定程度上的近代价值观和行业观,但根本上还是带着浓厚的传统色彩。他们主张学习西方,但仍不脱“古体今用”的藩篱。他们希望变革,甚至主张设议院,但仍然不敢非议君权。他们与近代知识人相比,在价值取向和知识结构上有着极大的差别。他们的价值取向,概言之即 “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荀子·劝学》)
大抵上说,晚清士大夫群体中的很多开明分子面对国家危机都在极为认真诚恳地探索着国家前行的路,他们选择了日本,并以此来认识西方的现代文明,当然他们的探索未必都符合历史的真实,然而倘没有他们的努力,以及勇敢的踏出的这一步,中国近代史将很难进步。只是他们长久的濡染了传统文化,有着以此而来的一整套价值信仰,深刻的社会危机,虽加重了他们的忧患意识,并激发了革新意识,但终于未能摆脱传统的藩篱。
只是,与其说他们是顽固的捍卫着传统,倒不如说是他们坚强的捍卫着信仰。在此时期,他们终究还是没有后来时期出现在心头的那种深刻的“文化认同危机”。他们没有经历过西方现代的理性训练,重“情”更甚于重“理”,他们更多的是从信仰出发来判断,却无法从理性出发来判断,因而在此基础上,虽产生了要求社会变革的意识,但依然未踏入近代化的轨道,这是受复杂的客观形势决定的。
一般来说,传统士大夫向现代“知识人”的转化是一个理性自觉与身份自觉的过程。概括而言,传统中国的精神可称为“礼教的精神”,它将社会成员维系成一个“家,国,天下”的人性网络,士大夫被作为了国家与社会运行的一部分,因而未能脱离成单独的个体,这样他们就很难成为一个具有自我主张的人。正如岛田虔次所指出的:“一般来说,在一个具有统一体性的社会圈之中,只有在成为其纽带的传统性统制无力化的时候,个人才能作为异端成为具有自我主张性的人物。”㉘因而我们现在来反观晚清士大夫的社会变革思想就不能不考虑到晚清社会的种种现实情况,不能单纯的责怪他们没有一种科学的观念了。
注释
①韩小林、冯君:《论甲午战前中国社会的日本观》,《嘉应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韩小林:《论李鸿章的日本观》,《广西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王晓秋:《近代中国与日本——互动与影响》,北京:昆仑出版社,2005年。
②吴艳杰:《郑观应“商为国本”思想浅析》,《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朱鸿翔:《试论郑观应的商战思想》,《商场现代化》2006年1月(上旬刊)总第454期。
③李莜圃:《日本纪游》,《小方壶斋舆地丛抄》第十帙,台北:学生书局,1975年。
④⑤阙名:《日本杂记》,《小方壶斋舆地丛抄》第十帙,台北:学生书局,1975年。
⑥阙名:《日本琐记》,《小方壶斋舆地丛抄》第十帙,台北:学生书局,1975年。
⑦薛福成:《筹洋刍议·商政》,见丁凤麟、王欣之编:《薛福成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41页。
⑧薛福成:《出使日记续刻》(光绪十八年六月三十日),见丁凤麟、王欣之编:《薛福成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611页。
⑨薛福成:《英吉利利用商务辟荒地说》,见丁凤麟、王欣之编:《薛福成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97页。
⑩钟叔河主编:《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357页。
⑪郑观应:《盛世危言·复考察商务大臣张弼士侍郎》,见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57页。
⑫郑观应:《易言·论议政》见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03页。
⑬⑭郑观应:《盛世危言·议院上》,见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⑮⑯吴振清等校整理:《黄遵宪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13页,第491页。
⑰⑱㉕佐藤慎一:《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7页,第8页,第12—13页。
⑲此所讲的只是士大夫群体价值观的一种抽象概述,并不能认为这个阶层中的每个个体都一定会依此而行。“士大夫”这个概念内涵可以从思想意识价值观念上讲,也可以从政体组织上讲,士大夫=学者官僚的特殊表达,注定这是一个两分的认识。士大夫是拥有双重身份的人,一种是文化身份,一种是政治身份。
⑳〔美〕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任菁译,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0年,第1-148页。
㉒〔美〕墨子刻:《摆脱困境——新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颜世安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页。
㉒张灏:《新儒家与当代中国的思想危机》,见《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保守主义》,台北: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第371页。
㉓朱一新:《朱侍御答康有为第三书》,见苏舆编:《翼教丛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7页。
㉔朱一新:《朱侍御答康有为第四书》,见苏舆编:《翼教丛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11页
㉖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卷下,见《制洋器议》,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
㉗黄遵宪:《日本国志·学术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787页。
㉘岛田虔次:《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68页。
责任编辑 东园
——士大夫的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