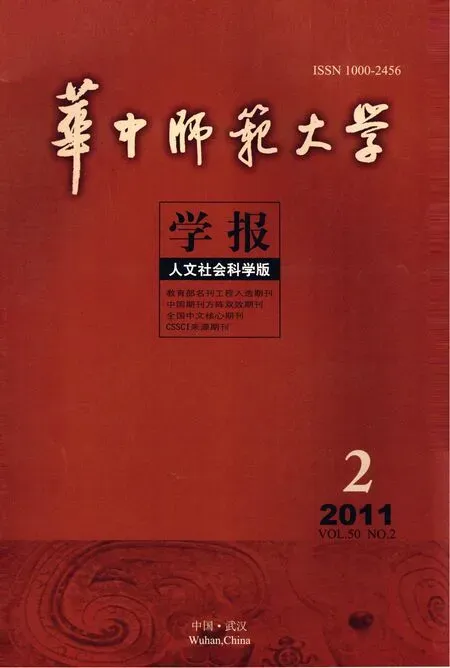蔡元培的学术观及其大学理念
喻本伐 喻 琴
(华中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蔡元培的学术观及其大学理念
喻本伐 喻 琴
(华中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蔡元培是中国知识界的卓越前躯。他的学术观,不仅有着深厚的哲学底蕴,而且能够对学术关系作出深刻辨析;至于他对学术独立、教育独立的倡扬和努力,不仅表明了他人格觉醒的力量,而且在构建制度保障体系方面也作出了尝试。在这种学术观的指导之下,他主持了中央研究院的创设和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在他所领导的对北京大学的改造和办理中,形成了以学术研究为内核的大学理念。这种理念,对于当代高等教育体制的改革和学术研究的深化,均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学术观;大学理念;思想自由;囊括大典;教育独立
蔡元培为进士出身,早年历任翰林院编修、绍兴中西学堂监督、嵊县剡山书院院长、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中国教育会”事务长(会长)、绍兴学务公所总理、北京译学馆教习。其间,他曾投身于革命运动:1904年在上海组织光复会,任会长;次年加入同盟会,任上海分会会长。1907年5月,他自费赴德国留学,旁听哲学、文明史、美学、教育学、心理学等课程。武昌起义后归国。中华民国创立后,他受命担任教育总长。后辞职赴德国、法国从事文化交流事业;发起成立法华教育会,任会长。1917年1月,他归国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对该校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旨在深化学术研究,使北京大学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最高学府。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为了变革中国官僚化的学术和教育制度,他领衔试行大学院制和大学区制,出任中华民国大学院院长。此制停废后,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将余生全部献给了中国的学术研究事业。蔡元培虽曾积极投身于革命事业,然而他毕生的兴趣所在,却依旧是学术和教育。本文试图通过对其学术观的论析,以揭示他不同流俗的大学理念。
一、学术观的哲学底蕴
蔡元培毕生看重哲学、科学、伦理学和美学。他的学术观,首先得益于严复的启蒙。蔡元培在《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一文中认定:“五十年来,介绍西方哲学的,要推侯官严复为第一。”①严复明确反对“中体西用”。在《原强》中,他对西方学术的基本认识是:“其为事也,一一皆本诸学术;其为学术也,一一皆本于即物实测。”同时,他严厉抨击了陆王之学的“师心自用”,并严肃指出:“盖学术末流之大患,在于徇高论而远事情,尚气矜而忘灾祸。”②这是基于科学主义或实证主义的学术观。在严复看来,中国近代的落后,在物质层面的不如人,只是表象;更为深层的原因,则在于精神、学理方面的不如人。因此,他明确主张“体用不二”。
当严复晚年放弃了他在甲午战败后的真知灼见时,蔡元培却毫不犹疑地接过了“学术救国”的大旗,支持和参与新文化运动,对各种外来的新兴思潮敞开胸襟,并致力于大学和研究院所的办理。他对于学术的价值,也有了更为笃实的认识。在《我们希望的浙江青年》的演说中,他明确指出:“民族的生存,是以学术做基础的。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兴衰,先看他们民族和国家的文化和学术。学术昌明的国家,没有不强盛的;文化幼稚的民族,没有不贫弱的。”③他又在《学术讲演会启事》中剀切指出:“我国近年所以士风日敝、民俗日偷者,其原因固甚复杂,而学术销沉,实为其重要之一因。教者以沿袭塞责,而不求新知;学者以资格为的,而不重心得。在教育界已庵庵[奄奄]无气如此,又安望其影响一般社会乎!”④据此可知,蔡元培视学术昌明为国家的命脉所系。
蔡元培首先是个儒家学者,他的君子风度也为众所公认。在他的学术观中,曾明确表述了对儒家哲学的赞同。他在《上海各学术教育机关欢迎华虚朋集会上的演说词》中有云:“我国学术史上,法家偏重群性,道家偏重个性,均不适于我民族的习惯。惟儒家能兼顾个性与群性,流行至二千年不替。”⑤但是,他在诠释“世界观教育”时,又对中国历代以“一流派之哲学、一宗门之教义梏其心”的思想钳制术深表不满,并试图引进西方哲学来更新这潭死水。他在《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一文中说:“世界观教育,就是哲学的课程,意在兼采周秦诸子、印度哲学及欧洲哲学,以打破二千年来墨守孔学的旧习。”⑥这种世界观教育之意蕴,实以“兼容并包”为内核;设若站在哲学的高度来表述,它便是打碎信仰的信仰。
具体而言,德国哲学家康德对于蔡元培学术观的形成影响至深。这是他留德的最为重大、持久的收获。1924年4月21日,他在《康德诞生二百周年纪念会上致词》中承认,康德对自己的思想“永远有巨大的吸引力”。他接着陈述的理由是:“只有在扩大知识和提高道德价值的基础上,世界才能够向前发展。在一个错综复杂、令人迷惘的世界里,特别需要具有这样一种精神。它能使最完美的知识和至高的道德的时代潮流融合在一起,并使崇高的永恒真理的理想得以发扬。”⑦客观说来,知识和道德便是蔡元培学术观中的两大要素。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提出了两个对立“物自体”的命题:一为“先验对象”的物自体,它是感性的来源和基础;二为“先验自我”的物自体,它是理性的来源和基础。蔡元培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一文中,将前者译为“现象世界”,而将后者译为“实体世界”;他对于这种二元论哲学的诠释为:“盖世界有二方面,如一纸之有表里:一为现象;一为实体。现象世界之事为政治,故以造成现世幸福为鹄的;实体世界之事为宗教,故以摆脱现世幸福为作用。而教育者,则立于现象世界,而有事于实体世界者也。”他接着又对这两大世界的区别进行了概括:“前者相对,而后者绝对;前者范围于因果律,而后者超轶乎因果律;前者与空间、时间有不可离之关系,而后者无空间、时间之可言;前者可以经验,后者全恃直观。”据此,他既蔑视“最浅薄之唯物论哲学”,又鄙薄“最幼稚之宗教”。在这套哲学体系中,蔡元培所推崇者,既不是政治家,也不是宗教家,而是教育家和学问家。因为只有他们,才可能具备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才可能“以实体世界之观念为其究竟之大目的,而以现象世界之幸福为其达于实体观念之作用”⑧。简言之,学术犹如由现象世界通达实体世界的津梁或舟楫。
这种建基于康德哲学的学术观,将科学、伦理和艺术均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因而明确拓宽了严复科学主义学术观的范畴。中国传统学术的主干为伦理学,西方工业化启动后的主流学术为科学。蔡元培接受了康德和席勒的影响,毕生重视美学和美育;他又接受了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孔德的影响,明确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从而将艺术哲学纳入学术研究的范畴,进而将其作为养成健全人格之襄助。由于蔡元培偏爱哲学思考,所以他的学术观置重于“高深学问”。但是,若从他积极支持实利教育、工读教育、平民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开展来看,他对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非但不排斥,甚至还多有服膺的表示。总的说来,蔡元培学术观的哲学支撑,既然是众流百家的结果,当然也就具备了兼容并包的特征。
二、学术关系论
1921年5月12日蔡元培访英时,在爱丁堡大学对留英学生组织的中国学生会及学术研究会发表了演说。其中,他专门论及学术关系:“学与术可分为二个名词,学为学理,术为应用。各国大学中所有科目,如工商,如法律,如医学,非但研求学理,并且讲求适用,都是术。纯粹的科学与哲学,就是学。学必借术以应用,术必以学为基本,两者并进始可。”接着,他以中国近代化中认识深化的历程为例,说明西方的枪炮、器物、医术、制度的优越,均有其内在的学理作为基础。因此,他谆谆告诫在座的诸君:“中国固然要有好的技师、医生、法官、律师等等,但要在中国养成许多好的技师、医生等,必须有熟练技能而又深通学理的人回去经营,不是依样画葫芦的留学生做得到的。”“要是但知练习技术,不去研究学术;或一国之中,练习技术的人虽多,研究科学的人很少,那技术也是无源之水,不能会通改进,发展终属有限。所以希望留学诸君,不可忽视学理。”⑨蔡元培在此所强调的,是“学体术用”关系。
在这次演讲中,蔡元培还特别强调了美术的效用:“外人能进步如此的,在科学以外,更赖美术。”“西洋科学愈发达,美术也愈进步。”这是因为:“美术所以为高尚的消遣,就是能提起创造的精神……因为美术一方面有超脱利害的性质;一方面有发展个性的自由。所以沉浸其中,能把占有的冲动逐渐减少,创造的冲动逐渐扩展。”⑩蔡元培在此所提倡的“美术”,实则艺术;除绘画外,还包括雕塑、装饰、音乐、戏剧、文学、书法等等。这种艺术,既非单属于“学”,也非单属于“术”。联系蔡元培有关“五育”的论述,可知“美育”由“美术”所派生。美育全称“美感教育”。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一文中,他明确指出:“美感者,合美丽与尊严而言之,介乎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之间,而为津梁。此为康德所创造,而嗣后哲学家未有反对之者也。”若据心理学而讨论五育的关系,蔡元培的看法是:“军国民主义毗于意志;实利主义毗于知识;德育兼意志、情感二方面;美育毗于情感;而世界观则统三者而一之。”(11)据此可知,美术虽为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之中介,然而它却是朝向或偏向于实体世界的。
那么,学与术究竟与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的关系若何呢?首先可以肯定的是,术属现象世界无疑。至于学,科学因其“范围于因果律”,有客观规律可循,因而亦属现象世界;而神学与玄学,因其“超轶乎因果律”,无客观规律可循,因而属于实体世界。值得特别说明的是,蔡元培摒弃了康德的宗教观,而以“高深学问”予以置换。这种高深学问,主要指伦理学和美学,即超功利的信仰、情感之学,它由自由精神和特异个性所代表。这种虚玄的信仰之学,若相较于科学的实用之学,无疑所占比例极小。这可由蔡元培有关五育并重的课程设计以观:“军国民主义当占百分之十,实利主义当占其四十,德育当占其二十,美育当占其二十五,而世界观则占其五。”(12)尽管这种“提撕实体观念”之学所占的比重最少,然而它却是蔡元培所最为看重的。他将此悬格为最高的原因,便是因为人与动物之分野,便在于精神追求之有无。当民国元年“临时教育会议”删除了“世界观教育”而由教育部颁行“四育宗旨”后,蔡元培视之为“残缺方针”的道理,便因其未能预悬自由且高远的精神目标。
若就科学之学而言,蔡元培在《北大新闻学研究会成立演说词》中承认:“凡事皆有术而后有学。”(13)这当然是基于认识论的阐释,属经验论范畴。据此可知,凡安根于现象世界之学术,均有着“术先学后”关系;凡游荡在实体世界里的先验的形而上学,既无一定之术与其对应,也不受空间和时间。这种属于实体世界的“自由精灵”之学,虽“无迹象之可求”,纯为玄想、体悟、推断的产物,然而却也并非某些唯物论者所断言的“鸦片之学”。无可否认,神学为形而上学;但是,除宗教之外,毕竟还存在着诸多形而上之“道”。
蔡元培的学术关系论,也有着明显承袭严复的痕迹。严复在《救亡决论》中有言:“西人举一端而号之曰‘学’者,至不苟之事也。必其部居群分,层累枝叶,确乎可证,涣然大同,无一语游移,无一事违反;藏之于心则成理,施之于事则为术;首尾赅备,因应厘然,夫而后得谓之为‘学’。”(14)这显然是就科学之学术所进行的界分。而蔡元培对此的发展、进步之处,便在于承认了“纯粹理性”之学的地位,并尽力拓展了思想自由的空间,此即为“道德心之自由”,从而超越了“认识力之有界”(15)。
蔡元培“学为基本,术为枝干”的主张,当时也曾招致质疑,并集中由大学改制问题而引发。1912年10月所颁《大学令》规定:“大学分为文科、理科、法科、商科、医科、农科、工科。”此即为“七科大学”之设。它将清末“八科大学”中的“经科”归并于文科,余皆承袭未变。与此令同时颁布的,尚有《专门学校令》。其中规定:“专门学校之种类,为法政专门学校、医学专门学校、药学专门学校、农业专门学校、工业专门学校、商业专门学校、美术专门学校、音乐专门学校、商船专门学校、外国语专门学校等。”显然,大学之设,偏重于“学”;专门学校之设,偏重于“术”。蔡元培主长北京大学后,始倡“学术分校”,计划将北京大学工科划归北洋大学,将商科归并于法科,并筹划法科独立设校(未果)。同时,他又在“国立高等学校校务讨论会”上,提出了“大学改制”的动议:称设文、理两科者,为“大学”;而法、医、农、工、商五科,则分设为“独立大学”。在《读周春岳君〈大学改制之商榷〉》一文中,蔡元培曾如是说:“鄙人以为,治学者可谓之‘大学’,治术者可谓之‘高等专门学校’。两者有性质之别,而不必有年限与程度之差。”在他看来,这一“大”一“高”,本无语义学上的实质差别,只因清末“我国曾仿日本制,以高等学堂为大学堂之预备,又现制高等专门学校之年限,少于大学三年或四年”,因而“社会上对于‘大’字、‘高’字,显存阶级之见”。有鉴于此,他“所提于校务讨论会者,不持前说而持一切皆为大学之说”。尽管名称可以通融,然而其学术分校的主张却坚定不移,他在该文中所陈述的理由是:“学与术虽关系至为密切,而习之者旨趣不同。文、理,学也。虽亦有间接之应用,而治此者以研究真理为的,终身以之。所兼营者,不过教授、著述之业,不出学理范围。法、商、医、工,术也。直接应用,治此者虽亦可有永久研究之兴趣,而及一程度,不可不服务于社会;转以服务时之所经验,促其术之进步。与治学者之极深研几,不相侔也。”(16)由此观之,蔡元培因重“学”而偏爱大学的意向显然。
有必要特别指出的是,蔡元培除学、术分论外,更多还是学术联用。这种学术概念的使用,实与“技术”概念相对应。所以说,这种学术,依旧是以学理作为核心内涵的。
在《〈植物学大辞典〉序》中,蔡元培又提出了“专门学术”的概念:“一社会学术之消长,观其各种辞典之有无、多寡而知之。各国专门学术,无不各有其辞典,或繁或简,不一而足。”(17)显然,与专门学术相对应者,理当为“综合学术”。它或可认哲学为代表,实为一切学问之学问。正因为它不可能一一皆获得实证,所以又可称之为“纯粹学术”。由此还可知,专门学术与“应用学术”的联系也相对为多。
蔡元培的学术关系论,是他学术观中的重要内容。在这方面,他更多地借用了德国哲人的思想成果,并与德国大学看重科研和理智的传统紧密相关。
三、学术独立论
蔡元培在从事资产阶级革命时,也曾试图借助学术的武器。他在《社会改良会宣言》中明确主张:“以人道主义去君权之专制,以科学知识去神权之迷信。”(18)此即以学术来改良政治和宗教。当中华民国成立、他出任教育总长之后,便本着“学术救国”的初衷,试图为教育立一“百世不迁之主义”,因而有《对于新教育之意见》(又名《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的发表。其后,不仅因为当局删除了其中的“世界观教育”一项,更因为他置身于政坛后难以忍受其污浊,方知“非我辈书生所能挽救”(19),于是力辞教育总长职,藉以保全人格,并为学术与教育保留自尊。
在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前,也曾颇费踌躇。这是因为:“当时在上海的老同盟会员,对蔡元培是否应去北大任职,颇有不同意见。多数人劝他不去就职,马君武尤坚决反对,认为北大太腐败,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而于自己的声名有碍。但也有少数人说,既然知道它腐败,更应该去整顿,即使失败,也算尽了心意。”(20)其后蔡元培之所以毅然赴京,便是因为他依旧怀抱着学术救国的热忱。这从他《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中便可看出。事实上,在他对北京大学的整顿和改造中,还致力贯彻了思想自由和学术独立的理念,从而使此期的北京大学成为了中国高教史和学术史上的一座丰碑。
在“五·四”运动后,蔡元培曾多次请辞北京大学校长职。1919年6月15日,他在《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中,真实地表达了自己的感受和意向:“我绝对不能再作那政府任命的校长:为了北京大学校长是简任职,是半官僚性质,便生出许多官僚的关系,那里用呈,那里用咨,天天有一大堆无聊的照例的公牍。要是稍微破点例,就要呈请教育部,候他批准。甚而部里还常常派了什么一知半解的部员来视察,他报告了,还要发几个训令来训饬几句。我是个痛恶官僚的人,能甘心仰这些官僚的鼻息么?”他还赞同袁世凯的看法,直认北京是个“臭虫窠”,并且接着指出:“无论何等高尚的人物,无论何等高尚的事业,一到北京,便都染了点臭虫的气味。”(21)他于是离京南下,多次辞职又被多次挽留,致使他被后人笑称为“中国高教史上辞职次数最多的校长”。不懂蔡元培者,可能认为如此“要挟”不值;可理解蔡元培者,方知在学术与政治的角力中被拉扯是何等痛苦!蔡元培总想为中国的未来预留一点希望,然而黑暗的政治现实和“政教合一”的传统,却总是将这希望撕成碎片。这当然可视为学术独立主张的碰壁,然而更应看到的是,这种“屡败屡战”精神的可贵。在政治强势的中国,真正能像蔡元培那样蔑视权力而倡扬学术的大学校长,在历史回眸中确实不多。据此可知,在蔡元培的心目中,学术独立的第一要义,便是学术理应独立于政治。
至于学术独立的第二要义,便是学术理应独立于宗教。1922年初,“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即将在清华学校举行第11届年会的消息甫经披露后,随即引发中国学界的普遍愤怒。同年3月9日,上海学生组织了“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发表宣言,通电全国,吁请共同抵制此次会议,激起了较大社会反响。3月20日,以李大钊为首的北京知名教授,共同发起成立“非宗教同盟”。同年4月4日—8日,基督教学生同盟年会如期在清华召开。该会闭会次日,北京非宗教同盟举行演讲大会,到会者千余人,蔡元培也应邀到会发表演说。他开门见山地指出:“我曾经把复杂的宗教分析过,求得他最后的原素,不过一种信仰心,就是各人对于一种哲学主义的信仰心。”本来,信仰自由理当宗奉;但是,“因为现今各种宗教,都是拘泥着陈腐主义,用诡诞的仪式、夸张宣传,引起无知识人盲从的信仰,来维持传教人的生活。这完全是用外力侵入个人的精神界,可算是侵犯人权的”(22)。有鉴于此,他尤其反对宗教“侵入”学校,进而影响学术。
就在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和非宗教同盟成立之时,蔡元培在《新教育》4卷3期上发表了《教育独立议》一文。该文不仅针对宗教的甚嚣尘上,而且针对政治的腐败骄横。其撰文的直接动因,实发端于“教育经费独立运动”,即针对欠薪而索薪,进而要求“指定确实款项作为教育经费”。他在该文中明确指出:“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的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人去应用的。所以,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和各派教会的影响。”接着,他毫不客气地指出了教育与政治的殊异:“教育是要个性与群性平均发达的;政党是要制造一种特别的群性,抹杀个性。”“教育是求远效的,政党的政治是求近功的。”教育权不宜交与政党的理由还有:“政党不能常握政权,往往不出数年,便要更迭。若把教育权也交与政党,两党更迭的时候,教育方针也要跟着改变,所以教育就没有成效了。所以教育事业不可不超然于各派政党以外。”(23)这里虽仅言教育而未言学术,但由于教育是传授知识和思想方法的事业,而大学教育更是以追求“高深学问”为职志的,所以若以学术来置换教育,当然并无不当。换言之,学术若由政府或政党来操持,也必将“没有成效”。
在该文论述教育必须独立于宗教时,蔡元培事实上是将教育与学术并论的:“教育是进步的:凡有学术,总是后胜于前,由于后人凭着前人的成绩,更加一番功夫,自然更进一步。教会是保守的:无论什么样尊重科学,一到《圣经》的成语,便绝对不许批评,便是加了一个限制。”尽管“各国宪法中,都有‘信仰自由’一条。若是把教育权交与教会,便恐不能绝对自由。所以,教育事业不可不超然于各派教会以外”(24)。在蔡元培看来,只有“超然教育”,才可能达成“超然学术”;无论是政府或是教会介入,均必然会影响教育或学术的良性发展。
为了从制度上保障教育独立和学术独立,在《教育独立议》中,蔡元培主张仿行法国“大学区”制,并进行了初步设计。尽管此方案在当时并无试行的可能,但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蔡元培却把握了政权更迭之初的有利条件,领衔试行了“大学院制”和“大学区制”。所谓大学院制,即将最高学术研究机构与教育行政机关合为一体,使其相对独立于政治或政府,从而以学术化取代行政化。蔡元培在《关于大学院组织之谈话》中指出,实行大学院制的“根本理由”有三:“一、学术、教育并重。以大学院为全国最高学术机关、教育机关。二、院长制与委员制并用。以院长负行政全责,以大学委员会负议事及计划之责。三、计划与实行并进。设中央研究院,实行科学研究。”(25)这段陈述,精到地概括了大学院的立制精神。所谓大学区制,即是将地方学术领导机构与教育行政机关合为一体的制度。它仿照法国,分全国为若干大学区,每区设立国立大学一所,以大学校长总理全区的学术研究和教育行政事务。当时有江苏、浙江、北平大学区的试办。大学区也不从属于地方政府,保有独立的精神,因而有利于地方学术与教育的发展。
尽管大学院议决废止了“党化教育方针”,然而大学院却因与“党化”精神不符而举步维艰。另一方面,此制试行后,由于传统的惯性,不仅未使行政机关学术化,反使学术机关官僚化,从而也引发了教育工作者的非难。1928年8月8日,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召开。会上通过了《设立教育部,废止大学院案》,决定将教育部隶属于行政院,从而使蔡元培学术和教育独立的理想破灭。此后,他晚年的心血,主要付诸于中央研究院的筹创与发展。
1927年11月20日,中央研究院筹备会议召开,通过《中华民国大学院中央研究院组织条例》,公推蔡元培为大学院院长兼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决定首先筹办理化实业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地质研究所和观象台。1928年4月10日,国民政府公布《修正国立中央研究院组织条例》,改中央研究院为独立机关,不再隶属于大学院。同月23日,特任蔡元培为院长。蔡元培辞大学院院长职后,便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致力于学术研究事业。在他的主持下,先后筹设了物理、化学、工程、地质、天文、气象、历史语言、心理和社会科学9个研究所,另设自然博物馆一座,使中国的科学或学术研究事业真正起步。诚如翁文灏所言:“蔡先生主持中央研究院的办法,是挑选纯正有为的学者做各所的所长,用有科学知识并有领导能力的人做总干事,延聘科学人才,推进研究工作。他自己则因德望素孚,人心悦服,天然成为全院的中心……所以中央研究院虽然经费并不甚多,却能于短时期内,得到若干引起世界学者注目的成绩。”(26)在蔡元培走向生命终点的这10余年间,虽然再也未能在学术独立的制度设计方面有所作为,但由他来主持中央研究院,至少也避免了政治的诸多干扰,并为学术研究事业保留了一份难得的尊严。
四、大学理念之要义
蔡元培的学术观,不仅决定了他的治学路向和特色,而且决定了他的办学思想。他对北京大学的整顿和改造,更是集中地反映了他的大学理念。当前研讨大学理念的文论甚多。凡切中肯綮者,多与蔡元培所论相合,因而也能与他的学术观相契。
所谓大学理念,简言之,即对大学的本质认识,或称理想中的大学、有关大学的理想。它是一股流动的精神,往往会因时、因地而变化;但若就其根本追求而言,它却也有一以贯之的指导思想。有基于此,大学理念通常也称为“大学精神”或“大学使命”,它须以学术研究为内核。具体而言,蔡元培大学理念的要义,可简明概括为如下数端。
其一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蔡元培对于“墨守孔学”、“思不出位”的中国治学传统深恶痛绝,视此为中国学术难以昌明的主因。中国古代官学教育曾经盛极一时,也曾有太学、国子学、国子监等最高学府的成功办理。然而自汉代“独尊儒术”始,这种专经教育便日益偏狭,便难有自由创发的空间;尤其自隋唐科举定制后,这种对经学知识的有限追求,更与出仕做官紧密勾连,从而使知识精英异化为官僚文人,并使他们主动放弃了追求思想自由的权力;当明清的文教专制日益强化之后,文字狱、绳愆厅等钳制思想的措施,更使自由思索和兴论立说成为了获罪的口实,乃至因此被定罪杀头,甚至还会株连九族。蔡元培成长于这种“万马齐喑”的社会现实之中,因而更是感之深、痛之切。他甲午战败归里后,曾借诗抒怀:“人生识字始生忧,百感茫茫不自由。”(27)当风气日开之后,他广阅西书,服膺进化论,眼界渐开,并尝试性地冲开了思想牢笼。他1901年赴上海后,更是思想日进,甚至信奉了无政府主义。当然,蔡元培有关思想自由的大学理念的形成,是在1907年留学德国之后;当他1913年旅居法国之后,通过倡导留法勤工俭学、组织华法教育会等活动,更使这种理念得以充实。所以说,蔡元培思想自由的大学理念,主要源自对欧洲文化、教育的认同和理解。
这种思想自由的理念,较早萌生于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兴起。当康德的心物二元论哲学定型后,重视理性、肯定个性和个人价值、维护人的自由等理念,便开始成为教育信条。洪堡服膺康德学说,并将其运用于柏林大学的创办之中,从而更为看重科学研究的价值,并从制度上保障了思想自由的权利。洪堡指出:“大学应视科学为一尚未完全解答之问题,因而始终处于探索之中。”(28)换言之,大学办理必须秉持“学术无禁区”信念。正由于洪堡为大学植入了自由研究的内核,所以一般认为,真正意义的现代大学起源于德国。蔡元培在留德的近4年时间里,深受这种大学理念的影响。或许可以这样假设,设若他不是以“中国的洪堡”自期,便不可能以曾任总长之身而出任北京大学校长。
蔡元培出长北京大学后,便以思想自由为“第一主义”,尽力培植早已沦丧的学术元气。他引入各家各派的学说,并听任其自由争鸣;除活跃课堂教学外,还尽力提倡社团活动。他认为,大学之“大”,实在于“有容乃大”;而有容之“容”,便表现为信奉“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通理。他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有言:“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29)
这种有容,还使“兼容并包”成为了“第一主张”。引新而不去旧,相反而实相成,实际成为了蔡元培的治校哲学。当他聘请梁漱溟来北京大学讲授印度哲学时,梁漱溟因蔡元培支持新文化运动而不无愤激地表示:“我这次进北大,除替释迦、孔子发挥而外,不再作旁的事。”而蔡元培却不以为意,连连笑着回答道:“好的,好的,北京大学需要多多研究各家各派学说的人。”(30)再,蔡元培本对马克思主义敬谢不敏,然而却能引进陈独秀、李大钊,并支持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发起成立“马客士研究会”,使北京大学成为最早接受和传播马列主义的阵地。凡此种种,均与中国传统的办学思想大异其趣,说明其大学理念具备了深厚的学术内涵。
其二为“囊括大典,网罗众家”。这与兼容并包主张密切相关,但又不尽相同。这种大学理念,即认大学为“大师”的汇聚之所,而并非兼容不学无术、鸡鸣狗盗之徒的机构。大学当罗致各派精英,并听任百家争鸣。现今所记取者,多为清华校长梅贻琦的相关论述。其实,早在1918年,蔡元培便明确指出:“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31)蔡元培出长北京大学后,文科聘请了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等,理科聘请了李四光、王星拱、任鸿隽、李书华、朱家骅、颜任光等,法科聘请了马寅初、陶孟和、高一涵、周鲠生、陈启修等;均极一时之选,并使教授年龄迅速年轻化,从而使校风大变,并以充满朝气与活力著称。
前已言及,蔡元培的兼容并包,还表现在引新并非绝对去旧上。如辜鸿铭虽长于英国文学,但因其倡言复辟论而引发社会舆论大哗;刘师培虽长于古文经学,但因其有变节的历史污点,又参与了“筹安会”的发起,故为世人所不齿;黄侃虽以“小学”名家,且以提倡“选学”而获誉,但他明确反对白话文,并处处与新文化运动作对;他如陈汉章、崔适等人,也因思想陈旧、教法古板等,不仅社会上多有非议,而且校内学生也吁请去之。蔡元培不为所动,并在《答林琴南君函》中,以公开信形式陈述了自己的师资聘用原则:“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在校讲授,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譬如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则听之。筹安会之发起人,清议所指为罪人也。本校教员中有其人,以其所授为古代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嫖、赌、娶妾等事,本校进德会所戒也。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狎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且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32)这里所言“第一种之主张”,便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里所言“进德会”,为北京大学师生所共组的修德团体,由蔡元培发起并担任会长。这种以“学诣”为主的聘师原则,实重“经师”,而对“人师”未作公同要求。这与中国传统的师资观也是大相径庭的。
既然要纳新,便必须吐故。蔡元培所秉持的裁汰原则,当然也是以“学诣为主”。对于不学无术的专任教员和滥竽充数的兼职教员,蔡元培依据自己的大学理念,毫不留情地予以辞退。即使对于外国教员,蔡元培也能顶住各方面的压力,不惧威胁地予以解聘。他在《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一文中忆及:“有一法国教习要控告我;有一英国教习,竟要求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来同我谈判,我不答应,朱尔典出去后说:‘蔡元培是不要再做校长的了。’我也一笑置之。”(33)看来,蔡元培为给名师腾出位置,宁可开罪达官显贵。
其三为“研究高深学问”。这既是对教师的要求,同时又是对学生的要求;如果从教育“专为将来”而论,则更是寄望于学生。蔡元培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中,首先要求学生“抱定宗旨”。他说:“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定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肄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他接着告诫说:“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34)换言之,大学并非官僚养成所和职业训练所,而是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它与功利主义的价值追求同道而异质。这种大学理念,看重内在的精神追求,即热衷于批判性思维和哲理性建构;这种大学理念,正是由蔡元培的学术观所派生,它赋予了大学发展知识和创新理论的根本任务,从而可能整合社会理智,并重塑民族文化。
分析这种大学理念,无疑是“精英教育”而非“通才教育”,是“古今中外”的教育而非“抱残守缺”的教育。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有言:“所谓大学者,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造成一毕业生之资格而已也,实以是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研究者也,非徒输入欧化,而必于欧化之中为更进之发明;非徒保存国粹,而必以科学方法,揭国粹之真相。”(35)这种“学术研究共同体”,必以“师生共同体”或“教学共同体”为基础;在这个阶段,教师宜称为“导师”,他并非仅仅以授课为职责,还应作为一个指路的人,并尽力激发学生的研究兴味。为此,大学应设立研究所或研究院,以此为共同研究提供合适的组织形式。
为了追求高深学问,大学教育宜以学生的自主和自动为前提。在此项原则之中,蔡元培的大学理念,颇与中国古代的“书院精神”相合。1921年8月,毛泽东等人在长沙船山学社旧址创设了湖南自修大学。当蔡元培接读《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后,认为该校“全与我的理想相合”,表示“我欢喜得了不得”。在《湖南自修大学介绍与说明》中,蔡元培指出:“大学所以难办的缘故,因为筹备大学的人把他的性质看错了。大学本来以专门研究为本位,所有分班讲授,不过指导研究的作用。”他虽肯定了该校“采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科学术”的办学宗旨,但却认为该校的基本精神在于:“以学者自力研究为本旨,学术之外无他鹄的,合吾国书院与西洋研究所之长而活用之。”(36)他以“研究所制”置换“学校制”的深意,即在于大学应首重学术研究而非知识传授。
其四为“实行超然的教育”。在前文介绍“学术独立论”时,已介绍了蔡元培教育应独立于政治和宗教的观点,并兼及大学院制与大学区制的试行。在此所要补充介绍的是,他在《教育独立议》中所设计的“超然教育”方案。
蔡元培保障教育独立的具体“办法”为:(1)“分全国为若干大学区,每区立一大学”;大学既负责学术研究,也负各级各类教育的实行之责。(2)“大学事务,都由大学教授所组织的教育委员会主持。大学校长,也由委员会举出。”即实行“教授治校”,校长也不得由政府任命。(3)“由各大学校长组织高等教育会议,办理各大学区互相关系的事务。”即实行大学自治,用以排除政治、宗教等纷扰。(4)教育部仅为执行机构,用以专门“办理高等教育会议所议决事务之有关系于中央政府者”,它“不得干涉各大学区事务。教育总长必经高等教育会议承认,不受政党、内阁更迭的影响”。(5)“大学中,不必设神学科”;“各学校中,均不得有宣传教义的课程,不得举行祈祷式”;“以传教为业的人,不必参与教育事业”。(6)“各区教育经费,都从本区中抽税充用。较为贫乏的区,经高等教育会议议决后,得由中央政府拨国家税补助。”(37)这套办法,是将法国、美国、德国诸制截长补短、参酌并用的结果。
分析这套办法,前四项,是使教育独立于政治的保证;第五项,是教育独立于宗教的保证;至于第六项,则是保障教育经费,以使其不被挪用的保证。总之,它所必须保障的,便是大学的独立精神。在蔡元培看来,大学的“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是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所以,他总是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左冲右突,即使每每是无功而返,他也无怨无悔。客观说来,试图实行这种超然教育,无疑“过于理想”,尤其是在那动乱和经济不发达的年代。但是,在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了的社会中,蔡元培的学术追求和教育理想是否依旧不具备实践价值呢?这确实是一个值得认真思索并给出回答的问题。
笔者认为,蔡元培的学术观,点中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命门。中国传统文化属依附型文化,唯政治之马首是瞻。它不仅缺乏“民主”和“科学”的因子,甚至还缺乏“艺术”或“美学”的元素;它所更为缺乏的,还有高屋建瓴的哲学思辨,以及毫不护短的自我批判精神。正是这种学术的缺陷和短视,阉割了教育的创新精神,使中国文化的土壤上,不可能萌生出现代意义的大学。而当西方的大学制度移植到中国来之后,不仅有土壤的不适,更有政治骄阳的过度和经济雨露的不足,因而便难免会有“南橘北枳”之讥。当中国当代大学认识到学术性、法人化和研究型的价值时,已准备迈出“去行政化”的一步。这固然可喜,然而若想取得长足的进步,窃以为,还须从重温蔡元培的相关主张做起。前一段炒得沸沸扬扬的所谓“钱学森难题”,其实蔡元培早已给出了答案。若以世界和亚洲的视野观之,今日北京大学的学术地位,未必便超越了蔡元培主校时的北京大学。当时的北京大学,似乎距“第一流的大学”还不算太远;而现今的北京大学,无论怎样高调地宣传,却难以拉近这掉队的距离。这近一个世纪的时间“虚掷”,难道便换不回那必需的良知和理性,难道还能继续容忍那明知不对的踟蹰、等待和犹疑么!
注释
①⑦⑨⑩(22) (23) (24)(36)(37)高平叔主编:《蔡元培全集》(4),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351页,第481页,第42页,第42-43页,第179页,第177页,第177-178页,第247页,第178页。
②(14)王栻主编:《严复集》(1),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3页,第52页。
③⑤(33)高平叔主编:《蔡元培全集》(6),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490页,第16页,第351页。
④ (13) (16) (17) (21) (29) (31) (32) (34) (35) 高 平 叔 主 编 :《蔡 元 培 全 集 》(3),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39-140页,第198页,第149-150页,第113页,第297-298页,第211页,第211页,第271页,第5页,第210页。
⑥(15)(19)高平叔主编:《蔡元培全集》(7),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97页,第497页,第313页。
⑧(11)(12)(18)高平叔主编:《蔡元培全集》(2),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33页,第132-133页,第135页,第137页。
(20)周天度:《蔡元培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86页。
(25)高平叔主编:《蔡元培全集》(5),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16页。
(26)翁文灏:《追念蔡孑民先生》,《中央日报》(重庆)1940年3月24日。
(27)高平叔主编:《蔡元培全集》(1),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65页。
(28)转引自陈洪捷:《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大学的影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页。
(30)汪东林:《梁漱溟答问录》,长沙:湖南出版社,1998年,第40页。
责任编辑曾新
2010-0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