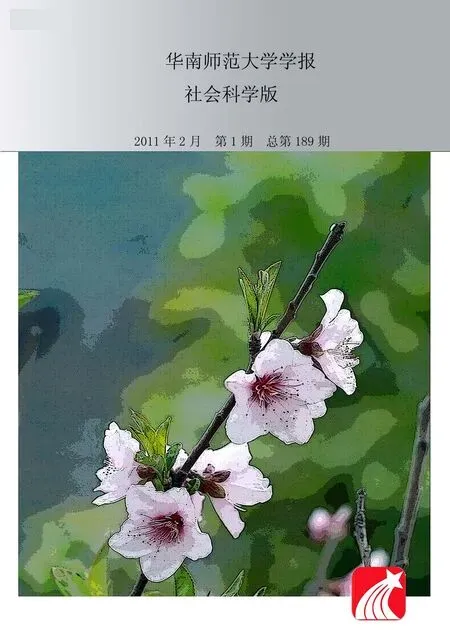互惠的还是整体的:WTO义务的性质
许 楚 敬
(华南师范大学 法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关于世界贸易组织(WTO)条约义务的性质,有学者比如约斯特·鲍威林(Joost Pauwelyn)将其区分为互惠的和整体的,认为大多数WTO义务都是互惠的,WTO义务是由许多双边和互惠的义务堆积起来的总和。他还根据这种互惠-整体的区分,得出结论认为若干WTO成员方可以彼此间修改WTO协定。[注]所谓彼此间修改(inter se modifications),是指多边条约的若干当事国缔结协定在它们之间修改该多边条约;所谓WTO协定,泛指所有WTO的涵盖协定(covered agreements),即《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附录1所列的各项协定。下文中提到的《WTO协定》系指《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一、国际公法关于条约义务性质的分类及其影响
国际公法中条约义务性质的分类一般认为是20世纪50年代杰拉尔德·菲茨莫里斯(Gerald Fitzmaurice)提出来的。菲茨莫里斯根据违反条约产生的结果,把条约分为双边条约和多边条约,并进一步把多边条约的义务区分为三类:(1)互惠(reciprocal)性质的义务;(2)相互依存(interdependent)性质的义务;(3)整体(integral)性质的义务。[1]
双边条约只涉及义务的简单交换,任何一方可以中止或终止,后来与其不一致的条约是有效的。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互惠型的多边条约的情形。相比之下,相互依存型的多边条约涉及缔约国之间利益的相互交换,任何一方为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可以中止或终止。[2] 27, 28其后与之不一致的条约是无效的。互惠的条约中规定的义务,可以概括为一个双边的国与国的关系。196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被认为是一个“互惠的”条约的例子。在“相互依存的”这类条约中,义务并非纯粹双边的,而一方的义务的履行取决于所有其他各方。每当一方违反其义务,他一定违反了对所有其他当事方的义务,并且进一步履行义务将没有多大意义。“整体的”条约义务的约束性质是独立存在的、固有的和绝对的。这种条约不能概括为国家对国家的义务,也不取决于其他当事方的履行。这类条约不能中止或终止。[2]28其后与之不一致的条约也是无效的。1948年《种族灭绝公约》可作为一个“整体的”条约的例子。
上述分类虽未被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以下简称“维也纳公约”)采用,但在公约中的某些条款可以找到其“踪迹”。根据维也纳公约,条约义务性质的分类产生了许多重要影响。修改“相互依存的”,特别是“整体的”条约的彼此间协定最有可能影响第三方的权利,以及不符合“整个条约的目的和宗旨的有效实现”。相反,修改“互惠的”协定的彼此间协定,则不容易产生这样的效果。这些“相互依存的”或“整体的”条约的彼此间修改可能难以通过维也纳公约第41条的测试。[3]因此,如果把WTO条约义务归类为双边性质,将导致对国家有权质疑违反义务的资格的限制,限制国家报复的权利。另一方面,如果把WTO条约义务归类为整体的或集体的性质,将导致一些相反的结果。[4] 420
二、WTO义务既具有互惠性又具有整体性
关于WTO义务的性质,鲍威林提出了一个独特的观点。鲍威林认为,大多数的WTO义务是双边的、互惠的,而不是整体的。他的主要论点是,WTO义务的目的是贸易,而贸易是在每两个国家之间产生预期效果的,是一个双边的事件。[5] 71因而是可辨认的、可分开的和可确定的。
鲍威林的结论是,WTO义务是双边义务,尽管他认为一些WTO义务,特别是那些管理型的义务具有某些集体(collective)性质。[6]作为一个法律制度,WTO法是有别于国际公法的其他分支,如人权条约和国际环境协定,这些其他分支的权利和义务是“整体的”,因为它们追求“集体的”或“普遍的(universal)”价值或“全球共有物(global commons)”。[5] 71, 72-73鲍威林认为,不像禁止灭绝种族、人权保护或环境保护,贸易和贸易自由化并不是一个价值。[5] 73违反WTO的贸易规则可能会影响到许多成员的权利,但它并不等同于违反所有成员方的集体权利或良知,而违反人权则不然。[5] 72因此,不论其他多边伙伴的意见如何,若干成员方彼此之间修改WTO条约应该被接受,只要不影响第三方的权利和义务。[5] 74而“整体的”义务则不得修改。
但是,鲍威林论点的基本前提是难以接受的。他的基本前提是,相对于国际公法的其他分支,如人权条约和国际环境协定,它们追求普遍的目标,享有权利和义务的“整体的”性质;而WTO法则处于相对低级的法律地位。这样的前提设定,自然就容易产生他所设想的国际公法各分支之间的冲突了。这些高级的规范也就可经常渗入低级的WTO法,为违反WTO法辩解了。[7]300
其实,从防止战争、保护和促进人权的角度看,贸易自由化本身可以要求自己的价值。关贸总协定产生的成因就是由于加速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的两次战争之间悲惨的“经济巴尔干化(economic balkanization)”。同样,“综合的、更可行的、持久的”多边贸易体制本身就是一个“全球共有物”。全球性的“个人福利增加的累积”本身,也足以赋予WTO规范集体的和普遍的性质。[7]301
WTO义务本身不仅关涉贸易,更关涉政府对与贸易有关的行为的预期。这些义务是无法量化的、不可分的,因而性质上基本是统一的。它们不能被视为双边的,而且应被认为是集体性质的。[4]419其理由是,WTO义务是一个WTO成员方对所有其他WTO成员方负担的义务。GATT第1条规定了最惠国待遇的义务。基于最惠国待遇,WTO成员方承诺把它们与贸易有关的利益、优惠、特权或豁免的最优惠待遇立即和无条件地扩展至WTO所有其他成员方。根据《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DSU)第19.1条,如果WTO专家组或上诉机构认定一WTO成员方的国内措施与一涵盖协定不一致,则应建议有关成员方使该措施符合该协定。这是基于所有WTO成员均负有遵守WTO协定,使其国内措施符合WTO协定的相同的集体义务。[注]《WTO协定》第16.4条规定:“每一成员应保证其法律、法规和行政程序与所附各协定对其规定的义务相一致。”
至于人权条约或多边环境协定中徒有虚名的 “整体的”义务,它们并非总是如此。事实上,并非每一个人权清单中的项目都应该获得普遍义务的光环。大多数人权条约缔约国数目有限,其清单中的更多项目是有争议的。同样,许多人权条约还没有得到批准。即使得到批准,排除这些“整体的”义务的保留条款,也比比皆是。[8]此外,将实体的非贸易的国际法纳入WTO法,可能违背WTO当事各方的意图,对实现人权和环境的目标,可能适得其反。非贸易的目标并非与WTO法的发展毫无关系,因为WTO协定的谈判者可能打算以贸易自由化作为一个减少贫困和改善全球福利(尽管它可能对环境产生不利影响)的工具。[9]126-127鲍威林倡导的人权义务优先于WTO法,把WTO以外的问题纳入WTO领域,将减损WTO法,并使WTO成为解决所有国际问题的场所,这与WTO只是一个管辖世界贸易的组织所扮演的角色相去甚远。[9] 130
三、区分WTO义务的互惠性或整体性没有意义
除了强行法,在国际法中没有固有的规范等级,包括条约与习惯之间。贸易法与人权法、环境法、海洋法等不同领域之间的规范,并不存在位阶高低的问题,更不存在人权法、环境法规范优于WTO法的问题,除非WTO条约对其与其他国际法之间的关系作出明确的规定。从条约的当事国必须善意履行条约规定义务的角度来说,所有条约义务都是平等的。*除了《联合国宪章》第103条。该条规定:“联合国会员国在本宪章下之义务与其依任何其他国际协定所负之义务有冲突时,其在本宪章下之义务应居优先。”一个国家不能援引其在另一条约下的义务来对抗其必须履行的条约义务,否则,就必须承担国家责任。因此WTO各成员方不得以其必须履行人权条约或多边环境条约下的义务为由,违反WTO协定的规定。在不同的条约规范之间区分条约义务的性质为互惠的或整体的,以决定哪项规范优先,实属异想天开。以WTO义务的互惠性或整体性的区分,作为彼此间修改WTO协定的依据,更是不足为凭。
笔者认为,WTO的义务既是互惠(互利)的,更是整体的。只看到WTO义务互惠的一面,而忽视了其整体的一面,是典型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或“一叶鄣目,不见泰山”的一种片面的观点。《WTO协定》序言中规定“期望通过达成互惠互利安排,实质性削减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消除国际贸易关系中的歧视待遇,从而为实现这些目标做出贡献,因此决定建立一个完整的、更可行的和持久的多边贸易体制”,似乎已经高度概括了WTO义务的性质。WTO义务不是一系列双边义务的简单总和,而是一个整体。通过这种“互惠互利的安排”,建立“一个完整的、更可行的和持久的多边贸易体制”。
因此,为了彼此间修改WTO协定的目的,把WTO的义务区分为互惠或整体,是徒劳的、毫无意义的。由于WTO义务是整体的,在若干WTO成员方彼此间修改WTO协定可能难以通过维也纳公约第41条的测试,这种行为将损害“整个WTO条约的目的和宗旨的有效实现”。WTO成员方必须善意履行WTO义务,“以提高生活水平、保证充分就业、保证实际收入和有效需求的大幅稳定增长以及扩大货物和服务的生产和贸易为目的”,“同时……寻求既保护和维护环境,又以与它们各自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需要和关注相一致的方式,加强为此采取的措施”。也就是说,追求环境保护、人权保护的价值本身是值得提倡的,但是必须以与各国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需要和关注相一致的方式进行。
总之,每个WTO成员方都应遵守和履行WTO的多边义务,而不是在享受WTO多边贸易体制带来的好处的同时,却以“WTO义务的性质是互惠的”为理由或借口,违背WTO协定。即使这样做可能是为了追求人权或环境的价值,也是不被允许的,除非经过WTO各成员方多边谈判,并达成共识。
参考文献:
[1] FITZMAURICE, GERALD. Yearbook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1958, II), UN Doc. A/CN.4/SER.A/1958/Add.1.
[2] FITZMAURICE, GERALD. Yearbook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1958, II), UN Doc.A/CN.4/115.
[3] PAUWELYN, JOOST. The Role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WTO: How Far Can We Go?.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01, 95 (3): 549.
[4] CARMODY, CHIOS. WTO Obligations as Collectiv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06, 17 (2).
[5] PAUWELYN, JOOST. Conflict of Norms in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How WTO Law Relates to other Ru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6] PAUWELYN, JOOST. A Typology of Multilateral Treaty Obligation: Are WTO Obligations Bilateral or Collective in Natur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03, 14 (5): 950.
[7] CHO, SUNGJOON. WTO's Identity Crisis - Review of Conflict of Norms in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How WTO Law Relates to Other Ru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By Joost Pauwelyn. World Trade Review, 2006, 5 (2).
[8] MINNOW, MARTHA. What is the Greatest Evil?. Harvard Law Review, 2005, 118 (7): 2134, 2156-2157.
[9] WORSTER, WILLIAM THOMAS. Competition and Comity in the Fragment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Brookly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08, 34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