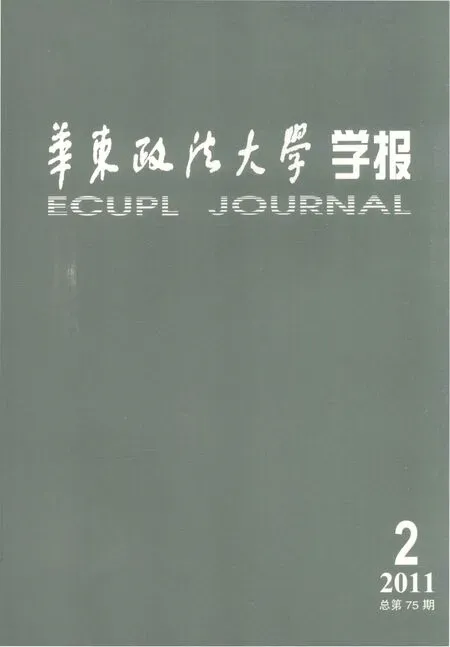珍视传统的革命家:从董老研究资料的搜集说起
苏亦工
珍视传统的革命家:从董老研究资料的搜集说起
苏亦工*
最近几年里,笔者对董老法律思想的研究进展甚微,主要原因还是资料不足,因此笔者把注意力集中在搜集资料上。尽管这方面的工作也是收获甚微,但还是想就此做一交流。
有关董老研究资料的搜集,就笔者所见,值得一提的有以下几项。第一件是1929年12月31日《董必武给何叔衡的信》,〔1〕编者加标题为《关于一大的回忆》,载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3辑(内部发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2页。原存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文件中。查业经出版的几部董老文集均未收录,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的《董必武年谱》(第99页)提到了此信。〔2〕目前出版的董老文集分别有聂菊荪、鲁明健等编:《(董必武)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及选集、年谱、传略编辑组编辑的《董必武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董必武政治法律文集》(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董必武统一战线文集》(法律出版社1990年版),还有后来出版的董必武法学文集编辑组编的《董必武法学文集》(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该信的内容比较简短,主要是回忆中共一大会议的情况,信中说一大会议没有宣言,“只向国际作了一个中国情形的报告。报告是李汉俊和董必武起的草,经大会通过”。据编者注,该报告的中文原稿没有看到。第二件是《杨兆龙法学文选》收录了一封杨兆龙《致最高法院董必武院长的一封信》,标题为《关于社会主义立法的若干问题》,据该书编者注说:“杨兆龙教授早在1950年全国首届司法工作会议上,经最高法院副院长张志让介绍与董老会晤,畅谈中国的法制建设问题,深得董老赏识,当即任命他到上海去出任东吴法学院院长一职。1957年下旬,杨兆龙教授就社会主义立法的若干问题,草拟了一封致当时的最高法院院长董必武的信。本想由《新闻日报》记者陈伟斯通过该报驻京办事处转送最高法院,但此信被截留。原件被砍头去尾作为‘反面教材’见于1958年《法学》第1期傅季重的批判文章的附注里,至今鲜为人知。”〔3〕郝铁川、陆锦碧编:《杨兆龙法学文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6页。关于杨兆龙的“右派”言论,可参见复旦大学校刊编辑室编:《毒草集——批判右派思想言论选辑之一》,1957年版(其他出版信息不详),第30-37页。第三件是1957年5月董老为国务院法制局法制史研究室编纂的《中国法制史参考书目简介》撰写的题词,全文为:“这本《书目简介》的编著,只是整理我国法制史资料的开端。希望有志这门学问的人赓续前进,扩展法制史的研究工作。”〔4〕国务院法制局(法制史研究室)编:《中国法制史参考书目简介》,法律出版社1957年版,书前墨迹。这段简短的文字以墨笔手迹的形式载于该书版权页之后,其性质介于题词和书序之间。全文虽然不过寥寥47字(不计标点符号),但从中仍能看出董老对我国固有法制及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视。
此外,笔者本人组织了两次采访:一次是2003年春季采访原最高法院副院长王怀安同志;另一次是同年冬季采访原最高法院副院长邢亦民同志。两份采访的实录均由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生孙琦整理撰稿,经笔者修订后分别发表于《环球法律评论》2003年夏季号和2004年夏季号。在这两份访谈录中,受访者都提到了有关董老的情况,可视为重要的口碑资料,用现在流行的说法叫做“口述历史”。注重和加强口述历史或口碑资料的调查、搜集和整理,在当前具有特别的紧迫性。许多曾经与董老共同生活和工作的同志,目前年事已高。光阴荏苒,这项工作如不抓紧,许多材料就很可能会永久湮灭。那不仅非常遗憾,也使我们丧失了更多了解历史的机会。
以上笔者介绍的那几件散见的材料,可以说并没有提供多少关于董老研究的充足信息,各材料之间也缺乏联系性,因此也不可能单凭这几个材料作出什么系统的研究,但是对这些材料的搜罗还是能给我们提供一些启示。
其一,研究董老的法律思想,不能把眼光局限于已经出版的各类董老文集上。搜集有关董老的研究资料,在有关档案正式解密之前,也不能指望有什么集中的、大规模的发现。但是,我们的研究工作不能静候等待,必须拓宽眼界,从点滴做起。譬如上面提到的《董必武给何叔衡的信》、杨兆龙致董老的信以及董老为《中国法制史书目简介》撰写的题词,都不见于各类董老文集之中,但其中提供的信息对研究董老的生平和思想还是非常重要的。为此我们必须把眼界放宽到其他国内外已经和尚未出版的各类文献上,大海捞针,有时也可能会淘沙见宝。
其二,我们不能忽视间接材料和旁证材料的搜集和利用。所谓间接材料和旁证材料,即并非直接涉及到董老但可能会对研究董老提供重要线索或帮助和启发的材料。譬如董老自幼受过良好的国学教育,1903年中秀才,后又东渡日本求学,并曾追随孙中山先生投身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前后,受新文化运动和俄国十月革命影响,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并投身革命事业。中共党内有许多老一辈革命家,譬如著名的“延安五老”(或十老),有着与董老相同或相似的经历,在思想、见解和情感上肯定也会有许多相通之处。因此我们研究董老的时候,不能忽视对他们的研究。
总之,通过对上述零星散见材料的发掘整理并结合既往已公布的资料加以研究,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一种认识:董老作为老一辈革命家和中共高层领导人,尽管在赞成和支持革命这一点上与他同时代的主流革命家有着共同之处;但是在如何对待法制、秩序和传统文化的问题上,却又与他同时代的主流革命家有着许多不同之处。
刚刚过去的20世纪,对中国来说堪称是一个疾风暴雨的革命世纪。在面对法制、秩序和传统文化时,主流的革命思潮可以概括为蔑视和破坏。
1928年春,井冈山的工农红军出击湘南至桂东县,4月初一,在该县沙田圩召开军民大会,毛泽东亲自撰写了一幅对联:“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新社会建设光明灿烂。”〔5〕胡为雄:《诗国盟主毛泽东》,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第235页。以后的半个世纪里,他确实如这幅对联的上联所说的那样,将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他不但领导中国共产党人推翻了旧政权,也砸烂了中国的旧文化,甚至连新中国成立后尚在草创且远未成型的法律和秩序,也被他发动的一连串政治运动冲击得支离破碎。
梁漱溟先生曾经指出:“我固早知在毛主席思想体系中,法律只是施政的工具,非其所重。此其例甚多。即如清季有法律学堂,民国初年有法政专门学校,今毛主席却不沿用‘法政’一词,而必曰‘政法’者,正谓无产阶级专政为主,固非若近世欧美立宪国家宪法高于一切也……此在理论上未尝〔不〕自成一说。毛主席《论人民民主专政》(见毛选第四卷)一文中有云:‘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坦率无饰,要亦无需乎掩饰耳。但建国初期中央各部院犹有司法部,史良任部长,后来便裁撤了。至今有各级法院之设,而事务甚清简。社会上有不少问题皆由公安部门以行政处分处理之。”〔6〕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7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29、430页。这是梁漱溟先生1977年2月22日访问雷洁琼女士后撰写的文章,其访问的目的在于以他自己对毛泽东法律观的所见寻求雷洁琼的印证。
毛泽东在1958年8月21日下午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也说过:“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民法刑法那样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我们基本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7〕《毛泽东思想万岁(1958-1960)》,出版信息不详,第109页;又见碧波:《法治:建国路上的两难选择》,载《炎黄春秋》2004年第2期。
英国著名政治理论家柏克对1789年法国大革命持否定和批判的态度。在他看来,法国大革命的暴力把一切美好的传统都摧毁了,并且从根本上“动摇了社会秩序和自由的基础,以及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一切美好的事物和人类文明的瑰宝。他预言这种毁灭性的破坏终将导致一种新的专制主义强权的出现,唯有它才能够维持社会免于全面的混乱和崩溃。而且这种专制主义还必然会蔓延到法国境外的整个欧洲。不久以后,拿破仑之登上舞台及其所建立的欧洲政治霸权,似乎是完全证实了他的预言。”据说,“这是历史学史上最罕见的准确预言之一”。〔8〕参见[英]柏克:《法国革命论·译者序言》,何兆武等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vii、iv页。不过,向称保守的柏克并非一味地反对革命,他赞成英、美的革命。因为在他看来:“英美的革命是以发扬传统中的美好的价值为目的的。”〔9〕参见[英]柏克:《法国革命论·译者序言》,何兆武等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vii页。
在如何看待革命的问题上,董老未必会同意柏克的见解;但是在珍视传统这一点上,董老肯定能与柏克产生共鸣。1949年以后,董老长期主持政法工作,他的基本主张就是尽快建立起法制和秩序,这也可以说是他后半生所追求的目标。对此,笔者曾有专文做过论述。〔10〕参见苏亦工:《开国前后的民主法治构想及其中辍——纪念董必武同志诞辰115周年》,载祝铭山、孙琬钟主编:《董必武法学思想研究文集》,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版。本文前面提到那些零星材料,正可以进一步加强和印证笔者以往的观点。
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董老也表现出了极大的同情,甚至可以说是温情,这就使他迥异于他同时代的主流革命家们。1965年1月,董老在游览成都武侯祠时,题写了一幅匾联:“三顾频繁天下计;一番晤对古今情。”上联是摘录杜甫诗《蜀相》中的原句,下联是董老对这段古今传为佳话的历史故事的由衷赞美。董老用一个“情”字联结古今,正反映出他对中国传统和中国文化的深情。在今湖北省罗田县城东北有一座坟茔,是近代著名方志学家、原武汉大学教授王葆心(1867-1944年)先生的墓地。墓前立有大理石碑及墓志3方,两侧石柱上刻有董老题写的挽联“楚国以为宝今人失所师”。上联所说的“楚国以为宝”系借自儒家经典《大学》中的典故:“《楚书》曰:‘楚国无以为宝,惟善以为宝。’”下联则似乎是叹惜今人失去了旧时代的文化大师。而该墓碑树立的时间,正是中国知识分子遭到严厉整肃的1957年。从这两组联语中,我们可以隐约窥见董老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真挚情感。笔者以为,这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家所应有的胸怀。
一场革命是否真的有益于一个社会的健康发展乃至人类的解放,或许并不在于它对传统的破坏,而在于对传统的扬弃,即扬善弃恶。中国拥有五六千年的文明传统,如此悠久的文化积淀,不可能没有糟粕,但也不可能尽是糟粕。而且,即便是糟粕,也未必没有化腐朽为神奇的可能性,简单地砸烂和抛弃均非可取之道。
关于传统和糟粕,楼宇烈先生说得很好:“我们常讲,对于传统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那什么是糟粕,什么是精华?这都要根据我们的现代社会而定,而且你说是糟粕,不一定的,你说是精华,也不一定的。为什么呢?精华的东西到了今人的手里面一用就变成糟粕,糟粕的东西通过今人运用也可能是精华。我这样一说,可能有人会认为是没有标准。那事实上就是这样啦,腐朽可以化为神奇,神奇也可以化为腐朽,关键的是今人如何去把握它,如何去运用它。所以我们不能赖我们的历史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多的包袱,那是因为我们今天的人不善于去运用它。今天的法治民主,都是我们今天实在的文化,在传统的文化中间是不会有今天的这些东西的,但是今天的东西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开发出来的。既然西方在走向近代的过程中,他们运用自己的传统希腊罗马的文化以及中国的传统——他们从中国这儿吸取到人本精神去抵制西方自己的神本精神、神本主义的东西,然后开发出了近代的这种理性主义的时代。这并不是说拿来就用,而是经过了消化开发的。既然西方人可以把我们传统的东西运用到现代,变成了现代的民主,为什么中国人就不能从自己传统的东西中开发出现代的东西来呢?现成拿过来是不可能的,传统的东西里面没有现成的现代的东西,必须要经过现代人的转化才可以。所以这个责任都在我们现代人的身上,简单地去区分糟粕与精华并不是一个好的办法,关键在于我们今天的人把这些东西如何转化。”〔11〕《中国政法大学学报》编辑部整理:《“中国文化与现代法治”对话录》,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
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中讲过一段名言:“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12〕中国基督教协会、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印发:《新旧约全书》,《马太福音》5:17-5:18。我想,董老投身革命的目的,或许正像耶稣·基督说的那样,并非是要废弃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法制,而是要“成全”!所谓“成全”,我的理解,即如楼宇烈先生所说,就是要从中国传统中转化和开发出符合现代精神的东西来,这就叫化腐朽为神奇。
(责任编辑:李秀清)
*苏亦工,清华大学教授,法学博士。本文系2010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华法制文明的传统与创新”(项目号10JZD002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