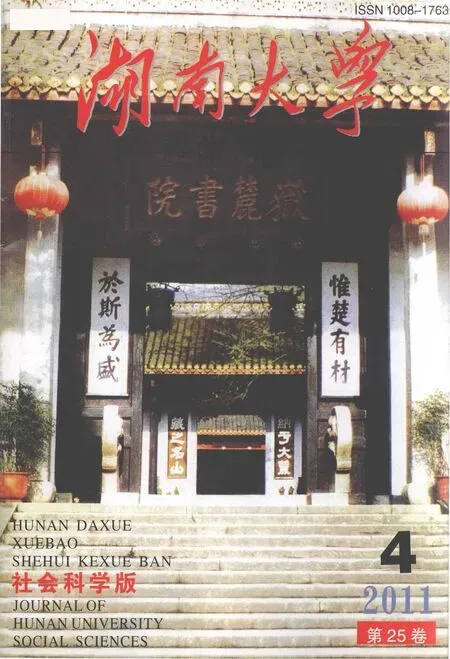从书写方式推测《史记·乐书》的来源*——兼说《乐记》成书的时代*
杨合林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南长沙 410081)
从书写方式推测《史记·乐书》的来源*
——兼说《乐记》成书的时代*
杨合林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南长沙 410081)
《乐记》现存两个文本,即《礼记·乐记》和《史记·乐书》。通过比较发现,两文本间文字书写多有不同,但《乐书》与《史记》的书写方式却有高度的一致性。由此可推测今本《乐书》虽是由后人补入《史记》的,但其中的《乐记》文本却有可能曾为司马迁所亲见并经手,或为司马迁为撰写《乐书》收集、准备的原始资料。这表明《乐记》应是传自先秦的一种关于礼乐文化的古文献,《乐记》在西汉多本并存、分途传播的事实也可证明此点。
《乐书》;《史记》;书写方式;来源
一 《史记·乐书》的书写方式
《乐记》现存两种文本,即《礼记·乐记》和《史记·乐书》通过对这两种文本的比对,发现二者文字上存在不少差异。进一步考察又发现,《乐书》与《史记》的文字书写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也就是说,《乐书》与《礼记·乐记》相异之处,莫不与《史记》相合,并且有着惊人的一致。请看:
《礼记 ·乐记》:“性之欲也。”[1](P1529)《乐书》作“性之颂也”。[2](P1186)《史记集解》:“徐广曰:颂 ,音容。”颂、容古通,《史记》常写作颂。《战国策·赵策三》:“世以鲍焦无从容而死者,皆非也。”[3](P736)《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作“世以鲍焦无从颂而死者,皆非也”。《史记索隐》:“从颂者,从容也。”
《礼记·乐记》:“是故强者胁弱。”《乐书》作“是故彊者胁弱”。《史记》强一般写作彊,《左传·哀公十五年》:“迫孔悝于厕,强盟之,遂劫以登台。”[4](P2175)《史记·卫康叔世家》作“劫悝于厕,彊盟之,遂劫以登台”。《战国策·东周策》:“韩强与周地。”《史记·周本纪》作“韩彊与周地”。《韩非子·难三》:“今时韩魏孰与始强。”《史记·魏世家》作“今时韩魏与始孰彊”。《楚辞·九章·怀沙》:“抑心而自强。”《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作“抑心而自彊”,宋人洪兴祖《楚辞补注》:“强,《史记》作彊。”[5](P144)
《礼记·乐记》:“老幼孤独不得其所。”《乐书》作“老幼孤寡不得其所”。《尚书·周书·洪范》:“无虐茕独而畏高明。”[6](P190)《史记·宋微子世家》:“毋侮鳏寡而畏高明。”“独”写作“寡”,《乐书》与《史记》相一致。
《礼记·乐记》:“屈伸俯仰。”《乐书》作“诎信俯仰”。《史记》屈多作诎,《老子》四十五章:“大直若屈。”《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作“大直若诎”。《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曲而不屈。”《史记·吴太伯世家》作“曲而不诎”。《战国策·西周策》:“我不能教子支左屈右。”《史记·周本纪》作“非吾能教子支左诎右也”。《楚辞·九章·怀沙》:“冤屈而自抑。”《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作“俛诎以自抑”,《楚辞补注》:“《史记》云:俛诎以自抑。”[5](P142)
《礼记·乐记》:“屈伸俯仰。”《乐书》作“诎信俯仰”。《史记》伸作信,《战国策·秦策四》:“不伸威。”《史记·春申君列传》作“不信威”。按,《礼记·儒行》:“竟信其志。”郑注:“信读如屈伸之伸,假借字也。”
《礼记·乐记》:“男女无辨则乱升。”《乐书》作“男女无别则乱登”。《史记》升多作登,《尚书·商书·高宗肜日》:“有飞雉升鼎耳而雊。”《史记·殷本纪》作“有飞雉登鼎耳而呴”。《尚书·周书·文侯之命》:“昭升于上。”《史记·晋世家》作“昭登于上”。按,《典引》蔡邕注亦作“昭登于上”。
《礼记·乐记》:“乐著大始”、“大公之志也”、“食三老、五更于大学”,《乐书》分别作“乐著太始”、“太公之志也”、“食三老、五更于太学”。《史记》大作太,《尚书·夏书·禹贡》:“大行、恒山至于碣石。”《史记
·夏本纪》作“太行、常山至于碣石”。《左传·闵公二年》:“非大子之事也。”《史记·晋世家》作“非太子之事也”。
《礼记·乐记》:“五谷时熟。”《乐书》作“五谷时孰”。《史记》熟多作孰,《尚书·周书·金縢》:“岁则大熟。”《史记·鲁周公世家》作“岁则大孰”。
《礼记·乐记》:“其治民逸者。”《乐书》作“其治民佚者”。《史记》逸写作佚,《逸周书·克殷》:“尹逸筴曰。”《史记·周本纪》作“尹佚筴祝曰”。
《礼记·乐记》:“天子之车也。”《乐书》作“天子之舆也”。《史记》也有引车作舆之例,《诗经·小雅·出车》:“我出我车。”又,同篇:“出车彭彭。”《史记·匈奴列传》均引作舆。
《礼记·乐记》:“天子之宝龟也。”《史记·乐书》作“天子之葆龟也”,唐人司马贞《史记索隐》云:“葆与宝同,《史记》多作此字。”又《史记·留侯世家》:“取而葆祠之。”刘宋裴骃《史记集解》说:“《史记》珍宝字皆作葆。”裴骃、司马贞之说不虚,《尚书·周书·金縢》:“无坠天之降宝命。”《史记·鲁周公世家》即作“无坠天之降葆命”。
《礼记·乐记》:“若非有司失其传。”《乐书》作“如非有司失其传”。《史记》引书以若作如之例颇多:《尚书·商书·微子》:“若之何其。”《史记·宋微子世家》作“如之何其”。《尚书·周书·金縢》:“不若旦多材多艺。”《史记·鲁周公世家》作“不如旦多材多蓺”。《论语·学而》:“未若贫而乐道。”《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作“不如贫而乐道”。
《礼记·乐记》:“将帅之士。”《乐书》作“将率之士”。《史记》引书帅多作率,《左传·闵公二年》:“夫帅师,专行谋。……帅师不威,将焉用之?”《史记·晋世家》作“夫率师,专行谋也。……率师不威,将安用之”。《左传·定公四年》:“其子蔡仲,改行帅德。”《史记·管蔡世家》作“其子曰胡,胡乃改行,率德驯善”。(按,《左传》杜注:“胡,蔡仲名。”)《左传·定公十二年》:“公山不狃、叔孙辄帅费人以袭鲁。”《史记·孔子世家》作“公山不狃、叔孙辄率费人袭鲁”。《国语·周语上》:“帅旧德而守终纯固。”《史记·周本纪》作“率旧德而守终纯固”。《战国策·秦策四》:“帅强韩、魏之兵以伐秦。”《史记·魏世家》作“率彊韩、魏以攻秦”。
《礼记·乐记》:“所以教诸侯之弟也。”《乐书》作“所以教诸侯之悌也”。《史记》引书弟作悌之例有:《诗经·大雅·泂酌》:“岂弟君子,民之父母。”《史记·孝文本纪》岂弟作恺悌。《诗经·小雅·青蝇》:“岂弟君子,无信谗言。”《史记·滑稽列传》亦引作恺悌。
上举凡十四字 :颂、独、彊、诎、信、登、太、孰、佚、舆、葆、如、率、弟;涉及典籍十种:《尚书》、《诗经》、《逸周书》、《老子》、《论语》、《左传》、《国语》、《战国策》、《韩非子》、《楚辞》,自上古迄于战国,涵盖经史子集各类。这些文字用例表明,《史记》的文字书写有自己的体例和风格,而《乐书》的书写无不合于《史记》。这之中很难找出反例,即很难找出先秦古书作“颂”而《史记》作“容”、古书作“诎”而《史记》作“屈”之类的例证,这说明《乐书》体现了《史记》的书写体例和风格。这显然不是“偶然的巧合”所能解释的。
二 《史记·乐书》的产生
今存《史记·乐书》的主体部分与《礼记·乐记》基本相同,历史上有《乐书》抄自《礼记》之说,其说甚妄,余嘉锡已著文澄清。[7]但时至今日,仍有因循旧说者,未免失之疏略。笔者通过比对两种文本的编次和异文,认为两文本属于同一文献的不同传授谱系,《乐书》非但不是抄自《礼记》,其文献价值比《礼记》版《乐记》还要优越和权威。[8]
《史记·乐书》从何而来?是否曾经司马迁之手?对此学术界至今尚无定说。一种意见认为,它是后人补续之作,并非司马迁手笔。其理由主要有二:一是据《汉书》的相关记载。《司马迁传》谓《史记》“十篇缺,有录无书”;《艺文志》“太史公百三十篇”注:“十篇有录无书。”又《汉书·司马迁传》注引张晏语云:“迁没之后 ,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所举十篇之名,《乐书》赫然在列。二是今本《乐书》其主体内容与《礼记·乐记》相同,只是在其前后安插上头、尾而已,这与《史记》的撰写体例明显不符。[9](P99)另一种意见认为,《史记·乐书》属于司马迁手笔。这以唐人刘知几为代表,他认为《乐书》是司马迁“草具未成”的半成品,后来学者南宋吕祖谦、清人王鸣盛、钱大昕均赞成此说。遗憾的是,自唐至清持此一主张者都没有提出确切的证据,因而响应者寥寥,远不及前一种意见影响之广。余嘉锡《太史公书亡篇考》对两派意见详加梳理、辨析,得出的结论也是《乐书》并非出自司马迁之手。[7](P49)
《史记》有严格的撰著原则和体例,对史料既严格信守又有所取舍、加工,其《史记·五帝本纪赞》说:
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余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
这说明司马迁对史料的态度非常审慎,为了探明上古史事,补《五帝德》、《帝系姓》、《尚书》等上古史文献之缺,他一方面深入民间进行田野考察,另一方面又以《春秋》、《国语》等现存史料详加参证。言必近是和力求雅驯可说是他撰著《史记》的两条基本原则。
司马迁出身史学世家,早年就接受过专门的“古文”训读和隶定等方面的训练。《太史公自序》说他“年十岁则诵古文”,又说曾“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所诵之“古文”和“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就是指各种传世古文献[10](P309),这之中自然包括儒家津津乐道的《诗》、《书》、《礼》、《乐》一类经典。《太史公自序》还说:“周道废,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于是汉兴……《诗》《书》往往间出矣……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史记集解》引卫宏《汉旧仪》也说:“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太史公是当时最有条件接触各种传世古文献的。
《太史公自序》提到其撰著《史记》的目的:“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撰著《史记》既是为了绍述周、孔,光大礼乐文化,有关礼乐的各类传世文献自然是司马迁关注的重点,说他为撰著《乐书》而经手过《乐记》是完全可能的。
今本《乐书》显然非司马迁原著之旧。其《太史公自序》云:“比《乐书》以述来古。”比,即编次,《史记索隐》解释说:“言比《乐书》以述古来乐之兴衰也。”也就是说《乐书》是要撰著一篇有关“乐”的兴衰史,今本《乐书》显然未能完成此一目标。它应该是由后人补缀而成的,但这种补缀却有可能依据了司马迁撰著《乐书》的草稿或整理、使用过的原始资料。
说今本《乐书》的材料曾经司马迁之手,还可从《礼》《乐》二书之序透出的信息得到间接证明。清人梁玉绳最先关注到《礼书》之序,他说:“史公《礼书》惟存一序,后人因其缺而取《荀子》续之。”又说:“《乐书》全缺,此乃后人所补,托之太史公也。”(《史记志疑》卷十五)其实《礼》、《乐》二书情况相同,二者同在《史记》失传十篇之列,同是取古文献成篇作为其主体内容。认为《礼书》序存,却怀疑《乐书》之序假托,未免游离两端。今人张大可《史记残缺与补窜考辨》云:“《礼书》、《乐书》篇前之序有‘太史公曰’,当是补亡者搜求的史公遗文,可以说这两篇是书亡序存。”其理由是:“《礼书》、《乐书》、《兵书》以及《武纪》四篇,补缺者均取成书补亡,并不妄作。由此可证篇前之《序》是史公原文。”[11](P169)此说不无道理,可说是对刘知几“草具未成”说的合理补充。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两《书》篇前之《序》,还有篇后之《序》。《礼书》篇后之《序》与今本《荀子·礼论》文字相同,而《乐书》篇后之序则被人认作是今存十一篇《乐记》之外的遗文[7],这说明两序文和正文一样是从现存文稿中抄撮而出。补亡者将其冠以“太史公曰”,当是误认它为司马迁所亲撰。而此种误认之所以发生,则是因为这些文字均在司马迁遗稿之内。补亡者并不知道它们皆为司马迁所隶定之先秦旧文,所以才会将其割裂为二——正文和序文。由此也可以推知,不仅今存《礼记·乐记》与《史记·乐书》不曾抄袭《荀子·乐论》,历史上关于《史记·礼书》抄自《荀子·礼论》的说法也是错误的。它们之间的同与异,乃是基于同一种儒门文献的不同传述。据此还可证明,《荀子》一书并非全由荀子或其门弟子所著,其中还包含有他们所传述的儒门文献,《礼》《乐》二论中的部分文字即属于此类。
再说后人补作《史记》,多取自可信史料,并不妄作,也是有案可稽。《史记·三王世家》褚先生曰:“臣幸得以文学为侍郎,好览观太史公之列传。列传中称《三王世家》,文辞可观。求其《世家》终不可得,窃从长老好故事者,取其封策书,编列其事而传之,令后世得观贤主之指意。”又说:“谨论次其真草诏书,编于左方,令览者自通其意而解说之。”知其所补皆为诏书和奏章一类的原始资料。又,《龟策列传》褚先生曰:“臣以通经术受业博士,治春秋,以高第为郎,幸得宿卫,出入宫殿中十有余年。窃好《太史公传》。太史公之《传》曰:‘三王不同龟,四夷各异卜,然各以决吉凶略窥其要,故作《龟策列传》。’臣往来长安中,求《龟策列传》不能得,故之太卜官问掌故文学长老习事者,写取龟策卜事,编于下方。”褚少孙补《史记》之阙,曾“之太卜官问掌故文学长老习事者”,也即利用过“太卜官”掌握的史料。这些史料中或者就有当年司马迁撰著《史记》时留下的材料。王鸣盛就认为:“《三王世家》,武帝之子,所载直取请封三王之疏及封策录之,与他王叙述迥异。则迁特漫尔抄录,犹待润色,未成之笔也。”(《十七史商榷》卷四)意谓褚少孙所补,根据的就是当日司马迁为撰著《史记》准备的史料。
至于《乐书》原著所以不存,则有两种可能:一是本未著成,一是原本毁损。笔者认为后一种可能性更大,因为据《太史公自序》:“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不仅篇数,连字数都说得如此具体,这说明《史记》本为“完璧”。所以不存,很可能与汉武帝时或稍后的人为毁损有关,原因是司马迁与汉武帝对待礼乐文化的态度多有抵触,这在当时是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的。
三 关于《乐记》成书的时代
《乐记》的成书时间,一说出自战国,系孔子弟子公孙尼子所撰;一说是西汉时期的产物,为刘德及其门人所著。笔者认为它应为先秦的产物。上面提到《荀子》之《礼》《乐》二论和《史记》之《礼》《乐》二书文字相合的情况,即可说明《乐记》的产生,不止在西汉之前,更在荀子之前,《荀子》和《史记》乃是取自同一种现存史料。现再从《乐记》文本在汉代的存在状况,讨论它传自先秦而非出自汉代的可能性。从现有史料看,《乐记》在西汉至少有四种文本,这就是(1)可能经司马迁之手的《史记》本,(2)戴圣编辑的《礼记》本,(3)刘德等人编辑的二十四卷本,(4)刘向校书所得的二十三篇本。进一步考察这四种文本的存在状况,可以发现它们之间互不相涉、各自独立。关于《史记·乐书》和《礼记·乐记》之间的关系,余嘉锡已经指出:“以《乐书》与《小戴记》校其篇次,诚有颠倒,然恐是《乐记》别本如此,与刘向校定本及小戴所见本原自不同,未必补史者以意为升降。”[7](P39)认为《史记》本和《礼记》本并刘向校定本之间互不相涉,这一说法是正确的,尚可从现存文本和相关史料中得到确切证明。以《礼记》和《史记》两种文本对读,二者编次、文字上的差异与优劣十分明显,二者之不属于同一个传授谱系显而易见。历史上,人们习惯于将属于不同传授谱系的东西强行拉扯在一起,因而出现过许多错误的说法。譬如《史记·三代世表》云:“于是以《五帝系谍》、《尚书》集世纪黄帝以来迄于共和为《世表》。”司马贞《史记索隱》案云:“《大戴礼》有《五帝德》及《帝系》篇,盖太史公取此二篇之谍及《尚书》,集而纪黄帝以来为系表也。”崔适反驳道:“惟此二篇之谍,即历代谱牒,太史公取于此,戴德亦取于此。戴德乃后仓弟子,后仓在孝宣世,见《艺文志》,世次在太史公后,太史公非取于《大戴礼》也。”[9](P68)说《乐书》取自《礼记》,所犯是同一类的错误。
刘向校定本与《礼记》本之间的不同,则可从刘向《别录》(见郑玄《礼记目录》)所记篇目得知,二者编次不一,而且,史书既言“刘向校书得《乐记》二十三篇”,则此本应是一直沉睡“秘府”,此前不曾现身,戴圣编辑《礼记》未必能看到。而当此本现身之时,《礼记》早已编成,不可能再来抄取刘向校定本了。
认为刘向所得二十三篇本就是刘德等人所编二十四卷本,更是不能成立。《汉书·艺文志》说:
武帝时,河间献王好儒,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献八佾之舞,与制氏不相远。其内史丞王定传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时为谒者,数言其义,献二十四卷《记》。刘向校书,得《乐记》二十三篇,与禹不同,其道寖以益微。
史书言之甚明,河间献王刘德等人所编二十四卷本即使包含有今本《乐记》的内容,也和刘向校定本“不同”,至少是属于不同的版本。又,此本至成帝时始由王禹献出,不仅司马迁及其同时人无法见到,戴圣(宣帝时立为博士,参与过石渠阁会议)恐怕也无缘得见。这说明刘德二十四卷本不仅和刘向校定本无关,和《史记》本、《乐记》本恐怕也没有什么联系。
《史记》本和刘向校定本《乐记》的不同,也可据刘向《别录》和今本《乐书》的比照得知,二者编次不一。另据《汉书·艺文志》:“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如淳注引刘歆《七略》说:“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据此可知,汉初至武帝之世,献书之风大盛,朝廷藏书之所甚多,分为外、内二系,《史记》本和刘向校定本应该就是分属此二系,《史记》本属外系,刘向校定本属内系。
这就是说,从汉代前期开始,《乐记》就已是多本并存,分途传播了。多本并存的事实表明,《乐记》在先秦应该即已写定。很难想像一个汉代新出的文本,当即就衍生出多种版本,并以不同的面貌和方式流传开来。史籍有关各种《乐记》文本的记载,没有一种显示出新撰的迹象。戴圣《礼记》各篇均取自先秦典籍,刘向校定本取自“秘府”旧籍,自不用说。刘德等所编二十四卷本是“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今本《乐书》也是取“成书”以补缺,或为司马迁所亲见和经手之古文献。这些文本应该都是在汉初“广开献书之路”的背景下涌现出来的。同源异流,一种文献多种传授途径,因而形成复杂的传播谱系,这在当时是很普遍的事。
[1] 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0.
[2] 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3] 何建章.战国策注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0.
[4] 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0.
[5] 洪兴祖《楚辞补注》卷四[M].北京:中华书局,1983.
[6] 《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0.
[7] 余嘉锡.太史公亡书考[A].余嘉锡论学杂著上册[C].北京:中华书局,1963.
[8] 杨合林.《礼记·乐记》与《史记·乐书》对读记[J].文学遗产,2011(1):123-125.
[9] 崔适.史记探源[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0]王国维.史记所谓古文说[A].《观堂集林》第二册[C].北京:中华书局,1959.
[11]张大可.史记研究[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
The Originality of Yueshu in Historical Records Seen from the Diction Style——The formative years of Yueji
YANG He-ling
(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 410081)
Now there are two versions of Yueji.They are Yueji in Liji and Yueshu in Historical Records.Comparatively speaking there is much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ext dictions of the two works.But the text dictions of Yueshu and Historical Records are very similar.From this we can conclude that modern version of Yueshu was added to Historical Records by later historians.The text of Yueji in Historical Records might be the data experienced and gathered for the composition of Yueshu by Sima Qian.It shows that Yueshu comes from the ancient documents of Li and Yue cultures of early Qin Dynasty.This is also proved by the fact that there were many versions of Yueji in existence and distribution in Xihan Dynasty.
Yueshu;Historical Records;diction style;originality
I206.2
A
1008—1763(2011)04—0075—05
2010-11-16
杨合林(1964—),男,湖南桑植人,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论、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