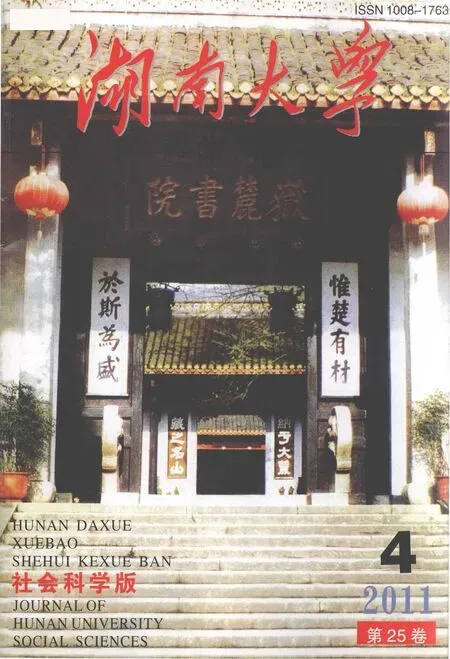现代分析哲学视野中的句本位语法*——为纪念黎锦熙先生诞辰120周年而作
杨光荣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成都 610064)
现代分析哲学视野中的句本位语法*
——为纪念黎锦熙先生诞辰120周年而作
杨光荣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成都 610064)
黎锦熙先生的《新著国语文法》及其句本位语法思想,就现代分析哲学的角度来看,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黎先生的句本位语法,是从句子这一思想的表象出发,去发现“一种语言底普通规则”,这与现代分析哲学创始人弗雷格的思想十分相似。黎先生的“实体词”与“述说词”的说法,具有较大的普适性,不但适合于汉语这种词根语,而且适合于羌语、却隅语等黏着语。“凡词,依句辨品,离句无品”,是对语言现象的正确描述,是“词性相对论”,它本质上是语义取值问题;以外延词和内涵词、外延词品和内涵词品的原理来阐释词性相对论,不但不觉得该理论没什么不妥,反而觉得它是超越时代的杰出见解。
句本位语法思想;现代分析哲学;词性相对论;外延词;内涵词
1924年,黎锦熙先生在他的《新著国语文法》中提出了“‘句本位’的文法”理论,从现代分析哲学的眼光来看,黎先生的理论和思想仍然具有参考价值。
下面,我们就思想和句子、外延词和内涵词、词性相对论以及语义取值等几方面来尽可能深入地探讨黎先生的语法思想,以就教于方家。
一 思想和句子
黎先生说:“诸君知道近来研习文法的新潮么?简单说,就可叫做‘句本位’的文法。”[1](P1)“若从句子底研究入手,则不但灵敏的词类智识、正确的词类用法可以得到,而且:(一)可以发现一种语言底普通规则;因为句子就是语言底单位,如果谙悉其各部分底主从的关系、彼此的衔接、确当的功能,好像一个老技师把他的机器弄得十分的精熟,那么,哪一部分发生了障碍,马上就可以找出其受病之点和治疗之方。(二)可以作学习或翻译他种语言的帮助;因为思想底规律,并不因民族而区分,句子底逻辑的分析,也不因语言而别异,所以熟悉了国语底句法,无论学习何种外国语,翻译何种外国文,自然要觉得工作容易些。若单讲词类底分品和变形,在西文已经是国各不同,在国语更是没大关系的了。(三)可以帮助心能底陶冶;因为做句子底逻辑的分析功夫,实是陶冶心能的一种妙法——从思想底表象(Outward form),即句子,去研究思想,而发现句中各成分所表示的思想各部分是怎样适宜而合理的,这便无异于研习一种思维术(怎样去思想)了。”[1](P1-2)
从这一段可以明确地看出黎先生句本位语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就是从句子这一思想的表象出发,去研究思想,然后以此为出发点,去发现“一种语言底普通规则”,而这“普通规则”“并不因民族而区分”,“也不因语言而别异”。黎先生的这一句子即思想的表象的思想,和现代分析哲学、语言哲学的创始人弗雷格的思想十分相似,弗雷格说:“什么叫作一个句子?一个句子是一个语音系列;但是仅当它有一个意义时才是句子。但以此不能说每个有意义的语音系列都是一个句子。当我们称一个句子是真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指它的意义。因此一个句子的意义是作为这样一种东西而出现的,借助于它能够考虑实真。那么,一个句子的意义是一个表象吗?无论如何实真不在于这种意义与不同的东西的一致,因为如果这样,关于实真这个问题就会无限地重复下去。我称思想为某种能借以考虑真的东西,并不是要以此给出一个定义。我把假的东西同真的东西一样也算作思想。这样我可以说,思想是一个句子的意义,但这不是要声称,每个句子的意义都是一个思想。自身非感官可感觉的思想用可感觉的句子表达出来,因此是我们可把握的。我们说,句子表达一个思想。”[2](P116)
弗雷格研究专家王路对弗雷格关于思想和句子的关系予以评介说:“首先,思想是用语句表达的。前面已经说过,句子是弗雷格探讨的思想的出发点。句子使思想具有一种独立性,人们可以通过句子对思想进行思考。”[3](P172)可以看出,黎先生和弗雷格具有极为相似的分析哲学、语言哲学思想,我们可以这样认为,黎先生的句本位的语法,是以分析哲学、语言哲学为根基的。这里要补充的是,弗雷格的《思想》一文,发表于1918-1919年,目前并没有材料表明黎先生看到过弗雷格的这篇文章,二人思想的相似只是一种类型的相似,是不同国度伟人思想的不谋而合。
二 外延词和内涵词
1892年,弗雷格发表《论意义和意谓》的著名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意谓”和“意义”的著名理论。他说:“显然,对于一个符号(名称,词组,文字符号)除要考虑被表达物,即可称为符号的意谓的东西以外,还要考虑我要称之为符号的意义的那种期间包含着给定方式的联系。因此,尽管在我们的例子中,‘a和b的交点’和‘b和c的交点’这两个表达的意谓是相同的,它们的意义却不同。‘昏星’和‘晨星’的意谓相同,但意义却不同”。[2](P91)
弗雷格的学生卡尔纳普在弗雷格将语言表达式的意义区分为“意谓”、“意义”的基础上,将1662年出版的由安东尼·阿尔诺、皮埃尔·尼科尔合著的《波尔·罗亚尔逻辑》一书中所提出的“外延”和“内涵”术语分别对应于弗雷格的“意谓”和“意义”,从而提出了外延和内涵的理论。[4](P188-190)
我们则于弗雷格、卡尔纳普有关“意谓”和“意义”、“外延”和“内涵”的理论基础上,将取值于“意谓”、“外延”的词称作“外延词”,将取值于“意义”、“内涵”的词称作“内涵词”。
金兆梓的“体词”和“相词”、黎先生的“实体词”和“述说词”以及朱德熙的“体词”和“谓词”,分别对应于我们这里的“外延词”和“内涵词”,“体词”、“实体词”就是“外延词”,“相词”、“述说词”就是“内涵词”。
金兆梓说:“我上面已经说过,语言文字是表达思想的工具。而思想的构成,就有两个顶要紧的观念”(Ideas):(1)体(Substance),(2)相(Attributes)。这‘体’和‘相’两者之间,有一种很密接的关系,说到“体”就会联想到他的‘相’,说到‘相’,就会联想到他的‘体’。譬如想着‘水’,同时就会想到‘透明’‘流动’‘冷’‘湿’等等水的相;想着‘火’,同时也就会想到‘发光’‘燃烧’‘热’等等火的相。再说我们若是想到‘透明’‘流动’‘冷’‘湿’‘发光’‘燃烧’等等诸相,同时也就联想到‘火’‘水’两种体。这因为我们所以能够知道有‘体’,是全靠着他们的‘相’的。所以唯心论者看物质,竟只认有相,不认有体了。[5](P29-30)“凡是标指‘体’的字 ,如‘水’‘火’,我们就叫他为‘体词’(Substance-words)。凡是标指‘相’的字 ,如‘透明’‘流动’‘冷’‘湿’‘发光’‘燃烧’‘热’等,我们就叫他为‘相词’(Attributewords)”。[5](P30)“凡体的种种相,可以把他归纳为两种:例如‘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一复句中,‘狡’和‘良’是‘兔’和‘弓’所固有的品态,我们就叫他为定相(Permanent Attributes);‘走’和‘飞’是‘狗’和‘鸟’一时的行动或现象,我们就叫他为动相(Changing Attributes)或现象(Phenomena)。凡是标指‘定相’或‘动相’的字,在文法上,为便利起见,统称之为抽象词(Abstract words),以便和标指‘体’的具体词(Concrete-words)对待。”[5](P30)
黎先生在金兆梓“体词”“具体词”和“相词”“抽象词”的基础上,采取了“实体词”和“述说词”的说法,黎先生说:“九种词类,大体是按照一般文法分别词品的通规而定的。但人们意识中反映的对象,实只具有三方面:一,实体;二,作用;三,性态。一个观念的内容,虽有完全具备这三方面的可能,但句法上语词的任务,各只能担当一方面,因之大多数有对象的语词,就在本质上照这三方面分为三大类:一,实体词,表示体的,就是名词、代名词;二,述说词,表作用的,即动词;三,区别词,表性态的,即形容词、副词。”[1](P18)
黎先生将“一个观念的内容”抽象为实体、作用以及性态,十分有见地,颇有点形式化的味道。
朱德熙继黎先生之后,采取了“体词”和“谓词”的说法,他说:“实词包括体词和谓词两大类。体词的主要语法功能是作主语、宾语,一般不作谓语;谓词的主要功能是作谓语,同时也能作主语和宾语。”[6](P40)但朱德熙将“是”排除在谓词之外,而黎先生将“是”“似”命名为同动词,一起列入述说词之内,是极有见地的。黎先生说:“此外附属于动词的,有一种同动词,是用来说明事物是什么,或说明事物之种类、性质、形态的。它必须把作为说明的词系在它的后面。例如
这桥‘是’铁的。太阳‘似’火。
‘是’‘似’两词,虽不是叙述桥和太阳的动作,但一个是用来判定桥的种类,一个是用来推较太阳的性质;重在说明主语,和叙述主语动作的动词有同一的功用,所以叫做同动词。”[1](P19)
从汉语之外的少数民族语言来看,黎先生将“是”列入述说词极为妥当,就拿麻窝羌语来说,“判断谓词ŋuə‘是’一般都称它为系词,在北部方言麻窝话中,因为它用得比较广泛,而且也具有谓词的各种人称、数、时间等形态变化。因此,也把它列为谓词一类。”[7](P190)黎先生的“述说词”和刘光坤先生的“谓词”范围最为接近。可以说,黎先生的述说词具有较大的普适性,不仅适合于汉语这种词根语,而且也适合于羌语、却隅语等黏着语。
三 词性相对论和语义取值
关于词类区分,马建忠说:“字无定义,故无定类。而欲知其类,当先知上下之文义何如耳。”[8](P55)
黎先生说:“词类就是每一个词的品性和在句中的作用;《新著国语文法》说‘凡词,依句辨品’,是对的;但又说‘离句无品’则是不正确的,即如复合词的构成,基本上是依据着独立的词类;”(《今序》)[1](P25)又说:“譬如一个‘人’字,一望而知其为名词,但若多找出句子来作例,就可证明用法无限制,因为它有时也作述语用,如古文中之‘人其人’(韩愈《原道》)是;有时又可作形附来用,如普通语词里的‘人熊’‘人参’‘人鱼’都是;有时更可作副附用,如古文中‘豕人立而啼’(《左传》)是。人字在所表观念的性质上,是一个纯粹确定的名词,已经没有疑义,犹且能够如此活用,而活用的时候,成分虽改,形体仍旧,并不像西洋文字都有词头(Prefix)或词尾(Suffix)种种形态变化的表示;这就不必跟他们一样地都说为词类转变,只须‘从句法成分上辨别出它的“用法”来’。名词就始终是名词,只把它区别为几个‘位’就行,即此可见中国文法的特质了。”[1](P17)
刘半农说:“就词的性质而论,我们可以把所有的词分为九类。”“词类之所由分,系于词性,即词本身的性格。”又说:“而这词的本身的性格,仍旧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换句话说,就是要辨明一个词的性格,非但要看这词的本身,还要看它前后所接的词,方能断定。”[9](P31)
何容将刘半农的说法称之为“词性相对论”,[9](P32)这里要指出的是,何容对刘半农的“词性相对论”基本上是持否定态度的,他说:“刘先生的词性相对论,和马氏的字无定类说,同样的是不能自圆其说的。”又说:“这说法(按:这里指黎锦熙先生的‘凡词,依句辨品,离句无品’)和词性相对论,字无定类说,是一致的。”[9](P32)何容正确地指出了马建忠的字无定类说、黎先生的凡词依句辨品离句无品说、刘半农的词性相对论三者之间精神上的一致性,这是一个杰出的见解。但可惜的是,何容又否定了词性相对论。
词性相对论,本质上是词义取值问题。任何一个词,其语义均由外延义和内涵义所组成,相应地,词义的取值范围只能是外延义和内涵义。而词义的取值方式则可以划分为“静态取值”和“动态取值”两大类。所谓静态取值,就是常规取值,即脱离语境的取值,就是黎先生的“离句无品”。事实上,并不是真的无品,只不过这个“品”或是外延义表现出的外延词品,或是内涵义所表现出的内涵词品,甚或是外延义、内涵义所共同表现出的外延词品和内涵词品。而“依句辨品”则是外延义表现为外延词品,或是内涵义表现为内涵词品。可以这样说,导源于马建忠的“字无定类”说,著称于世的黎先生的“凡词,依句辨品,离句无品”说,定性于刘半农的“词性相对”说,定名于何容的“词性相对论”,是一种具有远见卓识的语法理论。该理论反映了词性的真相,只不过囿于当时的条件,即使是该理论的创立者们也持怀疑态度。这里,我们以外延词和内涵词、以外延词品和内涵词品的原理来阐释词性相对论,不但不觉得该理论没什么不妥,反而觉得它是超越时代的杰出见解。
在词性方面,一直存在着两种观点:一种是词性绝对论,一种是词性相对论,人们往往以词性绝对论来否定词性相对论。事实上,词性绝对论和词性相对论并不矛盾,而是互补的;词性绝对论和词性相对论的关系,就如同物理学上牛顿的绝对时空观和爱因斯坦的相对时空观的关系,前者只是后者的特例,而后者则包含前者;词性绝对论和词性相对论的关系,就如同数学上直线和曲线之间的关系,前者只是后者的一个特例,而后者则包含前者。词性绝对论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将词典中词的贮存品性不变地移植到句子中,抱着静态的观点来看待词性,词类的活用之说便是这种观点的产物。词性相对论则采取动态的变化的观点来看待问题,更接近于事实的真相。
四 命题本位思想和句本位理论
命题本位思想是德国数学家弗雷格所提出的,句本位语法是黎先生在借鉴英国学者Leed等人的基础上提出的。弗雷格的命题本位思想和黎先生的句本位语法互为表里,相得益彰,反映了人类思维形式和人类语言形式的普适性。
弗雷格说:“只有在这里才促使我们将一个思想分析为一些不是思想的部分。最简单的情况是二分的情况。各部分是不同种类的:一类是不满足的,另一类是满足的(完整的)。这里必须考虑被传统逻辑表示为单称判断的思想。这样一个思想表达了一个对象的某种情况。表达这样一个思想的句子由一个专名和一个谓词部分组成,这个专名相应于这个思想的完整的部分,这个谓词部分相应于这个思想的不满足的部分。”“专名表示对象,因而一个单称思想涉及对象。但是人们不能说对象是思想的一部分,就象专名是相应的句子的一部分一样。冰雪覆盖的勃朗峰不是勃朗峰高达4000米以上这个思想的一部分。相反,人们只能说,这个思想的一部分以某种仍需考虑的方式相应于这个对象(意义和意谓)。通过分析单称思想,人们得到完整的和不满足的组成部分,它们当然不会孤立出现;但是一类的每一组成部分与另一类的每一组成部分一起形成一个思想。现在,如果不满足的部分保持不变,而完整的部分发生变化;那么就应期待,这样形成的这个思想将部分是真的,部分是假的。但是也能出现这样的情况,他们结合在一起是真的。例如,令以‘与自身相等’这一短语表达不满足的组成部分。在这种情况下这就是不满足部分的一种特殊性质。这样我们获得一个新思想(所有事物与自身相等),它与(二与自身相等,月亮与自身相等)这些单称思想相比是普遍的。‘所有事物’一词在这里处于专名(‘月亮’)位置,但它本身确实不是专名,不表示对象,而只用来赋予这个句子内容的普遍性”[2](P213)
以上部分,弗雷格表明了两点:首先,基于命题的思想是由不是思想的部分组成的,其中的一部分是满足的,而另一部分则是不满足的;其次,就思想的语言形式来讲,一个思想是由句子来表达的,而表达思想的句子则由一个专名和一个谓词部分组成。第三,专名和思想的满足部分对应,谓词和思想的不完整的部分对应。这就是弗雷格的命题本位思想的核心内容。
弗雷格的命题本位思想是以哲学本体论作为根基的。在一个思想中,和思想的满足部分对应的专名是可以表示对象的,即专名的意谓和对象对应。对此,王路有着精湛的分析:“在弗雷格的思想中,专名的意谓就是专名所表示的那个对象。专名可以表示具体的对象,比如亚里士多德,德国等等。专名也可以表示抽象对象,比如数1,2,3,……,‘最小的收敛级数’,等等。弗雷格把月亮比作意谓,实际上是借助月亮这种对象的客观性来说明意谓,特别是专名的意谓,说明专名的意谓是对象,是有客观性的。这也说明,弗雷格所说的专名是比具体的人名、地名、事件名更宽泛的。但是专名的意谓无论如何都是客观的,是对象。”[3](P247-248)
黎先生的句本位语法,则是从句子入手,“去研究思想”[1](P2),而且黎先生也认为“句中各成分”[1](P2)也是表示“思想各部分”[1](P2)的,这便是黎先生句本位语法思想的核心所在,这也是黎先生所说的“一种语言底普通规则”。[1](P1)
从哲学本体论的角度来看,黎先生“实体词”之一的“名词”也是指称对象的,例如“桥”“太阳”,都是客观的。
可以看出,弗雷格的命题本位思想和黎先生的句本位语法思想有着较为一致的本体论根基,只不过弗雷格从命题出发研究思想,而黎先生则从句子出发研究思想,而且他们都认为,一个思想是由几个部分合成的,合成的部分就语言来说也大致对当:“实体词”对当“专名”,“述说词”对当“谓词部分”。这就是说,弗雷格和黎先生均看到了思想和句子的同构对应关系:“命题”对当“句子”。应指出的是,弗雷格还将思想视为函数结构,因为他是数学家。
五 范畴语法及其后的萌芽
命题本位思想和句本位语法思想蕴涵着范畴语法的萌芽。
范畴语法是由波兰逻辑学家列斯涅夫斯基和爱裘凯维茨于上个世纪所提出的。该语法的基本观点是:“如果一个人关于语言的交际作某种简单关注的话,那末,他或者可以将它描述为基本上包含两个方面:(1)识别出这个世界中的某个实体;(2)关于这个实体述说些什么。识别某个实体的最典型的方法就是使用名称,而关于某种已经识别出来的东西述说些什么的最典型的方法就是说出一个语句。这就是范畴语法的出发点。只有两个基本范畴:‘指称的负荷者和真值的负荷者’,这就是语法范畴名称(N)和语句(S)。这样,通过选取一个名称,然后实行某种运算,即‘关于它述说些什么’,我们就产生了一个语句。描述这种类型的事件的一个正规方式,就是说我们将这个名称用作一个函项的主目,这个函项就产生一个语句以作为它的值。”[10](P155-156)对照一下范畴语法的基本观点,该观点和弗雷格的命题本位思想、黎先生的句本位语法思想是多么相似啊!
范畴语法是蒙太古语法的重要来源之一,是“MG处理自然语言的基础”。[11](P24)弗雷格所探讨的思想的普遍性和黎先生所追求的“语言底普通规则”在蒙太古语法中被实现了。“在自然语言和逻辑学家的人工语言之间没有重要的理论上的差别。的确我认为,在一个自然的和数学上的精确的理论之内,综合这两种语言的语形学和语义学是可能的。”[11](P5)可以看出,蒙太古语法的这一通用语法思想正是对弗雷格的命题本位思想(人工语言)和黎先生的句本位语法思想(自然语言)的统一。当然,也不能说蒙太古从黎先生的句本位语法中吸收了什么,只能说是一种不谋而合,一种类型上的相似而已。
时间已流逝了几十年,即使站在当代的角度来看,黎先生的《新著国语文法》及其句本位语法思想依然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1] 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2] 王路译,王炳文校.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3] 王路.弗雷格思想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
[4] 马亮.卡尔纳普意义理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5] 金兆梓.国文法之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6] 朱德熙.语法讲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7] 刘光坤.麻窝羌语研究[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8.
[8] 吕叔湘,王海棻.马氏文通读本[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
[9] 何容.中国文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10][瑞典]詹斯·奥尔伍德等著,王维贤等译.语言学中的逻辑[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
[11]邹崇理.逻辑、语言和蒙太格语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
Sentence-based Grammar in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 Analytical Philosophy ——To the 120thAnniversary of Mr.Li Jinxi’s Birth
YANG Guang-rong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Sichuan University,Chengdu 610064,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 analytical philosophy,Mr.Li Jinxi’s“Lasted Book on Chinese Grammar”and his theory on the sentence-based grammar are still of an important referential value.From sentence,the representation of thought,Mr.Li’s sentence-based grammar tries to find a“common rule of languages”,which is quite similar to the theory of Frege,founder of modern analytical philosophy.Mr.Li’s concept of“notional word”and“function word”has a great universality,which is not only suitable for Chinese,one of atomic languages,but also applies to Qiang Language and Queyu Language,which belong to agglutinative languages.“All words can only have parts of speech in sentences,and they’ll lose their parts of speech if they are separated from sentences”,this is a correct description on language phenomenon;it’s a“Relativism on part of speech”,and it’s essentially a problem concerning semantic sampling;it interprets the Relativism on part of speech with the principle of denotative word and connotative word,as well as denotative part of speech and connotative part of speech,which is felt as an outstanding opinion ahead of its time,instead of an inappropriate one.
Theory on the sentence-based grammar;modern analytical philosophy;Relativism on part of speech;denotative word;connotative word
H164.3
A
1008—1763(2011)04—0065—05
2010-11-16
杨光荣(1957—),男,山西太原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语言学博士.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字学与民族语言学.
——论胡好对逻辑谓词的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