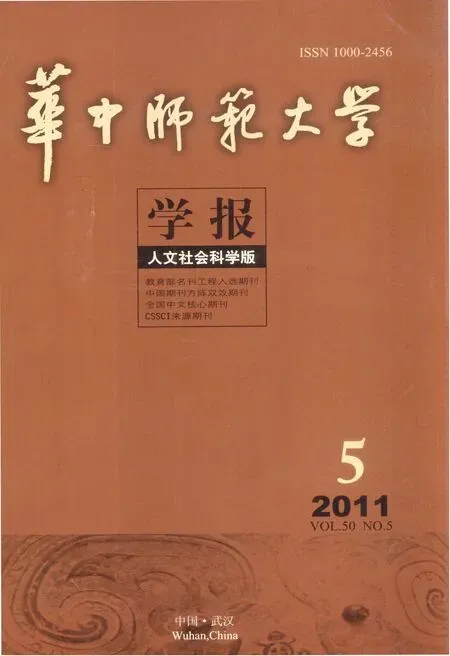南高学派与现代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
——以孔子观为中心的探讨
许小青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湖北武汉430079)
南高学派与现代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
——以孔子观为中心的探讨
许小青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湖北武汉430079)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北大新文化派的激烈反传统主张激起了南高—东大师生的热烈回应,催生了以“学衡派”为主体的南高学派。其后,南高学派以南京高师—东南大学—中央大学为中心,并扩展到南北多校,形成一个广泛而延绵的学术文化网络,造就了现代中国的一个学术社会。从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南高学派在柳诒徵、吴宓、郭斌龢、张其昀等倡导下,以《学衡》、《国风半月刊》、《大公报®文学副刊》和《思想与时代》为阵地,重塑孔子形象,发起“新孔学运动”,倡导“科学时代的人文主义”,并在60年代台湾复兴孔学,成为现代中国文化民族主义的一支重要派别。20世纪南高学派的演变历程,不仅表明后五四时代文化民族主义与政治民族主义自始至终交织在一起,而且也显示出南高学派的文化民族主义与北大新文化派的激进主义如影随形,成见与心结俱深。作为一种文化思潮,南高学派的民族主义与政治上权威主义经历一个由分到合的复杂过程,显示出现代中国文化民族主义与政治保守主义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
南高学派;孔子;新孔学运动;人文主义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以南京高师—东南大学为主体的“学衡派”,激烈地批评新文化派的反传统主义,高举“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旗帜,在学术文化与北大新文化派立异,形成了中国现代学术史思想史上“双峰对峙、二水分流”的格局,成为20世纪20年代学分南北的一个突出现象。长期以来,在新文化主流派的话语支配下,南高学派这段历史并不彰显。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界的研究取向发生了重大转变,围绕近代中国思想上的激进与保守争论激烈①。在这一背景之下,有关南高—东大与北大学术文化之争重新纳入研究者的视野,并取得相当丰硕的成果②。不过,检讨相关成果,已有研究多集中于五四时期的“学衡派”,且对于南高学派和北大新文化派的研究和看法,或多或少将派分的成因——往往是他指和后认——人为地当成事实,并渗入相关的史实与论断之中,容易造成先入为主和倒叙历史的弊病③。本文拟从历史主义的角度,以孔子观为中心,初步梳理南高学派的文化民族主义在现代中国的流变,进而探讨现代中国文化民族主义与激进主义及权威主义的相互关系。
一、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与孔子形象重塑
20世纪30年代初,周谷城就对五四时期的北大与南高进行过评论,称:“从前北大曾新极一时,凡奉行新教育主义的,当然到北大去。与北大对抗的有南高。那么反北大,而且专拜古典主义的,当然到南高为好。”④周氏观察虽有可商之处,但大体上揭示了五四时期北大与南高学分南北的历史。
北大与南高在学术文化上的分歧,主要表现为北大的《新青年》同仁与南高《学衡》诸友之间的文化主张对立。《学衡》是由南京高师-东南大学⑤一批反对北方新文化运动的教授于1922年1月创办的一份综合性文化杂志,直到1933年出版至79期停刊,前后共存在11年。其编辑部设在东南大学内的时间共二年半,即从1922年1月到1924年6月,共出了1-32期。东南大学时期的《学衡》是一份具有明显地缘特色的文化杂志,其主要编辑和撰稿人大部分为东南大学教授,尤其以文史哲学科为主。其核心成员有吴宓、梅光迪、刘伯明、柳诒徵、胡先骕,尤其以吴宓为自始至终的中坚。东南大学中主要撰稿人还有:萧纯锦、徐则陵、缪凤林、景昌极、张其昀、徐震谔、束世徵、向达等。这些学者就知识背景和人脉关系而言,有一个大至相同的特点,要么从清华学校毕业、留学美国而执教于东南大学,如刘伯明、梅光迪、吴宓;要么执教于东南大学或就学于东南大学,如柳诒徵、缪凤林、张其昀、景昌极等。二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师友关系,因此可以判断出《学衡》是东南大学的同仁杂志。《学衡》开篇即点明办刊目标:“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的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⑥其宗旨是站在中西文化融合点上,致力于国学和西学两个方面,并特别提倡“以吾国文字,表西来思想”⑦。这里所言的“吾国文字”即明确指中国传统文化。这一思想的提出是直接针对当时国内的文化研究现状而言的。汤用彤指出当时国人的文化研究有三种不良倾向:“诽薄国粹者”、“输入欧化者”、“主张保守旧文化者”,他认为这三种倾向的共同缺点是“浅”与“隘”,如主张“输入欧化”论,他认为其缺点是对于西方文化缺乏全面系统的研究,常以一得之见,以偏概全,“于哲理则膜拜杜威、尼采之流;于戏剧则拥戴易卜生、萧伯纳诸家”,“似乎柏拉图尽是陈言,而莎士比亚已成绝响。而激烈反传统者,则不值得一驳。”⑧文中所及杜威、尼采、易卜生等西方现代思想家,显然矛头所向是针对北大新文化派。《学衡》杂志成立后在文化观念与北大新文化派发生了激烈的论战。如文学的新旧、文白的优劣和新人文主义与实验主义之争等,其中一个焦点就是如何对待传统文化。以胡适、陈独秀为代表的北大新文化派,具有相当的反传统精神,虽然还谈不上“全盘性”,但是在儒学及礼教领域却表现得相当激烈,“打倒孔家店”更是成为一个最简洁的口号和象征。北大新文化派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尤其在孔子评价上,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承认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认定其是封建专制制度的理论基础,正是孔子与儒学造成今日中国的腐败与落后;2.孔子之道不适应现代生活;3.孔子之道与欧化背道而驰⑨。
与北大新文化派不同的是,南高的学衡派在孔子问题上,主张以批评的精神研究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本来面目,尤其应该剔出后来统治者强加在孔子身上的附会成份,他们提出两点值得注意的区分:一是“真孔”与“假孔”问题;二是孔子与儒学制度化后的中国。针对新文化运动者将中国今日的衰落归咎于孔子及其所代表的儒学之类的文化传统,学衡派主将之一柳诒徵便明确指出,中国社会衰落只是由于社会动荡和历史事件的无常,而不能将之归结到孔子和儒家身上。他说:“中国今日之病源,不在孔子之教……在满清之旗人,在鸦片之病夫,在污秽之官吏,在无赖之军人,在托名革命之盗贼,在附会民治之流政客,以迨地痞流氓,而此诸人固皆不奉孔子之教。”⑩他开出以儒家思想为救治中国近世之病的药方,就是从中国病象的表征中总结得来的,其矛头是直接针对新文化运动者以启蒙的姿态批判中国传统。在柳氏看来,孔子的真正价值在于他是中国文化的中心所在:“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点也。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下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在此,他极力表彰孔子的人格:“孔子以为人生最大之义务,在努力培养其人格,而不在外来之富贵利禄,即使境遇极穷,人莫我知,而我胸中浩然,自有坦坦荡荡之乐。无所歆羡,自亦无所怨尤,而坚强不屈之精神,乃足历万古而不灭。儒教真义,惟此则已。”⑪
为重塑孔子的文化伟人形象,学衡派有意将孔子时代与希腊文明起源进行并列比较,认为二者之间存在诸多契合之处。《学衡》杂志创刊号上将孔子与苏格拉底画像并列编排在一起,以示中西文化巨子的同等地位。胡先骕认为孔子是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齐名的世界文化伟人,其“学说为全世界已往文化中最精粹之一部也”⑫。胡稷咸论证说希腊文明的性质与中国文化颇相仿佛:“哲学家如苏格拉底、柏拉图所研究之主要问题,厥为人类道德之增进,与我国孔孟所讨论者同。”⑬郭斌龢也指出孔孟之道的“中正和平正”是一种人本主义,“与古希腊人之态度颇相似,平易近情,颠扑不破。”⑭
学衡派作为一种与新文化运动相悖的文化派别,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与《新青年》大不一样,刘伯明认为中国文化源远流长,断不能一笔抹杀,“自欧美之风东渐,吾国学子率喜趋向实利,……而以旧有文化为不屑研究,或无补于救亡。”⑮同样在东南学术界有很大影响的柳诒徵,在讨论大学生的责任问题时,对于学者的文化态度提出了三原则:一对于今人的责任主要为“改革”和“建设”;二对于前人的责任主要是“继承”和“扩充”;三对于世界之责任,主要是“报酬”和“共进”⑯。这种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态度,也是学衡派的基本文化立场。学衡派对中国文化的基本态度,也表现对国学的研究方法与新文化派大异其趣。《学衡》创刊时就宣称,“本杂志于国学,则主以切实之工夫,为精确之研究,然后整理而条析之,明其源流,著其旨要,以见吾国文化,有可与日月争光之价值,而后来学者,得有研究之津梁,探索之正轨,不至望洋兴叹,劳而无功,或盲肆攻击,专图毁弃,而自以为得也。”⑰矛头所向无疑是针对胡适“整理国故运动”及以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疑古思潮。梅光迪直接指责胡适的国学研究方法,认为“彼等又好推翻成案,主持异义,以期出奇制胜。且谓不通西学者,不足与言‘整理旧学’。又谓‘整理旧学’须用“科学方法”,其意盖欲吓倒多数不谙西洋文未入西洋大学之旧学家,而彼等乃独怀为学秘术,为他人所不知,可以‘大出风头’,即有疏漏,亦无人敢与之争。然则彼等所倾倒者,如高邮王氏之流,又岂曾谙西文、曾入西洋大学者乎?”⑱明显对胡适等人提倡的“整理国故”的方法、动机和学术根底提出质疑。
由此可见,与新文化派激烈地反传统不同,学衡派对传统怀有很深的敬意。学衡派这一主张对于东南大学学风的形成影响深远。何谓学风?正如时人所讲,“学风这个名词,也就是同一时空之教者与学者的行为、意态、思想、倾向,同时同地教者学者内外生活之综合的表现,就是学风。”⑲在柳诒徵、徐则陵、竺可桢等直接指导下,南高-东大的学生创办了《史地学报》、《文哲学报》等刊物。《史地学报》宣称:“近来自号新文化运动者,大都浮浮在信,稀为专精之研究。即其于所常谈之文哲诸学,亦仅及表面,而于专门学科,益无人过问;循是不变,将使名为提倡文化,而适以玷辱文化。”故他们决定组织中国史学会,“促进实学之研究”⑳。而《文哲学报》则取中西互采的立场,“本刊以研究文学哲学为旨,国故西学齐重互见,古言今说兼取并论,于哲学不宗一派,惟真是归,于文学不拘一格,惟美是尚,诚以学术本无畛界,而哲学示真理之广溥,文学寓情思之潜通,尤为至公无私之物。”㉑其基本学术理念与《学衡》相通,甚至外界批评者称其为“《学衡》的孙子”,以致南高学生公开辩驳:“譬如晨报上某君,骂《文哲学报》是《学衡》的孙子,无论《文哲学报》和《学衡》的主张未必尽同,就是《文哲学报》内部的主张,也未必彼此无异,发刊词内已经一不进则退声明。请问骂的人可得有骂的理由,或者骂的人自己承认是《新青年》、《新潮》等等杂志的孙子,所以步亦步,趋亦趋,发出那一口同声的议论,以为《文哲学报》,也是这样的,这也勉强算是一个理由了。”㉒在东南学风的熏陶下,张其昀、缪凤林、陈训慈、郑鹤声、景昌极、王焕镳、向达等学生辈迅速成长起来,成为南高学派重要传人。
对于五四时期南高学派的尊孔主张,也不断被后来的南高人所总结与肯定。郭斌龢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说:“当举世狂呼打倒孔家店,打倒中国旧有文化之日,南高诸人独奋起伸吭与之辩难。曰中国旧文化决不可打倒,孔子为中国文化之中心,决不可打倒。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南高师生足以当之。”㉓到了40年代,中央大学有人总结校史时,将郭氏的评论稍加变通,进一步加以发扬:“犹忆民国八九年间,当举世狂呼打倒孔家店,打倒中国旧有文化之日,本校学衡诸撰者,独奋起与之辩难曰,中国旧有文化决不可打倒。孔子中国文化之中心,决不能打倒。迨其后新说演变而为更荒谬之主张,其不忍数千年之文化,听其沦丧者。又一反其所为,乃大声疾呼:宏扬固有道德,建立本位文化,排斥浪漫思想者。”㉔到了20世纪60年代,张其昀回忆说:“民国八年(1919年)以后,新文化运动风靡一时,而以南京高等师范为中心的学者们,却能毅然以继承中国学统,发扬中国文化为己任。
……世人对北大、南高有南北对峙的看法。”㉕可见,五四时期以“尊孔”为中心的文化民族主张,成为南高学派的核心理念,也为这一学派不断继承和发扬。
二、“九一八”后“国难”下的“新孔学运动”
1925年发生东大易长风潮后,南高学人纷纷离开了大本营东南大学,北上清华、东北大学等地。经历北伐、迁都等系列政治变动后,20年代末30年代初,“南高学派”重要成员柳诒徵、张其昀、缪凤林等以中央大学为根据地重新联结。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中国的民族主义再度兴起,并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文化民族主义的高涨并走向成熟,其中文化复兴问题成为一个共识:文化复兴是民族复兴的基础或前提,复兴民族文化关键是提高民族自信心,尊重本国的历史和文化㉖。
在“国难”下,南高学人纷纷举起民族主义的大旗,重树南高学风,分处南北各地的南高同人,相互配合,发起了一场“新孔学运动”。
在北方,南高学派以清华的吴宓为主要联络点,以浦江清、张荫麟等为助手,以《大公报·文学副刊》为宣传阵地,倡导孔子的人文思想,率先发起“新孔学运动”。新孔学运动最早倡导者是学衡派西学思想导师哈佛大学的白璧德,白氏在《中西人文教育谈》中,特别希望以一种“人文的君子的国际主义”、“以中和礼让之道联世界为一体”,“吾所希望者,此运动若能发轫于西方,则中国必有一孔教运动。”㉗这一思想在后五四时期经白氏的中国信徒吴宓、梅光迪等不断宣传,成为学衡派成员的思想支柱之一。五四时期由于康有为、陈焕章等的“孔教运动”不得人心,南高诸人并没有发起“孔学运动”。不过到了九一八事变后,在“国难”之下,“新孔学运动”最早是由中央大学教授郭斌龢提出。
九一八事变后,郭斌龢在北平华文学校发表英文演讲,专门指出“孔学非宗教,而是一种人文主义。”认为中国一向以孔学立国,孔学是中国的国魂,“而近三十年来,孔学开腔重创,使国人失去信仰,思想无序,造成外患日重。”他为新时期救国开出药方就是发起“新孔学运动”。具体而言,“新孔学运动”包含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一)应发扬光大孔学中有永久与普遍性的部分,如忠恕之道、个人节操的养成等等,而铲除受时空间的影响所产生的偶然部分,如繁文缛节易流为虚伪的礼仪,及后人附会的阴阳家言等等;(二)应保存有道德意志的天之观念。(三)应积极实行知、仁、勇三达德,提倡儒侠合一、文人带兵的风气,如中国历史上诸葛亮、文天祥、王阳明、史可法,及清末之曾国藩、胡林翼等,皆以文人而握兵权。知耻近乎勇、杀身成仁、士可杀不可辱等古训,应尽量宣传,成为全国国民牢不可破的信条。(四)应使孔学想像化、具体化,使得产生新孔学的戏剧、图画、音乐、雕刻等艺术㉘。可见,“新孔学运动”的目标,就是要将此前孔子形象的重塑发展到一个综合的文化运动阶段,且与“国难”下的救亡运动联系起来。
郭斌龢的《新孔学运动》演讲稿由《大公报®文学副刊》发表,显然得到该刊主编吴宓的欣赏,且与吴宓的一贯主张相契合。早在20年代《学衡》早期,吴宓就大力宣传孔子的价值与孔教的精神,就是到了北方的清华后,他仍不改斯志,1927年还专门撰文,力陈孔子的价值和孔教的精义,批评“自新潮澎湃,孔子乃为攻击之目标,学者以专打孔家店为号召,侮之曰孔老二,用其轻薄尖刻之笔,遍致底讥。盲从之少年,习焉不察,遂共以孔子为迂腐陈旧之偶像,礼教流毒之罪人,以谩孔为当然,以尊圣如诳病。”㉙此时,郭氏“孔学运动”也激发吴宓的孔学观,吴宓在《大公报®文学副刊》发表《孔诞小言》一文,指出现在研究孔子,首要就是对孔子要持了解与同情的态度,“孔子之更为人认识崇敬,亦文化昌明学术进步必然之结果矣。”㉚言下之意,北大新文化派一系对于孔子的批评,乃是学术不进步的结果,也是造成中国今日难局的原因之一。
郭斌龢的“新孔学运动”号召得到中央大学南高学人的积极回应,中央大学同仁刊物《时代公论》先后组织发表了多篇尊孔文章,对郭文进一步发挥。其中张其昀在《时代公论》第十三号发表《教师节之日期》专文,主张以孔子诞辰日为教师节纪念日,为新孔学运动提出了一个切实的纪念方法。其后又在第十四期再著长文,再述教师节与孔学的关系,提出以孔子为诞辰日为教师节纪念日的四大理由:1.中国讲学之风始于孔子;2.中国以教授为职业始于孔子;3.中国教育宗旨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大纲始于孔子;4.中国文化统一始于孔子。张其昀在文中公开支持郭斌龢的“新孔学运动”,称:“吾友郭斌龢君,尝有《新孔学运动》,略谓中国向以孔学立国,孔学为中国国魂。近三十年来,为新派摧残抨击,孔学遂一蹶不振。国人根本信仰已失,思想界产生一种无政府状态。对此种无政府状态,在内政与外交上,完全暴露,长此不改,外侮将源源而来,此正爱国志士所深切忧虑,而亟思挽救者也。又谓孔学非宗教,而为一种人文主义,以人为本,不含神学与超自然之理论;此阶级之优秀者,每愿牺牲孔学牺牲生命与物质上之享受,则孔学实含宗教性;谓之为广义宗教,亦无期不可。又谓中国目前最要者,为一新孔学运动。此种新孔学运动,应为一切改革之原运动。哀莫大于心死,中国国心,已濒死境,新孔学实为使此将死之国心复活之恮良方。”㉛
对“新孔学运动”倡导最为有力的是《国风半月刊》,该刊也是九一八之后民族主义高涨下的产物。1932年9月1日《国风半月刊》在南京正式出版发行,核心成员有四,社长柳诒徵,编辑委员张其昀、缪凤林和倪尚达。其主要撰稿人为中央大学教授如范存忠、张江树、熊庆来、景昌极、卢于道、汪辟疆、胡焕庸、刘咸、谢家荣、郑晓沧、郑鹤声、萧一山、刘永济等,同时也吸引当时的一些国学大家如章太炎、欧阳渐、蒙文通和科学界的秉志、竺可桢、严济慈等为之撰稿。
柳诒徵在发刊辞中对创办背景作了清楚的交待:“张缪诸子倡为《国风半月刊》,嘱余为发刊辞。余曰:呜呼噫嚱!吾侪今日尚能强颜持吾国之风而鸣于世耶!淞沪之血未干,榆热之云骤变;鸡林马訾,莫可究诘;仰列强之鼻息,茹仇敌之揶揄。此何时,此何世,尚能强颜持吾国之风而鸣于世耶!”㉜正是在这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柳诒徵认为,时局比现在有人所担心的“季宋晚明”的历史重演更为严重,因为那时战伐媾和、蒙尘割地等一切还可以自主,但现在情势完全操之于外敌之手,“有史以来无此奇耻”。更为严重的是,“虽以总理遗教,昭示大经,欲复民族之精神,盛倡政治之哲学;而丧心病狂者,依然莫之或革,社会之震憾,风化之污浊,直欲同人道于禽兽,而一以饰以异域之所尝有,遂莫之敢非。”文中“一以饰以异域之所尝有”等语,实际上暗指曾以《尝试集》为名鼓吹西化的胡适等新文化派,柳氏对于新文化派猛烈批评,认为只有从民族历史文化之中,才能寻求救国之道,即“以炎黄胄裔之悠久,拥江河山岳之雄深,宁遂无奋发自强为吾国一雪此耻乎。”因此他明确地提出《国风半月刊》的宗旨:“本史迹以导政术,基地守以策民众,格物致知,择善固执;虽不囿于一家一派之成见,要以降人格而长国格为主。”㉝到第二年,《国风半月刊》在封面上以更为直接的方式,标明其宗旨为“一、发扬中国固有之文化;二、昌明世界最新之学术。”㉞从这一点而言,该杂志与东南大学时期的《学衡》有不少共通之处。
与《学衡》尊孔主张一脉相承,对于民族精神的恢复集中表现在:《国风半月刊》创刊不久就专门出版了纪念孔子的“圣诞”特刊(第三号),可以说这是该刊宗旨的一个明显标志。这一期共刊九篇纪念孔子的文章,这些文章首先回击社会上对于孔子的各种攻击。梅光迪在文章中礼赞圣教,力排诸子,他发现孔子平易近人,尽管在基本的原则上不让步,却并非不苟言笑的假道学。他批评“今日开口进化、自由平等博爱科学方法”的假道学、新名流,也不过是过去孔子所批评的“德之贼也”的乡愿而已。对于新文化运动以来,社会上猛烈批评孔子的现象,梅光迪认为“今日之乳臭未干儿,皆挟其一知半解之舶来学说,以揶揄孔子、掊击孔子者,此非仅孔子一人之厄运,实亦吾民族文化之厄运也。”㉟
柳诒徵先后撰有《孔学管见》和《明伦》两文。他批评近年对于孔子的两种态度——无论是打倒孔家店,还是以孔教号召天下,均是对于孔学的曲解,他认为“近年来有所谓专打孔家店呵斥孔老头子者,固无损于孔子毫末,实则自曝其陋劣。然若康有为陈某某等以孔教号召天下,其庸妄亦与反对孔子者等。真知孔子之学者,必不以最浅陋之宗教方式,欺自欺人,且以诬蔑孔子也。”㊱并重申人伦、伦理、礼教为今日研究中国学术、道德、思想和行为的根本问题,他反对新文化者的意见,重新以明五伦作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对于改变世风和稳定社会仍然具有巨大的精神力量。㊲其后,他又进一步指出:“中国文化的根本,便是就天性出发的人伦,本乎至诚。这种精神方能造就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有过去几千年光荣的历史。”只有一步步地发挥人伦的作用,“使中国文化的精神,从新发扬起来,那便是中国民族复兴的良药见了功效了。”㊳
缪凤林批评“今人却专以礼教诟病孔子”的现象:“现在一般对于礼教,非鄙不屑言,即谈虎色变;孔子也就被视为拂逆人性的礼教制造者或吃人礼教的代表。”缪凤林认为这实对于“礼”的误解,就其本质而言,“礼是社会的习惯,亦是社会的秩序。人类既已有了社会,自然有这些习惯和秩序。人既与人相处,为社会中一分子,自然须履行这些习惯和秩序。鄙夷固属不可,畏忌尤可不必。归罪孔子,更无是处。”㊴此外,《国风半月刊》的同仁对于孔子与民族精神的关系加以发挥,强调孔学依然是救国的良方。这如同郭斌龢所言,一年来外患虽深,而民族精神反趋消沉,国人迷途知返,“深信倡明孔学为起衰救弊之惟一方针”㊵。当然,在融合中西的旗帜下,他们也努力将孔子的思想与西方近代思想进行比较,以此证明孔子的思想不仅未过时,而且与西方思想有诸多暗合之处。
“南高学派”成员在南北报刊同时纪念孔子,倡导“新孔学运动”,既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孔反孔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有意识批判,也是民族危机时刻对传统文化的重新反思,“孔子”成了传统文化认同的最大象征,“新孔学运动”成为该学派借以重新集结的旗号。这一动向遭到北大新文化派胡适诸人对《大公报·文学副刊》的关注与批评。值得注意的是,中央大学文学院的一批文史教授所倡导的以“尊孔”为主旨的“新孔学运动”,后人往往将之与国民政府要人和地方大员倡导的尊孔读经运动联系在一起,认为这是中央大学保守主义的表现㊶,有意地将学统与道统联系起来,这一看法不仅失之于笼统,而且是将后来观念移加到当时人身上的误读。应该注意到《国风半月刊》的一批学人(主要是人文学者)当时倡导的“新孔学运动”,主要是以文化为出发点。事实上中央大学倡导的“新孔学运动”不仅早于当时官方尊孔文化政策的出台,而且待到官员舆论一致“尊孔”之时,他们却有意地保持低调,并时时提醒与官方保持应有的距离。郭斌龢1935年专门提到:“廿一年秋季,南高旧人曾就国风杂志刊印圣诞特刊,提倡尊孔。翌年而尊孔之说洋洋盈耳,见诸命令,形诸祀典,与新生活运动相表里,而此诸人者,力避挟策干时之嫌,退藏于密,惟恐人知,不敢应声附和以哗众而取宠。此独往独来不慕荣利之态度,真吾所谓南高精神笃实而有光辉的一种表现也。”㊷显然南高学人此时重树“尊孔”之旗,是想与“政统”划清界限的,中央大学人40年代回忆这段历史时,多引用上述文字,并加以改造,说明大学的独立性,“及二十一年秋间,本校旧人,曾就国风杂志刊印圣诞特刊,提倡尊孔。翌年而尊孔之说大行,且见于命令,崇诸祀典,与新生活运动相表里,而本校诸先进首倡此论者,类皆退藏于密,不以自多,斯非显而易见者乎。”㊸其本义与官方所宣传的文化统制的出发点还是有相当的区别。但到了抗战时期,南高学派的独立文化主张却发生了重要的转变,日渐与政治上的权威主义结合在一起。
三、从“科学时代的人文主义”到孔学复兴
20世纪30年代初,北大新文化运动主将罗家伦出长中央大学,社会上便有“北大战胜中大”之说,“南高东大中大校友总会”更采取不合作态度,并发起驱罗运动,虽未成功,但却埋下日后冲突的种子。特别是在在纪念南高成立20周年和迁校问题等问题上,罗家伦与南高旧人矛盾公开化㊹,致使1936年竺可桢出任浙江大学校长,以张其昀、郭斌龢为首的一批南高学人移席浙江大学;胡先骕出长中正大学,带走王易等一批南高学人,抗战中,南高成员借助于贵州的《思想与时代》、重庆的《中国学报》和江西的《文史季刊》继续宣扬一以贯之的尊孔主张。
1941年,张其昀更在浙江大学西迁遵义后创办《思想与时代》杂志,其创办有着明显的官方背景,竺可桢在1941年6月14日的日记中记载:“晓峰来谈《思想与时代》社之组织。此社乃蒋总裁所授意,其目的在于根据三民主义以讨论相关之学术与思想。基本社员六人,即钱宾四(穆)、朱光潜、张荫麟、郭恰周、张晓峰等六人。”㊺其中南高出身的张其昀是关键人物,不仅是刊物的主要创办者,更在刊物发展及与学人、官方的联系中起作举足轻重的作用㊻。先后为刊物撰稿的南高出身的学人除张外,还有郭斌龢、景昌极、梅光迪、楼光来、吴宓、缪凤林、陈训慈、胡先骕、范存忠等。其他重要骨干钱穆、朱光潜、张荫麟亦为同道之人,且自20年代以来与南高学人交往圈子来往密切,甚至有人认为,他们也属于保守主义或南方学人圈子㊼。
虽然《思想与时代》没有发刊词,并不等于没有宗旨,这可从其每期中刊登的“欢迎下列各类文字”中也透露出基本倾向,胡适在美国看到后认为其中前两项即是他们的宗旨,第一,建国时期主义与国策之理论研究;第二,我国固有文化与理想根本精神之探讨㊽。特别是1947年复刊后,作为主编张其昀明确其宗旨为:“科学时代的人文主义”。他解释说:“科学的文化是现代教育的重要问题,也是本刊的努力方向。具体说,就是融贯新旧,沟通文质,为通才教育作先路之导,为现代民治厚植其基础。”㊾除了科学外,更主要落脚点在人文主义的宣扬上。
郭斌龢撰文特别礼赞孔子为代表的“儒行”,“吾国固有文化,以儒家学说为中心。而儒家学说中,尤以理想人格之提示,最为具体,最为实效。人类行为之推动力,究极言之,非感情,非理智,而为想像。”“儒家所长,即在善用想像,提示其理想人格。”这种理想的人格,在古代或以成人、君子、士、贤等不同的名称称之,他细致区分了实际生活中的“小人儒”和“君子儒”之别,以“君子儒”为立国之精神,而“君子儒”正是孔子所首但是和实践的,“要其最终鹄的,在勉力求为智仁勇三方面平衡发展之完人。而‘儒’之一字,实际上尤为提示此理想人所通用之名称。”㊿在郭氏看来,如果能将孔子所倡导的君子儒发扬光大,就可以解决中国当下以及未来的重大难题。对于儒家文化的倡导,是《思想与时代》的一大主题,谢幼伟专门发挥了孔子的孝道思想,论证以孝作为中国社会重建的基础。郭斌龢在文后附有一篇“附言”,对于意义作了引申,认为“孝”作为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具有恒久的价值:“生产工具,经济制度,可因地制宜,随时更改。此一点人性,一点真纯优美之民族道德,断不当令其随家庭生产工具,家庭经济制度而俱去也。”他极力倡导孝文化,认为这是一个民族文化中应当的部分,即“一民族有一世族之中心思想,中心信仰。个人有风格,民族亦有风格。生活方式可变,独特之风格,不能尽变,亦不宜尽变。变当其所变,而守其所当守。”[51]
值得注意的是,同一时期另外两份南高学人杂志《中国学报》和《文史季刊》先后创刊,前者由汪辟疆在重庆主编,后者由王易在江西泰和主编,均极力宣传儒家文化与孔子思想。《中国学报》,除了继续像《学衡》、《国风半月刊》刊登旧体诗外,一个主要的内容则在于倡导“尊孔”。创刊号中首篇登载的李翊灼长文《中国学术与中国学报》,编者题记称:“至本篇树义立文,迥异时尚,读者幸勿以寻常文律视之矣。”故完全可视为《中国学报》的发刊词(本没有发刊词,编者称之为“循例之文,无关宗旨”。)李氏认为孔子的伟大形象来源于中国传统的六艺:“中国之学,重道德仁义之大经大本,而了轻术数方技之枝末。务得其精神,而遗其糟粕,其由来盖久矣。故孔子之于六艺,必达诸成人,如其言。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而深于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也;洁静精彻而不贼,则深于易者也;属辞此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52]其后李翊灼更将重点放在“礼学”复兴上,他论证在“国难”下“复兴中国民族,应自复兴中国之固有文化。”他力陈“中国文化的源泉,实以礼学为出发点,舍礼无所谓文化也。”所以,他将“礼学”复兴作为中华民族复兴的起点,文中细致地回答了以下两个问题:第一,复兴礼学是否为中国所必需要?第二,今日中国如何复兴礼学?[53]尽管《中国学报》坚持时间不长,出版期刊不多,许多活动亦无法真正展开,但从其文化思想倾向来看,无疑是直接继承南高学风,也成为南高学派在战时中国宣扬其文化民族主义的重要分支。
1949年中共取得大陆政权,以意识形态统一思想界,而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岛内文化激进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的论争仍在继续。1954年南高学人张其昀出任台湾“教育部长”,引起胡适在美国对南高的老校长郭秉文戏言:“南高征服了北大”,郭秉文却严正地回应:“学术为公,再不可有门户之见。”[54]胡、郭二氏一谐一庄,重提南高北大这一学术公案,不能说完全与人事变动无关。旅居香港的曹聚会仁则在回顾南高学派与北大新文化派的历史,进行了一番综论:“直到蒋氏天下穷居小岛,张其昀任‘总统府秘书长’,又转任‘教育部长’,这才是东南系稍抬头之时。北大系不甘示弱,其间斗争之迹,稍知世务的,一定看得很明白的。”[55]曹氏以局外人的身份,从张其昀出任台教育部长来观察南高学派与北大新文化派势力的消长,与北大派胡适所论如出一辙,集中反映出近代学派问题多与人事的纠缠在一起的复杂历史。
事实上,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张其昀主政台湾岛内教育后,在不同的场合,以其特殊的身份,撰文、演讲,纪念与宏扬南高的精神,而且在行动上恢复中央大学、创办中国文化学院,重树南高大旗。
张其昀在台湾多次南高中大的纪念演讲和撰文中,重申南高的历史悠久和学脉相传,特别指出与北大对峙的历史,在中大六十周年纪念演讲中,他称:“历史上几度成为国立大学的所在地,薪火相传,学统绵延,达一千七百年之久。这种光荣的历史,古今中外各国的大学,实未见其比。”“南高、北大,南北齐名。世人以为这是中国文化正宗与激烈派的对峙,固有其理由。事实的真相,则是北大为文学革命的起源地,南高为科学研究的大本营。”[56]对于南北学派的学风也进行了归纳:“世人或以为民国以来学风有南北两派,北以燕都为中心,南以金陵为大宗,北派趋于细针密缕,南派趋于崇楼杰阁。”[57]
在整个回忆中,张其昀将重点放在南高-东大-中央大学对于现代儒学复兴的重要意义,他宣称:“国立中央大学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儒学复兴的一个策源地。在五四运动以后,对中国历史文化持怀疑与抨击态度者,滔滔皆是。当时南京的我校,则屹立而不动摇,所谓‘钟山龙蟠,石头虎踞’,真为中流砥柱的气概。我校所倡导的新学术,虽深受西洋思想的影响,而不为所转移,而益充实光辉。这种儒学复兴运动,经过四十年的时间,由发轫而渐趋成熟,以期成为吾国学术的正宗,中国真正的文艺复兴。”[58]张其昀在60年代忆恩师刘伯明时,重提南高与北大20年代的历史,“他(指刘伯明——引者注)对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运动,持批评的态度。新文化运动很多治史学的人,但他们指史学狭窄化,甚至只成为一种史料学,他们往往菲薄民族主义,以民族主义为保守,是错误的。历贤前史,惟有民族主义才是国家民族继继绳绳发荣滋长的根本原因。当时南京高师,就学风而言,的确有中流砥柱的气概。”[59]有意思的是,北大派领袖胡适看到张其昀这一回顾时,还专门去信,谈及不能认同张氏这一评价[60]。显然,南高学派与北大新文化派之间的分歧与心结,在台湾时代还没有完全解开。
在实践南高学风方面,张其昀最重要的行动就是1962年创立了中国文化学院。中国文化学院其重要的源头就是“南高”,张其昀在《华冈学园的萌芽》一文中,首先将中国文化学院的“萌芽”其归结于“南高”,他写道:“南京高师,虽然只是国立高等师范之一,可是它的地位很高。民国十年左右,南高与北大并称,有南北对峙的形势。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而南高是人文主义的大本营,提倡正宗的文化。Classics一字,一般译为经典,南高大师们称之为正宗。从孔子、孟子、朱子、阳明,一直到三民主义,都是中国的正宗。本人在南高求学期间,正当新文化运动风靡一世,而南高师生,主张融贯新旧,综罗百代,承东西之道统,集中外之精神,俨然有砥柱中流的气概。面高北大成为民国初期大学教育的两大支柱,实非偶然。”[61]
中国文化学院的前身仍中国文化研究所,创办之初,他在答记者问时,谈及办学理想,称:“华冈讲学,承中原之道德,阳明风光,接革命之心传。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必有真知,方能力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所不得,反求诸己。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62]中国文化学院的办学理念更是继承南高的精神,张其昀对于华冈兴学,他在多种场合有大致相同的表述,他称华冈的理想为四个“综合”:(一)东方西方的综合;(二)人文与科学的综合;(三)艺术与思想的综合;(四)理论与实用的综合[63]。
中国文化学院的创立,其中的立足点,就是恢复传统的敬意,其中尊孔是其要点。张其昀接续20年代初学衡派的尊孔主张和30年代的新孔学运动,继续重申孔学大义,特别将孔子思想与人文主义联系起来,张其昀明确提出:“孔子是中国人文主义的创立者。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教师,他的诞辰已成我国的教师节。孔子学说与人文主义可视为同义语。孔子往矣,精神长存。孔子认为精神力较物质力为强固,故统治世界实为思想。孔子学说经无数者之阐述,而益发扬光大,称为近代孔学或新孔学。吾人深信中国人文主义精神,为人类共同的精神遗产,这是一种最伟大的道德与精神永无穷尽的潜势力。”[64]对于社会上批评尊孔与复古的保守倾向,他力辩孔子学说与现代文化的紧密联系,对于中国文化复兴更是不可动摇,“孔子学说为中国思想之主流,中国文化之大动脉。自孟子曾子以降,二千年来,薪火相传,皆以继承孔子之业为职志。历代儒者,抱负宏伟,态度积极,思博虑远,崇论宏议,务期见诸实践,造福人类,帮能使孔子学说益为发扬光大,从精神上、教育上创造中国长期统一之光荣史迹。”[65]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他在办理台湾教育时特别强调孔子思想在现在大学中的地位,认为孔子思想是文化复兴的基础,他在《大学教育与文化复兴》一文中强调:“孔子之学说对中华民族影响至大,孔子不朽的教泽,便是他集大成的方法与精神。”[66]所以其后在论及华冈精神时,他明确宣布:“华冈精神,即为大学精神。大学精神是什么呢?那是本校第一座建筑物所标榜的大成二字,也就是融贯古今,会通新旧,承东西之道统,集中外之精华,远溯孔子所倡导的集大成精神。”[67]在科学的时代里如何发表孔子的精神,张其昀特别择时出,“现代人文主者必须了解科学的方法与精神,与时偕进。”[68]
由此可见,在五六十年代的台湾,南高学派张其昀将其一贯的文化民族主义主张与国民党当局的文化民族政策结合在一起,在岛内宣扬儒家文化复兴运动,同样引起了文化观察家曹聚仁这样的评论:“过去三十年的‘世变’,真是伟大,其波澜之壮阔,比法国大革命、苏联大革命还要奇丽些,从文化的波澜,好似今日的中国大陆,乃是‘北大’系的天下,而台湾则是‘东南’系的世界,因此,学衡派的思想正在左右草山的风雨。”[69]曹氏评论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看到文化民族主义在岛内的复活,显示出南高学派在20世纪后半期的生命力,更表现出自40年代以来,南高学派与官方权威主义密切合作的历史,这种文化民族主义与政治上的保守主义的结合,集中地反映了五六十年代台湾的政治文化生态。
四、结语
在现代中国,以文化民族主义为主要特征的南高学派形成于五四时期,其成员的文化活动却长达大半个世纪。在现代中国的风云变幻的时代大潮中,南高学派以大学为主要基地,通过创刊刊物来联络同仁,极力宏扬民族文化,视孔子为中国文化的集大成者和象征,不断发起孔学复兴运动,成为现代中国文化民族主义的重要一支。透过南高学派文化民族主义演变历程,我们可以发现作为文化民族主义的一支,它有着这样一些突出的特点:
1.南高学派的文化民族主义,并非是一种严格意义上“保守”
正如美国学者史华慈先生对“保守”所作了的定义:“凡是未经反省地保持固有的行为、感受与思考之方式,这种惯性倾向可称为‘保守的’。”[70]显然,那种将“保守”视为一种落后、反动的贬义词的定性,不太适合南高学派的文化观。因为,从历史和比较的角度看,20世纪的南高学派的文化民族主义是一种开明的保守,一方面,对于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经过多重反思,视中国文化为承接新文化的主体,肯定了传统文化中蕴藏的现代意义,特别将孔子为代表的伦理道德和人文精神视为拯救现代西方文明病的良方;另一方面,主张中西文化的学习与互融,并不排拒以现代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而且这个学习也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这可从他们所办刊物的宗旨中表现出来。不过南高学派强调的是在批判西方现代文明弊病下向真正的西方文明正宗学习,其中在他们看来,西方文化的内核应以哈佛白璧德为首的“新人文主义”为中心。因此,从这种角度来看,南高学派的学人的文化立场是一种开放式的,民族本位与世界眼光二位一体的,更多地表现出一种人文主义的色彩,这也是后五四时代文化民族主义的整体时代特征。
2.南高学派的文化民族主义立场,或明或暗所针对以胡适为首的北大新文化派
五四时期,南高学派的文化民族主义与北大的激进主义进行了从文化到学术各方面的论战,形成了南北学术文化双峰对峙、二水分流的格局。20世纪30年代,南高学派倡导“新孔学运动”,同时倡导文言与“读经”,遭到北大派胡适等人在《独立评论》上的嘲讽。到了40年代,胡适对南高学人创办的《思想与时代》进行了或明或暗的批评。在五六十年代台湾岛内,南高学派与北大新文化派的人脉与思想之间的竞争或隐或显地交织在一起,其文化立场也多表现出歧义的一面。因此,南高学派的文化民族主义发展历程,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与近代文化激进主义(尤指北大新文化派)相对抗的历史,亦表明,“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是不可区分的、相互依赖的。它是保存与革新这样一个同等到重要的过程的两个方面。”[71]过去学者多以新旧来区分南北[72],这种简单的二元化区分容易遮蔽许多历史真相。其实北五四后学分南北的历史,实与北大派与南高学派有着复杂的人脉关系,且化作成见与心结,虽然南北各有新旧,但观念差异与人事纠葛之中,双方明争斗,且有意气用事在其中[73]。故而,南高学派的保守主义与北大的激进主义还如同硬币的两面,既有思维的同一性,又包含着复杂的人事纠结。双方围绕“孔子”的论争可以说贯穿于整个现代中国,反映出文化危机下寻找文化出路的不同方法与路径。可以预见,在中国的文化危机没有彻底化解前,这一争论还将以各种方式长期存在下去。
3.文化民族主义与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关系微妙
南高学派的文化民族主义,其诞生、传播、流转大半个世纪,不绝如缕,影响显然超越出学派的范围,个中缘由,还在于近代中国的民族危机与民族主义的不断高涨。南高学派的文化民族主义所具有强烈的民族文化优越意识,因此,有可以将其称为文化民族主义。在近代中国,一般意义上而言,文化民族主义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是文化取向与政治取向的背离[74],不过,在南高学派的文化民族主义演变史来看,却经历了一个由与政治保守主义关系由离到合的过程,文化与政治表现得十分微妙。在五四时期,南高学派的文化主张与政治之间保持相当的距离,他们批评北大新文化派“非学问家,乃功名之士也。”[75]实际上点明了五四文化激进主义的强烈政治取向。[76]北大新文化派随着国民革命的兴起,在20年代后逐步取得主导的地位。但国民党上台后,政治上文化上却一步步向保守主义退却,九一八后国民党文化政策的转向,在文化统制之下,尊孔读经和新生活运动日渐热闹,似乎与南高学派的“新孔学运动”合上了节拍,但此时的南高学派却努力保持文化的独立性,有意地与官方的文化政策保守距离。然而,抗战军兴,《思想与时代》不仅得到国民党当局的授意和资助,其文化立场与政治主张日益交织在一起,张其昀、钱穆、张荫麟等由文化的保守转向政治上的保守,表现出极端的民族主义倾向,在建国、国防、领袖与建都等政治问题上主张拥护集权,[77]北大新文化领袖胡适批评它有“反动意味”、“保守的趋势”和“拥护集权的态度”[78],更是有所本。到了台湾时期,张其昀复兴儒学主张更是成为国民党官方政治保守主义在文化上的实践。南高学派的文化民族主义演变的历史,表明在民族主义高涨的现代中国,文化民族主义与政治保守主义关系复杂而微妙。
注释
①争论文章可参考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的立场——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北京: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研究综述可参考郑大华、贾小叶:《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史上的激进与保守研究述评》,《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4期。
②学界已往的研究多集中于五四时期的学衡派,代表性的成果有沈松侨的《学衡派与五四时期的反新文化运动》(国立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1984年),以五四时代为历史背景,侧重与新文化派的比较中来探讨学衡派的文化见解与历史地位。郑师渠的《在欧化和国粹之间:学衡派文化思想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从文化观、史学思想、诸子学、教育等不同等方面对学衡派的文化思想进行了专题研究。高恒文的《东南大学与“学衡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研究了学衡派在东南大学的成长历程,注意到学衡派与东南大学内其他派别(如中华教育改进社、国学研究会)之间的联系与区分,特别指出不能将学衡派与东南大学等同视之。不过,近期已有学者注意从较长时段和相互脉络中来研究这一学派,著作方面的代表为沈卫威的《“学衡派”谱系——历史与叙事》(江西教育出版社,2007年),从长时段历史中选取五个相关刊物——《学衡》、《史地学报》、《大公报 ®文学副刊》、《国风半月刊》、《思想与时代》,来分别探讨学衡派的文化整合、历史寻根、文学批评、民族意识与国家观察的表现;论文可参考彭明辉的《现代中国南方学术网络的形成(1911-1945)》,(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29期,2008年5月,第51-84页)则从学人交往网络来展示一个不同于北方的学人文化圈子。
③桑兵:《中国思想学术史上的道统与派分》,《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并收入氏著《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术》,北京: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70-102页。
④周谷城:《官场似的教育界》,《社会与教育》第5期,1930年12月13日。
⑤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成立于1915年,简称“南高”,东南大学成立于1921年,简称“东大”。1921年-1924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与东南大学乃是一所学校,两块牌子,只是学生分属两种不同体制。1924年南高取消,该校统一为国立东南大学。
⑥⑰《学衡杂志简章》,《学衡》第1期,1922年1月。
⑦《学衡杂志简章》,《学衡》第3期,1922年3月。
⑧汤用彤:《评近人文化之研究》,《学衡》第12期,1922年12月。
⑨郑大华:《民国思想史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年,第 224页。
⑩柳诒徵:《论中国近世病源》,《学衡》第3期,1922年3月。
⑪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上卷),北京:东方出版中心 ,1988 年 ,第 231、234-235 页。
⑫胡先骕:《论批评家之责任》,《学衡》第3期,1922年3月。
⑬胡稷咸:《敬告我国学术界》,《学衡》第23期,1923年11月。
⑭郭斌龢:《新文学之痼疾》,《学衡》第55期,1926年7月。
⑮刘伯明:《杜威论中国思想》,《学衡》第5期,1922年5月。
⑯柳诒徵:《论大学生之责任》,《学衡》第6期,1922年6月。
⑱梅光迪:《评今人提倡学术之方法》,《学衡》第2期,1922年2月。
⑲陈东原:《养士制度下的学风问题》,《学风》第3卷第3期,1933年4月15日。
⑳陈训慈:《组织中国史学会问题》,《史地学报》第1卷第2号。
㉑《发刊要旨》,《文哲学报(南京高师文学研究会哲学研究会)》,第1册,1922年3月。
㉒景昌极:《随便谈谈》,《文哲学报》第2期,1922年7月。
㉓㊷郭斌龢:《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二十周年纪念之意义》,《国风半月刊》第7卷第2号,1935年9月。
㉔㊸马騄程:《国立中央大学校史》,《国立中央大学概况》(二十九周年校庆纪念),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学生自治会编印,1944年6月,第5-6页,第6页。
㉕张其昀:《吾师柳诒谋先生》,见《张其昀先生文集》(第 9 册),第 4712 页 。
㉖郑大华:《九一八事迹后民族主义的新变化》,见《“20世纪中国社会思潮及大陆赴台知识分子——纪念殷海光诞辰90周年学术研讨会”交流论文集》(2009年12月5日,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第 85-102页。
㉗转引自张其昀:《中国与中道路》,《史地学报》第3卷第8期,1925年10月。
㉘《新孔学运动》,《大公报®文学副刊》第199期,《大公报》1931年11月2日。
㉙吴宓:《孔子之价值与孔教之精义》,《大公报》1927年9月22日。
㉚《孔诞小言》,《大公报®文学副刊》第247号,《大公报》1932年9月26日。
㉛张其昀:《教师节与新孔学运动》,《时代公论》第15号,1932年7月8日。
㉜㉝柳诒徵:《发刊辞》,《国风半月刊》创刊号,1932年9月1日。
㉞《国风半月刊》第2卷第1号封面,1932年1月1日。
㉟梅光迪:《孔子之风度》,《国风半月刊》第3号,1932年9月28日。
㊱柳诒徵:《孔学管见》,《国风半月刊》第3号,1932年9月28日。
㊲柳诒徵:《明伦》,《国风半月刊》第3号,1932年9月28日。
㊳柳诒徵:《对于中国文化之管见》,《国风半月刊》第4卷第7号,1934年4月1日。
㊴缪凤林:《谈谈礼教》,《国风半月刊》第3号,1932年9月28日。
㊵郭斌龢:《孔子与亚里士多德》,《国风半月刊》第3号,1932年9月28日。
㊶如有学者在总结民国时期北京大学与南京高师-东南大学-中央大学的思想、学术传统的差异时,认为:“可以用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做简单的概括,也可以看做文化激进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的对立。”(沈卫威:《“学衡派”谱系——历史与叙事》,第43页。)这种概括多从思想文化上立论,虽切近主旨,但仍失之于过简、过偏。既漠视了二三十年代政治激变情势下,围绕政治中心南移,党派政治与制度安排对于这两所大学的巨大影响,也忽略了这两所大学本身内部思想学术文化的多样性及阶段性特征。
㊹参见拙作:《张其昀与南高学派》,《近代史学刊》(第7辑),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㊺竺可桢:《竺可桢日记》(第1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 ,第 515页。
㊻[77]何方昱:《“科学时代的人文主义”——〈思想与时代〉月刊(1941-1948)研究》,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集团,2008年。
㊼王汎森:《民国的新史学及其批评者》,见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上,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1-129页;彭明辉:《现代中国南方学术网络的形成(1911-1945),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29期,2008年5月。
㊽胡适1943年10月12日日记,见《胡适全集》(第33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524页。
㊾张其昀:《复刊词》《思想与时代》第41期,1947年1月。
㊿郭斌龢:《读儒行》,《思想与时代》第11期,1942年6月。
[51]郭斌龢:《〈孝与中国文化〉附言》,《思想与时代》第14期,1942年9月。
[52]李翊灼:《中国学术与中国学报》,《中国学报》第1期,1943年。
[53]李翊灼:《复兴礼学之管见》《中国学报》第2期,1943年。
[54]张其昀:《敬悼胡适之先生》,见中国文化大学华冈学会编:《张其昀博士的生活与思想》,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部1882年,第324-325页。
[55][69]曹聚仁:《学苑思故》,见《天一阁人物谭》,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280-281页,第216页。
[56]张其昀:《中大六十年纪念》,见《张其昀先生文集》第十七册,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8年“文教类二”,第8710页。
[57][58]张其昀:《国立中央大学的学风》,见中国文化大学华风学会编:《张其昀博士的生活与思想》,第441页,第440页。
[59]张其昀:《中华五午年史®自序(一)》,见《张其昀先生文集》第20册,第10837-10838页。
[60]张其昀:《敬悼胡适之先生》,见《张其昀博士的生活与思想》,第327页。
[61]张其昀:《华冈学园的萌芽》(1972年5月3日),见《张其昀先生文集》(第17册),“文教类二”,第9038页。
[62]张其昀:《答记者问》,见《张其昀先生文集》(第17册),“文教类二”,第8883页。
[63]张其昀:《华冈兴学的理想》,见《张其昀先生文集》第17册,“文教类二”,第9049页。
[64]张其昀:《孔学大义》,见《张其昀先生文集》(第21册),“序跋函札类二”,第11297页。
[65]张其昀:《〈孔子学说与现代文化〉前言》,见《张其昀先生文集》(第 20册),“序跋函札类”第 10771-10772页。
[66]张其昀:《大学教育与文化复兴》,见《张其昀先生文集》(第17册),“文教类二”,第8994页。
[67]张其昀:《大学精神》,见《张其昀先生文集》(第17册),“文教类二”,第9003页。
[68]张其昀:《新人文主义》,见《张其昀先生文集》(第10册),第 5062页
[70]史华慈:《论保守主义》,见傅乐诗等:《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保守主义》,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80年,第19页。
[71]美国《人文》杂志社编、多人译:《人文主义:全盘反思》,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3页。
[72]如王汎森曾指出,新旧转换的时候,“新”与“旧”的微妙分别渗透到每一种领域中。见氏著:《思想史与生活史有交集吗?——读“傅斯年档案”》,见《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35页。
[73]桑兵:《金毓黻与南北学风的分合》,《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5期。
[74]郑大华:《现代中国文化民族主义潮的历史考察》,《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4期。
[75]梅光迪:《评提倡新文化者》,《学衡》第1期,1922年1月。
[76]陈来:《二十世纪文化运动中的激进主义》,《东方》1993年创刊号。
[78]胡适1943年10月12日日记,见氏著:《胡适全集》(第 33 卷),第 524 页 。
2011-05-07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首都迁移与学术文化的分合”(07CZS018);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与自由关系研究”(07JJD770100)
责任编辑 梅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