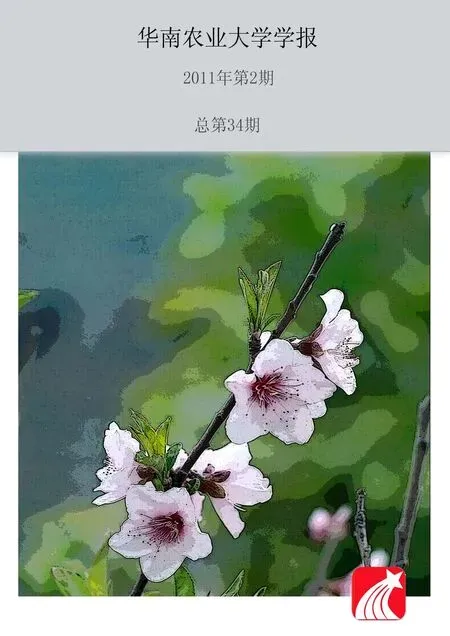灾害背后的政治
——晚明灾害频发的政治因素分析
鞠明库
(河南师范大学 社会发展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
晚明是中国历史上灾害发生最为频繁、危害最为严重的时期之一,“万历十年之后,无岁不告灾伤,一灾动连数省”[1]的局面,更为史上少有。严重的灾荒,不仅严重损害了晚明的农业经济、扰乱了社会秩序,也最终埋葬了明王朝的统治。几百年来,学界对晚明灾害频发的原因多有探讨,除考虑自然因素之外,也将眼光延伸到灾害背后的政治因素。关于晚明灾害频发的政治因素,学界虽有讨论[2],但尚不全面深入,实有深入探讨的必要。
一、救灾主体功能衰弱
“在我国传统的灾害救助体系中,政府发挥了救灾责任主体的作用。……我国历史上各朝政府从一开始就扮演了制度制定与推广、财政支付与兜底、检查与监督的重要角色。”[3]因此,救灾责任主体与灾害救济效果有着密切的联系。晚明时期,封建皇帝的怠政、官员的贪腐使得救灾责任主体功能衰弱,救灾效率十分低下,救灾效果自然不高。作为救灾责任主体的最高代表,万历皇帝从中期开始甚至连灾荒类的奏疏也经常留中不报。万历十二七年六月,户科给事中李应策的奏疏反映了这一问题:“臣查祖制:但有异灾、蝗蝻,即时奏闻。盖虞少稽则缓不及济耳。今各处奏报旱灾,止下抚臣贾待问一疏,魏允贞、曾如春、汪应蛟等各奏报久而未发。人窃惑之,谓从前未有报水旱留中者。”[4]6230皇帝对灾害的漠视和对荒政的懈怠,使政府的救灾工作处于停顿状态。万历三十七年,工科给事中马从龙奏称:“今岁四方报灾颇多,如直隶、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四川、江西、福建,或亢旱或淫雨或蝗蝻,每省无虑数郡。议蠲议赈,未奉明旨,盖从停阁。”[5]368在这种情况之下,地方政府更是不以救灾为急务,玩忽职守者有之,中饱私囊者有之。更为严重的是,作为救灾主体的各级政府甚至严重缺员。万历三十年“两京缺尚书三、侍郎十、科道九十四;天下缺巡抚三、布按监司六十六、知府二十五”[6];至万历末年,内阁阁臣只有一人,六部尚书中有三部无正官。至于级别较低的州、县官所需又不知几何。政府官员的严重缺员致使政府运转不畅,一旦遇灾,难以施以及时、有效的救济。万历间,冯琦的奏疏反映了这一严重问题:
窃惟安民之本,要在修举吏治。……今天下两司共缺七十余员,郡守共缺二十三员,加以迁转而尚未到任者,奉差而尚未选任者,则是天下见在任事之官与缺官而未任者,正相半耳。……夫以焚溺望救之民,当灾旱相仍之日,而待命于若有若无之政,听裁于乍来乍去之人。人望既轻矣,法令安得独重。法既弛矣,政事安得独修,故均之蒞民也,均之行政也。候代之官必不如初任,暂摄之官必不如久任,别署带管之官必不如专任佐贰,署掌之官必不如见任。今欲兴起吏治,莫如备官而考其成,因人而责其事。[7]
“天下见在任事之官与缺官而未任者,正相半耳”一语反映了万历间缺官问题之严重。见任官员的缺位使救灾主体功能衰弱,救灾体系发生断裂,救灾行政效率低下,以至小灾变成大灾,大灾变成严重灾害。
二、备荒制度名存实亡
(一)备荒仓储极为衰败
晚明时期,备荒仓储制度逐渐衰败。明前、中期救灾颇为依赖的预备仓由于没有可靠和固定的来源、守仓官吏的肆意侵盗、府州县官对预备仓管理的不关心等原因而屡兴屡废,无法有效承担起备荒的任务。明末,陈龙正甚至说:“至于今日,天下皆无复有预备仓。”[8]在这种情况之下,明中期以后具有民间自救性质的仓储——社仓和义仓开始在社会上大规模出现。然政府并不愿意民间自行管理社仓和义仓,总是试图将社仓和义仓纳入到自己的管理范围之中,使之成为政府荒政的一部分或可控制的补充资源。于是地方政府加强了对社仓和义仓的查考和干预,轻者影响了其正常运作,严重者将之变成官仓或强占其仓本。嘉靖八年,明政府接受王廷相的建议令全国建义仓,但强调政府的监管作用:“各府州县造册送抚按查考,一年查算仓米一次,若虚,即罚会首出一年之米。”[9]万历十六年浙江桐乡、乌程灾后,“吾镇二府何公(挺)必欲将民间义米贮常平仓作为官米,以邀功干名,已是差了,然犹为义米也。乃代之者夏公(尚忠)恶其琐屑,申分守道,将米价三百余两分贮乌程、桐乡库,备荒义米竟改为库银。”[10]当地富民捐出义米以备灾荒,却被官府变成了官米。万历三十五年,阳谷县合并四乡社仓二十六处,“建官廒而统贮于县,典之以吏胥,守之以仓夫。”[11]政府对社仓、义仓的干预,严重影响了地方富民捐谷的积极性,使社仓、义仓无法有效发挥其散放快捷、救灾迅速的优势,甚至威胁到其本身的存在。因此在晚明,社仓、义仓曾一度复兴,但很快又衰败下去,加之预备仓政的颓废,“自嘉靖起,虽有备荒之名,而无备荒之实,灾荒屡见,万姓流离。至于泰昌、天启、崇祯,尤不可问。”[12]409备灾仓储建设的极度衰败严重削弱了国家的救灾能力,灾害频发而危害越来越严重就成为十分自然的事情了。
(二)水利兴修基本荒废
在中国古代自然灾害中,水、旱灾所占比重最大,破坏性也最大。而与水、旱灾害形成与否的相关因素中,水利兴修与否成了最后一道关口。覃振曾言:“水患决非天灾,乃由于治水未努力。”[13]此话虽不无偏激,但却道出了水利失修与水旱灾害频发的密切关系。
客观而言,明前期封建政府对兴修水利还是比较积极的,也取得了不少成绩。然而在晚明,各地的水利设施逐渐荒废,水利失修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如万历时,巡抚应天右副都御史宋仪望奏:“三吴财用所出,水利最急。自嘉靖初抚臣李充嗣修治之后,未尝大修,沟港日淤,圩埂尽废,旱涝无备。”[4]1221万历《嘉定县志》云:“昔人以治水为大政,故二百年常通流不废。正嘉之际,其遗烈犹有存者。至于今,湮没者十八九,其存者如衣带而已。”[14]不仅江南水利失修,其他地区也存在类似情况,不再赘举。
晚明,尤其是万历朝开始国家财政十分困难,无钱兴修水利。各级官员更视兴修水利为末务,水利衰败成为必然之事。万历时户部覆南京户科给事中吴之鹏云:“迩来有司惟从事于簿书期会,修筑圩岸、疏浚防塘等项事宜,漫不经心,一遇岁凶,茫无措手。”[4]3488隆庆六年的诏书也对官员的这一行为做了强烈批评:“大江南北,国赋所出,全资水利。各处设有水利佥事,各府县又有水利通判、县丞等官,近来往往视为末务,上下因循,一遇水荒,即奏乞蠲免、赈济,引天灾以逃责,岂为民父母之道?”[4]123不少官员不仅仅将兴修水利视为末务,更有甚者将之视为中饱私囊的大好机会。以黄河的修治为例,黄河的修治历来为难事,明代曾有“三年一小挑,五年一大挑”的惯例。然万历以后,这一制度名存实亡,“凡大挑、小挑之费,俱入上下私橐。”由于得不到经常的疏浚,黄河河床越淤越高,以致“连年冲决”[15]。对于管河的官吏而言,他们早已将黄河的修治作为自己中饱私囊的大好机会,黄河决口,他们不仅不着急,反倒是幸灾乐祸,甚至是抱着期待。对此,顾炎武云:“天启以前,无人不利于河决者。侵尅金钱,则自总河以至闸官,无所不利;支领工食,则自执事以至于游闲无食之人,无所不利。……于是频年修治,频年冲决,以驯致今日之害,非一朝一夕之故矣。”[16]这正是明中后期黄河频频决口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 救灾环节充斥腐败
随着封建专制政体的日渐没落,晚明政治日益腐败,这种腐败不仅仅反映在官场,也反映在救灾的多个环节,为害尤深。
如报灾环节。报灾是整个灾害救济的第一环节,也是最为基础一个环节。及时、如实地上报灾情,是展开灾害救济的前提和基础。离开这一环节,其他环节都无从谈起。然而,在灾害发生后,“吏好谈时和年丰以约声誉,而讳言饥荒水旱以损功名,故恒有匿灾异以不闻,甚或饰饥荒为丰穰。”[17]191因此,晚明就出现了官员灾后匿而不报,或延迟奏报,或报而不实的情况,影响非常恶劣。明末孙绳武《荒政条议》也提到:“近见各州县报灾伤时,每多张皇其事,将无作有,捏轻为重,以为异日请赈之地。”[18]有些官员还利用手中的权力,收受贿赂,歪曲灾情。屠隆《荒政考》云:“余见里役之报饥民也,家有需索,人有纳贿,市猾之得过者,欲为他日规避差徭之地,则贿里役,以报饥民,民之实饥而流离者,以贫无能行贿而反不得与,则虽有赈济之名,无救小民之死。”[17]183报灾不实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因为没有真实的灾情信息就无法准确地确定救济方式和赈济数量,灾民自然无法得到有效的救济。
再又如勘灾环节。勘灾真实与否与灾民能否得到切实有效的救济息息相关,然由于官吏的渎职、腐败,这一环节也往往出现问题,从而严重影响赈济的效果。万历间,南直隶扬州府的高邮、宝应、兴化、泰州同罹灾伤。因泰州位置较偏僻,勘灾官不愿遍历,草率勘灾,从而使四地灾民面临不同处境,“高、宝、兴有灾之实,而亦有灾之名。有灾之害,而亦有灾之利。不幸之幸也!泰州同有灾之实,而独不有灾之名。同有灾之害,而独不有灾之利。不幸之不幸也!”[19]晚明陈继儒更是形象地描述了勘灾官漠视民瘼,借勘灾之机大讲排场、收受贿赂、弄虚作假的情况,其《赈荒条议》云:“官长踏荒,东踏则西怨,西踏则东怨,舟车所至,攀拥叫号,里排总甲有伺候之费,有送迎之费,有造册之费,有愚民买荒之费,不如一概,以全荒具申上司。”更有“得钱做荒,出钱买荒,其弊种种不一”[20]。可见勘灾官漠视民瘼、敷衍塞责之严重程度。
又如救济环节。在整个灾害救济过程中,救济环节最为关键,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救灾的效果。同时这一环节也最为复杂,腐败现象也更多。最为典型者莫过于杨文举浙江赈灾。万历十七年,神宗遣户科给事中杨文举往浙江赈济,“文举入境,顾左右曰:‘如此花锦城,奈何报荒,以欺妄挟制有司?’有司惴惴,盛供张伎乐。文举遨游湖山,作长夜饮,每席费数十金,有司疲于奔命。诸绅士进见,日已午,夜酲未解,愍愍不能一语,趋揖欲仆,两竖掖之堂上,糟邱狼籍,歌童环伺门外。置赈事不问,惟令藩司留帑金十一,贿当路藩臬,至守令悉括库羡赂之。东南绎骚,咸比赵文华之征倭云。”[21]这是典型的以赈济灾荒为名,行吃喝玩乐之实!更有甚者,还有些官员为做表面文章,欺上瞒下,竟然拿垂死的饥民做道具进行表演,没有丝毫的怜悯之心。《康济录》记载:“明末,州县官之赈粥也,探听勘荒官次日从某路将到,连夜于所经由处寺院中设厂垒灶,堆储材米盐菜炒豆,高竿挂黄旗,书‘奉宪赈粥’四大字于上,集村民等候。官到,鸣钟散粥。未到,则枵腹待至下午。官去,随撒厂平灶,寂然矣。皆耳闻目睹之事。”[12]434
四、政府决策脱离实际——以晚明黄河治理为例
政策失当也是导致晚明灾害频发的重要因素。与整体水利失修相比,明王朝对黄河倒是投入了很大人力、物力进行治理,但由于奉行“保漕”、“护陵”并重的政策,不仅治河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反而导致黄河水患的频发。
明王朝在永乐迁都北京以后的二百多年时间里,运河一直承担着江南地区向北京输送物资的重任,成为维系明王朝命脉的生命线。由于明代运河在航道上曾借用黄河徐州南至清口段,加之运河徐州北至临清段屡受黄河泛滥冲决,故而治河与保漕交织在一起。为了排除黄河决口、改道的干扰,保证漕运的畅通,明前中期封建王朝将保漕定为治河的首要任务。弘治六年,刘大夏奉命治河,孝宗诏云:“古人治河,只是除民之害。今日治河,乃是恐妨运道,致误国计。”[22]正德间,这一政策发生了变化。正德十二年,黄河大水,水位涨至泗洲祖陵陵门。由于明代祖陵的安危被统治者当作事关社稷的根本大政,所以这一事件引起了朝廷的高度重视,从而也引起明代治河宗旨和原则的变化。明代治河保漕由此开始转入一个新的阶段,即由过去的“保漕”为主转而为“保漕”、“护陵”并重。晚明时期,黄河治理即是在这一原则下艰难进行。万历间,治水专家潘季驯在论述治河任务时曾将护陵、保漕、保民列为治河的三大任务,他说:“祖陵当护,运道可虞,淮民百万危在旦夕。”[23]355常居敬更是将这三大任务排定主次:“首虑祖陵,次虑运道,次虑民生。”[23]497显然,上述二人所谈的三大任务中,护陵和保漕才是统治者最为重视的,民生只是其附带而已。
实际上,“保漕”和“护陵”并重的治河原则使治河陷入了两难境地:既要治理河患,又要南防侵祖陵、北防淤运道;既要保漕,又要护陵。顾此失彼,疲于应付;旧患未治,新患已酿。以潘季驯治河为例,明万历七年,淮河下游淤塞,为了保证漕运畅通,潘季驯实施了“蓄清刷黄”策略。他的做法是:高筑高家堰,抬高洪泽湖水位,蓄积淮河清水,出清口,用来冲刷河道及入海口,以达到“束水攻沙,以水治水”的目的。客观地说,“蓄清刷黄”策略的实施,对保漕确有一定的作用,但水位抬高对位于泗州的祖陵是个很大的威胁。万历二十三年,淮河大水,明祖陵被淹,高堰复决,高邮运堤决口。因洪泽湖水位高,泗州明祖陵被淹,这是明统治者所不能接受的,因此主张“蓄清刷黄”的治河名臣潘季驯被罢去了官职。可见保漕与护陵是难以兼顾的。
作为治水专家的潘季驯尚且如此,说明治河过程中“保漕”与“护陵”并重的复杂性。然而,正是这两个原则促使治河的官员为完成政治任务,往往不顾自然规律,逆河之性,强行改变河道流向,最终加大了黄河泛滥的频率和程度。根据黄河水利委员会所编的《人民黄河》的统计,“仅在明代的二百七十六年间,黄河决口和改道就达四百五十六次,平均约每七个月一次,其中大改道七次。”[24]根据陈志清的统计,明代黄河决口312次,平均0.88年决口一次[25]。这两个统计数据尽管略有差异,但都说明一点:明代黄河的决口和改道是在黄河水利史上非常罕见的。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除了黄河流域特有的自然因素之外,晚明的保漕、护陵并重的政策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应当指出的是,晚明时期也出现了如钟化民积极赈救河南灾伤的例子,但毕竟属凤毛麟角。在封建皇帝漠视民瘼、救灾责任主体功能衰弱、备荒制度名存实亡、救灾环节充斥腐败、政府决策脱离实际等因素影响下,晚明时期灾害发生频率趋于加快,灾害危害被极大放大,常常出现无灾成有灾、小灾变大灾的局面。最终结果是,崇祯末特大旱灾、蝗灾、疫灾三位一体的打击摧毁了明王朝的统治。
参考文献:
[1] 张 萱.西园闻见录[M]//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45.
[2] 鞠明库.灾害与明代吏治[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9,(4).
[3] 张 涛.中国传统救灾体系刍议[J].新华文摘,2006,(10).
[4] 明神宗实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5] 董其昌.神庙留中奏疏汇要[M]//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6] 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6173.
[7] 冯 琦.宗伯集[M]//四库禁毁书丛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636-637.
[8] 陈龙正.救荒策会[M]//中国荒政全书.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3:712.
[9] 申时行,等.大明会典[M]//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386.
[10] 李 乐.见闻杂记[M]//瓜蒂庵藏明清掌故丛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716-717.
[11] 董政华.民国阳谷县志·艺文三·建保赤仓碑记[M].济南翰墨斋南纸印刷局铅印本.
[12] 陆曾禹.钦定康济录[M]//中国荒政全书.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
[13] 邓云特.中国救荒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82.
[14] 韩 浚.万历嘉定县志·文苑一·永折漕粮碑记[M].万历三十三年刊本.
[15] 文 秉.烈皇小识[M]//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99.
[16] 顾炎武.日知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994.
[17] 屠 隆.荒政考[M]//中国荒政全书.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3.
[18] 孙绳武.荒政条议[M]//中国荒政全书.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3:592.
[19] 陈应芳.敬止集[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13.
[20] 陈梦雷,等.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食货典[M].北京:中华书局;成都:巴蜀书社,1985:83323.
[21] 林希元.荒政丛言[M]//中国荒政全书.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3:172.
[22] 明孝宗实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1356.
[23] 潘季驯.河防一览[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24] 张含笑.明清治河概论[M].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1986:11.
[25] 陈志清.历史时期黄河下游的淤积、决口改道及其与人类活动的关系[J].地理科学进展,20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