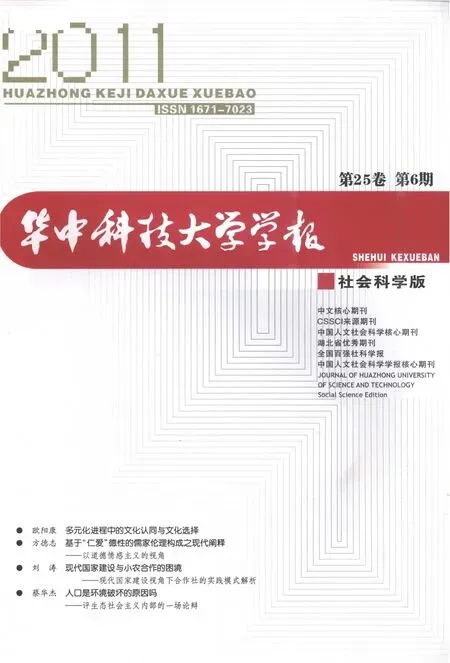种族政治压力下的政治现代性诉求——从《大同报》看满族留日学生的政治认同
邓丽兰,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天津 300071
种族政治压力下的政治现代性诉求
——从《大同报》看满族留日学生的政治认同
邓丽兰,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天津 300071
一批受西学知识洗礼的满族留日学生,超然于现政府与革命党之上,以救亡图存自任。他们主张以国民主义取代狭隘民族主义,满汉平等、满汉蒙回藏合成一中华民族。他们将外患问题、种族问题皆归结为政治制度问题,呼吁以立宪来建立责任政府。建立责任政府的第一步则是民选的国会。他们也信奉社会进化论,重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其政治理念具有鲜明的现代性。辛亥革命时期,《大同报》诸人对专制主义的批判,对政治现代性的诉求,无疑是具有革命性意义的。
宪政;革命;排满;国会
在革命神圣、革命价值至上的年代,辛亥革命被认为是不彻底的,不但封建王朝没有得到彻底的铲除,还被北洋势力窃取了胜利果实。而当告别革命、和谐为上的呼声日益高涨的时候,辛亥革命似乎又太暴力化了,它中断了清末的新政,开启了中国反复革命、循环革命的历史。是也非也,随着研究者视角的调整,辛亥革命的历史遗产也被反复的再审视、再解释。笔者不想追问这场革命的是是非非。这里,仅以一份满族留日学生所主持的刊物《大同报》为例,从他们所标举的政治理念中,揭示一种思想上的“政治现代性”是如何确立的。
“排满”虽是革命党人进行革命宣传的最鲜明的旗帜,但满民族在辛亥革命时期的具体处境与政治态度却十分复杂。林家有先生20世纪70年代的文章即揭示出20世纪初年下层旗人“无地可耕、无以为生”,甚至卷入抗捐、抢粮、逐税吏的民变当中,以及组织“联合急进会”之类的革命组织,呼吁“建立满汉联合共和政体”响应辛亥革命的情形[1]180。而满族精英分子也不纯是统治集团的一员,反而可能为统治集团的公开反对者。本文所叙述的以恒钧为代表的满族留日学生,便是其中典型的例子。
一
自孙中山在日本成立同盟会,矢志排满革命的政治运动蓬勃展开。以康、梁为代表的原维新派,则秉持君主立宪的救国方略。正是在这革命与立宪双峰争潮的时刻,立宪派领袖杨度提出“速开国会”的口号,以应对革命党人的“排满革命”。在他看来,“排满革命”之所以“几成为无理由之宗教”,就在于普通人民未必能理解学术化的政治法律理论,“吾辈若欲胜之,则亦宜放下一切,而专标一义,不仅使脑筋简单者易知易从,并将使脑筋复杂者去其游思,而专心于此事”[2]405。杨度似乎发现了从事社会运动的奥秘,但简单化的处理,以宗教化的姿态对待开国会,恐怕也难以像革命话语那样刺激人民的情感。不过,杨度的主张,一度成为立宪派阵营的共识。
正是在这样的时刻,一群满族留日学生创办了《大同报》。1907年6月29日(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十九日),《大同报》在东京创刊,编辑兼发行人“叔达”,主要撰稿人有恒钧、乌泽声、穆都哩、佩华、隆福、荣陞等。大同报社编辑所设在日本东京早稻田鹤卷町493号,发行所则设于北京崇文门方巾巷公益报馆内。杂志由群益书局经销,在全国十多个城市设立有经销处。①该刊于1908年3月27日改为《大同日报》,馆设北京琉璃厂土地祠内。目前,在研究晚清民族主义、满汉关系的论文中,对《大同报》的文章多有征引,如沈松侨《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28期,1997年12月;黄兴涛《民族自觉与符号认同:“中华民族”观念的萌生与确立》,《中国社会科学评论》(香港)2002年2月创刊号。李龙《另类视野中的满与汉——以满族留日学生为中心的考察》(《钦州学院学报》2007年4期)一文专文研究了《大同报》的民族国家思想。作者指出,在“排满”与“排汉”的两种极端言论中,《大同报》“更象一个中间派”,他们从立宪的立场上主张“融合满汉”具有积极的意义。《大同报》出刊后,一时间颇引人注目,“自出版以来,大受海内外同志诸君所欢迎,第一二两期俱已印刷再版,而第一期销售罄尽,爰再精印三版”[3]。
刊物奉杨度为精神领袖,请他题辞。杨度在《题辞》中,称《大同报》诸人为“旗人中之同志”,“为国民之前导”,赞扬恒钧等的办刊行为“尤为自有旗人以来所无之事”,“岂非中国之大幸”。在排满、排汉正呈现极端化而导致中国出现“内溃”危机的时刻,他希望以《大同报》同人的理智言论,“以明者导不明者”,为“责任中之责任也”。杨度坦率地承认,“大同报社诸同志以少数之人,孤危寡助,力排异议而为之,较吾人之事业尤难”,强调不能将满族人主张立宪、开国会的要求看成是“伪言”,“夫旗人亦中国人,为何而不可以主张立宪开国会,而必以不诚待之?”[4]在这份“题辞”当中,杨度既表达了感情上对恒钧等人的深切同情,又明确表明了与其在基本政治立场上的一致性。作为留学生群体的领袖人物,杨度寓所成为聚会场所,与他往来频繁的,既有革命党人,也有立宪派。
不仅如此,《题辞》也发表在杨度主持的《中国新报》1卷6期。该刊还为《大同报》作广告,称《大同报》刊为“留东八旗诸君”创办的“空前绝后之大杂志”,并称赞其内容,“第一号首论中国之前途,凡外患内治,人民政党,皆导以一定之方针;次论满汉问题,凡立宪问题种族问题,皆予以正当之解决”[5]。杨度的文章《国会与旗人》也发表在《大同报》上。显然,这一时期杨度与恒钧诸人有着颇深的交往,那份著名的《民选议院请愿书》也先后发表在两份刊物上。
而在《大同报序》一文中,乌泽声将该报的办刊宗旨概括为“吾人之欲改中国专制政体为立宪政体也,其惟一之方法即在排除人民程度不足之说,主张速开国会,此本报最大之宗旨也”。同时,他又具体将该报的主张具体化为:“一、主张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二、主张开国会以建设责任政府;三、主张满汉人民平等;四、主张统合满汉蒙回藏为一大国民。”[6]四者之中,君主立宪政体是核心。该刊设有论说、译述、论著、来稿等栏目。
该刊的主持者爱新觉罗·恒钧,字诗峰,是奕山的玄孙,官派留学日本,就读于早稻田大学教育及历史地理科。恒钧一直活跃于国会请愿运动及民初的议会当中,他参与领衔提出《民选议院请愿书》,又发起组织八旗人士国会请愿运动。乌泽声(1883-?)字谪生,吉林永吉人,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回国后,历任众议院议员,并一直活跃于新闻界,后在伪满洲国供职。穆都哩(?-1961),字辰公、六田,亦名穆儒丐、宁裕之,1905年,赴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攻读历史地理和政治经济,回国后在报界任编辑,同时创作小说,后成为作家。在近代中国留日史上,早稻田大学声名遐尔,上述几位早稻田满族留日学生,正是在这所政治氛围浓厚的学校中展开其言论生涯。
《大同报》所持的基本立场,是立宪派的立场。在他们看来,“政府之腐败依然,革命之风潮愈烈”,但“今日政府之所利非我全国国民之所利也,革命党之所利也非我全国国民之所利也”[7]。因此,他们自诩为国民利益的真正代表者,希望在政府之无能、革命党之破坏之外,另谋第三条出路。
除舆论宣传外,他们还参与了立宪运动的实践。1907年9月25日,宪政讲习会选派熊范舆、沈钧儒、恒钧、雷光宇等人赴京,将有100余人签名的《民选议院请愿书》呈送都察院。当时,参与领衔签署请愿书的恒钧是“花翎应封宗室”。1908年8月,《大同报》同仁又组织散发传单,发起八旗国会请愿,将八旗士民的请愿书送呈都察院,要求终止预备立宪,速开国会。请愿书由恒钧领衔,踊跃签名的八旗人士达一千多人。
二
身为满族人士,《大同报》同仁并未将中国的前途与清王朝捆绑在一起,相反地,他们深刻揭示专制政体的危害,鼓吹立宪救国。
恒钧指出,中国两千年历史是君主专制政体进化的历史,“二千年来由汉而晋而隋而唐而宋而元而明,夫本朝则集专制政体之大成”[8]。只有皇位争夺而无国民请求权利的问题,因而“只有君主革命而无政治革命”。而专制政体的弊害,在易陷于虐政,妨害国民之思想力及活动力之发达,以一人之自由意志为国家之自由意志,人民与国家没有直接的关系,等等。他还从天演进化之理,阐述中国之前途。他借用日本人松村介石的话,提出三条世界兴亡盛衰之道:“其一,专制国必亡,立宪国必不亡;其二,国小民少者必亡,国大民众者必不亡;其三,逆世界之大势者必亡,顺世界之大势者必昌。”[9]显然,他所理解的世界大势,就是专制政权必亡、国家分裂必亡。
《大同报》撰稿人还揭示了清廷统治下的政治现实,进而提出立宪救国的观点。在他们看来:“吾国以专制政体、放任政府之故,内政之不足以餍吾民久矣。以政府之腐败、官界之混淆,有争权逐利之恶剧,无惠民济国之布施,对内摧残国民之元气,对外断送国家之利权,求其行一政施一策足以差餍吾民之望者,已如凤毛麟角不可多观。是故致国家于濒危,溺国民于水火。”[10]而救亡之道在于立宪,“立宪乃所以救中国也”,为“立宪之政体为最优美之政体,其政府为责任之政府,其人民为自由之人民,无治者被治者之别,而皆对于国家负责任”[6]。总之,欲改良内政,改善外交,政府负责任,人民享自由,必须实现立宪政治。
本着对于立宪政治的理解,《大同报》重新阐释了国家、国民、政府的关系:“夫国家者,人民之集合体。人民者,国家之一个人。国家之利害,即人民之利害也。以个人参与国家之政治,犹之个人计算自身之利害。”[6]因此,国民个人的得失,是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的。
国民是与政治责任联系在一起的。“所谓国民者,谓有参与国务之权而非泛言人民者。比先哲有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此言可为国民二字最谛当之注解。人而不为国民斯已而,亦既斤斤然自诩曰我为国民,则即有监督政府之责任。”[10]只有有责任的国民,才能造就真正的现代政治。
而政府并不是国家,也不是君主一人施展权力的工具,“夫政府者,国民之产物也”。[6],政府的职责在于谋求国家的强盛与国民的幸福,因此放任的政府、不负责任的政府,无法达成其应该具备的功能,必须“改造责任政府以图最大多数之最大幸福”[11]。
在国家主义发达之时代,“救国之政策必以国家为本位,谋全国民之幸福”,而不能以党派、地域及种族之小团体为本位。中国者,非满人之中国,非蒙回之中国,亦非汉人之中国,“乃中国全体人民之中国也”;国民本为一体,有利害共同之关系,“亡则同亡,存则俱存”[7]。因此,必须合满蒙汉回藏五族为一中华民族,为政治上的团结,以国家为本位,同心协力,共济危难。
现代政治,归根结底是保证公民自由、对公权力施以法治限制的政治。尽管各国家的政制结构千姿百态,但这一根本要义是现代政治的精髓,也是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大同报》所代表的满族留日学生,批判中国君主专制政体,鼓吹立宪救国,倡导超越种族之上的国家观念,重视国家的责任在于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国民的责任在于参与国家政治,显然是顺应了时代潮流的呼声。
三
宪政是现代政治的最高目标,《大同报》所主张的“立宪救国”论认同了这一目标。但立宪的模式有两种,一为君主立宪政体,一为共和政体。
从政体进化的角度,《大同报》诸人推崇了君主立宪政体。乌泽声表示,“吾所主张之立宪,就国体而言,为单绝(纯)统一之君主国体;以政体而论,为代议从众完全无缺之立宪政体;以人民而言,为毫无阶级、自由平等之立宪国民。”[12]在他看来,自己主张君主立宪并不因为满人为君主,而是基于外患危机严峻,革命所从事的破坏会阻挠经济的发展。就内而言,蒙古在游牧时代,西藏在宗法时代,没有地方自治的能力,也就谈不上共和联邦。恒钧也强调,“本报既不主张专制,复不主张共和,所主张者惟君主立宪,此本报第一之主义也。”[8]因而,专制说与共和说都狂悖无当,只有君主立宪才是中国最好的选择。
具体地,以《大同报》为代表的满族留日学生主张设立民选议会以建立责任政府、地方自治、培养国民的政治能力,等等。
建立君主立宪政体的第一步,《大同报》认同了杨度“速开国会”的主张。乌泽声指出,没有议会的国家,绝对产生不了负责任的政府,“国会开后,则中国为立宪国,国会一日不开,则中国犹一日为专制政体也”[6]。国会比形式上的宪法更为重要,国会也是改造责任政府的惟一武器。
乌泽声认为,有了人民的监督,政府才不会腐败。国会是人民意志的表现,是国民的代表,“监督政府使依既定之国法而执行职务”、“参与立法务使法律与国民意志两相协合”。因此,国会的功能不是由正面执行政务,而是“实由傍面限制政府也”[12]。他还详细解释了西方国会通常具有的法律协赞权、财政监督权、行政监督权。隆福也认为,如果没有民选议会,依靠政府预备立宪,则宪政一万年也实现不了,“开国会三字是我国家宪政实行与否之真象也,亦我国家存亡之紧要关键也”[11]。
在《论开国会之利》一文中,乌泽声具体例举了开设国会的对内之利在扩张民权、改造政府、融和满汉、经营蒙藏;而对外之利在巩固国权、收回权利、扩充军备、竞争经济,“吾人救中国惟一之方法只有速谋开国会以监督政府,使之不放弃,使之不腐败,则国内一切困难问题皆可以根本的解决”[13]。这里,国会似乎成了解决国家危机的万应灵丹。
《民选议院请愿书》是中国民间的第一份请愿书,由此揭开了国会请愿运动的序幕。议院请愿书列举了召开民选议院的六条理由:人民监督与舆论声援、国家行政统一、财政税收合理、完善国家法律体系、使人民参与国家大政、消除种族隔阂[14]。请愿书还回应了各种反对设立议院的言论。《大同报》发表请愿书的同时,乌泽声写有一“跋”,称请愿书“乃我国民以少数之团体与政府第一次之宣战也,壮哉!以蜷伏数千年专制政体下之人民一旦奋兴蹶起,联翩结袂与政府开正当之谈判,冀早建设代表国民之机关,为实行宪政之先导,询我中国有史以来破天荒之举动也。吾不禁手为之舞,足为之蹈,心为之敬,胆为之壮,与四万万同胞同声一庆矣。”[14]当然,“速开国会”作为宣传口号尚可,如作为具体的宪政方案,是有操作上的缺陷的。这在于它的化约主义的倾向:如果没有议会党团,又如何使国会运转?如果没有一部宪法,国会又如何依法行事?宪政机制是一个成熟的连环套,仅仅靠口号是无法实现的。
《大同报》诸人还强调了建立责任政府的必要性。乌泽声认为,无论是依赖现政府,还是颠覆现政府的救国方案,都是不可取的,适当的的选择是改造现政府。在他看来,“未有国民放弃责任而政府能负责任者,亦未有国民负责任而政府能放弃者”[6]。立宪的政府,就是以负责任的国民,造就负责任的政府。政府中的一二人可能被威胁、利诱,国民亿万人却是不可威逼利诱的。议会的监督,国民的非议,政府才能承担其责任。
乌泽声详尽阐明了责任政府之组织、精神、责任。在他看来,“立宪国政府为一国责任行政之中枢,所以辅弼元首、出纳政令之机关,对于国民负一切之责,故谓之责任政府”。责任政府的精神,一在“君主不负责任”,二在“皇族不为国务大臣”,这两点是君主立宪的基本要义。而责任政府应该负担的责任,则体现为政治上之责任、法律上之责任两方面。前者意味着责任政府应有主义、有方针作为政治上的定盘针,“依此政纲主义为国务上之大政方针”,再定立具体的行政计划以图事业发达。法律上的责任也就是宪法上的责任,意味着即使君主也不能以命令取代法律,有行政裁判所一类的机构审查国务大臣的违法犯罪行为[15]。
召开国会,则是群策群力改造责任政府的惟一手段。改造责任政府为挽救危亡的紧要关键,“故必有国民监督政府,政府乃欲不负责任而不能。然则改造责任政府者,我全国民救国之第一要件也。要求政府开国会以期实行立宪者,又改造责任政府之惟一手段也。”[11]在他们看来,“夫人民结合而成国家,政府则发令施政以为之关;私藏集合而成公库,国会则预算决算以为之键。必国会成立而后政府对于人民负保障生命金钱之责任”[16]。总之,必须以民选议院来救济政府的黑暗、腐败,保障人民生命财产之安全。
通过对欧美立宪政治的了解,《大同报》同仁还进一步意识到,地方自治与国会为左右足,不能单足而行,“町村市郡府县之代议会即自治制度也,国家之代议会即立宪制度也”。西方立宪国家,有着由町村、郡市、府县到国家的层层自治结构。国会之下有府县会,再之下是郡会、市会,最底层是町会、村会。有了这样的人民代议会,才能议而后决,增进公共幸福。总之,“国家立宪之初级,必于自治制度入手。国民政治思想先于町村会小试之而后充之于国会,自无躐等弊。如未成立地方自治制而贸然欲开国会,犹幼儿未入小学而入大学也”[16]。因此,自治制度为立宪制度之基础。
无论开国会、建立责任政府、地方自治,都依赖于有政治觉悟的国民的参与。乌泽声表示,“夫立宪政体究极之目的,在以国民之共同意识为政治之元动力,宪法不过达此目的后之一形式耳”。无政治知识、无团结力的人民,只能构成无意识的社会、无意识的国家。立宪需要国民负担责任,“诚使国民能负责任,则国民之意思即强力之根源,由国民之意思发为强力,虽政府若何压制之,然不径达其目的不止也。”[6]总之,国民有团结的热力、有政治的知识,才能建立真正的立宪国。
《大同报》撰稿人批评了国民在政治上的麻痹性。文元指出,“自二千年以来,由汉而晋而陈而隋而唐而宋而元而明以迄乎本朝,只有皇统变迁问题,而无国民参与政治问题。国民既不负责任,斯政治不免于颓败”。在他看来,甲午战后的变法图强之所以毫无成效,在“无国民责之而遂造成一麻痹不仁之政府”。物必先腐而后虫生,国必自乱而后人乘之,“与其为野蛮的举动以排斥外人,何如为文明的举动以注意内治也。与其持消极的主义以破坏政府,何如持积极的主义以监督政府也”。[10]因此,政府的败坏,与国民不负担监督责任有关;必须国民先负起责任,才能强迫政府担负责任。
留日学生李庆芳曾出版了一本小册子《立宪魂》。李是官费留日的学生,入东京庆应大学法学系。乌泽声为李庆芳的书作序,哀叹“国民既无救国之能力,也无救国之思想,士以思不出位为道德,民以不闻政事为高尚”的同时,表示“文明列国革新之际,不惜以自由之血,招立宪之魂,以国民之颈,撄政府之锋”。他更进而断言:“夫立宪之结果,以国民之血争来者则有效,以政府之笔草就者,必无功。未闻不待国民合群策力要求立宪,而政府反能励精图治实行立宪者。”这里,他明确表明政府主导的预备立宪是不能成功的。而民众主导的国会请愿,也正是要取政府主导的预备立宪而代之,这就是“建设国民的立宪”。在他看来,“苟欲变我垂死就衰之专制国,为耀武雄飞之立宪国,希望之君主,依赖之政府,两无一可。然则能负此宏大艰巨之责任,有此转危为安之魄力者,非我国民而谁”。[17]乌泽声所主张的“国民的立宪”,比简单肯定官方预备立宪的真诚性要深刻得多。因为任何权力,都不会高尚到自套枷锁的程度,只有具有政治知识与经验的国民,才能真正地约束政府。
宪政的本质就是对公权力施以法治的限制,没有任何统治者乐于自戴枷锁。真正的君主立宪,也并不是来源于自上而下的恩赐,而是国民具有相当的政治知识与经验,能够成为制约公权力的实际力量。《大同报》诸人从希望政府采行君主立宪政体,进而重视“国民的立宪”,从主张速开国会,到意识到国会与地方自治双足而行,不能不说是一种认识上的深化。
四
针对革命党人的“排满革命”与统治集团中保守力量的“排汉主义”,《大同报》倡导“满汉平等”、“融合满汉”的“国民主义”。具体地,以开国会解决满汉政治平等,以撤废八旗制度解决旗人的特权问题、经济问题。
乌泽声指出,满汉问题的日激日烈,实为中国之大不幸,为断送中国的导火线。“近年以来,汉人唱排满,满人讲排汉,借此以煽惑国民,无贵贱,无老幼,无男女,心中脑中,无不萦结于满汉问题中,舍满汉交讧两方破裂,无所谓思想,无所谓事业,现今之内政外交,则置于不问不顾之列。”他将鼓吹“排汉排满”者视为“中国之蟊贼,而国民之公敌也”[12]。
乌泽声强调,今日满、汉民族是同民族而异种族的国民。他引用日本学者高田早苗的四大民族要素论,即同一之言语,同一土地住所、生活、职业及共同政治之下,宗教之同一,人种之混同,强调“满汉至今日则成同民族异种族之国民矣”。因为民族是“历史的产物也,随时而变化,因世而进化……故民族以文明同一而团结,而种族则以统一之血系为根据,此民族与种族又不可不分也。”在他看来,国民具有两层含义,即使事实上的含义与法律上的含义,“国民所以异于民族者,民族为文明上之团结,国民则为政治上之团结,民族为人种学上之意义,国民为法律上之意义”[12]。因此人种学上有满、汉之分,法律意义上则同为国民。
乌泽声进而区别了“民族主义”。他分为“血胤的民族主义”及“政治的民族主义”两类,而“政治的民族主义”也就是“国民主义”。他借用英国人甄克思的观点,宗法社会“以种族为国基”,这种“血胤的民族主义”也就是“非我种族,其心必异,非其种者,锄而去之”。不过,“今日此主义已绝迹天壤矣”。“政治的民族主义”即所谓“国民主义”,起于欧洲各国对抗拿破伦的“国民的国家”,也就是“以数民族混成一国民,以一国民组织一国家”。[12]中国的选择应是“国民主义”。
恒钧指出,人民是国家成立的一大要素,“欲释中国之定义,当以满汉蒙回藏五族人民为其构成惟一无二之原因”。他批驳了以纯粹汉人为中国的荒谬性,“世界主义,但有膨胀而无缩小,但取帝国主义,而无取亡国主义”。因此,长城以外为外夷、长城以内为华夏的观念已经不合于世界公理、公道,“今日之中国非汉人之中国,亦非满人之中国,乃满汉蒙回藏之中国”。[18]
《大同报》诸人认为,基于对外的考量,也不宜挑起国家内部的种族矛盾。乌泽声指出:“今日中国求适存于廿世纪国际竞争,有强权无公理之野蛮世界,非合全国之人齐心一致以图之不可,再不容有满汉问题发生。”[12]恒钧亦认为:“对外只有同心努力以撄外患,对内只有研究政治以谋改良,满之不如汉者削之,汉之不如满者改之。庶几享同等之权利,服同等之义务,内力充足,百废俱举,外患或可不来,中国或可久保。”反之,“若两方各持民族主义以求角胜于本国,不问能达其目的与否,就使达其目的,则国土必使缩小,人民必使缩小”。[9]恒钧也接受了严复翻译的《社会通诠》中的历史观,认为社会由图腾而宗法而军国,因此中国也应以军国主义对付外人的军国主义,“但有国界可言而无种界可分”[9]。在他看来,国家之利也是满汉之利,国家之害也是满汉之害,双方因感情的疏远对立而导致抛却政治而言种族,抛却国家而反对立宪,抛却外患而言满汉,实为国家之大不幸。裕端更是指斥排满、排汉之说是“不顾外患,惟招外侮,不察内治,惟事内讧”,他哀叹道:“呜呼噫嘻!亡国灭种,必基于此。吾思之,吾哀之。亡国灭种,吾不暇哀,吾哀亡国灭种之后,四万万之同胞,黄帝之孝子顺孙,负其罪者,不专归于异心异志者也。”[19]
除了呼吁满汉平等,主张国民主义外,他们还提出了具体的改革方案,即开国会以解决政治上的不平等状态,废除八旗制度以解决经济上的不平等状态。
乌泽声认为,种族问题解决难,而政治问题解决易,“种族之冲突,为历史上最剧之争战。”满汉问题是种族问题还是政治问题,他断言为“政治问题”[12]。种族问题的政治化,意味着必须开设国会、改造政府,将军事上、经济上、法律上、政治上各种不平等之制度摧陷廓清,“则满汉之畛畦悉泯,而国家之富强可期”。[13]在他看来,“满汉不融合即以政治不良为之原因,欲求满汉之融合亦当以政治改良为之结果。然不有开国会之原因,又未有收政治改良之结果者,故吾人之所主张即以开国会为融合满汉惟一之利器也。”因此,“未开国会之先,满汉以宗旨上之团结为宪政实行之前导;即开国会之后,满汉以政治上之融合为国民福利之归宿。”也就是说“要求开国会时为融合满汉之先声,实行开国会时为融合满汉之后盾”[13]。
杨度曾在《大同报》发表《国会与旗人》一文,主张裁撤八旗。杨度认为,过去旗人世袭终身充兵,拥有特权,但经过屡次改革官制之后,旗人丧失了特权,只剩世袭终身兵役之义务,而毫无生计自由、经营财产所有权的自由。因此,应该废除八旗军制。《大同报》旗帜鲜明地支持了杨度的观点:“裁撤八旗,示满汉以军事上之平等,停止旗饷示满汉以经济上之平等,嫠定法律示满汉以法律上之平等,改官制示满汉以政治上之平等,则吾人主张满汉平等之目的达矣。”[13]
总之,《大同报》所代表的留日学生,主张国民主义,反对排满排汉的民族主义,希望将种族问题纳入政治解决的轨道内,同时废止早已不合时宜的八旗军制,这是一种成熟的政治理性的表现。
五
从广义的政治革命的角度看,无论是君主立宪,还是共和革命,对于传统的专制政体而言,都是根本性的改造,都是一种政治革命。而从《大同报》所阐述的思想与政见看,他们的政治诉求中是确立了一种“政治现代性”的,这就是:国家的根本目的在保障人民的自由与幸福,政治的统治基础必须基于人民的同意,宪法、国会、责任政府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制度性保障。因此,他们成为清末国会请愿运动中能够认清历史趋势的满族民众的政治代表。
《大同报》也对清廷敷衍宪政大加抨击:“吾不知彼之所谓预备立宪者何在?即使如此预备,吾不知预备若干年而始有实行之一日也。”他们警告说:“若徒作搪塞之具,恐预备未终而吾国之前途有言之不忍言者。”[10]他们看到了清政府所处的危局,“今之政府欲东亦可欲西亦可,专制亦可立宪亦可,乃遨游于东西两可及专制立宪两可之间,以退处于被动地位”[8]。希望清政府顺应民意,挽回被动局面。
但是,基于狭隘的感情,他们将革命党人当成了卖国、祸国的祸害。他们曾如此谴责革命党人,“以君主即国家之原因,生排满之结果;以排满之原因,生反对立宪之结果;以反对立宪之原因,生主张共和之结果。中国之前途,人民之幸福,彼未尝一措意也”,甚至预言对方“流血拼命以去今日之君主,而彼党他日或为其所崇拜之专制魔王如明太祖者也未可知也”[12]。总之,革命党人的政策不足以救国,适足以亡国。
事实上,革命党人的民主共和方案,同《大同报》撰稿人所向往的国家政治建设方向是具有共通性的。辛亥革命时期的立宪与革命之争,既可朝着有利于现代政治文明建设的方向发展,构建政治上的“重叠共识”;也可以沦为你死我活的思想战,消除进步势力的合力。就此而言,这些满族留日学生对革命党人的指控是不公允的。
何况,历史不是纯由理性来推动和解释的,人类非理性的一面、情感的一面,同样左右着历史的进程。这群满族留日学生,部分地与体制内相联系,同时又欲以民众代表自任。但他们既未能在体制内掌握真正的权柄,而皇亲国戚的身份也使汉族民众并未接受他们的领袖身份。兼之满汉矛盾的尖锐化,他们的理性声音只能被时代浪潮所淹没。显然,《大同报》诸人的政治认同,彰显了学理思辩的高度,却不能构成时代思潮的主流,更多的是留下思想史上的意义。
从长时段的历史来看,成功的政治革命应该具有破坏与建设的两面性的。辛亥革命的失败或者还不在于它的不彻底性。真正的历史悲剧性或许在于,它似乎走向了激进的革命者与温和的革命者之间的一场内讧,完成了革命的第一步,也就是破坏的任务;而革命的第二步,即完成政治现代性建构的任务最终却失落了。
[1]林家有:《满族人民对辛亥革命的贡献》,载林家有:《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研究的新审视》,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2]刘晴波:《杨度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3]《大同报出版广告》,载《大同报(第3号)》1907-10-10。
[4]杨度:《题辞》,载《大同报(第1号)》1907-6-29。
[5]《大同报第一号第二号均已出现》,载《中国新报(1卷6号)》1907-7-20。
[6]乌泽声:《大同报序》,载《大同报(第1号)》1907-6-29。
[7]隆福:《现政府与革命党之比较》,载《大同报(第5号)》1907-12-10。
[8]恒钧:《中国之前途(续)》,载《大同报(第2号)》1907-8-5。
[9]恒钧:《中国之前途》,载《大同报(第1号)》1907-6-29。
[10]文元:《论对外患宜注重内政》,载《大同报(第4号)》1907-11-10。
[11]隆福:《论立宪之方针宜专注于政府》,载《大同报(第2号)》1907-8-5。
[12]乌泽声:《满汉问题》,载《大同报(第1号)》1907-6-29。
[13]乌泽声:《论开国会之利(续)》,载《大同报》(第4号)》1907-11-10。
[14]《民选议院请愿书附跋》,载《大同报(第4号)》1907-11-10。
[15]乌泽声:《论开国会之利(续)》,载《大同报(第3号)》1907-10-10。
[16]荣陞:《立宪政体之一斑(续前)》,载《大同报(第5号)》1907-12-10。
[17]乌泽声:《立宪魂序》,载《大同报(第5号)》1907-12-10。
[18]恒钧:《中国之前途(续第二号)》,载《大同报(第5号)》1907-12-10。
[19]裕端:《大同义解》,载《大同报(第2号)》1907-8-5。
Pursuit for Political Modernity under the Pressure of Racial Politics: The Political Identity of Manchu Students in Japan from“Da Tong Bao”
DENG Li-lan
(Social History Research Center,Nankai University,Tianjin300071,China)
A group of Manchu students who had accepted western education in Japan pursued to save China beyond the Qing government and revolutionists.They advocated adopting the political nationalism instead of racism.They claimed the equality between the Man and Han nationalities,and hoped to form the Man Han MengHuiZanginto a whole Chinese nationality.They ascribed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crisis to the problem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and called on a constitution movement to establish a responsible government.An elected parliament was the first step of this movement.They also believed in the theory of social evolution,and chased to bring the most people the greatest happiness.During the XinHai revolution,with the issues of“Da Tong Bao”,their critical attitude towards the despotism and their seeking for a political modernity meant a real political revolution.
constitution;revolution;anti-manchu;parliament
K257.5
A
1671-7023(2011)06-0082-08
邓丽兰(1966-),女,四川沐川人,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民国政治史、近现代中西思想文化交流。
2011-09-21
责任编辑蔡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