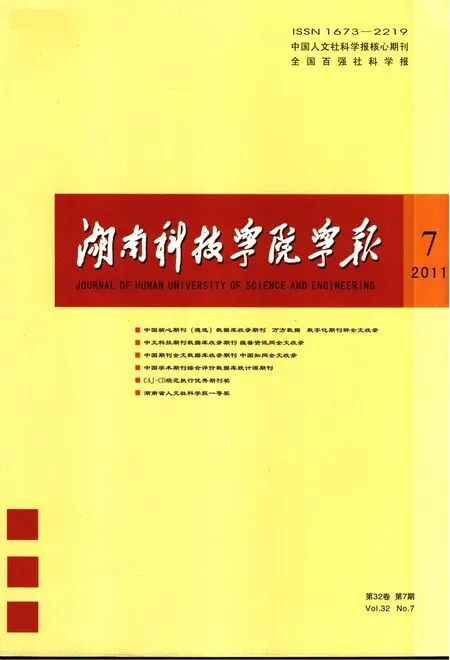性别角色视野下的女书文化
周红金
(湖南女子学院 女性教育研究中心,湖南 长沙 410004)
性别角色视野下的女书文化
周红金
(湖南女子学院 女性教育研究中心,湖南 长沙 410004)
该文从性别理论的视角诠释“女书文化”这一世界留存至今最为古老的性别记忆: 女书是以男性为中心的旧制度主流文化的亚文化,独特的自然环境和多民族互动背景下的人文环境造就了女书文化的唯一性,在其女书作品中反映了女性主体的吁求,并对当地女性性别角色起到积极的社会化功能。
性别;角色;江永女书;女性
人们对性别差异经久不衰的兴趣不是靠单纯的好奇心来维持的,而是来自对性别公正问题的关切。本文从性别理论的视角诠释“女书文化”这一世界留存至今最为古老的性别记忆:女书是以男性为中心的旧制度主流文化的亚文化;而女书文化是由女书作品、家传、做女红、做歌堂、赶庙会和结老同习俗等构建的一个功能强大文化体系,并在其女书作品中反映了女性主体的吁求,并对当地女性性别角色起到积极的社会化功能。性别角色理论的代表人物帕森斯以角色的视角分析了劳动的性别分工,他认为男性承担积极的工具性社会角色,女性承担情感性社会角色。[1]P29假如性别分工低于一定程度,那么婚姻生活就会消失,只剩下非常短暂的性关系。假如两性在根本上没有相互分离开来,那么社会生活的形式就完全不会产生。如果说分工带来了经济收益,这当然是很有可能的。但是,动分工的最大作用,并不在于功能以这种分化方式提高了生产率,而在于这些功能彼此紧密的结合。[2]P24波伏娃则认为女人不是天生的,她从女性主义视角将一个女人的生物学女性与她的性别角色和属性分开,这为我们解读和诠释江永女书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女书的产生和传承都离不开其生存和依附的自然与人文的环境。正是因为其天然土壤的独特性从而造就了女书文化的唯一性。
一 独处一隅的自然环境
江永县位于湘南、湘桂边境,在萌诸、都庞二岭之间,地属南岭山脉的山地丘陵区,四周皆为高山峻岭。江永县从古以来处于楚文化和越文化的夹缝地带、湘粤桂三个行政区的交壤之处,是一个地理偏僻、经济文化落后的山区。从《永州府志》、《江永县志》中可以看到,历代中央政府除在这一带设官理事、放逐罪臣外,几乎不再涉足县境。在漫长的封建社会,这里是朝廷流放发配罪臣之地,也是北方民族南迁避难之所。虽称不上世外桃源,但相对而言,这种闭塞的地理环境客观上影响了中央朝廷和地方封建势力对江永的控制,使江永成为中央与地方封建势力控制相对薄弱的地方。
女书主要流传地江永县上江圩乡,位于江永县东北部。其北有都庞岭,南有萌诸岭余脉铜山岭,同样也是僻壤边城。女书有两个含义:一是指至今流传在江永上江好一带的一种妇女专用的特殊文字,二是指用这种妇女文字创作、记录的作品。不管是属文字范畴的女书,还是文学范畴的女书都与女性创作主体这一特征息息相关。80年代仍在世的会写女书的义年华老人回忆说:“我年轻的时候,会写‘女书’的人很多,村村都有好些懂‘女书’的女子。我的伯娘、舅娘、姑娘、姨娘和她们的老同,都是用‘女书’写信来,写信去的。”[3]P59女书作为一种文字只在女性范围内使用,男性既不认识女书文字,也不想去认识女书,因此也就谈不上用女书来进行创作。男性何止是不用、不懂、不学,甚至在由他们掌握了话语权的正史、方志、族谱中对女书也只字不提。女性对女书无比珍爱,男性对女书不屑一顾,极端冷漠。所有的女书作品都出自当地妇女之手。女书以书面语言为主,有时也使用诗歌和民谣的形式。在过去的中国,妇女一般很少接受教育并受到男人统治,江永的妇女便通过这种独特的方式来分享感情、闲聊家常和交流生活经验。
恩格斯认为,“女性在不同的社会里、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她们的社会地位是根据社会经济、政治关系的变化而变化”[4]P2。而且民族志和历史学资料说明:女性从属男性的社会地位不是跨时期、跨地区、跨领域一直存在的。由于江永地处边陲,远离男权主流文化,在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下,中央朝廷与地方封建势力的控制难以得到有效的实施。主流的男权文化在这里受到了挑战,这里的妇女所受到的封建束缚较别处相对少一些。道光《永州府志·风俗》(卷5下)言:“其生女及并者,朝出耕,薄暮归,栉沐与少年子水亭杂坐讴歌,心许而目成,则倚歌和之,携手同归,父母弗禁。”又这里有男嫁“女”的习俗,寡妇经男方家族的同意可以再嫁,妇女改嫁后也可以带走自己的那份财产等。在江永出现的这一独特的社会性别角色现象,我们可以从文化、经济和政治等纬度来考察社会结构变更下的女性自我定位。
二 多民族互动背景下的人文环境
江永县境内有瑶、汉、苗、壮、侗等17个民族,24万人,其中少数民族人口占53.7%。处于湘桂边境、瑶汉杂居的江永,与瑶文化、壮侗文化及其渊源古越文化关系密切,既有着浓厚的中原文化传统,又杂融了瑶族的文化风俗,还留有古越文化的遗风。这里既有重男轻女的思想观念和男耕女织的生活方式,又有女性掌管家财的母系氏族的社会痕迹;既有三从四德、贞女节妇的传统观念,又有抢婚、不落夫家和妻兄弟婚的原始婚俗及恋爱、改嫁的相对自由。这种博大的奇特的背景文化就是女书生长的土壤,同时,通过对女书文化的多元性、能动性和交差性的研究,得出其产生和传承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中国民族互动和民族团结有力佐证。
对江永县潇水流域地区,女书的使用是独特的。江永县在湖南省的南部,与广西临界。那里的原住民组成了一系列非汉族的部落群。自6世纪以后随着汉文化的入侵,这个地区逐渐被同化了,但是一些固有的风俗习惯仍然存在。比如推迟结婚,即新娘结婚之后回到自己的娘家,直到生了第一个小孩之后才永久性地居住在夫家。在这期间,她偶尔回到夫家居住几次。另一在汉民族和少数民族之间共享的风俗是结拜兄弟、姐妹,这点在很多的口头文化和节日文化中体现出来。在少数民族地区,妇女一般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有相对的性自由。解放前,江永瑶族的宗教信仰、风土人情、风俗习惯都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民间保留的“族谱”、“过山榜”、“千家峒源流记”、“盘王歌”、“女书”、“师公经版”等古籍比比皆是。如:1983年,原中南民族学院讲师宫哲兵(现武汉大学教授)等在考察千家峒过程中,收集了“千家峒源流记”25件,在源口瑶族群众家中找到了一部最古老的瑶族盘王歌手抄本,共七任曲32段,据考是公元1265年的抄本,比正宗景定元年的过山榜早五年,比一般认为最早的盘王歌明宣统年间(1424—1435)要早 170年。2000年江永县民委杨仁里在源口小河边发现《扶灵瑶统纪》,这是江永平地瑶中最全的一部族源史记,它翔实记录了扶灵瑶的山、川、桥、路、田、土、宗、庙、历史、文化、堰坝、官府批文、瑶长制传袭名单等,是一本扶灵瑶的百科传书,有较高研究价值。可见女书在江永一带流传带有浓厚的民族色彩。
一个民族往往将自己的历史,将自己对于环境做出反应的种种经验即文化都儗聚积淀在自己的语言中。女书是妇女思想寄托的一种形式,每年五月十五是妇女拜祭姑婆的日子。在这一天妇女们都会带上自己的女书作品到姑婆庙焚烧,读唱女书,向姑婆诉苦,求姑婆保佑。因此,有很多女书作品是用来敬神的。女书传人的宗教信仰与当地瑶族同胞的宗教信仰一致,可见女书与瑶族有密切的关系。在复杂的社会结构中,正如处于某一社会地位的人其角色不是以单一的、而是以“角色丛”的形式存在一样,其地位也不是单一的,而是多重的,即构成了地位丛(status-set)。默顿提出:“一个人具有一系列不同的地位,而每一种地位都有其自己的角色丛,于是我称之为地位丛。”[5]P111女书妇女在各自的家庭中,她们同样也缠足,没有在户外劳动而是大部分时间在家纺织、缝纫、煮饭和做家务活。妇女们参加丰富的女性传统节日和仪式,建立了她们自己自愿成立的交往网络,即结拜金兰,其中,女书是她们交流的主要媒介。对这个地区的女性而言,一种具有性别特质的文化在被隔离的周围繁荣起来。
三 女书作品中女性主体的吁求
女书通过对男性形象的弱化、淡化甚或隐没来消解这种男性优越意识。女书里几乎找不到一篇以男性为主角的叙事诗,男性要么隐没,要么以一种配角、陪衬的面目出现,将男性从中心地位放逐到边缘地带。女书叙事诗里的男性形象软弱无能、粗鄙不堪。“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生孩子的简单工具。”[6]P52父权文化通过婚姻关系加强对女性的压迫,女书叙事诗通过对传统婚姻模式的突破解构父权制象征社会。
女书的内容80%以上都是诉苦情,用来记述妇女婚前婚后的苦难经历,发泄内心对黑暗社会的愤愤不平。“不论任何阶级,也不论在任何所有制下(尽管这些因素会以有趣的方式改变情况),妇女一般是作为男人的财产在社会生产中的生育和社会化方面起作用。妇女成了私人家庭生产模式的部分生产资料。”[4]P96在这种特定场景通过社会的相互交往塑造成的社会性别角色,一旦差异在创造社会性别时建构起来,这种差异就被用来强化社会性别所谓“本质”,在社会性别行为中进一步表现出来,并合法化地作为社会机制的一定组合。女书作为一种女性叙事的性别叙事诗,是一种基于女性意识的叙事。女性意识主要是指女性作家对女性这一性别特质从发现到审视定位的认知过程。“所谓女性意识,在其表现上大体可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以女性的眼光洞悉自我,确定自身本质,生命意义以及在社会中的地位与价值;二是从女性立场出发审视外部世界,并对它加以富于女性生命特色的理解和把握。”[7]P51女书作品在平白如话的叙述中仍然掩饰不住对女性由衷的赞美。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出,作为一种性别,女性自身的特点,无论是生理上还是心理上的与男性的差异,女性本身是接纳的,甚至是引以为骄傲的,这与父权制文化氛围下女性被鄙视、被厌弃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在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之下,三纲五常和三从四德的封建伦理道德通过对女性的思想、行动各方面的严格的限制和束缚,使女性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受到牵制和排挤,从而无法取得与男子平等的权利。但就是在这样的封建伦理道德的沉重束缚之下,女性仍然发出了对于平等、独立、自尊的吁求。女书作品“虽风格也是哀怨凄凉者多,但这群劳动妇女也有一些反映男女自由求学、平等任宦、要求解放的作品流传下来。”[8]P3
回眸历史,女性被置于父权制主流文化之外这已事实存在,与传统中国社会中产生的女性作品相比,女书写作则是以女性独特的经历和感受,尽力超越男权社会的种种价值标准书写,深入挖掘女性经历和感受中最本质的东西和开阔自身视野的创作。这些创作超出了传统女性写作狭隘性,女书中大声疾呼的是“已是朝廷制错礼,世煞不由跟礼当”,开启的是一个崭新女性主义创作视角,从而丰富了女书文化。
[1]T.Parsons,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the Family. In Ruth Anshen(ed)[A]. The Family: Its Function and Destiny[M].New York:Harper,1949.
[2]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M].渠东,译.北京:三联书店,2000.
[3]谢志民.江永“女书”之谜[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
[4]王政,杜芳琴.社会性别研究选择[M].北京:三联书店,1998.
[5]Robert K.Merton.Therole-set:problem sinsociological theory[J].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1957,(2).
[6]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7]乔以钢.中国女性的文学世界[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3.
[8]李格非.女性文字与女性社会(序言)[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
I206
A
1673-2219(2011)07-0061-03
2011-04-15
周红金(1978-),男,湖南江永人,湖南女子学院讲师,社会学硕士,研究方向为性别社会学。
(责任编校:王晚霞)
——女书习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