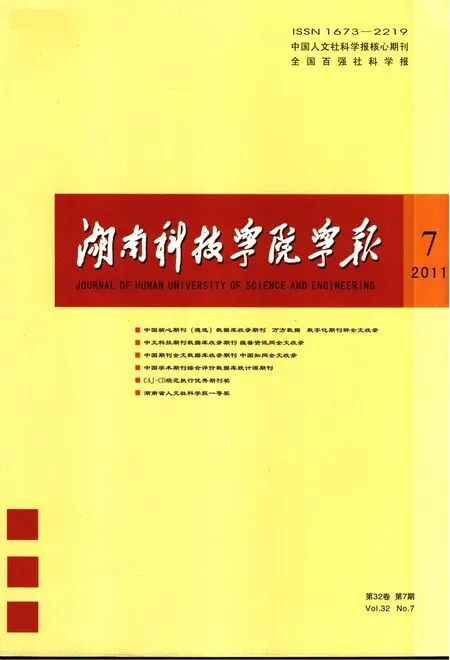其实还是士大夫问题
——高峰访谈录(二)
高 峰
(上海市委党校,上海 200233)
其实还是士大夫问题
——高峰访谈录(二)
高 峰
(上海市委党校,上海 200233)
编者按:本文为《湖南科技学院学报》编辑部张京华于2010年6月赴上海所作高峰先生访谈的一部分,内容主要为学术研究的方法评论,录音整理稿经作者审定并略有修改。
高峰;访谈录;士大夫
一
高峰(以下简称高):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是蛮成问题的。陈寅恪《寒柳堂记梦》未完成稿谈到在洪宪帝制的时候,士大夫那个丑态,看到这个情况,他觉得气节是最重要的,至于是立宪还是帝制,倒是其次。
张京华(以下简称张):是。
高:我非常能够体会他这种说法。有时候你看中国社会,现在哪怕你搞帝制也没关系啊,只要社会能有秩序啊。你人稍微有点气节,这个气节不是说要什么“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没到这么高的层面,就是在台面上也给自己一点面子。现在有些学者实际上是自己不给自己面子是吧?就是你在台面上自己给自己一点面子就可以了。实际上,像张东荪当初讲到中国文化的时候,他也蛮注意这一点,他说清朝之所以在后来一下子垮得那么厉害,武昌起义是很偶然的一件事情。清朝一下子就垮了,这只不过是清朝本身太站不住脚,而并不是因为当时革命党势力有多么大。那么清朝为什么会这么站不住脚,主要是因为士大夫太不像样。
张:清朝最后的退位当时做得很容易。一开始起义的时候好像很壮烈,很艰难,结果后来退位很容易。
高:后来发现很简单。
张:一股风就退位了。
高:可是那个时候,据国外学者研究,清朝的GDP可是世界第一啊。
张:哦,是吗?
高:国际上的经济课题研究说,一直到1889年,中国的GDP还是世界第一。1890年被美国取代,美国世界第一,中国世界第二。
张:1889年那还是慈禧在位啊。
高:慈禧在位。就是说鸦片战争时候,圆明园被烧等等事件出现时,中国的GDP仍然是世界第一。
张:所以当时经济其实不是问题。
高:经济不是问题,是中国文化有问题。我的感觉中国社会出问题一定出在内忧,而不是出在外患。只是因为内部太出问题了,外患才成为患。
张:多少年以来一说清朝就说鸦片战争,就说经济。
高:还是士大夫问题,是内部问题。用现在的话说,是公务员问题。
张:晚清李鸿章、张之洞他们都在位,清流啊。
高:但是这个没用。就是秩序垮掉了。像李鸿章,我看他也是绞尽脑汁。
张:也是硬撑。
高:要没他撑的话,恐怕还更快点。
高:当初,好像是同治中兴的时候吧,好像都认为大清了不得了。当然那时候没有GDP的概念,但是社会经济比较发达,那个船舰从德国买进来了,洋枪洋炮也进来了,北洋水师也建立起来了,那个造船厂也开始建立起来了。好像有一个人,叫什么名字我忘了,曾国藩的一个幕僚,他说我看大清帝国完了,不出五十年吧。他讲这话过了四十六年以后,大清帝国就倒了。曾国藩当时不相信。
张:这是人的问题。
高:社会乱掉了,没秩序。一个社会没有一个最起码的秩序。
张:还是吏治问题。
高:中国的问题也涉及高层。毛泽东针对这一点也有些想法,“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有这种想法。毛泽东一度把公务员打烂,把公检法、公务员全部打烂。
张:他说文化部是才子佳人部,教育部、卫生部是老爷部。其实发动“文革”的好多理由还是有原因的。
高:但是一打烂了呢,社会没人管了。
张:对,他操作不好,但他理由是有的。
高:中国近代史上有两次“公务员”被打烂了,就是官僚制被打烂了,一次是军阀混战的时候,一次是毛泽东的时候。这两次时候社会都还可以,军阀这么混战,社会没大乱。毛泽东时候,三年自然灾害饿死几千万人,社会也没大乱。因为它秩序在,秩序在的话,大家自动会跟这个秩序对位,知道自己是什么本分。
张:以前等级在的时候,那么农民知道自己这个本分,他就老老实实把田种好,他不会寻思去过锦衣玉食的贵族生活。你秩序一打掉了,那么就有人会问:你可以锦衣玉食,为什么我不能?
高:如果天下都去争锦衣玉食,怎么办?
张:高峰你说现在社会,先不说问题吧,问题一下说不完,那么它有一个办法没有?
高:我看没办法,至少我个人认为没什么办法。
张:做研究你是元老级的,应该有些想法。
高:我个人认为没办法。
二
高:一位上海作家来,他说要跟我谈谈中国文化。说到小孩读经,我说我现在不太赞成小孩子读经。他问我为什么不赞成,他倒是很赞成的,他要复兴传统文化。我说因为文化是一种制度性的体制,没这种制度保障了,你要把它重兴,那么社会上是怎么一回事情?经书上是怎么一回事情?你将来只有两种可能。
张:哪两种可能?
高: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就是培养更多的两皮儿、双皮儿。
张:对。
高:现在的小孩子,你镜头对着他,他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什么的都可以讲,但是最后什么事情都干,无所不用其极。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真的相信了经书上说的东西了,那这小孩将来就苦了,你没有给他人生的光明。
张:对。
高:我是不太赞成小孩子读经,因为他们不像我们,他们情况不一样。我们自己是有一个文化认同,他们既然已经生活在这个没有文化认同的世界上,那除非这个小孩将来大起来,他自己由于某种机缘产生了这种文化认同,那么我也支持他。现在有哪个小孩子,他说他感到对社会上的一切他都看不惯?他说他觉得还是儒家文化好?
张:这种很少啊,有也可能是神经病,才会这样看啊。韩寒可能是个特例。
高:是个特例。
张:韩寒不会是神经病,但是他不满意现实世界。
高:对。
张:但他也是个特例,八零后的人很少会这样看。
高:他老是要跟社会逆反一下。
张:他是八零这代的人,而且他是很有钱的。
高:他不靠你这个体制过日子。现在有很多学者,因为在体制内过日子,他会说很多话,他的人格就变得比较差劲儿。
三
高:我现在比较关注社会的行为传统。现在问题比较复杂,过去我们是比较单一的。从清末开始,中国不管是向日本,还是向英美,还是向俄国,向西方学习这一点是不变的,我们都想向西方学习,认为西方比我们强大,所以要向西方学习。我们为什么要学习他们的代议制,并不是因为代议制本身好,是因为他比我们强大,那么代议制可能是他们强大的一个原因。我们要立宪,为什么要立宪?因为西方比我们强大,日本立宪,没多久它就打败了俄国,并不是因为立宪本身好。但是现在呢?最近几十年的发展呢?你看西方金融危机出现了,看来他们的制度也有问题啊。中国的经济发展上去了,中国的GDP现在是世界第二,我们也不比他们差。因为本身你对事物的理解就不是从目的上去理解,而是作为工具理解的,那事情就很难办。所以我们现在,包括我个人都有这种情况,我觉得我们大部分学者现在处于一种茫然状态,因为他们两头落空。
张:怎么理解呢?
高:传统的东西呢他们扔掉了。现在四五十岁的一批学者,至少在二十年前他们还是想向西方学习的。包括像牟宗三他们这一代,向西方学习,特别在政治、在科学和民主这一点上对西方是没有疑问的。包括在一些行政制度上、管理制度上,对西方都是没有疑问的。
张:是的。
高:我们只是在儒家道德上,在道家境界上,在个人的心境上,可以保留我们自己的东西,其他东西学习西方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现在是西方也不过如此。可你再回过来吧,现在五十岁一代的人,这一代学术界的人能够担得起中国的传统文化吗?恐怕没有几个人担得起。有很多人做经学研究,我甚至能看出他这文章就是从电子文献上引上去的,我知道有些学者在做学术史。
张:他本来就把经学当史料,而史料俗一点说就是材料,材料那自然就是抄抄、贴贴。
高:从思想史上下降一点,我比较注重中国社会。并不是老说中国五千年文化传统,我比较注重人的社会行为。实际上,衡量一个社会好不好,衡量中国好还是西方好,有没有个标准,搞不大清楚,学术界的观点很不一致。现在学术界当中民族主义势力也蛮大,有一批学者专门研究西方的保守主义。我的看法是,在法学界里头似乎自由主义比较多一点,政治学界和国学界里头新左派和民族主义都不少。现在的问题是,实际上你一上来,你这个目标就不明确,你学西方并不是认为这个代议制本身有优点,而是因为代议制能带来强大,现在我们不用代议制我们也强大,这个就比较成问题。所以,我最近一段时间是比较悲观的,因为身体不好,我原先心里想到了很多的问题,但是很少有条件能够自己亲自去做这些课题。我看现在做学术史的无非就是几个路数,一个路数是最下等的,就是外面搞课题的那种研究,把史料堆积起来,堆得越多越好,号称是朴学,号称学陈寅恪,这是最下等的。上等一点呢,注意到这里头一些社会学层面的东西,注意文化的影响,这算是目前比较好的,能够注意到社会思潮和学术的互动,但也仅此而已。但是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就思想本身解读思想这点没弄清楚,这是硬件。社会跟思想互动,你把握这个思想没有?我们说要论证康德的思想跟当时的启蒙运动、德国社会的互动关系,前提毕竟还是以对康德思想本身的研究为基础的,这个是硬件,其他是软件。但这部分东西是最难做的。徐复观老早就说过,经学这样搞不行,老是说谁怎么说、谁怎么说,谁谈谁、谁谈谁,这样不行。你得把两汉当时的经义给说出来。比如说,两汉公羊家有一套理论,他们是怎么说的,古文家他们是怎样说的。但是这个东西没人搞,这个部分是硬件。现在的学者往往图方便,急于出成果。
张:你说硬件,其实就是一些很客观的问题,必须得好好梳理的,不能随便编造的。
高:对。现在学术界喜欢研究“思潮”,我承认“思潮”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就像英国剑桥学派说的那样,就是一种思潮的兴起不是突如其来的,一种学说兴起之前,往往社会上已经有很多类似的说法了。然后再有某个大人物倡导,再由国家执行就产生了,在这之前,社会上已经有很多这方面的说法流行着。英国很多思潮,乃至西方近代很多学说的产生都是这样的。但是实际上又不完全是这种情况,所以“思潮”的研究不能完全取代对某些思想当中一些逻辑脉络的研究。用我们中国传统说法,这种社会方式的研究是外学,而这个思想传统本身的研究是内学。但是现在搞“内学”的人越来越少了。
张:所谓“思潮”实际上有点儿贴不上是吧?似是而非的东西多一些。
高:实际上大家都不知道,所以大家就都乱说。乱说的东西太多了。
张:现在许可乱说,许可任何做法。
高:后来我就发现,一些新书里头乱说。乱说的多了,接下来还有几个人会去自己读《四书》《五经》?那还不是都听你们这几个专家学者的?
张:一代传一代,但都是复述。
高:后来就没办法了,再过四五年就没办法讲了。现在国学已经没办法讲了,再过四五年就更没办法讲了,这比较麻烦。所以我就觉得社会上如果不那么提倡国学,能让一部分人自己真正对国学有认同感,或者哪怕是有忤逆感都行,让他们自己去搞,可能还好一点。
张:那他们可能是在这个社会上得到既得利益最少的一些人。
高:差不多可以这样说。
张:也可以说是最无私的一些人,“无欲则刚”。另一方面,事实上你想欲也欲不到啊。
高:对。
张:所以只能刚,没办法。你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
高:是的。实际上我缺陷很多,因为很多地方借不了体制的光,但是也有一大优点,就是我看问题不受自身利益影响。
张:你说话就非常公正,没有主观的成见,用不着去考虑别的东西。
高:我也不考虑我跟某个学派或者某个人的关系什么的,我自己想发表什么意见我都可以发表,我只要觉得这个看法自己心里感觉比较踏实,我就可以说。本来呢,我一直不想特别挂在某个学派上,这个倒不是这两年身体的关系,我一直有这个看法。记得德国的一个历史学家说过,各个时代,它的发展可能有高潮有低潮,但是在上帝眼里是平等的。这个话我不敢说,因为我不知道上帝眼里看世界是什么样的,但是我认为各种学说、各种思想,都可以在某一个层次、某一个阶段上有它的一些成见,很多学说都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
张:是。
高:就是说,不必提倡哪个就必须要打倒另一个。因为我发现现在的学术界已经有这种倾向,就是无谓的党同伐异。搞西学的也有,搞国学的也有。实际上,老实说现在学者搞党同伐异,特别是国学,搞党同伐异也没这个资本。
张:现在有些不同意见在争,国学上就谁跟谁在争,什么观点跟什么观点在争,争得好像蛮凶的。就国学一个概念,大家的意见也大不一样。
高:现在国学这个争呢已经不太像样,已经落到第二义上了。因为现在很明显,你看关于国学的很多争论一上来就直接跟既得利益挂钩。
张:是。
高:有很多就是直接的利益相争。
张:那你说得太对了。现在怎么争其实都离不开利益。没有学派,只有宗派。
高:一上来就是第二义。第一义,实际上真正的东西,没几个人关心。报纸我有时候也看,看到他们国学家在争,我觉得一上来就是第二义。
张:是的。
G09
A
1673-2219(2011)07-0004-03
2010-06-21
高峰(1962-),男,上海人,毕业于复旦大学哲学系,任教于上海市委党校,兼任湖南科技学院濂溪研究所特聘教授。自2000年以来居家养疴,治学不辍。出版著作《大道希夷——近现代的先秦道家研究》、《禅宗十讲》、《春秋穀梁传译注》,编纂《十家论佛》等多种。
(责任编校:张京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