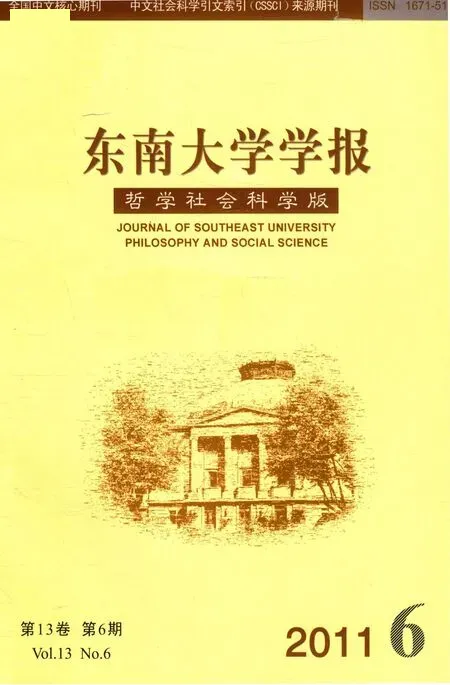论姚鼐的语言艺术
周中明
(安徽大学中文系,安徽合肥230039)
论姚鼐的语言艺术
周中明
(安徽大学中文系,安徽合肥230039)
姚鼐散文的语言艺术成就和特色表现在寓丰富于简洁、寓深意于言外、寓工妙于自然、寓浓郁于平淡、寓神气于音节等五个方面。姚鼐之所以能创造出上述语言艺术成就和特色,在于其能自觉地从语言艺术的角度把握文学的特性,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能熟练地掌握和发挥汉字和汉语言的特长,注重对现实的“亲览”等。
桐城文派;姚鼐;散文;语言艺术
为什么姚鼐的文章会被前人推崇为“举天下之美,无以易乎桐城姚氏者也”[1]?为什么连指责桐城派“舍事实而就空文”的近代著名学者刘师培,也盛赞“惟姬传之丰韵,……则又近今之绝作也”[2]?这其中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却不能不归功于姚鼐认识到:“文章之精妙,不出字、句、声、色之间”,从而在语言艺术上取得卓越成就。语言艺术不难于简洁,而难于寓丰富于简洁;不难于有深意,而难于寓深意于言外;不难于工妙,而难于寓工妙于自然;不难于浓郁,而难于寓浓郁于平淡;不难于有节奏,而难于寓神气于音节。姚鼐散文语言艺术的卓越,就在于它对这些难点有重大突破,从而创造了新的鲜明特色。请看笔者下面的举例论述。
一、寓丰富于简洁
由于世之不善于文者,或义失之赘,或辞失之芜,于是尚简洁之说兴盛。早在晋代陆机《文赋》即指出:“要辞达而理举,故无取乎冗长。”[3]138唐宋倡导古文运动的大师皆崇尚简洁,如柳宗元称赞“谷梁子、太史公甚峻洁”[3]462,欧阳修推崇文章“简而有法”[4]33。桐城文派更以提倡简洁著称。姚鼐说:“大抵简峻之气,昌黎为最,更当于此著力。”[5]又说:“作文须见古人简质、惜墨如金处。”[5]他在删削了陈硕士的文稿之后说:“陈无己以曾子固删其文,得古文法,不知鼐差可比子固乎?花木之英,杂于芜草秽叶中,则其光不耀,夫文亦犹是耳。”[5]
不但中国作家注重行文的简洁,外国作家也强调:“精确与简洁,这是散文的首要美质。”(普希金语)[6]269
仅仅是删繁就简,不难,难的是不只要简洁,还要精确、形象、传神,有丰富而深长的意味,做到寓丰富于简洁。那么姚鼐的作品究竟是怎样做到寓丰富于简洁的呢?
首先,用字极其精确、形象、传神,内涵丰富,意味深长。
例如他写沈锦在任顺天府南路同知期间,因蠡县“潴龙河涨,欲决堤矣,君尽力护之,身立风雨,堤竟以固。以艰去,蠡民泣送者塞路。”这个“塞”字,不只形象地刻画出“泣送者”的人数众多,而且蕴含蠡县人民对沈锦尽力护堤的那种衷心感激,听说他“以艰去”,即因亲人丧事辞官而去的那种依依不舍的惜别之情。如果把它改成“蠡民泣送者甚多”,那就既不及“塞路”二字形象如绘,令人如亲历其境,感同身受,又显得过于直白,毫无耐人寻味的魅力。
姚鼐的寓丰富于简洁,绝不只表现在个别字句的选用上,更重要的是反映在通篇文章的整体构思、选材和描写上。在清代桐城文派出现之前,人们往往把简与繁对立起来,如清代著名学者顾亭林说:“辞主乎达,不论其繁与简也。繁简之论兴,而文亡矣。”[7]而姚鼐的寓丰富于简洁,则避免了简与繁的矛盾。因为姚鼐认为:“理得而情当,千万言不可废,犹之其寡矣。”[8]104他不是以字数的多少、描写的详略为繁简的标志,而是遵从其桐城文派祖师刘大櫆的教诲:“凡文笔老则简,意真则简,辞切则简,理当则简,味淡则简,气蕴则简,品贵则简,神远而含藏不尽则简,故简为文章尽境。”[9]
为此,我们不妨举其《游双溪记》的全文为例:
乾隆四十年七月丁巳,余邀左世琅一青、张若兆应宿,同入北山,观乎双溪。一青之弟仲孚,与邀而疾作,不果来;一青又先返。余与应宿宿张太傅文端公墓舍,大雨溪涨,留之累日。盖龙溪水西北来,将入两崖之口,又受椒园之水,故其会曰双溪。松堤内绕,碧岩外交,势若重环。处于环中以四望,烟雨之所合散,树石之所拥露,其状万变。夜共一灯,凭几默听,众响皆入,人意萧然。
当文端遭遇仁皇帝,登为辅相,一旦退老,御书“双溪”以赐,归悬之于此楣,优游自适于此者数年乃薨,天下谓之盛事。而余以不肖,不堪世用,亟去,早匿于岩窔,从故人于风雨之夕,远思文端之风,邈不可及。而又未知余今者之所自得,与昔文端之所娱乐于山水间者,其尚有同乎耶,其无有同乎耶?[8]223-224
双溪,在安徽省桐城县西北的龙眠山麓。此文是乾隆三十九年(1774)姚鼐辞官归里之后,游览清初大学士张英晚年退居和死后墓葬之地——双溪而作。篇幅简短,而内涵丰瞻,情韵悠长,堪称“简为文章尽境”的代表作之一。它融写景、吊古与抒发自己的感触于一体,写景如“松堤内绕,碧岩外交,势若重环。处于环中以四望,烟雨之所合散,树石之所拥露,其变万状”。以松密如堤,称之谓“松堤”。以岩石上布满碧绿的青苔,称之谓“碧岩”。多么简洁而新鲜!细雨如烟,在风中时合时散。簇拥密集之树,光秃显露之石,合称为“树石之所拥露”。这一切在风雨中“其状万变”,显得千姿百态,胜似一幅优美的风景画,令人赞赏不已!接着写“夜共一灯,凭几默听,众响皆入,人意萧然”,则不仅把读者仿佛带入了一个真实而又梦幻般的仙境,而且更使作者那孤寂凄凉又悠然自得的心情宛如活现。吊古是本文的重心所在,然而它前有“宿张太傅文端公墓舍”作铺垫,后有“御书‘双溪’以赐”作呼应,因而使之完全跟“游双溪”形成不可分割的整体。张太傅文端公,即张英(1637—1708),字敦复,号乐圃,安徽桐城人。康熙六年(1667)进士,以编修充日讲起居注官,入直南书房,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卒谥文端,雍正即位后赠太傅。此文写张英以其深得康熙的重用,“登为辅相”,及退休后的“优游自适”,来反衬作者的“不肖,不堪世用”,只能“蚤匿于岩窔”。于今“从故人于风雨之夕”,怎能不感慨丛生呢?这里面该是有多么丰富的内容可写啊!然而此文却只以“其尚有同乎耶,其无有同乎耶”的问句作结,不只使其辞官后的“自得”之情跃然纸上,而且以其无穷余味发人深省。
由此可见,此文写得是多么“意真”、“辞切”、“理当”、“品贵”、“味淡”而“气蕴”,“神远而含藏不尽”,正因为作者如此从多方面以“简为文章尽境”,所以他就使“简”与“繁”的矛盾迎刃而解,达到了寓丰富于简洁的至美境界。
二、寓深意于言外
如果说寓丰富于简洁主要是得益于桐城派祖师刘大櫆的教诲,那么,寓深意于言外,则更体现为姚鼐的独创了。我国“古人为诗,贵于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10]277。宋代著名诗人梅尧臣说:“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他并举例说:“若温庭筠‘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贾岛‘怪禽啼旷野,落日恐行人’,则道路辛苦,羁旅愁思,岂不见于言外乎?”[11]267明代袁中道也说:“天下之文,莫妙于言有尽而意无穷。”[12]寓深意于言外,使散文达到跟诗一样含蓄有味、咀嚼不尽的优美境界,这恰恰是姚鼐散文语言艺术的又一显著特色,不过它不同于诗歌的“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而是从散文的特性出发,主要表现在句法的创新上。
(一)前后矛盾句法
例如他写朱澜在担任献县、河间县治河官时的遭遇:“公治运河有绩,而上官恶之,以报水迟解其职。”[8]323他既“治运河有绩”,理应得到褒奖或升迁,为什么反而“上官恶之,以报水迟解其职”呢?作者正是用这种前后矛盾的句法,促使读者不能不深思其言外之意:身为“上官”,怎么竟如此嫉贤妒能、颠倒是非、胡作非为呢?封建吏治怎么会容许这样的“上官”恣意倒行逆施呢?这该是令人多么怵目惊心啊!然而这一切作者皆未明言直叙,仅是通过前后矛盾的句法,使人“思而得之”。如此“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岂不显得比明言直叙更具艺术魅力?
(二)反差衬托句法
例如他在《朝议大夫临安府知府江君墓志铭并序》中写道:“临安府所属夷氓土司十,掌塞十五。旧土官谒知府,其仪严甚。知府坐堂上如神,阶下跪拜惶迫,不闻一言而出。君独接以和易,赐坐与问,夷情具悉,土官感恩,奉命愈谨,而事大治。”[8]366-367其主旨是要表彰江濬源为官的政绩。然而作者却以“旧土官谒知府,其仪严甚。知府坐堂上如神,阶下跪拜惶迫,不闻一言而出”,作为强烈的反差,来衬托“君独接以和易,赐坐与问,夷情具悉,土官感恩,奉命愈谨,而事大治。”[8]366-367作者采用如此反差衬托句法,不仅更加凸显出江君为官的作风平易近人,洞悉下情,得到土官的拥戴,终于取得了“事大治”的卓越政绩,而且以一个“独”字揭示出像江君这样的好官吏是独一无二的,在他之前或之后的历任知府皆是坐堂上如凶神恶煞,除了令下属“跪拜惶迫”,自己作威作福之外,毫无政绩可言。这一反差衬托,使读者足以想象其言外之意:在那个封建社会中,该有多少这类令人可畏可憎的封建官僚!江君这样独一无二的好官既然已经逝世,靠那些只知作威作福的封建官僚岂能达到“事大治”?这种言外之意,该是多么底蕴丰厚,令人玩味不已啊!
(三)彼此对比句法
例如他在《左众郛权厝铭并序》中写道:“其后一青丞湖北县,以获盗功,升为令。入京师,过余旅舍,篝灯夜对太息,忆君与应宿,虽为诸生,而方艺花竹为园,遨游歌咏山水,邈然不可逮也”[8]183-184。左众郛(1729—1775),明末清初爱国政治家左光斗的四世孙,安徽桐城人。毕生喜作诗自娱。姚鼐与他及其兄一青、妻弟应宿,四人从小就是“年相若”“志相善”的同里好友。此文即作于姚鼐辞官之后,四人“复聚于里中”的次年。它名为为左众郛作《权厝铭并序》,却以其兄一青与他及其妻之弟应宿作对比,说明一青在湖北虽由县丞而有功升为县令,他不但一点也不感到欣喜和高兴,相反,却忧心重重,羡慕众郛和应宿,虽然在科举上不得志,只考个秀才,不能做官,但他们因此而过着“方艺花竹为园,遨游歌咏山水”自由自在的生活,使他这个县令不禁深深地感叹远不可及。如此鲜明的对比,使读者不能不深思其言外之意:热衷于追求科举取士,即使如愿以偿,进入了封建官场,又有什么意思?哪有不做官,回归自然,过个性自由的生活来得自在、幸福呢!封建文人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呢?这里应该是反映了对封建统治的多么不满、哀怨、悲愤和失望的思想感情啊!
这种追求言外之意的句法,恰如姚鼐的侄孙和学生姚莹所说:“先生文不轻发议论,意思自然深远,实有此意,读者言外求之。”[13]137当代作家叶圣陶也说:“文艺作品往往不是倾筐倒箧地说的,说出来的只是一部分罢了,还有一部分所谓言外之意、弦外之音,没有说出来,必须驱遣我们的想象,才能够领会它。如果拘于有迹象的文字,而抛荒了言外之意、弦外之音,至多只能够鉴赏一半;有时连一半也鉴赏不到,因为没有说出来的一部分反而是极其重要的一部分。”[14]11
三、寓工妙于自然
追求“言外之意”,绝不是可以忽视“言内”的工妙,而是以“言内”的工妙为前提的。因此,我们有必要继续探讨姚鼐的文章是怎样做到“言内”工妙的。宋代叶梦得的《石林诗话》说:“诗语固忌用巧太过,然缘情体物,自有天然工妙,虽巧而不见刻削之痕。”[15]431可见我国古代诗歌早就创造了寓工妙于自然的艺术经验。姚鼐的散文创作,正是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他说:“文之至者,通于造化之自然。”[8]104“文章之境,莫佳于平淡,措语遣意,有若自然生成者。”[8]289所谓“措语遣意”,就是要讲究语言运用的工巧奇妙,只不过这种工妙,要达到“有若自然生成者”,也就是要寓工妙于自然。
那么,姚鼐的散文又究竟是怎样做到寓工妙于自然的呢?
(一)化无形为有形,使之具形象的直观性和生动性
例如他写“左笔泉先生之文,沈思孤往,幽情远韵,澄澹泬寥,如人入寒岩深谷,清泉白石,仰荫松桂之下,微风泠然而至,世之尘埃不可得而侵也。”[8]58它不是以抽象的叙述,而是以形象的描绘,写出了他读左笔泉之文所获得的独特感受。那“寒岩深谷”、“清泉白石”,该是多么优美诱人的境界!“仰荫松桂之下,微风泠然而至”,又该使人感到多么惬意!“世之尘埃不可得而侵也”,则更是高尚而可贵之至!它把“沈思孤往、幽情远韵,澄澹泬寥”等抽象的叙述,顷刻转化为别具诗情画意的至美境界,使读者从生动的形象之中,既极其奇妙地获得了对左笔泉之文的深刻感受,又十分自然地得到了读姚鼐工妙之文备感心旷神怡的艺术享受。
(二)化静为动,使之别具无比优美的意境和极其动人的艺术魅力
例如在《游灵岩记》中,他写“灵岩寺在柏中,积雪林下,初日澄彻,寒光动寺壁。”[8]222灵岩寺,是法空禅师于北魏正光年间(520-525)始建于灵岩山下。寺中的四十罗汉像为宋代宣和年间(1119—1125)所塑。皆属著名古迹。“寒光动寺壁”,“寒光”本是无形的,“寺壁”本是静止的,加一“动”字,即化无形为有形,化静为动,使那风吹树枝摇动,寒光使摇动树影照在寺壁上,即形成那生动活泼、优美胜于画的“寒光动寺壁”奇观景象,不只给人以身临其境的真切感、形象感、生动感,而且由此产生一种强大的艺术魅力,令人心旷神怡,赞美不绝。
在登上灵岩山之后,作者又写道:“登则周望万山,殊骛而诡趣,帐张而军行。”那四周此起彼伏的崇山峻岭,无疑是静止的。然而作者巧妙地以“殊骛而脆趣,帷张而军行”,把群山的气势写成如万马奔驰般奇形怪状,如帷幕张开、军队前进般雄奇壮观。这看似作者的突发奇想,实则恰如下文所写五胡十六国战乱时期,“当苻坚之世(十六国时期的前秦皇帝338—385)竺僧朗在琨瑞大起殿舍,楼阁甚壮”等历史人文景观相契合,显得十分自然贴切,仿佛把人们带入了那战乱的年代,不只意境优美壮观如画,且有一股足以引人深思遐想的艺术魅力。
(三)化无情为有情,使之更加妙趣横生,令人玩味
例如他在《游媚笔泉记》中写:“溪有深潭,大石出潭中,若马浴起,振鬣宛首而顾其侣。”[8]220“大石出潭中”,这本是既无生命,更无情感的自然景象,然而作者从水中大石的形状,巧妙地把它想象成“若马浴起”,赋予它以马的形态和生命,接着又写它“振鬣宛首而顾其侣”,即振动马鬃而回头看它的伴侣,使之成了含情脉脉,令人为之留恋忘返的奇妙景象。如此化无情为有情,就使本来死板单调的自然景象,被描绘得活泼生动、妙趣横生,显示出语言艺术所特有的魅力,给人以欣喜愉悦的艺术享受。
又如在《观披雪瀑记》中,他写披雪瀑“水源出乎西山,东流两石壁之隘。隘中陷为石,大腹弇口若罂,瀑坠罂中,奋而再起,飞沫散雾,蛇折雷奔,乃至平地。”以“大腹弇口若罂”,形容瀑水在狭谷中冲击成的石潭,不只使其形状如绘,而且化陌生为眼熟能详,令人倍感亲切可喜;接着以“飞”、“散”、“折”、“奔”四个动词,与“沫”、“雾”、“蛇”、“雷”四个名词,分别组成“飞沫散雾,蛇折雷奔”两句,即把那“瀑坠罂中,奋而再起”的景象比喻得有形有态,有神有气,有声有势,用字既简练之极,所刻画出的境界却又绚丽多姿、新奇壮观。令人不禁为之心驰神往,惊喜不已!
上述例证皆说明,姚鼐之所以能寓工妙于自然,是因为他作为“艺术家所见到的自然,不同于普通人眼中的自然,因为艺术家的感受,能在事物外表之下体会内在的真实”。“通过他的与内心相应的眼晴深深理解自然的内部”。[16]19因此姚鼐所追求的“自然”,绝非排斥或轻视人工技巧,而是要以自然为基础为前提,既充分发挥艺术家的洞察力和想象力,使其妙笔生花,又使这种工妙显得恰如自然天成,毫无人工刻意做作的痕迹,从而创造和达到了寓工妙于自然的至美迷人的境界。
四、寓浓郁于平淡
姚鼐说:“文章之境,莫佳于平淡。”[8]289可见他是以“平淡”为文章的至美境界。然而他所追求的“平淡”,绝非指平淡无味,而是指平淡自然的境界,是寓浓郁于平淡。因此,这种平淡之境,“使人初对,或淡然无足赏;再三往复,则为之欣忭恻怆,不能自已。此是诗家第一种怀抱,蓄无穷之义味者也。”[8]294如此说来,姚鼐的散文创作又究竟是怎样寓浓郁于平淡的呢?
首先,善用人物语言,使之看似平淡无味,实则旨味无穷。
例如姚鼐在《刘海峰先生传》中写道:当康熙末,方侍郎苞名大重于京师矣,见海峰,大奇之,语人曰:“如苞何足言耶!吾同里刘大櫆,乃今世韩、欧才也。”自是天下皆闻刘海峰。[8]308文中引用方苞“语人曰”几句,看似平淡无奇,实则字字千钧。它把方苞的自谦、重才、识人和竭力提携同乡后辈的高尚品格和冲天豪情皆浓缩于中,刻画得可谓如跃眼前,令人不能不为之瞿然感奋,由衷钦佩!
《清史稿·刘大櫆传》没有引用方苞的原话,只写刘大櫆“始年二十余入京师,时方苞负海内重望,后生以文谒者不轻许与,独奇赏大櫆。”[17]这跟上述姚鼐所写的相比较,即不难看出,姚鼐通过人物语言寓浓郁于平淡的可贵;《清史稿》的纯用作者叙述,不但显得十分平淡无味,而且还歪曲了方苞的形象,方苞为什么对“后生以文谒者不轻许与,独奇赏大櫆”呢?这岂不意味着仿佛是说方苞对刘大櫆出于同乡私情么?
《道光桐城续修县志·刘大櫆传》则写刘与吴阁学士玉“偕游京师,一时贤士大夫咸惊异其文,同里方侍郎苞尝曰:‘刘子今之韩愈也’。”[18]这虽然也引用了方苞赞赏刘大櫆为“今之韩愈”的话,但跟姚鼐所引用的方苞的话相比,则味同嚼蜡,黯然失色,完全失去了作为方苞的人物语言所特有的语气、口吻、神情、品位、气概等丰富的内涵和浓郁的情感。
可见用不用人物语言,怎样运用人物语言,这对能否寓浓郁于平淡,皆至关重要。
其次,善于描写人物,使之看似平淡无奇,实则贯注了作者的浓郁感情和深广意蕴。
例如他在《继室张宜人权厝铭并序》中写道:“宜人十七岁而归余,三十一岁而没。上事姑,中接娣姒,下抚诸子婢仆,无以异今时女子,而悖傲苟贱之事,所必无也。治家不能极于俭啬,而矜奢纵佚之事,所必不为也。尤喜称人之善,闻人不善,虽于余前亦绝不言。余迂谬违俗,仕不进而家不赢,宜人不怨,顾以为宜。然以余所遇不偶,独幸得宜人偕居室十五年,而今又死矣!……既没,所出子女各二,幼不甚知哀,而长女之恸不可闻。”[8]213乾隆四十三年(1778),姚鼐携其继室张宜人任教于扬州梅花书院。张宜人因“多产气虚”而于闰二月末殒于扬州。作者的遣词造句颇费匠心,如称张宜人对待长辈、同辈和小辈,“无以异今时女子,而悖傲苟贱暴虐之事,所必无也。治家不能极于俭啬,而矜奢纵佚之事,所必不为也。”前后字句,既对仗工整,又不刻板划一而富有变化;热烈赞誉,而又不过分夸饰,把一个善于待人和治家的贤妇形象,描绘得既属普通的常人,又贤良得可亲可敬。“余迂谬违俗……独幸得宜人偕居室十五年,而今又死矣!”此数句用笔极平淡,却不只把妻子对丈夫的体贴之心,丈夫对妻子的感激之情,皆刻画得如浓墨重彩,动人心魄,而且从中寄寓了作者对世俗和仕途颇为愤懑不满之意。“既没,所出子女各二,幼不甚知哀”,一句即活画出因其幼小而不懂事,因其“不甚知哀”而令人感到更加悲哀;“长女之恸不可闻”,这“恸不可闻”四字,看似平淡得不能再平淡了,而其实则寄寓了其长女因母逝世而悲痛欲绝以致伤心恸哭而达到令人“不可闻”的地步,其所表现的母女情深该是何等浓烈啊!
五、寓神气于音节
在姚鼐看来,最为重要的是:“意与气相御而为辞”,“文字者,犹人之言语也。有气以充之,则观其文也,虽百世而后,如立其人而与言于此;无气则积字焉而已。”[8]84这跟桐城文派的祖师刘大櫆所说的是一脉相承的:“行文之道,神为主,气辅之。”“神者气之主,气者神之用。”“神气者,文之最精处也;音节者,文之稍粗处;字句者,文之最粗处也。然论文而至于字句,则文之能事尽矣。盖音节者,神气之迹也;字句者,音节之矩也。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19]137姚鼐自己也说过:“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学者之于古人,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终则御其精者而遗其粗者。”[20]因此,我们这里有必要进一步探讨他的语言艺术究竟是怎样寓神气于音节的。
(一)以前后重复递进的字句,从而在音节上形成神浑气灏的回环美
例1:文之雄伟而劲直者,必贵于温深而徐婉;温深徐婉之才,不易得也。然其尤稚得者,必在乎天下之雄才也。[8]48
例2:夫内充而后发者,其言理得而情当;理得而情当,千万言不可厌,犹之其寡矣。[8]104
例3:虽然,如君年富而质美,进修而日强,且志日慕乎道德之盛。夫道德之盛者,不傲世而立名,不离物而矜己,谦而光,偕乎俗而不流。[8]108
上述三个例证,有其共同的特点:(1)前后皆有重复的字句,如“温深而徐婉”与“温深徐婉”,“理得而情当”与“理得而情当”,“道德之盛”与“夫道德之盛”,这种重复就在音节上形成回环往复;(2)从句意上看,它不是重复,而是递进,是通过回环往复,更有力地表达深一层的语意;(3)因而,一经朗读,就会使人感受到神浑气灏的回环美。
(二)以一系列的整齐排比语句,从而在音节上形成神远气逸的整齐美
例1:夫器莫大于不矜,学莫善于自下,害莫深乎侮物,福莫盛乎与天下为亲。言忠信,行笃进,本也;博闻、明辨,末也。[8]110
例2:太姒之所志,庄姜之所伤,共姜之所自誓,许穆夫人之所闵,卫女、宋襄公母之所思,于父母、于兄弟、于子,采于《风》诗,见录于孔氏,儒者不敢议;独后世有为之者,则曰不宜,岂理也哉?[8]121
例3:今夫闻见精博至于郑康成,文章至于韩退之,辞赋至于相如,诗至于杜子美,作书至于王逸少,画至于摩诘,此古今所谓绝伦魁俊,而后无复逮者矣。……然而究其所事,要举谓之为人而已,以言为己犹未也。[8]126
这三个例证皆说明,作者以一系列的整齐排比语句,或从性质、范畴上,指明“器莫大于”、“学莫善于”、“害莫深乎”、“福莫盛乎”是什么,或列举周文王之妻太姒以及庄姜、共姜、许穆夫人、卫女、宋襄公母等众多古代妇女的诗被孔子采录于《诗经·国风》之中,以批驳妇女不宜作诗的非议,或列举“学博”、“文章”、“辞赋”、“诗”、“书”、“画”等六个领域成就“绝伦魁俊”的人才,他们从西汉的辞赋家司马相如(前177—前118)到唐代的古文家韩愈(768—824),时间跨度长达九百余年。这就使读者的视野和胸襟大为开阔,感到有股排山倒海、波涛汹涌般的气势,令读者尽情领略其神远气逸的整齐美。
(三)以前后工整对称的字句,从而在音节上形成神伟气高的对称美
例1:今夫豫章松柏,托乎平地,枝柯上干青云;依于危碕,岸崩根拔而绝,土附之不足也。[8]110
例2:人观其言动恭饰有礼,而知其学之邃;读其文沖夷和易而有体,亦知其必为君子也。[8]193
例3:成祖天子之富贵,随乎飘风;正学一家之忠孝,光乎日月。[8]235
上述例证分别以“托乎平地”与“依于危碕”、“人观其言动恭饰有礼”与“读其文沖夷和易而有体”、“成祖天子之富贵”与“正学一家之忠孝”相对称的描写,显得形象鲜明,对比强烈,再三诵读,会令人感受到其神伟气高的对称美,尤其是方孝孺那不惜杀身成仁而“光乎日月”的献身精神,在那个旧时代实在具有动天地、泣鬼神的力量,把神伟气高的对称美发挥到了极致。
(四)以前后反差衬托的字句,从而在音节上形成神变气奇的抑扬美
例1:其自奉甚陋,或人所不堪,虽其家人皆窃笑之;然至族党有缓急,出千百金不惜也。[8]170
例2:余论说学问,必崇古法,盖世人所谓迂谬者;春池时独能信吾说而不疑,余固贤之,知其异矣。[8]298
例3:其于经也,辞义训诂之小者,未尝一一拘守程、朱,而大义必宗向,而信且好焉。因推明其旨,将以扶正道率后贤,是可谓君子之为学矣。[8]361
上述三个例证皆属采用先抑后扬的反衬句法,如以“其自奉甚陋”,甚至被人“窃笑”,这看是贬抑,而实则更强烈地衬托和颂扬了他对“族党有缓急”,“出千百金不惜”的高贵人品。“余论说学问必崇古法”,被世人贬抑为“迂谬”,则更强烈地衬托和颂扬了春池“独能信吾说而不疑”的难能可贵。姚鼐本意是要尊崇程、朱,要求对程朱“大义必宗向”,并“信且好焉”,但他却把容许“辞义训诂之小者,未尝一一拘守程朱”放在前面,采用如此先抑后扬的写法,就显得颇为公允,更易于为人们所接受。同时,如此反差衬托、先抑后扬的语句,也自然在音节上使人深切地感受到其别具神变气奇的抑扬美。
总之,说到底就是利用语音的节奏,形成神活气充的音乐美。因为只有神活气充,才能使字字句句有打动人心的力量;只有体现音乐美,把握好艺术节奏的审美作用,才能使读者更好地领会文学作品中声情并茂的审美意蕴。所以刘大櫆说:“文章最要节奏;譬之管弦繁奏中,必有希声窈渺处。”[19]137当代美学家朱光潜也说:“声音节奏对于文章是第一件要事。”[21]303
六、姚鼐之所以能创造上述语言艺术特色的原因
姚鼐为什么能创造出上述语言艺术特色呢?笔者认为,其原因主要有四。
一是由于作者不是把文仅看作载道的工具,只要求“辞达而已矣”![3]1而是明确地认识到“文者,艺也”[8]49,自觉地把文学与历史记述、政论说理和一般的应用文区别开来,从语言艺术的角度来把握文学的特性,因此他说:“文章之精妙,不出字、句、声、色之间,舍此便无可窥寻矣。”[22]本文前面所探讨的就是姚鼐如何在“字、句、声、色之间”下工夫,从而求得“文章之精妙”的。他显然不仅要求文通字顺的“辞达”,更重要的他是把语言作为艺术来作悉心的研究和不懈的追求。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坐守穷约,独仰慕古人之谊,而窃好其文辞”。“鼐之求此数十年矣,瞻于目,诵于口,而书于手,较其离合,而量剂其轻重多寡,朝为而夕复,捐嗜舍欲,虽蒙流俗讪笑而不耻。”[8]89我们要真正读懂读透姚鼐的作品,也必须有这般精神,下这番工夫。漫不经心地看看是不管用的,必须把它当作艺术品仔细玩味,认真思考,才能获悉其真谛。
二是由于作者虽然总的思想未能摆脱唯心主义的体系,但是他在思想方法上又确实具有不少朴素的辩证法。如他说:“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苟有得乎阴阳刚柔之精,皆可以为文章之美。阴阳刚柔,并行而不容偏废。有其一端而绝亡其一,刚者至于偾强而拂戾,柔者至于颓废而阉幽,则必无与于文者矣。然古君子称为文章之至,虽兼具二者之用,亦不能不无所偏优于其间。”[8]48本文所论述的他在语言艺术上寓丰富于简洁、寓深意于言外、寓工妙于自然、寓浓郁于平淡、寓神气于音节,跟他论述阴阳刚柔的辩证法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他在丰富与简洁、深意与言外、工妙与自然、浓郁与平淡、神气与音节之间,如同他所说的阳刚与阴柔之间一样,皆要“兼具二者之用,亦不能无所偏优于其间”,而反对“有其一端而绝亡其一”。这种“兼具二者之用”的辩证思维,运用于他的语言艺术,就必然使之别具神韵,韵味丰厚,足以引起人们艺术感受的震撼与满足,心灵体验的超越与升华。
三是由于作者能够熟练地掌握和发挥汉字和汉语言的特长。汉字不同于拼音文字只有记音的符号,它是形、音、义三者兼备的方块字,除了能使人听到声音,懂得其意之外,还有生动的形象不可分离地融合在一起。恰如闻一多所说:“唯有象形的中国文字,可直接表现绘画的美,西方的文字变成声音,透过想象才能感到绘画的美。”[23]汉字的词性非常灵活,同一个字,往往既可当名词用,也可当动词、形容词用。如前文所写披雪瀑水如“蛇折雷奔”,这里的“蛇”、“雷”二字本属名词,可是却用作形容词,来形容瀑水曲折如蛇前行,如雷奔驰发出令人震撼的轰轰声。如此形、音、义兼备,内涵丰盈,功能多样,用字非常巧妙自然,极其简洁、生动的描写,这在世界上又有哪个拼音文字能够做得到呢?汉字不只与拼音文字同样有音符,而且汉字还独有声、韵、调体系。文学语言富有节奏的音乐美,离不开声律和韵律的作用。汉语既可利用不同声、调有规律地搭配,构成语言的抑扬顿挫之美,又可把韵母相同或相近的字安排在一定的位置上,使它们互相呼应,造成有规律的周期性重复,使语言富有节奏感和韵律美。当代作家汪曾祺说:“中国语言有一个特点是有‘四声’,‘声之高下’不但造成一种音乐美,而且直接影响到意义。不但写诗,就是写散文,写小说,也要注意语调。语调的构成,和‘四声’是很有关系的。”[24]汉字和汉语言的这些特长,可以说被姚鼐的散文语言艺术发挥得淋漓尽致,使之声情并茂,不只以情感人,以理服人,而且声声入耳动听,令人思绪升腾。
四是由于作者对现实有深刻细致的观察和切身的生活体验。姚鼐是非常注重“亲览”的,如他在《宁国府重修北楼记》中所说的:“今夫江以南列郡之名楼,镇江有北固,宁国有北楼;其山势皆自南入城,陂阤再耸,楼当城北而面南山,此图可传、言可著者也。而其各有独绝之异境,非亲览不知,图与言不能具也。”[8]400他不满足于有“图与言”的介绍,而要经过自己的“亲览”,认知其“独绝之异境”,还要下一番考证、研究的功夫,然后才好下笔。如他写《登泰山记》,在他“亲览”之后,还对泰山的地理位置与古长城的关系作了准确的考证和记述;《游灵岩记》则对苻坚之世,“竺僧朗居于琨瑞山,而时为人说其法于灵岩,故琨瑞之谷曰朗公谷,而灵岩有朗公石焉”[8]222,作了历史介绍。下笔必须经过“亲览”与研究,这是姚鼐的语言艺术之所以既新鲜活泼、生动有趣,又内涵博大精深,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根本原因。
姚鼐的语言艺术当然也不是完美无瑕的,好用古语,故作艰深,即是其突出的缺陷之一。如在《左仲郛浮渡诗序》中写“江水既合彭蠡,过九江而下。”何谓“彭蠡”?原来这是鄱阳湖的古称,他把人人皆知的“鄱阳湖”,写成令人费解的“彭蠡”;又如《陈东浦方伯七十寿序》,何谓“方伯”?本指一方之长,后用以称古代诸侯中的领袖,明清时用作对“布政使”官吏的称呼,因陈东浦曾任江苏布政使,故称其为“方伯”;又如写陈东浦“今秋七月,先生七十初度”,何谓“初度”?原来是指“生日”,语出屈原《离骚》:“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这些都不必要地增加了读者阅读时的困难。
至美的作品无不由卓越的语言艺术所造就,但仅靠在语言艺术上下工夫仍有“得此遗彼之病”,难以达到至美境界。好在姚鼐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他曾对他的弟子陈用光叮嘱过:“夫文章一事,而其所以为美之道非一端,命意,立格、行气、遣辞,理充于中,声振于外,数者一有不足,则又病矣。作者每意专于所求,而遗于所忽,故虽有志于学,而卒无以大过乎凡众。故必用功勤而用心精密,兼收古人之具美,融合于胸中,无所凝滞,则下笔时自无得此遗彼之病也。”[5]
[1] 曾国藩.曾文正公文集(卷1)·《欧阳生文集》序[M].四部丛刊本.
[2] 刘师培.刘申叔先生遗书:左盦外集(卷13)·论近世文学之变迁[M].宁武南氏校印本.
[3] 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上册)[M].上海: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
[4] 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中册)[M].上海: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
[5] 姚鼐.姚惜抱先生尺牍(卷6)·与陈硕士[M].小万柳堂据海源阁本重刊本.
[6] 段宝林.西方古典作家论文艺创作[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0.
[7] 顾亭林.日知录集释(卷19)·文章繁简[M].四部备要本。
[8] 刘季高 标校,姚鼐 著.惜抱轩诗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9] 刘大櫆.论文偶记(之20)[M].光绪戊子桐城大存堂书局本《刘海峰文集》卷首.
[10] 司马光.温公续诗话[M]//清·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
[11] 转引自 欧阳修.六一诗话[M]//清·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
[12] 袁中道.袁小修文集(卷2)·《淡成集》序[M].中国文学珍本丛书本。
[13] 姚莹.识小录(卷5)·惜抱轩诗文[M].合肥:黄山书社,1991.
[14] 叶圣陶.文艺作品的鉴赏[M]//鉴赏文存,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15] 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中)[M]//清·何文焕 辑.历代诗话(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
[16] 罗丹.罗丹艺术论[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78.
[17] 清史稿(卷485)·文苑一·刘大櫆传[M].
[18] 道光桐城续修县志(卷15)·人物志·儒林[M].
[19] 刘大櫆.论文偶记[M]//郭绍虞 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下册),上海: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3.
[20] 姚鼐.《古文辞类纂》序目[M]//古文辞类纂(卷首),合肥:黄山书社,1992.
[21] 朱光潜美学文集(卷2)[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
[22] 姚鼐.姚惜抱先生尺牍(卷8)·与石甫侄孙莹[M].小万柳堂据海源阁本重刊本.
[23] 闻一多.女神之地方色彩[J].创造周刊,第5期,1922年2月号.
[24] 汪曾祺.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M]//王一川.汉语形象美学引论,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
I206.2
A
1671-511X(2011)06-0069-07
2010-12-28
周中明(1934-),男,江苏扬中人,安徽大学中文系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