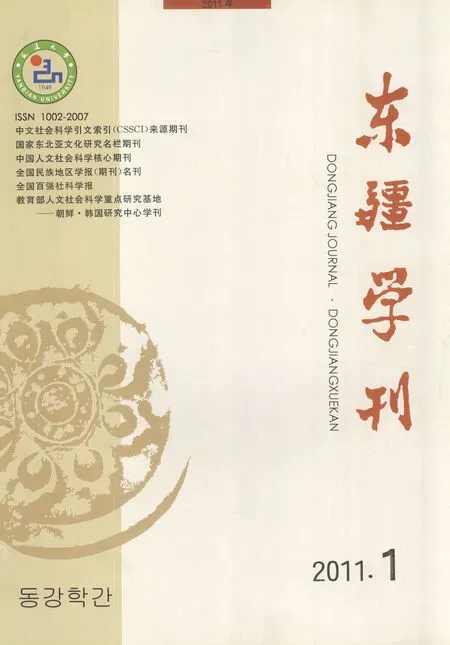试析朝鲜塔铭中的汉文化元素
李谷乔,李明非
试析朝鲜塔铭中的汉文化元素
李谷乔1,李明非2
朝鲜半岛与中国的文化渊源甚深。特别是在唐代,中华文化向周边国家都有传播,其中以朝鲜半岛所受到的浸润最为深厚。现以保存在《全唐文》和《唐文拾遗》中的16篇朝鲜塔铭为例,分别从佛教观念、人物刻画手法以及章法行文技巧方面来探讨朝鲜半岛所受汉文化、汉文学的深刻影响,并从半岛塔铭文鲜明的汉文化印痕里,感受中朝文化交往的悠远和深厚。
朝鲜;塔铭;汉文化元素
兴盛于唐代的禅宗,因其在心性理论上的独到造诣,特别受中古时期朝鲜半岛的欢迎。新罗朝(公元668—935)和高丽朝(公元935—1392)都曾输入大量中文佛教典籍,也都派遣大批留学僧来华学习。伴随着唐代禅学的东渐,朝鲜半岛的佛家逐渐接受了中国僧侣的丧葬习俗,同时,为高僧作盖棺定论的特殊文体——塔铭,也在这时传入了朝鲜半岛。
所谓塔铭,指德高望重的僧人或居士亡化后,为传扬其一生功德而撰写的铭文。因为是刻在石碑上,并砌于僧人归寂塔的正面,所以这类碑铭也被称作“塔铭”。中国的塔铭在唐代达到了兴盛期,涌现出大量经典之作。从现存文献看,朝鲜半岛的塔铭正是以唐代塔铭为典范,其在佛教思想、人物刻画手法、行文特色等方面,都呈现出大量的汉文化元素。
一、儒释合流的佛教观
朝鲜塔铭表现出鲜明的儒释合流、援佛济世的观念,大文豪崔致远在《有唐新罗国故知异山双寺教谥真鉴禅师碑铭并序》中写道:
《礼》所谓“言岂一端而已?夫各有所当”。故庐峰慧远著论,谓“如来之与周孔,发致虽殊,所归一揆。体极不兼应者,物不能兼受故也”。沈约有云:“孔发其端,释穷其致。”真可谓识其大者,始可与言至道矣。[1](10864)
慧远、沈约,一为晋末高僧,一为齐梁显宦,都是以儒学佛,深知儒家治世、佛家修心之道,认同两教相辅相成,同为济世之良药。崔致远在为新罗真鉴禅师正式写铭文之前,举慧远、沈约的例子,大谈儒释殊途同归,实是在传达当时朝鲜半岛的佛教观。
半岛高僧们也多持儒释合流、以佛济世的观念。本来,僧人应是避世而居,不愿与世俗接触的,但朝鲜的高僧们却愿意和皇亲贵戚交往。翻检《全唐文》和《唐文拾遗》中的16篇塔铭,可以确知,曾奉旨面圣的高僧多达11人,分别是:行寂、忠湛、无染、智诜、审希、利严、元晖、丽严、微、允多、庆猷。他们奉召来到京城,不仅仅是为国君讲经说法、祈福求祥,更有些人是来参议朝政的。
献康大王居翌室,泣命王孙勋荣谕旨曰:“孤幼遭闵凶,未能知政。致君奉佛,济海人,与独善其身,不同言也。幸大师无远适,所居唯所择。”对曰:“……就有三言,庸可留献,曰:‘能官人’。”[1](10871)
无染(朗慧和尚)学成归国后,经历了新罗文圣王、宪安王、景文王、献康王、定康王、真圣王六朝,他与历代帝王都有交往,颇得王室敬重,特别是献康王给予无染极高的荣宠。前面引文就是献康王大病初愈,向无染咨询国政时的一段对话。无染这时也完全抛开了佛家不问世事的“清净心”,从治国辅政的角度,简练地答复了国君当下的政治最要务是“能官人”,即选拔合适人才,委以重任。可见,无染虽身在佛家,却心存治道,有意消除儒家与佛家的差异,曾谕诫僧徒说:“道师(佛祖)、教父(孔子),宁有种乎?……或谓教、禅为无同,吾未见其宗……大较同弗与异弗,非!”[1](10871)可以说,无染是朝鲜儒释合流、以佛辅政的典型代表。
此外,行寂、审希、利严、元晖等,也都是出入王庭、以佛法助王化的僧人,其赞同儒释合流的言行都记载在他们的塔铭中:
(行寂)自欲安禅,终须助化。[1](10360)
——崔仁氵六兄《新罗国故两朝国师教谥朗空大师白月栖云之塔碑铭》
(审希)大师高拂毳衣,直升绳榻。说理国安民之术,敷归僧依法之方。[1](11129)
总之,朝鲜半岛的士大夫和高僧们,普遍倾向统合儒释、援佛济世的佛教观,这其实与他们来唐访学,耳濡目染唐文化有着极大关系。据严耕望先生考证:“自太宗贞观十四年新罗始派遣留学生起至五代中叶,三百年间,新罗所派遣之留唐学生,最保留之估计当有两千人……不但人数众多,且留居甚久。”[2](441)塔铭的作者,如崔仁渷、崔致远、崔彦、金颖等,都是著名留唐学生,他们或科举高中,或在唐为官,在漫长的旅华岁月中,唐文化浸透了他们的灵魂,极大地影响着他们的认知倾向。
我们再进一步考察唐代的宗教认知思潮,可以发现,社会上虽然儒释道三家并行,但主流认同的仍是儒家,绝大多数士大夫还是站在儒家的伦理和道德原则层面审视佛法旨义。柳宗元在《南岳大明寺律和尚碑》中说:“儒以礼立仁义,无之则坏;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则丧。是故离礼于仁义者,不可与言儒;异律于定慧者,不可与言佛……儒以礼行,觉以律兴。”[1](5936)白居易《策林·议释教》说:“若欲以禅定复人性,则先王有恭默无为之道在;若欲以慈忍厚人德,则先王有忠恕恻隐之训在;若欲以报应禁人僻,则先王有惩恶劝善之刑在;若欲以斋戒抑人淫,则先王有防欲闲邪之礼在。”[1](6852)
恰恰是以儒学佛,从外部思考佛教的价值,让士大夫们认同了佛家的调养心性,进而间接地也能协调宗法社会各方面关系的功效。如此一来,重主观、避世的佛教便同强调客观、积极入世的儒家一样,都具有了拯物济世的社会功能。这样一来,表面上两家变得没什么大矛盾了,似乎还可以并行不悖。对此,刘禹锡曾在《袁州萍乡县杨歧山故广禅师碑》做过一段精彩评说:“天生人而不能使情欲有节,君牧人而不能去威势以理。至有乘天工之隙以补其化,释王者之位以迁其人。则素王立中枢之教,懋建大中;慈氏起西方之教,习登正觉。至哉!乾坤定位,而圣人之道参行乎其中。亦犹水火异气,成味也同德;辕轮异象,至远也同功。”[1](6162)白居易讲得更明白,他在《三教论衡》里说:“夫儒门释教,虽名数则有异同,约义立宗,彼此亦无差别。所谓同出而异名,殊途而同归者也。”[1](6162)
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这种泯灭儒佛差异、赞同两教合流、共同为现实社会服务的观念,很有代表性,可以说基本上是唐代知识分子的主流认知。朝鲜遣唐留学生、留学僧,所亲历感知的也正是这样的佛教认知潮流。作为朝鲜半岛的知识精英,这些留学人员回国后,就把这种佛教观带回了本国,从而出现了唐朝佛教观在朝鲜半岛的盛行。
二、使用细节刻画人物
在写人技巧上,朝鲜半岛塔铭也承袭了唐代塔铭、墓志类文章的特点。
唐代的碑志名家,如张说,《旧唐书》称其“尤长于碑文、墓志,当代无能及者”。[3](3057)我们考察张说碑铭墓志类文章,发现他特别注重使用细节突显人物形象。在《唐玉泉寺大通禅师碑铭并序》中,张说就通过细节描写,表现了王室对神秀的极高优待:
久视年中,禅师春秋高矣,诏请而来,趺坐觐君,肩舆上殿,屈万乘而稽首,洒九重而宴居……遂推为两京法主,三帝国师。[1](2334)
神秀面圣时,不仅不用起立致礼,还可以乘轿上殿,甚至能受到武后的屈尊礼拜,并被尊奉为“法主”、“帝师”。其中,“趺坐觐君”、“肩舆上殿”纯属细节描写。张说用精简的笔法,形象地烘托出了神秀受皇室认可的特殊的佛教地位。
其实,这种通过细节刻画人物形象的手法,在唐代塔铭、墓志类文章中极为常见,不仅仅是张说这样的碑铭大家所独有的写作方法。正是受到了唐代同体裁文章的影响,朝鲜半岛的塔铭也经常使用细节描写,而且在表现皇室礼敬高僧方面,半岛作者的描写甚至更为细致。例如:
(献康大王)礼之加,焯然可屈指者:面供馔,一也;手传香,二也;三礼者三,三也;秉鹊尾炉缔生生世世缘,四也;加法称曰广宗,五也;翌日命振鹭趋风树鸠列贺,六也;教国中磋磨六义者赋送归之什,在家弟子王孙苏判镒荣首唱敛成轴,侍读翰林才子朴邕为引而赠行,七也;申命掌次,张净室要叙别,八也。[1](10871)
这是崔致远在《有唐新罗国故两朝国师教谥大朗慧和尚白月葆光之塔碑铭并序》中,叙述朗慧和尚面圣时所受到的极不寻常的礼遇。作者一连罗列了八项事例来突显献康大王对朗慧的优礼:从国王亲自为和尚供奉食物、传香执炉、缔结世缘,到加赠法号、命群臣庆贺,再到净室送别、命文臣作赋送行等,都一一详述出来,其笔触之细腻,让人惊叹。在现存的16篇朝鲜塔铭中,我们几乎都能找到详尽描述国王礼敬高僧的细节。
当然,细节描写并不只限于高僧受到礼遇的情节中;在高僧学养方面,半岛塔铭也倾向使用细节表现。例如:
(慧昭)谒神鉴大师,投体方半,大师怡然曰:“戏别匪遥,喜再相遇。”遽令削染,顿受印契。[1](10865)
(云居道膺)大师谓曰:“曾别匪遥,再逢何早?”(利严)对云:“未曾亲侍,宁道复来?”大师默而许之,潜惬元契……谓曰:“道不远人,人能宏道。东山之旨,不在他人;法之中兴,唯我与汝。吾道东矣,念兹在兹。”[1](11139)
(云居)谓曰:“戏别匪遥,相逢於此。运斤之际,犹喜子来……所冀敷演真宗,以光吾道。保持法要,知在汝曹。”以此传大觉之心,佩云居之印。[1](11146)
灌顶授记曰:“往钦哉。汝今归本,晓悟迷津。激扬觉海……”应时豁尔,得未曾有。[1](7381)
——金献贞《海东故神行禅师之碑并序》
以上都是师徒间的私下对话,如果不是塔铭作者在写作前做了详细了解,并且记述出来,后人则无从得知这么详尽的对话细节。而这些详实的谈话记录,无一例外地是在真切再现当时的留唐学僧受中国老师高度认可的场景。
三、前有“序”后有“铭”的章法行文特征
中国的塔铭,通常文体结构是前有“序”,用以记叙高僧生平功德,可以说是一篇人物传记;“序”后有“铭”,内容是对高僧的褒扬,相当于文末附上的颂词。序文以骈体居多,铭文则一定是韵文。从现存文献看,朝鲜半岛塔铭也沿用了中国前序后铭的结构方式,仿照唐文样式,使用骈化的序文和韵体铭文。
我们先考察铭文。半岛塔铭的铭文,常见的由四言、五言、七言古诗写成,其中又以四言古体诗居多,如崔仁氵六兄的《新罗国故两朝国师教谥朗空大师白月栖云之塔碑铭》:
至道无为,犹如大地。万法同归,千门一致。粤惟正觉,诱彼群类。圣凡有殊,开悟无异。懿欤禅伯,生我海东。明同日月,量等虚空。名由德显,智与慈融。去传法要,来化童蒙。水月澄心,烟霞匿曜。忽飞美誉,频降佳召。扶赞两朝,阐扬元教。瓶破灯明,云开月照。哲人去世,缁素伤心。门徒愿切,国主恩深。塔封峦顶,碑倚溪浔。芥城虽尽,永曜禅林。[1](10361)
这是一首古朴的四言古体诗,概括了朗空大师一生的德业。类似的以四言诗为铭文的还有《高丽国原州灵凤山兴法寺忠湛大师塔铭》、《有唐新罗国故知异山双寺教谥真鉴禅师碑铭并序》、《有晋高丽中原府故开天山净土寺教谥法镜大师慈镫之塔碑铭并序》、《高丽国弥智山菩提寺故教谥大镜大师无机之塔碑铭并序》、《高丽国溟州普贤山地藏禅院故国师朗圆大师悟真之塔碑铭》等。另外,《有唐新罗国故两朝国师教谥大朗慧和尚白月葆光之塔碑铭并序》、《有晋高丽中原府故开天山净土寺教谥法镜大师慈镫之塔碑铭并序》的铭词是五言诗,《大唐新罗国故凤严山寺教谥智证大师寂照之塔碑铭并序》、《有唐新罗国故国师谥真镜大师宝月凌空之塔碑铭并序》的铭词是七言诗。值得一提的是,半岛塔铭还有楚辞体和古体诗相结合样式的铭文,如《新罗国武州迦智山宝林寺谥普照禅师灵碑铭》的铭辞:
禅心不定兮至理归空,如活琉璃兮在有无中,神莫通照兮鬼其敢冲,守无不足兮施之无穷,劫尽恒沙兮妙用扉终。(其一)
有为世界,无数因缘。境来神动,风起波翻。须调意马,勤伏心猿。以斯为宝,施於后贤。(其四)
乘波若舟,涉爱河水。彼岸既登,惟佛是拟。牛车已到,火宅任毁。法相虽存,哲人其萎。(其五)
丛林无主,山门若空。锡放众虎,钵遗群龙。惟余香火,追想音容。刊此真石,祀法将雄。(其六)[1](11135)
与铭文相比较,序文的史料和文学价值要更高一些。半岛塔铭的序以骈文为主,间以散行单句。其骈体行文的特点,最突出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四六句式,语言对偶
1.四四句式相对:
命寄刳木,心悬宝洲。[1](10864)
焚叶为香,采花为供。[1](10865)
仪状魁岸,语言雄亮。[1](10875)
2.六六句式相对:
仍楼方便之门,果得摩尼之宝。[1](103594)
裨二主於两朝,济群生於三界。[1](10361)
洒法雨於昏衢,布慈云於觉路。[1](11133)
3.四四句与四四句相对,组成两个长联:
今思前梦,宛若同符;始觉曩因,犹如合契。[1](11143)
虽云得月,指或坐忘;终类系风,影难行捕。[1](10864)
清眼界者,隔江远岳;爽耳根者,迸石飞湍。[1](10866)
4.四六句与四六句相对,组成两个长联:
有学无学,才尝香钵之饭;二乘三乘,宁得药树之果。[1](7381)
甘泉忽竭,鱼龙惊跃其中;直木先摧,猿鸟悲鸣其下。[1](7382)
或闻异香,飞锡空而电奔;或观瑞云,乘杯流而雨骤。[1](7382)
5.六四句与六四句相对,组成两个长联:
先宴坐於松溪,学人雨聚;暂栖迟於雪岳,禅客风驰。[1](11129)
遽裁熊耳之铭,焉惭梁武;追制天台之偈,不愧隋皇。[1](11130)
以上是标准的骈偶句,属对精切,韵律协和。此外,半岛塔铭的骈偶句式还有三字句、五字句、七字句等,这里不再举例。
(二)使用典故
中国的骈体文在修辞上有用典的传统。《文心雕龙·事类》中说:“事类者(即指用典),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4](411)实际上,文章用典除了起到论据作用外,还能启发人联想,使文章语言简省,风格典雅含蓄。朝鲜半岛塔铭亦多使用典故,我们以下面数则为例,体会一下塔铭作者深厚的汉学功底:
西向陈仓,用显霸王之道;今来宝地,将兴法主之征。[1](11134)
不劳圯上之期,潜受法王之印。[1](11139)
爰切折梁之恸,亦增亡镜之悲。[1](11141)
甘罗入仕之年,□穷儒典;子晋升仙之岁,才冠孔门。[1](11148)
“西向陈仓”句,典故出自《史记·淮阴侯列传》。[5](2613)刘邦决意打回关中时,使用了“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之计。即在表面上命人抢修通往关中的栈道,以麻痹项羽的注意力,暗地里却从陈仓小路东进,刘邦与项羽争霸天下的序幕由此开启。“不劳圯上之期”句,典故出自《史记·留侯世家》。[5](2034)张良在下邳桥上遇一老者,老人故意将鞋丢落桥下,却命张良取回。张良愕然,因见老人年迈,强忍怒气取回鞋,并为其穿好。老人大笑,曰:“孺子可教矣,后五日平明,与我会此!”后来老人果然授给张良一部书,上写道:“读此,则为王者师矣”。“亦增亡镜之悲”句,典故出自《旧唐书·魏征传》。[3](2561)魏征死后,唐太宗十分惋惜,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后世用“亡镜之悲”比喻贤良逝世,国失栋梁。“甘罗入仕之年,□穷儒典”,典故出自《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5](2321)甘罗12岁就因功受封为上卿。“子晋升仙之岁,才冠孔门”,典故出自《列仙传》。[6](65)子晋,为周灵王太子,因不满灵王昏聩而出走。甘罗、子晋都是历史上以才学见称的著名人物。
从这些例句中使用典故的情况,我们可以感知到半岛塔铭作者对于古代中国文史知识掌握之纯熟。
四、结语
中国唐代文化的向外传播,以朝鲜半岛所受影响为最深。从大批派遣留唐学生,到大量输入中华典章;从使用中国天文历法,到采纳唐朝的衣冠制度,半岛接纳唐文化可谓是不遗余力。半岛塔铭的创作,就是中国佛家丧葬文化东传的一个外在表现,而其文章中所体现出的朝鲜佛教观念、人物刻画方法以及文体行文特征,更是带有鲜明的中华文化影响的印痕。正是通过剖析半岛塔铭的汉文化元素,我们才更加真切地感受到古代中朝文化交流传统之深远。
[1]董诰:《全唐文》,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2]严耕望:《新罗留唐学生与僧徒》,《唐史研究丛稿》,香港:新亚研究所,1969年。
[3]刘晌,等:《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
[4]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5]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6]王叔岷:《列仙传校笺》,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
[责任编辑 梁浚]
K 312.877.45
A
1002-2007(2011)01-0013-05
2010-09-25
1.李谷乔,女,吉林财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吉林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方向为佛禅与唐代文学;(长春 130117)2.李明非,男,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东北亚文学与文化。(长春 130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