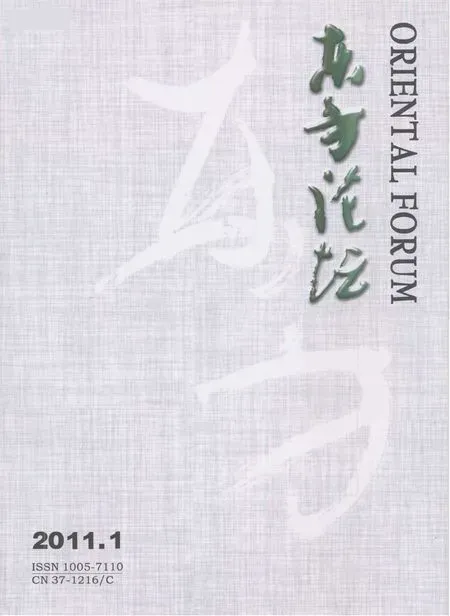中印古典诗学“韵”论美学意蕴的叠合与差异
程晶晶
中印古典诗学“韵”论美学意蕴的叠合与差异
程晶晶
(复旦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433)
印度九世纪的欢增和中国十一世纪的范温不约而同地提出关于“韵”的诗学命题。他们将“韵”视为诗歌艺术的最高审美理想,并且都建立起了关于古典诗学韵论完整的理论体系。他们在诗学理念、审美意识、审美理想等方面存在着叠合和差异。
韵;美学意蕴;中印诗学
中国十一世纪的范温和印度九世纪的欢增分别在各自的诗学著作里提出了关于“韵”的命题:范温在《潜溪诗眼》中提出:“韵者,美之极”①转引自钱钟书《管锥编》第四册,第1362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以下范温论“韵”的文字均出于此。,欢增在《韵光》中开篇就提出:“诗的灵魂是韵”②黄宝生译《梵语诗学论著汇编》(上册),第232页。昆仑出版社,2008年版,以下欢增论“韵”文字均出于此。。二人不仅不约而同地将“韵”视为诗歌艺术的最高理想,而且都建立起了关于古典诗学韵论完整的理论体系。将二者的韵论放在一起比照参看,不仅可以发现二位诗学家在理论视角、诗学理念和美学精神上具有的一致性,而且折射出中印这两个古老而伟大的民族在诗学观念、艺术思维方式和审美理想等方面的叠合和差异。其叠合处,可以让我们对诗歌艺术的本质和规律有更深的认识和把握,从而梳理出作为优秀诗歌魅力所在的“韵”的审美意蕴究竟是什么;其差异处,则恰好是弥补各自诗学理论不足的方向,双方可以选择性、创造性地吸收和发展彼此的长处。
一
一直以来“韵”论在中印古典诗学中都非常重要,也非常具有理论难度。欣赏一首好诗,常用的诗学批评术语是“韵”,优秀诗歌的魅力就在于“韵”,然而什么是“韵”?艺术中的“韵”如何体现,能否可以清晰地指陈出来?创作和鉴赏中如何切实把握到“韵”?“韵”究竟能否代表诗艺的最高审美理想?由于难以用科学的逻辑方法去分析“韵”,难以用清晰地语言去指陈表达,有些问题至今仍悬而未决。
面对这些困惑和难题,两位先人极有勇气,也极具眼光地进行了系统地探讨,并由此构建出一套完善的韵论体系,而且中印古典诗学都把韵视为优秀诗歌的评价标准,视为艺术追求的审美理想。范温言“韵者,美之极”,“凡事既尽其美,必有其韵,韵苟不胜,亦亡其美”,欢增说“诗的灵魂是韵”,优秀成熟的诗人应该展现诗中“如意宝树般神奇伟大的韵,让灵魂高尚的人们享受”[2](P354)。
对上述的问题,他们在有关韵的论述中,有的已经作了明确回答,有的仍然处于开放状态。对他们的理论细加分析,将有助于启发我们作进一步的思考和探讨。
有趣的是,二人的探讨都是以辩论方式开始的,都明确确立了优秀诗歌的魅力是“韵”。范温在《潜溪诗眼》中论韵,是和王定观展开的层层辩驳中进行的。针对王定观提出的疑问“独韵者,果何形貌耶”,范温没有回避,而是“试为毕其说”。他一一否定了王定观相继提出的“不俗之谓韵”、“潇洒之谓韵”、“生动之谓韵”、“简而穷其理之谓韵”等定义后,提出了“有余意之谓韵”的定义。指出韵在包括不俗、潇洒、生动、简而穷理等内涵之外,还具有远超这之上的内容。他说:“夫俗者,恶之先,韵者,美之极……其间等级固多,则不俗之去韵也远矣”。首先,韵是高高在上摄众美而又泠然不同于众美的极致之美,其有言“凡事既尽其美,必有其韵,韵苟不胜,亦亡其美”。其次,韵的根本美学内涵在于“有余意”,所谓有余意,就是“备众善而自韬晦”,即它的丰富涵摄性和含蓄圆融性。总之,范温将源自三代秦汉的声乐之韵、魏晋六朝的人物风韵、唐宋以降的审美之韵融合起来,分析了和韵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如韵的历史流变、审美内涵、发生机制,和学养才能、人格胸襟的关系等,建立了比较完整的韵论体系。他的理论价值在于将韵作为各门艺术共同的审美理想,明确指出韵是极致之美,中国艺术的魅力就在于韵。自范温系统论韵后,后人论韵基本没有超出他论韵的范围。南宋以至明清的韵论除了进一步肯定韵作为艺术的最高审美理想外,对韵论做了细枝末节地完善和深入,就范围而言大体上没有超出前人的地方,如明七子谢榛、陆时雍等。即使清代王士禛的神韵诗学蔚为大观,就其理论的价值和地位而言,也难以和范温等同而语。近人钱钟书就对范温的韵论就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融贯综赅,不特严羽所不逮,即陆时雍、王士祯辈似难继美也。”[2](P1363)
欢增在《韵光》中,开篇也对怀疑韵是否是诗歌的灵魂,韵是否存在以及韵的性质“不可名状”等看法进行了批驳,“还有一些人认为韵的灵魂只能由知音内心感知而不可言说,这说明他们缺乏考察”[2](P245)。他首先确立了韵是优秀诗歌的灵魂,或说诗歌的真谛就是“韵”,“智者们通晓诗的真谛,认为诗的灵魂是韵”[2](P232),“韵的性质是所有优秀诗人的作品奥秘,极其可爱。但以往哪怕思维最精密的诗学家也没有加以揭示”[2](P234);同时他认为要重视对韵的理论研究,“有志于创作好诗或鉴赏好诗的人们应该努力研究上述韵论”[2](P338),因为对韵的理论研究有助于我们把握到好诗的灵魂。对这些怀疑的观点,他予以了彻底的回击:“不可言状不是韵的定义,因为韵的意义可以说明,上述定义得以成立”[2](P339)。其次,他认为韵最主要的内涵在于“暗示义”,他对韵下的定义是:“若诗中的词义或词音将自己的意义作为附属而暗示那种暗含义,智者称这一类诗为韵”,“它是令知音内心喜悦的诗的真谛”[2](P238-P239)。欢增的韵论,吸收了梵语语法学,婆罗多《舞论》中的味、情论,婆摩诃的“诗庄严论”等理论精粹。在《韵光》中,欢增不仅对韵做了分类,并以韵为标准对诗进行了分类,而且对韵和庄严论(修辞技艺)、风格论、语言论、诗人学等方面的论题进行了辨析,创立了梵语诗学中的韵论体系。尽管后来论韵的理论家层出不穷,如十世纪、十一世纪的新护(其著有《韵光注》)和曼摩吒(其著有《诗光》),都对韵有再发挥,但其思想也都是基于欢增的韵论,其关于韵的理论也基本不出欢增的论述范围。
渊源于不同民族文化背景和不同民族语言的两位古典诗学家都对“韵”做了系统的论述,对我们不可不有启发深思的意义。关注中印古典韵论比较的人越来越多,稍早有季羡林先生《关于神韵》[3]已对中印的韵论有精辟的简论,其后金克木、黄宝生等诸先生在他们梵语诗学著作中亦非常关注中印韵论的比较。目前更有一大批年轻的专家学者着力于对中印诗学中的韵论研究,或是将文本做平行比较,如任先大、田泥《中印古典“韵”论比较研究》,或是描述韵论的历史演变,如袁向彤《中印古典美学中的“味”与“韵”论比较研究》,或是将二者放在中印传统诗学理论视野中,对二者韵论的内容异同进行比较,如杨晓霞《中印韵论诗学的比较研究》。而本文是通过二者韵论的比较,考察中印诗学韵论所体现的美学意蕴,试图达到对古典优秀诗歌之“韵”的审美特征和美学意蕴的把握。
二
范温和欢增的诗韵论,透析出二者在对待古典诗歌这门艺术时在诗学观念、审美理想和艺术思维方式上的叠合和差异。下文将从以心为统摄的审美感知方式、含蓄曲折的表现方式、沉迷忘我的审美心境和喜悦自适的美感效应四个方面展开论述。
(一)以心为统摄的审美感知方式
在审美感官的选取上,不同于西方艺术对视听感官的偏重和强调①西方的古典艺术突出强调了视听感官。从古希腊时起,西方艺术认为只有视听感官和美有联系,而将其他感官从美中排除出去,认为它们只能联系动物性的快适。后来黑格尔也坚持认为“艺术的感性事物只涉及视听两个认识性的感觉,至于嗅觉,味觉和触觉则完全与艺术欣赏无关。”(黑格尔:《美学》第1卷,第48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中印的古典韵论突出了听觉和味觉,更强调包孕五觉的“心觉”,感官的感受也不满足于生理的快感,而是要满足于心的愉悦,突出对心的诉求,这就是以心为统摄的审美感知方式。
其一,从字源上看,汉语“韵”字和梵文的dhvani(韵),词源上看都基于声音之道而来。黄宝生认为梵语dhvani一词源自动词词根√dhvan(发音、发声),词义为声音、回声、余音或音调,作为诗学术语,译作汉语的“韵”,最为贴切[7](P331)。
范温和欢增对“韵与声音”的描述有如下几点共性:
一从声音入手,重视听觉上的和谐。范温言韵,首先指出“自三代秦汉,非声不言韵”。“韵”不仅自上古时期起,就和声音、音乐紧密相关,而且一开始就与和谐匀称的声音联系在一起①古汉语中,韵同“均”。《说文解字》:“韻(韵),和也。从音,员声”,“裴光远云:古与均同,未知其审”。《文选•卷十八》中也有:“音均不恒,曲无定制。”李善注曰:“均,古韵字也。”按:均有动词、名词之分。名词的“均”是古代调音之器,《国语•周语》韦昭注云:“均者均钟,木长七尺,有弦系之,以均钟者,度钟大小清浊也”;均又可作动词,《国语•周语下》:“对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声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钟,百官轨仪,纪之以三,平之以六,成与十二,天之道也……’”这其中第一个“均”作名词,是调音器,后一个“均”是动词,意为调谐平和韵律。韵同均,与声音谐和相关。学界有以先秦古书《尹文子》中的韵为最早出现的韵字,此书真伪尚待文献材料的证明,但其中“韵商而含徵”之语表明了韵和音乐相关,指声音和谐是无疑的。从现今简化字“韵”的结构上看,拆开为“音”、“匀”,也保留了声音和谐匀称的本义。。在中国诗学里,诗法运用上的诗歌的押韵、诗文的韵律都是为了追求音声和谐的效果。欢增的韵论,吸收了梵语语法学的成果,认为:“学问家中,语法家是先驱,因为语法是一切学问的根基。他们把韵用在听到的因素上。其他学者在阐明诗的本质时,遵循他们的思想,依据共同的暗示性,把表示义和表示者混合的词的灵魂,即通常所谓的诗,也称作韵”[2](P242)。欢增在谈诗病的时候指出:“词音的刺耳”即是诗病之一。“韵是一种肢体完整的特殊的诗。它的肢体是庄严、诗德和谐音方式”,又言“不悦耳形成刺耳等等诗病,同样道理,悦耳形成诗德”[2](P242)。不仅某些音素的结合能展示味,而且某些音素还能用于厌恶,能加强味[2](P279)。此外,从语法角度,欢增还大量谈到了谐音、叠声等庄严的重要性②庄严,广义指装饰诗的因素,或说,形成诗的魅力的因素。狭义上,指修辞方式,如明喻、暗喻、双关等。(参见黄宝生:《印度古典诗学》,第242-24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和悦的听觉效果不仅是韵的基本因素,而且还能带来心理感受上的喜恶。
二指余音的效果:即声音上的绵延往复,不绝于耳。范温将韵定义为“有余意之谓韵”,又以钟声形容韵的:“大声已去,余音复来,悠扬宛转,声外之音”。在《韵光》中还处处可见将韵和余音联系起来的话语。欢增认为韵的要义在于暗示,而“暗示义逐步展示,犹如余音”[2](P259),又有“依靠词音的力量余音般暗示的韵”,“依靠词义的力量余音般暗示的韵”等话语。二人都以余音来形容诗韵,这种声音上的袅袅不绝、往复回旋的特征,在诗学上的意义即所谓从声音的节奏形式到心灵的节奏形式,从音声的律动到心灵的共颤③关于中西诗学以钟声、琴声余音不绝特征作譬喻的例子,还可参见钱钟书的举例,《管锥编》第四册,第1364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钱钟书言:“范氏释‘韵’为‘声外’之‘余音’遗响,足征人物风貌与艺事风格之‘韵’,本取譬于声音之道,古印度品诗言‘韵’,假喻正同”[1](P1364)。二人对诗歌所引发的“余音”般的审美心理感受达成了一致认识。
其二,味觉得到突出,这不仅从中印两个民族“美”字的字源意义上可以得到见出④中国的“美”字,其字源义来自羊肉味觉上的鲜美;无独有偶的是,梵文里的“美”(lāvanya),原义是咸味。(参见黄宝生译:《梵语诗学论著汇编》(上册),第244页,昆仑出版社,2008年版)。,还可以从文艺理论中对“韵”的强调中得到证实。味觉的突出,移用到诗学理论里:是从品尝食物之味到品尝诗歌的韵味,从口感之味过渡到了审美品味。
韵在中国诗论中常和味联系在一起,司空图论韵味在“咸酸之外”(《与李生论诗书》);苏门弟子李荐以羹的味道说明韵,“如朱弦之有余音,太羹之有遗味者,韵也。”(《济南集》卷八)[8](P149)。羹味是多种味的和合,“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左传•昭公二十年》)
印度古典文艺理论中,从婆罗多的《舞论》、到欢增的《韵光》,以至毗首那特的《文镜》,“味”论是一以贯之的主线。婆罗多在第六章“论味”中,也首先将戏剧的味和口感之味相联系。“我们首先阐明味。因为离开了味,任何意义都不起作用。味产生于情由、情态和不定情的结合。如果有人问:有何例证?回答是:正如各种调料、药草和原料的结合产生味,同样,各种情的结合产生味。正如食糖、原料、调料和药草产生六味,同样常情和各种情结合产生味性。……味怎么可以品尝?回答是:正如思想正常的人们享用配有各种调料的食物,品尝到味,感到高兴满意,同样,思想正常的观众看到具有语言、形体和真情的各种情的表演,品尝到常情,感到高兴满意。由此,戏剧的味得到解释”[2](P45)。欢增的味论大多源于对婆罗多《舞论》中“味”论的接受。他在韵的分类中,即本事韵、庄严韵和味韵中,特别强调味韵。他认为诗中的音素、词、句子,乃至整部作品都可以展示味。“创造的故事情节应该做到:它的每一个部分都蕴含味”[2](P290)。十世纪的恭多迦认为“大诗人的语言含有源源不断的味,充满生命活力,并不单单依靠故事”[2](P569)。
中印两个民族不仅重视听觉、味觉,事实上他们认为人的五官都具有审美知觉。已有学者在对中印审美思维方式的比较中指出“中印两大民族都有着基本一致的审美立场:都认为味、嗅、触、视、听五大感觉器官全部具有审美功能,在审美功能上,五大感官是平等的”[9](P205)。而且这五官的感官感受不是为了满足生理的快感,是为了追求心的愉悦。
中印的古人不仅以“心”感物,而且要求好的诗歌要悦“心”。陈子昂曾赞赏明公《咏孤桐篇》,“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遂用洗心饰视,发挥幽郁。”(《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一篇诗文竟能达到“洗心”的功用;欢增在分析艳情味时,也是注重心灵状态:“艳情味是最甜蜜、最愉快的味,因此,甜蜜的诗德附属蕴含艳情味的诗”,“而在分离艳情味和悲悯味中,甜蜜的诗德尤为突出,因为心在这里变得湿润柔软”[2](P251)。曼摩吒在论述诗德时,谈到甜蜜的特征,“甜蜜属于艳情味,令人愉快,引起心的溶化”[2](P725),都重视内心的审美感受。
(二)含蓄曲折的表现方式
就诗歌艺术的表现方法而言,范温和欢增都强调要含蓄委婉、曲折有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含蓄暗示的表现方式。中国的艺术表现往往以极简极隐晦的形式表现丰富的意蕴,由简示其深,由淡示其浓,以虚明其实。落实到诗歌里,如司空图所言:“不著一字,尽得风流”,“浅深聚散,万取一收。”(《二十四诗品•含蓄》)。明代陆时雍在《诗境总论》中亦有一段精彩的论述:
有韵则生,无韵则死;有韵则雅,无韵则俗;有韵则响,无韵则沉;有韵则远,无韵则局。物色在于点染,意态在于转折,情事在于犹夷,风致在于绰约,语气在于吞吐,体势在于游行,此则韵之所由生矣。[10](P1423)
韵产生于点染、转折、犹夷、绰约、吞吐、游行,这是在中国诗法中的表现。范温说韵是“备众善而自韬晦”,这个“韬晦”就是含蓄隐晦的表现方式。他批评六朝诗人曹、刘、沈、谢、徐、庾诸诗人的缺点是“割据一奇,臻于极致,尽发其美,无复余蕴,皆难以韵与之”。正所谓“示人以美而不示人以尽美”,因此他强调不露才用长,而要不明说、不说尽,要“体兼众妙,不露锋芒”。他推崇陶渊明的诗,在于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初若散缓不收,反复观之,乃得其奇处……行乎质与癯而又若散缓不收者,韵于是乎成”,陶诗的“韵”体现在平淡中包孕着绮丽,清癯中又蕴含着至味。
不明说,就是要委婉表达,就是要暗示。欢增认为韵的根本特征就是暗示,“暗示义清晰地展现为诗中的主要意义,这是韵的根本特征”[2](P274),并且他认为音素、词音、词义、句子,乃至整体篇章都可以表达暗示义的韵。
下面结合诗例试析之。诗例的选取是就二者在相同题材进行比照,以突出韵在艺术表现方法上的特点,这些诗可能并不代表中印诗歌艺术的最高成就,但也是颇有韵致的:
一是暗示的手法。暗示的方法又有几类:
如通过词的同音多义达到暗示的效果,如:
太阳的光芒白天照耀四方,夜晚消失,
及时地吸收和释放雨水,令众生喜欢,
也是渡过充满恐怖的轮回苦海之船,
愿它们带给纯洁的人们无限的幸福。
杨柳青青江水平,
闻郎江上唱歌声。
东边日出西边雨,
道是无晴还有晴。
上边这首诗,在梵语中“光芒”也可读作“奶牛”,“雨水”也可读作“乳汁”,即以奶牛隐喻太阳的光芒。欢增认为“这首诗中,依靠相同的词音理解两种意义(光芒和母牛),并理解这两种意义具有喻体和本体的关系。由于没有使用表示比喻的词,这种关系依靠词义的暗示”[2](P311)。而在下边这首熟悉的刘禹锡的《竹枝词》中,最后一句的“晴”,是作者有意借用和“情”字读音的相同,来传达两层意义(明言天晴,实言心情和感情,以与前面“闻郎江上唱歌声”形成情感上的暗示与呼应),读者只有体会到这个同音字不同意义间的转换,才能体会到诗者的匠心和诗歌真正内在的意味。
又如词义的暗示方法:
提着沉重的水罐,我匆匆赶回,女友啊!
直累得汗流喘气,我需要休息一会儿。
曼摩吒认为这首诗通过“累得汗流喘气”暗示“偷情的秘密”,是一个刚偷情回来的妇女为了掩饰偷情,对她的女友说的话[2](P614)。
李煜的《菩萨蛮》也是一首暗示和小周后偷情的词:
花明月黯笼轻雾,今霄好向郎边去。刬袜步香阶,手提金缕鞋。
画堂南畔见,一向偎人颤。奴为出来难,教君恣意怜。
通过“刬袜”、“手提”、“偎人颤”等词所具有的暗示性,含蓄地描写出偷情的紧张心情。
又如:
神仙说着这些话,波哩婆提低下头,
靠在父亲的身旁,数着玩耍的莲心。[2](P264)
见客入来,袜刬金钗溜。
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
上边这首诗出自《鸠摩罗出世》,描写神仙安基罗前来替湿婆求娶雪山神的女儿波哩婆提。通过波哩婆提低头、倚靠、数莲心等动作,暗示了她的羞涩和内心的喜悦。欢增认为这首诗是暗示过程明显的韵,意义依靠自身展示了不定情(羞涩)。
与此相仿,几乎采用相同手法表达了相似内容的是下边这首李清照的《点绛唇•蹴罢秋千》。这首词描写园中玩秋千的少女,在见到有客来访时,慌乱中滑落了头饰,羞涩地匆匆跑开,却又忍不住停下来倚门回首,明明是想要偷偷地打量来客,却假装在嗅青梅。这首词随着动作的连续展开而情态毕现,明人潘游龙评之:“如画。”(《古今诗余醉》),其词状小女儿家情貌如在目前,巧妙含蓄地展示了青春少女的情动娇羞。
上述例子,在内容和表现手法上都体现出较高的相似度:寥寥数笔勾勒的细微动作展示了内心情感的波澜,笔简而意足。字、词、义上的暗示,最终都是为了达到情味上的含蓄有容,诗韵有余。
“印度音韵学者的功绩在于把‘韵’从音韵学的范围扩大到了诗歌语言及词义的暗示、象征的美学功能方面。印度诗歌总是追求象征意味、弦外之音、言外之意,追求超越字面义、表示义而达到深远悠长的暗示义,使读者余味无穷”[11](P39),这点也正和中国的诗学理论相通。
二是曲折的表现手法。暗示包括暗示义和暗示者。欢增认为,除了词音和词义可以暗示,整部作品也可以成为味的暗示者,体现在情节和结构中。“故事情节的构成无论依据传说或虚构创造,皆因情由、常情和不定情合适而优美。抛弃情节中不协调的故事成分,另外创造适合意图中的味的故事成分。情节关节和关节分支的组合旨在暗示味,而不一味遵守经典规则。味的升起和平息依据实际情况,自始至终与主味保持联系”[2](P287)
事实上,这种曲折的结构,也就是曲语的艺术表达方式。印度的曲语论派认为优秀的艺术作品都应该具有曲折的表达方式,如《曲语生命论》的作者恭多迦说:“所有大诗人的作品都教导以新颖的方法获得成功的行为方式,具有曲折性”[2](P595)。他将曲语分为六类,其中就包括章节曲折性和作品曲折性。“说话者的行为蕴含无限热情,生动优美,心中的意愿得到展现;悬念贯穿始终,显示无穷魅力,这是作品组成部分(章节)的曲折性”[2](P562)他以《沙恭达罗》为例[2](P566-P568),国王在触景生情,唤起心底对爱人沙恭达罗一些模糊记忆时:
看到可爱的东西,听到甜蜜的声音,
甚至快乐的人也会内心焦虑不安,
他肯定回忆起了过去未曾想到的、
长久深埋在心中的一段前世姻缘。
尽管国王粗鲁地否认沙恭达罗,但这里由于暗示了国王心中依然保持着对沙恭达罗的爱情,会令观众感到喜悦,在前后情节的转折上也起着预示作用。
中国古典诗词中,这种曲折有致的情节结构方式的运用也非常常见,比如一首熟悉的小词:
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李清照《如梦令》)
清代黄蓼园有非常精妙的分析:“一问极有情,答以‘依旧’,答得极淡,跌出‘知否’二句来;而‘绿肥红瘦’,无限凄婉,却又妙在含蓄。短幅中藏无数曲折,自是圣于词者。”(《蓼园词选》)一首小令,宛如演出了一场情节跌宕起伏的戏剧。无限的情意正是通过曲折有致的情节结构含蓄表达出来。
三是不定情的诗法。婆罗多在《舞论》中将“情”分为三类:常情、不定情,和真情。“‘不定情’是指随时变化的感情,用以辅助或强化常情。婆罗多说:‘不定情引导各种具有语言、形体和真情的东西走向味’”[7](P43)。
曼摩吒在《诗光》中,讨论以韵为辅的诗,其中一类是“含混”,即暗示义不明确。
看不到你时,渴望看到你;看到你时,害怕分别。
无论是看不到你,还是看到你,我都没有快乐。
他分析说,这里暗示的是,既不要让我看不到你,也不要让我害怕分别。这其实就是不定情中的“忧虑”。 这自然会让我们想起司马光那句著名的“相见争如不见,有情何似无情”(《西江月》)矛盾心理,充分展现了爱情中甜蜜与忧愁交缠着的复杂心态,这种徘徊不定、百转千折的意绪展现方式恰恰是诗歌的韵味和魅力所在。
譬如中国著名“无题”诗人李商隐的无题诗: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由于诗中抒发的是不确定的情感,从而引发了各种对诗意的阐释,有认为是身世寄托的,有以为悼念亡妻的,有以为是写给名叫锦瑟的侍女等等。诗情的含混不明,不仅造成各尽其情的诗义的多重阐释,而且就审美感受和效果来说,也营造出诗境的朦胧模糊之美和品之不尽的余味绵长。
诗法作为方法,是传达、显示、表现韵的手段和途径,但终究不是目的。因此,范温和欢增认为优秀的诗人,对待诗法既要纯熟,又要超出诗法的拘囿。如范温所言,“夫惟曲尽法度,而妙在法度之外,其韵自远”。欢增认为优秀的诗人掌握诗法,可以有无穷的变化和运用,因此诗歌的创造源泉也是无限丰富不会枯竭。欢增对诗法的态度,更鲜明地体现在对庄严(诗歌的修辞方式,如隐喻、双关、夸张、奇想等)的运用上。庄严是诗与非诗的界限,而韵是评判诗歌优劣的标准。庄严只能被视为一种手段而不能成为目的,“始终记住庄严是为辅者,而不是为主者。必要时使用它,必要时放弃它。不要过分热衷于它。努力保持警惕,让它处于辅助地位”[2](P255)。
(三)沉迷忘我的审美心境
中印诗学韵论都描绘了一种沉迷忘我的审美心境。表现在中国韵论里是“冥然脗合”(范温语),表现在印度韵论里就是“梵我一如”。
范温以禅宗的“悟入”来喻黄山谷得书法之韵的“途径”和“境界”,言:“一超直入如来地者,考其戒、定、神通,容有未至,而知见高妙。”并进而言明悟入后得韵的境界:“自有超然神会,冥然脗合者矣。”韵的体悟如参禅入定,它的获得是通过个人的审美体验——悟,即沉浸在对象的世界里,“我”与对象“超然神会”,然后豁然朗畅,心知其妙。这种审美心境,一是要求主体内心虚空明净,二要忘怀自身,沉浸在艺术品的世界里。也就是老子说的“致虚极,守静笃”(《老子十六章》),和庄子所说的“心斋”、“坐忘”,这是天人合一状态,最终达到的是对世界至高的本原“道”的体悟。
在印度,这种审美心境就是“梵我一如”。梵在印度自吠陀时代起,就是主神,象征世界本原。世间万物是其形象显现;通过对物象观摩实现梵我一如。“梵我一如”的思想在《奥义书》中得到了充分展现,其意为“梵即我,我即梵,此之谓奥义,深密不可言说”[12](P23)。“外物全若忘,意与声音合,如水乳交融;遂尔归于一,心空顿然入”[13](P848)。欢增说“诗歌的灵魂是韵”,灵魂就是最高的存在,就是梵。“‘梵’是外在的宇宙终极原因,‘我’是人的内在灵魂,梵我如一,实现的是精神的欢乐。渴望与梵的结合,成为一切精神活动的最高目标。印度鼓励他们的艺术家在艺术的领域里进行梵的探索,凭借艺术亲证梵我同一”,“在韵论中,‘韵’被认为是诗歌的灵魂,几乎等同于梵,词句、词音、修饰等都为显示‘梵’而存在”[14](P33)。这种审美心境,就是一要内心纯净,不含杂念,二要内心平静,三全身心沉浸在对象里,四超然忘我,不以知识和理性去推理。新护说“一个有鉴赏能力的读者在读诗时,也会产生另一种超越文字的感知。作为一个有鉴赏能力的读者,他的心具有纯洁的直觉……读者(或观众)在理解了这些诗的文字意义之后,立即产生另一种超越诗句特定时限的感知。这是一种内心的、直接的感知”[2](P484-485)。这种审美心境,最终通向世界本体,达到对宇宙人生一种形上的体悟。
在虚静澄明的审美心境和冥然合一的审美体验方式上,中印古典诗学的韵论可谓异曲同工。
(四)喜悦自适的美感效果
中印的古典诗学都注意到优秀的诗歌艺术给人带来的审美愉悦的心理感受,即喜悦自适的美感效应。
范温在韵论中,以禅宗悟入来比喻得韵和达到韵的境界,即“自有超然神会,冥然脗合者矣”。范温以禅喻诗,“悟”不仅是了悟佛法的方式,即个体通过亲身的感受、领悟、体会达到豁然开朗的瞬间顿悟;也是获得禅意领悟后所达到的境界,即禅家所说的“万古长空,一朝风月”的禅境,“在瞬刻中得到了永恒,刹那间已成终古。在时间是瞬刻永恒,在空间则是万物一体,这也就是禅的最高境地了。”[15](P197)由于禅、艺致思特点的相似性:都注重身心感知、直觉体验和超然神会,因此中国的诗学家常以禅喻诗,严羽言:“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沧浪诗话》)诗家的“妙悟”,同样一是指学诗的途径即直觉体验的过程;另一层是指通过妙悟的方法达到澄明的诗歌境界。这种审美境界的获得也伴随着一种涣然冰释的内心喜悦感,有如佛家的“拈花微笑”,怡然自乐。
欢增是《韵光》中多处论到这种诗歌带给知音们的“喜悦”。他认为韵,“它是令知音内心喜悦的诗的真谛”[2](P238-P239),又如:“艳情味是最甜蜜、最愉快的味”[2](P251),“这种意义可爱而给具有鉴别能力的知音带来喜悦的诗无计其数,其中的这一类称作以韵为辅的”[2](P324),“好的内容生动活泼,知音们感到惊喜”[2](354)。另一位梵语诗学家恭多迦认为“诗是词句组合中安排音和义的结合,体现诗人的曲折表达能力,令知音喜悦”[2](P503),“新护将不受阻碍的艺术感知称作‘惊喜’”,“新护将‘惊喜’描述为不厌倦和不间断地沉浸在享受中。或者说享受者(即品尝者)沉浸在奇妙享受的颤动中”[7](P314)。喜,ānanda,在这里就是审美快乐。这种快乐,类似宗教体验的超越性。毗首那特描述味的品尝方式以及味的特征时,说:“由于充满善性,味完整而不可分割,自我启明,由欢喜和意识构成,摒绝与其他感知对象的接触,与梵的品尝是异父兄弟,以超俗的惊喜为生命,与品尝本身没有区别。它被知音们品尝,犹如自己品尝自己”[2](P832)。
金克木先生在《印度美学》一文中总结说,艺术品的“味”、“韵”必须能令人达到“喜”的境界,即“物我双亡”、主客合一[16](P9),这一思想“一直到现代在印度统治地位的哲学和美学理论都以这一点为出发点和归宿。不仅“情景交融”,而且是要求合一。这合一的精神境界便是“喜”[16](P11),“作为纯粹欢乐幸福的精神的‘喜’成为人生的也是艺术的最高境界。艺术欣赏得到同修行入定一样的精神境界。这成为近一千年间印度美学思想的主要线索”[16](P11)。
三
尽管在诗学审美理想、艺术表现方式、美感效果等方面,中印古典诗学显示了高度的一致。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些显著的差异和各自的偏重。
一汉梵语言的差异。源于汉藏语系的汉语和源于印欧语系的梵语,首先在词义的表现方式上有很大的差异。梵语是屈折语,词有性、数、格、时、态等多种复杂的变化,发音上也有变音和连音的复杂变化。因此,在梵语诗歌中,词本身就极具表现力。而汉语是孤立语,缺乏梵语这种词形上的丰富变化,字和词的意义相对独立固定。在语言运用上,往往是通过词序的组合方式和使用虚词等方法来表达意义的丰富变化。但二者也不是完全不能沟通,正如黄宝生先生所言,这种沟通的可能仍然是有的“梵语是屈折语,因而具有这种词形曲折变化的暗示作用。但究其实质,也可以说是词(以及词组)的暗示作用。汉语是独立语,没有这种词形曲折变化,但通过词序、词组、虚词等语法手段,也可以达到同样作用”[7](P353)。
其次是文体上的差异,即对“诗”界定不同。梵语诗学里的“诗”分为可看的诗和可听的诗,是包括戏剧、叙事诗、抒情诗等在内的纯文学形式,而不专门指诗歌。由于有着宏大的史诗源头和完整的神话体系,梵语诗歌中叙事诗很发达,在诗论中,也常选取“大诗”的篇章小节做分析对象,比如欢增、曼摩吒举例的诗作大部分是“大诗”①古典梵语诗歌一般分为大诗和小诗两大类。大诗主要指叙事诗,小诗主要指抒情诗。参见黄宝生:《印度古典诗学》,第19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有时也论述不受诗律限制的散文,“散文作品也要像诗一样,词语组合方式都要如上所述适合味”[2](P287);而中国古典诗歌以抒情诗为主体,即便是山水田园诗,虽句句写景,也是句句在写情。中国的叙事诗远不如抒情诗发达,叙事诗批评的成熟也比较晚,但中国的抒情诗里往往也有叙事性的技巧,比如前面举的一些例子。因此中印古典诗韵论,在论诗对象上,差异就较大。尽管文体上有差异,但某些诗学观念、审美理想和艺术表现方式上的共性还是可以进行比较的。
再者,和中国诗话中多直观印象式点评方式不同,印度诗学理论更注重的是诗法层面的形式技巧和诗法陈规的细致分析和罗列。比如范温评价陶诗“体兼众妙,不露锋芒”,“行乎质与癯而又若散缓不收”,这是对审美形态模糊地描述,缺乏严谨分明的逻辑分析。欢增在论韵时,则偏重逻辑分析。比如他将韵分为两大类:非旨在表示义和旨在依靠表示义暗示另一义。然后又对这两大类进一步分类;在“依靠词义的力量领会到另一种庄严的韵”中,他又细分隐喻韵、明喻韵、略去韵、补证韵、较喻韵、奇想韵、双关韵、罗列韵等等。其他诗论家也是如此,比如论庄严,下分谐音、叠声、双关、比喻、想象等,而比喻下又分明喻、隐喻、互喻、较喻等,其中隐喻又分八种、较喻则多达四十八种①参见毗首那特“论庄严”,选自黄宝生译:《梵语诗学论著汇编》(下册),第1054页,昆仑出版社,2008年版。;还有诗德和诗病的特征、种类等等,都尽可能的详细列出。“经过比较可以发现,中国韵论超越了对词与义的藩篱,着重的是诗歌整体所蕴涵的美,诗歌所表现的实际上是以诗人的主观体验为主的艺术境界。而印度韵论家还是在词、义关系问题上盘桓,囿于形式,所表现出来的主要还是作品的内容美”[9](P299)。这个差异,对中印诗学家而言正可互相借鉴。
此外,中国的韵论偏审美鉴赏,印度的韵论偏创作技法,可见韵论不仅可以用于审美鉴赏,也可用于指导创作,它不是不可直陈、不可名状的,而是具有可实践操作性的。
前文已说过,中印古典诗学韵论的叠合处,可以对我们把握艺术的审美本质和规律有所启发;而差异处,则是互补的方向,如何彼此借鉴,取长补短,不仅是诗人们以资学习的经验,也是诗论家的重要任务。
[1] 钱钟书.管锥编:第四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 黄宝生.梵语诗学论著汇编[M].北京:昆仑出版社,2008.
[3] 季羡林.关于神韵[J].文艺研究,1989,(1).
[4] 任先大,田泥.中印古典“韵”论比较研究 [J].吉首大学学报,2007,(2).
[5] 袁向彤.中印古典美学中的“味”与“韵”论比较研究[J].时代文艺,2008,(12).
[6] 杨晓霞.中印韵论诗学的比较研究[J]. 东方丛刊,2006,(4).
[7] 黄宝生.印度古典诗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8] 胡经之.中国古典文艺学丛编(二)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9] 郁龙余等.中国印度诗学比较[M]. 北京:昆仑出版社,2006.
[10] 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1] 邱紫华.印度古典美学[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12] 汤用彤.印度哲学史略[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13] 徐梵澄.五十奥义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14] 郁龙余等.印度文化论[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
[15]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16] 金克木.东方文化八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责任编辑:冯济平
On Aesthetic Connotation of "Yun" Between Chinese and Indian Classical Poetics
CHENG Jing-jing
(Chinese Department,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ion: Ānandavardhana, an Indian poetical theorist of the ninth century, and Fan Wen, a Chinese poetical theorist of the eleventh century, pose the propositions about rhyming. They hold that rhyming is the fascination of classical poetics, and also have established a theoretical system on rhyming. By comparison, we not only find some common features between these poetical theorists, but also comprehend the coincidence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Indian poetic theory, such as aesthetic conception, aesthetic ideal and thinking mode.
rhyming; aesthetic connotation; Chinese and Indian poetics
I0-03
A
1005-7110(2011)01-0064-08
2010-09-26
程晶晶(1982- ),女,安徽铜陵人,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生,主要从事文艺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