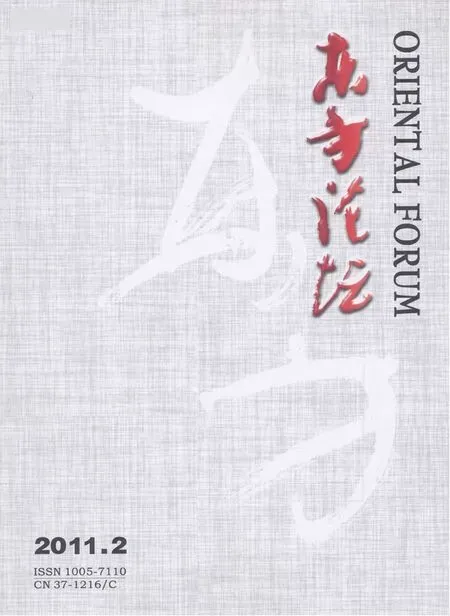论唐代科举制对骈文普及的促进作用
翟景运 牟艳红
(青岛大学,山东 青岛 266071)
论唐代科举制对骈文普及的促进作用
翟景运 牟艳红
(青岛大学,山东 青岛 266071)
中唐古文运动没有彻底改变骈文的主流文体地位,唐代仍是骈文风行的时代。唐代骈文的普及,除了骈文自身发展演变的历史惯性之外,科举制度发挥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唐代科举中的进士科考试以骈体诗文为重心,广大士子以骈文为必修课,科举制度遂成为骈文流行的制度保障。
唐代;骈文;古文;科举
唐代古文运动是骈、散两种文体的第一次较量,古文还不能说是对于骈文取得了完全的优势,骈文的影响不可小觑。古文运动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功,但由于外部和自身的种种原因很快衰落下去,晚唐五代直到宋初,骈文再度兴盛,直到北宋古文运动兴起,古文的优势才算是最终确立。从宏观上说,唐代仍然是骈文风行的时代。唐代骈文的普及,除了骈文自身发展演变的历史惯性之外,还有若干社会条件在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唐代科举中的进士科考试以骈体诗文为重心,广大士子以骈文为必修课,科举制度遂成为骈文流行的制度保障。
一、骈文在唐代的主流文体地位
古文运动改变了数百年来骈俪文体一统文坛的局面,有力地打击了风靡已久的绮靡浮艳的文风,开创了中国古代文章发展的新传统,但如果认为唐代古文运动使古文取得了完全的优势,则不免夸大了它的成果,将文体发展问题简单化了;唐代古文运动之后,骈文并没有从文坛上消失,骈文仍然占有巨大的市场,并且非古文所能轻易取代,这是当时的历史事实,对于古文市场的扩大和骈文的领地的保持,需要有客观、具体的分析。其实即便是在后来的整个传统社会,骈文一直保有自己通行的领域,始终未能为古文所彻底取代。
唐代古文运动之前,以改变文体为目的的改革,严格来讲只有西魏大统时宇文泰、苏绰的改革。苏绰所作《大诰》,摹仿《尚书》典正质朴的文体风格,点窜典谟,改变长久以来公牍文采用偶俪绮艳的骈体文的情形,基本上采用单行散笔,目的在于“建言务存质朴,遂糠粃魏晋,宪章虞夏”。苏绰的改革,就文章写作而言纯属彻头彻尾的复古,这类不尊重文章本身发展规律的改革当然没有前途可言。《周书》卷四一《王褒庾信传》说它是“虽属词有师古之美,矫枉非适时之用,故莫能常行焉”,此论可谓一针见血。从骈体文逐步得以定型的南朝,到古文运动逐渐兴起的唐代,对于骈文的批评始终未曾中断。不过批评的性质却不尽相同,有针对文风者,有针对文体者,大抵以针对文风的批评为多。文风的改良同文体的改革截然不同,它首先表明在根本上对于骈偶体制的认同,其次还会在客观上促进骈文的适应性,扩大其影响和流行范围。
制、敕、诏、册等中朝公文和表、状、笺、启、牒等幕府公文,科举考试所涉及的律赋、判词等文体,传统上都使用骈体,这在中唐古文运动鼎盛的时候也没有改变。六朝时期所形成的传统习惯,在唐代影响甚大,这个影响一直延续到两宋甚至整个传统社会。这是骈体文最为稳固的阵地。骈文和古文有所竞争和消长的领域,在于公文和考试文体之外的私人写作,比如书、启、记、序、墓志等等体裁。古文运动鼎盛时期,从骈文中夺过来若干体裁,原本使用骈体来写作,改由古文来写;随着古文运动声势的消退,被古文夺走的若干体裁又在一定范围之内还原为骈体。以墓志而言,这种体裁在韩愈的古文创作中数量最多,占到其32卷文集中的12卷,总计78篇;韩愈的碑志之作在古文运动中的影响也最大,是推广古文的一面旗帜。韩愈死后,随着古文运动的衰落,墓志又逐渐为骈体所占据。从《全唐文》所收墓志来看,元和、长庆以后至唐末,散体在墓志中所占的比例呈现递减之势。据笔者统计,《全唐文》卷731-760中,骈体墓志只有4篇,而散体者30篇,骈体仅占11.8%;卷761-790中,骈体5篇,散体24篇,骈体占17.2%;卷791-840中,骈体17篇,散体3篇,此时骈体占到了85%。骈体的增长在会昌、大中以后最为明显,可以说又恢复了绝对优势。其次如也是中唐古文写作重头戏的书、序。如果说墓志是史传的延续,那么书、序文便是古代议论文的支与流裔。如韩愈32卷文集中有9卷为书、序,柳宗元43卷文集中书、序占到将近四分之一的比例。到了晚唐,某些作家现存的此类体裁的作品竟然全部都为骈体,从中几乎看不到古文运动的影响。比如《全唐文》卷786为温庭筠文,共收其骈赋2篇、骈体状1篇和“书”7篇,中唐以来的“书”多用古文写作,温庭筠所作7篇,都是骈体;卷787为段成式文,所收11篇书、序,全为骈体;卷766为活跃在会昌、大中间的薛逢的15篇存文,计有律赋2篇、启9篇、书4篇,也都是骈体。除此以外,个别先前以散体为多的应用文,晚唐时采用骈体写作者反而逐渐多了起来。比如奏疏,一般围绕具体琐碎的事务生发议论,骈体较难措手,因此多用散体。《四六丛话•序章疏》云:“盖奏疏一类,下系民瘼,上关政本,必反复以申其说,切磋以究其端,论冀见从,多浮靡而失实;理惟其晓,拘声律而难明。此任、沈所以栖毫,徐、庾因之避席者也。”晚唐奏疏类文字采用骈体的比例也有所增长,如《全唐文》卷731-790大抵为元和至开成间的作品,其中奏疏为骈体者13篇,散体者47篇,骈体约占21.7%;卷791-840大约为会昌、大中以后的作品,骈体奏疏36篇,散体20篇,骈体比例高达64.3%。
从魏晋到中唐,骈文作为一种文体,其绝对优势已经维持了五百多年,形式上逐渐趋于精密完备。特别是在唐代,骈文成为选举人才的一项重要标准,文人们代相沿习,浸淫钻研,久而久之,便逐渐习惯了这种特殊的思维、写作方式,所要表达者自然而然地要出之以骈偶俪对,因此虽然经过几代文人的努力,古文已经渐趋普及,但骈文的影响仍然显得根深蒂固。除了个别特具才力和识见的杰出作家之外,无论是文章的基本语言结构,还是构思和布局,一般文人很难完全摆脱骈体的影响。包括古文家在内的作家群,有些人就是从学习写作骈文起步,致力于古文创作的同时也难免直接借助骈语骈句。“在唐代,写骈体文的人仍然多于‘古文’家。”[1](P29)“在整个唐代,骈文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整个中晚唐时代,骈文仍占主导地位。”[2](P450)
当时骈体文的这种强大“惯性”,是时代的特点,是古文运动发生发展的文化背景,也是古文运动所面对的最大阻力。造成这种惯性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唐代的科举制度。唐代科举,从地主阶级各个阶层广泛地选拔吸取人才,给资望浅薄的下层人士参与政权开辟了道路。律诗、律赋和判词是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都要出之以工整的骈体,德宗建中之前的策论也以骈体为多。唐代科举制度在扩大广大读书人进身之阶的同时,也将骈体文的地位更加巩固起来,成为骈文的“播种机”,同时也成为推广古文的一道障碍。后世科举考试虽然也多用骈体,但是古文已经普及,骈体已经彻底退守为一种专门文体,与唐代时两种文体尚处于对峙消长之势的情形是截然不同的。
二、唐代科举中的骈体写作
试诗赋主要见于进士科考试。考《旧唐书•玄宗纪下》,天宝十三载(754),玄宗试四科制举人,“词藻宏丽科问策外更诗、律赋各一首”,《唐会要》卷七六《制科举》说“制举试诗赋,自此始。”此外未见制举试诗赋的例子。唐初定制,进士试时务策五道,帖一大经;高宗永隆二年(681)依刘思立之请,加试杂文(包括箴、铭、论、表等)两篇。《唐摭言》卷一《试杂文》说:“至神龙元年方行三场试,故常列诗赋题目于榜中矣。”三场之中“先帖经,然后试杂文及策”。天宝之前,就有以诗赋居杂文之一,或者两篇全用诗赋的情况,但此时尚未形成制度。《登科记考》卷一永隆二年条说:“按杂文两首,谓箴、铭、论、表之类,开元间始以赋居其一,亦有全用诗赋者,非定制也。杂文之专用诗赋,当在天宝之季。”大概在中唐时期,三场试的顺序又有所调整,先诗赋,次帖经,最后试策,诗赋试的意义由此更显重要。
进士科是唐代科举考试中最热门的科目。唐代科举取士,多数情况下重诗赋而轻对策,重文章技巧而不重文章内容,这种倾向在进士科也表现得最为明显。早在开元二十五年(737)二月,就有诏书说:“进士以声韵为学,多昧古今……以此登科,非选士取贤之道”。[3](卷六三九)所谓“进士以声韵为学”,所针对的就是诗赋试。安史之乱以后,部分士人痛定思痛,寻找祸乱的根源,推及到科举制度,从而对科举制度的弊病给予深刻反思和严厉批评,以诗赋为主要内容的进士试就是被批评的主要对象。《通典》卷十七载赵匡《举选议》云:“进士者,时共贵之。主司褒贬,实在诗赋,务求巧丽,以此为贤。不唯挠其淳和,实又长其佻薄。”代宗宝应元年(763),礼部侍郎杨绾上疏论科举说:“近炀帝始置进士之科,当时犹试策而已。至高宗朝,刘思立为考功员外郎,又奏进士加杂文,明经加帖经,从此积弊,寖而成俗。幼能就学,皆诵当代之诗,长而博文,不越诸家之集,递相党与,用致虚声,六经则未尝开卷,三史则皆同挂壁,况复征以孔孟之道,责其君子之儒者哉!”[4](卷一一九)尚书左丞贾至也说:“今试学者以帖字为精通,而不穷旨义,岂能知‘迁怒’、‘贰过’之道乎!考文者以声病为是非,而唯择浮艳,岂能知移风易俗化天下之事乎!”他还认为这种舍本逐末的考试方法造成“末学之驰骋,儒道之不举”,是安史之乱的诱导因素之一,将进士、明经考试同政治动乱联系在一起,[5](卷七六五)因此他们都主张废除明经和进士科。但当时宰臣以“举人旧业已成,难于速改”来推脱,翰林学士则以“进士行来已久,遽废之,恐失人业”表示反对。[4](卷一一九)杨、贾等人的提议终究没能实行。不仅进士科没能取消,即便是改变进士科中最为人所诟病的诗赋考试也难以行得通。德宗建中二年(781)十月,中书舍人赵赞知贡举,一度罢试诗赋,代之以箴、论、表、赞[6](卷四四),但贞元初旋复旧制[7](P485),中间停试诗赋的时间最多不过五、六年。又文宗大和七年(833)八月,李德裕请依宝应二年杨绾上书之议,进士试以论议代诗赋,但次年九月李德裕罢相,礼部旋即罢试论议而改试诗赋。由此可见,在天宝末年以后的一个半世纪里,进士试停试诗赋的时间所占比例微不足道。
在众多要求改革科举内容的呼声当中,有一点需要特别注意:除了激烈反对骈文的古文家之外,真正否定骈文的情形并不多见,言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考试内容、录取标准与现实的需要不能衔接,或者说以诗赋为首要标准所取的人才与治国经邦的吏干之间存在着距离;主张取消诗赋试,并不代表否定诗赋本身,而是诗赋不适合作为考试内容和录取标准。因此无论改革的主张无论能否付诸实施,并不会从根本上触及骈体文的生存权。上面引及的杨绾的《条奏贡举疏》和赵匡的《举选议》都是骈文;权德舆在文学理论上主张“尚气、尚理、有简、有通”,他与陆贽、高郢一班人在主持贡举期间重经义、轻文辞的措施在精神上与古文家们有很大的一致性,这对古文运动的开展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但他们并没有明确否定或主张取消骈体文。《权载之文集》卷四〇有《明经诸经策问七道》,这是权德舆在贞元十七年至十九年知贡举时所出的试题,都是用工整的骈体文写出。因此,有必要把反对进士科试诗赋同否定骈文这两种主张严格区别开来,因为它们的实际意义是截然不同的。
诗赋为什么会成为唐代科举考试特别是进士科的稳固内容,首要的原因,在于诗赋试的要求毕竟还是同进士进入仕途之后的一部分工作相适应。《四库全书总目》卷六四《新唐书》提要云:“唐代王言(朝廷制诏类文章),率崇缛丽,骈四俪六,累牍连篇。”朝廷中诸如修史、编书、起草制诰诏令等(绝大部分是讲究辞采声韵的骈体文)文字工作需要由文士来担任,史官、中书舍人、给事中等官僚多为进士出身。因此开元间曾经一度流行“文学足以经务”[4](卷九八)、“大任必须有词学”[4](卷一〇六)等等说法。其次,律体诗赋作为考试题目也有其优长,这一点当时及后来人都有所认识。《册府元龟》卷六四一《贡举部•条制三》引大和八年礼部奏云:“(大和八年)十月,礼部奏进士举人,自国初以来,试诗赋、帖经、时务策五道,中间或暂更改,旋即仍旧,盖以成格可守、所取得人故也。”宋人沈作哲《寓简》引中书舍人孙何的话说:“唯诗赋之制,唯学优才高不能当也。破巨题期于百中,压强韵示有余地。驱驾典故,浑然无迹;引用经籍,若己有之……观其命句,可以见学殖之浅深;即其构想,可以觇器业之大小。穷体物之妙,极缘情之旨,识春秋之富艳,洞诗人之丽则。能从事于斯者,始可以言赋家流也。”明代胡震亨说:“唐进士重诗赋者,以策论惟剿旧文,帖经只抄义条,不若诗赋可以尽才。又世俗偷薄,上下交疑,此则按其声病,可塞有司之责。虽知为文华少实,舍是益汗漫无所守耳。”[8](P197)清人王芑孙《读赋卮言》说:“官韵之设,所以注题目之解,示程式之意,杜勦袭之门,非以困人而束缚之也。”把以上不同角度的论述总结起来,可以看出考试律赋的好处大致有这样三个方面:一是可以比较全面地考察应试者的知识水平及文字能力,二是便于主试官阅卷时衡量高下,三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抄袭经典或者旧文。实践证明通过这种考试还是能够“所取得人”,对于人才建设具有切实意义。
从律赋方面看,“律赋之盛,略与古文运动相应,亦在贞元、元和、长庆间”[9](P102)。对于这一耐人寻味的现象,马积高先生认为其成因有二:首先,古文运动兴起之前,作骈赋者众多,应试作律赋只需在一般骈赋基础上稍加检束即可,而在古文运动的影响之下,作古赋者渐多,喜好骈体者遂致力于律赋;第二,中唐以后,进士科愈益为士人所重,文人出身途径更加集中,不似开元、天宝之前文人出身途径多样,增加了文人从事律赋创作的动力,于是形成了古文盛、律赋亦盛的局面。
判词同样是标准的骈体文章。举子们礼部考试及第后,还要经过吏部的铨试,方可取得正式授官的资格。吏部铨试的选拔标准有四项:“一曰身,取其体貌丰伟;二曰言,取其言词辨正;三曰书,取其楷法遒美;四曰判,取其文理优长。……凡选,始集而试,观其书、判;已试而铨,察其身、言。”[10](卷十五)唐代铨选试判两道为定制,《唐六典》卷二载:“(吏部)侍郎出问目,试判两道。”“文理优长”的评判标准逐渐偏向“文”的一面。“主司之命题,则取诸僻书曲学,故以所不知而出其所不备。选人之试判,则务为骈四俪六,引援必故事,而组织皆浮词。然则所得者,不过学问精通,文章美丽之士耳。盖虽名之曰判,而与礼部所试诗赋杂文无以异殊,不切于从政,而吏部所试为赘疣矣。”[11](卷三十七)
在吏部主持的制科当中,还有拔萃一科,试判是主要内容,“选人有格限未至而能试文三篇,谓之宏词;试判三条,谓之拔萃,亦曰超绝,词美者得不拘限而授职。”[10](卷十五)“词美者得不拘限而授职”,仍然偏重在“文优”,而不是“理长”,可以看出当时评价应试判词的标准主要的并不在于内容,而在于形式,这一点与多数情况下礼部试诗赋的标准已经没有什么区别。
据元稹《白氏长庆集序》,白居易用骈体写作的一部分应试赋和百节判(即百道判)相当著名,被新进士竞相传写。白居易《与元九书》也说:“日者闻亲友间说,礼、吏部举选人,多以仆私试赋判传为准的。” 洪迈《容斋随笔》卷十《唐书判》条云:“凡试判登科谓之入等,甚拙者谓之蓝缕,选未满而试文三篇谓之宏辞,试判三条谓之拔萃。中者即授官。既以书为艺,故唐人无不工楷法,以判为贵,故无不习熟。而判语必骈俪,今所传《龙筋凤髓判》及《白乐天集甲乙判》是也。自朝廷至县邑,莫不皆然,非读书善文不可也。宰臣每启拟一事,亦必偶数十语,今郑畋敕语、堂判犹存。世俗喜道琐细遗事,参以滑稽,目为花判,其实乃如此,非若今人握笔据案,只署一字亦可。”洪迈所云可与元、白之说相印证。白居易应试赋、判在当时如此“抢手”,正因为它们是应试考生们的现实需要。
三、古文家在科举中的矛盾和困境
韩愈通过亲身经历,深感以雕琢藻绘之文取士的弊端,从而对这种文体感到不满,这是他提倡古文、试图以一种古奥奇崛、不同于流俗的文体来取代骈文的原因之一。他在《答李翊书》中劝勉后生学习古文要“无诱于势力”,但在势利面前不为所诱的又能有几人呢?行政公文的行文习惯不改变,科举取士的标准就不会改变,世人的写作习惯也就难以改变,骈文文体就难以彻底取消。古文家虽然身体力行、不遗余力地推行古文,但毕竟个人之力难以同制度相对抗,难以同世人的从众心理相对抗,因此韩愈不得不自叹:“虽几于成,其用于人也奚取焉?虽然,诗用于人者,其肖于器邪?用与舍属诸人。”韩愈在《与冯宿论文书》中描述当时古文创作的遭遇说:“(仆)时时应事作俗下文字,下笔令人惭;及示人,则人以为好矣;小惭者亦蒙谓之小好,大惭者即必以为大好矣;不知古文直何用于今世也;然以俟知者知耳。”由此可见当时凡“应事”即须作“俗下文字”,即骈体文,古文的市场逼仄狭小。社会上对文章的需求,无论就实用还是审美的角度而言,都在很大程度上同古文家的理想相反。古文家皇甫湜(约777-约835)评价韩愈古文说:“如长江秋注,千里一道,冲飙激浪,瀚流不滞,然而施于灌溉,或爽于用。”[12](卷六八七)一方面对其造诣表现出高度的推崇,另一方面也承认其缺乏市场和实用性。明人胡应麟指出韩愈“文字殊不为庙堂重”[13](P200),这是符合事实的。韩愈在《祭柳子厚文》中就曾慨叹:“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令吾徒,掌帝之制。”士子中举之后,必然要撰写各种各样的官样文章,科举考试骈文写作,正是为了适应这种现实的需求。又如沈亚之《与京兆试官书》云:“去年始来京师,与群士皆求进而赋以八咏,雕琢绮言与声病,亚之习未熟,而又以文不合于礼部,先黜去。”这通书信作于元和七年(812)冬,文中的“去年”乃指元和六年,这正是儒学复古和文学复古运动已经进入高潮的阶段,沈亚之仍然不免因为“未熟”“雕琢绮言”而被黜,由此可见唐代科场文风之一斑。相对于沈亚之来说,孙樵显然更能适应当时社会的需求。其《自序》云:“樵家本关东,代袭簪缨,藏书五千卷,常以探讨。幼而工文,得之真诀,提笔入贡,士列于时,以文学见称,大中九年叨登上第,从军邠国。”所谓“真诀”,无非就是应对科举考试所需要的骈文写作规范、程式和技巧,这是“叨登上第”的基本条件。
为了迎合世俗需要,一些本来擅长古文的人,也转而写作骈文。《唐代墓志汇编》所收《韩昶自为墓志铭》云:“及年十一二,樊宗师大奇之。宗师文学为人之师,文体与常人不同,昶读慕之。一旦为文,宗师大奇。其文中字或出于经史之外,樊读不能通。稍长,爱进士及第,见进士所为之文与樊不同,遂改体就之,欲中其汇。年至二十五,及第释褐,柳公公绰镇邠辟之,试弘文馆校书郎。”韩昶乃古文大师韩愈之子,在功利需要的推动之下也不免抛弃古文写作而改写骈体时文,可见世俗力量之强大以及唐代古文在这种力量面前软弱无力的一面。李商隐《樊南甲集序》云:“樊南生十六能著《才论》、《圣论》,以古文出诸公间,后联为郓相国、华太守所怜,居门下时,敕定奏记,始通今体。”《旧唐书》卷一九〇下《李商隐传》云:“商隐能为古文,不喜偶对。从事令狐楚幕,楚能章奏,遂以其道授商隐,自是始为今体章奏。”写作骈体章奏是掌书记等幕府僚佐基本的生存之道,故而欲罢不能,正如商隐在《樊南甲集序》中所说:“仲弟圣仆(羲叟),特善古文,居会昌中,进士为第一二。常表以今体规我,而未焉能休。”
以韩愈、柳宗元等人为中坚的中唐古文运动,可以说是一次有组织、有领导、有理论的文学运动,它之所以能够一度取得成功,是因为它还有其独特的策略,即通过广泛建立师弟子关系团结一大批古文方面的可造之材,从而壮大古文创作的队伍,扩大古文的影响。这个策略的实施,实际上还是依附于科举。根据唐代科举的惯例,应试的举子要在考试前把自己的文学创作呈送给当代政坛、文坛上有地位的人,请求他们向主司推荐,从而增加自己及第的希望,即所谓“行卷”。接受行卷的人,往往也是早年通过科举出身的高级官僚。韩愈入仕以后,已经在文坛上初步树立起古文的大旗,同时他不仅以儒家道统自任,而且还以“师道”自任,不顾世俗的“群怪聚骂,指目牵引”,乐于接纳、荐引后进,把推行古文与提拔后进这两件事情结合起来,由此形成了一种有利于促进这一新兴文学运动的连锁反应。李观、欧阳詹、李翱、李汉、皇甫湜、沈亚之、孙樵、樊宗师等古文家一般都被看作“韩门弟子”,他们共同构成了古文运动的骨干力量。柳宗元虽然缺乏韩愈“抗颜为师”的魄力,实际上也在实践着同样的策略,正如韩愈《柳子厚墓志铭》所说:“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其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赵璘《因话录》卷三说:“元和中,后进师匠韩公,文体大变。又柳柳州宗元、李尚书翱、皇甫郎中湜、冯詹事定、祭酒杨公(敬之)、余座主李公(景让)、皆以高文为诸生所宗;而韩、柳、皇甫、李公皆以引接后学为务。杨公尤深于奖善,遇得一句,终日在口,人以为癖,终不易初心。”由此即可清晰看出“文体大变”与“接引后学”之间的必然联系。
必须指出的是,利用科举制度达到推广古文的目的,虽然手段巧妙,却仍然绕不过骈文这一关。“行卷”这种行为毕竟是以科举考试为鹄的,无论是接受行卷的高官,还是行卷的举子,归根结底都是科举中人,不在科场中写出足以中举的骈体诗文,这种通过师弟子关系推广古文的努力也就收效甚微、甚至毫无意义了。或者可以这样说,要想获得鼓吹古文的最大“自由”,必须首先突破骈文考试这层“必然”的束缚。因此我们看到,众多韩门弟子中,除了樊宗师等极少数人之外,几乎全是进士词科集团中人;我们还可以看到,古文领域中所谓“唐宋八大家”,无一人不是进士出身,而且八位古文家无一例外都是骈文高手。
[1] 曹道衡.中古文学史论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3.
[2] 王运熙.中国古代文论管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3] 王钦若.册府元龟[M].北京:中华书局,1960.
[4] 刘昫等.旧唐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5] 李昉等.文苑英华[M]. 北京:中华书局,1966.
[6] 欧阳修.新唐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7] 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M].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
[8] 胡震亨.唐音癸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9] 马积高.历代辞赋研究史料概述[M]. 北京:中华书局,2001.
[10] 杜佑.通典[M]. 北京:中华书局,1984.
[11] 马端临.文献通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2] 董诰等.全唐文[M]. 北京:中华书局,1983.
[13] 胡应麟.诗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责任编辑:潘文竹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mperial Exam System of the Tang Dynasty and Its promotion of Parallel Prose
ZHAI Jing-yun MOU Yan-hong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266071, China)
Besides the inertia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arallel prose, the imperial exams of the Tang Dynasty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the prevalence of the parallel prose. All of the bureaucratic candidates had to regard writing parallel prose as their compulsory course; hence, the bureaucrat exam system became a safeguard of parallel prose.
Tang Dynasty; parallel prose; folk prose; imperial exam system
I207
A
1005-7110(2011)02-0085-05
2010-09-27
翟景运(1978-),男,山东兖州人,文学博士,青岛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牟艳红(1978-),女,山东青岛人,文学学士,青岛大学党委办公室科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