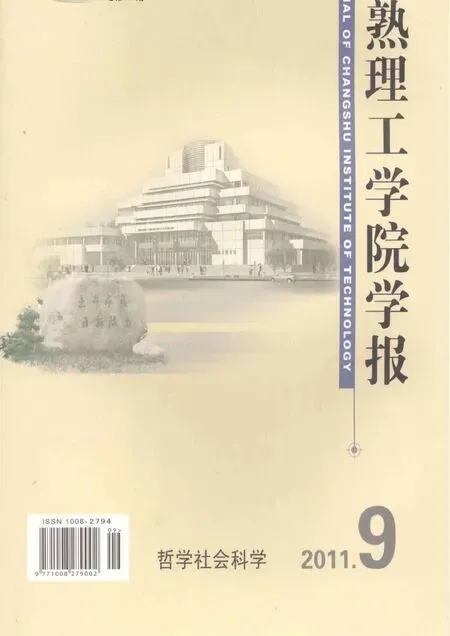非暴力革命
——以苏州为典型的辛亥革命又一模式
高钟
(苏州科技学院人文学院,江苏苏州 215000)
非暴力革命
——以苏州为典型的辛亥革命又一模式
高钟
(苏州科技学院人文学院,江苏苏州 215000)
1911年苏州的“和平光复”,堪称辛亥革命中非暴力革命的典型。这一典型引发了浙江、福建、广东等东南各省相继响应,形成了与武昌等地暴力革命相辅相成的辛亥革命又一模式。揆诸史实,苏州模式在汉阳失守、武昌岌岌可危之际,在东南财赋之地革命成功,并克服南京、截断运河,使清政府失去东南财赋与漕粮支持,无法持久,不得不逊位下台。辛亥革命首义于武昌,收功在江南,枢纽在苏州。漠视与否定辛亥革命中的苏州模式,有失历史公允。这一模式的产生,因缘于太平军之役后苏州及东南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以绅商为代表的雄厚社会力量保全地方之努力、地方官员之顺应时势、以东南文化精英为主体的立宪党人与革命党人主动合作等诸因素。
辛亥革命;非暴力革命;苏州
一、辛亥革命存在多种模式
长期以来,革命是暴动的观点深入人心,一谈革命就是暴力革命。特别是辛亥革命武昌首义是新军的枪剌将清王朝的皇冠挑落,暴力革命更似成了辛亥革命的唯一模式。其实不然。马克思、恩格斯都曾说过,历史是在合力推动下前进的。辛亥革命作为中国近代最伟大的革命,其推动力也不是单一的,而是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各政党派别合力运作的结果。当然,在这个合力之中,以孙中山、黄兴为首的革命党人起了主导性作用,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张謇、汤化龙等立宪派在其中的辅助作用;同时,也不能否定明敏地见机而作、弃暗投明的清王朝旧官僚黎元洪、程德全等人的历史作用。特别是不能否认以苏州为典型的立宪党人与革命党密切合作、以商会等社会中间阶层为主体团结旧官僚程德全、以“和平光复”形式而完成的推翻清王朝政权的非暴力革命的历史作用。这一以社会中层为主体、团结各政治派别力量结成反清统一战线的“和平光复”的革命形式,不仅维护了苏州社会正常的生产与生活秩序,对社会未造成破坏;还能利用清王朝苏州藩库中的四十万两白银为革命之经费,以江南机器局库存的大炮、枪支弹药为革命军之武装,组成江浙联军,攻下南京,为民国政府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毫无疑问,辛亥革命首义于武昌,收功则在江南,转折枢纽则在苏州。
对于非暴力的辛亥革命苏州模式,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前贤学者有不少研究,如章开沅、林增平主编的《辛亥革命史》,金冲及、胡绳武合著的《辛亥革命史稿》,李新等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王树槐著《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江苏省(1960—1916)》,马敏、朱英合著《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马敏著《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等,这些著作都有专章论述;此外,还有大批学术论文也有涉及,如李茂高等的《江苏光复与程德全》、王来棣的《立宪派的“和平独立”与辛亥革命》、李希泌等的《辛亥革命的两种起义方式》、马敏的《辛亥革命时期的苏州绅商》、耿云志的《张謇与江苏咨议局》、章开沅的《张汤交谊与辛亥革命》等等。这些著作与论文主要是在论述苏州及其带动下的江苏和平光复过程中进行评价,如王来棣认为,和平独立“固然加速了清王朝的覆亡,但最后又促使辛亥革命夭折”[1]1252;李茂高等人则认为:和平光复“在某种局部特殊情形下比武力光复更有利于革命,有利于人民。”[2]979马敏则注意到:“‘和平光复’之所以成为辛亥革命中地方政权变革的一种较为普遍的模式,有着远比种种个人因素更为深刻的历史和社会阶级结构方面的原因”[3]257,但马敏对这一深层次的原因未能展开研究。章开沅先生目光如炬地指出:“辛亥革命首先暴发于武汉,但决定全国局势者则为上海与江浙的相继独立。这说明东南地区和东南精英,不仅在近代中国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中,而且在全国政局变化中已经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因其总体实力不足以取代北方传统政治中心地位,而且东南精英乃是半新半旧的人物,所以辛亥革命只有以南北妥协宣告结束。”[4]99章先生在此已明白无误地指出,辛亥革命“决定全国局势则为上海与江浙的相继独立”,这也印证了“辛亥革命收功于江南、转折在苏州”的观点。
台湾学者王树槐先生对苏州“和平光复”于辛亥革命的重要意义有过充分的论述:“苏州的光复代表江苏省的光复,……自武昌起义后至上海光复前,其间二十五天,全国只有湖北、湖南、陕西、江西、云南、贵州六省光复。自上海光复至福建光复,其间六天,新增加的省份达六省之多。”[5]151其中新增加的六个省,基本上都是仿袭苏州的“和平光复”模式的。至南北议和成功之日,当时独立的省份已有十五个之多,其中和平光复的有六个省,为全部独立省份的五分之二。由此可见,以苏州为典型的“和平光复”的非暴力模式,是辛亥革命中一个与暴力革命相并行的革命模式。但是,这一重要模式长期以来一直受到漠视,不为主流研究所认可。
和平光复的苏州辛亥革命模式,长期不被认可的一个关键点,就是将革命与暴力等同的认识误区。实际上,革命不一定完全是暴动。革命是政治斗争中的一个极致的手段,他以完成政权更迭、政治纲领变换为根本。这种政权的更迭关系到权力、财富的根本性再分配,极易引起掌权的既得利益者不择手段地进行反抗,所以,暴力革命的形式比较多。但如果是民心已去,特别是武装力量的人心已去,那么,既得利益的掌权者失去了武力支撑,就无法进行暴力反抗;革命者为了社会的平稳发展,在某些方面做出一些人道主义的让步,和平的、非暴力的革命就有可能成功。张謇1912年《革命论》一文中诠释了革命之义:“革命之文,盖本于《周书·多士》,虞义以为将革而谋谓之言,革而行之谓之命。程传以为王者之兴,受命于天,故易世谓之革命。”[6]159“易世”,改变政权之所属是革命的根本之义,暴力与非暴力是革命的两种不同手段与模式。只要政权发生了根本的变易,即可称为革命,至于是否使用了暴力,只是革命的形式而已。我们不能因形式而否定内容。不能因为苏州的和平光复没有使用暴力,就认为其是对旧官僚的妥协。实际上,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两种革命模式。英国的“和平革命”与苏州辛亥革命就是一个典型。
二、辛亥革命中的暴力与非暴力是相辅相成的
辛亥革命中的暴力与非暴力两种模式实际上是交叉进行、相辅相成的。暴力中有非暴力,如武昌首义是暴力的,但在立宪党人汤化龙的建议下,请出黎元洪当都督后,湖北其他的府县,如宜昌、黄岗等地基本上是传檄而定、和平光复。这种与旧官僚黎元洪、立宪派中的激进派汤化龙结成反清统一战线的模式,不仅影响到后来的苏州,而且对革命的成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时,清王朝派到武昌镇压起义的海军司令萨镇冰与黎元洪有师生之谊,舰长又是汤化龙之弟汤芗铭,所以海军很快反正,调转炮口轰击汉口清军。首义之省尚且是暴力与非暴力的结合,其他各省亦是如此了。
其实,苏州的和平光复并不是完全没有武装力量的支持。早在革命之前,苏州与上海的商会就组织了武装的商团,成为国家武力之外的社会武装。这支武装对于苏州与上海的和平光复是起了主要作用的。除了这支社会武装之外,革命党人与立宪党人在清王朝的武装新军与警察中也做了很多工作,基本上将之争取了过来。在上海,陈其美单身进入机器局劝降受挫被扣时,是商团、警察及李燮和带领的军队包围机器局,迫使督办逃跑而救出陈其美的。所以,上海基本上是和平光复的。苏州也同样,程德全是一个开明的官僚,他对于革命党人在新军中的活动十分了解,对于民心的向背也了然于心,而这些正是他能顺应民心、和平光复的原因所在。
这一暴力革命与非暴力革命相辅相成的状况,在辛亥革命中比比皆是。如广东省,武昌首义后,虽然有各地民军蜂起,但省城却是在苏州光复模式的影响下而和平光复的。福建与浙江也是与苏州一样,即由新军发生了内在的转折,加上民军与商团的介入,基本上就“和平光复”了。以新军、商团、民军为后盾,主政的官员或者明于大势,主动弃暗投明、反正光复;或者大势所趋下,被迫“和平光复”,革命党人顺应时势地接受政权。
三、辛亥革命苏州模式的历史合理性
对于辛亥革命的苏州模式,多年来批评的多、肯定的少。主要是说与旧官僚妥协,革命不彻底,最后埋下了革命失败的根芽。这种批评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革命并不意昧着一定要破坏。而且,革命一定要包含一个建设阶段。所以,如果能以和平的、非暴力的方式完成政权的转移,这对于社会发展是有着极大的利益的,也是社会各阶层由衷拥护的。而能否以和平的方式完成政权的大转移、不引起社会的震荡与破坏,需要有成熟的政治经验与行政能力。当时的革命党人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没有实际从政的经验,缺乏这种政治操作的实际能力;所以,与有着丰富政治斗争经验的立宪派、旧官僚合作,是他们的明智选择,而不是什么无原则妥协。历史证明,这种合作对辛亥革命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的。人称“民国产婆”的赵凤昌回忆说:“党人赤诚革命,躬冒百险,不折不挠,毅勇信非恒流所可及。然蹈厉有余,治术不足,亦为无可讳言之事。方孙之初晤先公也,言及民生凋敝,当有以解其倒悬者,孙即作豪语,谓今当先免全国之田赋。先公立止之曰:信是则军政费安所出,群首归国门,一言而为万方瞩目,慎勿轻言之。……凡此均足见党人之坦率豁朗,而尚不习于治道,幸多机敏服善,不致贻之祸阶也。”[7]256革命党人以其一往无前之革命精神,旧官僚、立宪派以其执政之经验、政治斗争之谋略,三方密切合作、群策群力,在三个多月的时间内结束了二千年的帝制,其革命的成本之低、对社会的破坏之微都是前无古人的。而这正是辛亥革命苏州模式的一个历史贡献所在。
辛亥革命中暴力与非暴力的相辅相成,正是中国近代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反映。作为一个地域辽阔、自然条件呈现多元的国家,由此导致的多元的生产方式致使各地区间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存在显著的差别。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受西方市场经济影响较早,再加上河网密布、交通条件较好,明清之际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就诞生了很多的江南市镇,这些江南市镇,实际上是中国市场经济在没有外力的推动下,自发形成的传统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过渡的一个合理的方式。正是在这一社会发展方式的促进下,鸦片战争之前,江南市场经济就有了长足的发展,上海开埠更加快了这一发展趋势。东南沿海与中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上处于一个明显的由东至西的三级阶梯状态,东南高居于阶梯之顶,社会经济发展远远领先于中西部地区。而这一发展的突出表现就是形成了一个相当规模的绅商集团。上海与苏州的和平光复,主要是在这一集团的策动下告成的。民国《上海县志》记载:“革命事起,民党领袖与地方士绅,咸引(李)仲玉一言为重,乃博咨众议,密谋应付,而处处以保全地方,勿伤民命为要义。”①转引自马敏《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5页。苏州光复后,“于是又以各省代表分别导致各地绅商,合群力迫长吏易帜,各地多纷纷应之。”[7]249这一传统的社会领袖——绅与经济领袖——商的结合而形成的绅商集团,是当时东南社会的精英集合,这批精英以其文化、社会与经济的领导力与动员力,“合群力以迫长吏易帜”,从而促成了苏州及东南各省的和平光复。这正是苏州模式之所以能成功并推广的关键所在。
作为一个传统商业城市,苏州商人始终是苏州社会结构中的一个主要阶层;上海开埠使这个阶层发生了质的变化,一批新式的买办、企业主商人开始出现,并以其新的知识与财力成为商人阶层内的主导;商会的成立,使他们完成了现代社团的集结,并与新士绅联为一体,形成“绅商”阶层,并借助商会、商团、市民公社等新型的社会组织网络,对传统社会移步换形,完成了具有现代意义的基层社会自治;最终,以这种自治的力量对国家政府的挤压,“合群力以迫长吏易帜”,以非暴力的形式完成了苏州与江苏的辛亥革命。同时,精英文化的积累与商业传统,使苏州的士绅有着与商人阶层合作的传统,清末新政在政府鼓励工商的政策导引下,一批有着传统功名,又接受了西学影响的新士绅步入商海,成为一身而二任的“绅商”领袖。而自太平天国之役后,清政府捐纳之途大开,使大批商人以捐纳的形式获得功名,亦成为一身而二任的“绅商”,二者融为一体,绅商阶层无疑成为苏州与江苏新的社会结构中的主导阶层。相形之下,清末正在形成的学生与新军阶层,在苏州与江苏均不占主导地位。由此,他们激进的暴力革命的政治主张,在苏州与江苏也无法占据主导地位。
绅商出于自身的经济与社会利益,要求以非暴力的方式完成“易世”的革命。这种形式的革命对于广大人民的日常生活、对于社会生产、对于社会秩序都没有带来破坏与震荡,社会生产力得以保存并继续发展,这符合人民要求安定生活与发展生产的需求,这一模式因此也得到了人民的由衷拥护。当时就有民谣歌咏:“苏州光复苏人福,全靠程都督。”①参见《苏州文史资料》(1-5合集),苏州市政协文史委1990年编,第108页。这恰恰说明,苏州“和平光复”这一非暴力革命的形式符合苏州人民的内在要求,具有其内在的历史合理性,是当时民心所向的最佳革命形式。其他区域的暴力革命并不是人民的本意偏好暴力,而是统治者不愿放弃权力与利益,以其手中之武力压制人民“易世”的要求,人民迫不得已而取其次,以暴制暴,以暴力革命推翻对人民采取暴力的统治者。
冰冻三尽,非一日之寒。苏州“和平光复”的辛亥革命模式,是苏州地区经济、文化近百年潜移默化、与时俱进的结果。鸦片战争,特别是洋务运动之后,苏州得风气之先,一批传统士人开始了学习西方的最早探索,冯桂芬、王韬等即为其杰出代表;同时,一批新时代的商人亦脱颖而出,再加上太平军之役后历任的两江总督与江苏巡抚,绝大多数都能对世界大势有所了解,成为洋务大员与清末新政君主立宪的支持者。这三部分社会中上层人士的结合,就形成了强大的社会引领力量。而这三部分人,无论是从其自身利益或是社会发展之大局考虑,都不希望发生剧烈社会动荡之暴力革命。在他们的主导下,苏州“和平光复”就成为历史之必然了。
四、结语
“和平光复”的苏州模式不是偶然的,而是苏州所代表的江南文化与历史发展的结果。特别是上海开埠,苏州成为东西方文化直接交融的汇合点,在经济现代化的同时,苏州社会结构、文化均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作为“人文渊薮”之地的苏州,绅士不仅数量多,而且活动能力大,太平天国之役,他们避难上海,接受到西方文化,开始了从传统士人向新士绅的裂变。传统士人“先天下之忧乐”情怀与现代政治参入意识结合,使他们成为洋务运动、维新运动的主要推手。清末新政,他们借咨议局完成了组织的集结,同时,多年进出官场的经验,使他们具有娴熟的政治运作技巧与谋略,从而“在全国政局变化中已经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助产了中华民国。太平天国之役后,国家与社会力量发生根本性变化,“官不能离绅而有为”。处于绅士力量强大的江苏与苏州,受绅士力量与苏属之上海等地经济发展的双重挤压,晚清江苏督抚绝大多数都较为开明,故而洋务运动、维新运动、清末新政在江苏开展都比较顺利。特别是苏绅策动、江苏督抚首肯的“东南互保”,其实质就是一次对清廷的“和平独立”,开了辛亥革命“和平光复”的先河。
革命的根本属性是“易世”,暴力与非暴力是“易世”中常用的两种手段。两种手段其实是相辅相成的。暴力革命之中往往有着非暴力的形式参入其中,如辛亥革命之苏州模式;非暴力亦往往是以暴力之武装——军队为后盾的,军队的倒戈方使非暴力成为可能。“和平光复”的苏州模式,正是在苏州新军这一暴力武装的倒戈下而告成的。英国的和平革命,中国古代甚多的“禅让”,实质上都是非暴力的“易世”——革命。这一革命形式,对于社会秩序与社会生产的发展无疑有着重大意义。
[1]王来棣.立宪派的“和平独立”与辛亥革命[C]//中华书局编辑部.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3.
[2]李茂高,廖志豪.江苏光复与程德全[C]//中华书局编辑部.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3.
[3]马敏.马敏自选集[M].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
[4]章开沅.张汤交谊与辛亥革命[J].历史研究,2002(1).
[5]王树槐.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江苏省,1860-1916[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84.
[6]张謇.革命论[M]//张謇全集:第5卷.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
[7]赵尊岳.惜阴堂辛亥革命记[G]//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总102号.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Non-violence Revolution:Another Mode of the Revolution of 1911 Represented by the Peaceful Recovery of Suzhou
GAO Zhong
(School of Humanities,Suzho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uzhou 215000,China)
The peaceful recovery of Suzhou in 1911 could be regarded as a model of non-violent revolution which evoked the responses of the southeast provinces such as Zhejiang,Fujian and Guangdong,thus forming another mode of the Revolution of 1911.The model of Suzhou revolution succeeded in occupying the wealthy southeast regions when Wuhan revolution was in danger,Nanjing was conquered and the Canal was cut off,which led to the collapse of the Qing government with financial support of the southeast severed.The revolution of 1911 took place initially in Wuchang and achieved its success in the Jiangnan Area with Suzhou as its hub.Any neglect and denying of Suzhou mode in the revolution of 1911 was unfair.The emergence of the Suzhou mode has various kinds of reasons,such as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the southeast areas after The Taiping rebellion,the strong social power represented by the gentry-merchants,the local officials who followed the trend as well as the active cooperation of the Revolution Party members and the Constitutional Party members.
The Revolution of 1911;Non-violence revolution;Suzhou
K257.4
A
1008-2794(2011)09-0031-04
(责任编辑:韩廷俊)
2011-09-05
2011年度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立项课题“辛亥革命苏州‘和平光复’模式研究”(11LSA002)
高钟(1952—),男,湖北鄂州人,苏州科技学院人文学院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社会结构、民族主义与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转型、中国近代管理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