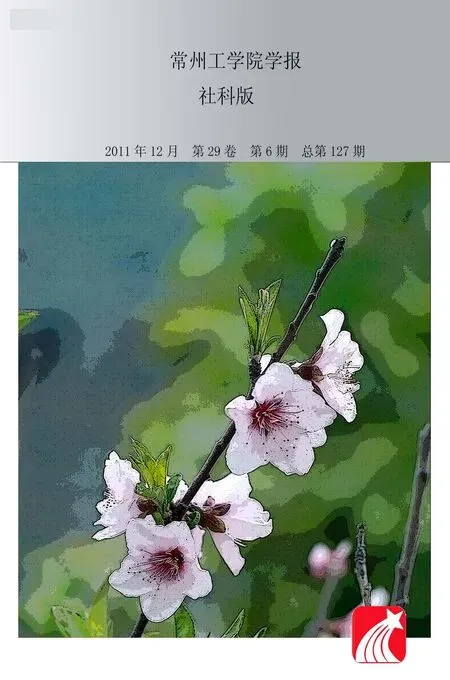日思夜梦的那片土地,究竟在哪里
——余光中《听听那冷雨》的文本细读
吴周文
(扬州大学文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2)
余光中,台湾著名的教授、评论家、翻译家、诗人与散文家,自称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并戏称“左手的缪思”,被台湾文坛称为“当代文学重镇”。祖籍福建永春,1928年生于江苏南京。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为躲避战乱在四川生活与读书11年。1947年就读于金陵大学外语系(后转入厦门大学)。1949年随父母移居香港,次年赴台岛,进入台湾大学外文系读书。1954年,与覃子豪、钟鼎文等共同创办“蓝星”诗社以及《创世纪》诗刊,提倡自由主义的创作。后赴美进修,获得爱荷华大学艺术硕士学位。回台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先后执教于台湾东吴大学、师范大学、台湾大学、政治大学、中山大学及香港中文大学。出版诗集21部、散文集11部、评论集13部,共出版著作40余部;翻译过《梵高传》等;现有《茱萸的孩子——余光中传》(傅孟君著)介绍于世。
赴台之后,余光中教授将自己沉郁而又浓烈的思乡之情,倾注于他的诗中,其中作于60年代的《乡愁》(“乡愁是……是邮票……是船票……是坟墓……是海峡”),便是最著名的一首。后来,台湾歌手杨弦将他的《乡愁》、《乡愁四韵》、《民歌》等八首诗谱曲传唱,从此,余光中以“乡愁诗人”驰名海内外。同时,他还写过一些怀念大陆故土的散文,《听听那冷雨》(以下简称《听雨》),则是其“乡愁”散文的代表作,已经成为当代散文的经典之作,而且入选多种散文选本和多种教材。(附带说明的是,选入中学语文课本的此文文本,多有删节,如江苏省使用的《现代散文选读》对开头的部分与结尾的部分,编者分别作了删节,两处加起来约千余字。据笔者所知,中学语文课本里除鲁迅作品外,都有不同程度的被删节或文字的被改动。笔者并不赞成随意删节余先生的作品。删节后,对理解与欣赏原作一般都有很大的影响。)曹惠民教授主编的《台港澳文学教程》称,在两栖诗与散文的台湾作家中间余光中的成就更为突出,“代表作如《听听那冷雨》和《高速的联想》……对知识分子建立在独特人生体验基础上而形成的丰富而复杂的精神世界,抓住其在某几个瞬间的主观印象和心理予以最充分的揭示,由此显示了思想与艺术的张力。”①这个评论,对我们理解《听雨》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这篇散文写于1974年,也正是作者离开大陆25年的时候。那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后期,海峡两岸的同胞相互阻隔与禁锢,不仅不能走动往来,而且连书信都不可互相通邮。我们理解《听雨》,必须抓住余光中作为诗人的一种特殊感觉。一般来说,诗人的感觉是敏锐、炽热、流动的,有时甚至是神经质的。而余光中写作其时诗的特殊感觉,是执拗地想念家国的忧伤。作者抒写这种感觉,很巧妙地抓住了一个特殊的意象——“雨”和“听雨”的行为来表现;尤其是抓住“听雨”时内心的疼痛感觉。这种忧伤和疼痛,创造了全篇扣动读者心扉的悒郁基调。
作品第二至三节,抒写作者因乡愁生“冷”雨的总体感觉及生成的缘由。
开头就用诗的夸张,写道:“惊蛰一过,春寒加剧。”台湾的春天尤其是在惊蛰之后,气候总是比较和暖的。作者却感到“春寒”而且“加剧”,显然这完全是夸大了的诗人的主观感受。“春寒加剧”的原因是雨季的“雨”,是躲不过的“潇潇的冷雨”,在心里的另一种感觉又是“潮润润的”。而这种“冷”与“潮”的感觉,既是“整个中国整部中国的历史无非是一张黑白片子”的沧桑感,更重要的原因,是离别故土的乡愁。诗人明明白白地说,这“冷雨”的感觉的生成是因为“二十五年,一切都断了……”;是因为“大寒流从那块土地上(祖国大陆)弥天卷来,这种酷冷吾与古大陆分担”;是因为感受这“古大陆”扫来的“酷冷”的雨,“也算是安慰孺慕之情”,故而感受到的是“冷”和“潮”。虽然用诗的夸张,强调了对雨的“冷”的感觉,但这种夸张的强调,却反复表现出诗人内心的真实:即对大陆故土缠缠绵绵的怀念,以及挥之不去的那种凄冷潮润的痛觉。诗人用自己的行动和想象,对“乡愁”进一步予以描述:“他”,在金门街到厦门街回家的路上彳亍行吟,希望狭长的巷子“永远延伸下去”,让“他”的思念之情随之绵绵缠缠,永不止息。于是作者按捺不住,直接点明“他”的乡愁:“他是厦门人……他同样也是广义的江南人,常州人,南京人,川娃儿,五陵少年……”作为中国人,作为海外游子的中国人,他日思夜梦的那片土地,究竟在哪里呢?余光中的回答:“当然是中国永远是中国。”——他在这里表明,“乡愁”的缠绵和疼痛,源于他的一颗中国心、一腔中国情。
接着,第四节作者用诗的联想,感觉“冷雨”的历史文化意蕴,借以抒写对故土的深挚思念。
诗人在说出“冷雨”感觉的缘由之后,其思绪与神魂一下梦回到“杏花、春雨、江南”的家国。这个诗意图画的描述最早出自于元代虞集的《风入松》:“为报先生归也,杏花春雨江南。”作者用这个典故,抒写他深深思恋养育他的“江南”的游子之情。“只要仓颉的灵感不灭美丽的中文不老,那形象,那磁石一般的向心力必然长在”,“太初有字……回忆和希望便有了寄托”,“翻开一部《辞源》或《辞海》……而一入‘雨’部,古神州的天颜千变万化,便悉在望中……”在这些追溯中华文化本源的背后,其实抒发的是作者对大陆故土之思。余光中对祖国传统文化的眷念,是他的“中国情结”。他在台湾写了很多诗,一会儿写李广、王昭君,一会儿写屈原、李白,一会儿写荆轲刺秦、夸父逐日等等,都是其对祖国的纠结。从上世纪90年代起,余光中带着夫人频频应邀回大陆讲学与观光,他的乡愁得以释放。而写作这篇作品的时候正值“文革”后期,惟其有着炎黄子孙的文化基因与心理定势,惟其对中华文化本源的纠结,所以在他感觉“冷雨”的时候,诗人自然围绕着“雨”的文化意蕴而浮想联翩,在心里千遍万遍地呼喊着他心中的“江南”,他对故土的深挚思念。
作品第五、六节,抒写“雨是女性”的诗意感觉及久别故土的隐痛。
第五节写诗人对“雨”的特有感觉。诗与散文作为抒写自我最直接的文学体裁,常常在文本里表现出作者很幽曲的思维活动与很微妙的心理变化。当诗人在神游故土家国的“江南”之后,再重新回到眼前的“雨”的时候,——他在高雄(在高雄住13年),踯躅于从金门街到厦门街迷宫式的雨巷里,心头涌起的那股神游故土故乡的温热,使情绪也变得温热了。他手中的笔也忽然变得温热了:“听听,那冷雨。看看,那冷雨。嗅嗅闻闻,那冷雨。舔舔吧,那冷雨。”诗一般的明快短句中,充盈着欢乐与舒畅的情韵。最突出的,是把眼前的“冷雨”,比喻成“最富于感性”的“女性”。女性是美丽的、阴柔的、多情的,因而也诱惑着诗人把春雨当成女人当成母亲(作者在《从母亲到外遇》一文中说过“大陆是母亲,台湾是妻子,香港是情人,欧洲是外遇”②)。去动情去感受的:从视觉上感觉,是“空蒙而迷幻”,是迷离惝恍的美;从嗅觉上感觉,“有一点点薄荷的香味”,是清新怡神的美;从味觉上感觉,是“草和树沐发后特有的淡淡土腥气”,是清醇本真的美。而其中破译“土腥气”的“也许地上的地下的生命也许中国层层叠叠的记忆皆蠢蠢而蠕”一句,又婉转地道出:诗人他站在台岛上,虽然面对着台湾的“春雨”,心底涌动的却是中国诗人的“中国情结”的感觉,显然,这是他爱国主义情感委婉的流露。
作品第六节,借对“雨”的感觉,进一步抒写诗人对祖国文化传统的眷恋。
诗人的思绪旋即又从感觉的现在时跳到感觉的过去时。将大陆的雨情雨景,与在美国基石山和台湾溪头的情景进行比较。美国西部的基石山虽美,但客居异国,感觉它缺少中国诗词里“荡胸生层云”或是“商略黄昏雨”的意趣,也没台湾“雨意迷离”的情调。台湾的溪头山虽美,但作为“江南”人移居他乡,只能有“在白茫茫里和溪头诸峰玩捉迷藏的游戏”的感觉。在诗人的感觉里,美国不如台湾,台湾又不如大陆的家国。“云缭雾绕,山隐水迢的中国风景,由来予人宋画的韵味。那天下也许是赵家的天下,那山水却是米家的山水……”这里作者又一次议论中国文化传统,借说山水说绘画说“中国风景”,抒写25年久别“江南”故土的眷恋,以及写作其时隔海“望乡”的惆怅与隐痛。
接下来的七至十四节,是全文写“听雨”的主体部分。写诗人自己一生“听雨”的辛酸感觉——那种“窗外在喊谁”的凄迷。
作者告诉我们,雨不仅可嗅可观,而且可“听”,可以感受其“美感”。但对此刻的诗人来说,他的感觉与在大陆听秋雨的感觉不同,“更笼上一层凄迷”。因为他把“听雨”与他的流离的人生经历联系起来了。我们读《听雨》,自然联想起戴望舒的《雨巷》,作者取了其《雨巷》的境界;也自然联想起宋末元初的蒋捷的词《虞美人·少年听雨在楼上》,余光中更多地是借鉴了蒋作的情调。蒋捷,阳羡(今江苏宜兴)人。入元后,持重气节,遁迹不仕,自号竹山。大约在晚年写成此作,用“听雨”概括自己的人生,曲写自己隐居山林的孤独与亡国之痛。余光中对蒋词作了改动,用“一打少年听雨……二打中年听雨……三打白头听雨……”来概括并抒写自己20多年来听“冷”雨的况味,是“冷冷的雨珠子串成”的凄迷,甚至感到迷失。所谓“十年前”的“摧心折骨的鬼雨”的“迷失”,是指上世纪60年代台湾文坛关于乡土文学与“现代派”之争,余批评甚至攻击台湾左翼作家及乡土作家,让人诟病至今。此事不为大陆读者所知。作者命意于“冷雨”,把思念大陆凄迷的感觉,诗化为“风吹雨打”的漂泊人生,以至凝成“窗外在喊谁”的诗句。雨声,是大陆母亲对漂泊在外的游子的呼唤!雨声,也是漂泊游子思念故土的心灵之和声。这是诗人“乡愁”的最形象最生动的诗性表达,这个诗句,无疑是全文的点睛之笔。
当诗人忍不住发出“窗外在喊谁”的抒情最强音之后,以下关于“听雨”的林林总总,都是写诗人内心凄迷的感觉。抒情散文有时就是这样,表面上叙事议论或描述情景,都是“王顾左右而言他”,曲写着弦外之音。余光中无论写忆念中的“听雨”,还是眼前的“听雨”,都是如此。借王禹偁建竹楼听雨说事,其实是说自己的向往,期盼着回大陆听那“古老的音乐”——这是比照自己内心的落寞孤独。在青少年时代“听雨”的记忆中,用视觉感受“听雨”,“她冰冰的纤手在屋顶拂弄着无数的黑键啊灰键”的感觉,是“一种低沉的安慰”——这是曲写自己内心的灰暗惆怅。在初到台岛时所居住的日式古屋里“听雨”,或者是黄梅雨的“湿黏黏”侵到“舌底,心底”;或者是台风台雨向他的矮屋“重重压下”;或是雷雨夜感受“一通又一通”的“羯鼓”;或者是江南的雨下遍了江湖桥船,下在四川下湿了那里的“布谷咕咕的啼声”,是“回忆的音乐”。而写作其时,台北的雨,因为遭遇无瓦无树的“公寓时代”,已经没了雨的“音韵”,成了“黑白的默片”——这些分明是指东说西,反衬身处异乡内心的疼痛。孤独、惆怅、疼痛,因听雨乡愁而生;孤独、惆怅、疼痛,构成了“窗外在喊谁”的凄迷感觉的内涵。
第十五节是结尾,写诗人对“故乡”的苦思苦恋,成了半生茫然无望的期待。
与开头呼应,诗人又从“听雨”的联想与想象中回到“雨巷”的情境。他由雨联想到“六角形的结晶体”雪花,由雪花又联想到自己已是白霜染发。“二十五年,没有受故乡白雨的祝福,或许发上下一点白霜是一种变相的自我补偿吧”,他神回梦游故乡家国,万般无奈而早生华发。连用“一位英雄,经得起多少次雨季?”等三个问句,反复强调“他”已等待很久,很遗憾地说:“厦门巷走了二十年与记忆等长。”这是痴情诗人心欲回归的苦思、苦恋、苦苦等待。何时能够梦想成真?接着把他的期盼,描述成一幅心理感觉的画面:“他”行吟在长街短巷中,无瓦的公寓在等他,一盏灯在等他,“整理青苔深深的记忆”在等着他……言外之意,说的是另一种踏上故乡的等待:如此天天、月月、年年、春去秋来、年复一年梦回神游,这是一个既无法实现又挥之不去的“望乡”的梦。奈何一个“愁”字了得!“前尘隔海。古屋不再。听听那冷雨。”作者用这三句话结束全文,把梦碎难圆、此“梦”绵绵无绝期的痛觉写到了极致。
其实,余光中并没有绝望,在此文之后的第18个年头即1992年,终于如愿,回到了他梦寐以求的故土家国。他回到养育过他的“江南”的时候,说过这样一段话:“我离开她时才二十一岁呢,再还乡时已六十四岁了:‘掉头一去是风吹黑发∕回首再来已雪满白头。’长江断奶之痛,历四十三年。洪水成灾,却没有一滴溅到我唇上。这许多年来,我所以在诗中狂呼着、低呓着中国,无非是一念耿耿为自己喊魂。不然我真会魂飞魄散,被西潮淘空。”还说:“烧我成灰,我的汉魂唐魄仍然萦绕着那一片后土。”③在他的诗《当我死时》中有这样的诗句:“当我死时,葬我,在长江与黄河之间,枕我的头颅,白发盖着黑头。在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这些话可以作为“屋外在喊谁”的“互文”来读,也是《听雨》思想内核最好的解释。
古诗有云,“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陶渊明《归田园居》),说的是人的本土性。人的个体,只有生活在养育他的故土上,才能获得自然、习俗、文化、人格精神上的绝对自由。从理论上看,人的本土性,是人性中的至性之一;当一个人离开他的故土或祖国之后,就离开了养育他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就自然会产生漂泊感与孤独感,这就是“乡愁”。不过飘零台岛的余光中作为教授与作家,与一般人比较,与一些漂泊海外的同胞作家相比,却又表现得很另类。他不仅强烈地依念他的故土,而且很执着地依恋祖国的文化传统与人文精神;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乡愁”不是逐渐淡薄而是与日俱增,故而“一念耿耿为自己喊魂”。唯其如此,这篇散文里作者所表现出来的“乡愁”就格外强烈。归根结蒂,他在“听听那冷雨”的情感宣泄之中,虽然凄迷、忧伤、哀痛,然而流动着的却是“汉魂唐骨”的爱国主义的音色情采。
余光中是由写诗转向散文的,把诗的思维、诗的灵感、诗的手法带到散文中来,就形成了他散文中的诗的艺术元素。这篇散文是诗性的。诗性首先表现在借鉴蒋捷《虞美人·听雨》与戴望舒《雨巷》的意境,并且通过自己的创造,用雨巷“听雨”的浮想联翩,把游子的痴心“乡愁”淋漓尽致地抒发出来,这是诗的构思与诗的概括。其次,如前所述,作者用诗人“冷雨”的感觉思维,并通过联想和想象写自己在不同的时间与空间里诗心的跳动;同时,叙事、写景、议论、抒情,都是“冷雨”的心理感觉,从头至尾、浑然一体地融成凄迷伤感的情调,因而更有浓郁的抒情色彩。笔者在《余光中“新散文”的审美理想及其价值》一文中说过这样的观点,他用“剪掉散文的辫子”的革命理论,身体力行到自己的散文创作,于是其散文就无疑充满了“革命”的色彩。“中、西艺术表现形式的会通和整合,使其文本具有古典主义和现代主义的色彩。举个例子,如《听听那冷雨》借鉴融会了宋末元初蒋捷的词《虞美人·少年听雨在楼上》和戴望舒的诗《雨巷》之意境,并且用情景交融的传统手法以及常见的叙事方式,来曲曲折折地抒写作者的‘乡愁’,这是中国的古典色彩。同时,作者又用‘现代派’的感觉思维和感觉语言的色调,动情地描述用生命‘听雨’的种种微妙感觉,这是外国‘现代主义’的作风。两者的整合,成为一个中西色彩兼容的典型文本。”④
《听雨》的诗性,更多地表现在作品的语言方面。作者在《剪掉散文的辫子》一文中提出创造一种“现代散文”的新文体,并且提出“弹性”、“密度”、“质料”三个审美标准,其中“质料”是对散文语言的要求。“它是指构成全篇散文的个别的字或词的品质。这种品质几乎在先天上就决定了一篇散文的趣味或境界的高低。”⑤可以说,他在《听雨》中进行了语言“质料”的实验,由于这种实验而使这篇作品具有了诗性的品质。具体说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隐秀地运用典故。全文三十多处用了典故,其中大多数暗将古代诗文的词和句活用,隐秀地在描叙之中,既不注明出处,又不加引号表明。例如:“回到台北,世人问起,除了笑而不答心自闲,故作神秘之外,实际的印象,也无非山在虚无之间罢了。云雾缭绕,山隐水迢的中国风景……”这段话中间分别活用了三位诗人的诗句:李白的“笑而不答心自闲”(《山中问答》“问余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白居易的“山在虚无缥缈间”(《长恨歌》“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渺间”)、杜牧的“青山隐隐水迢迢”(《寄扬州韩绰判官》“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活用典故,赋予作品的语言以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儒雅的韵味,这给读者预留了丰富的审美空间。第二,灵活地运用欧化句式。如:“雨在他的伞上这城市百万人的伞上雨衣上屋上天线上,雨下在基隆港在防波堤在海峡的船上,清明这季雨。”“雨……也下在四川的秧田和蛙塘,下肥了嘉陵江下湿了布谷咕咕的啼声。雨是潮潮润润的音乐下在渴望的唇上舐舐那冷雨。”这样的欧化或准欧化的句式,时而在作品中出现,是为了强调诗情的激情荡漾或者曲衷缠绵,有如京剧的拖腔,使情绪的抒写烘托得格外充沛与饱满。第三,叠词的大量运用。如文章开头:“……先是料料峭峭,继而雨季开始,时而淋淋漓漓,时而淅淅沥沥,天潮潮,地湿湿,即连在梦里,也似乎把伞撑着。”五处叠词形象地描述着春雨的“绵绵”,烘托着作者“乡愁”的缘起。如写听“暴雨”:“滔天的暴雨滂滂沛沛扑来,强劲的电琵琶忐忐忑忑忐忐忑忑,弹动屋瓦的惊悸腾腾欲掀起。”这里三处用叠词,把听暴雨的感觉写得逼真细腻,把内心的凄楚也烘托得恰如其分。大量叠词在《听雨》中很好地起到描述感觉、暗示心绪、整合语言音乐性的作用。正如方忠教授所说:通过语言的创造,“由少年听雨到中年听雨,诸种感受、万般情调融汇在一起,构成了立体的关于雨的交响曲。”⑥
总之,运用典故、运用欧化句式、多用叠词,为《听雨》增添了诗性,这是余光中在语言上与一般散文家殊异的作风。细细体味,表现了作者幽默的机智,从中可以体味作者一贯的幽默风格。不过这篇散文因写“乡愁”,所表现出来的只是淡淡的幽默。从上述语言实验的三个方面,我们可以管窥余光中散文语言个性风格之一斑。
注释:
①曹惠民:《台港澳文学教程》,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0年,第77-78页。
②③余光中:《从母亲到外遇》,《人生与舞台》,1998年8月。
④张王飞、林道立、吴周文:《余光中“新散文”的审美理想及其价值》,《当代作家评论》,2011年第3期,第43页。
⑤余光中:《剪掉散文的辫子》,《余光中散文精品选》,山东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9页。
⑥方忠:《台湾散文纵横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