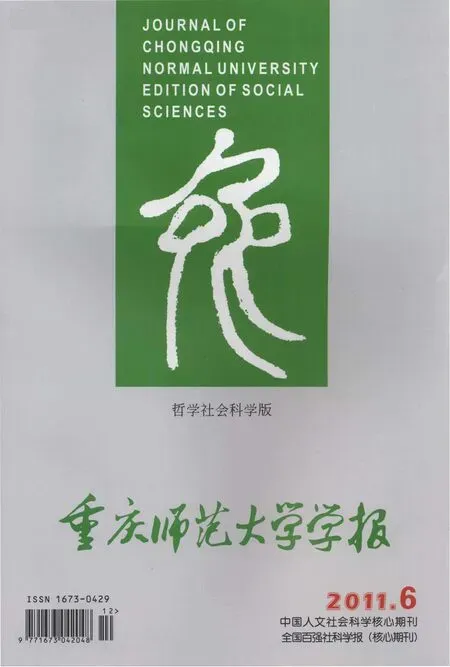乾隆中后期清政府对“啯噜”的严厉镇压与社会恐慌
龚义龙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重庆 400015)
乾隆中后期清政府对“啯噜”的严厉镇压与社会恐慌
龚义龙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重庆 400015)
乾隆中后期,四川及其周边地区“啯噜”活动频繁,已经严重地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清政府下决心铲除“啯噜”这一黑社会组织。但是,清政府面对着这一困境:将真正的“啯噜”与被怀疑为“啯噜”者、被裹胁入“啯噜”者区别开来,以打击真正的“啯噜”,而不致造成大的社会恐慌。而事实上,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这几乎是办不到的。“啯噜”镇压活动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社会恐慌,后果很严重。
乾隆中后期;清政府;“啯噜”;严厉镇压;社会恐慌
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者们对清代巴蜀“啯噜”及相关问题已经作了比较广泛的研究。拙文将既有学术探讨概括为哥老会与“啯噜”的渊源、“啯噜”的起源与发展、“啯噜”的性质与基本群众等几个方面。在既有研究基础上,本人曾对“啯噜”的基本群众、“啯噜”的日常活动、“啯噜”产生的社会根源作过一些学术探讨。[1]随着对《清代巴县档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三省边防备览》深入研究,本人对清代巴蜀“啯噜”的认识进一步加深,拟在此对乾隆中后期清政府对“啯噜”严厉镇压及其带来的社会恐慌进行分析。
“啯噜”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社会边缘群体”,因此,在“社会边缘群体”(包括窃贼、乞丐、川江水手等)数量庞大的清代巴蜀,要想铲除作为黑社会组织性质的“啯噜”,势必会牵涉到被怀疑为“啯噜”者、被裹挟入“啯噜”者,进而造成较大的社会恐慌。
在清代巴蜀“啯噜”这一社会群体中,真正的“啯噜”无疑具有黑社会性质。不管是从扰乱正常的社会秩序,从而对清朝统治构成间接的威胁,还是其活动的直接目的就是颠覆大清政权,依据《大清律例》,这部分“啯噜”都该遭到镇压。但是,被官府认为具有“啯噜”嫌疑的,还有诱赌、哄骗的川江水手,形迹可疑、行色匆匆的过路人,乃至小偷小摸的乞丐。而成群结伙的“啯噜”中,还裹胁有乞丐、水手及其他失业者,这就使得“啯噜”这个社会群体的成份变得十分复杂。
然而,“啯噜”这一“社会边缘群体”从最初三五成群,发展成为有组织的匪徒,经历了一个过程。清政府对“啯噜”的认识,以及对“啯噜”的政策变化也相应地发生着变化。
一、清政府对“啯噜”的最初认识
虽然在雍正年间、乾隆初年,“啯噜”活动已成为危害多省的社会问题,但是,直到乾隆四十六年(1781),深居宫闱的乾隆皇帝,以及“啯噜”活动频繁地区(包括湖广、贵州、四川、陕西等省)的封疆大吏,对“啯噜”的认识仍然表现得懵懂无知。该年7月7日乾隆皇帝发出上谕:“此等匪徒,聚集多人,抢劫拒捕,甚属可恶,断不可不尽法处治。著再传谕各督抚加紧搜捕,并遵照前奉谕旨,将拿获各犯严刑讯问,其因何聚集?所谋何事?”[2]7月14日,湖广总督舒常奏折也附和着乾隆皇帝的困惑:“‘啯匪’来历为何?因何聚集?意欲何为?”[3]
当然,这并不是说清廷朝野对“啯噜”的认识尽皆如此颟顸。事实上,有些人对“啯噜”还是早有认识的。
乾隆三年(1738),李厚望调任重庆已经接触“啯噜”案件。先是,四川有“啯噜”者,皆流民恶少,强悍嗜斗,动成大狱,而重庆为甚,积案几当通省之半。厚望至,阅其牍,叹曰“此皆无知犯法者也”。于是,“核其殴抵者上之,得省释者数百人”。[4]
乾隆八年(1743)10月,四川巡抚纪山奏称:“川省数年来,有湖广、江西、陕西、广东等省外来无业之人,学习拳棒,并能符水架刑,勾引本省不肖奸棍,三五成群,身佩凶刀,肆行乡镇,号曰‘啯噜子’。”[5]
乾隆九年(1744),御史柴潮生奏称:“四川一省,人稀地广,近年以来,四方游民多入川觅食,始则力田就佃,无异土居,后则累百盈千,浸成游手。其中有等,桀黠强悍者,俨然为流民渠帅,土语号为‘啯噜’,其下流民听其指使,凡为‘啯噜’者,又各联声势,相互应援。”[6]
这就是说,早在乾隆初年,重庆府官员李厚望已处理了大量“啯噜”案,四川巡抚纪山、御史柴潮生等也先后上奏,指出“啯噜”的基本来源正是数年来“湖广、江西、陕西、广东等省外来无业之人”。这些人又“勾引本省不肖奸棍”。最初,这些人“力田就佃,无异土居”,后来“累百盈千,浸成游手”,“学习拳棍,并能符水架刑”,“三五成群,身佩凶刀,肆行乡镇”,“桀黠强悍者,俨然为流民渠帅”,而其下流民听其指使。各股“啯噜”之间相互联络,壮大声势。显然,“啯噜”的所作所为已经严重扰乱了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但此时,官府仍然将“啯噜”案作为一般案件对待。
二、乾隆中后期清政府加大对“啯噜”追剿的力度
乾隆中期发生了几个震惊朝野的事件,乾隆三十六年(1771)山东王伦起义、乾隆三十三年(1768)“叫魂”案、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甘肃“苏四十三”起义。这些使得乾隆皇帝的神经绷得更紧。历次上谕透露出,乾隆皇帝与封疆大吏们似乎已经开始怀疑“啯噜”具有颠覆大清政权的性质,因而对“啯噜”追剿的力度明显加大。
乾隆四十六年(1781)7月30日,四川提督成德奏折指出,若任“啯噜”猖獗下去,恐怕会酿成王伦、苏四十三之祸。成德奏道:“匪徒敢于百十成群到处抢劫拒捕,若不即行擒获,尽绝根株,即可酿成王伦、苏四十三之事。窃查川省啯匪多系各处无籍游民,素无恒业,向来不过同伙三五人各处游荡,或于偏僻乡村临时行强抢劫行旅,一有禀报即严拿究惩,今竟敢百十成群,到处抢劫拒捕,实属罪大恶极。”[7]鉴于“啯噜”活动可能引起较大范围的社会骚乱,清政府对“啯噜”采取了严厉追剿的措施。
乾隆中后期,各级官府屡次发出严查“啯噜”的“安民告示”。这表明,乾隆四十六年(1781)前后,“啯噜”这个社会群体已成为中国社会一个严重的祸患,令清政府及老百姓大伤脑筋。
乾隆四十二年(1777)4月《重庆府下行各县牌文》曰:“案奉臬宪檄发查拿啯匪告示,当经本府照样刊刻板片,檄饬各属经书赴辕请领印发在案。”[8](105)乾隆四十七年(1782)又颁布《从重惩治川省啯匪专条》,《专条》称:“四川地广民稀,山路僻远,最易藏奸。各处无籍游民,蚁聚乌合,结伙成群,久为商旅地方之大害。是以另立川省啯匪专条,从重惩治。”[8](106)
据此,乾隆四十七年(1782)3月15日,巴县颁布《严惩啯匪新例》。《新例》称:“照得士农工商,各有恒业,医卜星相,并可营生。此外,或樵或采,或雇或佣,皆堪自食其力,不致坐困饥寒。即或命之不辰,穷饿而死,当属清白良民,得以保全首领,何苦丧心易志,竟为啯匪,抢夺伤人,身负大恶之名,死作无头之鬼。……为此,示仰县属居民人等知悉。嗣后咸宜恪遵法纪,各守恒业,宁使饥寒迫身,切不可流入匪类。所有奉到新例列后。计开:一、川省啯匪在旷野拦抢,未经伤人之案,除数在三人以下者,发烟瘴充军。一、四人以上至九人者,不分首从,俱改发伊犁,给厄鲁特为奴,均面剌‘外遣’二字。如有脱逃,拿获即行正法。但伤人者,即将伤人之犯拟绞监候,入于秋审情实。一、数至十人以上,无论伤人与否,为首拟斩立决,为纵拟绞监候,仍入秋审情实。被胁同行者,发遣为奴。其中倘有杀人夺犯伤差等事,有一人于此,即照场市抢劫之例,将首伙各犯,分别斩枭绞决监候。”[8](107-108)
清朝各级官府的“劝告”不可谓不是苦口婆心,“惩治条例”不可谓不严厉,却还是有人铤而走险,流为“啯噜”。这说明,根治“啯噜”仅仅停留在劝谕层面难以达到预期效果。为此,在颁布“惩治条例”的同时,清政府在湖南、湖北、贵州、四川、陕西等省开始了对“啯噜”更严酷的追剿。但是,要剿灭行踪不定、跪谲多端、为害多省的“啯噜”谈何容易!
乾隆四十六年(1781)8月9日,四川总督文绶即指出,要剿灭“啯噜”存在着很大的难度,“川省啯匪到处游荡,乘间抢劫,其踪迹本无一定,此处查拿则逃往彼处,非止重庆、夔州地方为然”。“啯噜”“白日绺窃为红线,黑夜偷窃为黑线,此皆匪类之市语。其首伙、名姓、排行率皆变易无常,即同时同案之犯,所供本伙姓名、籍贯亦各不相同,且有一人数名,皆非真名实姓,并拿获到案又另捏供姓名者,必彼此质认始知某甲即系某乙,总属鬼蜮伎俩”。[9]到处游荡,踪迹无定,白日绺窃,黑夜偷窃,这是查拿“啯噜”的一大难题。而“啯噜”的成员不用真实姓名,或一个人用数个名字,也使得缉捕不易。
更为重要的是,“啯噜”动辄“聚至百人之多,执持器械,拒伤兵役,且携带鸟枪、军器”[10](26)。“啯噜”已经成为一股股有组织的武装团伙,剿灭这些为害多端的“啯噜”实为十分困难的事情。更何况,“啯噜”始则结伙行强,继而闻拿四散,或伪装为水手,推桡寄食,或化为乞丐,沿途行乞,计图漏网。[11]
另文有述,每一伙“啯噜”或纠结一处,或将乞丐、稚童之类也卷入团伙,更是加大了剿灭和区分“啯噜”的难度。文绶即称,“啯噜”若在“沿途遇有匪类,即渐相纠结,并诱胁乞丐、童稚一路随行,希图人众难拿,逃往外省躲避,或散入各川佣工,及沿途兵役截拿急迫,复力拒图脱”。“现在严讯已获各犯,均供实因四处截捕严拿,窜避山林,沿途遇有匪类,即渐相纠结,并诱胁乞丐、童稚一路随行,希图人众难拿,逃往外省躲避,或散入各川佣工,及沿途兵役截拿急迫,复力拒图脱”。[12]
剿灭“啯噜”的难度越大,“啯噜”的社会危害越大,清政府越是急于将之剿灭。文绶的奏折、乾隆的谕旨似乎都表明了对“啯噜”应“务求根诛,永绝后患”。文绶奏称:“川省无籍游民平日不务生计,每多抢窃之事。自军需竣后(按指大小金川之役结束后),外省无业之人充夫觅食者亦多,当经分别编查押逐。其为匪犯案者,俱随时严拿获究。自乾隆四十一年(1776)至乾隆四十五年(1780),办获抢夺劫窃及拒捕伤人等案,计题咨枭斩绞决发遣各犯,每年一百数十名至二百数十名不等。近以梁山、垫江等县各报有抢夺刃伤事主、乡保之案,臣以啯匪党类本多,流害靡已,必须搜捕净尽,大加惩创,方可永除扰害。”[12](32)乾隆谕旨,“湖广、贵州各省若不特派大员专司擒捕,不足以专责成”,即派湖广提督李国梁挑选本标精兵壮丁300名,先由湖北至湖南、贵州一带,会同各该督抚实力搜捕净尽,毋使一名漏网。若此三省,目今已无贼匪,则竟往四川交界处会同文绶将川省啯匪一体搜捕净尽。李国梁接旨,与参将蔡鹏、守备李麟勋各带兵丁100名,分三路擒捕啯噜,一由湖南永绥各地方,无论城市荒村、丛箐峻岭之处,密行沿途搜捕;一由湖南属之澧州、湖北属之宜都、宜昌前赴施南一带地方督率搜捕,与四川督臣文绶商办督捕,务期净尽。[13](24)
三、严厉镇压与社会恐慌
事实上,乾隆中期,“啯噜”已成为有组织的团伙,其活动地点不一,各自的头目、成员各异,故而难以将某一股“啯噜”活动的来龙去脉弄清楚,我们只能将官府对“啯噜”搜捕、严惩,“啯噜”对抗、逃窜的一般情形展示出来。
在大江渡口拦截,交界地方设卡堵擒,在各地四处搜捕,成为清政府缉拿“啯噜”的重要方式。四川总督文绶即令在各大江渡口拦截,各交界地方设卡堵擒,又令在巴县、长寿、垫江、梁山、合州、大竹等地四处搜捕。最后在合州等处生擒“啯噜”一百余名(一次擒获80余名,一次擒获23名)。[14]
但是,在官府强有力追捕之下,“啯噜”往往窜逃于各省之间,这就增加了追剿的难度。为此,乾隆皇帝下旨各省会合追捕,并力搜剿。7月9日刘墉奏称,“川黔二省会合追捕,并力搜捕,以净余孽。即使湘与川黔接壤各处并无‘啯噜’踪迹,仍然要严密防范截拿,不敢少懈”。[15]由于各省会同追剿,“啯噜”日有报获。仍咨会各邻省交界一体防范盘缉,不难悉就歼除。7月24日四川总督文绶奏称,已获匪犯业有80余名。[16]尽管川省缉拿颇有成效,但在强有力的打击之下,“啯噜”纷纷逃逸川省,窜入别省。一方面,乾隆皇帝斥责文绶办事不力,另一方面严行申斥文绶亲身前往督率擒捕。同时谕令李国梁带兵先由湖北至湖南、贵州一带搜捕,如三省已无贼匪,即往四川交界处所,将四川“啯匪”搜捕净尽。[17]
当然,有些“啯噜”并不逃出川省,而是在当地高山密林处就近藏身。针对这种情况,追剿的官兵就需要深入各山林箐搜查、歼捕“啯噜”。[16]
在强有力的追剿之下,被打散的“啯噜”可能混迹于各厂做工,或混迹于水手、乞丐之中,或被乡村农户雇为佣工。为防止“啯噜”漏网,官府严饬所属多派兵役,于山僻村庄、水陆要隘搜查截捕,并饬各该厂员将各厂砂丁、背夫新来面生可疑之人,及重庆、夔州船行关口经过官商船只桡夫严加盘查。其各乡村收割雇工,向本有荐引保人及自备之镰刀、扁担等物可以查察,令地方官严饬乡保实力稽查。又,匪党中查有家室亲属者,恐其潜回藏隐,亦责成原籍地方官及保邻人等严密搜擒,不使混匿。采取这项措施,成效显著。7月27日文绶奏称,先后拿获“啯噜”90余名。[18]
对于“啯噜”的惩治,依照《大清律例》,不分首从,凡帮同拒捕之人,一面正法,一面奏闻,即并拒捕而随行为匪者,亦当发伊犁给厄鲁特为奴。本着这一原则,清政府对捕获的“啯噜”进行了严厉惩治。据8月25日、9月7日,舒常奏折,“啯噜”头目彭家桂、傅开太、吴荣三犯被处决枭示,王兴国、皮麻子被发给伊犁给厄鲁特为奴。[11]据7月5日、8月4日文绶奏折,胡范年等9犯分别枭示正法。首犯刘胡子、廖猪贩子、朱大汉以及同伙张小满速办示众。[19]据8月9日文绶奏折,经严督搜捕,擒获121名,其中,刘胡子即刘绣、廖猪贩子即廖荣系拿获各“啯匪”供出之首犯,还有凶犯江老七等20名,俱在梁山、垫江一带拿获。当将刘胡子即刘绣、廖猪贩子即廖荣二犯凌迟处死,仍枭首遍传各处示众。[20]据8月25日、9月7日舒常奏折,将严正纲、张和尚处决枭示,叶士明、李宏春、邹开太,虽属被胁随行,止于背包,匪徒抢劫时并未动手助势,但既入匪党,亦难轻纵,应发遣伊犁给厄鲁特为奴,照例刺字。[11]据10月22日舒常奏折,朱玉、孙达包子一伙随同已经正法之王三豹帮抢分赃,实属同恶相济,将二犯处决枭示。刘添贵、王文凤、匡阳泰三犯,虽被胁从,为日无几,并未助阵分赃,但既入匪党,亦难轻宥,应发伊犁给厄鲁特为奴。至王大富并非黄大富,张元保并非“啯噜”。李老七、吴魁应一并递籍安插。周潮盈随同拒捕各匪,助势分赃,实属同恶相济,拟将周潮盈处决枭示;刘玉彩、王成忠、胡添才虽被胁从,并没有助势分赃,但既入匪党,亦难轻宥,应发伊犁给厄鲁特为奴。张守仁虽非“啯噜”,而行窃多案,仍归案严办;至双瞽之李宗瑶同何锦堂、胡大昌、杨又高、杨名高,被李维高挟嫌妄扳,应与向周潮盈口角成隙之邓成德概行省释。[21]从上述对各“啯噜”案犯的惩治可以看出,清政府对已危及政权稳定的“啯噜”采取了极其严酷的镇压措施,而且对于首犯、胁从者的惩治政策是有区别的。
由于官府的严厉镇压,辗转奔逃、分散藏匿成为“啯噜”首要的避难办法。7月9日,刘墉的一道奏折就指出,一伙“啯噜”由贵州仁怀窜回川省之江津、綦江边界地方,分散潜藏。[15]对于较为强势的“啯噜”股匪而言,甚至会私立棚头,拒捕伤差。匪首刘老十、毛老九等七八十人,因查拿紧急,由四川窜逃贵州、湖广,复回川境。其余窜入湖广、贵州者百余人及七八十人不等。私立棚头,拒捕伤差。[22]刘胡子、廖猪贩子供认,最初与胡范年等抢夺,并在合州拒捕,后因胡范年等逃散被获,该犯等复为首,结伙逃往太平,窜入楚、黔等省,沿途纠众,屡次抢夺拒捕,杀伤兵役。[20]
也有“啯噜”易名改装,行乞僻乡。赵得相一伙,除擒获及格杀外,其余匪徒零星逃逸,或潜匿山箐,或易名改装,求乞乡僻。[16]还有“啯噜”充夫混迹。文绶奏称,“啯噜”节经搜截擒获,已星散逃匿,续报盘获匪党,每止两三同逃,并无结聚抗拿之处。川省到处皆山林僻径,既易窜匿,又或冒入铜铅盐厂及官商船只,充夫混迹。目下山田稻田均获丰收,秋粮遍野,乡农雇人收割或借托佣工寄迹觅食,均未可知。至前此查拿各匪,由川省自东壤界逃往楚省,转入黔省,由川省东南界窜回,经官兵追截捕获,追至垫江县一带,沿途陆续逃散。[18]
综上所述,清政府对“啯噜”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过程,乾隆前期清政府对“啯噜”基本上是作为一般案件处理的,但是,在乾隆三十三年(1768)“叫魂”案、“王伦起义”、“苏四十三起义”等事件发生之后,清政府的神经绷得更紧。考虑到“啯噜”猖獗严重地扰乱了社会秩序,特别是担心“啯噜”活动会直接针对清政府的统治,乾隆中后期,清政府明显地加大了对“啯噜”追剿的力度。在清政府严酷的镇压之下,“啯噜”或者辗转奔逃,或者混迹于乞丐、水手之中,或者遁入厂矿、农户佣工,而清政府对“啯噜”务尽根诛的追剿,无疑会导致追剿范围扩大化,从而导致社会恐慌。
[1]龚义龙.清代巴蜀“啯噜”始源探析[J].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
[2]乾隆四十六年七月初七日著四川湖广等督抚迅速搜捕啯噜毋存姑息上谕[J].历史档案,1991,(1).
[3]乾隆四十六年七月十四日湖广总督舒常等为已将续获啯噜皮麻子等飞饬解省事奏片[J].历史档案,1991,(1).
[4]向楚等修纂.巴县志[Z].卷九.官师下.民国二十八年刻本.
[5]清高宗实录[Z].卷203.中华书局,1985.
[6]嘉庆十年三月二十九日四川总督勒保奏.录副奏折[Z].
[7]乾隆四十六年七月三十日四川提督成德为报赴川省搜缉邻水一带啯噜事奏折[J].历史档案,1991,(2).
[8]清代巴县档案汇编[Z].乾隆卷.档案出版社,1991.
[9]乾隆四十六年八月初九日四川总督文绶为报实力搜捕啯噜务期无枉无纵事奏片[J].历史档案,1991,(2).
[10]乾隆四十六年七月初三日湖南巡抚刘墉为啯噜进入贵州并湖南侦缉截拿事奏折[J].历史档案,1991,(1).
[11]乾隆四十六年八月二十五日湖广总督舒常等为报审讯续获啯噜严正纲等奏折.乾隆四十六年九月初七日湖广总督舒常为报审讯定拟所获啯噜严正纲等事奏折[J].历史档案,1991,(2).
[12]乾隆四十六年七月十六日四川总督文绶为报前后拿获啯噜并仍四路缉捕事奏折[J].历史档案,1991,(1).
[13]乾隆四十六年七月二十三日湖广提督李国梁为报钦奉上谕起程督捕啯噜事奏折[J].历史档案,1991,(2).
[14]乾隆四十六年八月初四日四川总督文绶为报擒获啯噜刘老十等并已抵川东督捕事奏折[J].历史档案,1991,(2);乾隆四十六年七月五日四川总督文绶为报追捕啯噜并严办已获胡范年等事奏折[J].历史档案,1991,(1).
[15]乾隆四十六年七月九日湖南巡抚刘墉为复贵州拿获啯噜钟凤鸣并湖南虽无匪踪仍行严防事奏折[J].历史档案,1991,(1).
[16]乾隆四十六年七月二十四日四川总督文绶为报已将续获啯噜赵得相等处死事奏折[J].历史档案,1991,(2).
[17]乾隆四十六年七月二十七日湖广提督李国梁为报遵旨赴川省搜拿啯噜事奏折[J].历史档案,1991,(2).
[18]乾隆四十六年七月二十七日四川总督文绶为报严密搜捕川东啯噜事奏折[J].历史档案,1991,(2).
[19]乾隆四十六年八月初四日四川总督文绶为报擒获啯噜刘老十等并已抵川东督捕事奏折[J].历史档案,1991,(2);乾隆四十六年七月五日四川总督文绶为报追捕啯噜并严办已获胡范年等事奏折[J].历史档案,1991,(1).
[20]乾隆四十六年八月初九日四川总督文绶为复报先后拿获啯噜并饬各属文武查拿搜捕事奏折[J].历史档案,1991,(2).
[21]乾隆四十六年十月二十二日湖广总督舒常等为报审定拟办啯噜周朝盈等事奏折[J].历史档案,1991,(2).
[22]乾隆四十六年七月八日湖广总督舒常等为复严密擒拿川省啯噜事奏折[J].历史档案,1991,(1).
The Qing Government’Severe Suppression to“Guolu”and Social Panic in the Late Period of Emperor Qianlong
Gong Yilong
(China Three Gorges Museum,Chongqing400015,China)
In the late period of Emperor Qianlong,“Guolu”exercised actively in Sichuan and its surrounding areas,and it has seriously disturbed the normal social order,so the Qing government determined to eradicate“Guolu”-the triad society.However,the Qing government faced with the dilemma:in order to crack down on the real“Guolu”,without causing major social panic,the real“Guolu”,the suspected“Guolu”,and those who have been inducted into the“Guolu”should be distinguished.In fact,this was almost impossible to realize under the social conditions in the Qing dynasty.Severe repressing“Guolu”inevitable resulted in social panic,and the consequences would be severe.
in the late period of Emperor Qianlong;the Qing government“Guolu”;severe suppression; social panic
K24
A
1673-0429(2011)06-0082-05
2011-09-09
龚义龙(1968—),男,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博士。研究方向:区域社会经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