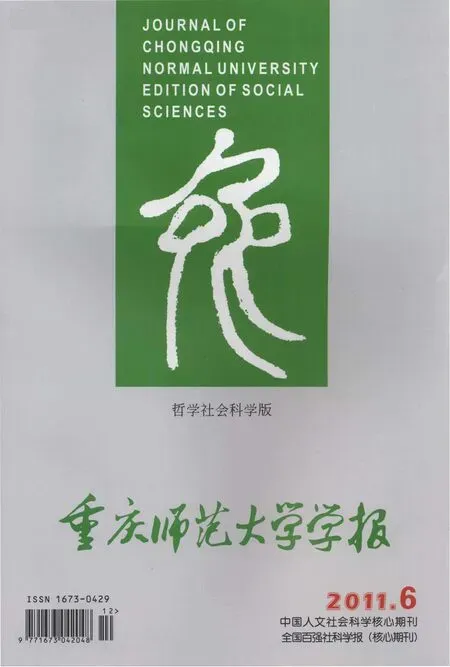论鲁迅的文学教育思想
周纪焕
(衢州学院 教师教育学院,浙江 衢州 324000)
论鲁迅的文学教育思想
周纪焕
(衢州学院 教师教育学院,浙江 衢州 324000)
鲁迅先生的文学教育思想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和创造性。他从文学具有“不用之用”的功能和形象直观的特点出发,将自己丰富的创作经验融汇于文学教育之中,坚持“教复非常教”的文学教学原则,开创了课内与课外相结合、阅读与写作相结合、教学与创作相结合的大文学教育实践之路,对有效推进今天的文学教育有着极大的现实意义。
鲁迅;文学教育;不用之用;教复非常教;实践路径
鲁迅是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教育家。鲁迅的文学教育思想是他在长期的文学教育实践中,以“启蒙”的文学创作思想为核心,充分认识到文学与教育的特点,并加以渗透、整合而形成的文学教育实践观,着重凸现于“不用之用”的文学功能观、“教复非常教”的文学教学原则和丰富多彩、成效良好的实践路径。这是文学教育的“鲁迅模式”,具有鲜明的个性、创造性和重要的当代价值。
一、“不用之用”的文学功能观
鲁迅先生高度重视文学教育,认为文学具有“不用之用”的社会功能、教育功能、审美功能和文化功能。这个观点最早见于他写于1907年的《摩罗诗力说》。鲁迅所谓“不用之用”有三层基本含义:一是文学在物质层面上不具有人之生存所需的诸如衣食住行上的实用价值和国家存在、发展的经济价值,文学“与个人暨邦国之存,无所系属,实利离尽”;二是在个人发展上,其“经世致用”的功效不占优势,“其为效,益智不如史乘,诫人不如格言,致富不如工商,弋功名不如卒业之券”;三是在精神层面上又是“有用”的,它能“益神”、“涵养人之神思”,从这个意义上说,“文章之于人生,其为用决不次于衣食,宫室,宗教,道德”,这也正是文学“之职与用”。[1](348-349)
关于文学的功能,鲁迅先生在发表于1913年的《儗播布美术意见书》中有更全面、深刻的论述:“美术之目的,虽与道德不尽符,然其力足以渊邃人之性情,崇高人之好尚,亦可辅道德以为治。”[2](47)这里的“美术”,并非狭义上的绘画,相当于今天所说的文艺,是涵盖了文学的,“美术云者,即用思理以美化天物之谓”,“如雕塑,绘画,文章,建筑,音乐皆是也”。[2](46)不仅如此,文学的力量是可以穿越时空,“表见文化”,“亦即国魂之现象”的。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武功文教,与时间同其灰灭”,而民族文化精神的传承流布,“赖有美术为之保存”,并且“长留人世”,“得以永住”。与其他艺术样式相比较,“人文之留遗后世者,最有力莫如心声”。[1](341)心声指语言,这里指诗歌及其他文学创作。
那么,文学为何具有这样优越的功能呢?
鲁迅先生认为,人类具有“受”、“作”二性。就接受来说,面对“曙日出海,瑶草作华”这样美的事物,“若非白痴,莫不领会感动”,也就是说人都具有欣赏美的能力。人既然具有“领会感动”的机能,对于善于思考的“一二才士”来说,就能使美的事物“再现”,“以成新品”,[2](45)文学艺术的创作也就产生了。“诗人”是“撄人心者”,而“凡人之心,无不有诗,如诗人作诗,诗不为诗人独有,凡一读其诗,心即会解者,即无不自有诗人之诗”,因此读者之心与作者之心是相通的。即使一般的读者对生活有所感悟而“未能言”,也能借助“诗人为之语”,而“握拨一弹,心弦立应,其声澈于灵府,令有情皆举其首,如睹晓日,益为之美伟强力高尚发扬,而污浊之平和,以之将破”。[1](345-346)
正因为鲁迅先生对文学的功用和机制有这样深刻的认识,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上,他果敢地作出“弃医从文”的决定,举起“启蒙”的大旗,力行用文学来教育、改造国民。“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3]在日本留学期间,寻找同志积极创办《新生》,和弟弟周作人翻译《域外小说集》,“志在灌输俄罗斯、波兰等国之崇高的人道主义,以药我国人卑劣,阴险,自私等等龌龊心理”[4]。在创作上,则怀抱“启蒙主义”,以“‘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为旨归,取材上“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5]
二、“教复非常教”的文学教学原则
文学既有那么明确、重要的精神价值和文化价值,在实施文学教育的过程中,应坚持怎样的原则才能达到理想的目的呢?
文学具有直观、形象的特点。鲁迅说:“盖世界大文,无不能启人生之閟机,而直语其事实法则,为科学所不能言者。”[1](349)“文艺之所以为文艺,并不贵在教训,若把小说变成修身教科书,还说什么文艺。”[6]文学的这一特点,决定了学生阅读、欣赏文学作品的过程,就是对文学作品自主体验的过程,与作者的心灵直接交流、对话的过程。对于作品所蕴含的“微妙幽玄”的“人生之诚理”,则在自主体验的过程中,能“直解无所疑沮”,因而无需教师“假口于学子”,进行直接灌输和“教化”。为使人们更易于理解其中的道理,鲁迅以给从未见过冰的热带人讲冰为例,说费尽口舌给他讲其中的物理学道理,他还是不懂“水之能凝、冰之为冷”是怎么一回事,若“惟直示以冰,使之触之,则虽不言质力二性,而冰之为物,昭然在前,将直解无所凝沮”。[1](349)这种通过“直示”教学、通过手“触”的实践,使热带人增加对冰的感性认识的方法,与学生对文学的理解来说是相同的,就是通过“读”的积极体验和感悟抵达作品的内核,进而思想情感受到感染、熏陶、浸润,精神境界得到提升。“帷文章亦然,虽缕判条分,理密不如学术,而人生诚理,直笼其辞句中,使闻其声者,灵府朗然,与人生即会。”这样的效力,“有教示意”,有益于人生,“而其教复非常教(着重号为笔者所加),自觉勇猛发扬精进,彼实示之”。[1](349)由此可见,鲁迅先生主张文学教育要坚持“教复非常教”的教学原则,其实质就是要遵循文学的特点,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突出学生学习的自主性、能动性。
此外,坚持“教复非常教”的教学原则,还要解决好学生的阅读兴趣,也就是要注意文学作品的趣味性和娱乐性,使他们阅之“兴感怡悦”。“由纯文学上言之,则以一切美术之本质,皆在使观听之人,为之兴感怡悦。”[1](348)只有在审美的愉悦中,才能完全实现文学教育“不用之用”之目的。美是“凭直感底能力而被认识”的,“美底享乐的特殊性,即在那直接性,然而美底愉乐的根柢里,倘不伏着功用,那事物也就不见得美了”。[7]因此,鲁迅主张将“职业的读书”和“嗜好的读书”统一起来,不能只顾及职业的需要而丢弃个人的兴趣,这对青少年学生来说显得尤为重要。鲁迅说,为职业而读书是“带着苦痛的”、“勉勉强强的”,嗜好的读书是“出于自愿,全不勉强,离开了利害关系”,那就跟打牌一样,“天天打,夜夜打,有时公安局捉去了放出来之后还是打”。解决了阅读的“有趣”,不仅使读者“在每一叶每一叶里,都得着深厚的趣味”,而且“也可以扩大精神,增加知识,但这些倒都不计及,一计及,便等于意在赢钱的博徒了,这在博徒之中,也算是下品”。[8]文学对人的精神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在“有趣”的良性影响下,可以有效地构建文学教育的良好环境,促使学生持之以恒地自觉地去阅读,汲取精神养料,并在不断的积淀过程中提高文学的鉴赏力。如果“吾人乐于观诵”,则将“如游巨浸,前临渺茫,游泳既已,神质悉移”,[1](348)达到文学教育的理想效果。
当然,鲁迅所倡导的“嗜好的读书”,绝非追求媚俗、低俗、庸俗的感官刺激,而是将“娱乐”与“审美”联系起来,将审美渗透于娱乐中,是“寓教于乐”。鲁迅说文艺“本有之目的”在“与人以享乐”,而文艺的“真谛”,就必须在这种自觉接受的“享乐”中,“起国人之美感”。[2](46)据林冰骨回忆,鲁迅在北京教育部任职期间,针对在临时教育会议上主张删却美感教育的谬说,大加挞伐,视之如猪狗。“时本部召开的临时教育会议,竟有主张删却美感教育的谬说。鲁迅在日记中叹息地记着:‘此种豚犬,可怜!可怜!’那时蔡先生主张以美育教育培养公民道德的教育方针,鲁迅先生是极力赞助的,并代蔡先生拟草这方面的文件。”[9]
三、多管齐下的文学教育实践路径
鲁迅有着丰富的文学教育实践经验,课堂教学横跨中学和大学。鲁迅在教育部任职期间,于1920年8月至1926年8月,兼任北京大学及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2年改为北京师范大学)讲师,讲授小说史;1923年10月,兼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后改名为女子师范大学)及世界语专门学校讲师,开设小说史课;1924年,被女子师范大学聘为该校国文系教授;1925年9月至1926年5月,到中国大学讲课,任国文系小说学科讲师。此外,鲁迅于1925年8月至12月,到新成立的黎明中学讲课,担任高中主科小说教员;1925年9月至11月,又到大中中学讲课,任高中部新文化学科教员。1926年9月至12月,任厦门大学文科教授,讲授中国文学史和小说史。1927年1月至4月,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讲授文艺论、中国小说史、中国文学史三门课程。纵观鲁迅先生的一生,不论他选择怎样的方式,始终与文学教育相伴随,对我们今天开展文学教育以极大的启示。
1.课堂教学运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
如何发挥文学的“职与用”,将文学之直抵人心的力量有效地传达给学生,达到教育“立人”的目的,鲁迅是很有办法的。从曾是鲁迅先生在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的学生回忆看,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启发学生独立思考,是鲁迅先生赢得学生喜爱和尊敬,并创造出绝佳的教学效果的法宝。
著名语言文字学家、教育家魏建功先生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二年级时,选修了鲁迅先生的小说史课程。他说,鲁迅先生“讲课的时候并不是‘照本宣科’”,“我们那时候听先生讲课实在是在听先生对社会说话。先生的教学是最典范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他为着自己的理想,整个精神灌注在教育青年的事业上,我们就幸福地当面受到他伟大的思想教育”。[10]鲁迅北大时的学生,现代诗人、翻译家冯至也赞道:“那门课名义上是‘中国小说史’,实际讲的是对历史的观察,对社会的批判,对文艺理论的探索。有人听了一年课以后,第二年仍继续去听,一点也不觉得重复。”[11](331)据陆晶清回忆,鲁迅先生在女师大讲课时,“深入浅出地讲教材”,“联系实际,提出问题并引导学生思考、分析问题。每听鲁迅先生讲一次课后,我们都要议论、咀嚼多时”。[12]俞荻说,鲁迅在厦门大学讲学过程中,“讲到某时代的代表作家及其作品的时候,善于引证适当的、丰富的资料来详尽地加以分析,雄辩地加以批判,说明什么应当吸取,什么应当摒弃”[13]。“诗孩”孙席珍说,鲁迅“在业务上从不满足于单纯的传授知识,总是重在启发、引导,要大家进一步去挖掘、探索、钻研,以求有更多、更大的发明和发现;在思想上,他从不以大声疾呼为能事,总是着重在指明方向、道路,鼓励大家不断地向前迈进,促进和推动大家努力去破旧创新”[14](351)。由此可见,鲁迅先生遵循文学教育的规律,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坚持“教复非常教”的教学原则,深入学生的内心世界,彻底摒弃说教式的灌输,以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拉近了文学与生活、文学与学生间的距离,启发学生去独立思考。这样鲜活的、灵动的课堂教学深受学生欢迎,甚至吸引了非文学专业的学生蜂拥来旁听。“这本是国文系的课程,而坐在课堂里听讲的,不只是国文系的学生,别系的学生、校外的青年也不少,甚至还有从外地特地来的。”[11](331)“鲁迅先生讲课的教室里,历来总是挤得满满的,不但无一空位,还有人坐在窗台上,甚至有站着在那里听的。”[14](350)这样的盛况,确实令人叹为观止。
2.开辟文学教育的第二课堂
鲁迅先生对青年学生的巨大影响,不是每周2-3个课时的课堂教学时间所能盛载得下的。“我处常有学生来,也不大能看书。”[15](257)鲁迅将离开厦大到中大的消息,“搅动了空气不少,总有一二十个也要走的学生,他们或往广州,或向武昌,倘有二十余人,就是十分之一”[15](268),而鲁迅在厦大的时间仅有四个月,足见影响之大。“他们总是迷信我,真无法可想。”[15](257)这样,鲁迅先生的文学教育之路,也就由课内走向课外,对年轻人的需求,总是有求必应,应接不暇,为一批文学青年的健康成长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做出了特别的贡献。
鲁迅先生非常重视课堂教学的有机延伸,他凭借自己渊博的知识,为学生提供针对性很强的参考书目,指导学生阅读,以帮助学生进一步理解有关知识,提高他们的学习能力、鉴赏能力和研究能力。常惠说,有一次鲁迅先生同他谈话,他问鲁迅先生,《楚辞·天问》是一篇很新奇的文章,如果不看注释就无法看懂。鲁迅说《天问》注释的很多,看汉王逸注的就行了,但柳宗元的《天对》还是要看一看,而且要将《天问》和《天对》对着看,这样会更有趣,会有更大的收获。由于这篇文章在普通的柳宗元文集里没有,鲁迅就让常惠到宣武门外香炉营头条图书馆去借济美堂本的《柳河东集》,后来果然借到了。“由于鲁迅先生的指点,我们除了上课外,还读到一些参考书”,“鲁迅先生讲完一学期的课程,就给同学们提出参考书,有《太平广记》、《小说考证》、《小说考证续编》及拾遗等”。[16]
为了回报青年学生的巨大热情,鲁迅先生设法创造条件在课外给他们答疑。尚钺说,鲁迅在北大上课时,经常提前半小时就坐在休息室中为学生释疑解难,但只要他一来,“许多早己在等候他的青年,便立刻把他包围起来。于是他便打开手巾包将许多请校阅,批评及指示的稿件拿出来,一面仔细地讲解着,散发着,一面又接收着新的”。这些学生也善于见缝插针,“先生每次下课时,许多同学都挤着跟他到休息室去发问,甚至一连几个礼拜我的一个问题还没有挤到他面前去求得解答的机会”。[17]
鲁迅先生一向注重文学青年的培养和扶持,随时注意发现新人。汪静之还是一个中学生时,就寄诗向他请教。“他认为孺子可教,就诲人不倦地指导我,仔细替我改诗,精心培植刚吐尖的萌芽。”[18]李霁野说,鲁迅先生对于青年人态度诚恳,“不会笑年青人幼稚”,在收到他的一篇小说《生活》时立即回答:“我略改了几个字,都是无关紧要的。可是,结末一句说:这喊声里似乎有着双关的意义。我以为这‘双关’二字,将全篇的意义说得太清楚了,所有蕴蓄,有被其打破之虑。我想将它改作‘含着别样’或‘含着几样’,后一个比较的好,但也总不觉得恰好。这一点关系较大些,所以要问问你的意思,以为怎样?”[19](105)鲁迅先生对于一个初学写作的人既悉心呵护,又细心周到地加以指导,实在令人感动。更难能可贵的是,鲁迅先生常常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甚至牺牲自己的健康,给青年学生改稿、校对、指导,如曾连夜伏案校对高长虹的稿子,累得“吐了血”[19](107)。鲁迅先生就是这样一个对青年人充满热情、乐于付出的长者,“他喜欢青年,不论认识不认识,写信去请教他,没有不详详细细回复的,他每星期的光阴,用在写回信大约有两天”[20]。
对于学生文学刊物的创办,鲁迅则视为自己的分内之事,十分热情地加以指导,扶持他们健康成长。陈炜谟、冯至、陈翔鹤等“沉钟社”成员经常到鲁迅先生北京的寓所讨教。“鲁迅先生对于我们的刊物很热心扶助,他是每期必读,而且还随时奖掖。鲁迅先生所编选的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沉钟社诸友的作品,几乎要占去一半的篇幅。他甚至还称道沉钟社是‘中国的最坚韧,最诚实,挣扎得最久的团体’。”[21]在厦大时,鲁迅支持并帮助文学青年先后成立了“泱泱社”和“鼓浪社”,并为这两个文学社团创办的《波艇》月刊和《鼓浪》周刊亲自撰稿、审稿、改稿并指导编印。“此地的几个学生,已组织了一种出版物,叫作‘波艇’,要我看稿,已经看了一期,自然是幼稚,但为鼓动空气计,所以仍然怂恿他们出版。”[15](160)
广泛地发表讲演,是鲁迅开展文学教育的又一有效方式。在广州期间,鲁迅先后应邀在中山大学、岭南大学、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广州知用中学及香港等地演讲,阐述其文学观点,号召人们向封建主义开战,创造了文学教育的辉煌一页。放弃教职之后,鲁迅的内心深处始终眷顾着教育事业,继续借到大中学校讲演等方式来和青年朋友交流。1929年5月北上省亲之时,应燕京大学、北京大学、第二师范学院、第一师范学院等院校之邀广为演讲。1932年11月,鲁迅从上海去北平探望母病,仍应邀赴各大学作了著名的“北平五讲”。这些演讲,从题目来看,如《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遵命文学与革命文学》,实质是新的文学观的启蒙,新的思想观的启蒙,意在引导青年学生与黑暗的社会现实进行不懈的斗争,是其教育情结的继续,是文学教育的继续。
3.坚持创作以发挥文学教育的更大影响
鲁迅先生在教学和写作间两头忙碌,深感难以兼顾。对此,鲁迅先生有着深刻的认识和精辟的论述。他说,作文章与教书这两件事“是势不两立的”,因为“作文要热情,教书要冷静。兼做两样时,倘不认真,便两面都油滑浅薄,倘都认真,则一时使热血沸腾,一时使心平气和,精神便不胜困惫,结果也还是两面不讨好。看外国,做教授的文学家,是从来很少有的[15](169)。”“我觉得教书和创作,是不能并立的,郭沫若郁达夫之不大有文章发表,其故盖亦由于此。”[15](228)
对于教学与创作性质不同、时间冲突所造成的顾此失彼的苦恼,现代文学史上的许多作家深有同感,最终放弃教职专心致志于创作。在老舍先生看来,在教书和写作两头奔波,一则影响身体健康,二则不利于创作。他在创作《骆驼祥子》之前,“总是以教书为正职,写作为副业……在学校开课的时候,我便专心教书,等到学校放寒暑假,我才从事写作。我不甚满意这个办法。因为它使我既不能专心一致的写作,而又终年无一日休息,有损于健康”[22]。1936年老舍辞职后,就创作了奠定他在现代文学史上崇高地位的的第一个长篇《骆驼样子》。郁达夫对此也有深切的体会,认为教书与创作是“绝对相克的”[23]。
基于这样的经验和认识,鲁迅本应放弃教学而专心创作,但在夏大、中大期间,他出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教学之余仍坚持文学创作,这实际上是其教育活动的有效延伸,通过手中的笔,扩大了对广大青年的教育影响。“为社会方面,则我想除教书外,或者仍然继续作文艺运动,或更好的工作。”[15](221)在厦大短短的一百三十多天时间里,鲁迅完成了《坟》、《华盖集续编》等几部书的编辑、校订工作,写下了十七万多字的作品,如《朝花夕拾》中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父亲的病》等。“四一二”事变后,鲁迅因营救被逮捕的进步学生的活动未能奏效而愤然辞职,实际在中山大学的时间并不长,但他一直到1927年9月27日才离开广州,前往上海。鲁迅在广州的八个月间,整理旧译作《小约翰》一部,旧作《野草》、《朝花夕拾》各一部,写下了杂文43篇、译文10篇、书信180封。鲁迅居住上海的十年间,除了应劳动大学校长易培基之邀在1927年11月初短暂地担任每周两小时的“文学讲座”外,[24]再也没有重执教鞭,而专心于他所热爱的文艺运动。期间,鲁迅于1929年5月、1932年11月两次赴京省亲,对一拨拨学生请求他去教书,则坚决谢绝。“今天上午,来了六个北大国文系的代表,要我去教书,我即谢绝了。”[15](298)“傍晚往未名社闲谈,知道燕大学生又在运动我去教书,先令韦丛芜游说,我即拒绝。”[15](303)
尽管鲁迅先生在职业选择上最终放弃了课堂、放弃了教学,但这是服从于教育的需要、服从于斗争的需要而作出的可贵选择,从中可以看到鲁迅先生对中国文学教育所作出的特殊贡献。因此,彭定安先生所论是恰当的:鲁迅“到上海之后,十年定居,虽然不曾到大学任课,但是,办社团、领导左联、提倡木刻、与许多青年通讯以至讲演、写信,也都渗透着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精神,以伟大导师的精神品格,以文化大师的学问道德,培养了一代一代,各个方面的人才。这是一位教育家的实践历史”[25]。
鲁迅先生因为深刻地认识到文学的“不用之用”的特殊功能,自觉地拿起手中的笔去做唤醒民众的“启蒙”工作,又认识到文学具有形象直观的特点,实施文学教育时坚持“教复非常教”的原则,尊重学生的主体性,运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能动性,启发学生独立思考,开创了课内与课外相结合、阅读与写作相结合、教学与创作相结合的大文学教育之路,为今天文学教育的有效推进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
[1] 鲁迅.摩罗诗力说[A].鲁迅论创作[C].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
[2] 鲁迅.儗播布美术意见书·鲁迅全集(8)[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3] 鲁迅.《呐喊》自序[A].鲁迅论创作[C].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
[4] 钱玄同.我对周豫才(即鲁迅)君之追忆与略评[A].鲁迅回忆录·散篇(上)[Z].北京出版社.
[5] 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A].鲁迅论创作[C].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
[6]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9)[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7] 鲁迅.《艺术论》译本序·鲁迅全集(4)[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8] 鲁迅.读书杂谈——七月十六日在广州知用中学讲·鲁迅全集(3)[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9] 林冰骨.所记忆的四十五年前的鲁迅先生[A].鲁迅回忆录·散篇(上)[Z].北京出版社,1999.
[10] 魏建功.忆三十年代的鲁迅先生[A].鲁迅回忆录·散篇(上)[Z].北京出版社,1999.
[11] 冯至.笑谈虎尾记犹新[A].鲁迅回忆录·散篇(上)[Z].北京出版社,1999.
[12] 陆晶清.鲁迅先生在女师大[A].鲁迅回忆录·散篇(上)[Z].北京出版社,1999.
[13] 俞荻.回忆鲁迅先生在厦门大学[A].鲁迅回忆录·散篇(上)[Z].北京出版社,1999.
[14] 孙席珍.鲁迅先生怎样教导我们的[A].鲁迅回忆录·散篇(上)[Z].北京出版社,1999.
[15] 鲁迅,许广平.两地书·原信[Z].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
[16] 常惠.回忆鲁迅先生[A].鲁迅回忆录·散篇(上)[Z].北京出版社,1999.
[17] 尚钺.怀念鲁迅先生[A].鲁迅回忆录·散篇(上)[Z].北京出版社,1999.
[18] 汪静之.鲁迅——莳花的园丁——从鼓励写恋爱诗到劝止写恋爱诗[A].鲁迅回忆录·散篇(上)[Z].北京出版社,1999.
[19] 李霁野.忆鲁迅先生[A].鲁迅回忆录·散篇(上)[Z].北京出版社,1999.
[20] 许广平.青年人和鲁迅[A].鲁迅回忆录·专著(中)[Z].北京出版社,1999.
[21] 陈炜谟.我所知道的鲁迅先生——应川大暑期俱乐会之约讲[A].鲁迅回忆录·散篇(上)[Z].北京出版社,1999.
[22] 老舍.我怎样写《牛天赐传》·老舍文集(15)[M].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23] 郁达夫.著书与教书·郁达夫全集(7)[M].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
[24] 杜力夫.永不磨灭的印象[A]鲁迅回忆录·散篇(中)[Z].北京出版社,1999.
[25] 彭定安.序孙世哲著《鲁迅教育思想研究》[J].鲁迅研究月刊,1988,(02).
On Lu Xun’s Thought of Literary Education
Zhou Jihuan
(College of Teacher Education,Quzhou University,Zhejiang,Quzhou324000,China)
Lu Xun’s thought of literary education is distinctly practical and creative.He integrated his wealth of creative experience into the literary education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literary function of“using without purpose”and features of visual image.He adhered to the literature teaching principle of“the reeducation is to teach”.Moreover,he created a practical way of great literature by integrating curricular and extracurricular learning,reading and writing,teaching and creating,which has a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in effectively promoting today’s literature education.
Lu Xun;literary education;using without purpose;the re-education is to teach; practical way
I206
A
1673-0429(2011)06-0116-06
2011-09-29
周纪焕(1961—),男,浙江江山人,衢州学院教师教育学院教授,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