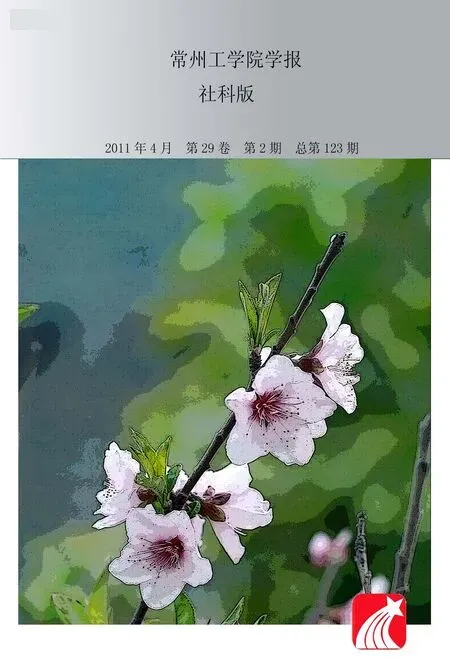自我价值的追求与幻灭
——论哈金小说《池塘》
李庆
(扬州大学文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2)
《池塘》是哈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虽然不像《等待》那样为大家耳熟能详,但它使哈金顺利走出了短篇小说的创作模式,为《等待》的成功奠定了基础,是哈金璀璨的创作生涯中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之一。《美国安魂曲》作者詹姆斯·卡罗尔评价说:“哈金的第一本长篇小说充分发挥了他在那些令人惊叹的短篇小说中所展现的才华——他在西方读者面前展开了一个真实的世界,而在他之前这个世界只不过在人们的想象和臆造中出现。哈金用他踏实的文笔、纯熟的人物塑造、机智,最重要的是用他的情感合理拆毁了文化的藩篱。作为读者只有感谢他。”①《池塘》中对主人公邵彬自我价值追求和幻灭的细致刻画是哈金式“伟大小说”的初探。
一、追求:孤独的反抗
故事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东北的一个叫歇马亭的偏远小镇,主人公邵彬是丰收化肥厂的一名钳工,妻子梅兰在百货商场上班,两人有一个可爱的女儿,日子看似红火,可幸福的背后却隐藏着一个心病——房子问题。两口子结婚后就住在梅兰单位分的宿舍中,只有一间房,本就狭小不堪,女儿出生后就更转不开了,梅兰每星期洗衣服要走七八里地,邵彬酷爱书法、画画,在这小房子里根本施展不开,全家最大的希望就是在“工人之村”拥有一套住房。恰逢丰收化肥厂分房子,邵彬几乎满足了分房的所有条件,可偏偏事与愿违,厂领导利用手中的特权将房子分给了比他晚三年进厂的侯尼娜。几次与厂领导交涉无果让邵彬怒火中烧,他利用自己在书画方面的才华,多次在报纸上发表漫画,甚至写申诉信上访,只是希望领导能明白他的难处,分到一处住房。可一次又一次的反抗,并没有改变邵彬艰难的处境,反而遭到厂领导一次更甚一次的严厉报复,最终落到被逼离开化肥厂、剥夺高考录取资格的境地。身处绝境的邵彬在报社同志的帮助下,只身来到北京,将自己的不幸遭遇刊登在《民主与法制》上,此举引起了金县领导的重视,邵彬终于得偿所愿离开了丰收化肥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故事结尾他仍然没能解决住房问题,全家还是挤在狭小的宿舍里。
(一)邵彬是一个孤独者
首先体现在他与环境的对立。故事一开始“邵彬在歇马亭已经住了六年多,从心里厌恶这个乡下小镇”②,他是一个十分擅长书法画画的知识分子,却在丰收化肥厂里当钳工,饱读诗书却无知音相伴,满腹才华无用武之地,生性傲慢加上郁结难抒使他不愿与“生存规则”同流合污。分房前,妻子梅兰曾嘱咐邵彬应该给领导送礼,可他却不愿意,认为厂里分房一向只依据实际需要和工龄长短,因此不需要花一分钱,结果可想而知。其次,他与集体对立。邵彬对分房不公的反抗,代表了大多数职工的心声,为何也会被孤立,其原因令人深思。起初邵彬登载漫画是受到工人们拥戴的,可随着反抗的升级、领导威逼利诱的加剧,曾经的工友表现出了对过分反抗的不理解,甚至为了保全自己的利益站到了对立面,咒骂邵彬是“疯子”,逼其不要再“疯”了。与领导的八次交锋,有六次是邵彬独自一人写信、上诉、承担后果,其他人不过是凑热闹、看笑话,摆出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姿态。在那个畸形的年代,人们往往习惯了忍耐和等待,习惯了以一个弱者的态度去面对一切,反抗者在他们眼中反而是“异类”,得不到拥护。邵彬是一个孤独者,他生性直爽,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他自负傲慢不愿与他人为伍,总是用自己的方式去争取想要的东西,他的孤独也注定了他的失败。
(二)邵彬是一个真正的反抗英雄
自从在《旅大日报》刊登了漫画后,邵彬的噩梦就开始了,扣发半年奖金,无故遭受毒打,众人面前被侮辱,做人的尊严和生存的希望消磨殆尽,可他仍“咬着牙发誓:我一定要住上好房子!他们一天不给我,我就一天不让他们安生”③。如此坚定的信念使他再次将矛头直指腐败官僚的要害。他把“杨晨一向迫害我”的标牌高举在县人民代表大学的礼堂上,将自己的不幸遭遇和腐败官僚的恶行公之于众,博得同情的同时又使杨晨声名扫地,成功让歇马亭“土皇帝”的升官梦化为泡影。一个小小的化肥厂钳工,一个典型的弱势人物,竟能对官僚这样的强势群体产生如此大的冲击,邵彬的反抗力量不可小看。噩梦很可怕,但伴随着噩梦而来的绝望更加可怕,邵彬时时都处于这样的极限境遇,他像极了“拜伦式的英雄”,坚持自己的理想永不放弃,即使路途过于艰难,环境过于恶劣,也不愿与丑恶为伍,高傲而倔强,孤独又忧郁。
孤独、反抗似乎是哈金笔下主人公们所共有的性格特征。反抗官僚主义的邵彬(《池塘》),等待真爱的孔琳(《等待》),坚持理想的杨教授(《疯狂》),追寻个人信仰的俞元(《战废品》),以及寻找自由生活的武男(《自由生活》),天生桀骜不驯的性格令他们无法与环境、集体相协调,他们都是孤独的反抗者。如此鲜明的共性与哈金本人的身份、经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哈金是一位美籍华裔作家,身份上属于两个国家,两种文化。近三十年的中国情缘割舍不掉,二十多年的美国生活又使他觉得“抵达比回归更为重要”④,“我觉得自己在文学上是个没有国家的人。美国看我是中国作家,中国看我是美国作家。我哪也不属于。”⑤游离于两种文化之间,立足于两种文化的边缘,希望通过第三国家少数族裔的“边缘”身份在美国主流文坛寻求一片天地,哈金及其主人公都注定是孤独的反抗者。
二、幻灭:自我的消失
歇马亭是个庞大的官僚系统,这里的生活充满着制约和束缚,令人窒息。邵彬的反抗意识一方面是性格使然,另一方面,环境亦是重要因素。邵彬的每一次斗争都是被逼迫的,都是外力作用的结果。他的结局也充满了悲剧意识,一个反抗官僚主义的叛逆者,最后竟沦为官僚主义的一员,昔日理想荡然无存,自我价值消失殆尽。正如书名《池塘》:这是一个充满污泥的地方,空气和水都弥漫着肮脏的气息,人只是其中的一条鱼,受尽支配和控制,无论怎样蹦达,都逃不出这池塘。
(一)被迫、无奈的反抗
邵彬只是化肥厂的一个小人物,没有地位,没有话语权,一切都受制于他人。他满腹经纶却做了钳工,他胸怀大志却无人问津,在浑浊的池塘里一沉默就是六年。然而他毕竟不是一条普通的鱼,注定要在池塘里掀起风浪,可这浪花却多为外力逼迫的结果。如果没有分房事件,邵彬也许永远只会做个沉默的小人物,如果刘恕和马宫没有咄咄逼人,他的反抗可能就不会那么坚决彻底。邵彬到《民主与法制》上访时,曾有这么一段话:“唉,生活咋就这么苦啊。只有一死才能脱离苦海。倒不是因为他怕死才活下来,而是老婆孩子还要靠他养活。活着更需要勇气。”⑥对邵彬而言,活着要受束缚,受压迫,活着没有选择,没有尊严,活着如身在炼狱一般煎熬难受。他之所以像蚂蚁一样卑微地活着,是因为世间还有割舍不掉的亲情和责任,为了亲人的安康和幸福,他只有鼓起勇气,放手一搏。
(二)斗争过程中的矛盾与彷徨
邵彬在与官僚势力作斗争的同时,内心也充满了害怕、不安和矛盾。当他把漫画投给《旅大日报》,领导大发雷霆而扣他半年奖金时,邵彬立刻后悔寄出那幅漫画,还责怪妻子为什么没有拦住他。当邵彬获得大学录取通知书时,他怕领导再一次暗箱操作,竟跑到马厂长家去陪笑脸、说好话,天真地认为领导会可怜他让他走。邵彬反抗的过程也是痛苦挣扎的过程,起初的目的只为缓解困境、争取权益,可是事情发展却完全相反,他被马宫、刘恕咒骂成神经病、疯子,他们在公开场合对他拳脚相向,在群众面前颠倒是非,使他身体上、精神上饱受折磨。邵彬每反抗一次,就受一次打击报复,并且愈演愈烈,本就艰难的境地没有得到一丝改善,反而雪上加霜,再无容身之地。
(三)自我价值的幻灭
邵彬是个有抱负的知识青年,他唾弃腐败的官僚制度,不愿为他们浪费一分钱,他对厂领导的反抗其实就是对整个官僚制度的反抗,可反抗是要付出代价的,邵彬在斗争、失败、彷徨、犹豫的过程中失去了自我,失去了昔日的追求与理想。邵彬当初的理想只是为分到一套房子,可随着事态的发展,他竟认为“房子只是身外物,不能看得太重”⑦,“正式转成了干部,房子总会有的”⑧,昔日的理想已荡然无存,反抗又有什么意义呢?故事最后,邵彬接受了杨书记的邀请,到公社负责宣传工作,一个一直与旧官僚体制作斗争的有为青年最终沦为了官僚体制的一员。新工作开始的第一天,邵彬犹如“南飞的大雁,快活得伸开了右胳膊,好像也长了翅膀”⑨。他仍然没有跳出这个池塘,曾经被他得罪的杨晨会轻易饶过他吗?他会如愿分到一套房子吗?就像是一出滑稽的悲喜剧,可笑之余也可怜主人公的悲剧人生。
说到悲剧,哈金笔下的主人公大多命运多舛。无论是走投无路的邵彬,等待十八年的孔琳(《等待》),还是陷入疯狂的杨教授(《疯狂》),他们的命运都具有悲剧性。为何哈金会如此钟情悲剧?首先,从移民经历来看,美国虽说是个包容性很强的国家,但排外思想一直没有完全摒除,一位华人想要在美国的大学从事教授一职难如登天,更何况是一文不名的哈金。初到美国,哈金看过大门,在餐馆打过工,生活很是艰难,好不容易找到教职工作却有着随时被踢走的危险,生活的艰难使哈金时刻保持着悲剧意识。在一次香港的演讲中,有位学生曾问过哈金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文学创作题材总陷入那么遥远的事情,为什么不能表现中国留学生留学生活的痛苦?”哈金答道:“海外留学生的痛苦,不是没有,但相比之下微不足道。”⑩对哈金而言,生活的痛苦大过一切,生活本就是一场悲剧。其次,从创作经历来看,哈金受俄国作家影响较多,这种影响是心灵的共鸣与震撼。《池塘》的首页就附着果戈理《死灵魂》中的一段话:“唉,说来说去,我仍然找不出一个有德行的君子作我的主人公。我的解释是这样的:有德之人已经变成了所有作家胯下的坐骑,被主人的皮鞭和顺手抄起的家什抽打。我现在觉得应该利用一个无赖。对,我们就应该骑骑他,兜上几个圈。”俄国作家带给哈金的是“生命的悲剧意识、悲悯和同情心”,“每部作品基本上都是一种失败,因为心里知道前人已经写过更好的了,很难超越。何况什么是成功?今天肯定是,明天就可能被否定。”悲剧意识时刻伴随着哈金,他的作品是在真实地表现生活,因为生活本就如此。
三、反思:对“池塘文化”的批判
一直以来,令哈金作品饱受争议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用英语书写中国故事,二是作品中大量对“文革”时代社会阴暗面的披露。关于为何用英语创作,哈金的回答相当直白“为了生存”。“我想通过英语写作。使自己与大陆的文学机器分隔开来。换句话说,我获得一种自由。”哈金用英语创作并非是迎合美国读者,他只是在寻求一个文化与文化之间的边缘地带,想让自己成为一个“放逐者”。而“流散者”的身份让哈金用一个与众不同的全新视角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在《池塘》中,哈金对80年代中国的官本位思想和群众的奴化心理进行了反思和批判。
(一)官本位思想
歇马亭是由层层的官僚系统统治的,杨晨是“土皇帝”,刘恕和马宫是“丞相”,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制约着人们的生活,是掌握话语的强权人物。首先,歪曲事实,颠倒黑白。邵彬在《旅大日报》上发表了名叫“一家人”的漫画,意在讽刺刘马贪污腐败,却被刘恕误解为:“咱们是人,不是牲口。千年前咱们就消灭了群婚制了。只有那些反动派才说噢我们共产党是共产共妻。”曲解寓意的同时又将群众的怒火引向邵彬,可谓“聪明绝顶”、一箭双雕。其次,暴力相向,为所欲为。邵彬去沼气工作会议投诉,刘马怕他横生事端就强行拦截,为了不让邵彬说话,刘恕“叉开双腿,把肥大的屁股坐在邵彬的脸上‘老子要闷死你’”,重伤邵彬不说,还毫无廉耻地将被邵彬咬伤的屁股拍成照片到处宣扬。此种领导简直与流氓无异,为达目的无所不用。哈金对官僚的批判式书写,意在反思80年代中国官本位思想的严重弊端。权力意味着强势和控制,它决定着小人的升迁与沉沦,而无权利者只能受其制约和束缚,成为被阉割的“他者”。
(二)群众的奴化心理
中国千年以来尊孔子为圣人,其“桃花源”式的大同思想深入人心,可惜儒家文化终沦为统治阶级统治人们思想的工具,美好的大同理想也成了奴化人们的帮凶。邵彬的悲剧一方面是官本位强权作用的结果,另一方面其战友、同胞也在相当程度上充当了帮凶的角色。就在邵彬犹豫是否要去县人民大会的时候,同车间的萧鹏私下说:“邵彬啊,振作起来。别让他们给吓住了。咱们机修组的工人都支持你。杨晨竟然把你的信转给刘恕,也应该受到批评处理。”此番话看似鼓励加支持,实则别有含义。既然是兄弟,就应同进退、共患难,为何只让邵彬独自反抗?原因只有一个:明哲保身。如果邵彬失败了,则与他无关;一旦邵彬侥幸成功了,自己也会跟着受惠。一举两得,何乐不为。他的这番话分明就是让邵彬承担全部责任,自己坐享渔翁之利,用心何其险恶。“咬屁股”事件后,刘马召开了职工大会,“来参加会议的职工空前踊跃,食堂里从来没有装过这么多人,有十几个人找不到座位,就坐在窗台上。”邵彬的反抗不是为个人,而是在为所有生活在最低层的职工争取权益,可怜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只是作为一个看客来看热闹。官僚的强势已经奴化了大众,面对强势,他们只是一忍再忍,一让再让。如果是强权让他们变成了“他者”,那么他们自己也成了帮凶。哈金通过绝妙的描写对大众的奴化心理作了强烈讽刺,揭示了中华民族的劣根性。
哈金对80年代中国“池塘文化”的批判看似有“自我东方主义”之嫌,但深入分析,与其说是批判,不如说是一种反思,一种关怀人性的良好愿望。纵观整个美国华裔文学史,从第一位美国华裔作家水仙花到第二代华裔刘裔昌、黄玉雪,再到80年代的汤婷婷、谭恩美、赵健秀,华裔作家们在作品中流露的自我身份的迷茫、文化冲突的压力和价值观念的失落,深刻再现了第一代华人移民及其后裔肉体和精神上的“流亡”与无所依托。游离于两种文化的边缘,不断寻求文化、身份上的认同贯穿了整个华裔文学作品的主题。而拥有新移民身份的哈金,其作品既有对前辈们的继承,更重要的是,他在作品中不断探索普遍人性和个人的生存困境,深入挖掘人性的深层脆弱,表现悲剧性的主题。哈金把中国作为一个广阔的社会背景去探索普遍人性和个人面临的生存困境等问题,客观地展现了特定时代下母国中国的社会状况和人民的生活状况,真实地描写了普通人并不美好的生活和他们的生存困境,从而揭示了普遍人性。
从《池塘》开始,到《等待》、《疯狂》、《战废品》、《自由生活》,哈金已经创作了5部长篇小说。从《战废品》开始,哈金的视角已经从中国转移到了朝鲜,《自由生活》则是哈金第一次尝试写美国的移民生活。究竟哈金以后还会不会创作以中国为背景的小说,答案不能肯定,但三十年的中国情缘是割舍不掉的,哈金式“伟大小说”的精髓不会改变。《池塘》是哈金长篇小说创作的开端,也是其“伟大小说”的初步尝试,主人公自我价值的追求和幻灭具有普遍意义。全球化的今天,移民作家跨民族、跨地域、跨文化的书写已成为世界文学的一大趋势,综观近十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移民作家也占据了不可小觑的席位。在世界多元化的背景下,新移民作家哈金的出现预示着美国华裔文学也将朝着多元化的道路发展。
注释:
④江迅:《“谜”一样的哈金》,《上海采风》,2010年第7期,第44页。
⑩双叶:《哈金印象》,《华文文学》,2006年第2期,第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