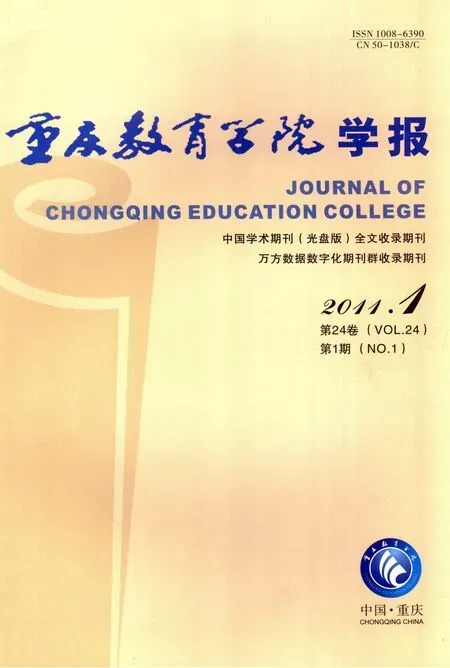论郑板桥家教思想中的弱势群体关怀
江净帆
(重庆教育学院,重庆 400067)
论郑板桥家教思想中的弱势群体关怀
江净帆
(重庆教育学院,重庆 400067)
郑板桥的家教思想比较集中地反映在了其家书中,而其家教思想的一个突出特征便是要求家人关怀周围的弱势群体,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要求家人代其向同宗寒族派发钱物;要求家人善待贫苦人家;要求家人设身处地为穷民着想。郑板桥关怀弱势群体的动因主要来自三方面:天地万物一体的平等观、儒佛福善祸淫的积德观以及儒家立功天地的济民观。
郑板桥;家教;弱势群体;关怀
家庭是社会重要的细胞单元,而在中国传统的宗法制社会下、家庭具有尤为特殊的地位,陈独秀在分析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的区别时,就认为西方是“个人本位”的社会,而中国则是“家族本位”的社会。[1]在这样一个家族本位的社会中,儒家将齐家视为了治国、平天下的重要前提,因而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庶众,都十分重视家教并衍生出了内涵丰富的家教思想体系,这些家教思想中的部分观点至今仍具有相当的启迪意义。本文就郑板桥家教思想中的弱势群体关怀提出共商,以促进对相关研究领域的关注、探讨。浅陋之处,敬请指正!
一、郑板桥家教思想中弱势群体关怀的主要体现
郑燮,字克柔,号板桥,江苏兴化人,为康乾时期“扬州八怪”的主要代表,以画、诗、书三绝名称于世。世人称其为“怪”,不仅在于其艺术风格上的书怪、画怪,也在于其棱角分明的鲜明个性。在郑板桥身上,有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狂傲不羁、藐视一切乃至世俗权富的气质,即使是在其家境贫寒的情况下也是如此,
《墨林今话》中曾记载他对待豪贵索画的态度:“豪贵家虽踵门请乞,寸笺尺幅,未易得也。家酷贫,不废声色。”[2]但就是这么一个刚性十足的郑板桥,却对处于社会下层的弱势群体表现出了柔性、细腻和怜恤的一面,这在他的家书中有集中体现。
郑板桥晚年出仕县令、任职在外,将家中托付给堂弟郑墨打点,故而经常有家书寄给妻子、堂弟和子女。这些家书较为集中地反映出其家教思想,而其家教思想中一个突出的特征便是要求家人关怀周围的弱势群体:
(一)周济同宗寒族
受宗法制社会结构的影响,郑板桥也有着比较强烈的家族同根意识。郑板桥虽然出自书香世家、父亲是个私塾教师,但其家族也算不上什么名门大宗,郑板桥完全是靠自己的勤奋考得一个功名、到50岁时才获得一个县令的职位。他出任县令后,并没有因为身份的改变而疏远同宗亲戚,却愈加注意与族戚的来往和关照。
在出任县令、经济状况有所改善以后,郑板桥曾三番五次写信给堂弟郑墨,嘱咐其代为派发钱财、以周济同宗寒族:“族人贫苦,固然可悯,故余每积省俸钱,寄归散给,聊表我赒悯贫族之义,”[3](P55)“敦宗族,睦亲姻,念故交,大数既得,其余邻里乡党,相周相恤,汝自为之,务在金尽为止。”[3](P11)郑板桥的这种周济并不是偶尔的点缀应景,而是历年的惯例并有派发的定数。对那些已经作古的族戚,郑板桥要求将钱财发给其子孙,如果子孙也没有、就将这些钱物用来修缮他们的坟墓。辞官之后,郑板桥再次回到了以卖字画养家的生活,但他对同宗寒族的援助却一直没有停止。
在经济上的周济之外,郑板桥也常常教育家人留意对族戚的细节关怀,“天寒地冻时,穷亲戚朋友到门,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佐以酱姜一小蹀,最是暖老温贫之具。”[3](P15)在操办女儿婚事的时候,考虑到贫族与邻佑的困难,他又专门写信给妻子,要求“凡贫族及邻佑之贺份,不论多寡,一概璧还。”[3](P67)
(二)善待贫苦人家
如果说,对寒族的周济乃是出自宗法制社会结构下的一种家族道义,那么郑扳桥对身边佃户、奴仆、儿子同学等等贫苦人家的关怀则更多出于深切的同情与自觉。
郑板桥常常教育家人尊重佃户、家奴,“愚兄平生最重农夫,新招佃地人,必须待之以礼……要体貌他,要怜悯他;有所借贷,要周全他;不能偿还,要宽待他。”[3](P16)他曾经在家中整 理旧书,偶然翻到了前代家奴的契券,他并没有用这个契券去追讨什么,甚至根本就不将这个契券拿出来示人,而是直接将它放在灯上烧毁了。在郑板桥看来,即使出自好心、将这个契券退给家奴,对家奴而言,也是“多一番形迹,增一番愧恧”,而他自己用人的原则是,“从不书券,合则留,不合则去。何苦留此一纸,使吾后世子孙借为口实,以便苛求抑勒乎?”[3](P16)
郑板桥晚年得子,对儿子十分疼爱、但教育也十分严格。他意识到“我虽微官,吾儿便是富贵子弟,”担心儿子因此会产生骄亢之气、不能与贫苦子弟善处,便写信要求儿子:“待同学,不可不慎。吾儿六岁,年最小,其同学长者当称为某先生,次亦称为某兄,不得直呼其名。纸笔墨砚,吾家所有,宜不时散给诸众同学。每见贫家之子,寡妇之儿,求十数钱,买川连纸钉仿字簿,而十日不得者,当察其故而无意中与之。至阴雨不能即归,辄留饭;薄暮,以旧鞋与穿而去。”[3](P26)在家奴子女方面,他也要求儿子平等待之:“家人儿女总是天地间一般人,当一般爱惜,不可使儿凌虐他。凡是食果饼,宜均分散给,大家欢喜跳跃。”[3](P21)
(三)同情穷民处境
郑板桥对穷民处境有着深刻的理解与同情。这种理解与同情使其对穷民不仅有一纸一契、一餐一鞋的关切,同时也有着更深沉的思虑和包容。
在小农经济的社会中,购置田产是一个家庭的大事,常人的思维通常是多多益善。但郑板桥对家人的教育则是,买田置产、足用则已,不能贪多扩展、断了穷民的生计,“将来须买田二百亩,予兄弟二人,各得百亩足也,亦古者一夫受天百亩之义也。若再求多,便是占人产业,莫大罪过。天下无田无地者多也,我独何人,贪求无厌,穷民将何所措足乎!”对于别人连阡越陌、数百顷聚集田地的现象,他又教导家人不要苟且合众、而要保持自己的德行:“他自做他家事,我自做我家事,世道盛则一德遵王,风俗偷则不同为恶,亦板桥之家法也。”[3](P16)
在郑板桥寄往家中的书信中,曾两次提及盗贼的问题。一次是儿子禀报家中失窃、准备报官追缉一事后,郑板桥的答复是:“如果损失不巨,不必追赃。窃贼固当执之于法,然彼为饥寒所迫,不得已铤而走险,不偷农户而窃宦家,彼亦知农民积蓄无多,宦室储藏丰富,窃之无损毫末,是即道亦有道之谓欤?与其农家被窃,宁使我家被窃。”[3](P71)还有一次,郑板桥与堂弟讨论买地筑屋一事,堂弟担心那块地可能存在盗贼隐患,郑板桥则不以为然、在信中说了一番话:“不知盗贼亦穷民耳,看门延人,商量分惠,有甚么便拿甚么去;若一无所有,便王献之青毡,亦可携取质百钱救急也。”[3](P11)
二、郑板桥家教思想中弱势群体关怀的动因分析
仔细体会郑板桥家教思想中的弱势群体关怀,深沉、细腻,就如后人评其画风一样,有一种真气、真意,没有任何矫情、伪饰,完全是设身处地为弱势群体着想,不图名分甚至情感上的任何回报。这种深沉、细腻的关怀,没有发自肺腑的理解、尊重和同情是做不到的。那么,这种关怀的动因又是什么呢?归究起来,大概有以下三点:
(一)天地万物一体的平等观
作为传统知识分子,郑板桥在宇宙观、世界观上深受“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并由这一思想衍生出了天地万物同为一体的平等观。郑板桥曾在家书中说:“夫天地万物,化育劬劳,一蚁一虫,皆本阴阳五行之气氤氲而出,上帝赤心之爱念。而万物之性人为贵,吾辈竟不能体天之心以为心, 万物将何所托命乎?”[3](P21)按照“天人合一”的观点,世界本于无极、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分阴阳、又化出五行之气,世界万世万物都是阴阳、五行之气氤氲交感而成,因此世界万物都由气构成、都本于一体,同气连枝、相互交感,在本质上本无什么区别。人与其他事物所不同者,只是人秉受的阴阳五行之气最为灵秀,故而人亦最贵。而郑板桥认为,人既然有这等可贵的天性,就应体悟天地化育万物的辛劳、怜悯万物。同时,因为万事万物都是本于一体的,因此这种怜悯和关爱应该是基于平等的相待之义,因此郑板桥在谈到自己与佃户的关系时候,就说:“彼称我为主人,我称彼为客户,主客原是对待之义,我何贵而彼何贱乎?”[3](P16)正是有了这种天地万物一体的平等观,郑板桥才能对社会弱势群体表现出真诚的尊重、也才能把这种尊重一以贯之地体现在其家教的思想中。
(二)儒佛福善祸淫的积德观
中国传统的积善思想并非佛教首传,由 “天人合一”思想衍生出的天道观中很早就蕴涵了积善意识,《周易》中就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天道观中的积善意识显然对郑板桥产生了影响,他在家书中论及贫富更替时便说:“天道,福善祸淫。彼善而富贵,尔淫而贫贱,理也”,并提出“存心是为人处,即是为己处”,[3](P16)这说明郑板桥并不排斥积善给人带来的现实功利性,而实际上,这种现实功利性也是郑板桥善待弱势群体的动因之一。同时,从郑板桥的个人经历来看,他曾与仁公上人、无方上人、青涯和尚等佛界人士有过密从交往,早年在扬州时也是寄住在寺庙之内,因此对佛家因果报应等思想也颇有心得。
儒、佛福善祸淫的思想已润化为郑板桥的自觉意识,对其行为的影响当然是方方面面的。而他在家庭教育中一再强调积德的观念,其中还有一个直接和重要的动因,就是积德为子息祈福。郑板桥所在的郑氏家族人丁不旺,他本人又是长房长孙,因此对子息殷望甚切。但偏偏不幸的是,郑板桥一生子息艰难,直到50岁以前都没有儿子,因此他为子积德的思想尤为浓郁,这也反映在了他的家书中,“余年将届五十矣,而膝下只有一女,望子情殷,思积些功德,所以治盗主捕而不主杀,问刑亦不尚严供。”[3](P39)晚年得子之后,郑板桥十分欣喜,自然把这个结果归于了积德、同时又期望积德能给儿子带来更多的善果,“余年至今五十有二始得一子,切望我弟多行善事,彼苍虽属莽莽,惟积德之报,屡试不爽,征诸《春秋》,记载亦夥矣。”[3](P54)
(三)儒家立功天地的济民观
郑板桥关切社会弱势群体的动因是十分复杂的,其中既有现实的功利性追求,也有着儒家立功天地、字养生民的责任意识,而这种责任意识与他坎坷的人生经历则有着密切的关系。
郑板桥一生多艰。虽然出自书香门第,但自幼家道中落,3岁丧母,14岁丧继母,30岁时还过着忧饥忧寒的日子。在30岁而立之年,他丧父又丧子,39岁丧妻,到40岁时才中举、44岁才中进士,又过了6年、也就是50岁时才得以出仕县令,52岁时始得一子、谁知道到57岁时又遭遇了老年丧子之痛,在61岁时则因为民请赈忤逆大吏而去官。应该说,这种坎坷的人生经历、尤其是前半生的贫苦生活使郑板桥对民间疾苦有着深刻的洞察与体会,因而对弱势群体也就有着更为丰富的理解能力和同情挚感。基于这种深沉的理解和同情,郑板桥无论是在做官的生涯还是在诗、书、画中,都表露出了对民间疾苦的强烈关怀。
郑板桥曾在家书中写道:“写字作画是雅事,亦是俗事。大丈夫不能立功天地,字养生民,而以区区笔墨供人玩好,非俗事而何?东坡居士刻刻以天地万物为心,以其余闲作为枯木竹石,不害也。若王摩诘、赵子昂辈,不过唐、宋间两画师耳!试看其平生诗文,可曾一句道着民间痛痒?”[3](P28)从此字里行间可以看出,郑板桥对毕尽一生以攻笔墨的选择并不十分认可,对他而言,理想的人生还是应该有一个所谓匡世济民的大舞台。而实际上,他出仕县令后、也确实地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过,并赢得了很好的官声。但无情的现实是,他虽然得到了百姓的拥戴、却并没有得到僚属的认可。在一次自然灾害中,他终于因为擅自开仓救济百姓触怒上司而被去官。
匡世济民的人生抱负没有实现,但关切民生的情怀仍然通过郑板桥的笔墨执着地表露了出来,他曾在画中题跋:“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并写下了《逃荒行》、《还家行》、《思归行》等一系列具有现实批判主义色彩的史诗。傅抱石先生曾经评论他说:“‘八怪’中,除他以外,我不知道哪一‘怪’,曾经‘怪’过当时荒淫无耻、民不聊生的现实,说出过几句同情人民的话儿来。”[4]也正是因为有着对民间疾苦的深切同情,才使得郑板桥不仅在官场、在书画,同时也在家庭教育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了对弱势群体的真诚关怀!
[1]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J].新青年,1915年第1卷第4号.
[2] 卞孝萱.郑板桥全集[M].济南:齐鲁书社,1985.74.
[3] 艾舒仁编.郑板桥文集[M].成都:四川美术出版社,2004.
[4]上海古籍出版社编.郑板桥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7.
[责任编辑 文 川]
On the care of disadvantaged groups in Zheng Ban-qiao’s thought of family education
JIANG Jing-fan
(Chongqing Education College, Chongqing 400067, China)
Zheng Ban-qiao’s thought of family education was reflected in his family letters collectively.One feature of his thought was that his families were required to show care to the disadvantaged groups of people.To be more exact, his families were required to distribute money and things to the poorer relative families for him, treat them kindly and think about their interests.The motive of his thought came mainly three views: equality view of all things in the universe, virtue accumulation view of Confucian and Buddhist kindness and Confucian idea of making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people and country.
Zheng Ban-qiao; family education; disadvantaged group, care
G40-09
A
1008-6390(2011)01-0159-03
2010-10-13
江净帆(1972-),女,四川泸州人,重庆教育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教育社会学、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及通识教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