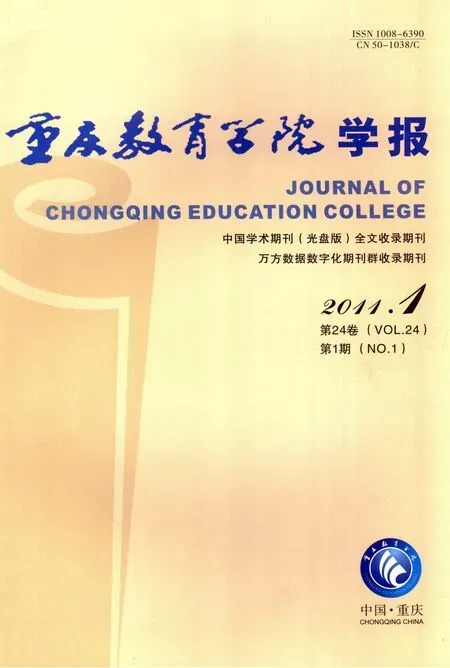唐宋时期重庆科举考试述论
吴洪成 ,闫志军
(河北大学 教育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唐宋时期重庆科举考试述论
吴洪成 ,闫志军
(河北大学 教育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中国科举制度于唐宋时期形成并逐渐完善,但这一制度在全国各地的发展状况并不相同,有各自的地方特点。重庆科举起步于唐代,但初期发展比较缓慢,应试人数也不多。至宋代科举在重庆得到了全面推行,中举人数也远远超过前朝,但分布不均衡,各地发展程度不一,这与地方区域政治、经济、文化及其地理位置等因素有很大关系。
唐代;宋代;科举考试;教育;重庆
唐宋两代,中国封建社会达到鼎盛并继续发展,封建教育也逐渐走向成熟,这不仅表现在古代官学制度的日益完善,而且体现在人才选拔制度上革命性的变革——科举制度的最终确立和日趋完备。唐代重庆地偏西南,高山阻隔,民族经济发展滞后,文化教育也难与发达地区媲美,故而科举制度的推行似乎也受到些许影响,但宋代重庆的发展却有后来居上之态势。历史地探索重庆科举制度的发展轨迹,不但能充实区域教育的内容,丰富巴渝文化的内涵,拓展中国教育文化的领域,同时也对西部大开发中地域特色文化建设,教育改革,人才资源的培育、选任及使用等方面都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唐代重庆科举的起步
科举制度是中国封建王朝设立科目进行考试以选拔官吏的制度。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称作科举。相对于之前的世卿世禄制、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科举取士抑制门阀、奖拔寒庶,更为公平、公正,因而有人称之谓有一定民主性因素的人才选拔制度。它历时1300年之久,对中国乃至世界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科举制度初创
隋开皇十八年(598年),隋文帝废除“九品中正制”,命五品以上京官和总督、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大业二年(606年),隋炀帝又令文武执事官五品以上者,按十科举人,包括孝悌有闻、德性敦厚、节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秀美、才堪将略、膂力骁壮等,其中“文才秀美”一科,即进士科。这种人才选拔制度的最大特点是把录取和任用权完全集中在中央。唐承隋制,全面推行科举取士办法。唐高宗李治咸亨年间(670~673年)的取士制度,大体分3类:由学馆出身的名“生徒”;由州县考选的名“乡贡”;由皇帝临时设置并亲自主持的名“制举”。设“明经”、“进士”等6科,犹以进士为重,但不易中选。
(二)重庆科举的发端
有唐一代,重庆府科举中进士者,合州、万县地区和云阳县各有进士 1 人,“涪州亦有人应试”[1]。
唐高宗时期(650~683年),闾丘军(合州人)与杜甫祖父杜审言同登进士第。武周载初元年(690年),他参加洛阳殿试策问,不被启用。唐中宗复位后,安乐公主主持朝政,赏识他的才华,任命他为太常博士。他能文工书,与陈子昂、杜审言齐名,曾书东蜀《牛头山瑞圣寺碑》、《滇南爨王墓碑》以及《刺史王仁求碑》,书法极佳,被称为当时之极笔。杜甫对其书法作诗《赠蜀僧闾丘师兄》[2]称颂,诗云:
大师铜梁秀,籍籍名家孙。呜呼先博士,炳灵精气奔。惟昔武皇后,临轩御乾坤。多士尽儒冠,墨客蔼云屯。当时上紫殿,不独卿相尊。世传闾丘笔,峻极逾昆仑。凤藏丹霄暮,龙去白水浑。青荧雪岭东,碑碣旧制存。斯文散都邑,高价越玙璠。晚看作者意,妙绝与谁论?吾祖诗冠古,同年蒙主恩。豫章夹日月,岁久空深根。小子思疏阔,岂能达词门?穷愁一挥泪,相遇即诸昆。我住锦官城,兄居祗树园。地近慰旅愁,往来当丘樊。天涯歇滞雨,粳稻卧不翻。漂然薄游倦,始与道侣敦。景晏步修廊,而无车马喧。夜阑接软语,落月如金盆。漠漠世界黑,驱车争夺繁。惟有摩尼珠,可照浊水源。
唐文宗时期(827~840年),夔州云安(今重庆云阳县)举子李远登科及第。李远出生年不详,约公元844年前后在世。《唐才子传》记载:远,字求古,大和五年杜陟榜进士及第,蜀人也。少有大志,夸迈流俗,为诗多逸气,五彩成文。早历下邑,词名卓然。宣宗时,宰相令狐綯进奏拟远杭州刺史,上曰:“朕闻远诗有‘青山不厌千杯酒,白日惟销一局棋’。是疏放如此,岂可临郡理人。”綯曰:“诗人托此以写高兴耳,未必实然。”上曰:“且令往观之。”至,果有治声。性简俭,嗜啖凫鸭。贵客经过,无他赠,厚者绿头一双而已。后历忠、建、江三州刺史,仕终御史中丞。[3]他的主要活动在武宗、宣宗两朝,大约在懿宗咸通中辞世。李远的作品传世不多,据《全唐诗》载,计有三十五首(其中二首重出于他人集中)及二句残句。李远诗尚无单行本,清人席启寓《唐诗百名家集》和江标《唐人五十家小集》录其诗。[4]
二、宋代重庆科举的初盛
宋代(960~1279)采用“重文抑武”的文教方针,较之唐代更重视科举取士,担任政府要职的政治实力派大都科举出身。宋代科举取士虽然基本上沿袭了唐代旧制,但也有自己的一些特点,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即滥与严。这一时期,科举制度在重庆也得到了全面推行,录取人数相当可观,而且一些僻远的州县也不乏中举者,这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宋代重庆教育的发展状况,表明重庆在全国的地位明显上升。
(一)滥、严相兼的科举取士
宋代科举承唐制,也分常科和制科。常科指科举中常设的科目,宋代有进士科、明经、九经、五经、学究、开元礼、三史 、三礼、明法诸科,也有武举。常科开始时每年进行1次,仁宗时改为2年进行1次,神宗时再改为3年进行1次,此后成为定制。制科是皇帝临时设置并亲自主持的选士科目,不定期考选,没有固定的章程和内容。宋代制科数目减少,且废置无常,高宗以后设有博学宏词科。
相对来讲,唐代进士考试中选的名额,极盛时一榜也不过50人,通常只有10~20人。而宋代最多时一榜曾达到1800余人,平时也是百人左右。可见宋代科举取士名额比唐代大大增加。这样做的结果,从积极方面讲,调动了士子应试的积极性,满足了朝廷对人才的需求,同时也满足了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使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得以缓和;从消极方面讲,造成了官僚冗滥,举人不实,败坏科举名声,教育质量严重下降。
在加大选拔力度的同时,宋代科举考试更加严密,考试规程日趋完善,以防止试场作弊,显示公正无私,选拔合格人才。例如:废除“公荐”,即明确禁止朝廷官员推荐考生应试,避免投献请托;裁抑世家子弟,限制其在应考中的特权,致使“公卿子弟多艰于进取”[5]。设立“别头试”,宋真宗下诏,“……举人与试官有亲嫌者,移试别头”[6],另派考官设场屋考试。实行“糊名法”,“真宗时,周安惠公起,始建糊名法”,即将考生的姓名、乡贯糊住,统一编号,然后判阅,“以革容私之弊”[7]。开创誊录制度,专置誊录院,设专人照录试卷,再送考官评阅,以堵根据笔迹或试卷暗号串通作弊之漏洞,“而后识认字画之弊始绝”[8]。 规定 “双重定等第”,“御试举人,设初考官先定等第,复弥之以送复考官再定等第,乃付详定官”。[9]根据此法,一篇试卷须经过三位考官评判,以力求客观与公正。宋代采取的种种严密措施,虽然目的是为了更有效的选拔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人才,但其中所包含的客观性和公平性是值得后人借鉴的。
(二)重庆的科举状况
宋代为统治需要,实施各项政策扩大科举录取名额及取士范围,并力求考试公平公正,这些举措都使士人受到鼓励,积极应试,从而加大了读书71人的数量,也因此使许多经济文化落后的地区产生进士。重庆科举“后来居上”,得到全面推行,并展现出不一般的历史与地域特点。
首先,宋朝中央政府在四川、重庆地区坚持实行“类省试”,给予特殊恩惠。宋代重视发展教育事业,以培养统治阶级治术人才为重大方针,并依据时局需要调整政策。南宋高宗建炎元年(1127年)十二月,因战乱道路阻梗,许多地方的举人难以赴应“省试”,高宗下诏“遂命诸道提刑司选官,即漕司所在州类试,率十四人而取一人”[10]。这就是南宋初期在四川等地实行的“类省试”(简称“类试”)的考试制度,“类试”合格者就得到相当于“省试”的资格,可以不再经过“省试”而直接参加殿试。随着战争形势的好转类,省试在其他地区实行两科之后于绍兴三年(1133年)就宣告结束了,但四川、重庆直到宋理宗时仍实行类试,巴渝地区的夔州(今奉节县)和昌州(今大足县)先后作过类省试的考试地。
在给予特殊恩惠的同时,与宋代日益严格的科举制度相应,宋中央政府对类省试制度同样加以严格的规定:“选差有出身清强见任转运使副或提点刑狱官充任监试,于逐路见任京朝官内选差有出身曾任馆职、学官,或有文学官充考试官,务依公精加考校,杜绝请托不公之弊。”[11]绍兴十三年(1143年),朝廷又下诏:“川陕诸州秋试举人,并用六月前锁院。”[12]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重申锁院制度,规定锁院时间为九月十五日,并由朝廷选派监视、考试官,以加强对类省试舞弊的打击。严格而完备的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为四川、重庆地区士人提供了公平竞争的机会。[13]
其次,重庆地区科举及第人数增加,覆盖面扩大,这当然和实行类省试这一特殊政策不无关系。有宋一代,在中央政府举行的科举考试中,四川、重庆被录取的知识分子几乎为全国之冠。据宋仁宗皇祐二年(1050年)田况所撰《进士题名记》:“益州自太平兴国以来,登进士第者,接踵而出。天圣、景祐中其数倍。至庆历六年,一榜得十八人,皇祐元年得二十四人,他州来学而登弟者,复在数外,其盛也如此。”[14]《重庆教育志》记载,宋代,重庆所辖州县先后中进士者208人,[15]另有重庆直辖后划入的涪陵、万县、黔江地区的及第进士21名。许多家族将科举入仕作为光宗耀祖、光大门庭乃至巩固家族显赫地位的重要手段,甚至出现了科第世家。《奉节县教育志》记载:宋代重庆奉节县生员中,有5人中进士:政和二年(1112年)壬辰科李裳,政和五年(1115年)乙未科裳弟李袭,裳子李公京、李公奕、裳孙李茂,呈大家族中举现象。为此,夔州府学前建五桂楼以示表彰。
宋代重庆参加科举考试被录取的人数不但增加,而且重庆大部分州县都有人中举,所分布的区域远远超过唐朝和五代,也为元、明所不及。但科举在重庆各州县的发展极不平衡,及第进士分布不均。据笔者所有资料统计,宋代重庆进士分布如下:合州104人,昌州60人,恭州20人,南平军20人,涪州6人,黔州5人,夔州4人,梁山军4人,大宁县 3 人,忠州 3 人。[16]
再次,宋代出现了重庆历史上第一个状元郎。在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下,承平时虽然三年一会试,但殿试第一也不那么容易,因为中国很大。从四川(含重庆)来说,整个明代只出了一个新都杨慎,整个清代只出了一个资中骆成骧。而在南宋,重庆巴县就有冯时行、蒲国宝二人先后考中状元。在记载中往往二人并称,当地的状元桥也可能是二人并指。巴县文庙中有双状元碑,清康熙四十五年进士、巴县乡贤龙为霖为此碑题诗云:“有宋多才子,比肩两鼎元,江山不曾改,红杏尚依垣。”[17]清周开丰有诗云:“巴国当南宋,冯蒲两状元,遗徽存石碣,可复继高蹇。”[18]
冯时行(?~1163 年),字当可。宋徽宗宣六年间(1119~1125年)进士第一人,号缙云先生,巴县(今重庆市北碚区)人。南宋高宗建炎中(1127~1130年)调奉节尉。绍兴中历江原丞,擢左奉议郎,知丹棱县,绍兴八年(1138年)召对,奏金人议和不足信,请选大臣重兵镇荆襄,使岳飞得专致力于江汉间。高宗命擢知万州。时行力主抗金,不附和议,深为秦桧所恶,坐废达十八年。直到秦桧死,才于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再起用,历知蓬州(蓬安),黎州(汉源)。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人败盟,高宗记时行名,召赴行往,时行病不能往,上疏慷慨陈词。后改知彭州(彭县)。未久擢右朝清大夫、提点成都府路刑狱。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卒于任。有《易论》2卷、《缙云文集》45卷。冯时行抗金报国大志,坚定不移,不愧豪杰之士。
冯时行是宋代川东理学流派的重要人物,在理学流播传承的关系中具有一定的地位。《宋史·谯定传》载:“定易学得之程颐,授之胡宪、刘勉之,而冯时行、张行成则是定之余意出。”[19]由于谯定不只是师承于程颐,还从蜀人郭襄氏受象数易学,所以其后学亦有义理派和象数派之分,胡宪、刘勉之、张浚属义理派,冯时行、张行成为象数派。冯视画卦,尝说:“《易》之象在画,《易》之道在用。”[20]并以此为标准,认为程颐易学在尽人事,通世道方面虽然精妙,然“往往舍画求《易》,故时有不合;又不会通一卦之体,以观其全,每求之爻辞离散之间, 故其误十犹五六”。[21]《朱文公文集》(卷 84)记载:朱熹曾赞冯时行“议论伟然”、“尤恨不得一见其面目,而听其话言也”。由此可见其学术造诣、地位及重大影响。
缙云山下五里梁滩坝为冯时行故里,后命名状元乡,有碑镌“状元乡”三字,乾隆修《巴县志》时碑尚存,现在还有状元碑车站。《大清一统志》中还有冯时行墓的记载,谓在巴县铜锣峡。乾隆年间《巴县志》谓冯时行:“绍兴时状元。县东鱼嘴沱,石崖下有南平老人墓,去此五十步,相传即状元墓。”
蒲国宝,南宋宁宗开禧(1205~1207年)中状元,重庆璧山县人,生平不详。明清时璧山县城建有冯蒲二状元坊,凉亭关石崖上刻有“尝怀抗书冯时行,太息通经蒲国宝”的对联,这表明蒲国宝与同邑冯时行先后鼎名。《巴县志》称:“苦竹溪源出鹿角乡,北流经雷家桥龙门湾鲤鱼石。其东有大宅,瓦上皆铸‘状元及第’字,传为蒲国宝故居。”其著作大都散失殆尽,现今只传下一篇《金堂南山泉铭》。蒲国宝“饱饫六艺,淹贯经史”,又书法精美,尤善楷书,今重庆市功城翠云寺内有手书“天池寺”匾额。故世后,葬于璧山蒲元乡蒲坎坝。
三、唐宋重庆科举考试分析
由唐至宋,科举制度在重庆逐渐推行开来,从初步发展到“后起之秀”,中举人数明显增加。有唐一代,重庆科举人才可谓寥若晨星,宋代则人文蔚起,贤良迭出。笔者分析认为,科举制度作为“国家抡才大典”,其盛衰固然受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大政方针的制约,但从地域的角度看,科举在各地的发展中,地方各种因素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重庆的科举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一)政治方面,行政区域中心的调整与科举的发展密切相关
一般而言,地方区域中心既是地方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也是文化、教育和人才中心,教育发展的起伏,人才分布的变化均与之有密切的关系。彭水县在唐宋时期是黔州都督府、黔中郡、黔中道、绍庆府的治所,唐朝时领辖50多个州,南宋时领辖56个州。黔州(今彭水县域)成为区域中心后,当地迅速兴起学校。在后唐及宋初都设有黔州儒学,这是渝东南地区设置最早的儒学。南宋时,黔州就有5人中进士。元代之后,黔州地位逐渐下降,至清初仅为酉阳直隶州的一个属县,人才中心已消失。在元明清的科场上,仅出现过3名进士,30名举人,远远落后于乌江流域土家族聚居的一般州县。[22]
(二)地方区域经济对重庆科举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唐宋时期,川东南地区农业经济不十分发达,而教育却发展得有声有色,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是这些地区虽然农业经济落后,但与前代相比还是有了更大发展,特别是工矿业中盐业的发展,使一部分人可以有一定的经济力量和时间去追求功名;二是这些地区商业普遍不发达,主要是农业耕作,这就限制了士子的成才走向,只能走上科举考试这条求“仕”之路,而农业的持续性为这条道路创造了相对稳定的条件。[23]
同时,重庆农业经济地理格局的变化,农业经济重心的转移也影响了科举的地区发展。自古以来,重庆的农业重心一直在渝东。渝东的巫山是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农业起步很早,肇始于新石器时期,大体与中原同步。巴人建国先在渝东,疆域开拓、经济开发渐次由渝东向渝西推进。西汉重庆8县,6县在渝东,渝西仅2县;东汉重庆9县,渝东7县,渝西2县。历魏晋南北朝直至唐代,重庆45县,渝东22县,人口40 499口;渝西23县,人口76 507口,渝西比渝东多出36 008口,农业经济的地理格局发生根本变化。至于宋代,渝东17县,137 848户,渝西15县,146 594户,渝西仍比渝东多9 746户,耕地面积相应也超过渝东。以上表明唐宋时期,重庆农业经济重心已经从渝东转移到了渝西。[24]这些变化对重庆的科举有重要影响,唐代科举推行之初,农业经济相对发达的渝东万县、云阳和涪陵等地就有人应试并中举,渝西只有合州一县有人应试。随着渝西经济的赶超,渝西各县区的及第人数也渐渐多于东部地区。有宋一代,东西两地进士分布差距明显。渝西:合州89人,铜梁14人,昌州36人,容昌13人,江津11人,南平军20人;渝东:武隆6人,彭水5人,云阳5人,奉节4人,梁山军4人,大昌2人,大宁、忠州、垫江、丰都各1人。[16]与唐代重庆科举的起步阶段相比,其中反差最大的就是合州与云阳县,合州发展最快,进士人数其时已居重庆各县区首位,而云阳县只有五人中举,农业经济对科举发展的影响可见一斑。
(三)重庆的学校教育与科举互相依存
科举是一种取士制度,中国古代学校则以养士为目标,“取”“养”之间必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唐代科举考生的来源一个是生徒,一个是乡贡。前者接受的是官学教育,后者实为私学出身。科举的实施与推行,促进了学校教育的发展,重庆一些地方的政府先后创设学校。例如,唐宪宗元和年间(806~820年)刺史韦处厚建开县儒学。长庆二至四年(822~824年),夔州刺史刘禹锡叹天下学校废,上奏《请减繁费,增设学校奏记》。另据有学者查考,唐代有巴州儒学,[25]唐宋时重庆已有学宫。唐代诗人戴叔伦有诗作描述了当时的涪州(即今重庆市涪陵区)设学兴教的情形:“文教通夷俗,均输问火田。江分巴字水,树入夜郎烟。”[26]
宋代实施“崇文抑武”的方针,举学设教,加强科举。北宋的三次举学运动试图解决学校教育与科举选士间的矛盾或问题,虽然最终都未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但每一次改革的实施,都推动了科举与学校教育的发展。科举制度日渐完备,学校数量不断增加。重庆也兴起了办学热潮,许多州、县纷纷创办起了地方学校,如北宋仁宗景祐年间(1034~1037年)郡太守徐舜俞建合州儒学于涪江之南。因水灾,哲宗元祐五年(1090年)郡守刘象功、石照会、杨廷杰始迁州治南。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年)州判何郯在府治东建夔州府儒学,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转运判官孔嗣宗重修。《江津县志》(卷六)记载:北宋治平元年(1064年),江津知县郑谔“肇就学治,以饬文教”,在江津治西修建孔庙,创办县学。北宋绍圣三年(1096年)忠州设学宫(县学)于州屏山麓文庙内。南宋绍兴元年(1131年)始建重庆府文庙和巴县文庙,府、县文庙即官学。府庙在今重庆29中学处,县庙在今重庆26中学处。宋窦敷 《黔江县修学记》记载: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黔江县令修复县学学宫。宋理宗宝庆年间(1225~1227年)夔州刺史何、教授任元癸建梁山县儒学于县城南。据统计,宋代四川、重庆建庙学共95所,在南宋的四川、重庆州县中,官学的覆盖率达42%,蜀人号称“虽遐陬荒裔,罔不遍焉”,表明当时四川、重庆的教育文化已经在全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了。[27]在这种背景下,科举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据统计宋代四川、重庆和江南的进士人数已经占了全国的80%左右,[28]而北宋时期四川、重庆进士数居前10位的第8位,南宋则跃居第4位,[29]宋代蜀籍人士为宰相者达27人之多。
(四)重庆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在重庆科举的发展中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南宋“类省试”因战乱道路阻梗各地举人难以赴应“省试”而设,后基本停罢,独川、陕地区得以保留。绍兴四年(1134)六月,高宗下诏,“复命川、陕类试”[30]。诏令中的理由已由先前的“军兴道梗”变为“川、陕道远”,这实际上是优待川、陕举子的特殊政策,[31]重庆举子自然也享受到这一特殊优待。像正规常态的省试一样,“类试”的录取人数是按比例配额的。“在南宋的大多数时期内,这两种省试的配额比例相同。但在12世纪的20年内,四川省试的配额比例较宽,它的比例达 1/14,而正规省试的比例为 1/17和 1/16。自 1183 年起四川类试才以 1/16 为率。”[32]
“蜀道难”给四川、重庆带来科举考试的优惠政策,沿江的水道也给当地科举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中国古代历代封建王朝将征自田赋的部分粮食经水道解往京师或其他指定地点,这种运输方式称做漕运。漕运其实是我国历史上一项重要的经济制度,给漕道所经之地带来很大的发展机遇。唐宋时代的西汉水(嘉陵江)是漕转茶马、川米、布帛的重要漕道,而合州为漕运转船之地,控扼四川的整个漕运,有“巴蜀要津”之称,“人生其间,多秀异而嘉,以诗书自乐”,[33]其重要性远远超过当时的恭州。[34]有宋一代,合州考中进士89人,恭州仅有4人上榜,相差20多倍,不能说与其地理位置没有关系。
唐宋实行科举制度,的确满足了封建君主专制政治的要求,收到了集权中央、巩固封建统治的效果,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在当时是一种比较合理、比较符合历史发展要求的制度。重庆科举制度的推进,也对地方的社会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当然,科举的是非功过需要客观评说,它犹如历史长河中留下的一些纪念性的遗迹,由人凭吊,耐人寻味。笔者仅以历史为经、地域为纬,择取唐宋两代、重庆一地略做浅析,抛砖引玉,以求当今时贤把科举制度的研究不断向前推进。
[1]四川省涪陵市志编纂委员会.涪陵市志[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389.
[2] (唐)杜甫.赠蜀僧闾丘师兄[A].高仁(标点).杜甫全集(卷四)[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46.
[3] (元)辛文房.唐才子传[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86.
[4] http: //baike.baidu.com/view/106396.htm.
[5] (宋)叶梦得.石林燕语 [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90.
[6] (宋)王栐.燕翼贻谋录(卷五)[M].台北:商务印书馆,1979.71.
[7] (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五)[M].北京:中华书局,1979.69.
[8] (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一)[M].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14.
[9] (宋)沈括.梦溪笔谈(卷一)[M].长沙:岳麓书社,1999.6-7.
[10]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三)[M].北京:中华书局,2000.262.
[11]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选举(四之二四)[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6.4288.
[12]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 150)[M].台北:文海出版社,1980.4729.
[13] 刘海峰,李冰.中国科举史[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4.201.
[14]转引自熊明安.四川教育史稿[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3.22.
[15]重庆市教育委员会.重庆教育志[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2.10.
[16] (清)常明,杨芳灿.四川通志·选举志(卷 122)[M].成都:巴蜀书社 1984.3685.
[17] http://ent.sina.com.cn/x/2006-11-11/01521323421.html.
[18] http://jiangshui.cqwx.net/bbs/viewthread.php?tid =26457.
[19] (元)脱脱.宋史·谯定传(卷 459)[M].北京:中华书局,1977.13461.
[20] (清)陆心源.宋史翼(卷十)[M].北京:中华书局,1991.110.
[21](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一)[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14.
[22]湛玉书,李良品.乌江流域土家族地区土司时期教育的类型、特点及影响[J].教育评论,2006.(1):92.
[23]吴洪成.宋代重庆的学术文化与教育[J].重庆师院学报,2003.(1):47-53.
[24]卢华语.唐宋时期重庆农业经济的几点变化[J].重庆大学学报,2002.(2):87-88.90.
[25]蓝勇.西南历史文化地理[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86.
[26](唐)戴叔伦.渐至涪州先寄(王员)外使君纵[A].熊笃.历代巴渝古诗选注[C].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82.
[27]吴洪成.重庆的学校[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77-78,79.
[28]肖忠华.宋代人才的地域分布及其规律[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3):19-44.
[29]缪进鸿.长江三角洲与其他地区人才的比较研究[A].缪进鸿,郑云山.中国东南地区人才问题国际研讨会论文集[C].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3.222-223,229.
[30](元)脱脱.宋史·高宗(卷 27)[M].北京:中华书局,1977.510.
[31]祝尚书.宋代科举与文学考论[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69.
[32](美)贾志扬.宋代科举[M].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5.189.
[33](宋)王象之.舆纪地胜(卷 159·合州)[M].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797.
[34]蓝勇.西南历史文化地理[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102.
[责任编辑 于 湘]
A study of the Imperial Civil Examination in Chongqing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WU Hong-cheng,YAN Zhi-jun
(Education College,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071002, Hebei, China)
The Imperial Civil Examination (ICE) of China came into being and was gradually perfected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However, developing differently in the country, that system had local color.Chonqing ICE, starting in the Tang Dynasty,developed very slowly at the beginning and only a few candidates went for it.It was not well carried out until the Song Dynasty and more candidates than before passed the examination.Nevertheless, it was characteristic of unbalanced distribution and uneven development which were greatly related to the factors of local politics, economy, culture, geographical position, etc..
Tang Dynasty;Song Dynasty; ICE; education;Chongqing
G529
A
1008-6390(2011)01-0154-05
2010-05-11
吴洪成(1963-),男,浙江金华人,河北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教育史研究;闫志军(1975-),男,河北邢台人,河北大学教育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教育学基本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