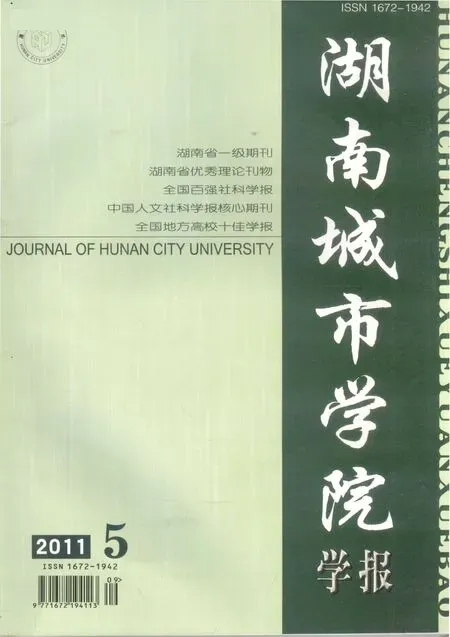“今文学”视阈下王闿运复古诗学的历史建构
王 成
王闿运诗学的复古与其“今文学”的复古立场是一脉相承的;复古不仅是其诗学观念生发的关键环节,而且是其诗学地位与诗歌成就得以认同的最大保证,“今所传《湘绮楼诗》,刻意之作,辞采巨丽,用意精严,真足上掩鲍谢,下揖阴何,宜其独步一时,尚友千古矣。”[1]21王闿运诗学选择独尊汉魏六朝诗歌及其主张,力主通经、治情、主文的诗学本体,诗法上尽法古人,在近乎服膺于古人诗学的立场下建构起了复古的诗学体系。虽然后人认为其诗学往往游离于社会现实之外,“极端的模仿古人,几乎没有‘我’在,几乎跳不出他所生活的时代空气以外。”[2]31但是,“王氏之诗,尚有不可磨灭者在”[3],他的诗学复古背后深藏的是晚清衰世文人的“为文之用心”,而这也正是王闿运以经淑世的“今文学”学术研究所体现出的价值取向之于其诗学的启发和渗透。
一、诗学生发的古典维度
作为晚清传统文人的代表,王闿运在诸多方面表现得较为保守,如反对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和革命运动等;但是,具有强烈自负且深藏“帝王之学”的王闿运,又往往表现出一种爱国者的形象,并且使其学术和文学在复古的基点上显现出一定的创见和变通。
(一)观既有复古诗学之态度
王闿运既然选择以复古作为诗学生发的基础,那么,他自然不会无视既有的复古传统,特别是明七子的诗学复古和晚清诗坛的弥宋诗学;而恰恰是在对它们的态度中,王闿运才逐渐明确了自身诗学复古的对象。他如是评说明七子的复古诗学:“明人号为复古,全无古色。”[4]538“可看明七子诗,殊不成语,大似驴鸣犬吠,胆大如此,比清人尤笑也。”[5]2358由此可以看出,王闿运对明七子的诗学复古是持批评态度的。他认为,明代七子的拟古、复古并没有达到复古所应具备之要求与高标,其尤对他们模拟初盛唐诗学且只是“剽窃唐人皮毛”的复古路径颇为不满;为此,在诗学复古选择上,王闿运也就否定了由明七子所开创的宗唐诗学。
当然,就晚清诗坛而言,复古仍是主导潮流,以“弥宋”为主的复古诗学当为诗坛主流;而以复古自居的王闿运却不谙当时诗学复古之道,对宋型诗及其“弥宋”诗派表现出极大的抵触与不屑,“无论何文,但属词成句,即自有章。……诗则不然,苏诗不成章,学苏诗者愈不成章。正使一二句偶似,于章则未也。……孟子、宋儒皆未成章也。九流之不及六艺,以无章耳。”[6]2378基于对诗学复古的认识,王闿运窃以为,就算是当下占据主流的“弥宋”复古诗学也不足为道;其不仅认为他们的诗学复古不仅取法不宗,而且影响诗道发展和误导世风,甚至忽视了诗学之本于情和文的独特魅力,“近代儒生深讳绮靡,乃区分奇偶,轻诋六朝。不解缘情之言,疑为淫哇之语,其原出于毛、郑,其后成于里巷。”[7]544-545
由此可见,在诗学复古对象的选择上,王闿运明确地表达了对尊唐与崇宋诗风的不满,从而表露出他所要进行的诗学复古,走的是一条不与同时代人同语的独特路径。
(二)寻诗学复古之古典维度
晚清时期,诗坛“弥宋”之风更甚;特别是同治、光绪年间,主张取法“三元”(开元、元和、元祐)的诗人比比皆是,真可谓“天下鹜逐”。面对如此情境,王闿运较为明确地表明了对“矜其奇诡”、“歌诗失纪”的宋诗派极大的鄙弃和不满。王闿运既不满明七子诗学复古的既有成效,又不主张“弥宋”诗学的复古路径,而是期望以一种更为高格和彻底的姿态进行诗学的复古。
在王闿运看来,将复古的维度上溯到汉魏六朝诗歌及其主张,无疑更具本源性和可取性,“陈子昂、张九龄以公干之体,自抒怀抱,李白所宗也。元结、苏涣加以排宕,斯五言之善者乎。刘希夷学梁简文,超艳绝伦,居然青出,王维继之以烟霞,唐诗之逸,遂成芳秀。张若虚春江花月用西洲格调,孤篇横绝,竟为大家,李贺、商隐挹其鲜润,宋词、元诗尽其支流,宫体之巨澜也。杜甫歌行,自称鲍、庚……”[8]532-533王闿运认为,唐代诸诗派皆承汉魏而来,而后世之宋诗、元诗、明诗等,自当皆为末流;为此,王闿运就为其诗学复古树立了正宗——汉魏六朝诗歌及其主张。王闿运认为,诗法应该完备于魏晋,若复古,则当取最为本源者为上;我们可以看出,王闿运诗学较之他人更为彻底的复古立场与决心。显然,王闿运对诗学复古对象的批评和选择体现了其“今文学”学术研究的复古立场,即彻底复古,返回本源,在追源溯流的基础上力求返本,追求一种更为正宗与本源的复古高标。
王闿运以彻底的复古立场明确了其诗学效法的对象,尔后,他又进一步对诗学复古的范围进行了界定,“七言较五言易工,以其有痕迹可寻,易于见好,李、杜门径尤易窥寻。然不先工五言,则章法不密,开合不灵,以体近于俗,先难入古,不知五言用笔法,则歌行全无步武也。既能作五言,乃放而为七言易矣。切记!太白四言之说,四言与诗绝不相干。作诗必先学五言,五言必读汉诗。而汉诗甚少,题目种类亦少,无可揣摩处,故必学魏、晋也。诗法备于魏、晋,宋、齐但扩充之,陈、隋则开新派矣。”[9]2373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王闿运将诗学复古的范围主要框定在了汉魏六朝的五言古诗;其不仅从师法、诗律上强调拟古作需从汉魏六朝古诗来求之的客观论断,而且对既已公认的代表诗家陈、李、杜等人进行了批评,形成了自身诗学复古的特殊价值取向。
二、通经、治情、主文的诗学本体
以汉魏六朝五言古诗为复古基点,王闿运建构起了自己的诗学体系。在诗学本体的营造上,王闿运以通经为起点,进而引出对“情”的阐发,再外化为“文”的形式,形成一条较为完善的复古诗学路径。通经、治情、主文的诗学本体是进入王闿运复古诗学的关键词,它们不仅表现出其“今文学”价值体系在诗学领域的有效渗透,而且也体现出诗人于复古诗学的独特认识和建构。
(一)“经术可入词章”的诗学起点
作为具有深厚学术背景的学人,王闿运的复古诗学必然会打上浓厚的学术底蕴。事实上,王闿运也确实如此,他将经义作为了诗学生发的起点,并且在对世俗之见的纠偏中为其诗学复古的展开奠定了基础。
对前人论诗不取经义的做法,王闿运是颇为不满的,“俗人论诗,以为不可入经义训诂。”[10]2164“今世所云经学、词章,即史家儒林、文苑,皆士人之一艺,入世之羔雁,曾非学也。圣人词无不章,学则垂经,虽自天生,亦由人力。……通经者未有不文,能文者未有无学。”[11]512在此,王闿运将不用经义论诗的做法称为俗人之见,并且以通经能文的圣人为楷模,极力主张 “当依经以立本”的论诗立场,“所谓经术可入词章。一贯之学,为文家上乘。”[5]2370当然,王闿运将“经术可入词章”作为诗学复古的起点,并不是简单地复归到以经入诗和以经解诗的传统;而是试图突破世俗诗学浅薄的表层论诗之道,鄙弃拟古不深、解诗不入的复古通病,进而以经义阐发模式在诗学领域打通一条意义得以再生发的“通口”。也就是说,王闿运的诗学复古有意遵循了“今文学”学术研究的价值体系,力图以通经之微言大义来寻求诗学的现实意义和当下功效。
因此,王闿运的“经术可入词章”,实际上是以经义阐发模式入“词章”,是一种思维模式、方法论和价值观上的承接,而这才是王闿运以通经为诗学本体建构取向之一的真实内涵之所在。如“我更西寻黑水南,遥将蒟酱寄鞮撢”。[12]1520作为赠答诗作中的一联,此两句似乎于字句上无外乎友情的抒发和渲染;但是,考虑到王闿运复古诗学所具有的学术背景,它实际上又在外在层面之外传达出一定的微言大义;“蒟酱”和“鞮撢”就于“春秋笔法”之中彰显了诗学的深层意蕴。“蒟酱”不仅化用了汉代“唐蒙开通夜郎古道”的典故,而且寄寓了诗人攘除外患之志向;而“鞮撢”更是直接的涉及到诗人“今文学”学术研究的思想内涵,将诗人心中的夷夏之辨——华夏中心论、以夏化夷的观点鲜明地表达出来了。
王闿运将“经术可入词章”作为诗学复古的起点,以求在思维模式和方法论上跟进其“今文学”学术研究的路径,从而将诗学的经世立场用一种迂回的方式呈现出来了。我们应该明确:王闿运诗学本体的通经维度同样指向了“治”,是一种为“治”的诗学价值表达,“词赋似小,其源在《诗》,《诗》者正得失,动天地,吟咏情性,达于事变,……夫赋无空疏之作,世鲜能通博之家,但患为不精,何至远而遂泥于此,留意是亦为政也。”[13]166
从王闿运整个诗学体系来看,其诗学主张似乎沉迷古人至深,往往见不出诗学之于当世的积极态度;而实际上,王闿运的诗学是在复古过程中承接了其“今文学”的学术理路,将诗学之“用”隐藏较深,有意“以词掩意”,于不露声色中彰显出诗学为“治”之本色。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将王闿运的诗学视之为“古董”,其在通经的诗学本体建构中已经明确了其诗学复古的逻辑起点——“经术可入词章”;而这不仅仅体现在反映社会现实和自身苦难的少量诗作中,如《圆明园词》《发祁门杂诗》等,甚至其整个诗学体系均可作如是观。可以说,以经观之,以用通之,是我们进入王闿运复古诗学的路口;而真正支撑起其复古诗学大厦的则是“治情”的诗学本体与用心。
(二)“治情”的诗学本体与用心
王闿运不仅在其复古诗学中多次论及到诗与“情”的关系,而且不吝以“诗缘情”、“诗贵情”、“诗主性情”等论断来表述自己的立场。王闿运诗学之“情”虽是以返回汉魏六朝“诗缘情”的诗学本体为基础的;但是,他并没有如汉魏六朝诗学那样单一注重一己之性情的抒发,而是对诗之“情”作了形上层面的开拓,即在“为己”与“为治”的价值旨归中对“情”进行了生发和诠释,从而最终实现了对“治情”诗学本体的建构。
诗与“情”是一种什么关系呢?王闿运是有自己的看法的,“诗以养性,且达难言之情。”[9]2272“古之诗以正得失,今之诗以养性情。虽仍诗名,其用异矣。”[14]2328“诗贵有情乎?序《诗》者曰:发乎情,而贵有所止;则情不贵。人贵有情乎?论人者曰:多情不如寡欲;则情不贵。不贵,则人胡以诗?”[15]379-380在此,王闿运明确了“情”之于诗的重要性,将有无情性作为诗歌产生的基础,从诗学发生学的角度赋予“情”本体论的地位。从论诗的历史渊源来看,王闿运以情立论显然是接受了陆机“诗缘情”的理论主张,“晋浮靡,用为谈资,故入玄理。宋、齐、梁游宴,藻绘山川;梁、陈巧思,寓言闺闼,皆言情之作,情不可放,言不可肆,婉而多思,寓情于文,虽理不充周,犹可讽诵。”[7]544-545王闿运是深信“诗缘情”的诗学法则的;而且,他力图恢复诗学“情”本体的努力,也确是相当执著与果敢的。为此,他甚至对奉为经典的《诗三百》予以否定,进而挑战具有深厚基础和传统的“诗言志”理论,“近人作诗,皆托源《诗三百》,此巨谬也。……论者欲以比古经,岂不谬哉?六义之旨,同于温柔敦厚,非以问世也。犹之“思无邪”,非五经有邪也。邪姑不论,而温柔敦厚固词赋之所同。诗不论理,亦非载道,历代不误,故去之弥远。”[6]2376-2377王闿运之所以作出如此论断,既是其诗学复古以汉魏六朝为高标的必然结穴,又是其试图对当世诗坛过于轻浮和势利的诗风进行纠正的努力。
当然,从诗学的历史传承以及王闿运诗学的表层维度来看,言“情”已不是什么新的主张,更难见出有何突破与创造,而王闿运复古诗学实现所谓的真似汉魏六朝诗学,即是其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了;倘若如此,王闿运也真就是个“活着的六朝人”。事实上,在既有的诗学评论中,王闿运仍然处于争论之中;为了厘清其诗学复古之于传统的承接与突破,我们需要进一步明了王闿运复古诗学之“情”的真实内涵。在生涯晚期,王闿运有过这样的论述,“已而看昨日日记,八十老翁自比林黛玉,殆亦善言情者。长爪生云:‘天若有情天亦老’;彼不知情,老不相干也。情自是血气中生发,无血气自无情。无情何处见性?宋人意以为性善情恶,彼不知善恶皆是情。道亦是情,血气乃是性。食色是情,故鱼见嫱、施而深潜,嫱、施见鱼而欲网钓,各用情也。”[5]2357王闿运复古诗学屡屡强调要“达难言之情”,其对“情”的建构却仍是比较通达和宽泛的。无论是与生俱来的秉性,还是道、善恶、食色等,都是人之“情”的应有范畴,也都是王闿运复古诗学所力图想要传达之要旨。由此出发,王闿运复古诗学的“情”就成为了个体的人现实存在的表征,是人之为人的本然规定性所在。因此,王闿运复古诗学之“情”,又表现出与汉魏六朝诗学一定的异质性:它不再单纯地强调诗歌的抒情本质,也不再留恋于“非长歌何以骋其情”的创作主旨,亦不再仅仅注重诗学意义生发的单一维度,而是力图表征完整的个体本质及其本然存在状态。
显然,王闿运复古诗学对“情”的框定,是在传承汉魏六朝“诗缘情”理论的表象下又作了一定的开拓。在王闿运看来,既然诗学是以表征个体的方式存在的,那么,“为己”自然就是诗学的题中之义了;为此,诗学对“情”的倚仗,以及“情”由诗发的理路,最终都离不开“为己”的价值旨归,“古以教谏为本,专为人作;今以托兴为本,乃为己作。”[16]551“亦以自发情性,与人无干。虽足以讽上化下,而非为人作,或亦写情赋景,要取自适。”[14]2325当然,王闿运复古诗学的“为己”向度并不是那种简单的吟咏风月与感怀伤悲式的“独语”或自言自语,而是寻求一种个体存在的本然状态。也就是说,诗歌如能展现个体本质,即是“为己”,进而才能够实现“自治”,而这也是其“治情”诗学本体的内在逻辑构成。虽然王闿运的复古诗学讲究“诗不论理,亦非载道”;[6]2377但是,他重“情”、“治情”,将“情”的表征与彰显指向“为己”的诗学意义,把“诗以养性情”的主旨落实为个体本然状态的呈现,本身就暗合了其“今文学”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即以“自治”达到“治天下”。作为对魏晋六朝诗歌及其主张的模仿,王闿运“为治”的诗学倾向往往是藏而不露的,我们往往只能从其诗学由“为己”而通达“治情”的路径中有所管窥,即以诗学正一己之“情”而正天下人之“情”。
王闿运始终认为,古之学为己而诗学昌盛,世道亦不危;今之学为人而诗学凋敝,世道亦乱;但今人却不知反求诸己,诗心人心愈乱,诗道世道不盛亦已。王闿运别出心裁、大张旗鼓地复古汉魏六朝诗歌及其主张,似有以诗正诗心(“为己”)进而挽救世道人心的主观用心,“诗者,持也。持其所得,而谨其易失,其功无可懈者。虽七十从心,仍如十五志学,故为治心之要。”[4]539“诗者,文生情。人之为诗,情生文。文情者,治情也。”[15]380诗以达情为主,而情亦能为诗;诗情合一,则在于“治情”。王闿运复古诗学中“诗”、“情”及关乎二者的“为己”、“自治”等,最终都可纳入到其“治情”的诗学本体。“治情”,即以诗歌来恢复人之常情与本性,而“非可快意骋词,自状其偏颇,以供世人之喜怒也”[7]544;若社会个体皆能依诗而“自治”,整个社会亦能大治,而这即是“治情”诗学的最终归宿。王闿运的“治情”诗学本体在“为己”而“自治”的向度上是较为敞开的;可以预料的是,对于具有经世意识和现世精神的王闿运而言,这绝然不是终点,“以词掩意,托物寄兴”的背后或许潜藏的是一位末世诗人的良苦用心,“然湘绮拟古,内容亦关涉时事。”[17]王闿运复古诗学“治情”本体的建构是相当隐讳和曲折的;但是,从整体来看,它仍然没有背离其“今文学”学术研究的价值立场,如“治情”本体对“诗缘情”的复兴、对“为己”的认同与营造,以及由此而孕育的诗学经世维度等方面,均可见出其“今文学”的深刻影响和渗透。
(三)主文的诗学追求
与“今文学”微言大义的阐发模式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王闿运复古诗学意义的生发也十分注重“文”对于“义”的掩饰,以求曲折婉转地表达诗学的“为治”倾向。为此,他尤其重视诗歌的外在形式——“文”,期望由模拟古诗之“貌”来进入到古诗之“神韵”,进而完善其复古诗学本体的建构。
王闿运说,“今之诗乃兴体耳”,“兴”既是诗人外感于物的情感媒介,又是性情感发的方式特色,“盖风、雅国政,兴则己情;风、雅反复咏叹,恐意之不显,兴则无端感触,患词之不隐。”[6]2376王闿运既要强调诗学的“情”本体,又要避免“情”之于诗学的伤害而滑向世俗诗学一端,再加上他对汉魏六朝诗学的膜拜立场;为此,其选择不同于汉儒诗教内涵且于晋魏六朝已逐渐深化的“兴”为诗之体,是具有很强的针对性的。“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18]172王闿运不仅看重“起情故‘兴’体以立”[19]325的诗学法则,反对诗学长期以来的浓厚载道传统;而且力求“兴”所赋予诗学之含蓄、婉转、深远的意义生发方式。在王闿运看来,“诗有六义,其四为兴”,[14]2325若要复兴“诗缘情”的诗学本体,就必然要倚仗诗之“兴”体;然后,再由“兴”所生发的诠释模式进入诗学之“情”,实现“情生文”与“文生情”的二元对生,从而建构起既符合诗学发展规律,又合乎自身诗学价值抉择的完善体系。
王闿运诗学复古的直接对象是汉魏六朝诗歌,绮丽、典雅、深情、华声的诗歌主张与风貌,自然是其首先效仿的对象,“夫神寄于貌,遗貌何所得神?”[20]540,如何模拟古诗之“貌”就成为其复古诗学体系十分重要的维度。关于辞采之绮靡,王闿运有过正面肯定,“近代儒生深讳绮靡,乃区分奇偶,轻诋六朝。不解缘情之言,疑为淫哇之语,其原出于毛、郑,其后成于里巷。”[7]544-545“诗涉情韵议论,空妙超远,究有神而无色,必得藻采发之,乃有鲜新之光。”[21]542王闿运深知辞采之丽对于诗学“情”本体的重要性,而且躬体力行,不仅取“绮”而自命“湘绮楼”,且“湘绮自壮年喜学刘希夷体,以明艳响亮为宗”,[22]292“今所传《湘绮楼诗》,刻意之作,辞采巨丽,用意精严,真足上掩鲍谢,下揖阴何,宜其独步一时,尚友千古矣。”[23]21这些都暗示了其于模仿中求得古诗之“貌”的初衷。
与此相适应,王闿运的复古诗学也十分强调用典,作为诗歌表现形式的一个层面,王闿运所强调的用典,不是以典凑诗而使诗流于苦吟与意象经营,而是力主用典于无痕和自然。他更加反对直白浅显的俗典堆砌,所谓“一用俗典,通首减色。”[24]2105一方面,王闿在复古诗学的用典,固然是为了伸张缘情而绮靡的诗歌风貌;另一方面,用典之目的也是为了诗学“情”本体的建构,而不应该有损于“情”的本然状态及其现实显现。因此,王闿运复古诗学所强调的用典是有所选择性的,用而不乱、掩而不直、丽而不张是其主要准则,这在其大量的诗作和诗评中随处可见;如《过王家营感旧》中的“得鹿真如梦,悲麟敢问天”等。
王闿运复古诗学的主文倾向还突出体现为对格调的重视,其在诸多诗论中都透露出以格调论诗的取向,“诗主性情,必有格律。”[16]551“既不讲格调,则不必作;专讲格调,又必难作。于是人争避难,多为七绝、七律,以为易成而又易入格也。”[9]2272
王闿运诗学“尽法古人之法”,重模拟、讲工夫,其力图在“音”、“律”、“调”等方面重现汉魏六朝诗风的复古理路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王闿运复古诗学所强调的格调并不是单纯的指“音”、“律”、“调”,而且还包括词采、体式、师法、诗境等层面,其是要在得古诗之气象与格调的标准下尽诗法之能事,从而最大限度而又不失章法地突显“文”的作用和意义。
总的来看,王闿运复古诗学的主文倾向显然是与其模拟汉魏六朝诗学密切相关的;然而,主文对于其诗学体系来说还有更深层的意义,那就是他所说的“以词掩意”,“故贵以词掩意,托物起兴,使吾志曲隐而达于自然,闻者激昂而思赴。其所不及设施,而可见施行,幽窃旷朗、抗心远俗之致,亦于是达焉。”[7]544王闿运认为,诗之本体在于人之“情”的显现,而且诗与“情”相互依存和共生;好的诗歌是由诗人本然状态所孕之“情”自然生发的,即“情”的现实再现。而事实上,历来的缘情诗学似有一种以“义”取胜的误区,往往容易忽视本然状态的“情”,而热衷于“世情”和一时、一地之情。此种专注于“义”的主观抒发与暴露的诗学,显然是无法客观表征个体本质及其本然状态的,甚至会造成一种泛情、滥情的世俗诗学取向(如王闿运批陶尊谢的诗学取向),从而背离“为己”而“为治”的复古诗学主旨。因此,“以词掩意”的主文追求在避免以义曲情的基础上,不仅是对当世晚清诗坛功利主义诗风远离“诗心”与“情”的某种非难,也是王闿运表达其复古诗学之价值旨趣的内在要求,而这也足以见出其“今文学”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及其表征方式之于诗学的深刻影响,“湘绮屡言诗非小道、可以之治心约情,……‘以词掩意’之法,重在以古人之情修持自己之情,如此,方能与湘绮所谓‘《诗》通《春秋》,义取自治’之旨打通。”[25]
[1] 汪辟疆.汪辟疆说近代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2] 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M].徐志啸,导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3] 胡先.评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J].学衡, 1923(18):1-26.
[4] 王闿运.湘绮楼诗文集:论文法答张正旸问[M].长沙:岳麓书社, 1996.
[5] 王闿运.湘绮楼诗文集·说诗:卷 8[M].长沙:岳麓书社, 1996.
[6] 王闿运.湘绮楼诗文集·湘绮老人论诗册子[M].长沙:麓书社, 1996.
[7] 王闿运.湘绮楼诗文集·论诗文体式答陈复心问[M].长沙:岳麓书社, 1996.
[8] 王闿运.湘绮楼诗文集·论唐诗诸家源流答陈完夫问[M].长沙:岳麓书社, 1996.
[9] 王闿运.湘绮楼诗文集·说诗:卷 6[M].长沙:岳麓书社, 1996.
[10] 王闿运.湘绮楼诗文集·说诗:卷 3[M].长沙:岳麓书社, 1996.
[11] 王闿运.湘绮楼诗文集·论经学词章人品之异答陈齐七问[M].长沙:岳麓书社, 1996.
[12] 王闿运.湘绮楼诗文集·帆海行,送刘伯固往法琅西,因寄曾劼刚公使,以示参赞陈松生、杨商农。余初约同往扬州,适得蜀书,遂先西迈·诗:第11卷[M].长沙:岳麓书社, 1996.
[13] 王代功.湘绮府君年谱[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9.
[14] 王闿运.湘绮楼诗文集·说诗:卷 7[M].长沙:岳麓书社, 1996.
[15] 王闿运.湘绮楼诗文集·杨蓬海诗集序[M].长沙:岳麓书社, 1996.
[16] 王闿运.湘绮楼诗文集:论诗法答唐凤廷问[M].长沙:岳麓书社, 1996.
[17] 钱仲联.论近代诗四十首[J].社会科学战线, 1983(2):295-304.
[18] 钟嵘.诗品序·中国古代文论读本[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
[19] 刘勰.比兴·文心雕龙·文心雕龙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2005.
[20] 王闿运.湘绮楼诗文集·论文法答陈完夫问[M].长沙:岳麓书社, 1996.
[21] 王闿运.湘绮楼诗文集·论五言作法答陈完夫问[M].长沙:岳麓书社, 1996.
[22] 杨钧.草堂之灵[M].长沙:岳麓书社, 1985.
[23] 汪辟疆.汪辟疆说近代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24] 王闿运.湘绮楼诗文集·说诗:卷 1[M].长沙:岳麓书社, 1996.
[25] 朱洪举.王湘绮诗学思想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 2007:154-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