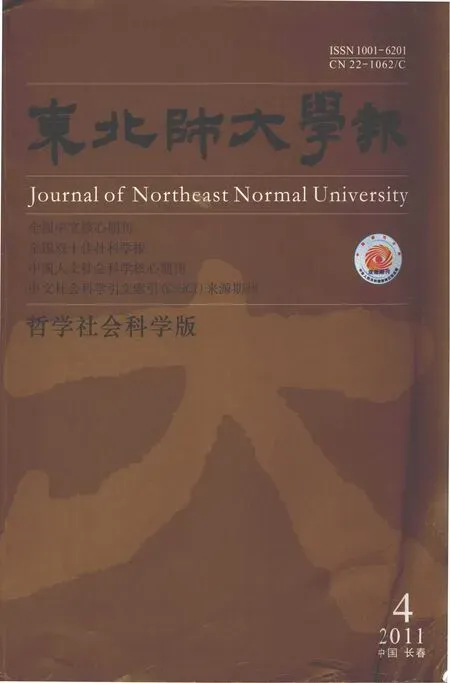现代性语境下跨文化作家超越创伤的书写
周桂君
(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吉林长春130024)
现代性语境下跨文化作家超越创伤的书写
周桂君
(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吉林长春130024)
与现代性语境相伴而来的是人的创伤感。遭受创伤,就必然要解释创伤。文学作为审美的意识形态,在解释创伤中独具优势。当今时代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个人有更多的机会生活在多元文化语境下。多元文化造就了跨文化作家,这个作家群体与现代性语境下的创伤感关系密切。跨文化作家的多元文化视角是在创伤体验中形成的,他们身上都不同程度地体现着流亡情结,这也使跨文化作家获得了世界眼光。
现代性;创伤;跨文化作家
一、现代性与文学中的创伤书写
理解现代性(modernity)要从理解现代开始。欧洲历史可分为三个阶段:古代、中世纪、现代。广义上,现代指中世纪以后,狭义上,现代指1870-1910年这段时间,甚至特指20世纪。广义上的现代经历的主要历史事件有印刷术、清教徒革命、美国独立、法国大革命、1848年的革命运动、俄国革命、两次世界大战。现代性是人们从哲学高度抽象出的现代社会的本质,从思想观念上把握到的现代社会的属性。现代性为人们带来了益处,但它也有阴暗面。社会发展带来的负面结果,如环境污染、人类精神与道德的危机等都是现代性批判的不可逃避的问题。
与现代性语境相伴而来的是人的创伤感。在现代环境下生存的人们面对的是一个飞速发展的世界,一个充满危机的世界。人们不断地遭受创伤,并在创伤中调解自己,以适应社会,获得生存的空间。遭受创伤,就必然要解释创伤。通过对创伤的反思,才能在创伤中进行自救,并在痛苦中走向成熟;创伤的文化意义在于“创伤已用来塑造个人和民族的经验……神经科学可能会终有一天能够弄清楚控制每一种创伤表现的过程,但是,即使到那个时候,我们依然需要衡量那些塑造我们的故事,因为创伤事件不是在真空里发生的。”[1]349这就是说,反思创伤不是神经科学的专利,因为创伤发生在社会中,受到各种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
文学在解释创伤中独具优势。可以说,书写创伤是文学永恒的主题,现代性又为作家提供了一个史无前例的让人们经受创伤的舞台,文学便有了更大的空间来思考和书写现代性语境下的创伤。创伤的经历引起人们痛苦的体验与情感,也引人思索。“悲怆艺术最能刺激病态情调和激情”[2]5孔子《论语·阳货》中写道:“《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可以怨”指的就是文学可以抒发痛苦的情感,表达痛苦的感受,从而成为艺术创作的源泉。
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诗学》中提出卡塔西斯说。朱光潜先生认为,卡塔西斯指的是“宣泄”,就是说,艺术能使某些过于强烈的情绪因宣泄而达到平静。罗念生先生则认为,它指的是“陶冶”,认为伦理德性要求适度,只有将过强或者过弱的情绪调解到适度,才能培养伦理品德。无论如何理解亚里士多德的卡塔西斯说,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这个学说表明文学对人类情感的平衡有重要意义。
书写创伤还能让痛苦中的人看到希望。希腊神话中有一个故事——潘多拉的盒子,讲的是主神宙斯因普罗米修斯盗了天火给人类,十分震怒,决定惩罚人类,派遣美丽女子潘多拉去完成这一使命。宙斯送给潘多拉一个盒子。当她打开盒盖时,一股黑色烟雾从盒中飞出,弥漫了天空,黑雾中是嫉妒、奸淫、偷窃、贪婪等罪恶和病痛、疯癫等灾难,它们飞落在大地上。好在盒子最底下最美好的东西“希望”还没来得及飞出盒子时,潘多拉就把它给关上了。潘多拉的盒子代表的是灾难与邪恶。更重要的是盒子底下还有希望。正因为有希望——“灾难的忠实的姊妹”(普希金:《致西伯利亚的囚徒》),人才能够经历创伤,走过痛苦,生存下去。如果说潘多拉的盒子象征的是痛苦人间的话,那么留在盒子底下的没有飞出的“希望”就是人类在世上生存下去的精神支柱,而文学就是提醒人们希望的存在。
文学书写创伤的另一个原因,是在创伤的述说中实现人的完整性。卢卡奇的艺术理论贯穿着这样一种思想:艺术品是以人为中心的,要把人提升到完全的社会人格境界,实现人性的完整。刘建军先生指出,传统主体论有关“‘人是主体’的说法是一个无法自圆其说的伪命题。因此我们要对‘人是主体’的理论进行重新阐释。我们认为,人是主体,但同时要承认,人又是‘不完整的主体’。”[3]124刘先生进一步分析指出,“从人与对象的宏观角度而言,在人类与外在世界的关系中,人类和对象世界都是不完整的主体。这是因为,人和对象之间,都是以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存在的。”[3]124
人有自然属性,也有社会属性,所以,“对象”指的主要是自然与他人。人与自然是一种互补的关系,人与人之间也是一种互补关系。刘建军先生还指出,“在人与人的内部关系中,每个个体也都是不完整的。社会是由亿万个‘不完整的个体的人’组成的,这就决定着人与人之间也是互为对象的不完整主体关系。两个或者两个以上不完整的个体的人,在一定的关系中才能形成一个特定时期的‘人的主体’。个人意义上的‘个体’,阶级或行业意义上的‘个体’都是不完整的,都是需要他者的。”[3]125
对自我利益的维护,或者说自私(这里的“自私”是哲学意义上的),是人的本性,人要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作为对象的他者也要维护自己的利益,所以人在补充自己的完整性时,必须在冲突、斗争、调解中求实现。而在这个过程中,文学会发挥它特有的作用。文学作品一旦问世,它就走入了一个与读者和世界的对话圈中。美国批评家艾布拉姆斯说过,“每一件艺术品总要涉及四个要素……第一个要素是作品,即艺术产品本身……第二个要素便是生产者,即艺术家。第三个要素……世界。最后一个要素是欣赏者,即听众、观众、读者。”[4]4文学作品面世后,在艾布姆斯所说的四大文学要素的链条上运行,它影响人们思想的活动也就开始了。这样,文学为人了解自己立了一面镜子,也为人认识世界提供了参照。了解自己,也认识他人,就有助于人与自然、与他人建立良好的关系,在互补中实现人的完整性。
自然和社会是文学产生的母体。《文心雕龙:原道篇》有言:“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锦绣山河、日月变幻,这美景似乎是大自然信笔写就的诗章,它启迪着人的心灵。社会则为文学提供了另类丰富壮丽的图景。《文心雕龙·时序》又言,“故知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文学从来不是空中楼阁,即使是最远离现实的文学也是社会意识的反映,因为逃避现实本身就是一种对待现实社会的态度。所以丹纳坚信“文学也受到时代的影响。艺术作品必然与条件完全符合,任何时期的艺术都是按照这一规律产生的。”[2]2
作品的背景是作家生活背景的一部分,研究作者生平对创作的影响是一种传统的文艺学的研究方法。虽然形形色色的文学理论让这种研究方式显得有些过时,但它是不会退出历史舞台的。方法是“主体与客体的中介,它一方面固然决定于客体,另一方面也联系着主体。”[5]29-30只研究客体,而不研究主体的对作品的研究是偏面的。雷·韦勒克对社会学文学研究颇有微词,但他也不得不承认,文学研究是脱离不了作家的社会学。
二、跨文化作家与多元文化视角
世界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全球化倾向越来越明显。随着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推进,人们生活的空间更大,选择的机会更多。人一生中可能会多次迁移,游走于各种文化之间。于是在文艺界出现了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这就是跨文化作家群体的涌现。下面我们先从文化概念入手来解释跨文化作家,并从跨文化作家的特点出发进一步探索跨文化作家与现代性语境下创伤书写的关系。
文化的概念首先是在人类学领域发展起来的。文化被看做是一个民族的属性。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国文化,美国文化,是将文化的概念建立在民族和种族的基础上。这种看似准确的分类,对具体的人而言其实是很含糊的。例如,两个作家都是美国作家,一个是犹太裔美国人,一个是华裔美国人,如果将他们都归属于美国文化,那是不准确的,将事实简化了,忽略了影响他们成长的异质文化因素。而如果按种族来划分的话,则又忽略了他们接受美国文化的事实。这就是说,文化的分类只能以其主体成分作为依据,由此,有批评家主张文化所指称的就是“主体文化”(subjective culture)
“‘主体文化’框架将个人看成文化群体得以存在的基础。每个人都将过去的经验摆到台面上。这些过去经验的基础是社会化,以及那些被重要的他者,如合作者、同龄人、社会群体和家庭成员强化了的知识。通常,这些经验或是含糊的,或是心照不宣的,它们影响着人们可能采用的观点。当这些方面的共同点出现在集体中时,我们就称之为文化。就是说,文化存在于人们的经验与期待的横切面上。”[6]13-14这也就意味着,“主体文化认为文化即是分享共同态度、价值观及行为准则。”[6]14
作为了解文化的出发点,主体文化的概念对我们来说是重要的,但是当今时代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人们有更多的机会生活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受多种文化熏染。有不同文化背景生活经历的作家就是跨文化作家。
文化与人的关系是相互的。首先,文化是由人建构的,人们创造性地建构文化。因为“文化不是一辆已经载满了一套历史和文化商品的购物车。我们这样构建文化:从过去的、现在的架子上选取物品……换言之,文化是变化的:他们被借用,混和,重新发现并重新诠释。”[7]58反过来,文化塑造人的身份,人的身份来源有很多:信仰、健康、教育、生活体验、民族、性别、家庭、性取向等等。人是在与他所从属的文化的对话中不断寻找自我,并渐渐确立起生活的位置的。跨文化作家被多元文化所塑造,同时,他们又以自己的艺术进一步塑造多元文化的时代品味。
跨文化作家是全球化时代的产物,这个作家群体由于深受多种文化的影响而表现出自己的独特之处。这些特点又与现代性语境下的创伤关系密切。
跨文化作家的多元文化视角是在创伤体验中形成的。“多元文化视角的前提是认为文化是一个集体的社会性现象,由社会成员创造商定。其核心由认知因素组成,诸如基本的信念、假设或者指导群体成员思考、感觉和行动的文化知识。身体的表现,语言的、非语言的行为和象征性的事件,处在文化最明显的层面,是文化网络的一部分。”[8]40由于多元文化视角的前提是将文化认定为“一个集体的社会性的现象,由社会成员商定”,这就意味着主体文化的消解,或者叫去中心化,向外在的世界敞开。通过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下生存,跨文化作家切身地体验异质文化。“不知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跨文化作家好就好在此身不在庐山中,因为不在,而又熟悉,所以可以做到旁观者清,准确地体验世界与人生。
多元文化视角还意味着“一种共享的文化定势可能出现。这样,个人最有可能成为多元文化的携带者,因为他们在某一时刻属于不同的文化群体。”[8]40这正是跨文化作家的情形。跨文化作家不仅仅是多元文化的携带者,更是多元文化的传播者。正像上面所说的,文学作品一旦面世,就进入了与读者和世界的对话圈中,多元文化就这样进入了流通领域。当然,这里还要避免一种误解,认为跨文化作家笔下写的就是多元文化问题。跨文化作家笔下的作品直接涉及多元文化的并不多。文学是要写人的,并不是文化的解说词。多元文化更像空气一样浸透着作家的每一个细胞,像雨露一样滋润着作家的心灵。如果把作品比作花朵的话,当读者看到那些美丽的花朵的时候,却很少有人想到那催开花朵的雨——那雨露就是文化。
多元文化视角与主体文化视角是冲突的。虽然当今世界的人们对多元文化已并不陌生,但主体文化思想仍然是占主导地位的。获得多元文化视角意味着跨文化作家是在经历创伤的过程中培养起自己认识世界的态度的。
三、跨文化作家与创伤体验
跨文化作家通常有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生活的经历,这种生活经历使他们在许多场合成了陌生人。如果他出生在异国或者在那里度过了童年,他是作为一个外来者,生活在异国的土地上,而当他回到自己的国家,在那里,他仍然感到自己是一个外来者,因为异国的生活已让他与其所属的那个国家的文化有了距离感。一般来说,跨文化作家往往具有流亡情结。“流亡的思想就是流亡的人,无家可归的人,陌生人的想法与其‘所受的教育’。这是一种因为远离‘家园’处在移位和不确定的情况下,处在一种不同的母语环境下,不同的语言传统和文化中而产生的连根拔起来的想法。流亡的思想有自我强加的作为‘陌生人’的准则。这个‘陌生人’是作为一个客居国文化的‘陌生人’或移民,并从一个外来者的视角发展起他的身份意识的。”[9]593这个流亡者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建构他的身份,而这种对自我身份的建构会对他的思想产生深刻的影响。同时,在人格形成过程中,有跨文化经历的人会更多地面对沧桑的世界,感受创伤的体验。当赛珍珠(Pearl Buck)回到美国时,虽然她的外貌证明她是这个国家的一员,但在这个国家里,她感到陌生;而作为一个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在中国她仍然是陌生者——两个国家的陌生者。
然而,流亡并不只给予跨文化作家以伤痛。“如果真正的放逐是一种永久损失的状态,它为什么这样容易就被转化成一种潜在的、甚至是日益丰富的现代文化的动机?……现代西方文化多数是放逐的、迁移的。”[9]592赛珍珠通过对中美两个国家文化的吸收、理解和传播,终于在书写中超越了文化的隔膜,将流亡中的创伤变成人生的财富。出生在非洲的莱辛(Do ris Lessing)在英国奋斗,印度的奈保尔(V.S.Naipaul)在西方世界打拼出一片天地,这些跨文化作家成功地走向世界的例子表明流亡并不是损失。这正是《孟子》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篇中所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对于作家来说,流亡则更有价值。跨文化作家有机会接触到现代性语境下的多重创伤体验,这决定了他们作品的深刻性和现代意识。
跨文化作家从另类文化的角度观察问题、思索问题。他既是某种文化的参加者,又是旁观者,而同时,他又可充当文化的中介,将各种文化在作品中融会贯通来理解世界,这样,跨文化作家的视角又具有世界性。这就是说,跨文化作家关心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式都是针对全人类的,而不是将自己局限在某一主题或者某一思想上。仅以莱辛的为例,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莱辛的《金色笔记》的主人公是一个独身女人,小说主要讲述了她的生活经历。这使得女权主义评论家们异常兴奋,称之为女权主义的宣言。富有反讽意味的是莱辛自己却拒绝加入女权主义的阵营。“但是这本小说并不是妇女解放的号角。它描写了许多女人的情感:挑衅性行为、敌对心理、不满。小说将这些情感诉诸纸面而已。”[10]9莱辛的拒绝表明她不屑于任何主义的偏激与狭隘。莱辛是一位具有极其广阔视野的作家。自1950年发表《野草在歌唱》(The Glass is Singing)以来,已写了五十多本书,体裁广泛,内容丰富,涉及殖民压迫和种族问题、共产主义思潮、两性关系、阶级关系、女性解放、世界政治、人类历史、自然灾害、战争、原子弹、人类末日、太空时代、现代人心理和神秘主义体验等等。
英国作家弗吉尼亚·沃尔夫(Virginia Woolf)曾为女性对世界体验的局限性发表过自己的看法,她说:“对于《傲慢与偏见》、《呼啸山庄》、《维莱特》和《米德尔马契》的作者来说,除了中产阶级家庭的起居室和客厅外,其他生活领域的每一扇大门都是紧闭着的。她们不可能有战争经验或者航海经验,也不可能有政界经验或者商界经验。不仅如此,就连她们的个人感情生活,还要受到法律和习俗的重重限制。”[11]51伍尔夫看到了女性小说家的症结所在,但是她自己也由于生活范围的局限,无法走入广阔的天地。“按照格式塔(gestalt)心理学的观点,人们之所以有能力由一个形象辨认出其整体,就在于人们的头脑中有对这一形象的整体的认知印象。”[12]伍尔夫没有做到的,莱辛做到了。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她不为自己的性别所限,不为主体文化所束缚,而是站在广阔的地平线上纵观古今,思考全人类的问题。莱辛所思考的问题正是现代社会及未来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她要写的是人,不只是女人,而是所有的人。她要写的是人性和人所生活的世界。如果说跨文化视角是在创伤的体验中形成的,那么,伴随而来的世界性眼光则是痛苦结出的甜蜜的果实。
[1]Farrell,Kirby.Post-traumatic Culture[M].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8.
[2]H·丹纳.艺术哲学[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
[3]刘建军.人的本质和“不完整主体”理论及其应用[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1).
[4][美]M.H.艾布拉姆斯.镜与灯[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5]陈鸣树.文艺学方法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6]Goto,Sharon G.and Chan,Darius K.-S.A re w e the same or are we different?A social-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of culture[A].Cultures:Insights from Master Teachers[C].Edited by Nakiye Avdan Boyacigiller,Richard A lan Goodman,and Margaret E.Phillips.Routledge,2003.http://www.myilibrary.com.myaccess.library.utoronto.ca/brow se/open.asp?ID=7954Crossing.
[7]Ferman,Bernardo M.Learning about our and others'selves:M ultip le identities and their sources[A].Insights from M aster Teachers[C].Edited by Nakiye Avdan Boyacigiller,Richard A lan Goodman,and Margaret E.Phillips.Routledge,2003.http://www.myilibrary.com.myaccess.library.utoronto.ca/brow se/open.asp?ID=7954Crossing Cultures.
[8]Sackmann,Sonja A.and Philips,Margaret E.One's many cultures:A multip le cultures perspective[A].Insights from M aster Teachers[C].Edited by Nakiye Avdan Boyacigiller,Richard A lan Goodman,and Margaret E.Phillips.Routledge,2003.http://www.myilibrary.com.myaccess.library.utoronto.ca/brow se/open.asp?ID=7954Crossing Cultures.
[9]Peters,M ichael A.Wittgenstein as Exile:A philosophical topography[J].Educational Philosophy and Theory,2008,40(5).
[10]Lessing,Doris.Preface.The Golden Notebook.London:M ichael,1972.
[11][英]弗吉尼亚·伍尔夫.女性与小说[A].伍尔夫读书随笔[C].上海:文汇出版社,2007.
[12]王萍,王冬梅.空灵意境的营造与动态结构的平衡——中西诗学话语中的空白观对比研究[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2):116.
Traumatic W riting of the Cross-cultural W riters under the Con text of M odern ity
ZHOU Gui-jun
(School of Fo reign Languages,No 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24,China)
What accompanies the context of modernity is traumatic experience.Trauma experienced needs an interp retation.Literature,as an aesthetic ideology p lays a key role in the interp retation of trauma.And now we live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in w hich an individual has mo re possibilities to live in a multip le cultures circumstances.M ultip le cultures cultivate cross-cultural w riters,w ho bear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ir ow n.That is,a close relation w ith trauma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ity.For one aspect,the perspective of cross-culture is formed in traumatic experience of crosscultural w riters.The complex of an exile is show n in different degrees in the cross-culturalw riters.For another,traumatic experience benefits cross-cultural w riters too.That is,these w riters see the world as an organic w hole,w hich means,w hat they aremostly concerned about is the w hole human being and their existence.
Modernity;Trauma;Cross-cultural W riters
I106.4
A
1001-6201(2011)04-00111-05
2011-05-12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09YJA 752009)
周桂君(1965-),男,辽宁北票人,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文学博士。
[责任编辑:张树武]